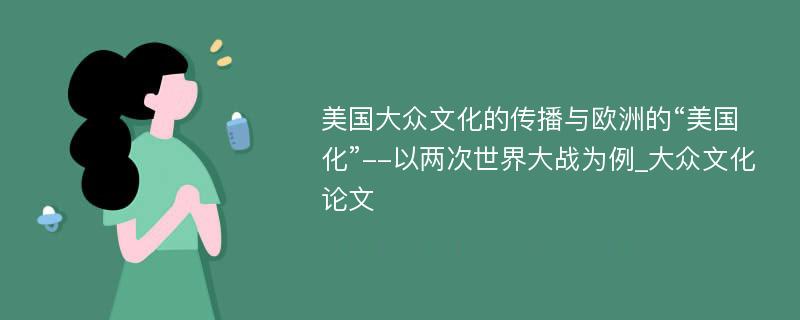
美国大众文化的传播与欧洲的“美国化”——以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国论文,两次论文,欧洲论文,大众论文,为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712.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0246(2007)01—0157—07
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经济上成为世界第一强国,美国逐步实现了向现代大众消费社会的过渡,与此同时,美国经济向外扩张的步伐日益加快,能够体现出现代大众消费社会主要特性的文化产品随即大规模地被输往国外,“美国化”的现象由此在大量消费这些产品的社会开始出现。可以说,一个国家与美国经济往来越频繁,“美国化”的程度就越高,两者是成正比例发展的。20世纪之后,与美国经济关系比较密切的欧洲国家(主要指西欧国家)最先感到“美国化”的威胁。欧洲既是美国大众文化产品制造商和销售商最为关注的庞大市场,也成为“美国化”的第一块试验场所。
一、欧洲人对“美国化”的早期描述
在国际学术发展史上,“美国化”这一术语出现较早。按照美国西北大学教授比尔·格兰瑟姆的考察,“美国化”最早出现在19世纪50年代初期的法语(s’américanizer)中。当时美国这个年轻的共和国正处于经济崛起的前期,其在北美大陆展现出生气勃勃的文化气象不仅吸引着欧洲大批的贫苦人前往寻找平等与致富的机会,而且对旧世界经院式的贵族文化产生了不小的冲击。这种冲击尽管在很大程度上是间接的,甚至是微不足道的,但已足以引起那些竭力维护本国悠久文化传统的法国上层人士的忧虑。法国著名诗人夏尔·博德莱尔认为,已经“美国化”的穷人将失去关于“物质世界和道德世界现象、自然界和超自然界现象各自特性的差异思想”。[1]58 由此可见,法国人对“美国化”的反感和抵触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不过,在前往美国的欧洲移民脑海中,美国是“普通人的乌托邦”的形象。用德裔美国学者汉纳·阿伦特的话来说,这种“大众喜爱的美国”对“富有的资产者、贵族和某类知识分子来说无疑是一个梦魇,他们意识到平等是对文化的威胁,而不是自由的希望”。[2]10 另外一种说法是,“美国化”这一术语在19世纪30年代最早出现于英国,到19世纪50年代就传遍了欧洲其他国家。这一术语起初指美国的机械发明和技术创新引起欧洲政治家和知识分子兴趣和抵制的现象。[3]7 尽管对“美国化”这一术语在欧洲学术界出现的时间和地点还存有歧义,但显而易见,这一时期欧洲人对“美国化”的忧虑主要在于美国内部发展对外部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欧洲国家的普通人成批地前往美国寻求发财致富的机会也就是这种吸引力所致。生于瑞士的美国宗教历史学家菲利普·沙夫在1856年宣称:“如果一个国家被奠定在真正的世界主义基础之上,被赋予一种无法抵制的吸引力,它就是美利坚合众国。我们的地球转动似乎不会终止人类的迁徙,直到地球的毁灭。移民们从四面八方构成一股不间断的洪流涌向我们的海岸。”[4]3 沙夫这段话没有出现“美国化”这个词语,但显然包含这方面的意思,在当时美国思想界和学术界很有代表性,这也恰恰是欧洲社会精英所最为担心的。19世纪末叶,当美国大踏步地迈向国际竞技场,尤其是美国在海外掀起大规模的经济扩张时,美国境外的许多有识之士明确提出“美国化”这一问题。1880年6月,伦敦一家名为特拉法尔加广场开业,有人就称这标志着“伦敦进入了被称为美国化的一个阶段”。[5]2 1889年7月13日,布朗热将军在伦敦的讲话中明确提出了“法国的美国化”。他这里所谓的“美国化”,主要指法国在政治体制改革上追随美国的模式。[6]2 洛根太太1889年6月在巴黎接受采访时对“欧洲变得美国化”深表遗憾。[7]14 德国财政大臣巴龙·蒂尔曼在1899年9月27日的讲话中承认,如果任何人观察一下柏林过去十几年的发展,他们一定会对普鲁士首都在工业上和商业上“美国化”感到吃惊。[8]21 这些文章多没有对“美国化”提出明确的批评,而且只是针对某一方面而言,但从字里行间也可以看出作者们对正在崛起的美国的深刻忧虑。
20世纪初,“美国化”在国际学术界已经基本包含了这一术语的现代意义。1901年,英国新闻记者威廉·斯特德出版了名为《世界的美国化》一书,表明了20世纪世界发展的主要趋势之一。美国学者佩尔斯认为这本书的主旨表达了20世纪之初主要是欧洲人对世界“美国化”的恐惧心理,他们“对文化一致性的忧虑,知识分子和艺术家标准的下降,民族语言和传统的消失,在美国习俗和心境的压力下一个国家独特的‘身份’的不复存在等等”。[9]495 其实,就斯特德个人而言,他并非是从完全消极的角度来论述世界美国化的。这本书的开首之语表明了作者的基本观点:“世界的美国化是一个相当不必要引起英国某种抱怨的术语。它甚至被视为对英国的公然冒犯,表明这个世界正在被美国化。这一进程的真正归宿是(世界)将被盎格鲁化。”[10]1 他写这本书的本意是希望唤起讲英语世界的醒悟,以美英为中心联合起来,共同对付对盎格鲁种族发展的威胁。所以他在书中使用了“重新联合(reunion)”这一术语,并在结论中提出了摆在大英帝国面前只有两种选择,一种选择是,如果英国人“决定把英帝国的存在与讲英语世界的美国结合起来,他们可以永远继续是所有世界大国中最强大的有机组成部分,保持海洋优势和陆上牢不可破,对敌人进攻的忡忡忧虑将不复存在,而且能够对这个星球的各个部分产生不可抵制的影响”。另外一种选择是“接受美国代替我们成为讲英语世界的重心,逐渐地失去我们广大的殖民地,最终衰落到一个讲英语的比利时的地位”。[10]396 作者显然是赞成第一种选择。作者没有用消极的眼光来看待世界的“美国化”,但却以醒目的书名把美国文化转变他文化的强大能力昭白于天下。这也正是以后研究世界“美国化”的学者很少不提斯特德这本书的原因所在。
在20世纪初年,美国已经成为一个世界经济大国,所以,“不管美国愿意与否,美国巨大的经济优势将直接或间接地把欧洲和世界领上政治、社会和文化生活的新道路”。[11]436 这正是欧洲国家一些精英人士的深刻忧虑之处。随着美国在世界政治舞台上的崛起,美国大众文化也借着美国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强大力量向全球蔓延,而且势头难以遏制。在此进程中,“美国化”不仅成为学者们非常熟悉的一个术语,而且是欧洲国家所面对的一个严峻现实,欧洲也由此成为“美国化”的最早试验场所。
二、欧洲国家的“美国化”问题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欧洲一些具有忧患意识的人士尽管已经提出了“美国化”的问题,但往往是对一种发展趋势的忧虑或预测,一般人并没有强烈地感受到自己的文化受到来自美国的一种新生活方式的冲击,欧洲国家也没有把美国大众文化的传播视为大不了的事情。一战之后,这种状态完全改观。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在英国、法国、意大利、荷兰和德国(1933年前)放映的电影中,60%到95%是美国拍摄的。美国的爵士乐和文学作品在欧洲变得相当普遍。[12]58 欧洲国家采取了一些措施试图限制这股“洪水”的进入,但最终收效甚微,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形成了欧洲历史上“美国化”的第一次高潮。下面以德国和法国为例来说明这一令欧洲精英十分担忧的现象。
美国大众文化对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德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德国人对“文化”的理解和美国人很不相同,这与德国的文化传统有很大的关系。德国人善于抽象思维,习惯于从深奥的层次对人类面对的问题以及终极目标进行阐述与理解,这种文化毫无例外地由精英所创造和享有。从理论上讲,这样一种崇尚“高雅文化”的氛围很难提供给“大众文化”传播的空间。然而,事实恰恰相反,美国生活方式一战之后在德国迅速传播开来。德国人开始着迷于爵士音乐,到处放着美国流行歌手路易斯·阿姆斯特朗和比利·霍利戴的歌曲。好莱坞影片深受民众欢迎。正如托马斯·桑德斯的研究表明的那样,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电影公司常常采用美国的商业惯例,寻求美国的投资,吸收美国的审美和技术形式以打败国内外竞争者。[13] 出生于俄国的德国艺术家塞尔日·佳吉列夫1926年强调说,美国的“影响已经随处可以感觉到——在绘画、戏剧以及音乐方面……作曲家学会了爵士乐的风格,美国甚至在古老保守的芭蕾惯例上也说了算”。[14]269 作为一个芭蕾剧团的经理,佳吉列夫目睹了德国音乐所谓“美国化”的过程,他这番话尽管只是涉及自己熟悉的专业领域,但却是美国大众文化在魏玛共和国时期对德国社会发生影响的真实写照。实际上,作为战败国,德国尽管在战胜国的面前受尽屈辱,但也与其他欧洲国家一样大踏步地迈向现代消费社会,已经走在前面的美国自然成为德国人效仿的“榜样”。因此,在许多德国人看来,美国成为他们的国家走出面临之困境的希望。
法国在20世纪初就对“美国化”深感忧虑,如1911年8月26日,一个自称为“法国语言之友”的协会在巴黎组织活动,抗议法语和法国习俗的“美国化”,主张把那些来自美国的“粗俗”词汇从法语中彻底剔除出去,以保持法语的纯洁性。[15]C3 法国人对美国大众文化尽管一直颇有微词,社会精英从未放弃抵制来自大洋彼岸的文化入侵,但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法国的“美国化”程度丝毫不亚于德国。1929年,艾尔弗雷德·布雷斯主编的一本书中收录了萨斯曼写的一篇文章,记录了巴黎当时的“美国化”现象。作者描述说,在法国首都,一个人能出生于美国医院,在美国人开办的学校上学,去美国教堂做礼拜,隶属于美国军团、基督教青年会、康奈尔、哈佛或美国妇女俱乐部;在偏爱的咖啡馆或美国图书馆阅读在巴黎的美国人办的三家报纸之一;在许多美国式的小酒吧品尝着威士忌,喝着由美国牛奶工送来的牛奶,吃着当地美国人生产的甜玉米和冰激凌;去观看曲棍球比赛、拳击赛以及其他进口的运动项目;得到美国牙医和医生的关照,最后被一个美国殡仪员所安葬。[16]163—167 萨斯曼把生活在外国城市的一个人从生到死的经历与美国国内并无多大差别,他的描述也许有些夸张,但也足以表明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生活方式在法国已经得到广泛的传播,对人们的日常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这一时期法国人看来,“美国化”与现代性密切联系在一起,美国“意味着现代性、权力和繁荣”。[17]491 德法两国所面对所谓“美国化”现象也程度不同地存在于其他欧洲国家。
在这一时期,好莱坞在大众文化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当时去美国的法国观光者把美国描述为城市化和机器化的社会,这个社会的主要文化吸引力便是好莱坞。在他们看来,“好莱坞似乎是美国文化精髓的展现”。[18]10—11 好莱坞能够长期在欧洲国家电影市场占据主导地位,首先在于对多数人具有吸引力。以后成为法国研究美国文学权威的罗歌·阿瑟利诺教授回忆说:“我尽可能多地观看美国电影,其中很多影片是30年代中后期在巴黎看的:告密者、鸭羹(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到美国俏皮话)、摩登时代、富贵浮云(我看了多次)、死角、浮生若梦以及白雪公主等。”[19]70 阿瑟利诺这番话其实是对当时成千上百万欧洲人对美国电影钟情的真实描绘。当然,人们喜欢观看好莱坞影片并不必然意味着对影片中表现出的生活方式的模仿,但的确有相当多的人是这样做的,他们竭力在自己能力所及范围内模仿好莱坞影片中男女主角的举止言谈和衣食住行。在这方面,欧洲年轻人显然走在了前面。1925年1月,《纽约时报》刊文认为,欧洲更年轻一代的“美国化”正在飞快地进行。[20]15 这一时期被炒得沸沸扬扬的“美国化”主要是指好莱坞对欧洲社会产生的强大冲击力。面对好莱坞的冲击,欧洲政治和文化精英不只是担心本国电影市场沦入美国之手,主要忧虑好莱坞威胁了国家的认同和欧洲各国的生活方式。《纽约晨邮报》1923年刊登的一篇文章警告说:“电影对美国犹如旗舰曾经对英国一样。如果不受到及时遏制的话,靠着这种手段,山姆大叔也许希望某一天使世界美国化。”[21]11 这种观点在欧洲社会精英中很有代表性,多少有点“危言耸听”的味道。
欧洲的“美国化”归根结底是以美国大众文化为媒介的“美国生活方式”向境外的大规模蔓延,这对于固守传统的欧洲社会来说也许是“不祥之兆”,但却是难以抵制的。美国学者埃德加·莫勒1928年出版了名为《这个美国的世界》一书,莫勒本人也许对美国生活方式体现出的主要特征持批评态度,但却明确承认这种生活方式代表了现代社会的发展方向。用他的话来说,“美国显然是一个受到多数人支配、缺乏教养、无审美情趣的功利主义社会。欧洲正朝着相同的目的走去,尽管比较缓慢,还戴上一幅正人君子的面具”。[22]126 所以他在这本书中专章论述了欧洲社会在经济、娱乐、习俗、消费、金融等各个方面已经变得“美国化”。很有意思的是,莫勒对美国大众文化似乎有“不屑为伍”的口气,但对美国在进入20世纪之后对欧洲乃至对世界会产生强大影响却充满信心。他在最后一章谈到“美国的未来”时将“欧洲的美国化”与“两千年前左右的地中海世界的罗马化”进行了比较,认为欧洲“美国化”只是一种表面的现象,历史已证明“希腊从未变成罗马”,所以,“欧洲将不会从根本上被美国化”。[22]23—26 莫勒的这种观点也许主要针对欧洲精英人士对欧洲“美国化”的担忧,继而会采取一些不利于美国经济扩张的措施。说到底,莫勒还是从维护美国根本利益这个角度来论述这一在当时已被许多欧洲人炒得沸沸扬扬的问题。
法国社会学家安德烈·西格弗里德认为,标准化和大规模生产的到来、几乎不可思议的战时繁荣以及20年代经济的急剧扩张构成了“美国化”的成熟阶段。在他看来,不管是工作方法,还是日常生活本身,没有什么能够避免这种以现代性为主要特征的生活方式的巨大冲击。美国化已经“转变了一切”。[2]71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教授维多利亚·德格拉西亚指出,大致从1890年到20世纪40年代,“美国化”涉及到这一时期美国历史上出现的大众消费社会作为一种模式在国外的互换及其构建。[24]193—194 德格拉西亚划分的时间段正是其他工业国家向消费社会的过渡时期,美国生活方式的影响自然就比较显而易见。一些欧洲精英曾对美国方式提出质疑,但更多的人还是希望从美国的发展过程中寻求欧洲未来的答案。不管是采取消极抵制,还是抱着积极的态度,都反映了美国现代生活方式对欧洲社会的影响。
三、欧洲精英对“美国化”的抨击
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欧洲知识精英就发出了抵制美国大众文化传播的呼声,试图维护欧洲传统文化的“纯洁性”。如德国具有见识的记者罗伯特·穆勒大声疾呼整个德国与其他欧洲联合起来共同抵制美国的生活方式,以把欧洲文化从日常生活事务受美国文化的影响中拯救出来。[25]25 战争结束后,美国大众文化在欧洲的传播形成了高潮,致使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许多欧洲知识精英以不同的文笔形式消极地描述了以“现代性”为主要特征的美国文化,尤其对欧洲生活方式产生强大冲击的好莱坞进行诋毁性的攻击,试图在民众中形成“恐惧”之感,自觉地构筑起抵制美国大众文化的意识。
1922年,英国学者科利尔出版了一本题目为《美国方式:一种世界性威胁》的书,作者认为,美国生活方式首先“使人类标准化”,其次是“它的标准明显低于世界其他地区受过教育的普通人所达到的水平”。作者最后提出了“如何抵制美国生活方式的冲击”这一问题。[26]4—5,158—163 这本书篇幅不长,充其量只能算是个小册子,作者也带有明显赞成社会主义的倾向,但却从一个方面反映了当时欧洲激进人士对“美国化”的担忧。法国学者乔治·迪阿梅尔在他写的一本书中为欧洲人描绘出美国社会在机器的操纵之下人们变成“幸福”动物的场景。他断言,受美国电影影响的任何人实际正走在堕落的路上。在他的笔下,美国文化是低级趣味的幻想,“给欧洲观光者留下的印象是,人类生活逐渐接近我们所知道的昆虫的生活方式”。[18]12 迪阿梅尔以犀利的文笔为欧洲人提供了美国将对世界构成威胁的毛骨悚然的可怕图景。
马尼克斯·海芩是比利时很有名气的诗人和小说家,1927年出版了名为《发现美国》的观光游记。他在这本对美国的观感集的序言中写道,“美国电影对我们的思想和行为产生了影响:通过系统地对任何有问题的事情视而不见,美国电影造成了一种理性冷漠的氛围,它是毁灭我们稳定大众生活的一个因素”。[27]24 门诺·布拉克是当时荷兰一位很有名的年轻学者,他在1928年发表了一篇论文,题目为“我什么拒绝‘美国’”。布拉克在这篇文章中对“美国”这个在欧洲人脑海中的概念进行了阐释,明确提出了欧洲主义所包含的内容。在他看来,欧洲主义实质上是欧洲求生存的反应,旨在抵制美国生活方式对欧洲社会的冲击。[28]37—48 对欧洲主义的张扬构成了这篇文章的重要内容之一。一位英国评论家1932年写道:“他们的确没有认识到,美国电影导演和公司这种活灵活现地集中于他们大城市的堕落的污点……正在逐渐地破坏世界对美国公民身份、美国方式和道义的尊重,给世界带来这种疑虑,即美国整个国家是有大量的堕落者或白痴所构成,比无用的低能儿和神志不清者更糟。”[29]85—86 这种观点为很多欧洲学者所持有,旨在告诫人们好莱坞影片中所描绘的情节是现代社会的“弊端”,只会导致人们沉迷于物质享受的“堕落”。因此,好莱坞中宣扬的价值观显然与欧洲文化格格不入。西班牙周刊《命运》1939年9月刊文指出,西班牙的价值观和美国的价值观迎面发生冲突,美国制造的“每件东西都是对我们的攻击——不管是富人还是穷人……美国一直不公开宣传一种国家和宗教理想。在欧洲部分年轻人中间,存在一种对美国生活方式和电影的危险热情……这种热情总是伴随着对我们自己身上体现出的最深刻和最真实的东西的轻蔑……模仿是趋向祖国解体的第一步”。[30]104—105
上述这些观点多少有点“危言耸听”的味道,未必会有效地阻止美国大众文化在欧洲社会的传播,也很难促进在民众中形成自觉的抵制意识,但的确反映了欧洲知识精英的“忧虑”情感,同时也是欧洲文化中对美国的“偏见”在新时期的体现。按照他们的观点,美国人也许是富裕强大,但他们注定受像亨利·福特那样的商人所支配,这些商人把他们的国人训练成为大众生产者和消费者,形成了一个由舒适的循规蹈矩者和文化庸人构成的社会”[18]2。
四、如何认识这一时期欧洲的“美国化”
对美国大众文化的传播,欧洲人具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对普通人来说,美国文化产品丰富了他们生活的选择,给他们的闲暇时间带来愉悦的享受。他们完全是从实用的角度来消费美国文化产品的,并非必然意识到这种消费会导致维系国家认同的传统文化受到威胁,甚至逐渐解体。因此,他们对美国大众文化的传播很少有激烈的抵触情绪,除非这种文化与他们的直接经济利益发生冲突。这恰恰是美国大众文化能够迅速在欧洲“蔓延”开来的一个重要外部因素,也是享有文化特权者的最大的担忧。所以,“美国化的主要恐怖之一是,欧洲绝大多数大众热情地接受它,它或多或少地反映了他们想要的东西。一些对美国化感到悲哀者也承认,他们深恶痛绝的这种转变是内部力量而不是外部力量的产物”。[31]82—83 当然,对欧洲精英们来说,他们未必不喜欢美国的文化产品,但打心底里不愿意这些产品中体现的文化内涵在社会上传播,以便由此威胁了他们享有的文化特权,进而使维系一个民族内聚力的国家认同不复存在,最终使社会各阶层都认可的社会等级次序出现“无序”状态。[32]136—137
所以,在这些精英的眼中,美国大众文化可谓“洪水猛兽”,不仅与他们所享受的高雅文化难以两容,而且最可怕的是瓦解了现行统治的文化合法性基础。因此,“许多欧洲知识分子把美国生活方式解释为对他们享有西方文明特权地位的挑战”。[32]39—40 许多学者对这一时期欧洲“美国化”的研究都涉及到欧洲精英对文化的“合法统治权”的问题。实际上,这种权力本身就是一种普通阶层很难得到的资源,可以通过上升到国家层面上政策的制订与执行使精英们把这种资源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反过来奠定他们享有控制国家政策制订和操作社会正常运行的合法性的基础。因此,随着美国大众文化的传播,原先他们独占的文化资源开始呈分散化的态势,过去一直被排斥在高雅文化活动之外的普通民众开始具有了分享文化资源的意识,继而要求参与国家政治和经济资源分配的过程,并对精英们享有的文化控制权的“合法性”提出挑战与质疑。对他们来说,这样一种状况多少有点“是可忍,孰不可忍”的味道,他们把导致这种结果出现的“罪魁祸首”归于美国大众文化的传播对国家传统认同的瓦解。这样,他们必然要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资源试图限制或遏止住美国大众文化的蔓延之势。不管是通过文人笔下的“恐怖”描写或理论阐释,还是通过国家相关政策的制订与执行,从维护一个民族文化内聚力的角度讲,对美国大众文化传播的抵制具有时代的合理性,但这种传播毕竟不是类似军队入侵的有形行为,后者可以激发起全民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而前者恰恰相反,它是在民众对美国文化产品的消费过程中完成的。美国文化产品从表面上看与其他商品无多大差别,并不具有像外国人手持枪炮在异国土地上横行无忌的赤裸裸入侵的特征,它们对人们思想观念的影响不是靠着枪炮的威逼或压力,而是在获得身心满足的愉悦体验中实现的。这是一种潜移默化地改变传统生活方式的过程,消费这些产品的个体很难觉察到自身的变化。欧洲精英们尽管意识到所谓“美国化”的严重性,他们也试图通过各种方式阻止这种趋势的发展,但很难形成全民抵制的运动。
“美国化”固然与美国的经济强大有很大的关系,但却反映了这种文化至少在当时代表了现代社会发展的方向。美国学者艾伦·富洛研究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法国向现代消费社会过渡时商店营销方式受美国经营理念的影响而得出的结论之一是:“美国化进程的传递力似乎不会毁灭国家的认同,反而会促进或重构现存的文化和经济特征。”[17]510 这一结论尽管只是针对法国某一领域而言的,但对认识这一时期欧洲“美国化”的实质深有启迪。
标签:大众文化论文; 法国经济论文; 精英文化论文; 精英主义论文; 美国社会论文; 法国文化论文; 精英阶层论文; 经济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