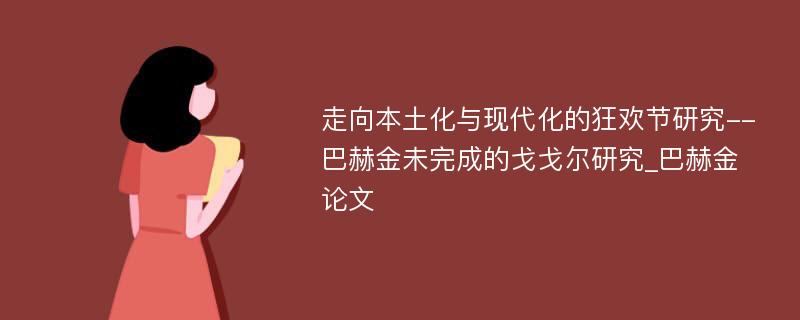
走向本土化和现代化的狂欢化研究——巴赫金未完成的果戈理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巴赫论文,本土化论文,未完成论文,走向论文,果戈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巴赫金的研究中,现在所能找到的直接与果戈理相关的研究文章有:《拉伯雷与果戈理——论语言艺术与民间的笑文化》、《讽刺》、《果戈理之笑的历史传统和民间渊源问题》等。从这些文章中我们不仅可以发现巴赫金的果戈理研究的基本思路和概貌,而且可以发现,巴赫金通过对果戈理的研究,深化了他对狂欢化问题的思考。这种深化性体现在巴赫金将狂欢化问题本土化和现代化了。
在《费朗索瓦·拉伯雷的创作与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民间文化》中,巴赫金开宗明义指出:要解开拉伯雷为世界文学留下的谜团,“只能通过深入研究拉伯雷的民间源头。”“拉伯雷就是民间诙谐文化在文学领域里最伟大的表达者。”(注:《弗朗索瓦·拉伯雷的创作与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民间文化》,《巴赫金全集·拉伯雷研究》,河北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3-4页。)为此,巴赫金深入到中世纪的民间诙谐文化、狂欢节文化之中进行了考察,著名的狂欢化理论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得以展开的。那么,巴赫金的果戈理研究呢?在《拉伯雷与果戈理——论语言艺术与民间的笑文化》一文中,巴赫金写道:“这里我们要讨论的是现代笑文学史中最重要的一个现象——果戈理的创作。我们关注的,只是作品中民间笑文化的因素。”(注:《拉伯雷与果戈理——论语言艺术与民间的笑文化》,《巴赫金全集·文本对话与人文》,河北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7-18页。)很显然,这一思路是与拉伯雷研究一脉相承的,但是巴赫金并没有简单将果戈理研究作为拉伯雷研究的另一个例证,而是进一步提出了新的课题:“我们不拟涉及拉伯雷对果戈理的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通过斯特恩和法国自然主义派)的问题。对我们来说这里重要的是果戈理作品的这样一些特点,它们同拉伯雷无关,而是来源于同家乡土壤上民间节庆形式的关系。”(注:《拉伯雷与果戈理——论语言艺术与民间的笑文化》,《巴赫金全集·文本对话与人文》,河北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7-18页。)这种对“来源于家乡土壤上民间节庆形式的关系”的研究正是巴赫金将狂欢化研究本土化的重要步骤。
首先,巴赫金指出乌克兰民间节庆生活和集市生活构成了果戈理小说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在他看来,“《狄康卡近郊夜话》中的多数故事,都是用果戈理十分熟悉的乌克兰民间节庆生活和集市生活组织起来的……节日本身的题材、悠闲快乐的节庆气氛,决定了这些故事的情节、形象和语调。”(注:《拉伯雷与果戈理——论语言艺术与民间的笑文化》,《巴赫金全集·文本对话与人文》,河北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7-18页。)在《夜话》中,各种与节日相关的迷信、特殊的自在快乐的气氛使得生活脱离了常轨,特别是其中的鬼怪的嬉戏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巴赫金认为,这些鬼事的性质、情调和功能与中世纪的狂欢节中的地狱形象有着深刻的相似性,更不用说《夜话》中所描写的吃喝和性生活场面所体现出的节庆的、谢肉节狂欢的性质了。巴赫金通过对乌克兰民间文化的发掘为果戈理研究建立了一个蕴含丰富的文化宝藏,使果戈理小说的狂欢化问题从一开始就奠基于本土化的民间文化语境之中。
其次,在巴赫金看来,乌克兰的民间笑文化不仅构成了果戈理小说的外观,更重要的是在结构和风格上也有着强烈的渗透。巴赫金发现,狂欢化最重要的特点怪诞现实主义传统在乌克兰十分强大而且极富生命力。这一传统的发源地就是乌克兰的宗教学校和神学院,在那里,漫游的学生和低级的僧侣在整个乌克兰境内传播着引人入胜的口头文学,如滑稽故事、笑话、幽默小品、讽拟语法等。同时,乌克兰平民知识分子的餐桌谈话的传统也相当强大,这些都不能不影响到果戈理。正因为如此,巴赫金指出,“在果戈理的彼得堡小说和整个后来的创作中,我们还可找到民间笑文化的其他因素,而且首先见于风格本身。”(注:《拉伯雷与果戈理——论语言艺术与民间的笑文化》,《巴赫金全集·文本对话与人文》,河北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7-18页。)
最后,巴赫金指出,“这些作品中的果戈理之笑,是纯粹的民间节庆之笑。……果戈理之笑的这一民间基础,尽管后来发生了重要的演变,却一直保持到最后。”(注:《拉伯雷与果戈理——论语言艺术与民间的笑文化》,《巴赫金全集·文本对话与人文》,河北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7-18页。)果戈理小说早期的幽默风格和后期的讽刺特色历来是人们研究的重要内容。巴赫金同样将研究的重心放到了对果戈理之笑的研究上,不过,他的思路是研究果戈理之笑的民间性,特别是这种本土化了的民间性。在他看来,“果戈理的笑谑问题,只有在研究民间笑文化的基础上才能正确地提出和解决。”(注:《拉伯雷与果戈理——论语言艺术与民间的笑文化》,《巴赫金全集·文本对话与人文》,河北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7-18页。)巴赫金将果戈理研究置于历史的维度进行考察,指出,“植根于民族民间笑谑的真正博大的俄罗斯讽刺,只是到了果戈理创作中才出现。”(注:《讽刺》,《巴赫金全集·文本对话与人文》,河北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45页。)在此之前,俄罗斯的民族风格尚处在萌芽状态。无论是罗马讽刺、梅尼普讽刺还是中世纪的讽刺都是成长于欧洲地方性的民间文化之中,直到文艺复兴时期才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时期。而到了果戈理时代,俄罗斯的民间文化已自成一体,从而为果戈理小说奠定了坚实的民间文化基石,乌克兰的民间节庆笑谑、民间讽刺喜剧的形式都成为果戈理讽刺作品的直接的渊源。进而巴赫金发现,“在果戈理的创作中,我们几乎可以找到民间节庆文化的所有因素。”(注:《拉伯雷与果戈理——论语言艺术与民间的笑文化》,《巴赫金全集·文本对话与人文》,河北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7-18页。)而且它们都是植根于俄罗斯民间文化土壤之上的,绝非一般性地采用民间性的概念所能够涵盖的。
在狂欢化问题上,巴赫金的果戈理研究明显地向前迈进了一大步,这就是挖掘出了果戈理世界的现代性因素。在果戈理研究中,巴赫金一方面延续了在拉伯雷研究中所阐发的狂欢化理论的基本观念,另一方面则通过对果戈理个案的研究将狂欢化理论现代化,而后者正是巴赫金果戈理研究的另一重要特色。
果戈理的笑与拉伯雷的诙谐有着明显的相似性,这种相似性从两人作品的外观及其精神实质上都可看出来。在巴赫金的果戈理研究中,探讨果戈理与拉伯雷的传承性是其重要的部分。其一,巴赫金发现了果戈理小说与拉伯雷小说在狂欢式的情节结构上的相似性。比如说,“《夜话》的前言(特别是第一部的前言),在结构和风格上很接近拉伯雷的前言。”(注:《拉伯雷与果戈理——论语言艺术与民间的笑文化》,《巴赫金全集·文本对话与人文》,河北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7-18页。)再比如,“《死魂灵》所依赖的基础,是欢快地(狂欢般地)游历地狱、漫游死亡国度的形式。《死魂灵》非常像拉伯雷小说的第四卷,即庞大固埃的旅行。……《死魂灵》的世界,是欢快的地狱世界。这个世界从外表看更像凯维多的地狱,但就内在本质来说却接受拉伯雷第四卷的世界。”(注:《拉伯雷与果戈理——论语言艺术与民间的笑文化》,《巴赫金全集·文本对话与人文》,河北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7-18页。)等;其二,巴赫金清理了从拉伯雷到果戈理之间的文化和文学的传承关系,这主要是指果戈理小说与欧洲传统的渊源。巴赫金发现,“果戈理又与欧洲讽刺的优秀传统相联接(与拉伯雷一脉相承)。在果戈理作品中,我们可以找到怪诞的讽刺(夸张的肯定与否定),傻瓜与骗子讽刺的因素,贪食讽刺的因素,幽默对话等等。”(注:《讽刺》,《巴赫金全集·文本对话与人文》,河北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45页。)其三,从这些文化渊源的分析中,巴赫金展开了对果戈理作品狂欢化的研究,指出果戈理的笑的狂欢性。这种狂欢性与拉伯雷小说中的狂欢性在精神实质上具有一致性,如正反同体性、自由解放性、积极崇高性等。在他看来,“果戈理在民间的笑文化土壤上培育起来的‘积极的’、‘美好的’、‘崇高的’笑,没能得到人们的理解(直到今天在许多方面仍然如此)。”(注:《拉伯雷与果戈理——论语言艺术与民间的笑文化》,《巴赫金全集·文本对话与人文》,河北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7-18页。)“果戈理的怪诞不是简单地突破规范,而是否定任何企图变得绝对永恒的那些抽象的僵化的规范。这种怪诞要否定‘不言而喻’之事的显而易见性,要否定‘不言而喻’的世界;它要表现真下的意外性和不可预料。它似乎在说:期待善行,不应求之于固定而习惯之东西,应该求之于‘奇迹’。这种怪诞蕴涵着人民的更新和向上的思想。”(注:《拉伯雷与果戈理——论语言艺术与民间的笑文化》,《巴赫金全集·文本对话与人文》,河北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7-18页。)正是这种精神的一致性,使得果戈理研究成为巴赫金狂欢化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是,巴赫金的果戈理研究并非拉伯雷研究的简单重复,也非为狂欢理论找到了另一个例证,巴赫金的果戈理研究有力地推动了狂欢化理论的现代化进程。这主要表现在:首先,巴赫金发现了果戈理狂欢化的世界感受的浪漫主义色彩,这种世界感受在他的作品中得到了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如果戈理小说中对荒诞的躯体观的表现、一贯始终地把人名改造成绰号的方式等,在果戈理小说中俯拾皆是。其次,果戈理作品中的讽刺是对当代现实的否定,这是其狂欢化现代性的重要表现。果戈理笔下的农奴制度的荒谬与可笑、小公务员生活中的种种艰辛与痛苦都具有强烈的针对性,其结果,就使得果戈理小说“对当代现实的形象性否定,达到了十分深刻和有力的程度。这种否定不仅指向封建农奴制度,而且还针对新兴的资本主义。”(注:《讽刺》,《巴赫金全集·文本对话与人文》,河北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45页。)这无疑是果戈理作品所具有的现实意义。最后,巴赫金发现了果戈理世界的交往性特征,正是这一特征,使果戈理作品中的狂欢化具备了现代性。
在他看来,“果戈理在作品中组织笑的语言,目的不在于简单地指称个别的消极现象,而在于揭示世界这一整体的一个特殊的方面。从这个意义上说,笑的领域在果戈理作品中成为交往的领域。”(注:《拉伯雷与果戈理——论语言艺术与民间的笑文化》,《巴赫金全集·文本对话与人文》,河北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7-18页。)在这个交往世界中,我们看到了两个相互冲突和相互作用的世界:“一个世界是相当合法的,官方的,用官衔和制服组织起来的,表现为对‘都城生活’的想往。另一个世界则是一切都极为可笑而又极不严肃,这里唯有笑是严肃的。”(注:《拉伯雷与果戈理——论语言艺术与民间的笑文化》,《巴赫金全集·文本对话与人文》,河北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7-18页。)而且,这种交往性是永无止境的、开放式的,“这个笑的世界总是为新的相互作用敞开着大门。……因此,果戈理世界的整体性,从根本上说就不是封闭的,不是自我满足的整体性。”(注:《拉伯雷与果戈理——论语言艺术与民间的笑文化》,《巴赫金全集·文本对话与人文》,河北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7-18页。)在巴赫金看来,这是最为重要的一点。正因为如此,“果戈理的世界,因此是永远处于交往领域的世界。在这个领域里,所有的东西又变得具体可感,……一切全成了真实的、现代的、实际存在的东西。”(注:《拉伯雷与果戈理——论语言艺术与民间的笑文化》,《巴赫金全集·文本对话与人文》,河北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7-18页。)果戈理作品狂欢化的现代性也由此而显得异常突出的。
值得一提的是,在巴赫金的狂欢化研究中,陀斯妥耶夫斯基的狂欢化问题与果戈理的狂欢化问题还不太一样,巴赫金的陀氏狂欢化问题的研究由于其论题的自我限制(即从一开始就将陀氏的狂欢化问题的研究限定在了诗学范围之内:“本书论述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诗学问题,因之对他的创作,仅仅是从这个角度加以考察”,(注:《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巴赫金全集·诗学与访谈》,河北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4页。)因而,在巴赫金的陀氏狂欢化问题上,远远没有在果戈理研究中放得开,其现代性形象也显得相对模糊一些。这也从另一方面确证了果戈理研究在巴赫金的狂欢化研究中的重要性和独特性。尽管如此,巴赫金的果戈理研究并没有像对陀氏的复调小说研究和拉伯雷的狂欢化研究一样深入、细致和丰满。相比之下,巴赫金的果戈理研究还处在一种未完成的状态之中。巴赫金唯一一篇相对完整的果戈理研究是《拉伯雷与果戈理——论语言艺术与民间的笑文化》,而《果戈理之笑的历史传统和民间渊源问题》本来是巴赫金的独立的果戈理研究,却又只留下了一个提纲和基本的思路,这不能不说是巴赫金留给后人的永远的遗憾。
在这永远的遗憾中,巴赫金为后世的果戈理研究,特别是对果戈理笑与讽刺问题的研究留下了巨大的研究空间。比如说,巴赫金指出,果戈理之笑的特点“这不是狭窄的讽刺之笑。别林斯基和六十年代名家想把他仅看作是一个纯粹的(狭窄的)讽刺家。”(注:《果戈理之笑的历史传统和民间渊源问题》,《巴赫金全集·文本对话与人文》,河北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54页。)这实际上是迈出了走出别车杜的重要一步。众所周知,在果戈理研究中,社会历史学批评是影响深远的角度,普希金对他的“含泪的笑”的判断、别林斯基“以愚蠢开始,接着是愚蠢,最后以眼泪收场”的“生活的可笑的喜剧”的概括、(注:[俄]别林斯基:《别林斯基选集》第1卷,译文出版社1980年版,第183页。)鲁迅的“无事的悲剧”的分析等直到现在还深刻地影响着我们对果戈理的评价,而巴赫金早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就指出了这种研究的时代局限性。在他看来,果戈理的讽刺不是狭窄的讽刺,即不是一种简单的否定性的讽刺,而是包含了肯定的、高尚的、积极内容的讽刺,是一种崇高的讽刺。“正是这个‘低下’、粗俗、民间的性质,据果戈理看来使这种笑谑具有了‘高尚的面孔’。他还可以补充一句:这是神圣的面孔,因为在古代民间喜剧的民众笑谑中天神们就是这么笑的。对于当时已有的和可能的种种解释来说,这种笑(即把笑的事实视为一个剧中人物)是无法说明的。”“果戈理感觉到自己的笑谑是对世界的一种直观认识,具有普遍性,可同时在十九世纪‘严肃’文化的条件下又不能为这种笑谑找到应有的一席之地,也得不到理论上的论证和阐释。”(注:《拉伯雷与果戈理——论语言艺术与民间的笑文化》,《巴赫金全集·文本对话与人文》,河北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7-18页。)
这种时代局限性不仅仅是别林斯基们所具有的,即使是果戈理自己也未必有清醒的认识。在巴赫金看来,“他(指果戈理)比讽刺作家要广要博,但自己搞胡涂了。”(注:《果戈理之笑的历史传统和民间渊源问题》,《巴赫金全集·文本对话与人文》,河北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54页。)“当他发表议论解释自己为什么笑的时候,他显然不敢彻底揭示这笑的本质,它的普遍而广泛的民间性。他时常用那个时代的狭隘道德来为自己的笑辩解。他的辩解要迁就读者对象的理解水平,所以便不由自主地降低了、局限了他那笑谑作品进发出来的巨大的改造力,有时是真诚地想把它范畴在官方的框架之内。”(注:《拉伯雷与果戈理——论语言艺术与民间的笑文化》,《巴赫金全集·文本对话与人文》,河北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7-18页。)
但是狂欢化是民间的、非官方的,当果戈理自觉不自觉地将自己限定在官方的框架之内时,其实也是把自己讽刺的力量削弱了。巴赫金没有避尊者讳,而是深刻地指出了果戈理创作所存在的不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