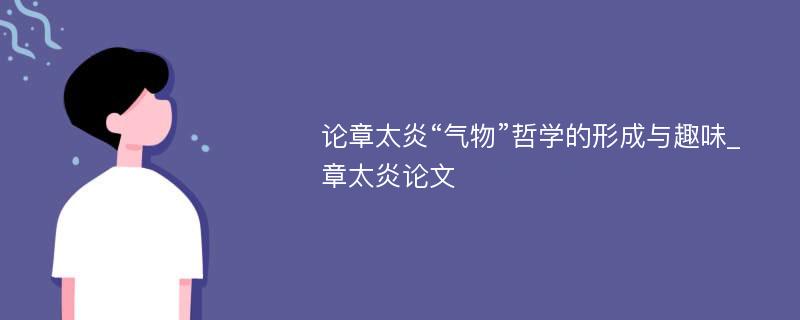
“操齐物以解纷,明天倪以为量”——论章太炎“齐物”哲学的形成及其意趣,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章太炎论文,意趣论文,哲学论文,明天论文,操齐物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竹内好在他的名著《鲁迅》里提出一种理解鲁迅的方法——实质上也是一种诠释思想人物的基本方法——亦即不是后设性地通过鲁迅有形的思想表达来追溯地解释他的思想形成,而是能够深入于鲁迅将形未形的思想展开过程,去探究那种促使鲁迅成为鲁迅的思想原理的形成过程。这是一种从“有迹可寻”的思想言说,深入到其“所以迹”的原理内部的诠释方法,其所诠释的对象,实质上已经从作为思想者的鲁迅,上升为作为生命原理的鲁迅,或者说,是作为思想的原理与生命的原理合一的鲁迅。这样一种思想的原理,是一种还原到思想动态性的运作机理,它是促使生命成为一种有机统一体的原理,同样的,这样一种生命的原理也是一种凝聚生命成为一种有机的思想运动的原理。这样一种原理,竹内好称之为“回心”,是那种生命和思想的原理通过自我否定地方式往复循环所形成的轴心。这一“回心”之轴的形成时期,往往在其思想的显性表达之前、之下,是一种潜隐性的“沉默”或“黑暗”时期。就鲁迅而言,竹内好认为,这个时期正是他发表《狂人日记》之前在北京“抄古碑”的时期,那是一个“没有任何动作显露于外”的时期,“呐喊”尚未爆发为“呐喊”的时期,“只让人感受到正在酝酿着呐喊的凝重的沉默”:
我想象,鲁迅是否在这沉默中抓到了对他的一生来说都具有决定意义,可以叫做“回心”的那种东西。我想象不出鲁迅的骨骼会在别的时期里形成。他此后的思想趋向,都是有迹可寻的,但成为其根干的鲁迅本身,一种生命的、原理的鲁迅,却只能认为是形成在这个时期的黑暗里。所谓黑暗,意思是我解释不了。这个时期不像其他时期那么了然。任何人在他的一生当中,都会以某种方式遇到某个决定性时机,这个时机形成在他终生都饶不出去的一根回归轴上,各种要素不再以作为要素的形式发挥机能,而且一般来说,也总有对别人讲不清的地方。……读他的文章,肯定会碰到影子般的东西。这影子总在同一个地方。虽然影子本身并不存在,但光在那里产生,也消失在那里,因此也就有那么一点黑暗通过这产生于消失暗示着他的存在。①
不过,问题在于以何种方式来厘定生命中的某个时期为“回心期”。在竹内好看来,这是一个人在他一生当中都会以某种方式遇到的某个决定性的时机,正是这样一个时机决定了他生命和思想的轴心和运作的方向。这样一种决定性的时机,就是一个人自我形成的契机,它可能是一场有形的事件,也可能是一场发生于无形的灵魂震动,也可能是一种刺激后的沉潜与发酵。对这样一种时机的发现,固然需要经过传记资料的梳理,需要通过其自觉的思想表达来分析,但更重要的是,需要能够既通过这些有形资料,又能够穿透这些思想资料,从其一次元的思想表达,进入其二次元的思想形成的契机当中。②当我们进入思想的二次元的时候,其思想的变化,就不是外缘刺激下的不自觉地调整,而应该说经由一定的外缘条件,对其思想原理的不断运用、发挥和充实。因此,思想的变化恰恰变现了“通过表象的二次元转换而得以显露给我们的本质层面的回心”③。只有如此,我们才算是把握住了诠释和理解思想人物之所以成为其自身的所以然的核心。
竹内好研究鲁迅的方法,作为一种诠释思想人物的基本方法,实际上也可以施之于对其老师章太炎的解读。
1903年7月至1906年6月底,章太炎因“苏报案”被囚系的三年,是他前一时期昂扬的政治和思想实践被迫中断的三年,除了零星流散出的“狱中谈话”与《读佛典杂记》之外,这三年也是章太炎一生当中唯一的思想言论空白期,应该说这三年是章太炎的被迫沉默期。与此同时,这三年也是章太炎主动研读佛典,特别是以法相唯识系佛典为主的时期。很多学者都曾注意到这一时期对于章太炎之后思想转折的重要意义,都曾论及“狱中读佛典,使他的学术思想和他撰著《訄书》时相比,有了重大转变”④,都认为系狱期间是“章太炎学术思想特别是哲学思想转变的关键时期”,而促使这一转变的关键是“读佛典”⑤。不过,对于发生在这一时期的从关心经、史、政俗问题、“以孙卿为宗”,渐而经由读佛典而转向“玄门”,这些观察都将其仅仅理解为思想兴趣、思想内容以及思想形态的变化,而未能充分探究何以研读佛典这一外缘竟然可以促使章太炎的思想世界发生如此激烈的转折,于是也便未能准确评估发生于此一时期之思想变化对于章太炎自身思想形成的深刻意义。或许,我们只有利用竹内好提供的分析鲁迅的方法,从章太炎一次元的思想表达之转变深入于其二次元的思想原理之形成,才能充分揭示这一时期对于章太炎的完整意义。
实际上,章太炎在自己之后人生的不同阶段,特别是1910年之后,在其学术思想的“中年论定”阶段之后,曾多次回溯此一时期对于他的重要意义。他在撰于1913年的《自述学术次第》中说:
余少年独治经史、《通典》诸书,旁及当代政书而已。不好宋学,尤无意于释氏。三十岁顷,与宋平子交,平子劝读佛书。始观《涅槃》《维摩诘经》《起信论》《华严》《法华》诸书,渐进玄门,而未有所专精也。遭祸系狱,始专读《瑜伽师地论》及《因明论》、《唯识论》,乃知《瑜伽》为不可加。既东游日本,提倡改革,人事繁多,而暇辄读藏经。又取魏译《楞伽》及《密严》诵之,参以近代康德、萧宾诃尔之书,益信玄理无过《楞伽》《瑜伽》者。少虽好周秦诸子,于老庄未得统要,最后终日读《齐物论》,知与法相相涉,而郭象、成玄英诸家悉含胡虚冗之言也。既为《齐物论释》,使庄生五千言,字字可解,日本诸沙门亦多慕之。⑥
实际上,章太炎对康德、叔本华著作的研读并非始自出狱东游日本之后,而在狱中研读佛典之际即已开始“参以近代康德、萧宾诃尔之书”。以西方哲学与佛典相互参究、会通说明,实质上表明了章太炎佛典研读的特质,其实并非是究心佛说、趋向解脱,而毋宁说是以对佛典中纯粹“玄理”的哲学性探讨为旨趣。而这一探讨的结果便是被他自诩为“一字千金”的《齐物论释》这一成熟的哲学论述的完成。因此,我们可以说这一时期的转折意义在于它开启了1906年出狱之后的成熟的哲学论述阶段。而在1915-1916年间完成的《菿汉微言》中,对这一思想转折作了更为细致的说明:
余自志学迄今,更事既多,观其会通,时有新意。思想迁变之迹,约略可言。少时治经,谨守朴学,所疏通证明者,在文字器数之间,虽尝观诸子,略识微言,亦随顺旧义耳。遭世衰微,不忘经国,寻求政术,历览前史,独于荀卿、韩非所说,谓不可易,自余闳眇之旨,未暇深察。继阅佛藏,涉猎《华严》《法华》《涅槃》诸经,义解渐深,卒未窥其究竟。及囚系上海,三岁不觌,专修慈氏、世亲之书。此一术也,以分析名相始,以排遣名相终,从入之途,与平生朴学相似,易于契机。解此以还,乃达大乘深趣。私谓释迦玄言,出过晚周诸子不可计数,程朱以下,尤不足论。既出狱,东走日本,尽瘁光复之业,鞅掌余闲,旁览彼土所译希腊、德意志哲人之书。时有概述邬波尼沙陀及吠檀多哲学者,言不能详,因从印度学士谘问,梵土大乘已亡,胜论、数论传习亦少,唯吠檀多哲学,今所盛行,其所称述,多在常闻之外。以是数者,格以大乘,霍然察其利病,识其流变。而时诸生适请讲说许书,余以段、桂、严、王未能满志,因翻阅大徐本十数过,一旦解悟,的然见语言文字本原,于是初为《文始》。而经典专崇古文,记传删定,大义往往可知,由是所见,与笺疏琐碎者殊矣。却后为诸生说《庄子》,间以郭义敷释,多不愜心,旦夕比度,遂有所得,端居深观,而释《齐物》,乃与《瑜伽》《华严》相会,所谓摩尼见光,随见异色,因陀帝网,摄入无碍,独有庄生明之,而今始探其妙。千载之秘,睹于一曙。次及荀卿、墨翟,莫不抽其微言,以为仲尼之功,贤于尧舜,其玄远终不敢望老庄矣。⑦
在这段自述学术次第当中,章太炎更为自觉地“观其会通”,将自己“思想迁变之迹”约略以“囚系上海,三岁不觌”为轴心期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个阶段的主题是朴学治经、寻求治术、历览前史,诸子之微言仅“略识而已”,只是随顺旧义,且因寻求治术的关系,而以荀子与韩非的学说作为衡评诸家的不易之准则。虽亦涉猎佛藏,义解渐深,但尚未“窥其究竟”。而在上海狱中的三年则因索读到适合于以朴学之方法研治的佛典,而最终对大乘甚深义趣有所解悟,且同时把“释迦玄言”作为衡评晚周诸子的标准。在东渡日本后的阶段,则继续把“大乘”佛理作为理论标准,将希腊、德意志哲学以及印度吠檀多、胜论、数论哲学“格以大乘”,考较其得失之故,察其流变之原。在对这一阶段的自述中,章太炎特别提到了他在朴学治经阶段所从事之学问上的长进,一是于语言文字的然见其本原;二是于经典专崇古文,一改过去琐碎笺疏的作风,而能够从纪传删定中见其大义。这一阶段最为重要的创获则为以《瑜伽》《华严》会通《齐物》,完成《齐物论释》,将千载之秘,霍然解明,认为东夏独有庄生能明此“摄入无碍”、“随见异色”的平等佛理。正是在此最高玄理之解明完成之后,他则能够进一步“操齐物以解纷”,重新会通荀、墨、孔诸家而一改过去之成见。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不同于《自述学术次第》中仅从哲学论述之成熟展开着眼论及三年囚系读佛典的意义,在这里章太炎将此经由读佛典所获得的哲学上的解悟,扩大到了其小学发明与经学创获上。这似乎说明,三年囚系时期佛典研读的意义更具有思想原理突破的意味。在《菿汉微言》中紧接上文,章太炎则对《菿汉微言》之成文缘由以及它在自己思想迁变当中的位置做了进一步的说明:
癸甲之际,厄于龙泉,始玩爻象,重籀《论语》,明作《易》之忧患,在于生生,生道济生,而生不可济。饮食兴讼,旋复无穷。故唯文王为知忧患,唯孔子为知文王。《论语》所说,理关盛衰,赵普称半部治天下,非尽唐大无验之谈。又以庄证孔,而耳顺绝四之指,居然可明。知其阶位卓绝,诚非功济生而已。至于程朱陆王诸儒,终未足以厌望。顷来重绎庄书,眇览《齐物》,芒刃不顿,而节族有间。凡古近政俗消息、社会都野之情状、华梵圣哲之义谛、东西学人之所说,拘者执着而鲜通,短者执中而居间,卒之鲁莽灭裂,而调和之效,终未可睹。譬彼侏儒,解遘于两大之间,无术甚矣。余则操齐物以解纷,明天倪以为量。割制大理,莫不孙顺。程朱陆王之俦,盖与王弼、蔡谟、孙绰、李充伯仲。今若窥其内心,通其名相(宋儒言天理性命,诚有未谛,寻诸名言,要以表其所见,未可执着。且此士玄谈,多用假名,立破所持,或非一实,即《老》《易》诸书,尚当以此会之,所谓非常名也),虽不见全象,而谓其所见之非象,则过矣。世故有疏通知远、好为玄谈者,亦有文理密察、实事求是者。及失主静主敬,皆足澄心,欲当为理,宜于宰世。苟外能利物,内以遣忧,亦各从其志尔。汉宋争执,焉用调人,喻以四民,各勤其业,瑕衅何为而不息乎?下至天教,执邪和华为造物主,可谓迷妄。然格以天倪,所误特在体相,其由果寻因之念,固未误也。诸如此类,不可尽说。执着之见,不离天倪,和以天倪,则妄自破而纷亦解,所谓无物不然,无物不可,岂专为圆滑无所裁量者乎?⑧
从这段自述我们可以知道,《齐物论释》完成之后的学术思想趋向,应该说是对“齐物”哲学的原理加以多方面运用的结果。《菿汉微言》即是围绕“齐物”哲学原理在多方面深入运用而得诸多创获的结集。在这个阶段,对《周易》《论语》《老子》的研究更进一步,认为“文孔老庄是为域中四圣,冥会华梵,皆大乘菩萨也。”将通过佛典会通庄生而得之齐物哲学原理,推广而通之于文孔老,终于实现文孔老庄与佛的终极会通。根据这种会通的结果,章太炎认为自己已经能够将“齐物”“天倪”的原理广泛运用到打通一切对于“古近政俗消息、社会都野之情状、华梵圣哲之义谛、东西学人之所说”的拘泥执着,而在超越居间调停之论的基础之上,真正做到“无物不然,无物不可”的“各从其志”的齐物平等境界。
于是,章太炎总结平生学术曰:
自揣平生学术,始则转俗成真,终乃回真向俗,世固有见谛转胜者邪!后生可畏,安敢质言?秦汉以来,依违于彼是之间,局促于一曲之内,盖未尝睹是也。⑨
如果说《齐物论释》的完成,一方面意味着章太炎对“真”的追求达到了其最高理解,而另一方面正是这种关于“真”的最高理解自身所包含的题中应有之义,要求它必须容纳自身的对立面即俗,需要为“俗”提供一个与“真”等量齐观的位置,而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真”。这表明,《齐物论释》是“转俗成真”的至高点,同时也是“回真向俗”的原理起点。于是,在这里,我们似乎终于发现了那个真正决定思想形成与转化的轴心,亦即章太炎对“真”的独特追寻。而这个轴心的发端,恰如上文所述,应该在“囚系上海,三年不觌”的“读佛典”时期。围绕“真”的轴心之发端与“真”的原理之成熟,我们可以将章太炎的思想迁变之迹再次划分为这样三个时期,第一时期是“囚系上海”之前的阶段,也可以称之为《訄书》的时代,是在其经学、小学、史学研究的基础之上,通过探究“社会政法盛衰蕃变之所原”⑩的社会理论,来重建民族文化的阶段,也可以称之为关心社会政俗的求“俗”阶段。第二时期即是经过囚系狱中读佛典的“回心”契机,“真”的追寻之发端和开展的阶段,表现在思想论述上是他针对反满革命的形势,回应包括保皇改良、无政府主义等思想论调,而展开的激烈批判时期,也就是一般所说的主笔“民报”时期。在上文所引章太炎的自述文字中我们并没有见到他对自己这些政论文字的说明,但恰恰是这些政论文字中蕴含着他的最初的求“真”的哲学思考,成为他所建设的“真”的原理的初步展开。实际上,在章太炎自己的思考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的一种持续的努力,亦即不断地将外缘性的思想回应,逐渐上升为更具普遍意涵的理想型,从而在他的理论思考当中获得原理性地安排。因此,对于这些政论性文字,从其语境外缘的角度,从论战的对话关系出发来理解其思想内涵,固然是极其重要的思想史功夫,但如何从这种论战性的一次元的思想反应进入其思想形成的轴心原理,却应该是我们解读这些文字时同时需要深入关注之处。这个时期实质上即是所谓“转俗成真”的时期。第三时期则是以《齐物论释》的完成为标志,这一方面是他求“真”原理的最终完成,而同时也是他具体运用此原理,从而实现所谓“回真向俗”的阶段。
这三个时期的划分,恰如章太炎自己所说,是以他的所谓“见谛转胜”为依据的,而他所谓“见谛”,实质上正是对所谓“真”的“见谛”。用“见谛转胜”来刻画自己思想的形成过程及其阶段性,实际上正是对思想形成的阶段性关系的恰当说明。所谓“转胜”意味着阶段之间是一种自我的否定,而这恰与竹内好所谓“回心”(converse)的意义相当,因此,所谓“转胜”是一个通过自我否定不断实现自己思想的自觉发展的过程。而对这样一种通过自我否定以获得自我发展的最为恰当地表述,应该说正是佛教唯识学理论当中的“转依”。它是一种通过某种觉悟性的契机实现的生命方向的转化,这样一种转化是一种通过对导引生命的轴心的转换来实现的,生命在轴心的转换中赢得了新的导引力量。章太炎思想形成和迁变的过程应该说正是这样一种“转依”的过程。
如果章太炎思想迁变之迹依据的是以“真”为轴心对真俗关系的不同安排作为“见谛转胜”的内在原理的话,那么构成其“见谛”内涵的“真”究竟何所指呢?相应地,“俗”又何所谓呢?或者说,作为“真”的原理是由何种基本主题构成的呢?在经过了“三年不觌”的沉默之后,章太炎东渡日本之后最初发表的两篇文字——《东京留学生欢迎演说录》与《俱分进化论》——似乎颇能呈现其思想突破之后的“见谛”之内涵。
1906年6月29日章太炎出狱后随即前往东京,7月15日即在东京留学生的欢迎会上发表演讲,提出了“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的道德”,“用国粹激动种姓,增进爱国的热肠”(11)的著名口号。在这篇文字中,之后《民报》时期出现的基本主题差不多都有所流露。首先在关于宗教的看法中,他尝试“用华严、法相二宗改良旧法”,将佛教改造为一种“万法唯心”的无神论,成为一种合乎哲学的宗教,并以此来构建一种勇猛无畏的革命道德,这样一种经由佛教来建立宗教、通过宗教来增进道德的思考,分别成为此后《无神论》《革命之道德》与《建立宗教论》诸论的主题。他对于革命者“自尊无畏”道德情操的强调,实际上就已经是其在《建立宗教论》中试图建立的“自识为宗”的“唯心胜义”之教的滥觞。而这样一种唯心胜义之教的基本内涵则是对一种“依自不依他”的义务论道德所表达的价值内在自足性的肯认。与此同时,他对佛教的提倡更是着眼于“佛教最重平等”的性格,在他看来,佛教的平等性实质上即表现为对“妨碍平等的东西”的批判和祛除。这表明,对“平等”和“价值内在自足性”的关心,已经构成为其出狱后首篇文字的基本主题。其次,尽管作为演讲主题的“宗教”和“国粹”是为革命动员的目的而提出的,但在“国粹”名义下所涵括的内容则是章太炎《訄书》阶段前后的以经、史、小学为主的学术领域,也正是所谓“俗”的领域。关于这一领域的价值判断,一方面受制于革命动员的需要,而另一方面也随着他对“真”的见谛转胜而产生不同的判断。因此,在一定意义上,“宗教”与“国粹”的并列,实际上就已经开启了日后关于“真”“俗”关系辩证的模式。
同样的主题其实也呈现于时隔近两月在1906年9月5日的第七号《民报》上发表的《俱分进化论》(12)中。在该文中,章太炎已经尝试从“种子识”与“种子”关系的角度,来阐明“善恶并进”之“俱分进化”的道理。所谓“俱分进化”即在阐明善恶种子平等缘起的道理,而其目的则在于取消“进化论”以及作为其反面规定物的“厌世论”所设定的一元终极的价值观。他在批评本着赫尔特曼(哈特曼)调和进化与厌世的观点而产生的两种态度之后,提出了一种庶几接近所谓“无漏善”亦即绝对善的可能:
纵令入世,以行善为途径,必不应如功利论者,沾沾于公德、私德之分。康德所云“道德有对内之价值,非有对外之价值”者,庶几近于“无漏善”哉!何以故?尽欲度脱等众生界,而亦不取众生相,以一切众生,及与己身,真如平等无别异故。既无别异,则惟有对内在之价值,而何公德、私德之分乎?其次,无勇猛大心者,则惟随顺进化,渐令厌弃。……然随顺进化者,必不可以为鬼为魅、为期望于进化诸事类中,亦惟选择其最合者行之,此则社会主义,其法近于平等,亦不得已而思其次也。(13)
所谓“无漏善”,即康德所谓“道德有对内之价值,非有对外之价值”所强调的依从绝对命令而实现的道德的无条件性。这说明道德自身即具有自足内在的价值,而并非取决其他任何功利目的。在章太炎看来,这种具有内在自足价值的道德,即庶几接近于佛教所谓的“无漏善”。恰如康德仍然需要一种无目的的目的论作为这种道德的自足内在价值的论证一样,章太炎对这样一种具有内在自足价值的道德的论证则是从“真如平等无别异”出发的。所谓“真如平等无别异”,即是在内在价值之肯认意义上的平等义。可见,相较于《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录》,《俱分进化论》中已经非常自觉地建构起了“内在之价值”与“真如乎等无别异”之间的原理性关联。并且,值得注意的是,在这里章太炎已经将“社会主义”的平等观作为“真如平等无别异”“退而求其次”的追求来看待。
通过对这两篇出狱后最初发表文字的分析,我们似乎可以找到章太炎囚系三年“读佛典”而获之回心突破的基本内涵,也是其“见谛”的基本原则,那就是对“内在之价值”和“真如平等无别异”的追求。实质上,他之后的思想形成和发展便是对乎等与内在价值之间相互揭示和相互充实之关系的追寻过程。而他所谓“真”的见谛,即发端于此,并成为他今后思想发展的核心。《齐物论释》之最终完成,即是对此一核心原理的最高整合。因此,对《齐物论释》中平等理论的分析可以更为完整地呈现章太炎“真”之见谛的全部内涵。下面就让我们来深入《齐物论释》的文本,通过章太炎最为成熟的哲学表达,来充分探究其思想原理的究竟内涵。
《齐物论释》一书是章太炎非常珍视的著作。他在《自述学术次第》中道及《齐物论释》等书之撰述时,颇为自得:
中年以后,著纂渐成,虽兼综故籍,得诸精思者多。精要之言,不过四十万字,而皆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不好与儒先立异,亦不欲为苟同,若《齐物论释》《文始》诸书,可谓一字千金。(14)
《齐物论释》的写作体例是据《齐物论》七章,先本文,后释文,逐章加以疏释。加上释篇题和序共有九个部分。1911年归国后修改此书而成之《齐物论释定本》一卷,在文句诠释上引申更为丰富,但主题没有变动和增加。《齐物论释》的诠释原则正如他在序言中所说是“儒墨诸流,既有商榷,大小二乘,犹多取携,义有相征,非傅会而然也。”也就是说,以佛理诠释《齐物论》并非傅会,而是因为“一致百虑,则胡越同情,得意忘言,而符契自合”,是由于根本上两家“义有相征”。那么,之所以仍然需要以佛理诠释《齐物》,那是因为“《齐物》文旨,华妙难知”,而魏晋以下,解者虽众,但都“既少综核之用,乃多似象之辞。”更为重要的是,以往旧释的《齐物》解释,都不能彻底解明齐物平等的确切内涵,而以所谓“世俗所云自在平等”为“齐物”。因此,有必要利用已经得到充分阐释的《瑜伽》平等之义,来贯通解释并进而重构《齐物》难知之理。作为《瑜伽》与《齐物》相征之义的“平等义”的内涵,章太炎曾有如下的概括:
体非形器,故自在而无对;理绝名言,故平等而咸适。(15)
所谓自在无对,即是就自体真我的内在价值自足而言;所谓平等咸适,即是根据此内在价值自足而成就之“物各付物”的真正“平等”。这样一种平等观念的内涵,首先需要与另外两种典型的平等观加以区别,必须经过与这两种平等观的论辩才能最终得以确立。这样两种平等观,一种即是所谓“博爱大同”之平等见,是所谓博爱大同的普遍主义平等观;另一种则是所谓“自在平等”的平等观,这是以往对“齐物平等”的主导性理解,其根据则是郭象的“适性平等”观。
乌目山僧黄宗仰在为《齐物论释》所作后序中指出:
以为《齐物》者,一往平等之谈,然非博爱大同所能比傅,名相双遣,则分别自除,净染都忘,故一真不立。任其不齐,齐之至也。……今太炎之书见世,将为二千年来儒墨九流破封执之扃,引未来之的,新震旦众生知见,必有一变以至道者。(16)
章太炎所发明的“一往平等”齐物平等观,必须与那种“等视有情、无所优劣”的“一往平等”之论相区别。“博爱大同”的“平等”即是旧的“一往平等”之论的典型。这种平等观是章太炎所极力避免和批判的,在章太炎看来,“博爱大同”的平等是一种“齐其不齐”的平等,是以一种普遍的平等观念“齐不齐以为齐”的平等,背后总是预设了一种一元论的价值,因此基于一元价值而来的平等在实质上一定是一种彻底的不平等见。而且这种平等往往是所谓“志存兼并者,外辞蚕食之名,而方寄高义”的借口;即使如主张“非功”的墨子,他的“兼爱”也是要假“天志”而对“违之者分当夷灭不辞”,与景教、天方等一神教的平等主义同类。同时,章太炎的“任其不齐”“不齐而齐”的平等观也不是“自在平等”可以涵括的,如果说“自在平等”是一种具有虚无主义倾向的相对主义和多元主义的话,那么章太炎所发明的“不齐而齐”的平等,则可能从根本上克服这种相对主义和多元主义的平等。章太炎所主张的所谓“毕竟平等”,其关键在于“离言说相,离名字相、离心缘相”,是“名相双遣”“分别自除”的“任其不齐而齐之至也”的平等。这是一种通过否定旧的有分别的价值秩序而在“自证”中“直观自得”的平等。因此,是否经过了“破执”“丧我”的思想和实践的步骤,是章太炎的“不齐而齐”的“毕竟平等”观区别于“博爱平等观”和“自在平等观”的关键。章太炎在“理想型”上所建构的所谓“不齐而齐”的平等与上述“自在平等”与“博爱大同”的乎等之间的关系,在中国学术史上对应着以墨家为代表的“泛爱兼利”的平等与以郭象为典型的“适性”平等,而在章太炎当时的语境中,则对应着一元论的无政府主义、进化论(章太炎也称之为进化教)和一神教,以及革命者中的道德上的犬儒主义;而在当代的语境下,则显然具有与一元论的普遍主义和多元论的特殊主义之间的论辩意义。因此,在当前的背景下,如何澄清章太炎的毕竟平等观与郭象的具有相对主义性格的适性平等观之间的微妙不同,相对于对“博爱大同”的一元论平等观的批判,便特别具有更进一步的现实和理论意义。本文对章太炎《齐物论释》中平等观的疏释中将重点辨析其与郭象的平等观的不同。
章太炎的《齐物论释》尽管是依文释义,但其解释却具有一定程度的结构层次上的系统性。下面我们即依据文本尝试将章太炎齐物平等的理论加以系统的构拟(17),藉此来深入阐明他的平等观的内涵。
在《释篇题》中,章太炎在辨明《齐物论》题目究竟是否应该如王安石、吕惠卿他们那样将“齐物”属读时指出,“齐物”属读的错误在于“不悟是篇先说丧我,终明物化,泯绝彼此,排遣是非,非专为统一异论而作也”(18),可见,章太炎将《齐物论》根据其主题分成前后两个部分,“先说丧我,终明物化”,而其主旨则在于“泯绝彼此,排遣是非”。这说明章太炎是以“丧我”与“物化”为核心来诠释《齐物论》的,二者之间不仅具有结构上的先后关系,更具有逻辑上的系统关联。因此,我们可以根据章太炎的提示来构拟其《齐物论释》的理论逻辑和思想义趣,将其分成逻辑上层层递进的三个主题:“丧我”、“无我证真”、“物化”或“和以天倪”。
首先,关于“丧我”的内涵,章太炎说:
《齐物》本以观察名相,会之一心。名相所依,则人我法我为其大地,是故先说丧我,尔后名相可空。(19)
可见,“丧我”即是空其名相,即是破除以人法、彼此、是非、见相为对待的名相分别。
既破名家之执,而即泯绝人法,兼空见相,如是乃得荡然无阂。若其情存彼此,智有是非,虽复泛爱兼利,人我毕足,封畛已分,乃奚齐之有哉。(20)
这也就是说,经由“丧我”而实现的破封执、去分别的状态,是齐物平等的前提。因此,所谓“丧我”即是破除“我见”,同时也是将附着在“我见”之上的固有的价值秩序加以否定,摆脱固有价值秩序所树立的“情存彼此,智有是非”的价值观念的束缚和左右。他说:“大概世间法中,不过平等二字。庄子就唤作‘齐物’。并不是说人类平等、众生平等,要把善恶是非的见解一切打破,才是平等。”(21)那种“泛爱兼利”的平等由于仍然有彼此之别、是非之念,因而其平等必然是“强不齐以为齐”,并不能从根本上消除人我之间的“封畛”,即使达到了“人我毕足”的状态,也并非真正的“平等”。而那种所谓“自在平等”的观念,实际上也是一种“含胡虚冗”的平等,也是因为它并未能从根本上破封执、去分别。
对于“自在平等”的批判是理解章太炎“不齐而齐”平等观的关键,而章太炎辨析“自在平等”与“不齐而齐”的平等之间微妙不同的关键,即在于“平等”是否是在“丧我”、“破执”之后,所以,“破执”“丧我”是“平等”能否真正建立的根本前提。
关于“自在平等”意涵的经典表达,是郭象在《逍遥游》里所主张的“物各有性,性各有极”的“自得”意义上的“适性平等”:
夫小大虽殊,而放于自得之场,则物任其性,事称其能,各当其分,逍遥一也,岂容胜负于其间哉?(22)
所谓“平等”是在“物任其性,事称其能,各当其分”意义上的“自得”,这种“自得”是“小大虽殊”前提下的“自得”,也就是说大小之间虽然有别,但仍然可以在小安于小,大安于大的意义上实现“物任其性”、“各当其分”的“自得”意义上的“平等”。这种“自得”的目的在于取消“以小羡大”和“以大临小”的压迫性格局,但这种自得却仍然保留了“小大”之间的秩序,承认了“小大”之间在“小大”意义上的差别,这就是所谓“大小之辩”的真实意味。郭象还说道:
夫时之所贤者为君,才不应世者为臣,若夫天之自高,地之自卑,首自在上,足自居下,岂有递哉?虽无错于当而必自当也。(23)
天地、首足、君臣之间的秩序是不能改变的,要改变的是错于所当的状况,而“自得”即是使天地、君臣、首足之间“必自当”而已。因此,
臣妾之才而不安臣妾之任,则失矣,故知君臣上下手足外内,乃天理自然,岂直人之所为哉!(24)
所安所足之性即是天理自然,因此只要能够自安其性、自足其性,即是对天理自然的实现。不过,这种所安所足之性是块然自生、不得不然的自然。因此,“丧我”便是忘却“人为”意义上的“忘我”:
吾丧我,我自忘矣,我自忘矣,天下有何物足识哉!故都忘外内,然后超然俱得。(25)
郭象的“丧我”是“忘我”之义,而所谓“忘”则是“玄同”的另一种说法:
夫忘年,故玄同死生,忘义故,弥贯是非,是非死生,荡而为一,斯至理也,至理畅于无极,故寄之者不得有穷也。(26)
“玄同”即是“弥贯”是非、彼此、死生之间的差别,“荡而为一”的状态。在“玄同”的状态下,
夫莛横而楹纵,厉丑而西施好,所谓齐者,岂必齐形状同规矩哉! 故举纵横、好丑、恢诡、谲怪,各然其所然,各可其所可,则形虽万殊而性同得,故曰道通为一也。(27)
“道通为一”的“一”,或者说“荡而为一”的“一,”并非“齐同为一”的“一”,亦即并非“齐形状同规矩”意义上“齐不齐以为齐”的“一”,而是“各然其所然,各可其所可”意义上彼我都能够“自得其性”的“一”,是所谓“彼我均”意义上的“一”。于是,“道通为一”的“玄同”观照之下的“大小之辩”,便具有了如此的内涵:
各以得性为至,自尽为极也,向言二虫殊翼,故所至不同,或翱翔天池,或毕志榆枋,直各称体而足,不知所以然也。今言大小之辩,各有自然之素,既非,亦各安其天性,不悲所以异,故再出之。(28)
无论“翱翔天地”还是“毕志榆枋”,只要能够“各称体而足”“各安其天性”,不“跤慕之所不及”、“不悲所以异”,那么“大小之别”便不构成对我们的束缚和困扰。于是,蟪蛄不羡于大椿之长生,斥鷃不贵大鹏之能高,太山不大于秋毫,“苟足于天然而安其性命”,也就实现了“无大无小”、“无寿五夭”的“道通为一”的“玄同”境界。可见,“无大无小”并非取消了大小之间的区别,而只是“玄同”了大小的区别,“忽忘”于大小的区别。严格说来,这正是“相对主义”的典型态度。钱穆先生曾一针见血地指出郭象此说的实质:
如《庄子逍遥游》,明明分别鲲鹏学鸠大小境界不同,但郭象偏要说鹏鸠大小虽异,自得则一。(29)
显然,郭象这种所谓适性自得的境界,是一种在大小秩序既定前提下的,安于固有大小秩序的自得,也是对既定大小之性的适应。作为这样一种适应的理论表现即是“相对主义”,以及在“相对主义”基础上的“多元主义”。无论是相对主义还是多元主义对既定秩序的批判,其实都不会破坏或否定既定秩序的前提,它不仅不是对普遍主义一元论的真正克服与超越,而且是在承认既定秩序下对支撑既定秩序的一元主义或普遍主义的补充或补强。因此,“相对主义”和“多元主义”不仅无助于从根本上改善世界的价值秩序,甚至有可能逃避了促进新的价值秩序形成的责任。这样一种态度在现实人生的表现上则是一种消极的玩世不恭,一种无可无不可的两可状态,甚至有可能演变为一种身心相离的苟且态度,成为一种“无性情的放荡”(30)(钱穆语)。
以往关于章太炎的齐物平等思想的主流诠释当中,实际上占据主导地位的观点仍然是将其混同于郭象,含胡笼统地将其看作是一种“相对主义”的平等观。例如最具代表性的观点是认为“在《齐物论》下,只有同而没有异”,根据这种观点,“一往平等的极端推论又把他带到了‘真妄一原’的路上”,“这种认识论的特点,就在于‘泯绝彼此、排遣是非’,‘破名相之封执、等酸咸于一味’。在这里,一切的事物,便如‘暗夜里的牡牛’,尽归齐同而无所差异。”(31)显然,这种观点将“泯绝彼此、排遣是非”的去封执、破名相的“丧我”诠释为了郭象式的“忘我”意义上的“齐同”差别而实现的“无所差异”的状态。齐同差异意味着取消了事物之间的“质”的差异。与“齐不齐以为齐”的“齐同”是将“差别”转化为“同一”有所不同,这种“齐同”则是不以“差异”为“差异”意义上的“齐同”。尽管存在着关于“齐同”理解上的不同,但二者都诉诸“齐同”差异,则是一致的。这种将章太炎的平等混同郭象式平等观点,根本上误解或者说没有能够抉发出章太炎毕竟平等观的更为隐微而深刻的内涵。他们没有看到,章太炎的“不齐而齐”的平等实质上是对“差异”的彻底维护。章太炎的毕竟平等观,是在维护“差异”绝对性的前提下实现的“差异”间的平等,是差异者彼此都在“是其所是”的意义上实现的平等。之所以会发生这样的误解,关键即在于这种观点未能深刻把握章太炎《齐物论》诠释中的第一个环节“丧我”的全部内涵。
同样是“泯绝彼此、排遣是非”意义上的“丧我”,何以郭象式的“丧我”带来的是“不以差异为差异”的“平等”,而章太炎式的“丧我”则是在尊重“差异”意义上的“平等”呢?同样的“丧我”何以会带来不同的平等状态?问题的关键在于郭象式的“丧我”仅仅是“忘我”意义上的在不改变规定“差异”的秩序的前提下,主观地取消了“差异”,“不以差异为差异”;而章太炎的“丧我”则是在破除由“差异”的秩序所规定的“差异”的观念的前提下,改变规定“差异”的秩序,从差异自身出发来获取规定差异自身的权力。因此,章太炎的“丧我”“破执”同时即是一种通过改造观念中的既定价值秩序来实现的改造世界的批判性实践。真正的乎等是在对固有价值秩序的改造中实现地对差异之所以为差异的解放,是在差异是其所是的意义上实现的平等。同样是“丧我”,经由对“我”的否定而带来的结果是不同,这种不同不仅取决于所丧之“我”的内涵,更取决于“丧我”之后所证境界的实质。也就是说,“丧我”之后是什么而“丧我者其谁”的问题,是理解二者不同的机窍。
于是,我们可以进入章太炎平等观的第二个层次,亦即“无我显真”:
我苟素有,虽欲无之,固不可得。我若定无,证无我已,将如槁木枯腊邪?为是征求我相名色,六处我不可得,无我所显,真如可指,言我乃与人我法我异矣。其辩曰:绝待无对,则不得自知有我,故曰非彼无我。若彼无我,虽有彼相,谁为能取,既无能取,即无所取。由斯以谈,彼我二觉,互为因果,曾无先后,足知彼我皆空,知空则近于智矣。假令纯空彼我,妄觉复依何处何者而生,故曰不知其所为使。由是推寻,必有心体,为众生依止,故曰若有真宰。(32)
如果“我”本来即存在,那么即使想否定它也是不可能的;如果“我”本来便不存在,那么对“我”的否定的结果难道不就是槁木枯腊一般的断灭境界?当然不是。这是因为“无我所显,真如可指”,对“我”的否定实际上是为呈现“真如”,此“真如”即是与被否定的人我法我相异的“真我”。所谓“真我”是绝待无对的,而人我法我则是彼此相待。因此,只有彼我皆空,绝对无待之“我”才会呈现。反面论之,正是由于存在着这样一种绝对无待的真我,妄觉下产生的彼我分别才可能有所依止,否则便“不知其所为使”。因此,所谓绝对无待的“真我”,其实正是众生依止的“心体”。
在这里,由无我所显之“真如”,被直接等同于“真我”。在后来的唯识学正统看来,这是典型地“真如”“正智”不别的毛病。不过,在章太炎这里却自有其道理。章太炎后来在《菿汉微言》中对于无我、真我、幻我的关系曾有更精确地说明,他说:
佛法虽称无我,只就藏识生灭说耳。其如来藏自性不变,即是佛性,即是真我,是实,是遍,是常。而众人未能自证,徒以生灭者为我,我岂可得邪?……今应说言:依真我(如来藏,是实、遍、常),起幻我(阿赖耶,非实、遍、常);依幻我,说无我;依无我,说真我。(33)
“无我”者是无生灭之我,生灭之我即是“幻我”,因为有幻我,所以要否定之,故是“依幻我说无我”;幻我可无,即能自证真我,故是“依无我说真我”;同时,若无“真我”,“幻我”亦不可能,“真我”是“幻我”成立的前提,故是“依真我说幻我”。在他看来,“真我”与“彼我”“妄觉”的关系,虽不是正向的能生所生关系,却似乎是一种突然自生的依止因。显然,在这里章太炎借取《大乘起信论》里的真如不变随缘说来解释真我与妄觉现起的关系。在此基础之上,章太炎进一步展开了关于“真我”与“幻我”各自内涵及其关系的深入阐明。他运用唯识学的八识理论,将此“真我”证成为“阿罗邪识”(阿赖耶识)或“菴摩罗识”:
真宰即佛法中阿罗邪识,惟有意根恒审思量执阿罗邪识以为自我,而意识分别所不能见也。……以是五义,辗转推度,则谓有真我在。盖灵台者,任持根觉,梵名阿陀那,亦以含藏种子,名曰灵府,梵名阿罗邪。其体不生灭而随缘生灭者,佛典称如来藏,正言不生灭体,亦云菴摩罗识。……由是寂静观察,灵台即现,执此恒转如瀑流者,以为自我,犹是幻妄。唯证得菴摩罗识,斯为真君,斯无我而显我耳。是故幻我本无而可丧,真我常遍而自存,而此菴摩罗识本来自尔,非可修相,非可作相,毕竟无得,故曰求得其情与不得,无益损乎其真。(34)
在他看来,庄子所谓“灵台”则为任持根觉的“阿陀那识”,而含藏种子的“阿罗邪识”,则是庄子所谓“灵府”,都是对心体的不同状态的说明:就其不生灭的心体而言,此识可称之为“菴摩罗识”,亦称“如来藏”;就其任持根觉而言,此识即“阿陀那识”;就其含藏种子而言,此识即“阿罗邪识”。对此“菴摩罗识”的证得,是通过“无我而显”的,是对意根执持阿罗邪识而成之所谓自我亦即“幻我”的否定而所显现的“真我”。“幻我”就其是幻而言,其实本无可丧者,认识到其为虚幻即是对“真我”的证得。“真我”是“常遍而自存”的,是真正的“真君”“真宰”,“本来自尔”,是绝对无待而无所依傍的,这就是“菴摩罗识”。证得“菴摩罗识”的过程,实际上即是一个否定和批判现实世界的过程,是一个超越小我的过程,在此意义上证得的“真我”,自然具备一种绝对无待意义上的价值自足性,其“无待”并非是郭象式的主观状态中泯绝彼此的“自得自足”,而是一种无所依傍的“价值自立”。因此,在“无我显真”的过程,即是一种“自尊无畏”的道德实践的过程:“无畏”是一种批判现实的勇气,而“自尊”则是这种勇气的动力来源,那是对“真我”的价值内在自足自立性的肯认。章太炎《民报》阶段所试图通过建立“自识为宗”的“唯心胜义”之宗教而建设的革命者的道德,其背后的原理即在于此。如果将这样一种“无我显真”的批判性极端发挥的话,便产生了被学界一般认为具有虚无主义倾向的《五无论》。不过,在我看来,《五无论》中所谓无政府、无聚落、无人类、无众生、无世界之“五无”,实际上是以一种极端的否定态度来表达一种彻底的批判精神,而其目的或旨趣仍然在籍此批判和否定,来建设一个由价值上自立自足的真我构成的世界。
不过,问题在于如何在证真之后重新安立俗的世界,如何重新确立真我与俗我的必要关联。章太炎关于“真我”与“幻我”关系的说明并未就此打住,他开始从“无我显真”进入到齐物平等论证的第三个层次,亦即唯心与缘起的关系问题,在这个层次上他提出了著名的“和之以天倪”的原理。这个问题的实质即是在“显真”之后如何重新面对“俗”的世界。章太炎对《齐物论》中“随其成心而师之,谁独且五师乎?”的解释就是在解明“种子”与“种子识”的关系。他说:
此论藏识中种子,即原型观念也。色法无为法外,大小乘皆立二十四种不相应行,近世康德立十二范畴,此皆繁碎。今举三法大较应说第八藏识,本有世识、处识、相识、数识、作用识、因果识、第七根本有我识(人我执、法我执),其他有无是非,自共合散成坏等相,悉由此七种子支分观待而生。成心即是种子,种子者,心之碍相,一切障碍即究竟觉,故转此成心则成智,顺此成心则解纷。成心之谓物也,眼耳鼻舌身意六识未动,潜处藏识意根之中,六识既动,应时显现,不待告教,所谓随其成心而师之也。……人情封略,亦观世者所宜知也。次举意根我识种子所支分者,为是非见。若无是非之种,是非现识亦无。其在现识,若不忍许,何者为是,何者为非,事之是非,亦无明证。是非所印,宙合不同,悉由人心顺违以成串习,虽一人亦犹尔也。然则系乎他者,曲直与庸众共之,存乎己者,正谬以当情为主,近人所云主观客观矣。……是云非云,不由天降,非自他作,此皆生于人心。心未生时,而云是非素定,斯岂非以无有为有邪!夫人虽有忮心,不怨飘瓦,以瓦为无是非心,不可就此成心论彼未成心也。然则史书往事,昔人所印是非,亦与今人殊致,而多辩论枉直,校计功罪,犹以汉律论殷民,唐格选秦吏,何其不知类哉?《老子》云‘道可道,非常道’,董仲舒云:‘天不变,道亦不变。’智愚相悬,乃至于此。(35)
章太炎对“种子”的理解显然有悖于唯识学理论的说法。他把种子理解为柏拉图意义上的原型观念或“相”,而“成心”就是“种子”。作为“种子”的“成心”,即是眼耳鼻舌身意未动时潜藏于“藏识意根之中”,而在六识已动时,应时显现的观念。因此,若无“是非”之“种子”,或者说若无“是非”的观念,便不会有在现识当中所呈现的“是非”判断,亦即“是非现识亦无”。“是非”分别的出现,都是对现识中所应现的“是非”种子或“是非”观念的认可,若不将其作为“是非”来认许,那么事实上的“是非”便无根据和明证。这就是所谓“随其成心而师之”。而“是非”观念或种子作为“成心”的产生,都是“由人心顺违以成串习”,是从人心顺违的感受中熏习而成的。这些人心顺违的熏习包括有主客观两方面。主观方面是所谓“存乎己者”的“当情为主”的习惯性判断带来的影响,客观方面则是所谓“系于他者”的与庸众“曲直所共”所带来的后果;“存乎己者”与“系于他者”的主客两方面的“串习”便成为“成心”或“种子”的来源。由于“串习”的形成依赖于不同时空条件,因而在不同条件下“串习”有不同,因而“是非”的“成心”便有所不同。因此,“是云非云”都“不由天降,非自他作”而是都产生于“人心”,来自于“成心”,其实也就意味着来源不同的时空条件下的“串习”。这说明“是非”并非素定,而不能“以无有为有”,将此并非素定的“是非”,作为不变之天道,那样便会犯“以汉律论殷民,唐格选秦吏”的不知类的毛病。章太炎的此番论证旨在说明,“是非”等价值判断或分别其实都是缘起的产物,是成心与串习相互作用的结果。这也就是说,价值判断或价值分别并非得自“素定”的普遍的标准,自然不能放之四海皆准。与此同时,既然价值判断或价值分别都出自“成心”,那么所有的价值判断或分别其实都是可以从其所产生的条件出发相互加以理解的。这是以“种子”(“成心”或“原型观念”)来解明缘起的道理,并以缘起理来安立俗界的意义所在。
正是在此意义上,章太炎提出了他的“凡万物与我一体之说,万物皆种以不同形相禅之说,无尽缘起之说,三者无分”的说法。所谓“三者无分”,即是将“万物与我一体说”和“万物皆种以不同形相禅说”,在“种子说”的基础上解释为“无尽缘起说”。所谓“无尽缘起”即是对“此有故彼有”的缘起道理在相互观待依持,彼此相摄相入的“事事无碍”、“理事无碍”意义上的进一步发挥,就其实质而言是对唯识学四缘中“增上缘”的极端发展。诚如吕激先生所云,华严的“无尽缘起”说是把佛家所讲的缘起归结于佛境。(36)因此,“无尽缘起”说根本上是一种从佛境出发看待世界的方式,或者说是从佛境出发来说明世界的缘起。但章太炎却将此“无尽缘起”说理解为种子或观念之间的相摄相入,他认为,法藏立“无尽缘起”说的用意,与《庄子》“寓言”篇中“万物皆种也,以不同形相禅”的意趣相同,是所谓“万物无不相互为种”之义,“一种一切种”,即是“一即一切,一切即一”。而这正是“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一体”的原理。这三者之间的一致,即是在从原理上说明“万物与我一体”的意义,而“万物与我一体”所要表达的正是万物与我之间的彻底平等义。由于种子之间相摄相入的“相互为种”之义,使得万物之间的分别不再具有实在性,从而也使得打破万物之间的分别、使得万物之间的相互沟通成为可能。正是在此基础之上,缘起的道理被发挥为俗界层次上万物平等的原理。
如果以“相互为种”之义为内涵的“无尽缘起”说更为充分地说明了世界的缘起性质,那么对世界的缘起性质的认识与“真心”或“真我”有何关系呢?或者说缘起的道理作为说明俗界的原理与“真界”的发明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关联呢?“真心”或“真我”对于“缘起”的意义何在呢?在他看来,“真心”或“真我”的存在首先是为了解决缘起的动因问题。由于“无尽缘起”中相互增上的关系无法解决最终决定的究竟第一因,因此犯有“无穷过”,于是,理解缘起的关键在于要认识到“因缘及果,此三名者,随俗说有,依唯心现,即是心上种子,不可执着说有,是故缘生亦是假说”,也就是说,缘起其实仅是心上种子变现,“随俗说有”而不可执着为有,是“依唯心现”。缘起的动因需要从心体中寻找。他说:
今说生之所因,还待前生,展转相推,第一生因,唯心不觉,不觉故动,动则有生,而彼心体非从因缘和合而生,所以尔者,世识三时,即心种子,因果之识,亦心种子,不以前后因果而有心,唯依心而成前后因果。如是说无因论,乃成无过。(37)
作为心体的藏识是超越因果的,由于因果、三时都首先是作为心种子而存在于心体之中,所以心体应该不在缘起当中,非从“因缘和合”而生,反而前后因果却“依心而成”,心体是缘起所依。心体对缘起的依持作用,是所谓“唯心不觉,不觉故动,动则有生”,这种作用具有“第一生因”的意义,但又不是在因果关系意义上的生因,而是一种“万物之生,皆其自化,则无作者”意义上的作者生因,因此也可以看作是“无因论”。于是,我们发现在章太炎这里,心体与缘起的关系,由于未能完整地理解唯识学中四缘说的内涵,不能明确区分所缘缘义与因缘义、增上缘义的关系,“生因”与“无因”的关系没有得到彻底的清理,从而将阿赖耶识缘起依稀仿佛地替换成了真如缘起的不变随缘与随缘不变。
不过,问题在于章太炎对真如缘起说进行了自己的创造性发挥,从而创造性地安顿了真心与缘起或者说真与俗的关系。这就是他的“和之以天倪”的原理。
所谓“天倪”,即是所谓“自然之分”,而“自然之分”即“种子”,他说:
言天倪者,直训其义,即是自然之分。……即种子识。然则自然之分,即种种界法尔而有者也,彼种子义说,为相名分别习气,而与色根器界有殊。令若废诠谈旨,色根器界还即相分,自亦摄在种子之中。《寓言篇》云:“万物皆种也,以不同形相禅,始卒若环,莫得其伦,是谓天均。天均者,天倪也。”是则所谓无尽缘起。色根器界,相名分别,悉号为种,即天倪义。若就相名分别习气计之,此即成心,此即原型观念,一切情想思慧,腾掉无方,而绳御所限,不可窜轶,平议百家,莫不持此。所以者何?诸有知见,若浅若深,悉依此种子而现世识、处识、相识、数识、作用识、因果识,乃至我识,此七事者,情想之虎落,智术之垣苑。是故有果无因,有相无体,现色不住于空间,未来乃先于现在,为人所不能念,自不故为矫乱及寐语病狂者,凡诸儒林白衣,大匠祆师,所论纵无全是,必不全非边见,但得中见一部,不能悉与中见反也。倒见但误以倒为正,不能竟与正见离也。故离天磨珍说,随其高下,釁瑕沓见,而亦终与三等俗谛相会,转益增胜,还与自然种子角议。所以者何?一种子与多种子相摄,此种子与彼种子相倾,相摄非具即此见具,相倾故碍转得无碍,故诸局于俗谛者,观其会通,随亦呈露真谛。然彼数辈,自未发蒙,必相与争明,则迫光成暗,苟纳约自牖,而精象回旋,以此晓了,受者当无膏肓之疾,此说同异之辩,不能相正,独有和以天倪。第一章说和以是非,休乎天钧,此谓两行,已示其耑萌矣。康德批判哲学,《华严》之事理无碍,事事无碍,乃庄生所笼罩,自非天下至精,其孰能与于此尔。则天倪所证,宁独生空,固有法空,即彼我执法执,亦不离是真妄一原,假实相荡,又非徒以自悟,乃更为悟他之齐斧也。(38)
所谓天倪即是种子识,“自然之分”即是种子识中所藏之种子,即“种种界法尔而有者”。这些种子不仅包含相名分别习气,更将色根器界收摄于内。“色根器界,相名分别,悉号为种,即天倪义”,这也就是说,“天倪”即是种子,亦即原型观念。所谓无尽缘起,即是在“万物皆种”意义上的相摄相入,实质上是万物在“原型观念”层次上的彼此之间相摄无碍,而所谓“万物一体”也正是在“原型观念”层次上的一切种子之间的相摄相入意义上的“一体”。于是我们可以建立起一种从“一体”出发观照万物差别的基本视角,认识到差别其实是可以在其原型观念或种子的意义上相摄相入的,因此,差别并不绝对;但同时,“一体”也并不能取代差别,因为“种子”应时而现演为“差别”是必要的,否则将没有所谓的“万物”。将这样一种“世界观”用之于衡量思想议论,我们便发现,“百家议论”在实质上即是“一切情想思慧”,虽“腾掉无方”,但它却仍然受“原型观念”之绳御限制,出于原型观念。因此,持此原型观念即可以“平议百家议论”,因为,“诸有知见”,不论其“若浅若深”,就其实质而言“悉依此种子而现世识、处识、相识、数识、作用识、因果识,乃至我识”,这七个方面,所有“情想”与“智术”都不出此范围。在此意义上,不论是“诸儒林白衣”还是“大匠祆师”,其所论即使并非“全是”,但必定不会全无所见。恰如“边见”与“中见”、“倒见”与“正见”的关系,总是相互依赖。其根据即是种子之间的本来相互依赖、相摄相入,“一种子与多种子相摄,此种子与彼种子相倾,相摄非具即此见具,相倾故碍转得无碍”。于是,对于差别可以在种子之间的相互依赖相摄相入的意义上寻其会通的可能。因此,即使是局于俗谛者,只要观其会通,也总会呈露真谛。因此对待百家议论的态度,不应该是“相与争明,迫光成暗”,绝对化差别和对立,而是能够从事事无碍、理事无碍的无尽缘起之理出发,观其相摄相入之会通,“和以是非”。在“会通”的基础之上,实际上差别也具有了如其实际的根据,亦即根据万物“自然之分”,来重新安顿万物和世界,此即“和以天倪”。“天倪”所证的世界,是“真妄一原,假实相荡”的世界。
章太炎在《国故论衡》中的《原道》篇里通过韩非“道”与“理”的关系来说明“真如”的不同层次:
韩非曰:“道者,万物之所然,万理之所稽也。理者,成物之文;道者,万物之所以成。物有理不可以相薄,而道尽稽万物之理,故不得不化。不得不化,故无常操;无常操,是以死生气禀焉,万智斟酌焉,万事废兴焉。天得之以高,地得之以藏……道与尧舜俱智,与接舆俱狂,与桀纣俱灭,与汤武俱昌。譬诸饮水,溺之多饮之即死,渴者适饮之即生……”此其言道,犹浮屠之言如耶(译皆作“真如”,然本但一“如”字)。有差别,此谓理;无差别,此谓道。死生成败皆道也。(39)
道是万理之所稽,理与理之间在道的层次上是“不可以相薄”的,若从道的层次上来看万物之理,都是不得不然的自然自化之理,因此,万物之理各有不同;然而万物之理在都是不得不然、不得不化而成的意义上,则同归于道。如果说“道”是真如的话,那么真如便是总稽差别之理者,为差别之理所共具;同样的理便是真如在万物中所展现的明其差别的理。道是共相之道,理是自相之理;前者是作为共相的真如;后者是作为自相的真如。无论自相还是共相,无论无差别的道还是有差别的理,都是真如的展现形式。真如在道的意义上是共相,真如在理的意义上是自相。这也就是说,差别之理亦是真如的形式之一。正是在此意义上,章太炎又进一步发挥和之以天倪的道理,最终建立起了真俗两界关系的最高原理,真俗平等的原理。
“和之以天倪”是在破封执、去分别、证真我的前提下,以种子或原型观念为根据会通万物差别,并在会通之后重新安立“俗界”的原理,是说明“俗”之所以为“俗”的原理。从种子或原型观念出发,“俗界”的学说或事物,一方面可以打破其差别的绝对性,另一方面则可获得从其自身限定性条件出发的理解和安排,从而获致其各自存在的理由。在此基础之上,我们便可以引申出“和之以天倪”的第三层含义,亦即在真俗各有自足自立道理的意义上重新安排真俗之间的关系,使得“俗界”也由此获得其相对“真界”的自足自立的价值。若根据唯识学中的三性说来说明,“和之以天倪”首先在破除遍计所执,其次在破执的前提下显现圆成实性的真实,同时,在此破执显真当中,安立起世界的依他起的缘起性来。如果说遍计所执性须彻底破除的话,那么依他起性则具有自身的自立性,尽管并非圆成实性意义上的绝对真实,但却是具有真实性和清净性的存在,尽管其存在是有条件的但也因而其存在是可以从条件出发加以说明其具体道理的。于是,通过“天倪”的三层内涵,章太炎最终圆满表达了“毕竟平等”的原理。首先,通过破执显真,在破除固有价值秩序的前提下,确立起每一个体自足自立、绝对无待的价值,从而确立起无所依傍的自尊无畏的道德,这即是“不齐而齐”;其次,则能够从每一个体所依赖的具体限定性条件出发,来理解其所以如此的缘由,从而在相互依赖、相摄相入的无尽缘起意义上确立起一个并不相互冲突而是能够相互会通的俗界,这即是“物各付物”;第三,则经过再次辩证,在真与俗之间确立起更高一重的综合“物各付物”与“不齐而齐”的平等关系:俗与真一样,都是可以自足自立的领域,因此,俗与真之间也是平等的。在这里,章太炎并未特别在圆成实性和依他起性之间明确一种真实性的层级关系,而是彻底贯彻平等的精神,确立起了最高意义上的“真俗平等”观。如果套用唯识学中根本智与后得智的关系来说明的话,所谓“真俗平等”即是后得智的境界。经过后得智所看到的世界,是一个“真妄一原”、“事事无碍”的佛境世界。世界仍然是这个世界,但却具有了不同的意义,成为展现真实的世界,成为真实世界的一种“具体”形式。在克服了将“俗”执着为“俗”的遍计所执之后,“俗”便具有了在一定条件下展现“真”的意味。因此,“俗”虽然并非就是“真”,但却具有了“真”性,是“真”的一种“具体”形式。同时“真”也只有在“俗”当中才能够克服其“真际”的抽象性,具有其“实际”而具体的意义。这正是佛教当中从共相智向自相智的跃升。因此,“真俗平等”便成为齐物平等的终极意义,它意味着平等必须是“具体”而“实际”的平等。平等不是抽象的平等,不是停留于“真际”理想中的平等,而是能够穿透事物之间的隔别,在具体事物之间发生的实际而具体的平等。严格说来,这种具体的平等只发生在物物或人人相对的具体情境当中,是“物各付物”之后的价值对等性。这才是“不齐而齐”。
真正的平等不仅不是抽象的“一往平等”意义上的普遍平等主义,而且也并非抽象的“自在平等”意义上的多元平等主义,而是发生在个别与个别、具体与具体之间的“不齐而齐”的价值对等性,那是一种因为差异所以平等的平等性。这种意义上的平等是一种“尽性”意义上的平等,而非“适性”意义上的平等。“各尽其性”与“各适其性”的区别,在于是否能够给予个体一种充量发展且自作主宰的条件,在于是否接受和承认外在秩序所规定的“性”的内涵;只有这种意义上的平等性才真正建立起了个体之特别性的价值。(40)这三层平等中的每一层都具有了齐物平等的意涵,而只有彻底实现了三层次的平等才是齐物理想的最终实现。只有在“不齐为齐”的平等观之下,个体乃至文明的价值自主性才能够真正建立起来。而这种平等性不是对启蒙价值的一次元的简单回应,而是在二次元的层次上对启蒙价值的重塑:只有从个体乃至文明价值的具体的自主性出发,而不是从任何一元论的普遍主义的抽象宣称出发,也不是从任何多元主义的相对主义态度出发,启蒙的价值才是可欲的。
实际上在这三个层次的平等之间是存在着运用方向的不同的。恰如章太炎所说,“转此成心则成智,顺此成心则解纷”,第一层次的平等,即是“转此成心则成智”意义上的平等,它是通过一种否定性的、批判性的方式确立起的个体自足自立的价值,并进而带来所谓“不齐而齐”之平等结果。而第二第三两个层次的平等则可以说是“顺此成心以解纷”,是以一种建设性的方式理解和安排世界。这样两种方式其实也正相应着章太炎思想形成的不同阶段:前者是他转俗成真的阶段,也是他的思想形成中着眼于“破执求真”的批判性时期;后者则是他“回真向俗”的阶段,也是他的思想形成中趋向于“以真立俗”的建设性时期。可见,《齐物论释》中论证平等的三个层次其实呼应着他一生学思、实践的两个阶段,是对他一生学思、实践的理论升华。齐物哲学本身即是对支配他一生学思、实践的生命和思想轴心的理论自觉,也正如侯外庐所言,他的哲学的创辟,是他的“人格性的创造”。(41)
注释:
①竹内好:《思想的形成》,《鲁迅》,《近代的超克》(李冬木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第45-46页。
②关于思想史研究中一次元与二次元的关系问题,请参见孙歌:《竹内好的悖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6-37页。
③竹内好:《政治与文学》,《鲁迅》,同上书,第110页。译文参考孙歌的译文。
④姜义华:《章太炎思想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52页。
⑤姚奠中、董国炎:《章太炎学术年谱》,山西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88页。
⑥章太炎:《自述学术次第》,《中国现代学术经典》之《章太炎卷》,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642-643页。
⑦章太炎:《菿汉微言》,《章氏丛书》下册,第960页,世界书局本。
⑧章太炎:《菿汉微言》,同上书,第961页。
⑨同上书,第961页。
⑩章太炎:《中国通史叙例》,《訄书》重订本《哀清史》第六十,《章太炎全集》第三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325页。
(11)章太炎:《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录》,《章太炎政论选集》,中华书局,1977年,第269-280页。
(12)章太炎:《俱分进化论》,《太炎文录初编》别录卷二,《章太炎全集》第四卷,第386-395页。
(13)章太炎:《俱分进化论》,《章太炎全集》第四卷,第395页。
(14)章太炎:《自述学术次第》,《中国现代学术经典章太炎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642页。
(15)章太炎:《齐物论释序》,《章太炎全集》第六卷,第3页。
(16)宗仰:《齐物论释》后序,同上,第58页。
(17)这一理论构拟主要依据的是《齐物论释定本》。
(18)章太炎:《齐物论释定本》之《释篇题》,《章太炎全集》第六卷,第61页。
(19)章太炎:《齐物论释定本》,第70页。
(20)章太炎:《齐物论释定本》《释篇题》,第61页。
(21)章太炎:《论佛法与宗教、哲学以及现实之关系》,载《中国哲学》第六辑,308页,三联书店1981年。
(22)郭象:《逍遥游注》,第9页,《庄子》,台湾艺文印书馆印行。
(23)郭象:《齐物论注》,第38页,《庄子》,台湾艺文印书馆印行。
(24)郭象:《齐物论注》,第38页,《庄子》,台湾艺文印书馆印行。
(25)郭象:《齐物论注》,第31页,《庄子》,台湾艺文印书馆印行。
(26)郭象:《齐物论注》,第67页,《庄子》,台湾艺文印书馆印行。
(27)郭象:《齐物论注》,第45页,《庄子》,台湾艺文印书馆印行。
(28)郭象:《逍遥游注》,第16页,《庄子》,台湾艺文印书馆印行。
(29)钱穆:《魏晋玄学与南渡清谈》,《中国学术思想史沦丛》卷三,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69页。
(30)钱穆:《魏晋玄学与南渡清谈》,《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卷三,第69页。
(31)侯外庐:《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史》,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69-270页。
(32)章太炎:《齐物论释定本》,第70页。
(33)章太炎:《菿汉微言》,《章氏丛书》下册,第926页,世界书局本。
(34)章太炎:《齐物论释定本》,第71页。
(35)章太炎:《齐物论释定本》,第73页。
(36)吕澂:《中国佛学源流略讲》,中华书局,1991年,第199页。
(37)章太炎:《齐物论释定本》,第113页。
(38)章太炎:《齐物论释定本》,第108页。
(39)章太炎:《原道》下,《国故论衡》卷下,中华书局,2008年,第515页。
(40)也有学者将这种平等性称之为“个别性”(individuality)。参见美国学者穆惟仁(Viren Muthy)的研究:The Philosophy of Zhang Taiyan:The Resistance of Consciousness (Leiden,Brill,2011).
(41)侯外庐:《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史》,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1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