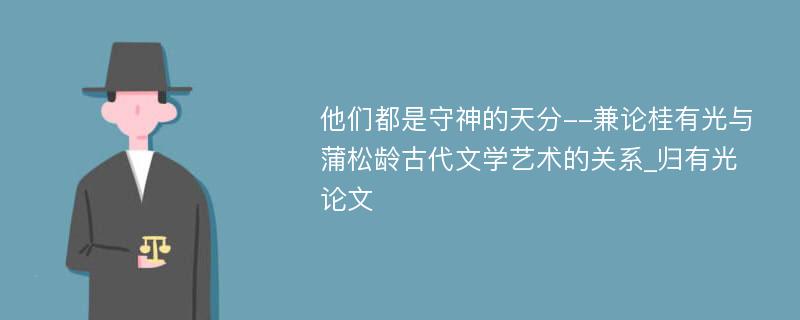
彼皆绝代才 形去留其神——归有光与蒲松龄古文艺术相通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古文论文,去留论文,有光论文,蒲松龄论文,艺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6 文献标识码:A
归有光和蒲松龄是时隔百年、身处两代的两位伟大的文学家,归有光以古文见长,而蒲松龄以小说独步,所以人多围绕在蒲松龄“文言短篇小说之王”的光环下,而对其“苍润特出,秀拔天半”(注:清朱缃《〈聊斋文集〉题辞》,见盛伟编《蒲松龄全集》(第三册)。)的古文却少有论及。本人对两位大家心慕已久,多读其文发现二者在心态上相似处极多(见拙作《古文寓意与小说言情——归有光与蒲松龄心态相似论》,载《蒲松龄研究》2001年第1期)。这些人性的光辉折射于古文创作,便在其艺术魅力上产生了许多相通之处。蒲松龄在《聊斋文集·自序》中说:“余少失严训,辄喜东涂西抹,每于无人处时,私以古文自效。”清代孙济奎也说:“而先生诗、古文辞,亦自成一家,不愧于古作者。”(注:《〈聊斋文集〉跋》,见盛伟《蒲松龄全集》(第二册)。)这里提到的“古文”、“古作者”虽然指称广泛,但归有光及其古文无疑是首列其中的。我们知道,康熙年间,《震川先生集》付梓流传,此时正当蒲松龄的青年时代,作为一个敏感的文人,他不能不受当时笼罩文坛的归有光文学主张和创作实践的影响。蒲松龄曾在其《聊斋志异·司文郎》一文中,借瞽僧之口,鲜明地表达了自己对归有光的尊崇之情,只是蒲松龄终生不及一第,布衣荒儒,难入赫赫宗派之殿堂,虽宗归自命,却不为人所认同,但其承继相通之处,历历文中,终不可掩,以下我们将分四点详析之。
小文洁体,不舍细节
我们知道,由唐宋而下,古代散文作品大多已由秦汉时代的鸿篇巨制变得相对短小,至晚明的小品文,这一趋势发展到高潮。到清代以戴名世起的桐城文人更在理论与创作领域大力提倡小文章。古代散文形制上的这种变化,一方面是与散文有意无意地渐渐疏离载道、实用的功利目的,转而注重对散文家本人的愿望、情感、理想的表达息息相关。另一方面,注重细节、善于白描的《史记》笔法和小说手法在明中叶以后对古文创作产生了巨大影响。这两方面同时也对归有光和蒲松龄古文形制和描写方式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从而形成了许多相通之处。归有光和蒲松龄由于自己足羁一隅的狭小生活范围和连年不第的曲折人生道路,产生了眼界收束思维的现象,从而限制了其作品的取材范围,多描写身边人、平凡事,表达了对家乡的依恋和对故园的怀念,形成了其细腻动人、追忆自问的内敛心态。这种由文以载道到直抒胸臆的目的转换,使得他们的古文呈现出一种短小紧凑、洁而有体的形制特点。
《寒花葬志》是归有光的千古名篇,其文仅仅一百一十二字,正是历历可数,但却字字珠玑。在这篇小文中,我们看见稚嫩活泼的小姑娘寒花“曳深绿布裳”的轻盈步态,她削荸荠却“持去,不与”作者的调皮举动,她“即饭,目眶冉冉动”的憨然之态。作者锁定角度,精选细节,白描深画,寥寥几笔,一个活的寒花便于主体之中呼之欲出了。但是,归有光并不想仅让我们的感受止于所见,他在文末告诉我们寒花已逝,“事我而不卒,命也夫”。文至此戛然而止,一篇小文就这样涵盖了生的意趣与死的无情,鲜活的短暂与冰冷的永恒,这种对于美好的刻画愈细愈小,这种流逝的悲哀就愈痛愈恸,文愈小,而藏于深海的冰川则愈给读者更为无限的感发空间,小文而为至文,其妙就在于此。
蒲松龄的古文形制虽稍长于归文,但其摹物写心,更是活现逼真。在其《龙泉桥碑》一文中,蒲松龄写尽了人行险途之态:
淄,山邑也,率倾侧少坦途。或升之高,则以腕捺膝,力作努;其下也,腰膂无屈骨,一踵踔地,橐橐然。每步,须发为颤;少纵,则奔不自禁。
读其文,顿觉心胆俱提,屏息止气,跟随文走,一收一纵。真正是令读者“须发为颤”。整个路险、人惊、心惧皆用白描手法,淋漓尽致地表现在这一捺膝、一踔地的细节之中。
由此可见,归有光和蒲松龄之所以能从明中叶以后众多擅写小文的大家中脱颖而出,一方面是因为他们本身的心态气质与古文体制的发展相契合,另一方面却源于他们对这种小文洁体的恰如其分的把握,即以典型情节充实之,以白描手法刻画之,使得文虽小而不浅,言虽短而意长,而这种细节和白描手法的成功运用无疑是借鉴了《史记》笔法和小说手法,无论他们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
闻一多先生在《神话与诗·文学历史动向》中认为:
明代的主潮是小说,《先妣事略》、《寒花葬志》和《项脊轩志》的作者归有光,采取了小说的以寻常人物的日常生活为描写对象的态度和刻画景物的技巧,总算是沾上了点时代潮流的边儿(他自己以为是读《史记》读来的,那是自欺欺人的话。)
闻先生认为:归有光的小文之所以突出,在于他适应时代文学潮流,吸收了许多小说的写作技巧,这当然是正确的,但他把归有光对于《史记》笔法和小说手法的借鉴截然分开并否定前者,这是不太恰当的。
我们知道,古代散文中的史传文一支,同时又是小说文体的重要渊源之一。小说与古文的这种同源异流现象,使得“小说手法”对古文创作的渗透几乎是无法抵御的,正如清人平步青在《霞外捃屑》中所言:“古文写生逼肖妙处最涉小说家数。”尤其是进入明中叶以后,随着小说创作的繁荣,越来越多的古文家在自己的创作中借鉴了“小说笔法”。作为古文家的归有光推崇《史记》,但是他在《归震川史记图识凡例》中也认为《史记》与被传统文人轻贱的平话小说在叙事方式、描写手法等方面有异曲同工之妙,也正是由于吸取了从《史记》到平话小说所采用的细腻传神的白描手法,归有光才能不规于唐宋八家的成法,对古文的写法作出了创造性的突破,创作出了如《先妣事略》、《寒花葬志》和《项脊轩志》等一批情辞并得、凄恻动人的佳作,因此,否定任何一方面都是片面的。
而蒲松龄作为一代文学大师,更是一身而兼古文家与小说家之二任。他一方面沉浸于对传统《史记》笔法的痴迷,坦言“余少时,最爱《游侠传》,五夜挑灯,恒以一斗酒佐读”(注:蒲松龄《题吴木欣〈班马论〉》。),另一方面又在《聊斋志异》的创作中达到了文言小说创作手法的颠峰。因此,如果说他的古文对于《史记》笔法的借鉴是传统文体自身潜移默化的浸濡,那么,他的古文创作艺术与小说手法便如一剑之双刃,反复之间,本是一体,无所谓谁先谁后,谁大谁小。但就本文来说,我们还是要从古文的角度来审视他的小说手法对其古文创作艺术的渗透,其中最突出的就是细节刻画和白描手法了。触及此处,我们脑海中很容易便会浮现出《聊斋志异》中婴宁的形象:她以“视碧桃开未”作离开的借口,出门前“以袖掩口”、“细碎莲步”,出门后放开莺喉,纵声大笑,神情意志,“如乎人人意中所欲出”(注:冯镇峦《读聊斋杂说》。),如此精妙的言行细节描写,真可谓“诸法俱备,无妙不臻”(注:冯镇峦《读聊斋杂说》。)。这种炉火纯青的艺术手法自然地融入了其古文创作。《责白髭文》是一篇学司马迁传记文,构思文风近于韩愈《毛颖传》的作品,近似于唐代的一种传奇小说。在文中蒲松龄与拟人化形象髭神反复辩难,文辞犀利。作者滔滔雄辩,其气势不让仲孺骂座,其行文浩如韩文之海;髭神辞穷而“逡巡”、“瞠目”、“拱手”告败,其尴尬之态真是惟妙惟肖,细节白描之处精彩叠出,跃然纸上,备得《聊斋》之神。所以有人说:“为文之法,得此(《聊斋》)益悟”(注:清但明伦《聊斋志异·序》。),更有甚者说:“《聊斋志异》一书,为近代说部珍品,几乎家弦户诵,甚至为研文之用。”(注:《负暄絮语》。)由此可见,蒲松龄在古文创作中对于小说手法的借鉴已为当时文人所普遍接受并加以体会研学了。
似不经意,余韵悠长
明代王锡爵曾在《明归太朴有光墓志铭》中赞归文曰:“所谓抒写怀抱之文,温润典丽,如清庙之瑟,一唱三叹,无意于感人,而欢愉惨恻之思,溢于言语之外。”即于不经意处说不经意之话,营造一种意境,余韵悠长,这是归有光古文艺术的一个显著特点,同时也为蒲松龄的古文创作所继承。而这种似不经意、余韵悠长的艺术特色更多地源于他们对文章结尾的艺术处理。
归有光在其《文章指南》中仅比较著名的结尾处理方法就总结了至少五种:结尾垂戒法;结尾括应法;结尾推广法;结尾推原法;结尾有余法。而此处我们提到就是“结尾有余法”。对此,归有光这样阐释:“人于结束处多忽略,谓文之用工,不在尾,殊不知一篇命脉归束在此,须要言有尽而意无穷,如清庙三叹而有余音,方为妙手。”在《项脊轩志》的结尾处,他这样写道:“庭有楷杷树,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今已亭亭如盖矣。”作者在回忆昔日与妻把手教书,而当初植树之人却奄然而逝,人去树存,睹树思人,其所营造的孤苦凄凉之境,萦绕着一种哀而不绝的余韵,正是言有尽而意无穷。又如《野鹤轩记》以“夜来风雨,崖崩不落,山鬼夜号”作结所营造的一种凄厉之境;《张自新传》结尾忽现鹘突:“自新家在新洋江口,风雨之夜,江涛有声,震动数里,野老相语,自以为自新不亡云。”笔调慷慨,夺人魂魄,将张自新的形象立体化地呈现于读者之前,余韵悲怆,苍凉难禁。
如果说归有光是先有一种关于结尾处理的理论框架,然后充实以自己的真情实感,从而产生了这种似不经意、余韵悠长的艺术效果,那么蒲松龄则同工而异曲了。蒲松龄对于文章韵与境的看法比较个性化,他没有先从文法的出发点考虑,而是源于自己精神气质的自发而为,纵荡之中,再规以为文之法,然后达到余韵悠长之境界。
蒲松龄在《聊斋自志》中道:“自鸣天籁,不择好音,有由然矣。”而要理解他的深心,只有去深刻领会庄子对于“天籁”之所指。在《庄子·齐物论》中,有“人籁”、“地籁”、“天籁”之说。依庄子解释,人籁就是“比竹”,即人吹箫管所发出的声响,地籁是指大地“众窍”在风吹雨打中发出的声响。这都是指具体的,可见可闻的物象。而“天籁”却不是“别有一物”(参见《郭注》),它本身就存在于“人籁”、“地籁”之中,但又跃出它们之上。它是指以深、远、玄、虚、无限为特征的一种精神状态。纳入艺术中来看,这正是中国艺术哲学、艺术精神中的精粹蕴义[1]。蒲松龄素嗜庄子,以为“千古奇文,至庄、列止矣。”(注:蒲松龄《〈庄列选略〉小引》。)庄子的艺术精神已经融入他的创作思想中,以至于认为“时文家窃其唾余,便觉改观”。但是,他崇尚的也只是庄子的艺术精神,而对其哲学却颇不以为然,认为“因其文之可爱而探之于冥冥者则大愚”(注:蒲松龄《〈庄列选略〉小引》。),并曰:“以庄、列之奇才,今并驱而就七十子之列,宁非快事哉!”(注:蒲松龄《〈庄列选略〉小引》。)。即以儒家之温柔敦厚怨而不怒之道,来中和庄列深玄远虚之才,再加上他颇为自得的为文之法“文贵宕,宕得要灵……文贵煞,煞得要稳合”(注:蒲松龄《作文管见》。)等,这样一纵一收之下,御风而行的蒲松龄翻然落地,吟咏之间便促和妙远,意在余韵了。
《述刘氏行实》是蒲松龄为纪念发妻刘妻所写的一篇文章,在结尾处他这样写道:“先是(刘氏)六十时,便促营寿域。或有货柏材者,松龄购之曰:‘谁先逝者占此。’刘氏笑云:‘此殆为我设,但不自知何日耳。’殁后,周身具备,乃于十月十五日午时葬焉。”相濡以沫的老伴倏然而逝,实在令蒲松龄悲难自抑,甚而至于“迩来倍觉无生趣,死者方为快活人”(注:蒲松龄《悼内诗》(之六)。)。大悲而为至文,因此他在以细腻的笔法回忆了刘氏操劳艰苦、任劳任怨的一生之后,并没有在文末大放悲声,而是以回忆他与刘氏生前买寿域时的几句戏言淡然而结,正是“昔日戏言身后意,今朝都到眼前来”(注:元稹《三遣悲怀》之三。)。言犹在耳却生死异途,文虽止而意难断,至悲至痛绵延文中,寥寥数语,斯韵、斯境、斯人、斯情,不以日久而淡,不以地远而隔,视以归文“亭亭如盖”之语,谁能不叹两先生为文华双绝!如此妙笔在蒲文中比比皆是,如《聊斋自志》中之“青林黑塞”之境,《毕公权〈困佣诗〉跋》中“鬼才之叹”皆为神来之笔,余韵悠长。
可见,我们所谓归有光与蒲松龄古文创作的不经意处绝非信手拈来,而是经过千锤百炼,才殊途同归,最终达到一种余韵悠长的境界,正所谓“极炼如不炼,出色而本色”(注:刘熙载《艺概》。)。
长于用典,富于唱叹
归有光和蒲松龄都自幼博览群书,聪颖强记,师法众家,绝不同于以“记诵套子”求取功名的文人。清代钱谦益曾评归有光曰:“弱冠尽通《六经》、《三史》、八大家之书。浸渍演迤,蔚为大儒。”(注:钱谦益《震川先生小传》,见周本惇校点《震川先生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正因为有这样的学问功底,所以他在行文中能信手拈来,时常用典,其自然贴切,恰如使盐入水,不仅能救文章之平淡,更有温润典雅之美。《答余质甫书》便是非常典型的一篇,在这篇书牍体古文中,归有光在心潮澎湃、浪然雪涕的状态下向知心朋友诉说自己的满腔悲愤。短短一篇小文中连用了《诗经》中的《柏舟》、《绿衣》、《谷风》等典,其中《柏舟》、《绿衣》都是咏叹主人公受排挤、仁而不遇、忧伤愤怒的作品。归有光以此自喻都是为了表明自己愤世嫉俗的为人处世态度。而引用《谷风》中“我躬不阅,遑恤我后”的弃妇之语,更是以此来映照自己怀才不遇、凄凉伤感的心情。其情极愤而其文法不乱,恰当的用典使文章在纡徐委备之中极尽悲怆苍凉之情,但却避免陷入琐碎之中。动人的故事,优美的诗句,加上作者用心灵所注入的忧伤之情,使得这篇文章极富温润典雅之美。其他如《草庭诗序》、《容春堂记》、《畏垒亭记》、《陶庵记》等都体现着这种美感。
蒲松龄的学术根柢同样是宏博深厚的。我们从其古文用典可知,被他采撷过的古书数目不下几十种。举凡诸子百家、左国史汉、诗经屈赋、唐宋诗文以及历代的小说戏曲、野史笔记,无不一网兼收,洪炉并铸。如其《拟判·漏泄军情大事》:“……项伯与子房有旧,遂成联夜之婚姻;子反听华元登床,竟告军情之隐秘……”,其中项伯泄楚之军情于张良,见《史记·项羽本纪》;子反泄楚之军情于华元,见《公羊传·宣公十五年》。再如《拟判·夜禁》:“……城外寒山半夜钟,尚复披星而往;枝头啼鸟三更月,依然衣锦而行。若非待鸡鸣于函关,即欲盗狐裘于内寝……”,其中“寒山钟”“枝啼鸟”用张继《枫桥夜泊》典;“待鸡鸣”“盗狐裘”见《史记·孟尝君列传》;“衣锦夜行”则见《史记·项羽本纪》。其他至如《为花神讨封姨檄》、《陈淑卿小像题辞》、《张视旋〈悼亡草〉题词》等,全篇几乎句句用典,这些典故具有深刻的历史内涵,丰富了文章的内容,增添了文章词采,提高了作品的艺术性。
同时,相似的经历,共同的苦难,又使这两位内敛型的古文家满腹“天凉好个秋”的心态,欲言之,又止之,问天不语,以歌代哭,回肠荡气,形之于文,便如“清庙之瑟,一唱三叹”。在《娄曲新居记》中,归有光在前两段比较汉代马援的故事和班超“不敢望到酒泉郡,但愿生入玉门关”的哀叹后,转而在下段之始长叹:“嗟夫,人生百年之内,为日有几?欲穷万里之道,日驰骛而不知止者,何也?”从而把文章自然地转入对主人公沈翁的介绍,并从中抒发了自己白首无为、首丘依风的感叹,使文章在音韵跌宕之中波澜壮阔,平添悲壮之色。又如《先妣事略》中“世乃有无母之人,天乎,痛哉”的浩叹使文章在结尾处艺术和情感同时达到高潮。《二二圹志》中所云“呜呼!余自乙未以来,多在外,吾女生既不知,而死又不及见,可哀也已!”更是在唱叹之中贯穿着强烈的感情起伏,表达了深沉的悲伤,其中夹杂着多少对于幼女二二生不知、死不见的莫大愧憾。
蒲松龄古文中的唱叹之意稍为直白,但其感人之力却不稍逊于归有光。如在《族谱引》一文中,他痛心于封建大家族亲情荡然、分崩离析的现状,愤而写道:“自一人起而鱼肉之,遂大半离逖而一乡少,又一人出而蹂躏之,遂举族四散而一乡空矣。积至今日,尚忍言哉!呜呼!”面对家族的败落,蒲松龄心不忍之,有力却不足,这时的他也只能长太息以掩涕,在一唱三叹起伏跌宕之中寻求一点儿心灵的安慰了。而在《聊斋》中,他就更是长叹若泣了:
……独是子夜荧荧,灯昏欲蕊;萧斋瑟瑟,案冷疑冰,集腋为裘,妄续幽冥之录;浮白载笔,仅成孤愤之书;寄托如此,亦足悲矣!嗟乎!惊霜寒雀,抱树无温;吊月秋虫,偎栏自热;知我者,其在青林黑塞间乎!
百字小文,连连三叹,正是音扬之,顿挫之,如旷晓凄角,静夜清瑟,声弦一发,心神为颤。不禁使人感叹文人最苦,终生难脱昏灯冷案之子夜,却时时难忘红袖添香之良宵;鬻文之力不足以糊一家之饿口,孤仁之心定欲乎拯万民于倒悬;万人白眼,荷戟徘徊,生前寥落,死后凄凉;待到洛阳纸贵日,却是一抔黄土掩风流。写者叹,读者叹,在这种情感的激荡共鸣中,蒲氏之叹已超越个体而升华为千古文人之浩然长叹!贺拉斯说得好:“必须按作者的愿望,左右读者的心灵。你自己先要笑,才能引起别人脸上的笑容,同样,你自己得哭,才能在别人脸上引起哭的反应。”强烈的触动感和震撼力正是他们唱叹之法的艺术魅力之所在。
理路分明,神法相生
陈柱曾指出:“故明清两代,实可谓以八股为文化之时代焉。此时代之古文,时受八股之影响不少;盖无人不浸淫渐渍于八股之中,自不能不受其陶化也。”[2]归有光和蒲松龄生活于这样的社会文化大背景中,自然也不能例外。但是,他们的古文却没有流于时俗,呆板生硬,面目可憎,而是在法度脉络中透出一股气息神理,更具生命力。其根源就在于他们把握住了时代文学的特征,一方面提取八股文法来陶铸古文的结构行文,另一方面又以古文之神来补救时文内容的腐陋,从而达到一种理路分明、神法相生的艺术境界,并以此来纠正他们周围的一些不良文风。
归有光是明中叶的制义大家,甚至被推为“制义百世不祧之宗”(注:章学诚《文史通义》,见《章学诚遗书》,北京:文物出版社,1976。),他一直在理论和实践中致力于时文文法与古文神理的结合。黄宗羲在《明文案序》中指出归有光的古文中“时文境界,间或栏入”,钱基博也在《明代文学史》中指出:“唐顺之、归有光纵横轶荡,以时文为古文。”同时,归有光又身处以王世贞为代表的“后七子”文势如日中天之时,整个文坛为“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摹拟之风所笼罩,归有光对此深恶痛绝,直指“今世相尚以琢句为上,自谓欲追秦汉,然不过剽窃齐梁之余,而海内宗之,翕然成风,可为悼叹耳。”(注:归有光《与沈敬甫书》,见周本惇校点《震川先生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对于摹拟剽窃之风的痛心使他对古文神理有自己更为深刻独特的思考:
故余读常不废,时有所见,用著于录。意到即笔不能留,昔人所谓兔起鹘落时也。……余尝谓观书,若画工之有画耳、目、口、鼻,大小、肥瘠无不似者,而人见之,不以为似也,其必有得其形而不得其神者矣。余之读者也,也敢谓得其神,乃有意于以神求之云。(注:归有光《〈尚书别解〉序》,见周本惇校点《震川先生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文中以作画喻观书,对怎样才能达到“意到即笔不能留”之境界作出了解释,其途径就是得其神。如同画工只在外形上极力摹拟不能达到真正的“似”一样,读书和创作要是只停留在字比句拟的阶段也是不成功的,而应“以神求之”。
邓云乡在《清代八股文》中以《项脊轩志》为例探讨了归有光古文中蕴涵的八股文法:“《项脊轩志》开始俨然破题、承题。通篇所写,在作‘旧’字。正是老于八股文手法所写出的文字。”文章题目为“项脊轩志”,而其首句即为“项脊轩,旧南阁子也”,以两行散句点破题义;下二句又说“室仅方丈,可容一人居”,继续拓开题目的意思;在首二句破题处又立出一个“旧”字,下文写作中,紧紧扣住这个“旧”字展开:旧阁子、旧人、旧事、旧心情,以至于全文都笼罩上一层淡淡的沧桑感。可见,这种鲜明的时文结构出现于归有光的古文中,不但没有束缚呆板之嫌,反而在启承转合之中极尽草蛇灰线之能事,寓有法于无法之中,与神并生,从而理路分明,神法相生。
而蒲松龄更是一生与制义为伍,并在少年时就显露出这方面的天赋。顺治十五年(1658年),十九岁的蒲松龄在科举考试中初露峥嵘,应童子试“即以县、府、道三第一补博士弟子员,文名籍籍诸生间”。当时主持道试的山东学道施闰章称赞他的制义文“一勺之多”为“观书如月,运笔如风,有掉臂游行之乐。”(注:参看清人王敬铸《聊斋制艺文》,山东省图书馆藏清刊本.)因此,蒲氏虽然一生佗傺失意于科场,但其作为时文之高手却是不争之论。
同时,与归有光所处“秦汉派”盛行之时相似,蒲松龄所处的清前期是一个“神韵说”弥漫文坛的时期。王士禛所说“神韵”,“大抵为诗歌所具有的一种含蓄蕴藉、空灵淡远的韵味”[3]。可见,神韵之说虽起于诗歌,但其中“含蓄蕴藉、空灵淡远的韵味”作为一种艺术追求与古文神理正是不谋而合,因此,“神韵说”对于文章审美层次的发掘自是功不可没,但稍纵即陷入飘渺的偏颇。正如张海明所说,神韵论者“知道好诗会有余言外,韵味无穷的欣赏效果,却不去考察产生这种效果的内在原因:他们懂得神形有别,妙不可言,却不明白神赖形显,妙不虚生。”[3]正是形之不存,神将焉附,此时纵然妙笔生花,玄之又玄,也不过“但具三毛”、“便空食盐”之流,徒增一笑耳。
而且此时蒲松龄与王士禛之间的关系极为密切。在其《聊斋文集》中就收有《与王司寇阮亭先生》等书信四封,往来问讯论文不绝。作为文学家的蒲松龄不可能无视于“神韵派”的这种偏颇,所以他的古文中对于时文之法的借鉴之处更多一些,也更灵活一些,不拘骈散定字,重在脉络布局,神法之中,气势压人。《募葬郝飞侯序》便是典型的一篇。在文章开头虽为四句偶对而非两句散写,但其作用与破题同,点出“朋友无归,曰‘于我殡’”,即为殡葬之事;下面承题突出“怜才”、“重义”这两个交友原则,然后起讲进一步发挥题意,明确指出郝飞侯正是一个“落落文章”与“轩轩气概”之士,与上文相呼应。下文可谓入题,先以四个对句写出郝飞侯流落而亡,幼子难葬的凄境,然后文入正题,以“名士之下场堪悼,孤儿之皴肤谁怜”六股偶句,为起中后股,其中极尽唱叹离合之功。后省束股,以“如有同志,即列尊名”扣题落下。真正是一篇脉络清晰、无法不备的小制义文,但诵读之间又不觉得生硬呆板,为法所限。既无圣人意,也无夫子言,唯觉音韵顿挫之间一股“解橐”、“瘗逆旅之书生”、“捐资”、“收良朋之骸骨”的书生意气穿行其中,如长虹贯日,令读者击节。朱缃之言最妙:“然则华不注之形模,惟先生文似之。华不注神骨,惟先生文得之。”确实,这种神形结合、神法相生、理路分明所体现的妙处惟有“华不注”山的神姿形模方能譬之。
论而至此,回顾全文,我们主要是通过对文章的形制结构、结尾的艺术处理、语言运用的起伏和文章的内容与表现方法四方面来探讨了归有光和蒲松龄古文创作艺术的相通之处,即:小文洁体、不舍细节;似不经意,余韵悠长;长于用典,富于唱叹;理路分明,神法相生。其中“小文洁体、不舍细节”和“理路分明、神法相生”又是他们的古文借鉴小说和时文手法后所体现的时代文学艺术特征。由此可见,处于明清同一文化大背景之中,蒲松龄虽不能跻身归氏门篱,但他对归文神理的领悟却是提魂摄魄、得其精髓,相通之处,潜行文中,与那些对震川“竞为模仿”,“改头换面而为古文”的“黄茅白苇”之流自是不同。“彼皆绝代才,形去留其神”,我们要于千古大家的承继相通之处有所领悟,则必需要不拘成说,越形求神。
收稿日期:2002-02-10
标签:归有光论文; 蒲松龄论文; 古文论文; 史记论文; 聊斋志异论文; 震川先生集论文; 聊斋志异电视剧论文; 项脊轩志论文; 寒花葬志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