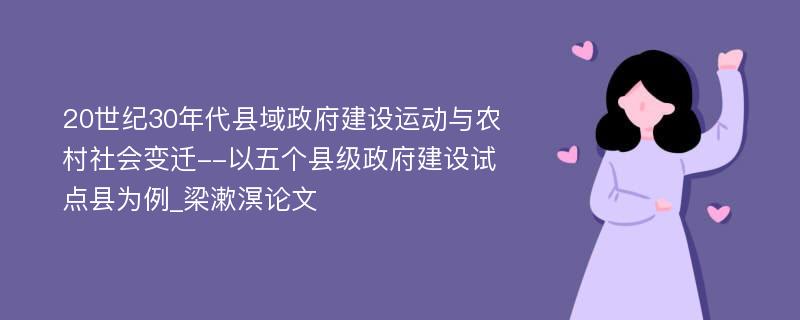
20世纪30年代的县政建设运动与乡村社会变迁——以五个县政建设实验县为基本分析样本,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县政论文,样本论文,乡村论文,年代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64.39;D693.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0214(2003)04-0090-10
从1933年至抗日战争爆发前,南京国民政府与乡村建设派合作掀起了一场县政建设运动,全国有11省积极响应,共有20个县被划为县政建设实验县。经过四年的实验,以江苏省江宁县、浙江省兰溪县、山东省邹平县与菏泽县、河北省定县的实验各具有特点,成就较为突出。迄今为止,史学界对这场运动的研究尚不够深入,其研究视角和成果主要集中在“乡村建设”和平民教育方面,如郑大华的《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李汝东、李志惠的《晏阳初与定县平民教育》(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吴相湘的《晏阳初传》(台湾,台海出版社1994年版)和马东玉的《梁漱溟传》(东方出版社1993年版)等;刘海燕的《30年代国民政府推行县政建设原因探析》(《民国档案》2001年第一期)虽论及县政建设,却只局限于具体原因的探讨。对于县政建设形成的历史过程、时代特征,以及由县政建设而引发的乡村现代化进程的历史鉴训等问题,尚未触及。本文略去了对具体史实的过多罗列,更多地关注于整个运动过程前因后果的系统探讨和它对乡村社会由传统向现代变迁的影响。
一
20世纪前期的中国,“常在‘天灾、人祸、内忧、外患’的四面楚歌之中”[1](p71)。南京国民政府于此时发动县政建设运动,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其一,天灾人祸不断,农村经济濒临崩溃。近代以来,由于文化和社会权威阶层流向城镇,乡村社会出现了文化荒漠化和政权痞化的现象,农业生产方式逐步落伍,缺乏现代化的动力;加之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封建统治者的掠夺、连年的军阀混战和不断的水旱灾害,乡村经济出现了严重的衰落局面。20世纪30年代前后,情况更加恶化。首先是受世界范围内经济危机的影响,衰落的乡村经济雪上加霜。南京国民党政权建立不久,西方就爆发了空前的经济危机。资本主义国家为转嫁经济危机而设置了贸易壁垒,同时利用不平等条约加紧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各国的商品倾销更造成了中国农产品出口受阻,价格猛跌。以米的输入为例,据海关统计,1931年输入12820801担,1932年为26841203担,1933年为25912944担[2](p121)。在价格上,1931年,洋米平均每担比国米低0.22元,1932年低0.84元,1933年低0.26元[3](p35)。由于洋米比国米便宜,几乎完全占据了中国市场,并引起了中国农产品的价格急剧下跌。据国定税则委员会的报告计算,上海各种粮食1933年11月和1932年11月的价格比1931年同期平均下降26%。这三年来棉花的收获量虽逐年上升,比1931年分别增加了8个百分点和35个百分点,其价格却分别下降了1%和19%。在西方国家的贸易壁垒面前,中国农产品的输出也遭到了沉重的打击。1931年中国农产品为4亿2千1百万元,1932年比上年减少了1亿6千8百万元,1933年又比1932年减少了1千2百万元[4](p825、826、827)。其次是更大规模的内战。国民政府成立以后,战争的频度更高,规模更大,在1927-1930年的3年间,动员有10万人以上的内战多达30次。到了1930年春,更是酿成了有百万军队参加、战线绵延数千里、持续达七个月的中原大战,严重破坏了农业的正常生产。随着混战而来的苛捐杂税和兵匪横行,使农村的生存和社会环境进一步恶化。这一时期爆发的自然灾害影响范围更广,损失也更惨重。据文献记载,1928-1929年,冀、豫、陕、鲁、甘、热等省大旱,灾民达5千余万;1931年夏秋之际,华中、华东16省江河泛滥,仅皖、鄂、湘、苏、浙、赣、豫、鲁等八省386县的水患重灾区经济损失就达22.8亿多元,相当于国民党政府当年关、盐两税收入的5倍;[5](p230-231)在空前的天灾人祸打击下,中国农村经济濒临崩溃,并进一步影响到了工商业,使刚刚在中原大战中获胜的蒋介石政权面临着巨大的经济压力。因此,如何应对农村经济濒临崩溃的局面,以增加对乡村资源的占有,是国民党政权发动这场运动的直接动因。
其二,内忧外患不断,国民党政权的统治基础岌岌可危。近代以来,日本对中国一直虎视眈眈。东北易帜以后,日本并不甘心对东北控制利权的丧失;尤其是20年代末世界范围的经济危机发生以后,军国主义势力的膨胀使其加快了对中国侵略的步伐。1931年秋和次年初,日本趁中原大战方靖、中国国防空虚之机,相继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变。在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政策下,东北不足三个月就全部沦陷,淞沪停战更是签下了屈辱之约。东北是中国的资源宝库,失去了东北,使蒋介石政权失去了一块重要的资源集聚地,扰乱了中国人口和商品的正常流动。同时,日本侵略者得陇望蜀的野心更使蒋介石政权感受到了严重的威胁。在内忧方面,对农村的控制不力一直是国民党政权的一块心病。1927年以后,国民党建立了南京政权,并表面上完成了国家的统一,但其统治基础主要在城市,农村一直是其统治的薄弱环节,其在农村推行的所谓“县自治”体制也因制度设计不合理、乡村精英势力的痞化而蜕变为鱼肉百姓的土豪劣绅专政,乡村社会的阶级矛盾激化。例如,1932年11月1日,江苏扬中人民就自发反抗国民党苛捐杂税,万余农民举行暴动,烧毁七户恶霸地主的房屋。12日,该省睢宁县七百多农民又因增加田赋,举行抗捐示威,捣毁了区公所。[6](p460)这种自治体制的推行,“所得结果,与中央及全国人民之所期望,不啻相差百倍”[7]。同时,在大革命中失败的中国共产党利用当时的革命形势,逐渐从城市走向农村,打土豪,分田地,开展土地革命,集聚革命力量,根据地遍及鄂豫皖赣等省的广大农村,严重威胁到了国民党本已十分薄弱的乡村统治基础。另外,在农村经济濒临崩溃的情况下,平教会等一些乡村教育团体和梁漱溟等一些既不满国民党的统治又反对共产党阶级斗争革命方式的乡村改良主义者也开始了乡村建设的工作。“各种乡村建设实验区如雨后春笋般在全国各地涌现”[3](p108),乡建派逐步形成了一股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这股社会力量成为国共两党农村阵地的争夺者,尤其是执政的国民党,把这种乡村建设运动也看成是威胁其统治基础的潜在力量。面对着内忧外患的压力,国民党政权不得不考虑如何加强对乡村社会的控制,以巩固其统治的基础,这也是其发动县政建设运动的根本原因。
基于上述社会历史背景,蒋介石政权认为:“国人深知非安内无以攘外,非充实国力,无以言抵抗。安内也,充实国力也,非安辑地方,培养元气,则仍流于空泛。”[8](p39)为了应对统治危机,加强乡村控制,消弭土地革命,并增强其资源占有效能,国民党政府“受着这种种危难之刺激,深觉民族国家的复兴大业,应从‘庶政’改革入手,而改革庶政的基础,是在于为‘政治骨干’的县政建设”[9](p71) 。这样,在“完成地方自治”的口号下,于20世纪30年代掀起了一场全国性的县政建设运动。
20世纪30年代初乡村建设运动渐成气候,尤其是定县、邹平和无锡三个乡建运动中心的影响日益扩大,引起了南京国民党政权的关注。1931年春,蒋介石邀请晏阳初和梁漱溟南下会谈。据晏阳初回忆,他曾和蒋氏夫妇“说了三个下午三个晚上……蒋先生虽然疲倦上楼休息,还留蒋夫人和我续谈到很晚才得辞出”[10](p295)。后来,中央军校教官毛应章受蒋介石委派到定县考察,经较长时间实地考察,他对农村之实际成绩,“周览无疑”,归来后即写成长达近10万言的报告书上呈蒋介石。许多国民党要员也不断到乡村建设实验区进行考察,并建议蒋介石纳乡村建设运动于政府轨道,在全国范围内仿效定县、邹平设立实验区。由此,国民政府内政部开始筹备第二次全国内政会议,以推动县政改革。
县政建设运动的直接起源是第二次全国内政会议。对于这次会议,国民党政府特别重视,内政部为筹备这次会议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在未开会之前,先分三组,到各省区视察。……并根据各省详密报告,然后草拟提案,每一重要提案,皆经过十余次之讨论”。而且,“会中所提各种方案,皆经过相当时日的准备,各地代表,故本其历年来办事之经验,以为所提方案的根据,即内政部的提案,亦经过缜密的手续”。[11](p11)如内政部准备提交会议的《县政改革案》,黄绍竑等就曾先行电约定县晏阳初和邹平梁漱溟等人帮其参酌。同时,内政部还特邀请了许多内政专家如晏阳初、李景汉、梁漱溟、高践四等与会。会议于1932年的12月10日上午开幕,15日下午闭幕,主题是“完成地方自治,整理‘匪区’善后,奠定国防基础,促进行政效率,统一内务行政”[12](前言p1)。“尤以县政改善为当今之急务”[13](p92)。这次会议的提案审查委员会分为民政、警政、礼俗统计、土地水利、卫生五组,在不足一周的时间里,讨论通过了400余件议案,审议了200余件建议案,效率之高,在国民党历次会议中可谓少见。在审议通过的议案中,《县政改革案》最为重要,该案指陈了现行地方制度的六大缺点,并有针对性地制定出了县政改革的10项方针:“(1)厘定地方行政系统确立县之地位;(2)充实县政府组织提高县长职权;(3)划分省县权限增进行政效率;(4)确立县财政系统实行预算决算制度;(5)设立县政建设实验区及县政建设研究院;(6)举行县长总登记;(7)增加县政府经费提高县行政人员待遇;(8)整理县行政区域增设新县治;(9)积极筹设县参议会;(10)提高县政视察地位明定考绩标准。”[14](p150-151)根据议案精神,内政部拟定了《各省设立县政建设实验区办法》,从总纲、组织及权限、经费、实施的方式与程序等方面对县政建设实验区的设立作了原则上的规定。该项办法提交大会审议,经与会代表多次讨论修改后一致通过。
会后,内政部将《县政改革案》会同《各省设立县政建设实验区办法》一起呈奉行政院,经行政院第一一七次会议议决通过,中央政治会议第三六六次会议议决备案[12](p1)。1933年8月,内政部正式颁布《各省设立县政建设实验区办法》,并通令各省,要求在最近期间内依照该办法的规定在省区内选择一县或数县作为推行县政建设的实验区,报内政部转呈备案。同年十月,内政部又根据各省县政建设实验县在设立中出现的问题,致电各省政府,对于《各省设立县政实验区办法》之根本精神分为六项详加阐述。[12](p5-6)此后,县政建设运动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展开。
二
县政建设运动从第二次全国内政会议闭暮后启动,至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结束。全国11个省的20个实验县中以江苏省江宁县、浙江省的兰溪县、山东省的邹平县与菏泽县、河北省的定县“各具有特点,最负时誉”[12](p56)。
下面就以这五个实验县为典型范例,来对县政建设运动作一介绍和分析。
江宁自治实验县作为代表国民党官方立场的实验县,是成立最早的县政建设实验县。早在1933年2月,该省就通过于《江宁自治实验县县政府暂行组织条例》,“在未奉部颁县政建设实验区办法以前,于二十二年六月间即奉军事委员会蒋委员长所发中政校拟具之江宁县政设计委员会组织条例及实验县计划……设立县政委员会,推荐县长,实验县于焉成立”[7](p137-138)。此后,根据内政部《各省设立县政建设实验区办法》、《江苏省辽宁自治实验区设计委员会组织条例》(1933年7月通过)和《江宁自治实验县组织规程》等法规,首先对县及县以下的政制进行了改革。江宁的改革,以地政改革和公路修筑成就最大。在地政方面,江宁实验县依靠人才、资金和技术优势,仅用两个半月就完成了多年来悬而未决的全县土地陈报和税制改革。江宁县田赋每年应征107万元,1927至1932年的田赋实征为应征的28.24%,土地陈报和税制改革完成后的第一年,田赋实征95万元(奉令减漕米7万元),达到了应征额的95%,并追征了1932年的欠粮20万元[5](p200)。在公路修筑方面,实验县制定了三年计划,以五十万元完成县交通网。不过,这个样板工程曾遭到社会上的广泛批评,县长梅思平也承认“这主意打差了”[5](p200),应当将筑路之钱用在农业改良上。
兰溪实验县是另一个代表国民党官方立场的县政建设实验县,它的成立时间比江宁稍晚。由于兰溪实验均是“依照江宁县成规”所制,它的实验内容和步骤也与江宁基本相同,只不过方法上有所区别。兰溪实验县的土地清查虽比江宁费时稍长,成本却少得多,江宁土地陈报花费两万余元,而兰溪之土地清查仅用了两千元,而且成效也是显著的。据统计,改制前,“兰溪历年田赋,实征数仅及三成”,改制后,实征达应征的八成以上[6](p186)。在公安方面,兰溪实验县在消极方面主要是整顿原有之保卫团,加强社会治安管理;在积极方面则是抽训壮丁,以取代警察,并在乡村仿照“剿共”省份推行保甲制,使原有一些赌毒之风盛行的乡村有了很大改观。兰溪实验县没有江宁那么多的特殊条件,其实验经验对于国民党一般县份的改制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定县实验县是在原平教会定县乡村建设实验区的基础上成立的。“该省(河北)县政建设实验区,仅于二十二年四月与该省县政建设研究院同时成立,实验区县长由研究院实验部主任(霍六丁)兼任,其时在部颁办法以前”[12](p24)。1928年6月,平教会专门成立了统计调查部,并根据“以县单位作实验对象”的计划,逐步将调查范围扩大到了全县。1933年河北省县政建设研究院和定县县政建设实验县正式成立以后,平教会与研究院分工合作,前者偏重于已有调查材料的整理与实验,后者负责实验过程中的实地调查。平教会定县实验在政制改革方面,主要是根据实际情况对县政府实行裁局改科,县以下则废除了区制,改革了乡村设置,增添了选举产生的乡镇建设委员会,并在行政村成立了公民服务团,打算以此来组织民众,取代基层的保甲制。建设方面的实验可概括为三大方式、四大教育、六大建设,即在科学的社会调查的基础上采用社会式、学校式、家庭式三大教育方式,推行文艺、生计、卫生、公民四大教育,以完成政治、教育、经济、自卫、卫生、礼俗六大建设。其中,以识字教育、文艺教育和生计、卫生教育的成绩最为彰显。定县的识字教育主要是结合实际生活,推行导生制和平民学校,历时最久,收效很大。另外,定县合作社制度的推广也有一定的成绩,到1935年冬,正式成立的各种合作社即达130多个。在卫生教育方面,定县推行了农村卫生三级保健制度,即保健员、保健所和保健院,并推广种牛痘。1934年全国天花流行,人口大量死亡,其中定县仅有数人。俞焕文对此颇为惊讶,认为“定县天花已经绝迹,[17]。定县这些成就得到了当时社会各界的认可,其实验方式被称为“定县模式”。
邹平与菏泽两个实验县的县政建设实验依托的是山东省乡村建设研究院。“该院于民国二十年三月筹备,六月成立……溯其由来,河南村治学院是其前身……自该院成立以后,(山东)省政府即指定邹平县为试验区(院设邹平县),由梁漱溟主持其事“[12](p38)。
第二次全国内政会议以后,该省又划定菏泽县为邹平县政建设实验县的姊妹县。1933年以后,根据第二次全国内政会议的精神,实验的重点转到了建设上来。首先,乡建院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了裁局改科的县政府改革,这也是实验县中最早的裁局改科实验。其次,废除原有的区乡镇制度,仿照古代乡约制度,设村学、乡学这种政教合一的组织,实行以教驭政。同时邹平实验十分注重民众的组织与道德教育,并将之与民众生活的改善充分结合起来。邹平实验成就最大的是美棉推广、合作事业和乡村自卫。乡建院从1931年就开始在邹平孙家镇及其附近18个村实验纯种脱里斯棉的种植,1932年实验成功以后,推广到27个村147户,种植874.2亩。到1935年,全县能种棉的基本都改种了脱字棉[8](p59)。同时,邹平还组织了美棉运销合作社,减少了中间商的盘剥,增加了农民的收入。在乡村自卫方面,则利用古代乡射制度,训练民众,组织民众,组织联庄会。1935年,邹平的民众自卫组织发展成拥有2500人的正规民团,从而根绝了匪患,小偷、流氓犯罪现象也大为减少。素称匪患重灾区的菏泽在自卫方面的成就尤为突出,1934年,山东巨匪刘黑七窜扰鲁西,附近各县无不遭其蹂躏,但他慑于菏泽10000多训练有素的民团团员的威力,环绕其县而不敢入其境[19](p61)。邹平、菏泽的实验,梁漱溟为其精神指导,以邹平为代表,带有很浓厚的新儒学气息,在当时产生了重大影响,其经验曾被称为“邹平模式”。
五个实验县的县政建设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江宁兰溪模式、邹平模式和定县模式均在当时产生了重大影响。尽管抗战全面爆发后,这些县先后沦陷,实验也被迫中断,但其实验经验却被国民政府借鉴,可以说成为抗战时期“新县制”设计的思想资源。
三
上述五个实验县的县政建设方案不一,各具特点。但是,由于乡村社会结构变动的地域特征并没有形成质的差别,加以国家权力一体化政治的介入,因而,尽管在具体的进程和操作方式上有所区别,甚至在参与力量和主体上也有所不同,县政建设运动整体上却有着共同的历史特征。概而言之,主要有四个方面。
第一,从县政建设运动的政治表现来看,政府主持下的国家力量和社会力量的竞争发展是这个运动的总体特征。县政建设运动是由国家力量和社会力量共同参与的一个乡村改造实验,这两种不同质的力量又可分为三个派别:定县的平教会实验派,山东邹平、菏泽的梁漱溟乡建实验派和江宁、兰溪的国民党实验派,他们分别代表了不同的利益团体,其实验的出发点和指导理论也因此不同。江宁和兰溪代表了执政的国民党,它的目的是为了加强国家权力对乡村社会的渗透控制,消弭革命势力,同时尽可能多地支配乡村资源。因此,江宁、兰溪实验就以政制的实验为出发点,主张由上而下,用行政组织和技术来促进乡村建设,以寻求一套更有效率的乡村社会管理体制。正如时人所评:“中央所设的两个实验县,根本没有什么理想,老实不客气地说,是实验政制与政策。”[15](p205)邹平、菏泽和定县的乡建派虽同属于“在野”派,由于成员组成和代表的社会阶层不同,所持有的理念也不一样。梁漱溟等代表了由传统向现代化转型过程中的乡村士绅阶层,他们以“继先圣之绝学”为己任,从中国“伦理本位、职业分途”的特殊社会结构的认识出发,认为只有通过新儒学在乡村社会的确立,来实现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嫁接,中国才能建立起走向现代化的文化根基。因此,邹平、菏泽实验的乡村建设充满了新儒学的精神。晏阳初等人则代表了受过西方现代高等教育的爱国知识分子阶层,他们接受了西方的民主思想,并从西方现代化的历史经验中认识到,民众的科学化、知识化,尤其是乡村民众的科学化、知识化才是中国现代化的基础。定县的实验指导理论就是一种平民教育和科学实验的理论。江宁、兰溪实验就称自己是“方法的实验”、“政治的实验”和“整个县政”的实验,定县和邹平为“主义的实验”、“社会的实验”和“民众”的实验[20](p199-200)。三个派别在同一个运动中从事乡村改造工作,根据费孝通的理论,“在时势权力中,反对是发生于对同一问题不同的答案上,但是有时,一个社会不能同时实验多种不同的方案,于是在不同方案之间发生了争斗,也可以称作‘冷仗’,宣传战,争取人民的跟从。为了求功,每一个自信可以解决问题的人,会感觉到别种方案会分散群众对自己方案的注意和拥护,因之产生了不能容忍反对的‘思想统制’”[21](p174)。然而,在这个运动中,所谓的“思想统制”并没有出现,呈现出的反而是一种共同参与、竞争发展的局面,其原因就在于各方共同的现实需求。从国民党的角度来看,社会力量的乡村改造无疑“是一把双刃剑”[22](p240),最初对它们并不予正式认可;当梁漱溟等把设立邹平实验区的计划呈送国民党时,国民党就以“全国除了国民党已故总理孙中山的故乡广东中山县特别划为实验县外,不得再有第二个实验县的名称”[23](五.p1012)为由批驳了它。但是,面对着不断加重的内忧外患,刚在中原大战中站稳脚跟的蒋介石政权急需加强对乡村社会的控制,国家事实上的不统一和国民党本身与农民的背离使其缺乏独自改造乡村社会的能力,从其本身的需求和“两害相权取其轻”的策略考虑,国民党也认可了乡建派在乡村的活动,并通过官方主持的县政建设运动将其纳入自己可以掌控的范围。这种策略至少起到了三个作用:1.使乡建派这些潜在的乡村竞争者暂时不会变成自己的敌人。2.可以利用其人力,物力和智力来为自己改造乡村的目的服务。3.由于定县、邹平和菏泽都处于地方实力派控制之下,并得到了他们一定程度的支持,认可这些社会力量的活动也可以缓和国民党中央与地方实力派的关系。在社会力量方面,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很不像一个真正的国家”[23](五.p344),社会人士对当政者显然不满。当蒋介石第一次召见梁漱溟时,梁就拒绝前往;后来勉强与蒋介石见了一面,梁对蒋介石的印象也是“这个人很虚伪”[23](七.p199-200)。但是,他们又不主张像共产党那样以阶级斗争的方式改造乡村。而且,到了30年代初,如果没有国家权力的介入,他们的乡村建设已经很难再有进一步发展的余地了。故而,当蒋介石召见晏阳初时,他反应十分积极。虽然国民党和乡建派在改造乡村方面的思想和目的都不相同,但在20世纪30年代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基于一种共同的需求,双方最终在县政建设运动中走到了一起,形成了一种政府主持下国家力量和社会力量共同参与乡村社会改造、竞争发展的局面。
第二,从运动的经济表现来看,整理财政制度,改良传统农业,重视乡村副业,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乡村经济走向市场化是各种实验方式的共同特征。由于县政建设运动发生于中国农村经济濒临崩溃的背景之下,所以实验县都比较重视乡村经济的恢复;同时,随着中国日益卷入资本主义的市场体系,商品经济化是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江宁采取的主要措施是:在地政方面,开展土地陈报以杜中饱。实行土地陈报后,江宁实验县改组了粮柜,改进征收制度,实行自封投柜的办法,杜绝了征收人员的中饱私囊,减轻了农民的经济负担。在财政方面,整顿苛捐杂税,废除柴捐、鸭行捐、鸭铺捐等杂捐,取消正副税,统一税则,减轻税率,实行一条鞭税制,商品经济有了较快发展。改制第一年,契、牙、屠宰、锡箔等杂税收入就有4-5万元[7](p138)。同时,江宁在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也投入颇多,如修建蓄水池,建造牛王灞、汤水闸,疏浚河道,从而改善了农业的生产环境。兰溪在地政方面采用了土地清查的办法,农民的经济负担亦有所减轻。杂税方面原有各种苛杂多至30余种,自1934年1月1日起分三期整理,陆续取消夫行捐、活猪捐、青枣捐等不合理杂税13项,有利于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16](p194)。邹平与菏泽的实验更侧重于“养”的方面,主要是改良农作物品种,推广美棉种植和棉花运销合作,发展农村副业,开展农业合作,以此来增加农民收入。仅以美棉种植和运销合作为例,1935年,邹平全县所有能种棉的乡村基本都种了研究院推广的美棉,该种棉每亩比原有钦氏棉增产10%-20%,质量上乘,平均每担增收10-16元[3](p59)。定县则拥有资金和技术的优势,在农作物和禽畜改良上下的功夫也最大。在猪种改良方面,定县改良的猪种平均每头比本地猪多产肉18.6%,可增收3.72元,仅此一项,全县每年即可增收8万多元[10](p412);其推广的力行鸡每年的产蛋量是本地种的4倍多,并实行全村鸡瘟注射,增加存活率,这些改良有力地推动了农畜产品的商品化。另外,这几个县都比较注重完善乡村保卫机制,以维护正常的农业生产秩序;引进城市资金建立合作社和信贷处,促进农村金融流通和生产发展;改进行政机构和行政制度,增加管理效能。这些改良活动虽说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农村经济的衰退状况,但在一定程度上却促进了农业走向市场化。
第三,从县政建设运动的文化表现来看,在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文化之间采取兼容并蓄和借鉴融通的态度是运动的另一个重要特征。一战以后,西方世界逐渐兴起了一股对资本主义文明进行反思的潮流。在西方世界反思潮流影响、国内民族救亡和国家现代化的巨大压力下,五四时期激进的反传统主义潮流趋于平静,国人开始冷静地思考如何才能将传统与现代、东西方文化融通起来,以找到一条适合国情的发展道路。关于这方面的文化争论充斥着30年代的整个十年,无论是乡村建设派、平民教育派,还是包括江宁、兰溪的三民主义实验派,都是这其中的一分子。他们在一定程度上都继承了五四时期科学与民主的一些传统,延续了中西文化冲突和融通的过程。他们在争论的同时,又在实践中不断检验自己的理论,一方面在理论上立足于对民族文化的创新,从传统中挖掘新内容,并引进现代的科学技术与团体组织来充实之;另一方面用乡建的实践来不断地检验和修正自己的理论。邹平的乡学、村学挂着旧式乡约的外表,却具有一定现代团体的内涵;他们的县政改革、庄仓合作和农业的改良,都体现着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文化的结合。一个国家处于社会转型期,由于受文化变迁的巨大冲击,往往会出现社会失范的现象[24](p75)。梁漱溟等在邹平利用传统文化中的一些积极方面,以遏制社会失范加剧的做法也是值得借鉴的。再如晏阳初等平教会同仁,代表了受过西方现代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阶层,他们作为西方现代科学知识的拥有者,甚至是西方宗教的信徒,仍然从传统的“正身诚意”、“修齐治平”和“民本”等思想中寻找改造中国乡村的动力,以支持乡村科学化、现代化的实验。晏阳初在《九十自述》中说,他将整个生命都耗在“忧求”之间,“不论在中国,或是在海外,都是民本思想的实践,而以天下一家为最高宗旨”[10](p455)。江宁和兰溪同属国民党CC派的实验县,他们在改进乡村行政体制和行政技术、加强乡村控制的方面,也兼容并蓄了现代技术和传统文化,一方面吸收了西方地方自治的制度,一方面又借鉴了传统的村里制、保甲制,辅之以现代行政技术,以中西合璧的保甲管理体制取代了运行不良的自我管理体制。兰溪的保甲推行是形诸明令的,江宁的保甲推行则有实无名。梅思平曾说:“江宁也办保甲,可是有保甲之实而无保甲之名。……江宁的联保切结比别的县份要办的严密的多。”[25]而这种保甲与传统不同,更多地被赋予了现代行政管理的职能。因此,尽管县政建设运动各派在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文化的取舍上程度不一,但在文化融通和文化创新的价值取向上却是相似的,这也是县政建设运动总体上的文化特征。
第四,从县政建设的实验方式上来看,将学术研究和政治建设相结合是县政建设运动最为明显的特征。各个实验县虽然指导实验理论不同,实验内容也各有侧重,但在实验县的设置方式和实验方式上却是相同的,都设立了县政建设研究院,或以大学为研究依托,将学术研究与县政建设结合起来。江宁和兰溪的实验均是以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为学术研究依托的。据江宁试验县统计:江宁县的县政委员会委员均是“党国要人”,江宁县政主持者多半为中央政治学校师生,县长梅思平是中央政治学校行政系主任,县府职员百十人中,大学毕业48人,专科毕业13人,大学肄业5人,受高等教育者占五分之三,其余均毕业于中等学校[26](p173);兰溪实验县县政委员会委员为省府各厅负责人,县长胡次威是中央政治学校社会系主任,其职员情况与江宁差不多;邹平、菏泽的实验是以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为依托的,该院实际主持者梁漱溟是哲学家,曾任北大教授,研究院成员大部分是原河南村治学院成员,所招学生也均受过新式教育;定县实验被时人认为是“以第一流的人才开创的第一流的事业”,其实验的学术研究机构是由平教会主持的县政建设研究院,院长晏阳初是留美博士;平民文学部主任陈筑山曾留学日本11年,到定县以前任国立北京法政专科学校校长;平教会《农民报》主编孙伏园,曾留学法国,任教北京大学,去定县以前任《晨报·副刊》主编;视听教育部主任郑锦曾留学日本10年,到定县前任他创办的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校长;熊佛西、瞿菊农均为哈佛大学博士;冯锐是美国康奈尔大学农学博士;汤茂如和李景汉是哥伦比亚大学硕士;谢扶雅、刘拓均是留美博士[27](p321-323)。同时,平教会在定县的实验方法也是比较科学的。他们在将小范围的生计实验成果推广应用时,摸索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即将整个推广制度分为生计巡回学校、表证农家及实施推广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对农民“施以适合的教育,授以切实的技术”;第二阶段选择表证农家,“将实经验获心得教授其他农民”;第三阶段“用表证农家,将其在本部领导下所获得之知识与技能,表证经验及结果传授予一般农民”[10](p324)。这种科学的方法和审慎的态度,使定县实验获得了“科学实验”的美誉。将学术研究与县政建设结合起来,增加了改革决策的科学性,减少了实验的盲目性,从而提高了县政建设的成效。这也是五个实验县都能够取得一定成就的重要原因之一。
四
现代化是工业化和民主化产生和发展的过程,是在工业化和民主化推动下,社会形态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化的过程。[28]县政建设运动就是中国现代化历程中规模比较大的一次乡村现代化实验。它的运作模式、实验方式和实验内容都为中国乡村现代化留下了许多历史经验和教训。
首先,要推动乡村现代化,必须有高效能的政权,能够动员全社会力量,将国家和社会力量结合起来。现代化过程中,“在确立投资的优先权和设立适合经济发展的法律制度两个方面,强大而有效的中央政权的作用是无可替代的”[29]。但国民党政府却是个既不团结又无效能的弱势政府,“政府对于最低限度的维持治安责任都放弃了,还能为人民谋福利吗”?[23](p344)在要求中央政权强大而有效能事实上却又不可能的情况下,对基层进行改良,实现基层体制的“优先合理化”却是可行的。从五个实验县的县政改革实践来看,他们都抓住了这一点。改革前,国民党的县级政权主要是根据1929年公布、1930年修正的《县组织法》来组织的,横的组织是局科并立,省厅与县府各局是直线控制关系,从而造成政府空疏,县长没有实权;纵的体制是县—区—乡(镇)—闾—邻制,数字式的编制不合传统习惯,繁多的自治层级编制更使政令窒碍难行。实验县成立以后,他们对县及县以下乡村政权的建设都比较重视。在县政权建设上,五个实验县都施行了裁局改科;在县以下乡村政权建设上,五个实验县各有特色:江宁是废闾邻,改行村里,注重乡镇;兰溪是加强对乡镇的督导,乡镇以下推行保甲;邹平菏泽是以乡学(乡农学校)、村学取代旧式乡村政权,并加强乡村自卫体制建设;定县则是废除区制,充实乡镇,基层乡村设立公民服务团。这些县的县政改革,加强了五个实验县的政权效能,增加了政府权力对基层乡村的渗透度。特别是邹平和定县,不仅能使上令下行,也能做到下情上达,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发挥社会个体积极性的现代化需求。
30年代初,在内忧外患的巨大压力下,由于国民党政权本身的孱弱和低效能,使其不得不调整与部分社会力量的关系,社会力量才能得以在县政建设运动中与官方力量并驾齐驱。县政建设运动也因此呈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发展方向——国民党实验县的官治和社会力量实验县的自治。国民党县政实验的主要目的在于加强对乡村社会的控制,积聚乡村资源,消弭革命,巩固统治。以宽容的态度让社会力量参与县政建设,只是时势逼迫之下的无奈之举罢了。受利益的驱使,一旦局势有所缓和,执政的国民党政权就会利用它掌握国家机器的优势,加强对社会力量的控制,整个运动就开始向官治的方向逆转。尽管社会力量时时在提醒自己:“我们与政府合作也不要紧,但不要因为与他合作而失掉了自己。”[23](p581)力量对比上的差异却使这种趋势根本无法改变。梁漱溟所遇到的乡村建设运动的两大难处之一就是“高谈社会改造而依附政权”,到了1937年,“这个矛盾,以现在的趋势来看,象是更要加重的样子……如此结果下去,有让乡村工作行政化的趋势——乡村工作变成地方下级行政”[23](五.p574)。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种现象是与30年代体制争论中独裁压倒民主的发展趋势相一致的。正因为如此,最初参与县政建设实验的共有20县,四年下来,稍有成绩的仅有五个,其中三个是社会力量早在运动前就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两个是国民党的“样板”县。这也说明:国民党政权不是一个能推动中国乡村整体走向现代化的强大而有效能的中央政权,县政建设运动失败的结局也就成为必然。
其次,改良财政,开辟财源,为建设提供充实的资金,是乡村现代化的另一个重要条件。清末以来,农村经济萧条、资金短缺一直是阻碍“新政”推行的重要因素。国民党统治时期也毫不例外,“湖南自民国十七年五月成立省自治筹备处,自治训练所,各县自治筹备处,积极从事筹备,用去省款七十余万,县款二十余万,结果不到两年光景,通统烟消火灭,其所以然,就为‘……需费极巨,在目前牵萝补屋之省库,即有不可为继之势’”[23](p244)。各县在开展县政建设初期也都遇到了这个问题。以江宁和兰溪为例,其解决这一问题的措施主要是:1.整理地政,打击美国学者杜赞奇所说的乡村“赢利型经纪”阶层。江宁的土地陈报和兰溪的土地清查都是比较有成效的,但并不是没有阻力。江宁开展土地陈报的初期,“恶势力及向不完纳粮款之大户,极力反对,加以破坏,进行深感不便”[7](p138),但由于乡村政权改造的完成,政府的有力,不足两月,这些老大难问题即告解决[7](p134)。兰溪情况与之类似。2.整顿苛捐杂税以增加税收。江宁和兰溪在开展县政建设过程中都对本县税制进行了改革,主要是归并税目,改进税则,完善征收制度等等,既减轻了民众负担,又促进了乡村商品经济的发展,更增加了政府税收。定县和邹平、菏泽农业改良、合作社、精简机构的方法可以用“开源节流”四个字来概括。
然而,从五个实验县在县政建设的实际运作中来看,它们的财政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的解决。表面上看,定县和江宁的实验经费最为充裕,但定县的资金是外来的,江宁是不用上缴田赋的,邹平、菏泽与兰溪每年能得到省府的大量补贴。可见,解决乡村现代化所需资金问题的根本途径在于发展商品经济(包括引进外资),将农业推向市场。正如前文所述,这一点他们都有所意识,但没有一个有力的中央政府来为他们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农作物改良了,增加的产量甚至抵消不了因受外国农产品倾销影响粮价低落而造成的损失,中国乡村所谓的副业也只能在资本主义倾销的夹缝里苟延残喘。而且,国民党虽有像江宁、兰溪整理地政那样比较成功的经验,但政权本身的孱弱却使它无法将这种经验推广到其他县份。因此,没有社会整体的改革,改良并不能解决乡村现代化资金缺乏问题的全部。
再次,乡村民众的知识化和乡村社会管理的合理化也是推进乡村现代化的重要条件。科举废除以后,“乡村士绅向城市的流动逐渐加剧,他们到都市新式学堂接受新学教育”。“由于这种新式教育是适应城市工业社会发展的,从而使这种流动变成以城市为中心的单程流动”[30](p343)。到了五四前后,这种人才持续的单程流动使乡村出现了文化荒漠化和政权痞化的现象,土豪劣绅专政下的乡村文盲率高达90%以上。在余家菊等人“乡村教育危机”的呼号下,平教会等教育团体开始走向农村,30年代县政建设运动的兴起使这方面的问题有了一定的改观。江宁和兰溪两个实验县的骨干力量是中央政治学校的师生,两个实验县从某种意义上成了该校的实习基地,从而使中国正规院校的人才培养发生了从城市学历型人才向社会实用型人才转变的方向性变化。平教会的“博士下乡”则体现了爱国知识分子自身要求转变的自觉性,在定县参与这一运动的留洋博士、硕士、学士和大学校长、教务长以及著名的报刊主编等高级知识分子一般有二三百人,最多时达到五百人以上[3](p539)。邹平的山东乡村建设学院亦是这种转变的典型,成立两年就培训乡建骨干630人。在输入人才的同时,五个实验县都比较重视农村的教育问题,并结合实际创造了一些实用的乡村教育方式,如邹平、菏泽的乡学、村学和成年培训部,定县的平民学校“导生传习”和“统一的村学”实验,江宁、兰溪的乡镇学校制和中心学区制等等。据统计,邹平1937年1月共有成年培训部271处,学生12019人,妇女部5处,学生188人[31]。定县的平教会1935年在吴咬村等10村开办了男女导生训练班[32](p205)。江宁1934年有县立学校121所,学生11000人;乡镇学校102所,学生4080人;私立学校3所,学生205人;实验小学2所,私塾学生400人[7](p140)。从这些数字来看,它们在乡村文化输入和乡村教育方面确实取得了一些成绩。
任何一种现代化的动力都应该来自其内部。由于中国乡村进入近代以来出现了文化和社会权威阶层流失的问题,乡村本身缺乏向现代转型的基础和动力,确实需要外部文化与人才的输入。因此,我们钦佩20世纪20-30年代那些走向乡村的官方和非官方的文化团体,他们甘愿舍弃都市生活走向乡村的精神至今仍值得我们学习。他们从外部向乡村的文化输入和人才输入在乡村现代化的启动方面也确实起到了一些作用。但是,从五个实验县的实践来看,他们的县政建设实验没有一个能够持续下去。表面上看来,这些实验是因战争的爆发而中断的,更深层的原因却是乡村社会缺乏持续推动现代化的动力。为什么在外来文化和人才输入乡村以后仍会出现这种结果呢?至少有三点是可以肯定的:1.外来的文化自身不可能成为乡村现代化持续的动力。进入近代以来,中国始终没有在文化上形成城乡一体化的现代化根基,以牺牲乡村为代价的现代化道路反而使乡村文化阶层大量流失,城乡在文化上出现了严重的脱节。从知识结构上看,县政建设运动中的外来知识分子都是都市化工业文明教育的产物,尽管他们在乡村濒临崩溃、民族面临危亡之时走向了乡村,也曾设想通过与农民同吃同住的方式努力把自己融入乡村社会之中,但他们作为脱离乡村已久的都市市民阶层,由于文化上的隔阂,再想真正融入乡村社会之中已不是个人努力所能办到的。梁漱溟等就承认,运动后期所遇到的“号称乡村运动而乡村不动”的难处,是由于他们和乡村“没有打成一片”、“未能代表乡村的要求”而产生的[23](p575)。30年代县政建设运动中的知识分子最终离开了乡村,60-70年代下乡的知识分子在80年代大部分又回到了城市,这些历史事实证明,外来文化力量本身不可能成为推动乡村现代化的持续动力。2.外来文化团体在乡村自身现代化动力的培养上缺乏制度性的机制。外来文化和人才的输入是暂时的,如果在乡村社会内部培养不出一种能持续推动乡村现代化的动力,外部的文化和人才输入一旦中断,乡村社会的现代化也就会随之陷入停滞。这五个实验县最初并不是没有注意到这一点,甚至提出了“乡村运动天然要以农民作为基础力量,而向前开展”[23](p575-576)的口号。因此,这些外来文化团体除了在平民教育上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财力以外,还在组织民众方面下了功夫,例如江宁、兰溪现代保甲制的推行,定县“公民服务团”的设计和邹平、菏泽“乡学(乡农学校)”、“村学”的组织,都是他们在这方面的探索。尤其是定县和邹平,其县政建设实验被称为“民众的实验”和“社会的实验”。当时,他们的实验确为已陷入绝境的乡村带来了一些希望,但始终停留在“人为”的层面,没有形成一种乡村自身现代化动力培养的制度化机制,从而仍走上了“人存政举,人去政息”的老路。3.这种由外来文化团体发动的县政建设运动不可能从根本上清除阻碍乡村现代化动力形成的羁绊。近代以来,阻碍中国乡村现代化的因素主要有外部恶劣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和乡村政权的痞化、土地占有的不均、大多数农民的基本生存问题没有解决等等。这些造成乡村经济衰败的问题,在国家政权没有合理化以前,单靠外来文化团体的改良努力是无法解决的。大多数民众在衣食无着的情况下,其自发学习文化的积极性是很有限的。平教会在定县劝说农民参加平民学校时,有的农民就提出说:“看见某某人读过书还没有饭吃”;甚至说:“你老的好心肠,饱不了我的饿肚皮”。1934年,定县青年妇女文盲率为73%;1935年,6-12岁儿童入学率不足40%。[33](p10)邹平的学龄儿童教育是五个实验县开展的最好的,到1935年入学率仍不足50%。因此,可以说,社会大环境没有根本的改观,外部文化和人才的输入对乡村的影响就很有限;没有制度化的乡村文化普及和人才培养,也就培养不出乡村自身的现代社会力量。
到30年代初,“地方自治这件事,实行始于光绪三十四年,已经有二十多年的历史,日子也不算短了;可是直到现在仍然看不见一点踪影,还在倡议之中,全国任何地方,都无其可行之端倪”[23](p309)。恶劣的外部环境,不断的天灾人祸,经济濒临崩溃,政治不上轨道,文化荒漠化,县政建设运动就是发生在这样一个非旧亦非新的转型期,也可以说是中国现代化历程中最痛苦的阵痛期,它的意义不言而喻。它的探索表明: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后发展中国家来说,国家政权的优先合理化是乡村现代化启动的前提,同时,对于乡村现代社会力量的培育,才是乡村现代化持久发展的根本保证。面对中国乡村现代化艰难曲折的历程,我们不能忽视历史给予我们的重要启示。
【收稿日期】2002-07-09
标签:梁漱溟论文; 邹平论文; 1932年论文; 台湾国民党论文; 抗日战争论文; 菏泽论文; 经济建设论文; 社会改革论文; 蒋介石论文; 江宁论文; 社会变迁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