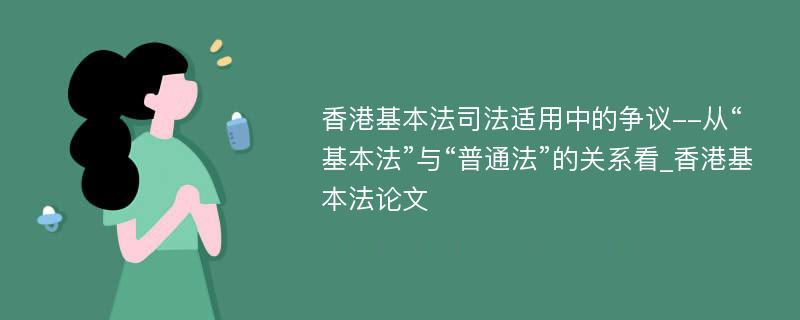
香港基本法司法适用中的争议——从基本法与普通法关系的角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香港基本法论文,普通法论文,基本法论文,司法论文,角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F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8049(2010)07-0011-12
根据“一国两制”原则,《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以下简称基本法)保留了回归前香港原有的普通法传统。香港回归后,关于基本法和普通法关系的争议不断。香港基本法如何在实行普通法传统的香港法院中进行司法适用,香港普通法又应如何适应基本法的框架进行适用和发展,这一个全新的课题在香港回归以来的司法实践中屡现分歧。本文以香港基本法的司法适用为视角,分析基本法司法适用过程中造成基本法与普通法分歧的原因,并试图寻求消除两者紧张关系的对策,以从制度上规范基本法的司法适用。
一、基本法的司法适用
基本法的司法适用指基本法在实行普通法传统的香港法院司法活动中的具体适用。香港回归以来围绕基本法司法适用的争议集中体现在香港法院是否享有违反基本法审查权① 以及香港法院如何行使基本法解释权两个方面。这两项司法权的归属及行使影响到香港法院对案件实体争议的判决,集中体现了香港法院对基本法与普通法关系的理解。香港终审法院在吴嘉玲案中提出:“在处理上述受争议的问题(即案件的实体问题)前,我等首先说明宪法赋予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的司法管辖权,然后再为解释基本法制订恰当的处理办法,这两点至为重要。”②
1.1 香港法院违反基本法审查权
香港基本法没有授予香港法院违反基本法审查权。违反基本法审查权问题发端于1997年的马维騉案③,香港法院在该案中首次确认了香港法院对本土法律是否抵触基本法享有审查权。1998年5月20日张丽华案进一步提出在适当的情况下,特区法院或许确实有权审查全国人大的法律和行为是否符合基本法。④ 随后,张丽华案上诉到香港终审法院与吴嘉玲案合并审理。香港终审法院在判决中重申特区法院的宪法性管辖权,宣告特区法院不仅“有权审核特区立法机关所制定的法例或行政机关之行为是否符合基本法”,而且“有权审核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行为,以确保这些行为符合基本法”⑤。
香港终审法院判词一经发布,即在内地和香港掀起轩然大波。1999年2月16日,香港法院发表澄清声明,表示其原判决并没有质疑而且特区法院也不能质疑全国人大常委会“根据基本法和基本法所规定的程序行使任何权力”。但这一澄清只是承认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法律解释权,对于特区法院所主张的违反基本法审查权及其合法性没有作出任何的说明。⑥ 随后,1999年6月2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首次释法明确地表达了不同意香港终审法院这段判词的意见,认为它无权判决国家最高权力及立法机关的行为是否符合基本法。⑦ 此后香港法院有关违反基本法审查权的司法实践回到第一个宪制性案例——马维騉案所确立的轨道上来,即香港特区法院可以审查特区立法会制订的法律是否与基本法相一致,但不可审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立法行为。马维騉案作为普通法上的先例为香港法院在之后的各类案件中所遵循。“在香港回归后诉讼至法院的有关本土立法是否符合基本法的案子,清楚地显示出在1997年7月1日以后,香港法院拥有广泛的违宪审查权。”⑧ 例如1999年3月23日的国旗区旗案⑨,香港高等法院上诉庭宣布香港《国旗及国徽条例》第7条和《区旗及区徽条例》第7条中关于禁止侮辱国旗和区旗的刑法保护违宪而无效。⑩正如香港终审法院首席大法官李国能在2007年法律年度开启礼上发表的演辞中所承认的:“香港回归以来司法复核个案比回归前大大增加,司法复核已经成为我们的法律体制中已确立和不可或缺的一环。”
1.2 香港法院基本法解释权
基本法第158条规定基本法解释权属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香港法院对自治范围内的条款行使解释权。基本法没有规定释法应采用的方法。有关释法方法的分歧和冲突在吴嘉玲案得到了集中体现。对吴嘉玲案所涉及的基本法第24条的理解,香港终审法院采用普通法的文义解释法。全国人大常委会在首次释法中采用成文法的立法原意解释法,并认为“终审法院的解释不符合立法原意”。(11) 2001年7月20日庄丰源案再次引发有关释法方法的争议,但香港终审法院并没有遵照全国人大常委会的释法方向,没有根据立法原意解释基本法,而是再次坚持以普通法解释基本法的立场,并系统阐述了解释基本法的方法。(12) 对香港终审法院的这一做法,全国人大常委会没有进一步表明态度,而仅仅“表示关注”(13)。由此,香港法院以普通法解释基本法的做法成为先例,在之后一系列有关基本法的案件中得到遵循。例如2006年7月13日的梁国雄和古思尧诉行政长官案(14)中,在解释案件涉及的基本法第30条、第39条与第39条第1款明确在香港适用《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规定以及1991年《香港人权法案》之间的关系时,香港法院采用了吴嘉玲案中所确定的按照宽泛和通常的意义解释基本法的方法以及采用梁国雄和其他人诉香港特别行政区一案(15) 中所确定的对基本法有关居民权力条款的限制采用严格解释的方法解释基本法,引发了对基本法解释方法的广泛讨论。
二、基本法司法适用争议的原因
香港法院违反基本法审查权和基本法解释权涉及基本法司法适用中的法律方法选择问题,即应以什么方法对基本法进行法律适用并在适用中解释基本法。(16) 马维騉案提出了对香港本土立法的违反基本法审查权,此案作为香港回归后违反基本法审查权的先例被之后的案件所遵循;吴嘉玲案确立了采用普通法字义解释方法解释基本法之后,以普通法解释基本法成为判例规则得到遵循。从第一起基本法诉讼案开始,香港法院自始至终坚持以普通法的传统适用和解释基本法,并根据普通法上的法官造法和遵循先例原则逐渐发展成为一项普通法的规则。虽然全国人大常委会在这两项重要的司法争议中进行了首次释法,但是释法对于违反基本法审查权的不肯定不否定态度,对于基本法解释方法的沉默,都没能从根本上解决以普通法传统适用和解释基本法的做法。笔者以为,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有如下几个方面。
2.1 基本法与普通法法律推理和法律思维方式的差异
基本法是成文法,普通法是判例法,成文法和判例法的差别不仅仅在于法律表达形式不同,更重要的是,其代表了两种不同的法律思维方式和法律推理方法。成文法注重法律规则,要求法律适用和法律解释必须确保对法律规则稳定的陈述,法院应根据已有的法律规则对案件作出裁决。基本法是我国以内地成文法传统和技术主导的立法体制的产物,其制订解释和适用都无法脱离成文法的影响。与此相反,普通法主张遵循先例,法官在案件中适用制定法时,往往看这些制定法条文的规定是否符合法官在先例中确立的具有最高效力的普通法规则,只有符合普通法原则的制定法规则,才能被法官适用。(17) 香港法院作为基本法的适用者,根据普通法传统,在适用和解释基本法时自然采用普通法的法律推理模式和法律思维模式。
违反基本法审查权争议折射了基本法和普通法两种不同的法律推理和法律思维方式在基本法司法适用中的冲突。基本法没有明文规定香港法院拥有对抵触基本法的法律的审查权,依照成文法的法律推理和思维方法,任何政府机构,包括司法机构都只拥有法律明确授予的权力,法律没有授予的,不能自我占取(18)。因此,香港法院不能根据基本法的隐含规定或者以所谓“剩余权力”为由自我创设违反基本法审查权。普通法传统却认为,解释法律和决定相互冲突的法律在案件审理中的适用与否是法院固有的权力。“将既定规则适用于特定案件的人必然要解释这种规则。如果两部法律相互抵触,法院必须决定适用其中哪部法律。如果一部法律是违宪的,而该法与宪法都适用于同一案件,则法院必然要么无视宪法,适用该法;要么无视该法,适用宪法。”(19) 据此,在违反基本法审查权问题上,香港法院认为:“香港特别行政区享有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基本法第19(1)条),而特别行政区各级法院是特区的司法机关,行使特区的审判权(基本法第80条),在行使基本法所赋予的司法权时,特区法院有责任执行和解释基本法。毫无疑问,香港法院有权审核特区立法机关所制订的法例或行政机关之行为是否符合基本法。倘若发现有抵触基本法的情况出现,则法院有权裁定有关法例或行为无效。法院行使这方面的司法管辖权乃责无旁贷,没有酌情余地。”(20) 显然,在香港法院看来,即使基本法没有明确规定香港法院违反基本法审查权,但是基本法第19条和第80条有关香港法院享有独立司法权和终审权的规定,第158条关于香港法院对基本法解释权的规定;第8条和第11条关于基本法最高法律效力地位的规定以及剩余权力理论都隐含了香港法院的违反基本法审查权。(21)
就释法权争议而言,成文法认为法律解释是与立法权、司法权彼此独立的一种国家权力,立法机关自行解释其所制订的法律。基本法有关释法权的措辞也体现了成文法的这一思维方式。基本法明确表达其释法权是“属于”全国人大常委会,而不是采用“赋予”或“授予”的措词。同时,考虑到香港特区的普通法传统,基本法也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香港法院行使基本法解释权。但是这两种解释权之间是有本质区别的。全国人大常委会是行使基本法释法权的当然主体,香港法院的释法权来源于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授权,两者之间是授权与被授权的关系,这决定了香港法院的解释权具有有限性、被授权性、从属性和非终局性。普通法对于释法权的理解与成文法大不相同。普通法认为法律解释不是一项独立的权力,而是附着于司法审判活动的一项必然活动,法律解释是法官在裁判案件过程中对成文法的解释,没有法律的适用不需要法律解释。而且,在权力分立的架构下,法律解释权应当属于法院,而不能由立法机关行使,法官通过在具体案件中解释法律达到对行政权、立法权的制衡。因此,基本法既然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授予香港法院解释权,香港法院的解释权就不能受到监督。基本法与普通法对于释法权理解的差异使得全国人大常委会的释法行为引发了学界不同的意见。批评意见认为,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解释超越了基本法的授权,干涉司法独立,危害香港法制传统,从而为以后全国人大常委会干预香港司法提供了先例。(22) 甚至当庄丰源案中,香港终审法院没有追随全国人大常委会释法的方法,没有按照筹委会的意见解释基本法,强调法院的责任是确立法律的立法原意,而不是立法者的原意者时,有人认为这样做是敢于向全国人大常委会说“不”,维护了普通法的释法原则,体现了香港的司法独立。(23)
释法权争议中关于释法方法的选择也反映了基本法和普通法的不同法律思维方式。基本法没有规定释法方法。对于这种立法上的空白和漏洞,大陆法系基于对立法权和司法权分立的强调,严格禁止法官对立法机关制订的法规中有缺陷的、相互冲突或者不明确之处进行解释,法官须将此问题提交立法机关作权威性解释。在此种制度下,法官在法庭中仅是听证争论事实并从法律中寻觅出既定的法律后果,(24) 法官无权创制法律。但是,保留普通法传统的香港法院认为:“香港法院解释基本法的权力除了受基本法第158条第3款对法院就‘范围之外的条款’进行管辖权的规限以及受全国人大常委会根据第158条而作出的解释的约束外,解释法律便属法院的事务,此乃特区法院获授予独立司法权的必然结果。”(25) 因此在面临基本法对释法方法缺乏规定的时候,香港法院认为其有权为“解释基本法制订恰当的处理办法”(26)。
2.2 全国人大常委会与香港法院立法解释和司法解释的差异
从1804年法国《拿破仑法典》到1896年《德国民法典》,再到1937年《瑞士债务法典》和1942年《意大利民法典》(27),成文法传统认为:解释法律应探求法律的立法原意,以保障制订法的稳定和准确实施,法官要按照最符合立法原意的意思来解释法律,使法律意义符合立法者在制定法律条文时的真实想法。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基本法的释法权来源于中国宪法,在性质上属于立法解释。遵照国家成文法传统的立法体制和立法解释方法,全国人大常委会释法采用成文法的立法原意解释方法,认为:“法律解释是对法律含义的阐述,是进一步明确法律规定的具体含义,忠实于立法原意,不能简单地看条文的字面含义,不能根据个人理解随意解释。”(28)
出于对香港普通法传统的尊重,基本法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授予香港法院释法权。香港法院基本法解释权属于司法解释,香港法院在司法活动过程中行使基本法解释权,司法活动在普通法传统下进行,自然也就用普通法的传统解释基本法。普通法传统认为,立法原意是不可捉摸的,是主观的,而且法官也无权把自己的想法作为立法者的想法。(29) 普通法一般采用字义解释规则、黄金规则和弊端规则对法律进行解释,其中“普通法下,文义解释是法院最常用和最优先适用的方法”(30)。香港法院解释基本法时也主要采用普通法的文义解释方法。“法院根据普通法解释基本法时的任务是诠释法律文本所用的字句,以确定这些字句所表达的立法原意。法院的工作并非仅是确定立法者的原意,法院的职责是确定所用字句的含义,并使这些字句所表达的立法原意得以落实。法例的文本才是法律。法律既应明确,又应为市民所能确定,这是大众认为重要的。”(31)
吴嘉玲案淋漓尽致地体现了成文法与普通法的解释方法之间的明显差异。案件涉及对基本法第24条第3款第3项和第22条第4款的解释。(32) 香港终审法院认为,“法院在解释第三章内有关那些为两制中香港制度的重心所在,并受宪法保障的自由的条款,应该采纳宽松的解释。然而,法院在解释有关界定永久性居民类型的条款时,则只应参照任何可确定目的及背景来考虑这些条款的字句”(33)。“对所用字句以及赋予这些字句含义的用于习惯及惯用方法必须加以尊重。”(34) 因此,对于第24条第3款第3项的规定,终审法院认为:“‘[永久性]居民……所生的……子女’,不论是婚生还是非婚生,这些都是该等居民所生的子女。非婚生子女与婚生子女两者没有分别,同样是该等居民所生的。我等认为这是该条文显而易见的意思。”对于第4款规定,终审法院认为:“中国其他地区的人不包括香港居民,这些子女无须内地有关机关批准,即可进入香港特区定居。”(35)
全国人大常委会反对香港终审法院的这一解释,认为“终审法院在判决中对上述基本法条款所作出的解释,不符合立法原意”。全国人大常委会采用立法原意方法解释基本法的这一规定。“基本法第24条第2款第3项这一立法原意体现了防止内地人口大量涌入香港,有利于维护香港的长期繁荣稳定……基本法第22条第4款……的立法原意正是肯定内地与香港之间长期以来实行的出入境管理制度……这一立法原意,完全是为了保证内地居民有序赴港,是符合香港的整体利益的。”(36) 因此,对于第24条第3款第3项的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释法认为:“无论本人是在香港特区成立之前或者以后出生,在其出生时,其父母双方或一方须是符合基本法第24条第2款第1项或第2项规定条件的人。”对于第4款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释法认为:“包括香港永久性居民在内地所生的中国籍子女,不论以何种事由要求进入香港特区,均须依照国家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向其所在地的有关机关申请办理批准手续,并持有有关机关制发的有效证件方能进入香港特区。”(37)
对于释法中有关资料的援引,全国人大常委会在首次释法时就引用了相关立法资料:“本解释所阐明的立法原意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区行政区基本法》第24条第2款其他各项的立法原意,已经体现在1999年8月10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的《关于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24条第2款的意见》中。”与此相反,普通法却认为,法院在作出解释时不能参考有关立法初期的记录、提案报告以及立法备忘录等历史性资料,因为这些资料仅仅只能表明立法时的意图,而真正的意图只能从法律文件的表现形式中寻找,而且立法材料只表明个人观点,与法律中最后规定的相应条款无必然联系,从提案到通过法律,经过各种观点的交锋与妥协,立法意图难以在此过程中保持一致。因此吴嘉玲案中,终审法院认为:“外来资料对基本法的解释有一定的帮助作用,但法院必须谨慎运用,特别是法律颁布后的说明性资料;如果没有全国人大常委会具有约束力的解释,当法院认为法律文本语言清晰时,任何性质的外来资料都不能影响法院的解释”。(38)
全国人大常委会和香港终审法院对于基本法解释所造成的社会后果是截然不同的。“根据终审法院的解释,内地新增拥有香港居留权资格的人士至少167万,吸收这些新移民将为香港带来巨大压力,香港的土地和社会资源根本无法应付大量新移民在教育、房屋、医疗卫生、社会福利及其他方面的需要,因此引发的社会问题和后果将会严重影响香港的稳定和繁荣,是香港无法承受的。”(39) 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释法虽然化解了这一社会危机,但是并不能消除双方法律思维方式的冲突,也无法彻底化解香港对于基本法解释方法的不认同和对解释结果难以接受的局面。
2.3 基本法制度和制度执行的缺失
以成文法形式写出的基本法,简要扼要,应对基本法的司法适用,显然存在很多空白需要填补,基本法司法适用中的争议与基本法有关制度和制度执行的缺失不无关系。
基本法第158条规定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和香港法院的释法权,条款内容的不周延性是引发释法权争议的制度原因,这些已经实际引发释法权争议的制度缺失(40) 至少涉及以下问题:第一,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解释权是否有所限制。尽管香港终审法院最终在刘港榕案中承认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基本法的解释权并不限于在诉讼中提请解释的情况,(41) 但这此之前,这一观点并未得到香港法院的一致认可。香港终审法院曾经认为:“即使终审法院作出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全国人大常委会也只可以对例外条文进行解释。”(42) 第二,全国人大常委会对于授权特区法院自行解释的特区自治范围内条款是否有权解释。早在对基本法草案征询意见时,就有意见认为“人大常委会进行自我约制,不对基本法中纯粹涉及特别行政区内部事务的条款作解释”(43)。第三,对于是否属于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条款的判断权归属,尽管全国人大常委会已经通过释法的行为表明,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判断这些条款是否属于应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的条款,但是在释法之前的吴嘉玲案中,香港终审法院认为其是判断的唯一主体。“我等认为在审理案件时,惟独终审法院才可决定某条款是否符合上述两个条件(即提交人大常委会解释应符合的类别条件和有需要条件),也只有终审法院,而非全国人大常委会,才可决定这些条款是否符合‘类别条件’,即是否属于‘范围之外’的条款。”(44) 第四,特区法院的提请是否是全国人大常委会释法权行使的唯一程序。三次释法行为已经表明,全国人大常委会可以应国务院(45) 或委员长会议(46) 的提请行使释法程序,但在刘港榕案中,香港终审法院认为特区法院提请是唯一程序。“(全国)人大解释权的运用应受到自我约制,在终审法院没有提出要求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解释的情况下,全国人大常委会没有权作出解释的。”(47) 第五,其他一些释法中尚未明确的程序问题。例如,特区法院对释法的理解有误时的解决程序。庄丰源案中,香港终审法院认为,全国人大常委会首次释法中第二部分最末尾一段陈述不属于人大常委会作出的具有约束力的解释的情况,因此,该段陈述不能影响终审法院以普通法对《基本法》第24第1款条作出正确解释后得出的清晰含义。又如促使终审法院提请释法的强制性程序;其他法院提请终审法院裁决时的程序等等。
另一方面,基本法中也有相关制度涉及基本法司法适用中基本法与普通法的关系,但是这些制度尚未付诸实践,导致对普通法和基本法关系的错误认识以及对保留为香港特区法律的普通法的错误定位。基本法第160条规定香港原有普通法要成为香港特区法律必须根据基本法进行适应化,适应化程序包括事先审查和事后审查两种。由于普通法判例数量众多,因此,在1997年2月23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通过的《关于根据基本法第一百六十条处理香港原有法律的决定》中没有对普通法进行逐项审查,只是规定了包括普通法在内的香港原有法律适应化的原则。事后审查则要求在特区成立之后,如果发现普通法与基本法相抵触的,按照基本法规定的程序进行修改或者废除。这一程序迄今并没有真正启动。普通法审查制度的实践运作缺失导致司法适用中对普通法没有正确的定位,也诱发了以普通法规范基本法的不正常现象。
值得关注的问题是,香港特区政府长期以来默许香港法院以普通法传统适用和改造基本法。例如在涉及违反基本法审查权的案件中,作为当事人的香港特区政府并没有质疑香港法院对香港本土条例的审查权;即使是在马维騉案中曾经质疑香港法院违反基本法审查权的香港政府代表律师,也在后面的诉讼中放弃了这一立场:“我等应指出代表入境处处长的资深大律师马先生在本法院聆讯本案时已不再坚持政府较早前在香港特别行政区诉马维騉一案所持的立场。他实际上同意特区法院拥有我等所述之司法管辖权去审核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行为是否符合《基本法》,并且同意该案在这方面的判决与我等所阐述之立场有抵触之处,实属错误。”(48) 庄丰源案中,诉讼双方都同意:“香港终审法院应采用普通法的处理方法解释该条款”,认为这是符合基本法中有关香港特区享有以普通法为基础的不同法律制度的规定。(49) 这固然可以解读为特区政府对香港司法独立的尊重,但从另一个方面,也可以看出香港法院对本土立法违反基本法的审查以及以普通法解释基本法的这一司法过程,香港特区政府也是认可的。
面对香港法院在基本法司法化中的各种做法,全国人大常委会缺少对其给予制度性回应。尽管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了数次释法,但是释法始终没有正面、直接和明确地解决问题。以违反基本法审查权为例:“全国人大释法内容没有质疑终审法院违宪审查的权力,故香港的终审法院在违宪审查这问题上的态度,在没有受到挑战的情况下,得到了承认。”(50) 释法方法争议也存在相应的问题,在全国人大常委会采用立法原意解释基本法后,香港法院仍然坚持以普通法方法解释基本法,面对香港法院的“强势态度”,全国人大常委会却对释法问题始终保持沉默;甚至在香港终审法院对庄丰源案作出与全国人大释法不尽一致的解释后,全国人大常委会也仅仅是“表示关注”。(51) 非制度化的回应缺乏稳定性和可预见性,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基本法司法化的争议,反而可能导致对现有制度的曲解。
三、基本法司法适用争议的实质:普通法的适应化
《中英联合声明》确定了基本法与普通法在香港共生之关系,基本法与普通法的关系是正确定位这两种法律体系共生关系的关键。在基本法司法适用中,香港法院认为,普通法是香港的法律传统,基本法是外来法律,外来法律在普通法的传统中适用,自然应符合普通法的规则。这体现了香港法院对基本法与普通法关系的理解,这一观点显然是对基本法和普通法关系的错误解读。
3.1 普通法不能解释基本法
以普通法传统适用和解释基本法,从本质上歪曲了基本法与普通法之间的关系。1997年香港回归,不仅是主权的回归,而且是法律根本规范的回归。回归前的香港普通法是根据英国的法统,即《英皇制诰》和《皇室训令》的规定明确其适用的合法地位,并进行本土化和适应化发展,从而在香港法律制度中逐渐占据主导性地位。回归后,香港普通法得以保留,香港法律和司法制度基本没有变化,但是香港法律的根本规范已经发生了变化,中国宪法和香港基本法取代英国宪法性法律成为香港的根本规范。“根本规范的特征是:它的效力并不以任何其他法律规范的效力为依归,即不可能提供任何法律规范作为它的效力的理由,而其他法律规范的效力最终都要追溯至这个根本规范的规范。”(52) “1997后香港一切规则的有效性取决于一个基本规范,这个基本规范的有效性来自于中国宪法。”(53) 中国宪法和基本法成为香港法律的新的基本规范,是香港一切法律制度的效力来源。在香港特区实行的一切法律都不能违反中国宪法和香港基本法的规定。根本规范的改变要求普通法必须适应新的宪制秩序进行调整。英属殖民地独立后,新独立国家和地区的普通法纷纷在新的宪制秩序下进行本土化和适应化调整,这是不可改变的发展规律。香港也是一样,基于基本法的规定得以保留的香港普通法,必须根据基本法的规定进行适应化变革。
因此,香港法院以普通法传统适用和解释基本法扭曲了基本法与普通法之间的关系,使得基本法要通过法官的解释进行一种转换,才能成为法律规则加以适用。这样,基本法有可能在普通法的解释下衍生出新的规则,变成法官改造后的基本法,并按照遵循先例的原则,使这种普通法成为特区法律中起决定性和依据性的部分,其结果就是体现全国人民共同意志的基本法被转换和隔离了。(54) 更重要的是,香港法院以普通法传统适用和解释基本法,要求基本法根据普通法的传统进行调整和适应化,使得普通法成为基本法的法源,基本法必须服从和遵守普通法,这从根本上颠倒了基本法与普通法之间的关系,损害了基本法的权威。
3.2 违反基本法审查权——并非予以保留的普通法传统
中国宪法和基本法的实施意味着香港普通法从普通法占主导地位转变为在成文法体制下的普通法,普通法的一切原则和规则必须适应中国宪法和基本法这一成文法体制的要求。基本法第8条保留了普通法在香港特区的效力,但是也对普通法在香港特区的适用提出了两点基本要求:一是能够予以保留的普通法必须属于香港原有法律;二是予以保留的普通法不能同基本法相抵触或未经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机关作出修改。香港法院适用普通法必须符合上述两点要求。
那么,在基本法没有明文规定香港法院违反基本法审查权时,基本法明确保留普通法是否就给香港法院违反基本法审查权提供了足够的法理依据?我们试根据基本法关于保留香港普通法的规定,看看能否从基本法所保留的香港普通法中寻找到香港法院行使违反基本法审查权的根据。众所周知,英国是不成文宪法国家,实行议会至上原则,英国普通法没有对国会立法的违反基本法审查权。英国普通法移植到香港后,虽然根据香港的情况进行了本土化,但是普通法移植的根本目的是维护英国在香港殖民统治的宪制秩序。《英王制诰》和《皇室训令》没有授予香港法院审查本土法律以及英国立法是否与这些宪法性文件相抵触的权力,根据香港普通法规则:“所有的法院受英国枢密院司法委员会规则的约束”,因此,香港法院的司法权限显然不能超越英国法院的司法权限,英国法院不享有违反基本法审查权的普通法传统显然也对香港法院有约束力。因此,在1991年之前,香港法院没有任何一起对香港本土法院是否违宪进行审查的判例。(55)
回归前香港法院违反基本法审查权的提出源于1991年英国对《英皇制诰》第七条的修改以及港英政府赋予《香港人权法案条例》至高无上的地位,开启了香港法院根据《英皇制诰》和《香港人权法案条例》审查香港本土立法的历史。1995年的李妙玲案(56) 中,香港最高法院上诉法庭对香港法院违反基本法审查权予以权威性确认。由此建立了香港法院违反基本法的审查权,并成为回归后香港法院自立违反基本法审查权所遵循的“普通法传统”。
然而,根据基本法中明确的保留普通法传统的条件,这一“普通法传统”并不能在回归后被继续保留。一方面,李妙玲案据以形成的法律依据已经被废除,由此形成的判例已然没有法律效力。根据普通法,法院可拒绝遵守先例,条件之一便是“对于一后来已为成文法或更高级法院所废止的或已在上诉时被撤销的先例,法官不会跟踪之”。(57) 香港违反基本法审查权产生的重要前提是港英当局在1991年赋予《人权法案条例》凌驾性的地位,并由此修改《英皇制诰》,将有关人权法案的内容引入宪法性法律中。这一法律由于与基本法相抵触,在1997年2月23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根据基本法第一百六十条处理香港原有法律的决定》中,作为李妙玲案依据的《香港人权法案条例》中的相关条款已被认定为因与基本法相抵触而无效。根据无效法律作出的判决也应当无效。另一方面,根据普通法不能违反制定法的普通法规则,李妙玲案也不能构成一个有效的先例。遵循先例是普通法的传统,所谓的遵循先例原则,《牛津法律大辞典》就此阐述:“任何一个基于先例基础上的规范,其效力低于建立在制定法和次级立法之上的规范的效力,因此,制定法或次级规范可以凌驾于任何基于先例而产生的规范,甚至将其废除。在有争议和冲突的案件中,制定法是有优先权的。”香港回归后,基本法没有规定香港法院的违反基本法审查权,而是将违反基本法审查权授予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因此,李妙玲案中所建立的香港法院审查权也违反了作为制定法的基本法的明确规定,应当被废除。
四、应对基本法司法适用中的争议
4.1 正确处理普通法与基本法、与特区其他法律之间的关系
从违反基本法审查权到基本法解释权,基本法司法适用中的争议归根到底都是对普通法与基本法、与特区其他法律之间关系的错误认识。正本清源,需要正确理解普通法在香港法律体系中的定位。
回归前的普通法在香港的法律体制中占据主导地位,回归后的普通法是在基本法所构建的法制架构下香港特区法律的渊源之一。基本法是香港特区的宪法性法律,是香港一切法律规范中的根本,是普通法能够保留在香港特区适用的法律根据。没有基本法的许可,香港普通法也不能成为香港特区的法律。“从某种意义上讲,依照基本法对九七前香港普通法的适应化过程,即是依照基本法授予普通法的法律效力的过程。”(58) 普通法必须适应这一宪制秩序的变化,融入基本法所构建的成文法体制中,任何以普通法传统改造、适用、解释和评判基本法的行为,都是本末倒置的行为。因此,香港法院不能以与基本法相抵触的普通法传统为根据自立违反基本法审查权,香港法院也不能以普通法原则解释基本法。
香港特区的成文法还包括在香港适用的全国性法律以及香港特区立法机关制订的条例和附属立法。在香港适用的全国性法律是由全国人大制订的,关系到国家专属的国防和外交权力,普通法也不能挑战这些全国性法律的效力。香港特区立法机关制订的条例是香港成文法的主要构成部分。回归前香港普通法传统中,成文法是优先于普通法的。回归后,根据基本法的规定,普通法可以被香港特区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所修改,这也足以表明,香港特区立法机关制定的条例在效力上高于普通法。
唯一可能接受普通法审查的其他特区法律是附属立法。这一点,《牛津法律大辞典》明确指出:“联合王国没有完全承认司法审查是一种司法机关可以对未生效的立法机关的法律进行质疑和审理的学说,在联合王国,议会的法律是不能被质疑的,然而授权立法的有效性可以被审查。”香港沿袭英国的普通法传统,回归之前,香港法院可以审查由政府部门或者独立的管理机构制定的各种附属立法,法院可以相关附属立法越权为由宣布无效。回归后,基本法保留了这一普通法传统,因此香港回归前有关司法审查的规定和习惯,如果不与基本法相抵触的,将继续为香港特别行政区所采用。根据香港《释义及通则条例》第38条“合法行使权力的推定”的规定,“凡条例授权力予任何人:(a)订立任何附属法例;(b)订立任何文书;或(c)行使任何权力”,只要该附属条例或文书或行使权力的文件已说明是根据条例所授权力而行使的,则推定附属条例或文书和权力已经恰当地履行了条例所要求具备的条件。(59) 可见,附属法例或者权力都源于条例的授权,必须在授权的范围内行使。任何人或机构如果认为上述行为超越条例授权的,均可请求香港法院进行司法审查。
4.2 推进常态化的普通法事后审查机制的形成
《基本法》第160条规定了对普通法的事先审查和事后审查机制,全国人大常委会在根据第160条对香港原有法律进行审查时,实际上并没有对数量众多的普通法进行一一审查,而只是规定了普通法适应化的原则,也即对普通法进行事后审查的原则。香港回归之后,这一事后审查机制也没有在实践中建立和实行。可以说,香港法院迄今为止适用的所有普通法判例和规则都尚未经过事后审查,尚未确定是否抵触基本法。这些未经审查的普通法传统存在着与基本法相抵触的可能性,当然不能作为适用和解释基本法根据。另一个需要接受事后审查的普通法是香港特区成立后由特区法院新创设的普通法规则。普通法推行的法官造法和遵循先例原则,使得特区法院在审判案件的同时又通过案例创造了新的普通法规则,基于对香港特区终审权的尊重,全国人大常委会不能对香港法院的判决进行审查,但是一旦香港法院判决中蕴涵的法律规则或原则成为香港判例法时,这些新判例法规则作为香港特区法律的一个构成部分,也不能与基本法相抵触,也应该接受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事后审查。
因此,有必要根据《基本法》第160条的规定,结合1997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一百六十条处理香港原有法律的决定》中所确立的普通法适应化的原则,审查回归前在香港适用的普通法判例和规则以及回归后香港法院新形成的普通法规则,使其与基本法相适应,并逐步形成以基本法为根本规范的香港特区普通法形成机制,完成香港普通法向香港特区法律的过渡,使普通法成为香港特区法律的重要组成部分。
4.3 维护全国人大常委会对特区的违反基本法审查权
基本法没有授予香港法院违反基本法审查权,但是规定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违反基本法审查权,根据基本法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对特区立法享有备案审查权、对基本法享有最终解释权、对香港原有法律享有事先审查和事后审查权。可以看出,全国人大常委会是特区的违反基本法审查机构,全国人大常委会拥有判断特区立法包括条例和普通法是否违反基本法的审查权,这是不能剥夺,不能否定也不能取代的。
收稿日期:2010-04-09;修订日期:2010-06-15。
注释:
① 违反基本法审查权指香港法院根据基本法对香港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是否违反基本法进行审查,并确定被审查的香港法律效力的权力。学界多称之为“违宪审查权”。鉴于香港基本法不是香港的宪法,而是香港的宪法性法律,本文认为,香港法院的这一权力应称为“违反基本法审查权”更为恰当。
② 吴嘉玲及其他人诉入境事务处处长案,FACV14Y/1998.(中译本判案书)
③ HKSAR v.Ma Wai Kwan,David & Others,[1997] HKLRD761.
④ Heung Lai Wah & Others v.The Director of Immigration,FACV16/1998.
⑤ 吴嘉玲及其他人诉入境事务处处长案,FACV14Y/1998.(中译本判案书)
⑥ 香港终审法院1999年2月26日的澄清性判决。FACV000014AY/1998.
⑦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二十二条第四款和第二十四条第二款第(三)项的解释》。但遗憾的是,全国人大常委会的首次释法也没有对香港法院的违反基本法审查权表示否定。
⑧ 黄江天著:《香港基本法的法律解释研究》,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2004年版,第208页。
⑨ 香港特别行政区诉吴恭劭及利建润案,[1999]3 HKLRD907.
⑩ 本案涉及此两条特区立法是否违反《公民权利及政治权力国际公约》、基本法及香港人权法案条例的问题。香港高等法院认为此两条特区立法违反基本法无效。案件随后上诉至香港终审法院,1999年12月15日,终审法院由五名法官组成的合议庭一致裁定,推翻高等法院上诉庭的这一判决。
(11) 乔晓阳:《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二十二条第四款和第二十四条第二款第(三)项的解释(草案)》的说明》。
(12) 庄丰源案中,香港法院坚持“在解释基本法中必须适用普通法”的立场,并认为,解释基本法应当根据“法律文本中明确表示的语言所代表的立法意图,并不是立法者自己的意图”;外来的资料对解释基本法有一定的帮助作用,但法院必须小心运用这些外来资料,特别是法律颁布后的说明性资料。而如果没有人大常委会具约束力的解释,当法院认为法律文本语言清楚时,任何性质的外来资料都不能影响法院的解释。The Director of Immigration v.Chong Fung Yuen,FACV No.26 of 2006(中译本判案书)。
(13)“就香港特区终审法院对居港权案的判决,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发言人发表谈话”,《法制日报》,2001年7月22日。其中写道:“我们注意到,1999年6月2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对香港基本法有关条款作出解释以来,香港特区法院在涉及居港权案件的判决中,多次强调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基本法所作的解释,对香港特区法院具有约束力,并以此作为对一些案件判决的依据。但是香港特区终审法院7月20日对庄丰源案的判决,与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有关解释不尽一致,我们对此表示关注。”
(14) Leung Kwok Hung & Koo Sze Yiu v.Chief Executive of the HKSAR,HCAL107/2005.
(15) Leung Kwok Hung & Others v.HKSAR[2005]3 HKLRD 164,FACC No.1 & 2 of 2005.
(16) 陈友清:《1997—2007:一国两制法制实践的法理学观察——以法制冲突为视角》,2007年西南政法大学博士论文,第89页。
(17) 蒋朝阳:“从香港法院的判决看基本法的解释”,《港澳研究》,2007年7月夏季号,第84页。
(18) 邵善波:“成文宪法对香港原有司法体制的影响”,《港澳研究》,2007年冬季号,第73页。
(19) Marbury v.Madison,1 Branch 137,2L.Ed.60(1803).
(20) 吴嘉玲及其他人诉入境事务处处长案,FACV14Y/1998.(中译本判案书)
(21) 此外,学界还认为,基本法允许香港终审法院在审判案件时可以参照其他普通法适用地区的司法判例,在相关案件中,确立美国违反基本法审查权的马伯里案,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也是根据法院是法律的最终解释者这一规定推导出美国法院的违反基本法审查权。徐志群:“论香港特别行政区司法审查权的扩大”,纪念香港基本法颁布十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2000年4月。还有学者认为,基本法允许香港原有法律传统的保留,回归前香港法院已经有违反基本法审查权的先例,根据遵循先例原则,香港法院应该具有违反基本法审查权。陈弘毅:“论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的违反基本法审查权”,《中外法学》,1998年第5期。
(22) 陈文敏:“司法独立是香港重要基石:对内地法律专家的评论的回应”,佳日思等主编:《居港权引发的宪法争论》,香港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23) 2001年7月21日,香港各大报章的专题报导。黄江天著:《香港本法的法律解释研究》,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2004年版,第375-376页。
(24)同(23),第16页。
(25) The Director of Immigration v.Chong Fung Yuen,FACV 10 & 11/2000.
(26) 吴嘉玲及其他人诉入境事务处处长案,FACV14Y/1998.(中译本判案书)
(27) 1804年法国《拿破仑法典》第1156条规定:“在契约中,应探求契约当事人的共同意思,而不应停留于字句的文字意义”。1896年《德国民法典》:“解释意思表示,应探求其真意,不得拘泥于字句”。1937年《瑞士债务法典》第18条第1项:“为了判断一个契约的方式和条款,须探求各当事人真正和共同的意思,而不停留于其可能因为错误或为了掩盖该契约的真正性质而适用的不正确的词语和名称。”1942年《意大利民法典》规定:“解释法律必须根据上下文和立法者的意图探求文字的真实意思,不得附加其他意义。”
(28) 参见乔晓阳在2004年4月7日到9日就全国人大常委会2004年4月6日对香港基本法附件一第七条和附件二第三条有关规定的解释会见香港各界人士时的讲话。“乔晓阳一行就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基本法附件的解释与香港各界会面”,http://www.gmw.cn/01gmrb/2004-04/09/content_11322.htm,2010年1月访问.
(29) 李浩培著:《条约法概论》,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344页。
(30) 陈弘毅:“当代西方法律解释学初探”,梁治平主编:《法律解释问题》,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
(31) The Director of Immigration v.Chong Fung Yuen,FACV No.26 of 2006.(中译本判案书)
(32) 基本法第24条第3款第3项规定“第(一)、(二)两项所列居民在香港以外所生的中国籍子女”;第22条第4款规定“中国其他地区的人进入香港特别行政区须办理批准手续”。
(33) 吴嘉玲及其他人诉入境事务处处长案,FACV14Y/1998.(中译本判案书)
(34) Minister of Home Affairs v.Fisher[1980]AC 319,329 E.
(35) 吴嘉玲及其他人诉入境事务处处长案,FACV14Y/1998.(中译本判案书)
(36) 乔晓阳: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二十二条第四款和第二十四条第二款第(三)项的解释(草案)》。
(37)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二十二条第四款和第二十四条第二款第(三)项的解释》。
(38) 吴嘉玲及其他人诉入境事务处处长案,FACV14Y/1998.(中译本判案书)
(39) 董建华:《关于提请中央人民政府协助解决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有关条款所遇问题的报告》。
(40) 邹平学:“香港基本法解释机制若干争议性问题探析”,《香港基本法、澳门基本法研讨会论文集》,2008年,胡锦光著:《中国宪法问题》,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315页。其他学者也做了大量研究。
(41) 刘港榕诉入境处处长,[1999]3HKLRD 778.
(42) Lau Kong Yung and 16 Others v.Director of Immigration,FACV 10 & 11 of 1999.
(43) 《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草案)》征求意见稿咨询报告(5),1988年10月,第468页。
(44) 吴嘉玲及其他人诉入境事务处处长案,FACV14Y/1998.(中译本判案书)
(45) 全国人大常委会1999年6月24日的首次释法:《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二十二条第四款和第二十四条第二款第(三)项的解释》以及全国人大常委会2005年4月27日的第三次释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五十三条第二款的解释》都是应国务院的提请进行释法。
(46) 全国人大常委会2004年4月6日的第二次释法:《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附件一第七条和附件二第三条的解释》,本次释法是应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委员长会议的提请进行释法。
(47) Lau Kong Yungand 16 Others v.Director of Immigration,FACV 10 & 11 of 1999.
(48) 吴嘉玲及其他人诉入境事务处处长案,FACV14Y/1998.(中译本判案书)
(49) The Director of Immigration v.Chong Fung Yuen,FACV No.26 of 2000(中译本判案书)。
(50) 香港特别行政区诉吴恭劭及利建润案,[1999]3HKLRD907,第71页。
(51) “香港特别行政区终审法院7月20日对庄丰源案的判决,与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有关解释不尽一致,我们对此表示关注”,《法制日报》,2001年7月22日。
(52) 陈弘毅:“香港回归的法学反思”,《从理论到实践: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Butterworth Asia Hong Kong·Singapore·Malaysia(1998).p.173.
(53) Wacks,China,Hong Kong and 1997:Essay in Legal Theory,HongKong University Press,1993,p.179.
(54) 蒋朝阳:“从香港法院的判决看基本法的解释”,《港澳研究》,2007年7月夏季号,第87页。
(55) 1991年之前香港法院有关《英皇制诰》的案件都是一些涉及政府行政行为合法性的司法审查,而不是对立法的违宪审查。林峰:“基本法对香港司法审查制度的影响”,《法学家》,2001年第4期,第109-110页。
(56) Lee Mui Ling and another v.A.G.[1996]1 HKC.
(57) 洪秉钺、关道培著,郑振武译:《香港法律指南》,中华书局香港有限公司,1995年版,第21页。
(58) 董立坤:“论香港的普通法”,《港澳研究》,2005年创刊号,第87页。
(59) 香港《释义及通则条例》,香港法例第1章第38条。
标签:香港基本法论文; 普通法论文; 法律论文; 全国人大常委会论文; 法律规则论文; 释法论文; 立法原则论文; 司法程序论文; 法官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