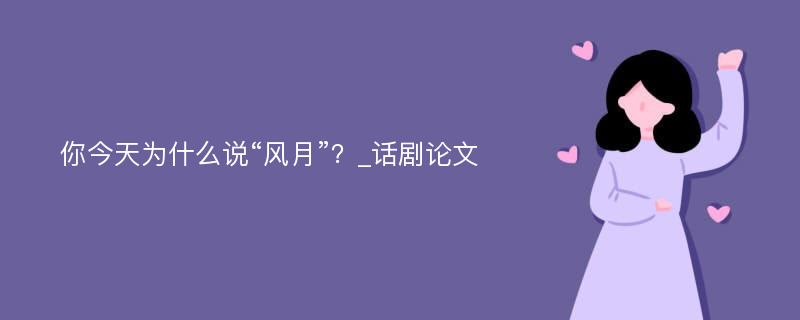
今日缘何说“风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风月论文,今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日,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推出的五幕话剧《风月无边》引起了观众的极大兴趣,据悉戏票已预售出大部,票房收入已达100多万, 这在当下的话剧舞台上实属难得,自然也引起戏剧理论界和媒体的关注,各家报刊争相发表评论,“人艺”也召开了有关专家、剧评家以及记者在内的座谈会听取各方面的意见。迄今为止,对《风月》一剧的评价无外乎三种:充分肯定的;完全否定的;大部肯定但觉存有缺憾的。但是无论如何,我以为《风月无边》这出话剧还是有许多话题值得我们进行思考和研究的。
话剧品种的“另类”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是大众十分关注的剧院,拥有一大批“人艺迷”,无论她上演什么剧,都会有一批忠实的观众前来观看。这是历史形成的。因为她有着焦菊隐先生创立的人艺风格,有着一茬接一茬的艺术成熟、手法娴熟、功底深厚的导演和演员,有着全剧“一棵菜”精神的无比敬业的全体演职员工,有着新中国话剧史上骄人的业绩。而此次由北京人艺院长著名剧作家刘锦云编剧、著名导演林兆华和青年导演李六乙联合执导的《风月无边》,几乎启用了院内最强的演员力量:濮存昕、徐帆、梁冠华、何冰、吴刚以及特邀外请的几位演员,加上著名美术师易立明的舞美灯光服装设计,强大的创作集体和演出阵容无疑为其市场运作提供了成功的基础与保证。事实也正是如此,如果从剧场的反映和票房的预售情况来看,《风月》是成功的。
与人艺不同时期的不同风格的话剧相比,《风月无边》既非老舍风格的北京风味,也非郭氏风格的历史品评,更非曹禺风格的人生极致,同时也不同于近些年来人艺一剧一格的许多剧作。它所追求的可说是另一种风格,或说纯粹是一种意境。它的优雅的表演、诗化的导演、空灵典雅的舞美以及幽蕴风致的音乐设计,给首都热闹喧嚣甚至躁动不安的话剧舞台吹来的,是一股沁人心脾的杨柳春风。看后很有令人耳目一新、神情一爽之感。观众普遍的反映是:好看!
话剧的“好看”有几种,它可以场面热闹见长,亦可以思想深刻取胜;可以强烈的戏剧性引人入胜,亦可以丰富的人物形象发人思悟。
而《风》剧所走的却不是这些路子。如果用一个字概括它的成功,我以为是一个“美”字。说它是艺术的惟美我以为也并不为过。以美取胜——这在近年来、以至可以由此上推至新时期以来话剧舞台上,是很鲜见的“另类”品种。
长期以来,话剧界都在自觉、不自觉地恪守着一条不成文的原则,那就是所谓话剧的“战斗性”传统。这一方面与话剧进入中国之时及其形成过程中的历史时代背景有关,另一方面则是由于话剧这种艺术的灵活快捷而使我们为了一时的政治需要人为地为其“增负”有关,以至让人们几乎忘记了话剧的另一个非常重要的艺术属性——审美。对于戏曲人们可以不计内容而去单纯欣赏它的唱腔美、舞蹈美,可以专为听一位演员而去看熟而又熟的剧目——其形式已经大于、或曰优于了内容。而对于话剧则很难做到这一点。但《风》剧在此方面已露端倪。有些人就是为欣赏濮存昕、徐帆、梁冠华等大牌而去,更有些人看过后还想再看,就是要感受那舞台深邃幽远空灵的意境,就是要听听徐帆唱昆曲,就是要让心灵在那幽幽咽咽、如泣如诉的笛声中得到片时的宁静与解脱……多少年来的话剧干预政治、干预生活、高堂教化、故作深沉的毛病不见了,有的是倜傥风流,满台风月。没想到进入2000年之后,话剧也可以完全赏心而悦目了。
形式和内容——谁更重要
如果就《风》剧的内容——剧本——来看,业内人士是颇有微词的。一说该剧缺少高潮,或说它的高潮缺少必要的铺垫,雪儿跳江自杀没有其逻辑上的必然性与合理性;一说该剧主要人物的性格没有发展,从开场到结束,人物基本上是在原地停顿;一说该剧的主要人物李渔与历史上的李渔相去甚远,剧情和人物都显得过于单薄;一说李渔本是一个很复杂的人物,现在在他身上看不到在明末清初那种政治高压、文化高压之下知识分子的压抑忧患和复杂心态,缺乏历史的社会的深度与厚重。
作为一个历史上的真人,李渔确属毁誉参半的历史人物,与他同时乃至后世之人对他的评价天上地下,歧义数百年。然而剧作者既没有截取由明入清那一段动荡历史去抒写一代文人李渔的动荡心路、情感变迁,也没有截取晚年李渔撰写他一生最高成就的《闲情偶记》时的艺术皈依、人生感悟,而是以李家班搬演他的剧作《比目鱼》为主要载体,抒写他与他的家伎雪儿、霁儿以及袁姨等几个女人之间的情感性灵。于是历史上真实的李渔似乎不再重要,复杂多义的李渔变得简单,剩下的便是玉笛檀板,浅吟低唱,轻歌曼舞,风月无边了。将这样一个文本搬上话剧舞台,目前的呈现便成了一种最佳状态的外在形式。在这种充满诗情画意的形式里,一些先天的不足都被美的包装掩藏起来,可以忽略而不计了。这得益于导演的聪慧,得益于舞美的造境,得益于音乐的悠雅,得益于演员的功力,更得益于昆曲的唱腔音乐——它本身就具备的“独立审美价值”。
以传统的观点看问题,内容决定形式,形式反过来影响内容;内容是形式的内在依据,形式是内容的外在体现。二十多年来,中国话剧在内容上比起老一辈剧作家如曹禺、老舍的作品说来,没有太多的超越,甚至没有超越,所作的大多是在形式上的花样翻新。所以对于那些只重形式翻新而无内容新意的作品,批评家谓之“形式大于内容”。
然而这句具有贬意的批评在《风月无边》面前似乎有些显得少了些力度。可以这样说:《风》剧正是在它的舞台呈现的全部形式中找到了表现其内容的最佳状态。在这里,形式即内容,抽去其形难言其实。
形式变成一个重要的卖点,一种独立的审美,变成此剧的支撑和神韵。很多人已不再注重剧情的合理、逻辑的周全,人物的单一以及明显的疏漏,戏剧的文本意义已经在看戏过程的不知不觉之中发生置换。正如到天安门看升旗,升旗就是升旗,内容早已了然,而还要去看的原因是要在国旗班那一系列升旗的仪式中感受一种伟大崇高,接受一次灵魂洗礼,体味一回庄严神圣;亦如大批海外华人到黄帝灵祭祖,内容已不重要,重要的是要亲身参加那神圣仪式,重要的是这形式背后的民族精神所带来的强大的血的凝聚力。《风》剧的意义抑或也在于此?!
今日缘何说风月
《风》剧的编剧是刘锦云,其开山之作是新时期以来影响巨大的话剧《狗儿爷涅槃》。之后又创作过《背碑人》《阮玲玉》直至这回的《风月无边》。导演林兆华则更是新时期以来创作颇丰的一位大导演,导过各种风格流派的作品。此次他们俩人的再度合作,有一点相通之处,那就是各自都从喧嚣走进沉着,从“深刻”走进平和,褪尽火气走入美的天地,共同演绎生死的恋情、自由的人性、痴迷的执著。从这一角度看问题,这也许可以视为话剧向其本体——艺术审美的回归,进入了一种人生人性层面的追求。也许预示着话剧艺术由此而进入了一种真正的艺术的美的可以剥离种种负担范囿的独立审美层面。但是,如果换一个角度看问题,便会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那就是:一个关注现实关注农民关注社会的剧作家,一个富有忧患意识和反思精神以及责任感使命感都很强的剧作家,十几年来从现代农民的典型狗爷退至三四十年代的影星阮玲玉,再退至封建士大夫情趣中的李渔,以李渔之风月浇心中之块垒?这种创作现象说明什么呢?即便是写李渔,也是写得缩手缩脚,我们的剧作家是在逃避什么呢?
今日缘何说风月?我以为这不是锦云先生的问题。不管怎样,锦云还在写话剧,有多少八十年代曾经叱诧风云的话剧作家早已撂笔了!?
看看八十年代的话剧舞台:《报春花》《枫叶红了的时候》《狗儿爷涅槃》《桑树坪纪事》《小井胡同》《大雪地》《田野又是青纱帐》《榆树屯风情》……一大批反映现实的作品。这还不去说那一大批“探索性”剧目。再看看九十年代乃至目前的话剧舞台:《人民公敌》《科诺克或医学的胜利》《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死无葬身之地》《居里夫妇》《等待戈多》《玩偶之家》《哈姆雷特》《社会形象》《盗版浮士德》《三毛钱歌剧》《钦差大臣》……一大堆外国剧目,直至与《李白》攀谈,寻找那《风月无边》。
我们的话剧怎么了?我们的剧作家上哪儿去了?
有评论家说:“戏剧(特别是话剧)进入九十年代出现了个奇怪现象:开放以来第一代作家集体性失语——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停止创作。这种情况当然有着深刻的内部外部原因,但其中一个不容回避的事实是:作家的创造能力遇到了现实的挑战,作家无法对现实作出自己满意的艺术回应。”另外,我们有许多剧作家当了官之后笔下也就迟钝起来,更有许多人干脆去触“电”挣钱了。留下的人则必须手持双刃剑、横向作战——一边面对市场,一边面对主管,又要讨好,又要挣钱——自然累得可以。风花雪月、才子佳人,轻松愉快些也好。
标签:话剧论文; 戏剧论文; 李渔论文; 风月论文; 艺术论文; 人艺论文; 爱情电影论文; 中国电影论文; 智利电影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