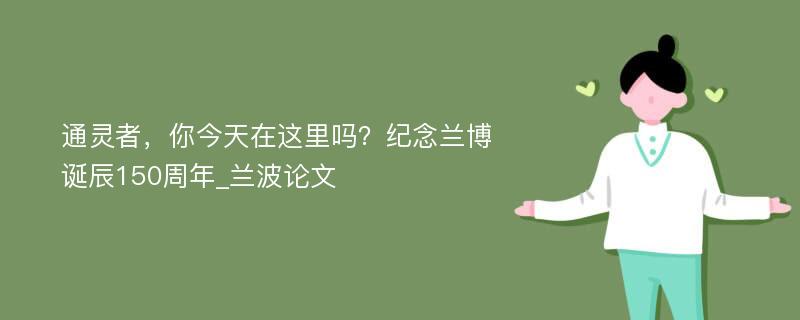
通灵者,今安在?——纪念兰波诞辰150周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诞辰论文,周年论文,通灵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很少有这样的诗人,时过境迁,只要他的诗歌与灵魂再现,总令人耳目一新;他像一个温柔的孩子,只要喃喃低语,总在发出含混不清的语音,而这种声音不仅发人深省,更在不经意间,将人们带入一个又一个深美的梦境——这就是法国诗人、被称为通灵者的阿尔蒂尔·兰波(Arthur Rimbaud,1854-10-20~1891-11-10)。
但越是这样的诗人,这样的通灵者,越容易被淹没在“大师”与“天才”的赞誉中,这些赞誉与其说是光环,不如说是圈套,套住了世代的孩童,转世的兰波——因为当他们说出谁是“大师”或“天才”的时候,这个人已和常人相隔万里;而它的潜台词则是:除了兰波,还会有第二个“通灵者”吗?不会有了,而兰波这个天才也已经故去。试想,如果这些人与兰波生活在同一个时代,他们又会怎样对待他呢?有这样一些细节一直为世人所忽略,而骄傲的巴黎人就更不愿意提起了:1870年8月29日,当16岁的兰波带着美梦离开家乡,那个沉闷的小城夏尔维勒(Charleville),第一次来到巴黎的时候,——“刚下火车就被抓住,因为没有一分钱,还欠了13法郎的火车票钱,我被带到了警察局”(兰波书信,1870年9月5日),(注:引自《兰波作品全集》,东方出版社,2000年,本文作者译,第323页,第379页,第330页,第4页,第23页,第65页,第328页,第319页,第12、17页,第21页,第138、140页,第137、139页,第260页,第203页,第110页,第221页,第207页,第219页,第219页。)幸亏他的老师乔治·伊桑巴尔收到他从监狱里寄出的求助信,才将这个可怜的孩子保释;而现如今,在巴黎,从塞纳河畔的书摊,到大大小小的精品书屋,当兰波诗集和兰波肖像、手迹纷纷被放在最显著的位置之际,谁愿提起那不愉快的当初?然而这一切,后世的人们不应该忘记。除了阅读兰波从监狱里发出的求救信,最好再了解一下兰波在放弃文学之后的经历和他当时的心情:“糟糕的食物、肮脏的住所、单薄的衣衫,种种忧郁、烦愁”(兰波书信,1891年2月20日)。(注:引自《兰波作品全集》,东方出版社,2000年,本文作者译,第323页,第379页,第330页,第4页,第23页,第65页,第328页,第319页,第12、17页,第21页,第138、140页,第137、139页,第260页,第203页,第110页,第221页,第207页,第219页,第219页。)可想而知,这些境遇和感觉不仅来自于病痛及长年在沙漠中的旅行、漂泊,更缘于心中的悲苦、孤寂。我想,了解并重新认识这一切,是我们今天重读兰波诗歌的前提。否则,一个“天才”再加一个“大师”的称谓,会让死去的兰波再次死去,孤寂的兰波更加孤寂。
我们今天纪念兰波,有必要忏悔、反省,想想兰波如果活在今天,会比当初更幸运么?我们今天纪念兰波,就是要将这位曾经忍受了种种孤独和苦难的孩子,迎回人类温暖的家庭——如果说今天的人类还有些温暖,那么这些暖意也只来自于尊重灵魂的心灵。而一个受苦的孩子,为什么会在他所处的时代创造出奇迹?我想,也许正因为他在苦难的岁月里始终保持着一颗童心。孩童的心灵也许正是成为一个通灵者的前提,就好像“质本洁来还洁去”的花魂、鸟魂,才真正配得上“通灵宝玉”。
听听兰波对“通灵者”(voyant)的描述:“必须使各种感觉经历长期的、广泛的、有意识的错轨,各种形式的情爱、痛苦和疯狂,诗人才能成为一个通灵者;他寻找自我,并为保存自己的精华而饮尽毒药。在难以形容的折磨中,他需要坚定的信仰与超人的力量;他与众不同,将成为伟大的病夫、伟大的罪犯,伟大的诅咒者——至高无上的智者!——因为他达到了未知!他培育了比别人更加丰富的灵魂!他达到了未知;当他陷入迷狂,最终失去视觉时,却看见了视觉本身!”(兰波书信,1871年5月15日)(注:引自《兰波作品全集》,东方出版社,2000年,本文作者译,第323页,第379页,第330页,第4页,第23页,第65页,第328页,第319页,第12、17页,第21页,第138、140页,第137、139页,第260页,第203页,第110页,第221页,第207页,第219页,第219页。)
重读兰波的诗歌、书信并回顾他的生平,让我们重新思考这个通灵的孩子如今会给我们怎样的启示。
一、“起初的爱心”——将伤痛化为美
兰波诗歌的开篇,就献上了一份《孤儿的新年礼物》,诗中写道:
卧室布满阴影,人们隐约听见
两个孩子温柔伤心的低语。
他们正歪着脑袋,昏沉沉地梦想,
长长的白窗帘随风颤抖、飘扬……
——窗外受冻的鸟儿正互相贴近……(注:引自《兰波作品全集》,东方出版社,2000年,本文作者译,第323页,第379页,第330页,第4页,第23页,第65页,第328页,第319页,第12、17页,第21页,第138、140页,第137、139页,第260页,第203页,第110页,第221页,第207页,第219页,第219页。)
这首诗是写两个伤心的孩子,在新年到来之际,躲在大窗帘后面互相取暖,因为他们的母亲刚刚去世;在这个“没有羽毛,没有温暖的巢穴”里,这两个孩子又经历了一场场美梦,梦见了“金光闪闪的糖果,亮晶晶的首饰”,旋转的舞步,母亲的亲吻……
像这样凄美的场景在兰波的诗歌中一幕又一幕地出现,惊心动魄。比如在诗歌《奥菲利娅》中:
黑暗沉寂的波浪上安睡着晚星,
洁白的奥菲利娅像一朵盛大的百合随风飘动……
千年就这样过去,自从忧伤的奥菲利娅,
这白色幽灵在黑色长河上漂移……(注:引自《兰波作品全集》,东方出版社,2000年,本文作者译,第323页,第379页,第330页,第4页,第23页,第65页,第328页,第319页,第12、17页,第21页,第138、140页,第137、139页,第260页,第203页,第110页,第221页,第207页,第219页,第219页。)
在黑白相映的场景中,诗人拨动了心弦,触及到人类心灵深处、梦想深处最深切的诗意与苦楚,而这些“纯客观”的描述同时蕴含着至深的爱与同情,因而使得这样的场景、这样的诗句刻骨铭心。
再看《惊呆的孩子》:一群饥寒交迫的穷孩子在雪雾之中,撅着屁股扒在窗前,看那面包师油腔滑调地哼着歌谣,从炉膛里取出热烘烘的面包……
还有《乌鸦》、《星星在呻吟》中所描绘的战争之后的场面:乌鸦成群地飞过,无辜的牺牲者静卧荒野。尤其是在《深谷睡者》中,诗人动情地描述了这样一位年轻的士兵,他像一个病弱的孩子,脸色苍白,仰面朝天,躺在深谷的花丛中,“阳光在他的绿床上洒下泪雨”,但是——
花香已不再使他的鼻翼颤动,
他安睡在阳光里,一只手搁在前胸,
在他胸腔右侧,有两个红色的弹孔。(注:引自《兰波作品全集》,东方出版社,2000年,本文作者译,第323页,第379页,第330页,第4页,第23页,第65页,第328页,第319页,第12、17页,第21页,第138、140页,第137、139页,第260页,第203页,第110页,第221页,第207页,第219页,第219页。)
时光流逝,生命飘失,留在人类记忆深处的,并非轰轰烈烈的战争场面,而是硝烟刚刚散去之后的情景。尽管这一切只是瞬间的画面,但却包含了历史,包含了人间的悲欢离合。而一代又一代,人类至今重演着以往的悲剧,也正因为如此,通灵者的诗歌愈读愈美,我们仿佛在诗中与逝去的灵魂面面相觑。
我常想,为什么20世纪诸多现代派的诗歌及绘画作品,在经历了一个世纪的风雨之后纷纷凋零;就连波德莱尔的《恶之花》今天看起来也已失去了当年的神奇与魅力;而为什么兰波的诗歌却越读越美好,越清新?道理并不复杂:化腐朽为神奇,不如将伤痛化为美;而要做到这一点,一个人必须保存“起初的爱心”。
有爱才有灵。而单凭技巧的种种艺术,都将随时光的流逝凋零、枯萎。正如《新约·启示录》(第2章4节)说:“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而面对兰波,面对他的诗,深藏其中的爱与美一同将人们惊醒。
二、让酒神与日神干杯
尼采在他的第一部著作《悲剧的诞生》中曾以酒神与日神来表述艺术的起源,这与柏拉图的灵感说其实存在着某种契合——柏拉图将艺术灵感的来源描述为神灵附体,陷入“迷狂”状态。而尼采认为,当酒神从内心迸发,产生“整个情绪的激动与亢奋”,艺术“作为驱向放纵之力”,(注:尼采《悲剧的诞生》,周国平译,北京:三联书店,1986年,第2页。)支配并迫使人们开始创作,以释放所有情绪。这与兰波所说的“经历各种形式的情爱、痛苦和疯狂”,“为保存自己的精华而饮尽毒药”不谋而合。而这里的“毒药”(les poisions)似乎比酒更烈,对人伤害更深;事实上也正是如此,兰波因啜饮“毒药”(不仅是麻醉品),在灵光四射的同时过早地耗尽了年轻的生命。
兰波在书信中更明确说出:“当他(诗人)陷入迷狂(affolé),终于失去视觉时,却看见了视觉本身!”——“视觉”,不正是日神引领人类看见的景象么?——尼采说:“我们用日神的名称通称美的外观的无数幻觉”。日神“作为驱向幻觉的力量”,它的状态是梦,主导造型艺术,如绘画、雕塑;酒神作为“驱向放纵之力”,(注:尼采《悲剧的诞生》,周国平译,北京:三联书店,1986年,第2页。)它的状态是醉,主导非造型艺术,如音乐。那么诗歌呢?应该是先醉后梦。
尼采用酒神与日神的学说完美地解释了希腊神话与《荷马史诗》的诞生:一个因内心冲突而痛饮美酒的古希腊人,醉卧牧场,梦见四周的山林溪谷中,现出形形色色半人半兽的神灵……而比尼采晚十年出生,早九年去世的兰波说:“所有的古诗都归于希腊诗歌,和谐的生命”(注:引自《兰波作品全集》,东方出版社,2000年,本文作者译,第323页,第379页,第330页,第4页,第23页,第65页,第328页,第319页,第12、17页,第21页,第138、140页,第137、139页,第260页,第203页,第110页,第221页,第207页,第219页,第219页。)——兰波并没有读过尼采,他自己的内心明明是冲突的(像尼采所说的那样,像古希腊人一样),但他认为,古希腊人的生命归于和谐。巧合的是,兰波关于“通灵者”的书信与尼采的《悲剧的诞生》写于同一年——1871年。这是怎样的英雄所见略同!
如果说尼采是酒神与日神学说的奠基者;兰波则是这一理论的实践者甚至化身。所不同的是,尼采强调的是酒神狄俄尼索斯,并且认为崇尚酒神的艺术高于崇尚日神的艺术;而兰波这个通灵的孩子则认为,诗人应该是个voyant[voyant这个词源于voir(看),拉丁文videre,而voyant则是“慧眼人”、“视觉超凡者”,译成通灵者属意译];与此同时,兰波也强调“迷狂”,并有诗为证。看看《地狱一季》的狂乱篇章,再读一读《醉舟》,那比比皆是的“神圣的混乱”,还用别的什么来证明兰波确曾醉得飘飘欲仙,甚至不醒人事么?
可见兰波这个自称“被缪斯的手指触碰过的孩子”(注:引自《兰波作品全集》,东方出版社,2000年,本文作者译,第323页,第379页,第330页,第4页,第23页,第65页,第328页,第319页,第12、17页,第21页,第138、140页,第137、139页,第260页,第203页,第110页,第221页,第207页,第219页,第219页。)(兰波书信,1870年5月24日)也确曾被酒神触碰过;岂止是碰过,分明是爱过,赏赐过。少年时期,他常常沉醉于自己内心的原始冲动。比如在《太阳与肉身》一诗中,诗人抑制不住对希腊古神的崇拜,纵情放歌——
太阳,这温情与生命的火炉,
将燃烧的爱情注入沉醉的泥土,
当你躺在山谷,你会感觉
大地正在受孕,并溢出鲜血……
思想,这匹被禁锢了太久的野马,
让它从人类的头脑里蹿出!(注:引自《兰波作品全集》,东方出版社,2000年,本文作者译,第323页,第379页,第330页,第4页,第23页,第65页,第328页,第319页,第12、17页,第21页,第138、140页,第137、139页,第260页,第203页,第110页,第221页,第207页,第219页,第219页。)
灵魂在诗中找到“光辉的肉体”,思想蹿出苍白的牢笼,希腊众神一一从梦中现形,从心底复活。这是怎样的形象——
在夏日朦胧的月光里,德律阿得斯
(树神)
赤身裸体,站在镀金的苍白之中,
呜咽的河水浸染了他的满头青丝,
在阴暗的林间空地,青苔布满星辰,
这位林间仙女,默默仰望着苍穹……(注:引自《兰波作品全集》,东方出版社,2000年,本文作者译,第323页,第379页,第330页,第4页,第23页,第65页,第328页,第319页,第12、17页,第21页,第138、140页,第137、139页,第260页,第203页,第110页,第221页,第207页,第219页,第219页。)
在此,生命的原始冲动化为了真实可见的形体甚至肉体。再看《醉舟》,是一只小船喝醉了,还是诗人自己心醉了?总之,这里的“我”已不再是作者本人,而是自言自语、浪迹天涯的一叶醉舟——
我梦见雪花纷飞的绿色夜晚
缓缓升腾,亲吻大海的眼睛,
新奇的液汁涌流循环,
轻歌的磷光在橙黄与碧蓝中苏醒!
……
我看见恒星的群岛,岛上
迷狂的苍天向着航海者敞开:
你就在这无底的深夜安睡、流放?
夜间金鸟成群地飞翔,噢,那便是蓬勃的未来?(注:引自《兰波作品全集》,东方出版社,2000年,本文作者译,第323页,第379页,第330页,第4页,第23页,第65页,第328页,第319页,第12、17页,第21页,第138、140页,第137、139页,第260页,第203页,第110页,第221页,第207页,第219页,第219页。)
全诗整整一百行,通篇都是ABAB的交叉韵,自然天成,天衣无缝。记得后期象征主义诗人瓦莱里曾说过:诗永无定稿。意思是诗歌都可以无止境地改下去,越改越好。也许瓦莱里或马拉美的诗歌就是这样。但这种说法在兰波这里似乎行不通,兰波的诗一气呵成(虽无从考证),与前两者相比,兰波很显然更得酒神的恩宠。而在瓦莱里与马拉美这两位诗人那里,似乎只有日神大行其道。
从兰波的全部作品和他一生的经历来看,他的灵魂乃至生命正如一叶醉舟,由醉入梦,由梦成为“通灵者”,继而看见“视觉本身”,看见梦的深处,那心灵深处最壮丽、奇异的景色。
三、“我”是另一个——超越“有我”与“无我”
如果将《醉舟》中的“我”理解为作者本人,有些地方就不合适了,比如:
比酸苹果肉在孩子的嘴里更甜蜜,
绿水浸入我的松木船身……
我正航行,这时,沉睡的浮尸碰到
我脆弱的缆绳,牵着我后退!
我,一叶迷失的轻舟陷入杂草丛生的海湾,
又被风暴卷入一片无鸟的天湖……(注:引自《兰波作品全集》,东方出版社,2000年,本文作者译,第323页,第379页,第330页,第4页,第23页,第65页,第328页,第319页,第12、17页,第21页,第138、140页,第137、139页,第260页,第203页,第110页,第221页,第207页,第219页,第219页。)
可见这里的“我”并非作者本人,而是醉舟;是小舟在说话,自言自语,自歌自舞;这样看来,醉舟顿时获得了灵性,与飘荡的灵魂相互应和。
通读兰波的诗文,其中的“我”一会儿是流浪儿,一会儿是小铁匠,一会儿是苦闷的少年修士,一会儿又是狂奔狂喜的醉舟,随后又变成了不知什么人,飘到了不知什么地方,直到折戟沉沙,又变回一个无辜的孩童,却依然是一名勇敢的“盗火者”。(注:兰波在1871年5月15日写给保罗·德梅尼的信中说:“诗人是真正的盗火者。”见《兰波作品全集》,第331页。)
这已不是什么秘密。早在1871年5月15日的那封文学书信中,兰波就大声宣布:“我”是另一个。用兰波的话来说就是:Je est un autre.这是一种有意违反常理,但另有一番道理的说法,相当于英语的I is someone else.而非I am someone else(法语通常的说法应该是Je suis un autre)。为什么这样说呢?再读一遍《醉舟》就明白了:既然“另一个”(un autre)是第三人称单数,那么前面的动词不也要随之改变么?与其说是“我”后面的动词变了,不如说是那个“我”变了,“我”已不再是原先那个固定、单一的“我”,而顷刻间变成一个自由人,甚至自由的物体,自由的灵魂了!
这岂止是一种文字游戏。即便是一种游戏,也是一种严肃的、有突破性意义的游戏。为了多一点这样的游戏,还需要多一些像兰波这样的孩子,这样的通灵者。由于有了对自我的突破,有了自由飞翔的灵魂——不仅是“神灵附体”,而且是“我”的灵魂穿透他人的心胸,附着到别人与别的物体上去了!
兰波就是这样,以文字解放心灵,由心灵解放文字;直到文字与心灵彼此渗透,创造出奇幻的新世界。而这种创造,这个变换不定的“我”,给我们怎样的启示呢?
提到文学中的“我”,我们自然会想到王国维先生在《人间词话》中的精辟论述:“有有我之境,有无我之境。”“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无我之境,以物观物,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注:《人间词话讲疏 钟嵘诗品讲疏》,许文雨编著,成都古籍书店,1983年,第170页。)但除此之外,是否还有另一种境界呢?
从兰波的诗中我们看到,有一种既非“有我”,也非“无我”的境界:“无我”,但有“我”;“有我”,但非“我”。“我”是谁?“我”不是我,“我”是另一个(Je est un autre)。
说起来有点玄,但其实不难理解。除了兰波的《醉舟》之外,再看看鲁迅的《孔乙己》,普希金的《上尉的女儿》就明白了;其中的确并非“有我之境”,也非“无我之境”;“我”在“有我”与“无我”之间:当你把“我”看成作者的时候,你错了;当你把“我”看成不是作者的时候,你又错了。
总之,有如“一朵花告诉我她的姓名”(注:兰波在1871年5月15日写给保罗·德梅尼的信中说:“诗人是真正的盗火者。”见《兰波作品全集》,第331页。);兰波告诉我们:“我”是另一个。
四、字母也是象形文字——那么汉语呢?
18世纪的德国美学家莱辛在他的著名美学论文《拉奥孔》(1776年出版,副标题“论诗与画的界限”)中,论述了诗歌与造型艺术的区别,指出诗与画首先是媒介不同:画用颜色和线条为媒介;诗歌用语言作媒介。其次,从题材上看,画较适宜描绘静止的物体;诗更适宜描写流动的动作。第三,从受众所用的感官来看,画是通过视觉来感受静止的物体;诗是通过听觉来捕捉流动的声音。总之,这两者的区别,即“空间艺术”与“时间艺术”的区别。莱辛继而又论述这两者之间如何取长补短。(注:参见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第308-312页。)
莱辛的这一理论在大部分情况下,在西方语言的范畴中,当然是正确的,但对于东方语言,尤其是至今保存着象形成分的汉语而言,就未必合适了。这里不一一列举汉语古文字中的象形文字,只说一句唐诗:“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崔颢《黄鹤楼》)。即使在今天的简体字中,我们也不难看出其中草木、河流、太阳与飞鸟的形象和颜色。其中那个“川”字不还在流动么?用眼睛也能欣赏到诗中的颜色与线条,这在汉语里十分普遍。
而我们这里谈论的是兰波。兰波与此有什么关系呢?请看通灵者的《文字炼金术》:“现在,让我来讲讲有关我的疯狂的故事。很久以来,我自诩能享有一切可能出现的风暴,可以嘲弄现代诗歌与绘画的名流。”(注:兰波在1871年5月15日写给保罗·德梅尼的信中说:“诗人是真正的盗火者。”见《兰波作品全集》,第331页。)尽管在这里兰波并没有嘲笑莱辛先生,也不知《拉奥孔》这篇论文兰波是否读过;尽管莱辛先生在今天依然很值得尊重,但《拉奥孔》中所说的美学原则,的确被兰波的一首小诗打破。这首诗就是一度被称为“天书”的《元音字母》:
A黑,E白,I红,U绿,O蓝:元音,
终有一天我要道破你们隐秘的身世:
A,围着腐臭嗡嗡地飞行,
苍蝇身上的黑绒胸衣。
阴暗的海湾;E,汽船与乌篷的纯朴,
巍巍冰山的尖峰,白袍皇帝,伞形花的颤动;
I,殷红,咳出的鲜血,醉酒
或愤怒时朱唇上的笑容;
U,圆圈,青绿海水神圣的激荡,
遍布牛羊的牧场的宁静,炼金术士
深刻在皱纹上的智者的安详。
O,奇异、尖锐而庄严的号角,
穿越星宿与天使的寂寥:
——噢,奥米茄眼中紫色的幽光!(注:兰波在1871年5月15日写给保罗·德梅尼的信中说:“诗人是真正的盗火者。”见《兰波作品全集》,第331页。)
这首十四行诗看起来有点古怪,好像儿童的拼字游戏,但仔细想来,它应是诗人“文字炼金术”的代表作。“鼎为炼银,炉为炼金”;(注:《旧约·箴言》,中国基督教协会印发,第17章3节。)17岁的诗人(作于1871年)在此想炼什么?用兰波自己的话说就是:“我尝试过发明新的花、新的星、新的肉和新的语言,我相信自己已获得了超自然的神力”;(注:兰波在1871年5月15日写给保罗·德梅尼的信中说:“诗人是真正的盗火者。”见《兰波作品全集》,第331页。)而“诗歌中古老的成分(lavieillerie poétique)在我的文字炼金术中占有重要地位。”(注:兰波在1871年5月15日写给保罗·德梅尼的信中说:“诗人是真正的盗火者。”见《兰波作品全集》,第331页。)这种“古老的成分”是什么?与字母“隐秘的身世”有什么联系?兰波没有说。我想就是象形文字。
从《说文解字(卷十五)》中我们了解到,古人“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察鸟兽的痕迹,创造了八卦及文字。想来人类的祖先在最初创造文字时,都离不开“近取诸身,远取诸物”所造就的象形文字。
而透过已经抽象化了的字母文字,这位Voyant终于看破了它们隐秘的身世和来历。在此,想像力与洞察力合而为一;儿童的“炼金术”将字母一一“回炉”,还原为它们原始的形象、本来的面目。他成功了!
通灵诗人用一场“文字游戏”告诉我们:像孩童一样望文生义,透视文字的原形,追忆文字的起源,你将从最古老的成分中,获得最新的发现。
五、新的道与新的禅——兰波生命的启示
“道”与“禅”是两个地道的中国字,在西方文字中几乎找不到与之相应的词,然而“道”与“禅”的精神和智慧却是人类所共有的。尽管兰波生前无缘接触到汉语(他学过拉丁文、俄文和阿拉伯文等多种文字),未能用前人留下的象形文字创作,但他给我们的启示不仅在文字与诗歌中,更在生命的意义上。
兰波全部的文学生涯在14岁到19岁,19岁之后就放弃了文学,先是去参加了荷兰的雇佣军;三星期后便开小差,去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和意大利等地旅行;1878年又到塞浦路斯当了一名监工;1880年去了埃塞俄比亚、亚丁……做过武器贩子、咖啡出口商、摄影记者、勘探队员……生活中的屡屡失败使他变得神色严峻、面容憔悴;直到1891年回到马赛,在做了截肢手术之后日夜哭泣,这位曾写出《醉舟》的诗人生前用的最后一个比喻竟是“我的右腿现在已肿得像个大南瓜”,临终前的最后一句话是对邮船公司的经理说的:“告诉我,什么时候才能把我送到码头?”——文如其人,生命中的兰波也同样不惜一切代价,奋力冲向未知,结果使得他的生命与文字同样陷入了“神圣的混乱”:痛哭、狂喜,颓败、胜利,孱弱、强力,逃亡、进军,诅咒、赞美,邪念、善心,亵渎、虔诚,混乱、纯粹……所有这些对立的因素交织、缠绕在一起,相互矛盾、冲突,却浑然一体。正如“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注:《道德经》第21章,第7章,第2章,《老子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38、11、3页。)
但在这里,我们没有必要再去探究混沌中的混沌,恍惚中的恍惚;那是许多“学者文人”最爱干的事情。相反,我们在这里纪念兰波,就是要将诗人的灵魂从恍惚与混沌中解救出来,寻找那一叶醉舟漂泊天涯的轨迹,找到那条承载诗人灵魂的生命河流。
在今天看来,兰波的生命是清澈的,他的灵魂如此圣洁。可为什么不仅在世俗的眼里,就连在他自己看来,他的身心也都充斥着罪恶:于是——“我拿起武器反抗正义”……“‘你将是个恶棍……’魔王又大声叫喊,——他给我戴上一顶如此美丽的罂粟花冠。‘用你所有的胃口、你的私心和所有深重的罪孽,去赢得死亡。’”(注:《地狱一季》引言,见《兰波作品全集》,第183-184页。)这是怎样的一个魔鬼,他使出了怎样的魔法呢?兰波并不明白。
丹麦童话作家安徒生在一篇童话《白雪皇后》中说了这样一个故事,在我看来,这个故事里包含了对这个问题的明确答案:“有一天,魔鬼造出了一面镜子。这面镜子有一个特点,那就是,最美丽的风景在这镜子里就会像煮烂了的菠菜;最好的人不是现出使人憎恶的样子,就是头朝下,脚朝上,没有身躯,面孔变了形,认不出来。”(注:《安徒生童话》,叶君健译,少年儿童出版社,1990年,第166页。)我想,会施魔法的兰波不幸也中了魔鬼的魔法,常常从魔鬼造的这面镜子里照见自己——有诗《地狱一季》为证。然而更可怕的是,安徒生告诉我们,后来这面镜子碎了,碎成粉末,飘到世人的眼睛里,而每一粒粉末,都具有整个镜子的魔力。——兰波就是这样被变成了一个“恶棍”。连他自己也不清楚,“出于怎样的疯狂、怎样的错误,现实中我才如此虚弱?”(注:《地狱一季》引言,见《兰波作品全集》,第183-184页。)但如果换一面镜子呢?从天光云影中,我们又将看见怎样一个兰波?
同样的沙漠,同样的夜,我又在银色的星辉下睁开疲惫的双眼,而生命的主、朝拜初生耶稣的三博士,心、灵与思想依然无动于衷。我们何时才能在沙滩与群峰之上,向着新的劳动、新的智慧致敬!为暴君、魔鬼的逃亡,迷信的终结而欢呼——成为最初的使者——迎接人间的圣诞!
天国之歌,人民的脚步!奴隶们,我们从不诅咒生活。(注:《地狱一季》引言,见《兰波作品全集》,第183-184页。)
我想,这才是真正的兰波。他的一生从发明新的语言,到创造新的智慧,新的生命,至死不与世俗妥协,通灵者探寻“未知”的脚步何曾停息?
许多人都为兰波日后放弃文学而扼腕叹息。我想,其实兰波一生从未停止创作,只是把原先写在纸页上的诗歌写到烈日之下的荒漠、丛林中去了!
我们今天在心里纪念兰波,只盼这位通灵者的灵魂能够复活,像一个远古和来来的孩子,回到我们当中。是的,这位昔日走向荒漠的诗人,至今仍走在我们的前面——“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注:《道德经》第21章,第7章,第2章,《老子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38、11、3页。)
今天,当我们为兰波的诗歌而沉醉,是否应低头沉思,并抬头望去——通灵者,今安在?那么多人想成为文学家、诗人,可谁来承担诗人悲惨的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