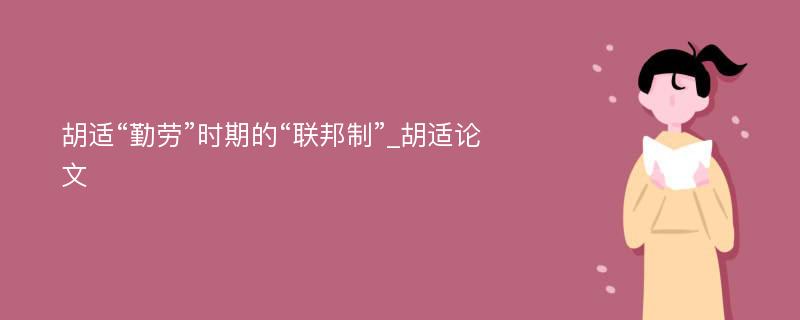
胡适在《努力》时期的“联邦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胡适论文,联邦论文,时期论文,努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通常认为,胡适办《努力》(1922—1923),声音最响亮、影响最大的是由胡适起草并发起的《我们的政治主张》,这个主张引人注目的是后来反复为人所讥讽的“好政府主义”。如果以今天的眼光观之,《努力》最值得注意的并不是什么“好政府”,而是它一直在为之努力但后来却中途而废(废于国民党北伐)的“联省自治”。这是一个效仿美国联邦制的建国主张,它暗含于“好政府”中却未曾言明,但它在《努力》后来的篇幅中以及“这一周”的系列中,得到了较为充分的阐发——只是还未引起我们今天的充分注意。
胡适是一个联邦主义者,这应因了国内自1920年掀起的“联省自治”的潮流。当广州政府发生“孙陈冲突”时,胡适既反对国民党根据旧道德攻击陈炯明,也多少遗憾于陈采取炮轰的方式驱逐孙中山(认为打破了南北均衡,有碍于南北和议)。但在政治主张上胡适认同陈而反对孙,并指其为“倒行逆施”。孙陈冲突,要害在于孙要通过北伐统一中国,而陈却主张弥兵息祸,走“联省自治”的道路,努力把广东建设成一个模范省。由于孙中山打的是“统一”牌,而“联省”又被简单地视为“分裂”,因此,在一个盛行“大一统”观念的民族国家,持统一主张的肯定占据着意识形态和道德上的双重优势,这种状况,直到今天。但问题在于,中国自辛亥之后,原本就是统一国家,至少是形式上的。恰恰是护法运动使它分裂,于是才有这一北一南两个政府,也才有这两个政府如何统一的问题。
无疑,南方的孙中山是要武力革命的,而北廷也不甘示弱。这一南一北在军事上较劲,夹在中间的湖南便吃不消了。因为南方政府的护法战争,使湖南首当其冲,受祸连连。而它的北面,又是北洋直系在湖北大兵压境。当此南北两军鏖战之际,倍感压力的湖南督军谭延闿于1920年率先挂出“联省自治”的旗子,试图以“独立”的姿态,将湖南拉出南北政争之外,且不许双方加兵于湘境。本来是逼出来的“联省自治”,不料在全国群起响应。从1920到1922年,“联省自治”的热潮,便在华夏大地蔓延开来。
“联省自治”在当时的中国具有多重意义。它首先就意味着息兵。陈炯明是反北伐的,孙中山北伐失败后,自然要怪罪于陈。在孙后来向国民党所作的报告书中,他指责陈和湖南当局勾结,“一则阻我前进,一则绝我归路”。即使如此,孙中山也不得不承认:“不过湖南方面的阻遏,决不是湖南当局几个人的意思。湖南当局,固然也不愿意,曾与陈炯明通声气,但湖南人民不愿意,比当局尤切。因为湖南连年被兵,人民苦不堪言,并且此时北军尚驻扎在岳州,眈眈虎视,北伐军一北进,北军便蜂拥南下,湖南将复为战场;所以在那年三月内,湖南许多公团,曾组织哀吁团,一面派代表赴桂,哀请北伐军勿入湘境;一面电请吴佩孚、肖耀南,撤退驻守岳州的北军。故阻遏北伐军的前进,尚不能归咎于湖南当局接受陈的诱惑……”①
反对战争,反对武力统一,不独湖南,国人无不具此心愿。但,孙中山是个执意要北伐的人,这对北廷当然是威胁。北方军阀可能不在意陈炯明的广东省政府,但无法不在意孙中山的广东军政府。很有意思的是,直系军阀吴佩孚在一次通电中这样指责南北政府:“南责北以非法,北责南以捣乱,但见其交责,不闻其自反。夫统一必由我成,近于专制,改革必遂我意,近于独裁。虽各以爱国为名,然以己意代民意,以己是代国是之足为和平障碍则一也。”② 这南北各打五十板的通电其实更多是打在南政府的七寸上,尽管这位秀才军阀也是想以武力统一中国的。
有趣的是,身为文人的胡适和也是秀才出身的军阀陈炯明虽然没有打过交道,但在一些关键的地方他们却识见相同。反对武力统一,呼唤南北议和,走美国联邦式的道路,在联省自治的基础上,实行全国统一。这一共识,如果陈炯明可以实实在在地在广东落实,胡适却只能在《努力》上申张。今天看来,当时中国没有比联省自治和停止武力更重要的事了,因此《努力》在这件事上所付出的努力显然比它的其他议题(比如“科玄论战”等)都更重要,也更具历史意义。
1922年8月14日,胡适随同蔡元培、蒋梦麟、李大钊等与吴佩孚的首席幕僚孙丹林见面,“我们谈的都是很恳切的忠告。孙的态度很不好。他似乎还在那儿做‘武力统一’的迷梦。……孙说时颇得意;他又说,‘要是我肯给子玉(即吴佩孚,笔者注)上条陈,只消两师兵直捣广州,什么事都没有了。’这句话使我们大生气。孑民先生说,‘那么吴子玉也不过是一个军阀!’梦麟说,‘吴子玉何不先打过山海关看看!’说到后来,他的态度稍软下来了,也承认吴佩孚对于联省自治应该逐渐改变态度,不可没有一个退步。”③ 此时孙中山已被陈炯明逐出广州,逐渐得势的吴佩孚却企图在武力上跃跃欲试,因此,胡适在“这一周”中的态度颇为峻急:“武力统一是绝对不可能的,做这种迷梦的是中国的公贼!”另外,针对另一支正在崛起的政治力量,他们试图用革命的方式完成统一,胡适的态度也很鲜明:“大革命——民主主义的大革命——是一时不会实现的;希望用大革命来统一,也是画饼不能充饥。”④ 让胡适没能料到的是,革命并非画饼,国民党的第一次北伐失败了,但几年后的第二次北伐在蒋介石手上却成功了,它不仅是武力的,也是革命的。国民党及其后来原本就是革命党,革命在它们那里,离开了暴力和武力就什么都不是。随着内战性质的北伐成功,中国政局发生了根本变化:一、维持了十几年的共和框架彻底颠覆,为一党专制所取代。二、苦苦挣扎的美国联邦式的努力彻底破产,代之的是苏俄式的集权大一统。从此,中国告别了“美国之途”,走上了“苏俄之路”。
据胡适日记,陈炯明在逐走孙中山之后,曾派人在京邀胡适吃饭,饭桌上,来人代为表达陈炯明的意思,请胡适南下广东办大学。胡适拒绝了,“我劝他转告陈炯明,此时先努力把广东的治安办好,不妨做一个阎锡山,但却不可做杨森。借文化事业来做招牌,是靠不住的。”⑤
案:前曾言,胡适和陈炯明在一些关键的地方识见相同。如其举例,在陈炯明邀胡适南下前曾邀陈独秀南下,南下的陈独秀和陈炯明交谈时,一则劝其加入共产党,一则劝说他“要干不能徒侍军队,广大的工人群足负很大的任务”。陈炯明明确表示反对,他的观点是:“现阶段中国劳动运动只宜做劳工教育运动,最不好是拿劳工做政治本钱,这恶风气一开了头,往后将不可收拾。”⑥ 同样,胡适的《我们的政治主张》发表后,一拨激进青年致信胡适,一则反对他的主张,二则倡议“平民革命”,到民间去唤醒民众。对此,胡适在“这一周”中表态:
“到民间去”四个字现在又快变成一句好听的高调了。俄国“到民间去”的运动,乃是到民间去为平民尽力,并不是到民间去运动他们出来给我们摇旗呐喊。“到民间去”乃是最和平的手段,不是革命的手段。”⑦
异曲同工!不把自己的主张作政治煽动,更不把民间力量诸如工、农、商、学作为自己的政治本钱和运作对象,比如二十世纪我们常见的学生运动其实是运动学生。陈炯明不论,胡适对此非常清醒。他哪怕失去学生,也不会运动学生。1936年初,胡适与信汤尔和,一贯不主张学生罢课的胡适如此“自清”:
我从不曾利用过学生团体,也不曾利用过教职员团体,从不曾要学生因为我的主张而牺牲他们一点钟的学业。⑧
二
“联省自治”的母本即美国,这是仿效美国政制而欲使之在中国实现的一种政治努力。作为一场运动,它虽然是在1920年开始兴起,但作为一种思想,早在戊戌维新时代就已萌蘖。在粱启超眼里,“共和政治也,联邦政体也”。辛亥革命时,山东宣布独立,省咨议局向清廷提出八项条件,第五条即“宪法须注明中国政体为联邦政体”。后来上海都督陈其美通电各省,请派代表在上海开会,试图商讨如何建立一个永久性的民国政府,而这个政府的组织形式和原则,也是以美国制度为蓝本。通电说:“美利坚合众国之制,当为我国他日之模范”。倒是临时政府成立后,为求统一故,中央集权的思想压倒了联邦自治的思想。但,此后,章太炎、蔡元培、章士钊、张东荪等士林中人都是力持美国联邦主义的。
“联省自治”这个词相传是章太炎的杰作,它是美国联邦主义在中国的本土化。这个词有两个基本诉求:一,各省自己制定宪法,依照省宪建立省政府,不受中央和他省干涉。二,在此基础上,由各省代表组织联省会议,制定联省宪法,以完成国家统一。在当时南北两个政府都以正统自居并希求用武力统一中国时,联省的思路是止息战争,和平统一。胡适无疑是联省的赞助者,《努力》也不断在这方面做工作。但反对联省的势力也很大,概而略之:一,主张革命的共产党人比如陈独秀是反对联省的。二,同样主张革命的国民党人也是反联省的,孙中山北伐就是例子。三,北洋势力中的吴佩孚,四,当时北美的一批留学生(包括张闻天在内的四十余人),他们都在反对联邦制。胡适在《努力》上与这几种反联省的势力都有过交锋,以上他对孙中山的批评,已经大大开罪了国民党。这里我们不妨再看他和共产党人陈独秀的争执。
陈独秀的观点具有相当的普遍性,一是认为联省自治其实就是军阀割据,而军阀割据恰是当时的乱源,因此他主张集中民主主义分子组织强大的政党,倾覆军阀,建设民主政治的全国统一政府。另外,陈独秀认为自治重在城镇乡,而不宜到省,到省,那就是联邦制,而联邦制不合国情。显然,潜伏在这一观点之后的,则是全国大一统的思路。
这里有一个误区,它既是历史的,也是现实的:即“联省自治”是分裂,而“中央集权”是统一。自周秦以降,“统一”已经成为华夏民族最牢固的一种民族心理,作为一种集体无意识,无论何时何地何事何因,谁主张分裂,则举国共诛,谁声称统一,则举国皆同。联省的主张由于和当时武人割据的现实相因应,所以很容易招致分裂的罪名,而陈独秀和孙中山也正是分别以此为号召。
事实上,胡适既是一个联邦主义者,也是一个统一主义者。1922年6月27日,陈炯明逐走孙中山的第十一天,胡适等一干人在顾维钧家聚会,讨论国是。据胡适当日日记,“李石曾、王雪廷提出一个商榷书,提倡一个‘邦联制’(confederation),名为‘分治的统一’,实则严格的分裂。我起来痛驳他;因为王君自说是略仿美国最初八年的邦联制,故我说,不去采用美国这一百三十年的联邦制,而去学那最初八年试验失败的邦联制,是为倒行逆施!是日加入讨论的人,没有一人赞成他们这个意见的。”⑨ 从胡适的态度到最后一句,可见“统一”不仅是一种人心,也是一种禁脔。王雪廷不过一主张而已,以至胡适峻急如此,而他本来并不是这样的。同样,在6月中旬的“这一周”上,胡适的态度很鲜明:“统一的条件的中心必是承认联邦式的统一国家,这是无可疑的。但联邦式的国家全不是现在这种军阀割据式的国家。”⑩ 既联邦,又统一,是当时胡适的基本诉求。
就联邦制而言,如果统一不成其为问题(美国是联邦国家,没人会认为它不是一个统一国家),那么,胡适和陈独秀(包括孙中山)的冲突到底在什么地方呢?他们的分歧实质上是:一个统一的国家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政制。作为一种制度表述,它表现为这样两种对抗形式:“中央集权制vs联邦分权制”。陈、孙属于前者,胡适属于后者。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难看出,中央集权的统一不是国土意义上的统一,而是中央统治权力的统一。同样,联邦的分权不是国土意义上的分裂,而是解分中央集权为地方权力。两者的焦点锁定在“权力”上,它们是统一国家范畴内权力资源的不同配置。
什么是联邦制?请听听英国勋爵阿克顿的声音,他说的非常透彻:“联邦制:它是权力之间相互并列的关系,而不是权力之间相互从属的关系;它是一种平等的联盟,而不是上下之间的等级森严的秩序;它是相互制约的各种独立自主的力量;它是权力之间的相互平衡,因此,自由出现在其中。”(11) 以美国联邦制为例,美国政府和各州政府并不是权力隶属关系,而是相互并列关系,美国总统并不能任命任何一个州长,后者必须来自各州的民选。因此,美国作为一个统一国家,它是各州之间的平等的联盟,其中亦不存在各州之间的倾轧。那么,国家与州之间的权力又是如何配置的呢?如果说“权力者”无论国家还是州都由票选而定;那么,“权力”无论是国权还是州权都由宪法(省宪和国宪)来决定。宪法既是权力的来源,也是权力配置的机关。其配置方式,中央取“例举主义”,地方取“概括主义”,此即凡是例举出来的权力属于中央外,其他未曾例举的权力一概属于地方。两者相较,中央的权力是有限的,而地方权力无限。这也是地方自治的含义。由于联邦制的政府权力有国家和州两个平行的层次,因此这样一种权力配置又称“复合制”。
和“复合制”对应的“单一制”即中央集权制。所有的权力“九九归一”俱属中央政府,由中央政府再把相应的权力授予给它下面的成员单位,比如州或省。这样,州省与中央的关系就不是并列关系而是等级森严的隶属关系,州长和省长不过是中央政府派出去的地方官员。根据权力来自谁便对谁负责的原则,地方官员可以不对地方负责而必需要对中央政府负责。它的权力配置和联邦制相反,是中央取“概括主义”,地方取“例举主义”,亦即地方权力是有限的而中央政府的权力则无限。中国自周秦以降的郡县制即是这种中央集权的单一制,它的权力路线图就是一个自上而下的尖宝塔结构,由中央而郡(省)而县(市)而乡(区),以下(包括乡)则为自治(以上陈独秀就认为自治只能维持在乡和城镇的层次)。各个行政区划的权力无不来自它的上层,最后一直可以上溯到中央,这就是中央集权的“大一统”。
走了两千多年中央集权大一统的老路,到最后一个王朝满清覆亡,王纲解纽,国人便想改弦更张,效法和尝试美国联邦制了。而当年美国人之所以不考虑单一制而取联邦制,就是因为他们觉得后者更适合于广袤的大陆,适合于多种族构成的人民。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胡适批评陈独秀时这样说:“自从秦始皇以来,二千多年的历史确然呈现一种‘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大势。这二千年历史的教训是:中国太大了,不适合于单一制的政治组织。”至于陈独秀一面批评联省自治,一面把当时的军阀割据视为“中国政治纠纷的根源”,胡适“很诚恳的替他指出:他所举的只是纠纷的现状,并不是纠纷的根源;只是乱,并不是乱源。”那么,乱源到底是什么呢?在胡适看来,正是和中央集权相配套的武力统一。所谓“合久必分”,便是中央统治力的衰退,原分封的各地军阀便闹起了分裂。而“分久必合”则是一个军阀用武力消灭其它军阀,从而形成新的中央集权,又开始新的分封。中国两千年的历史都没有突破这分合循环的怪圈。所以,无论面对历史还是现实,胡适俱认为“军阀的封建与帝制的运动都是武力统一的迷梦的结果”。他批评袁世凯在民国三、四年间,国内“联邦论”已起,仍把“袁家将”分布到各省,即便如此,依然不能遏制各省独立的趋势,而袁则误解病源,以为皇帝的名号可以维系那崩散的局面,故推行帝制。因此“为强求统一而封建军阀,然而封建军阀却使各省格外分裂,遂成了独秀说的政治纠纷的现状”。(12) 而欲解决军阀割据这个政治纠纷,胡适的态度是:“今日决不能希望中央来裁制军阀;裁制军阀与倒军阀的一个重要武器在于增加地方权限,在于根据于省自治的联邦制。”(引同上)这是胡适读了陈独秀“对于现在中国政治问题的我见”后,在《努力》上回答的一封公开信,题目就是“联省自治与军阀割据”。
读了胡适的文章,也收到了胡适的信,陈独秀写过五页信纸给胡适,胡适把它粘贴在自己的日记中。如果说胡适是要用省自治的方式来遏制地方军阀,那么,陈独秀的态度更明确:“中国事无论统一联治,集权分权,无论民主的政治或社会主义政治,不取革命的手段,都只是一场滑稽剧。这是我牢不可破的迷信。”(13) 把革命视为自己的迷信,陈独秀不愧是老革命党。目的可以暂时不论,解决现下的问题只有革命一途,革命包办一切。那么,历史的走向是胡适的呢,还是陈独秀的呢?很明显,胡适又失算了。不仅共产党人陈独秀是要革命的,南方的国民党也是要革命的。孙中山临死前的嘱咐就是:革命尚未完成,同志仍须努力。此时共产党和国民党已经在革命的大纛下开始合作,完成孙中山遗嘱的就是蒋介石武力统一的“国民革命”,就是北伐。1926年北伐军进入湖南时,湖南省宪终止,随之终止的便是自1920年也是由湖南开始的历时六年的联省运动。后一年,北伐成功,历史又回复到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和历史不同的是,这次大一统是党统,党统彻底宣告了美国联邦制在中国的破产,同时也宣告了苏俄政制在中国的起来。从此,苏俄体制便正式登上了中国政治的历史舞台。
案:当共产党人陈独秀把联省当作分裂来反时,一直在湖南的青年毛泽东却是个非常热情的联省主义者。1920年毛泽东在上海《时事新报》发表“反对统一”的文章,声称:“胡适之先生有二十年不谈政治的主张,我现在主张二十年不谈中央政治,各省人用全力注意到自己的省,采省们罗主义,各省关上各省的大门,大门以外,一概不管。”关起门来干什么呢?建设一个“湖南共和国”。毛说:“索性不谋总建设,索性分裂,去谋各省的分建设,实行‘各省人民自决主义’。二十二行省三特区两藩地,合共二十七个地方,最好分为二十七国”,而“湖南人没有别的法子,唯一的法子是湖南人自决自治,是湖南人在湖南地域建设一个‘湖南共和国’。”此刻,毛泽东的思想资源源自美国19世纪初的“门罗主义”。美国总统门罗当年发表国情咨文,宣称“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其要义在美洲不管欧洲的事,欧洲也别管美洲的事。美洲的门罗主义到中国就是“省门罗主义”,湖南是湖南人的湖南,中央和外省都别管。这难道是要搞分裂吗?不,在其他的文章中,毛泽东说:“我们觉得湖南现在所要的自治法,即与美之洲宪法和德之邦宪法相当。中国现在四分五裂,不知何时才有全国宪法的出现。在事实上,恐怕要先有各省的分宪法,然后才有全国的总宪法,一如美、德所走上由分而合的路。”(14) 从毛泽东的个案,可见当时联省自治有相当的民意基础,且中国十多个省已开始或准备实行之,它之最终毁于北伐战火,只能说历史走错了房间。
三
在国民党孙中山和共产党陈独秀之外,反对联省的一个重要人物、同时在当时也是最有实力的人物,便是北洋直系的吴佩孚。吴佩孚声称,给他三年时间,他一定能统一中国,当然是用武力。1922年8月,吴佩孚的一份通电,其中第二条便表达了他对联省的反对。胡适以这份电报为底本,以“吴佩孚与联省自治”为标题,在“这一周”中对吴进行了公开的批评。
对于国家政体,吴主张“须以单一之形式,贯彻分权之精神”,而联省在他看来,不过是“不惜分崩割裂以立法”,这是和孙中山陈独秀一样的论调:联省就是分裂。因此,胡适指谓:“无论联邦与联省,并不妨害国家的统一。……因为统一民主国尽可以包含联邦式的统一民主国。”胡适说:“假使我们能做到像美国那样的联邦式统一,难道我们还不能满足吗?”(15)
插:有趣的是,吴是个军头,未留学过北美,他有此见,不足为论。差不多与此同时,留学北美的中国学生康白情、张闻天等四十多人从太平洋那边对联省发表意见,他们的“制宪庸议”连日在国内报纸上发表,引起了胡适的注意。这拨身在联邦制度中的人也是反联邦的,他们认为:“自联邦说兴,国内士大夫狃于现状,乃揭橥联省自治,欲易我二千年来沿习善制。”原来秦始皇的中央集权制在这些留学生眼中是“善制”!“中国自秦始皇兼并六国后,郡县制度确立,即属单层统治权。以至于今,就是临时约法,修订宪法,宪法草案等所载,也全采单层统治权。”因此,他们的结论是:“依据历史,依据帝国政府权力的让与,依据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本意,我们的宪法,必采单层统治权,本不成问题。”这个不成问题的问题,在胡适眼中是一个大混淆,即“把郡县代表统一,又把封建和联邦看作一样”。(16) 尤其是后者,封建本是中央集权的产物,它就是中央集权对地方权力的让与,就像袁世凯把自己的亲兵亲将分封到各地一样,它怎么能够和权力本来就来自地方的联邦制相提并论?
从这里可以看出,封建与联邦的不同,就是地方权力来源的不同。而这个不同,又牵涉到那个时代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民治。民治是新文化运动的两大遗产之一,即陈独秀所标举的“德先生”。以上陈独秀反联邦时也是打着民主主义旗帜的。可是在陈独秀那里,民主只是一个口号,并不曾落实也无从落实。因为民主的落实需要具体的路径,而联省自治在当时恰恰可以成为中国民主的路径依赖。因此,胡适在这次批评吴佩孚时,乃是从民治角度出发的,看起来是批评吴佩孚一人,其实它的批评面甚广,同时包括“三民主义”的孙中山,扮作“德先生”的陈独秀,以及其他士林。
吴佩孚的统一可以归结为八个字:“集权于国,分权于民”。胡适责问:“试问怎样才叫做‘集权于国,分权于民’?依吴氏的具体办法,省长必由中央任命,难道就可算是‘集权于国’了吗?那么,又怎样‘分权于民’呢?吴氏一面说‘宜民自治’,‘分权于民’,一面又怕‘省长而入选,非军阀则贾氓;县长而入选,非乡愿则地痞’。他又说,‘政治甫入轨范之日,民选之利尚在无何有之乡,而其为害已不可胜纪’。如此看来,‘分权于民’四个字也只好留在无何有之乡了。”(17) 联省的要义之一,便是省长民选而不由中央委派,而委派的省长,他的负责对象只能是中央而不是地方,比如当年由北洋皖系派至湖南的督军张敬尧,在湖南胡作非为,为害甚烈,搞得湘人怨声载道,最后为湘人所驱逐。因此,联省意义上的省长民选,具有多重意义。首先,它是对中央集权的“去专制化”,其次,它是权力制衡的一种有效方式,复次,它是民治在中国实行的具体落实。就最后一点而言,民治必自地方始,因为民总是生活在和他利益攸关的地方空间中。大于地方的空间虽是价值上的递进和超越,但就自治言,它的排次却在地方之后。如果中央权力是选举的,但地方权力比如省,却是中央委派的,那么对地方来说,它依然不是自治的。反之,如果地方权力来自地方票选,而中央权力却无从问及,那么,就这个地方言,它依然可以是自治的。因此,民治也好,民主也罢,包括民权,如果不是餍足于口号(陈独秀和孙中山是把这个口号叫得震天响),北美联邦制就是当时最切近实际的推行方式。
然而,吴佩孚反对民选的理由也是摆得上桌面的,民众“组织未备,锻炼未成”。即使是借口,但实情也未必不是如此。那么胡适如何应对呢?胡适说:
我们要明白承认:民治主义是一种信仰。信仰的是什么呢?第一,信仰国民至多可以受欺于一时,而不能受欺于永久。第二,信仰制度法律的改密可以范围人心,而人心受了法制的训练,更可以维持法治。第三,民治的本身就是一种公民教育。给他一票,他今天也许拿去做买卖,但将来总不肯卖票的一日;但是你若不给他一票,他现在虽没有卖票的机会,将来也没有不卖票的本事了。胡适的意思,不是等组织完备、锻炼已成再推行民治,而是民治本身就能教会民众如何实行民治,此所在在游泳中学会游泳。(18)
因此,胡适这样归谬吴佩孚:
若因为“组织未备,锻炼未成”,就不敢实行民治,那就等于因为怕小孩子跌倒就不叫他学走了。学走是免跌的唯一法子,民治是“锻炼”民治的唯一法子!若依吴佩孚的兢兢怀疑,那么,我们也可以说:“组织未备,锻炼未成,究其终极,总统而入选,非军阀即奸雄;议员而入选,非政棍即财主!”我们何不也改总统为世袭皇帝,改议员为任命的呢?(同上)
最后,胡适指出,现在重要的问题乃是从事权角度确定,哪些权力归中央,哪些权力归地方,至于“吴佩孚驳民选省长的理由,是绝对不能成立的。(同上)
胡适仅仅是在驳吴佩孚吗?非也。持吴氏类似看法的,并非吴氏一人。比如,这是鲁迅的声音,当时的鲁迅对共和政治之类颇不以为然,他说:“大约国民如此,是决不会有好的政府的;好的政府,或者反而容易倒。也不会有好的议员的;现在常有人骂议员,说他们收贿,无特操,趋炎附势,自私自利,但大多数的国民,岂非正是如此的么?这类的议员,其实确是国民的代表。”(19) 那么,怎么办呢?鲁迅的方子是“此后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20) 鲁迅的意思很显然,先人而后制度,人的问题不解决,什么制度都没用。另外一个是胡适的朋友张慰慈,他是留美学政治的,是政治学博士。他在他的《政治概论》第七章中,提出的问题是“民治的政治制度有没有制造良好公民的效力?”这个问题在胡适那儿是肯定的,在鲁迅那儿则是否定的。张慰慈以虚拟的口吻说:“有人说,好人民须由民治或共和政体造就出来的。人民只有在民治制度之下才能得到政治上的训练,才能变成好公民。反转来说,人民如果没有执行政治的权利,永不能得到那种相当的政治训练,永没有做好公民的机会。”这其实就是胡适当时的思想,然而张慰慈并不同意,他认为:“这样一种观念,在理论上也许是很对的,但在事实上却是没有根据的。”因为“民治或共和制度决没有单独制造良好公民的能力”。(21) 在这个意义上,张慰慈和鲁迅又是曲径暗通的。对此,胡适在给张氏这本书作序的时候,再次表达了自己的观点:“民治的制度是一种最普遍的教育制度”:“凡经过长期民治制度的训练的国家,公民的知识和道德总比别国要高的多。”然后,胡适以自己留学时见过的两次美国大选为例,指出美国公民所以谙熟大选程序,盖在于“他们只不过生在共和制度之下,长在民主的空气里,受了制度的训练,自然得着许多民治国家的公民应有的知识……”因此,“民治制度的最先进的国家也不是生来就有良好公民的;英国今日的民治也是制度慢慢地训练出来的。至于那些采用现成民治制度的国家,他们若等到‘人民程度够得上’的时候才采用民治制度,那么,他们就永永没有民治的希望了。”(22) 最后一句话,分明说的就是中国了。
可以看到,当联省问题变成民治问题时(联省必然诉诸民治,而离开联省,当时的民治不过是空谈),人,还是制度:这个问题就摆上桌面。吴佩孚以人为理由来延缓制度(后来国民党的“训政”也是同样逻辑),鲁迅以人为先而后制度,张慰慈至少也小看了制度的作用;那么,胡适呢,他的选择是制度优先,由制度而后人。这是胡适民治思想的基本思路,这一思路一直延续到1930年代“民治与独裁”的思想论战,也一直延续到我们能否民治的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并给今天的我们以启发。
注释:
① 转引李剑农:《戊戌以后三十年中国政治史》,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331页。
② 转引陈定炎:《陈竞存(炯明)先生年谱》(上),台北:桂冠图书公司1995年版,第381页。
③ 曹伯言:《胡适日记全编》卷3,第756页。
④ 胡适:“这一周·41”,《胡适文集》卷3,第437页。
⑤ 曹伯言:《胡适日记全编》卷3,第786页。
⑥ 陈定炎:《陈竞存(炯明)先生年谱》(上),台北:桂冠图书公司1995年版。第495页。
⑦ 胡适:“关于《我们的政治主张》的讨论”,《胡适文集》卷3,第334页。
⑧ “胡适致汤尔和1936年1月2日”,《胡适来往书信选》中,第295页。
⑨ 曹伯言:《胡适日记全编》卷3,第710页。
⑩ 胡适:“这一周·9”,《胡适文集》卷3,第408页。
(11) 阿克顿:《自由与权力》,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379页。
(12) 胡适:“联省自治与军阀割据”,《胡适文集》卷3,第371—372页。
(13) 转引曹伯言:《胡适日记全编》卷3,第811页。
(14) 转引李玉刚:“青年毛泽东与湖南自治运动初兴”,载集体编:《一九二零年代的中国》,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
(15) 胡适:“吴佩孚与联省自治”,《胡适文集》卷3,第425页。
(16) 胡适:“这一周·50”,《胡适文集》卷3,第447页。
(17) 胡适:“吴佩孚与联省自治”,《胡适文集》卷3,第425页。
(18) 胡适:“吴佩孚与联省自治”,《胡适文集》卷3,第425—426页。
(19) 鲁迅:“华盖集·通讯”,《鲁迅全集》卷三,第21—2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20) 《鲁迅景宋通信集·八》第22页,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
(21) 转引胡适:“《政治概论》序”,《胡适文集》卷3,第324页。
(22) 胡适:“《政治概论》序”,《胡适文集》卷3,第324—325页。
标签:胡适论文; 陈炯明论文; 孙中山论文; 陈独秀论文; 联省自治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努力论文; 历史论文; 吴佩孚论文; 联邦制论文; 马克思主义论文; 五四运动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