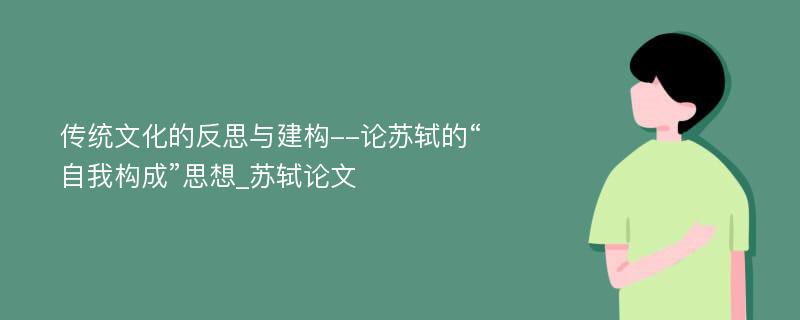
对传统文化的反思与建构——论苏轼思想的“自己构成自己”,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传统文化论文,苏轼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934(2002)05-0045-06
苏轼是北宋时期极富创造力的“全能作家”。其创造力的旺盛,基于其主体的先进思想。苏轼的先进思想是什么?是儒、释、道吗?应如何理解苏轼先进思想与儒释道传统文化的关系?当今学者们在分析探究苏轼思想时,总在儒释道思想圈子里为其做定量分析,或主或次或混合,结果使之与其他同样受到儒释道影响的士子们形成为没有本质差别的类型人物,看不到苏轼独具特性而又鲜活的思想特性。
儒释道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确曾对苏轼思想发生过重大影响。但苏轼作为“社会结合的主人”,他有一个能主动接受这些影响的自我个性主体。由于他个性主体性的作用和他处世哲学的“实用”观念的制约,他对主体外部的儒释道和百家思想的汲取,实行了“重要性”和“选择性”的集构、解构和建构工程。这样,儒释道等传统文化思想对苏轼产生的影响,便决不是整体性的影响,只能是零散的、片段的、局部的。而是由他个性、观念的特质去批判地吸收,使之复合交融,转化为他自身特质的有机组成部分。再者,思想建设还随着时代、社会的变化发展而变化发展,特别是主人公处世实践的坎坷曲折遭遇,总是促成他激烈的反思和总结,对已集构的文化影响进行再认识、再清理、再整合,并进行解构后的重新建构,最后形成他自己一生主导思想的总特征和总倾向。这些总特征和总倾向,当然与原来陶铸他思想成长的儒释道等思想文化有着渊源关系,但他已对之施行了超越,并使之转化成为苏轼自身所特有的独立思想体系的一部分了。诚如苏轼所形容的:“孔、老异门,儒、释分宫。又于其间,禅律交攻。我见大海,有北南东。江河虽殊,其至则同。”(《祭龙井辩才文》)儒释道三者矛盾斗争,最后殊途同归,有如江河虽殊,但最终共入大海——江河之名便被消融了,形成了另一种崭新的“大海”的质变事物。按照现代科学认识论的光辉论点,思维建构的规律是“自己构成自己”,并具有其特定的方向和角度。黑格尔在《逻辑学》(上卷)中说:“只有沿着这条自己构成自己的道路,哲学才能成为客观的,论证的科学。”其原因是精神运动的进程具有复杂性,其本质是自己规定自己,自己与自己同一,因而它必然是自己构成自己。
苏轼“自己构成自己”的第一要素是他自称的“野性”自由个性(见其《游庐山次韵章传道》“野性犹同纵壑鱼”)。其“野性”自由的巨大文化意义在于:以“野性”个性为起点进行选择,并对封建社会的种种不合理现象和信条发生怀疑和抗争,从而推演出他对整个人生旅途的肯定和对宇宙真相的领悟,乃至对客观存在价值的认同。
苏轼“自己构成自己”的第二要素是“实用”。他的处世准则是:“皆欲酌古而取今,有意于济世之用。”(《答虔卒俞括》)“实用”——“求实”,正是哲学思想领域中的首要概念之一。“实用”由于注重事实,而具有对存在“重要性”进行选择的必然特性。苏轼以他的锐敏性,通过对儒释道的观察分析、探索渗透,选择出具有“实用”价值的因素方面,补充和建构着自我思想体系。
苏轼“自己构成自己”的第三要素是“高怀远度”和“高风绝尘”的人生审美理想。“高怀远度”,即高尚的胸怀和高远的器度。“高风绝尘”,即高风亮节和超脱世俗的志趣。这便从而建构了他独特的自由自适思想体系。
苏轼思想“自己构成自己”的发展历程,经过了集构、解构、建构三个阶段:
一、集构阶段:
主要指苏轼青少年时期,他在北宋社会时代的大背景下,以其出身、个性特征吸取儒释道及百家精华而逐渐集构成他的自我思想框架。苏轼作为一介“寒儒”,出身于“三世皆不显”的“世衣”“布衣”家庭,自小就经历着“少年辛苦事犁耕”(《野人庐》)的艰辛生活,目睹着“野人喑哑遭欺谩”(《和子由蚕市》)的悲惨现实,早在幼年的心灵里播下质朴勤劳、反抗压迫、同情弱者的思想感情种子,并孕育着他崇尚自然、爱好自由的“野性”品性。这些个性品格决定了他对儒释道思想的选择性和舍弃性,成为他生命意识的本源。苏轼是在浓重的儒教家庭环境中成长的,自读书起,即思步后汉志士范滂后尘,而“奋厉有当世志”,赞赏西汉贾谊和唐代陆贽的指陈时弊、谏议剀切品格,论述古今成败,不为空言。又以他崇尚自然、崇尚自由的“野性”品格与老庄道家天然相接,“今见《庄子》,得吾心矣。”(苏辙《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再者,其母程夫人信奉佛教,教以莫害幼鸟;父洵早年游嵩、洛及庐山诸寺,与诸长老交往之事,皆有所闻;“轼年八九时,尝梦其身是僧,往来陕右”(见惠洪《冷斋夜话》卷7《梦迎五祖戒禅师》)。于是,儒家的忠孝仁义、诚明中庸,道家的道法自然、超然物外,释家的真如圆通、淡泊明净等思想精髓都被融入他幼小心灵之中,铸成他生命意识中的一部分。与此同时,在这个集构阶段中,也已积蓄着他对儒释道等信条内部的矛盾冲突及其缺憾的体验,开始进入了“自己构成自己”的轨道。
二、解构阶段:
经过朝政变法与反变法的激烈冲突,儒释道对人的异化和反异化的尖锐斗争,特别是屡遭贬抑、流放的痛楚体验,使苏轼在大反思中对儒释道等进行着全面的清理、洗濯、批判和扬弃——即进行总体性的解构和重组,并在选择吸取后达到他重新建构的目的。
对儒家的反思和解构:苏轼自幼尊儒术,但在后来的社会实践中又着重从“儒者之病多空文而少实用”(《与王庠书》)方面进行了批判。在贬黄州的大劫难中,他首先对儒家“学而优则仕”的信条进行了“去中心”的解构,认识到“故我”的“从仕废学之荒唐”和“故至黜辱如此”的悲惨后果。他因之要重建起“今我”。从补外起,而后又陆续在贬黄州、惠州、儋州的困窘历程中,对“用之则行,舍之则藏”、“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等儒家信条进行了抵制和解构。他说:“杀马毁车从此逝,子来何处问行藏?”(《捕蝗至浮云岭山行疲苶有怀子由弟二首》其二);又说:“人生如朝露,意所乐则为之,何暇计议穷达?”(《答陈师仲主簿书》)。特别在老年撰述《易传》、《书传》、《论语说》等著作中,苏轼对儒家的整体哲学思想体系进行了深层的批判和解构。他的原则是:“自以意作”。“其所不然者,虽古之所谓贤人之说,亦有所不取。”(《上曾丞相书》)“与孟子辨者八。……辩而胜,则过于孔子矣。”(《论语说》)其解构儒学的最光彩处,是批判儒学基础和灵魂的“性”、“情”论,他极富见地的把儒家“以为喜怒哀乐皆出于情”的传统观念颠倒了过来,旗帜鲜明地指出:喜怒哀乐是仁义礼乐的基础,但皆出之于“性”,而非出之于“情”。并从而尖锐指出“离性以为情”的儒家论点,是将人们引向无知无欲的状态——成了“老子之‘婴儿’”,(《韩愈论》)实在是可悲可叹的浅薄之见。苏轼同时还认为,传统儒家从来强调“以礼节情”,所谓“非礼勿视,非礼勿听”,这是用先验的伦理、名分、尊卑、等级、道德来规范人的行为和感情生命,他以鲜明的“以情释礼”的论点加以驳斥和对抗道:“夫圣人之道,自本而观之,则皆出于人情。”(《中庸论中》)这又大胆地倒置了“情”与“礼”的关系,敲碎了“以礼节情”的枷锁,使“情”的自由生命腾越而出。再者,苏轼还以其人性观点,尖锐批判了正统儒家的“重义轻利”观和“君民”关系观,发展了他偏于“悲歌为黎元”的关心民瘼的情感立场,赢得了历代人民的爱戴。他在《苏氏易传》之《贲·彖》中,明确提出了“刚柔相济”的论点,从而修正了儒家偏重刚强而忽视柔顺的观念,并以之作为处理君臣关系的信条。
对佛家教义的反思和解构:主要表现在他对“出生死、超三乘”和“超然玄悟”及“极乐世界”等迷信学说的反对态度。他之学佛重佛,如在黄州焚香安国寺,主要是“佛为我用”,是为了达到他“期于静”、“物我相忘”、“解烦释懑”、“自慰”、“自幸”和修炼自身道德品性的目的。(引号内文字参见苏轼与诸友人书信)他曾清晰地结论说:“佛书旧亦尝看,但暗塞不能通其妙;独时取其粗浅假说以自洗濯。若农夫之去草,旋去旋生,虽若无益,然终愈于不去也。若世之君子,所谓超然玄悟者,仆不识也!”(《答毕仲举二首》之一)这就等于宣布了他是不相信佛教的。一直到病逝常州前夕,他与径山维琳长老应对“大限将至”的偈语时说:“平生笑罗什,神咒真浪出(任意乱说)!”(《答径山琳长老》);将没时,“钱济明侍其旁,白曰:‘端明平生学佛,此日如何?’坡曰:‘此语亦不受!’遂化。”(见惠洪《跋李豸吊东坡文》)可见,东坡至死申明“不受”,决不将自己的灵魂付托给虚妄无稽的西方极乐世界,表现了他对佛教的决绝态度。
对道家思想的反思和解构:苏轼对待老庄思想和道家教义,颇有所偏爱和崇尚,但也多有批判和解构之意。他之遭贬黄州斋居天庆观,其性质与焚香安国寺的态度基本一致。他是找个静处,“燕坐其中”,脱离世尘、“厚自养练”(《与秦太虚》)。他对老、庄学说的精神实质,和对佛学一样,是抱有一定的谨慎和警惕态度的,他说:“学佛、老者,本期于静而达,静似懒,达似放,学者或未至其所期,而先得其所似,不为无害。仆常以此自疑,故亦以为献。”(《答毕仲举二首》之一)苏轼批判、解构道家思想,还表现在对避世隐士的看法上,他一生崇尚陶渊明,但对陶消极避世归隐田园的自我消融颇有微词。他以其积极用世的心态——以险为乐、植根现实实践的高蹈情怀,与陶渊明的怡然自得式的消隐形成鲜明的对比。苏轼批判、解构道家教义的最典型事例,是他在《雪堂记》中所记述的关乎“客”(道家根本观点的代表者)与“苏子”(自己)的一场争辩:“客”主张“人”要摈除心智,形如稿木,心同死灰,以达到与天地万物同一的境地。而“苏子”却突出表达了他独立自由意识的积极立场。当“客”先询问“苏子”:“子,世之散人(指嗜佛习道的方外之士)耶?拘人(指崇尚儒教而”趑趄于利害之途“的庸人)耶?”而后尖锐批评了苏轼建雪堂、绘雪壁的“智”是毫无价值的,认为那是一种自我“蔽蒙”。故“客”殷勤邀请“苏子”去做“藩外之游”。然而“苏子”拒绝了他,阐明自己既不做“散人”,也不做“拘人”;并以其“性之便,意之适”的锐利武器,指出了“子之所言者,上也”,但道家所称颂的“至人”、“圣人”、“神人”,如同“龙肉”一般,是现实中不存在的事物:而“我之为”,虽属“下也”,却是一种适用于人类处世的、既不脱离现实又不拘泥现实,既“不傲睨万物”,又不汲汲于功名利禄的高超思想境界。正因为苏轼一生已参透了佛、老的精神实质,故他始终没有去当道士或和尚,也没有去做隐士,只是把佛、老当作一种“独取其粗浅假说以自洗濯”的营养资料而已。
三、建构阶段:
解构的目的是为了建构,苏轼是在解构儒、释、道思想之同时,以其个性需要和实用价值标准进行着他思想体系的建构工程。
1、熔铸儒释道的建构特点:儒释道思想作为封建时代的统治思想,经过数千年的历史积淀,它们有其符合社会实际需要的合理因素。故有些原来属于儒释道思想体系的部分,已转换成为苏轼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如忠孝仁义道德观及“尊主泽民”的凛然大节,均基本遵循其精神。如在贬黄州的大劫难中,他仍说:“虽废弃,末忘为国家虑也。”(《与滕达道六十八首》之二十)又说:“吾侪虽老且穷,而道理贯心肝,忠义填骨髓,直须谈笑于生死之际。……遇事可尊主泽民者,便忘躯为之,祸福得丧,付与造物。”(《与李公择十七首》之十一),对于佛、老思想,他则以之“陶写伊郁”,慰其谪贬之苦:“一付维摩、庄周,令处置为佳也。”(《与蔡景繁十四首》之十二)或者对释道的消静寂空、参禅顿悟、遗忘荣辱、养炼身心做到心领神会,构成他主体意识的一部分。但是,苏轼吸取、融通儒释道和百家精粹,无不打下他“个性”与“实用”的烙印。他是把儒释道等当作一种思维的工具、一种借以发掘自我内心世界的契机,他所运用的儒释道等语词,实是作家情感、心灵与之相互生发的生命外化形式。他走进了儒释道,又走出了儒释道,只有从“走出”的视角观察,才能真正把握到苏轼思想构成的内核和实质。
2、苏轼“自己构成自己”的认识论和方法论:苏轼与在文学创作上所主张的艺术创造综合论——“体兼众妙”和“通其意”相一致,是一位思想建构综合论者。他一方面反对任何偏执一隅、片面、单一运用儒释道的拘泥做法,如他有一段惊心动魄的总结性言论道:“自汉以来,道术不出于孔氏,而乱天下者多矣。晋以老庄亡,梁以佛亡,莫或正之。”(《六一居士集序》)这是因为:“时有可否,物有兴废”,不能“知其一,不知其二。”(《议学校贡举状》)故苏轼在另一方面又深刻地看到了儒释道等之间的相互对立斗争、矛盾互融、辩证统一的关系。如他精辟地指出:“庄子盖助孔子者。”(《庄子祠堂记》)他以为庄、孔两者的关系是“阳挤而阴助之”,“余不可以不辨。”(《同上》)再者,儒道与佛的关系,也同样是“通其意”的。这种相互统一、综合交叉、洗濯磨治的认识,便构成了苏轼思想发展的核心和灵魂。
四、建构独立自由自适思想体系的理论根据及其历史文化意义
苏轼以其探寻人生意义和生命价值为走向的“思无邪”和“无待”的光辉理论,及其“性之便,意之适”、“任性逍遥,随缘放旷”的反禁锢以释放感性生命自由的实践,建构起他独立的自由自适思想体系。
1、“思无邪”的建构理论:苏轼借用孔儒“思无邪”的文字形式,在含义上做了全新的解释:“凡有思皆邪也,而无思则土木也。孰能使有思而非邪,无思而非土木乎?盖必有无思之思焉。夫无思之思,端正庄栗,如临君师,未尝一念放逸,然卒无所思。”(《续养生论》)苏轼认为,人非土木,谁能无思?但有思,便必然陷入世俗功利的邪路上去。而无思,又会失掉主体的思想竟志,成为无知觉的土木。他最后归结到“无思之思”的命题。前一“思”字,指人对世俗功利(即“邪”)的追逐;后一“思”字,则指对污垢尘世醒悟之后所获得的人生价值的思考。苏轼又在《思堂记》中进一步论析“思无邪”的思维特点道:“嗟夫!余天下之无思虑者也。遇事则发,不暇思也。未发而思之,则未至,已发而思之,则无及。以此终身,不知所思。”苏轼说的“遇事则发”,是倡导人们背离功利私欲的思虑,崇尚“正念”的直观感受体验,不受“邪思”所束缚,只遵循内在的感性生命而舒卷自如,任随外在事物的变迁却能自适安畅。正所谓“物至心亦至,曾不作思虑。随其所当应,无不得其当。”(《成都大悲阁记》)如此则人们即可以从风云变幻的人生崎岖中豁然跃出,通向精神的超越和自由。
2、“无待”:即舍弃对世事人生的一切依赖,与“无思”相辅相成。苏轼说:“吾生本无待,俯仰了此生。”(《迁居》)他的“无待”,已超越庄子的虚无和逃避,而是对世事变故的不惧不馁,无喜无忧,纵浪大化,与自然统一,在清静中求得了个体生命自由的实现。他说:“问我何处来?我来‘无何有’(指《庄子》的“无何有之乡”)。”(《和陶拟古九首》其一)苏轼抛弃了浊尘,放意于“无待”,人从那里来,又到那里去?吉凶福祸算什么?皆无所挂心。一切均发自心理本体,不依待任何外在的动因。其生命完全变成一个自足体、自适体,一个自然发展的流程。这便使他超越了时空,达到了“也无风雨也无晴”(《独觉》)的精神本体境界,树立起了他“任性逍遥,随缘放旷”的潇洒人生观,通向了“高怀远度”和“高风绝尘”的审美理想。所谓“独立万物表”(《和陶杂诗十一首》其六)、“浩然天地间,惟我独也正”(《过大庾岭》),一种博大无碍,辽阔无垠的胸襟,一种自我完善感、灵魂归宿感、深沉哲理感,溢于言表。
这是苏轼涵盖了儒释道精华而又独立于三教思想体系之外的崭新创造——即他一方面融汇三教之精粹,度以己意;同时,又用三教的相互龃龌、相互解构,从而超越三教,创造出自己的思维新形式、新体系。它的巨大历史文化意义在于:自由自适思想的建构具有着呼唤自由和独立自主的性质,从某种程度上讲,它似乎已孕含了现代民主的“自由自主”的萌芽因素。它的诞生,稚嫩而富有生命力,虽然还不能发生撼动封建制度的威力,但也堪称是驱散社会黑暗的一线曙光。它为当时和后世遭受折困的落魄士子提供了追求美好人生理想的蓝本,和探索自由民主思想通路的有益借鉴。延至明代中叶,它对以王阳明、李贽、三袁、汤显祖等为主所形成的轰轰烈烈的浪漫洪流,发生了异代相接的积极影响。——苏轼期待“后世”君子对自己理解的愿望,终于在明代中叶的浪漫洪流中实现了。这种异代相接的现象,并不违反历史发展的规律。诚如理论家皮亚杰所阐述的:“高级形式的建构不得不经过一段比人们想象得更长得多、更困难、更不可预料的过程。”(《发生认识论原理》106页)可以说,苏轼思想的“自己构成自己”,具有着解构古典儒释道和催生着近代浪漫思潮的建构意义。
因此,苏轼所创造的自由自适思想体系,具有明显的超前性质,它堪称是出现在北宋中后期的一种先进思想。它与现存的儒释道思想相较,具有明显的新颖性和独创性特质。它向人们提供了如何学习和吸取传统文化精华,从而促进自我创造的范例。它启示我们:一个具有座标式历史地位的解构者,他必须首先是个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从集大成到解构、到建构,表现了他变革发展的三大特质。苏轼是在解构古典传统中,获取了精神与创造的巨大自由,而达到他自然本体状态和境界的。
苏轼是屹立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创造之神,也是活跃在北宋文化园地里的自由之魂。
收稿日期:2002-03-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