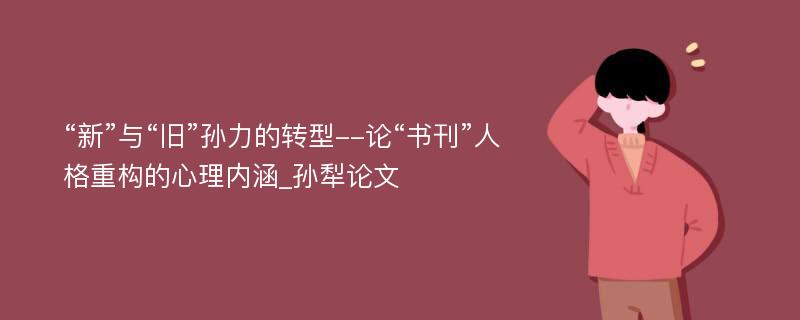
“新”、“老”孙犁的蜕变——论《书衣文录》人格重塑的心理内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格论文,内涵论文,心理论文,孙犁论文,书衣文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5293(2002)06-0078-07
《书衣文录》是孙犁将用毛笔题写于书皮上的文字整理、辑录而成的一本奇特罕见的散文集,近12万言。其主体部分写于“文革”后期(1974—1976年)。这位从少年时代起就惜书如命、爱了一辈子书的老作家,面对多年来费神劳力购藏、在动乱中几经抄掠而发还、满身疮痍的大量藏书,无比伤感痛惜,于是悉心洁修、包装之,并在书衣上或题跋,或写书话,或记日记,或发感慨,用以“排遣积郁”,自安心神。他于此种劳作,可谓椎心泣血,旷日持久。
就作家一生60年的创作生涯(1995年《曲终集》写讫孙犁即封笔)而言,《书衣文录》可说是他由一位风格鲜明的名家而进入20世纪中国文学大师行列的先兆与津梁;而就孙犁在由战争时代经17年和“文革”步入新时期的不少老作家中,终于能独独不期然而然地真正达到自我实现阶段,成为文学巨匠的实在的心路历程而言,应该说,《书衣文录》是作家自身在精神炼狱中以艰苦卓绝的悲壮情怀,开凿的一条通向人格整合和蜕变的精神隧道。
本文拟从历时性角度,论述《书衣文录》所体现的作家孙犁在“文革”中自我调整、人格重塑,即由“老”向“新”蜕变的途径和意义。
1
众所周知,40年代中期以后,孙犁以《荷花淀》等作品而蜚声文坛。他鲜明的风格和独特的艺术个性,受到了广大读者的喜爱和关注。随着时间的推移,评论界逐渐发现:孙犁的创作,着重描绘人民群众在抗战中的美好心灵和人性,自觉地为文学保留着相对独立的地位,而尽力避免和警惕以一时的政治、政策消解文学本体的审美特征。然而,正当这位风华正茂的作家凯歌行进之际,他的作品受到批判,这给孙犁心里布下了一道阴影。解放初期,孙犁仍坚持自己的创作原则,这方面的显例是中篇小说《铁木前传》。但在文学政治化、作为工具性存在的思潮日益厉害的五六十年代,孙犁不可能完全放手创作,只因为《风云初记》在李佩钟这个知识分子形象上花了些笔墨,还须在作品的最后一节为之辩护,便是此种症候的一个表征。应该说,孙犁身上成为文学大师的潜质在“文革”前被严重压抑。我们知道,孙犁性情孤僻、耿介,甚或有些执拗,这就决定了他绝不会投合“左”风日炽的文学界大势;相反,他宁肯搁笔,也不会按流行的准则为文。“从1956年到1966年,十年病期,孙犁除了写有少量诗歌、散文和作品题记之外,基本没有什么新作问世。”[1](P108)几篇抒写本心的文章,如《左批评右创作论》、《黄鹂》等,写好后被他置诸箧中,不欲发表。上述种种情况,加上孙犁几十年来从未在政治运动中写过一篇批判别人的文章,这一切都昭示着:孙犁被平淡的表象和历史的尘埃所遮蔽的特立独行的风姿及深有蕴含的慧心卓识,是异常难能可贵的,随着岁月的推移,愈益闪耀着夺目光彩。
然而,在评说上述情况时,我们不能回避孙犁性格和行为中的矛盾。他固然清高、孤僻、耿介,但又优游寡断,胆小谨慎,而因多年养成的相当厉害并被泛化到待人接物的全经验的“洁癖”,未免往往过分爱惜自己的羽毛。在发觉越来越难于以己之文才用世的情况下,他逐渐滋生并强化了一种观望之意、退隐之志。我认为,这一点是孙犁研究的一个枢纽所在。
性格是人的行为的主要驱动力。孙犁对文学的爱好,是超乎凡常的,形成了强大的审美情结。在战争年月,他热情高涨,不畏艰险,勤奋创作。这有他的创作实绩为证,也可以从他致康濯的大量信函中看出。然而,作家很难超越环境的制约和自身性格中负面东西的影响而从事创作。孙犁说过:“我写文章是兢兢业业的,怕犯错误。”[2](P129)“全国解放以后……思想领域的斗争被强调了,文艺作品的倾向,常常和政治斗争联系起来,作家在犯错误后,就一蹶不振,在写作上,大家开始执笔踌躇,小心翼翼起来。”[3](P91)不言而喻,就个人因素而言,正是孙犁性情中负面的东西(主要是胆小),促使他在解放后逐渐走上了消极的半退隐之路。他曾亲历过某诗人被捕的惊心场面,又耳闻目睹了不少作家、艺术家受到种种迫害的情形。实际上,建国后文艺界一连串的批判运动,已使具有敏感、柔弱气质的孙犁成了惊弓之鸟。50年代中期起他大量求购古籍,想当一名藏书家,未始不包含着退隐读书、别寻所乐、静待时机之意。而直到“文革”之前,他花费一些时间养花养鸟,虽说有养病的成分,但多少也与疏离文坛的心态有关。可以设想,如果没有十年浩劫所加于作家的磨砺,那么,孙犁将会一直处于创作上的停滞状态,而不会实现创作上的大飞跃,取得《耕堂劫后十种》那样辉煌的成就。
有人谈到孙犁时指出:“‘文化大革命’前他长期搁笔的根本原因不是病,而是他的禀赋、气质、审美情趣、艺术个性等‘不合时宜’,而且他也不愿改变自己去迎合‘时宜’。他宁愿久长地沉默。”[4](P123)这种看法是就孙犁气质性格中的正面因素而言,所论极是;然而如上所述,孙犁的胆小、谨小慎微以及在解放后日益形成的惊弓之鸟的心态,这些负面的东西,是这位作家在建国后创作不丰乃至长期搁笔的另一原因。
如此看来,孙犁要在文学活动上取得超越自己的过去、迥出众流的成就,就必须消除自己人格中负面的东西,即降服那胆小、退避的魔障,在严峻的考验中实行艰难的自我调整与人格整合、蜕变。“文革”对于民族和包括作家在内的广大人民群众来说,是一场浩劫;但在“艺术的源泉”、“生活体验”和促使作家悟道的意义上,却玉成了孙犁这位大器晚成的文学大师。
2
历史表明,人生不到绝处,往往不能大彻大悟。“文革”作为一场空前的浩劫,它从反面教育了、惊醒了千万人。1982年,孙犁在一篇杂文中指出:“我敢断言,经过‘文化大革命’这场血的洗礼,大多数的迂夫子,是要变得聪明一些了。”[5](P178)其实,富于哲人气质的孙犁并不“迂”,他虽离政治较远,但却能从大体上洞明世事。“‘文化大革命’刚开始,我的脑子还是很清楚的:这又是权力之争,我是小民,不去做牺牲。”[6](P96)有着如此的基点,在亲身经历了这场劫难后,他的认识不要说比常人要深刻,纵令和其他老作家相比,也颇多警拔过人之处。他所获得的对于社会人生的大彻大悟,无形中带动了他的自我调整和人格整合,使他终于实现了心灵的蜕变。评论界所说的由“老孙犁”到“新孙犁”,正伴随着这样一个过程。
运动伊始,孙犁即被揪斗,受辱。他不堪侮辱,当夜触电自杀未遂。“此后,还是想死。”[6](P97)多次想跳楼,准备吞服安眠药,用镰刀……但终于都没有做到,直到被“解放”。无论如何,这些念头和做法,是一种深刻、痛切的关于死亡的体验。众所周知,孙犁一直将“文革”看作“邪恶的极致”。对此,他强调“我体验很深,可以说是镂心刻骨”[2](P121)。实际上,他形成了一种积淀到意识深处、难以控制、经常驱动的“文革情结”。而关于死亡的体验,则是这一情结的核心。事实上,他通过死亡体验,无形中从绝处和悲郁情怀中萌生出一种历史感、危机感和生命意识,从而明显地提升了人格境界。当然,在这风雨路上,他有苦恼、犹疑和迷茫,也有探索、醒悟和决断。《书衣文录》记录着孙犁的跋涉足迹。
1972年11月在《广艺舟双楫》书衣上题道:“此证余已搬回原住处,然处逆境,居已不易。花木无存,荆棘满路。闭户整书,以俟天命。”[7](P14)可见他在艰难处境中清醒的待变心理。1974年4月24日在《潜研堂文集》书衣上题道:“能安身心,其唯书乎!”[7](P17)表明了装修书籍以安身心的私衷。1975年11月14日在《北齐张肃墓文物图录》的书衣上题道:“从热爱现实到热爱文物,即旅行于阴阳界上,即行将入墓之征,而并一小石之志,不可得也。”[7](P69)1975年5月31日在《乐府诗集》的书衣上题道:“昨夜忽拟自订年谱,然又怯于回忆往事,不能展望未来,不能抒写现实,不能追思过去。如此,则真不能执笔为文矣。”[7](56)这类话昭示了他“提前进入死亡状态”,方生方死,徘徊于生死之间,并在其间自审自思,艰难地进行着自我定位。通过装修图书,孙犁在一定程度上排遣着积郁,但却无法从根本上消除他那浓重的悲郁情怀;而离开此途,他作为纯粹文化人,作为万难勾消自己的作家身份、无法忘情于往日梦魂牵绕的文学事业的痴迷者,其身心将无处寄托。“死亡”体验虽不大见诸字面,但分明隐含在他自伤身世、自哀现景的字里行间。1975年10月6日之夜,孙犁在《竹人录》的书衣上题写了如此惊心动魄的话语:“……余幸存于九死,徘徊于晚途,一灯之下,对此残编,只觉身游大雾四塞之野,魂飞惊涛骇浪之中。”[7](P64)其内心充满了张力与冲突,那种晦暗、阴森、悲凉的况味,颇类似于鲁迅《野草》的某些篇章。百感集心,对“死”言“生”,抒情释愤,不吐不快。至于对“文革”的“大不敬”,就不复顾忌了。置之死地而后生,行至绝处而悟道。“人为什么会把‘生’‘死’‘置之度外’?因为他已经‘提前进入死的状态’,在精神上无所顾忌了。所以就道家的思想来看,‘出生入死’,既已‘退出’了‘生’(生活世界,事功世界),则‘虎无所用其爪,兵无所用其刃’,因‘以其无死地’(《老子》第五十章)。”[8](P203)孙犁后来曾说:“在这一时期,我不仅没有和那些帮派文人一校短长的想法,甚至耻于和他们共同使用那些铅字,在同一个版面上出现。”[3](P94)这就说明孙犁能从生命哲学的高度认识“生”与“死”的意义,决然退出当时“文革”的现实与“事功世界”。因此,他虽身陷劫波,但却凛然不可犯,几次让掌权者大碰钉子。在《书衣文录》这个精神家园里,他反思、慨叹着自己身份难明的处境:“昨晚为家人朗诵白居易书信三通,中有云:又或杜门隐几,块然自居,木形灰心,动逾旬日。当此之际,又不知居在何处,身是何人。”[7](P20)诵、录白札,行自念也。又为对时世的间接抗议。只有彻底摆脱浊世的挟制,才能回到“自身”而重新“开始”,得到“重生”。这种“重生”指的是“‘道德’上‘重新’获得‘自由’。”[8](P207)但它不能靠“斗私批修”而获得,而只能凭借生命哲学的觉悟和提升,并在现实中通过可行的途径来体现。一旦将由死亡体验而生的历史感、危机感和道德上的自由感融入了自我的生命意识,主体就会达到较高的主体性水平,不断围绕着确认自我的身份,提出自己所应完成的任务,以做当下所能做的工作来为实现生命的意义而开辟道路。1975年5月14日,孙犁在《小约翰》书衣上题道:“(鲁迅)先生当时,如此热爱此书,必有道理。今日为之装新,并思于衰老之年,阅读一遍,以期再现童心,并进入童话世界。”[7](P52)其精神上之生机及对光明的憧憬之情,灼然可见。1966年在《金陵春梦》书衣上题道:“黄卷青灯,寂寥有加,长进无尺寸可谈,愧当如何?[7](P14)1975年10月21日在《戚序石头记》书衣上题道:“中年以后,以文学为职业,文章讲授,均曾涉及此书,残存尚有数种,然内容已多忘记,此学荒废甚矣。[7](P66)见出他在世事剧变之中,仍存念于文学事业与自我价值。而延宕了几十个春秋的对《红楼梦》的研究和对红学的属意,至今不能释然。既“业”文学,便决不随风使舵,别有所求。旧“业”难弃,此情难绝。同时,孙犁的胆子也变大了。胆从识来,无私无畏。1975年12月11日,他在《朱文公文集》书衣上题字,大声疾呼:“……呜呼,荆棘满路,犬吠狼嗥,日暮孤行,只可披斩而进也。”[7](P73)其愤懑、激越、决绝有加,拒斥、憎恶“文革”的立场坚如磐石,显示了凌霜傲雪的铮铮铁骨。孙犁并非不知,他在书衣上所题的话,一经发现,必招致不测。但他全然置之不顾。应该说“文录”的写作体式及作为其承载物的书衣,是孙犁在荆天棘地中为自己开辟的一条可致幽远、休养生息的小径,也是为自己打造的一叶顶风破浪的扁舟,还是他在浊世中独创的饱蕴文化意味的工作平台。于此,他喘息,他抚慰伤口,他与书籍对话,与古人神晤。他心里埋藏的“地火”聚积着、奔突着,它们终必冲破“文录”的框架,化作腾跃当空的耀眼“火龙”——1975年3月破例拟题、题于《河海昆仑录》书衣的《“今日文化”》,令人惊骇:“……人事纷纭,毁誉交至。红帽与黑帽齐飞,赞歌与咒骂迭唱。严霜所加,百花凋零;网罗所向,群鸟声噤。避祸尚恐不及,谁肯自投陷阱?遂至文坛荒芜,成了真正无声的中国。他们把持的文艺,已经不是为工农兵服务,是为少数野心家的政治赌博服务。戏剧只有样板,诗歌只会吹牛,绘图人体变形,歌曲胡叫乱喊……”[7](P46)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表明孙犁已经在血泪的教训中告别了过去那种谨小慎微、洁身自好的精神状态,无形中大大强化了其人格结构中“胆”(意志)和“识”(认知)的分量与力度。他不再压抑自己对现实社会的真实情感,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知、意、情的统一,朝人格整合的方向前进着。于此,“老孙犁”向“新孙犁”转换蜕变的影像清晰可见。
一位学者在阐述西美尔的生命哲学时指出:“现代人必得体验死亡这一‘存在的形式’,他通过死亡而震醒了自己的麻木,于是死亡是现代人生命的重新塑造者,因为通过死亡,形成了全新的自我生命意识。”[9](P91)如果说,“文革”前十年孙犁被抛入了一种“非本真生存”状态;那么,经过“文革”中的磨难和死亡(本真之死)体验,他在逐渐地向“本真生存”状态挣扎和过渡。“死启示着空,澄明着无。只有死这一大限,把消融于日常浑噩烦心之中的此在从异化状态中唤醒,从‘常人’那里夺回,夺回到本真的个别性在世的可能性面前,从而由大畏转向大无畏,并洞明在世之真谛……”[9](P114)显然,由胆小、退避到大无畏,是“老孙犁”转换蜕变为“新孙犁”的关键性心理动因;舍此,他将难以实现自我调整和人格重塑。
3
就《书衣文录》所体现的孙犁的人格重塑而言,尚有以下数端似应予注意。
第一,关爱、珍重自己,无条件地积极自我看待。人本主义心理学家罗杰斯将无条件积极看待,视为人格重新整合的一个前提。[10](P289)所谓“无条件积极看待”,原是罗杰斯改变人格的受辅者中心疗法之咨询的三个条件之一,“指咨询者对受辅者表示真诚和深切的关心,尊重和接纳。”[11](P562)在一定意义上,可以将“文革”后期的包书皮和写《书衣文录》看作孙犁以特殊的文学活动所进行的自我精神治疗。不过,在此,治疗者与被治疗者双重身份合一,它的进行在孙犁来说是不自觉地。虽有此区别,但道理则一。他人的无条件积极看待,在孙犁这里变成了无条件积极自我看待。在“文革”那种罗网广设的岁月里,虽说有几位故交和同事对孙犁比较关心和同情,但真正能够疗救孙犁痛苦的,则舍他本人莫属。固然,在《书衣文录》中,孙犁也怀着忏悔和自我批评的态度,审视、剖析自己的缺点,如痛言对结发妻子“有惭德”[7](P78),自责“余于友朋,情分甚薄”[7](P60)。但无论如何,总是关切自己的处境和命运,从不自暴自弃。1974年7月4日,他在《风云初记》书衣上题道:“著作飘散,如失手足。余曾请淮舟代觅一册,彼竟以自存者回赠……,余于所为小说,向不甚重视珍惜。然念进入晚境,亦拟稍作收拾,借慰暮年。”[7](P22)著作是心血所凝,晚境凄凉,收拾著作即自爱也。1975年4月27日在《西域之佛教》书衣上题道:“昨夜梦见有人登报,关心我和我的工作,感动痛哭,乃醒……”[7](P50)同日,在《海日楼丛札》书衣上题道:“晚年多病,当谨言慎行,以免懊悔。余感情用事,易冲动,不明后果,当切戒之。”[7](P51)寓自爱于自戒之中。
第二,提高自主性,消除外部世界的价值条件的影响。不少心理学家都将这一点作为提高个体化水平、自我实现的重要条件。马斯洛曾选择出48位杰出人士研究,概括出15条自我实现者的特征,其中一条是:“有较强的自主性和独立于环境和文化的倾向性。”[10](P271)罗杰斯认为人格改变的方向上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主体“越来越感到自己是评价的立足点,而不再总是按照外在的标准来评价经验。”[12](P123)如果说,“文革”前孙犁虽不认同主流文学思潮的许多观点,但他也并不针锋相对地陈述己见。那么,“文革”中,他对社会上流行的文化观、文学观,不用说根本不会苟同,且屡屡以行动冒犯之。照当时的标准,《书衣文录》中所题的图书,除鲁迅著作外,皆莫非“毒草”,例当扫除。但孙犁对之非但不批判,反而悉心洁修包装,珍爱至极。甚至,在所题的文字中,追思古人、故事,评说图书内容、版本,流连印刷史,俨然一副潇然世外的意态。他回忆30年代自己得到瞿秋白所译《海上述林(上)》时“如捧珍物,秘而藏之”的情景,慨叹今日“革命不断,批判及于译者”[7](P29);悼念诗人远千里、评论家侯金镜;高度评价柳宗元、欧阳修、蒲松龄等作家的文学成就;比较昔日的开明、北新、水沫、生活等出版机构各自的优长等等。孙犁确乎在独立思考,在以自己的价值标准评量文化现象,言必己出,决不鹦鹉学舌,依傍权威。1975年4月初,与他同居的张某离去,“临别赠言:‘现在阶级关系新变化,得确信,老干部恐怕还要被抄家。你在书皮上写的那些字,最好收拾收拾。’”[7](P132)而孙犁并未遵从。可见,当主体增强了自主性时,其人格风貌就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第三,对经验、感受较为开放。“文革”前,孙犁对自己的许多情感、感受、经验,采取一定的防卫性措施,不使其充分化、个性化,容或不无明哲保身之意。现在,他的人格处于裂变之中,故能在有限的范围、运用特定的形式,来真实地抒发、诉说,提炼自己的经验、感受和感情。百无聊赖,寂寞烦躁,如实言之;“往事不堪回首”,“心如木石”,凭心说之;对结发妻“怀惭德”,剖心示之;与同居者张某之纠纷,依次记之;而对国事之忧虑,对藏书之痴情,或直书,或曲达,皆缘书缘事发而为文。其中,1974年4月所作的百字《书箴》,是其“书痴”之情的艺术化概括,涵义颇丰,感人至深;而几处关于“情欲惑人”的危害性及自己的体验,痛切言之,似上升到人生哲学高度,深具警世作用。而孙犁直率道出,足见其胸怀磊落。
第四,保持和显示强烈的审美感。马斯洛将“具有强烈的审美感”作为自我实现者的特征之一[10](P271);这原系对各界精英普遍而言,但它对于艺术家来说显得更为重要。历史表明,当政治意识形态畸形地不断高涨时,它会造成对人们审美感的严重压抑与无形消解,从而使人们不同程度地丧失创造力。“文革”及其文艺创作状况,就说明了这一点。孙犁是艺术素养与美学修养很深厚的作家。《书衣文录》的写作证明,他是将文学的审美本质和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当作自己的生命看待的。纵令环境险恶,他也要供奉心中的美神,营构真善美的精神家园,用自己浸透着审美感的心血来浇灌它。他为“残破有损的书包皮,不惮烦,不辞累,将无生命之物看作活生生的友朋故人,情意缠绵深切,‘工作’时颇多悠思遐想”,“他是以作家艺术家常有的变态的审美心理看待劫余发还的图书的,是将自伤自叹自怜自慰之情推之于书的,又是在手抚目注、沉思默念的过程中,无意识地与书进行着旷日持久,不易觉察的价值互证和修补自己残破的梦的事。”[13](P57)视书为友人,是由实用视角向审美视角的转换,是日常情感向审美情感的升华。对书曰“故人”,曰“久别的游子”,惜其“垢污残损”、“周身疮痍”,皆根于爱。由爱而生痛生惜而益爱之。此种升华到审美层次的情感,对孙犁来说是不可驱除的。1976年9月11日,他在《苕溪渔隐丛话》书衣上题字,自析爱书之癖时说:“余见他人读书,极力压迫书籍以求方便,心颇痛之,然在彼人,此种感情实难理解”,“(余)旧习本宜改过,但不近书则已,近书则故态复萌,因既在身边,即难不顾而生情,有之为累,生之为痛,乃法则也。”[7](P91)可以说,没有这种力度相当强的审美情感的驱动,《书衣文录》的写作,将是不可能的。
应该指出,这种审美情感,推动作家围绕着“书”这一主线进行回忆和想象,从而产生了不少富于审美意味的艺术画面。多少年前购书的场景,今日包书的场景,对原藏书人命运的悬想,对友人杨朔当年在河间一盏油灯下“聚精会神,展览刀布”[7](P91)情景之回忆,等等,都极为动人。审美情感的渗透与艺术想象的运用,不仅说明《书衣文录》不是普通的日记和书籍题跋,而是有着审美特质的文学作品;而且还说明,一位作家要在“文革”那种令人窒息的岁月里真正迈向人格整合,就不能不在一般的自我实现者的应有特征中,更为着重于与艺术有着直接关联的几个方面。见之于心理功能方面的情感与见之于思维方式方面的想象,是文学艺术最重要的特质。如果严重地钝化了这两者,那么,作家将不复成为作家。仅就艺术想象而言,它对于作家的人格整合的作用尤其不容忽视。“人的想象之中,重新设立了一个自我,重新获得了一种超现实的时间空间。这种超时空感使人变成了一个完全不同于日常生活‘旧我’中的一个‘新我’。他的心态、意念、感觉、情感起了极大的变化,他开掘出一片心灵世界全新的领地。想象突破了生活的晦暗性,而在一种审美意象性的投射中,完成意义世界价值世界的诞生。想象使人得以打破自身的枷锁,设定个体永恒的图景。”[9](P73)——新时期孙犁的全部文学活动,不是延伸、扩大、显现了《书衣文录》在作家人格重塑上的潜在意义吗?不是将“文革”时期压抑过甚、积淀丰厚、浩茫连天的心理蕴蓄,化为一道道美丽的彩虹吗?
评论界将新时期的孙犁称之为“新孙犁”,这是相对于“文革”前的“老孙犁”而言的。不待说,“新”是对“老”的扬弃,它形成了新的质态,并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如果说,“老孙犁”使人想到荷花飘香,那么,“新孙犁”则使人想到苍松傲霜。后者的风采显现在这位作家新时期的创作与评论之中,不可掩抑,为世公认。新时期孙犁的不少文字,具有遒劲、冷峻、凝重的特色,这显然自他的人格蜕变而来。实际上,《书衣文录》大体上也呈现了如此的风格,只不过由于时代的高压,它的“文革”部分在上述特色之外更多地浸透着悲凉意绪而已。因此,对孙犁的“新”、“老”转换、蜕变和文风演变,我们不可不细察其端倪。要之,不应忽视,孙犁的人格蜕变起始并奠基于“文革”之中;它以潜隐的形态和奇特的物化体式,吸引着人们去体味,去研究。
收稿日期:2002-01-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