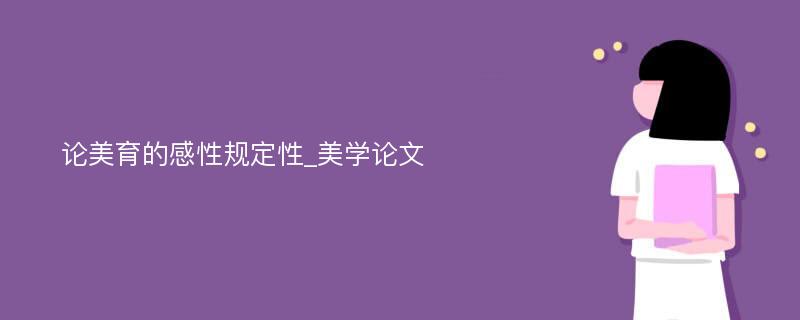
论审美教育的感性规定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规定性论文,感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40-0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124(2002)04-0033-06
在理性主义,尤其是认知理性盛行的现时代,“应当反省一下,为什么感觉的确定性原则被抛弃,而相反,抽象化的表象却被提出作为真理的标准。”[1](P39)当然,我们并不是要否定理性,我们只是要调和理性与感性的对峙,还感性以应有的地位。也许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保持着浪漫情怀,才能“诗意的栖居”。席勒认为不能用原则摧毁感觉而成为蛮人,因而,“培育感觉功能是时代更为紧迫的需要。”[2](P42)这必须走审美教育的道路,通过审美教育培养感觉能力。席勒所指出的道路应该坚持走下去。
一、审美教育理论基础的感性规定性
美学无疑是审美教育的最重要理论基础。“美学”(Aesthetics)一词在鲍姆嘉通那里是指“感性之学”,他是在悍卫人类的感性生活的价值,强调感性认识的重要性,“感性认识的美和事物的美,本身都是生命的审判,而且是无所不包的完善”[3](P6)。也就是说,美学绝不仅仅是同理性认识相对应的另一种认识行为,它首先应该是一种自在自为的自然的生命行为。在此基调上,一般认为美学研究的问题都同每一个个体的感性生活有关,与人的感性相关联的经验和创造的喜悦,既是美学的起点也是美学的归宿。美学告诉人们美是多样的,是具体的,是感性的,目的是要人们自己去看、去听、去感受,要使人相信自己的感觉,并通过自己去造就自己灵敏的感官,否则审美情趣、审美鉴赏都无从谈起。
现在所用的“美学”一词比“感性学”更为大众化,但它恰好消解掉了鲍姆嘉通用Aesthetics来命名这一学科的积极意义——强调对象本质。因此,有学者提出重建“感性学”来考察美学的新的可能性。“我所构想的感性学……涉及以各种事实与现象——感觉、感性、与感觉相关的事实与现象、感性的事实与现象……一切的一切。”[4](P170)这正符合了Aesthetics的原初之意,既关注生命体自身的品质,又探究被感受体的性质,同时亦重视精神性因素对行为的渗透。
我们从Aesthetics所构成的对象本质出发,认为“美是被感知的存在在被感知时直接被感受的完满……首先是感性的完满……其次是,美是某种完全蕴含在感性之中的意义”[5](P24)。这里所涉及的两种美可以称之为“浅易的美”与“艰奥的美”。“浅易的美”是一种和谐的美,是一种感觉的美,它是以一种完善的形式呈现,使人没有修改的念头。但它绝不是视、听、触觉感受的简单的要素,它同时直接感受到由形式所表现的意蕴。我们必须“体验”,必须对有意味的形式的直接介入才能感受到一种“韵律”——是外在形式对主体内在生命韵律的共振。这种表现是一种整体的完满,是一种以“好的形式”呈现在我们面前,表现的是一种协调。“艰奥的美”是一种“冲突的美”,一种“发现的美”,一种解释的美,它所呈现的感性形式首先就给人一种不愉快。我们必须在理性引导下对其呈现的意蕴进行介入式的理解,领悟其韵味——外在形式对主体内在信念与理想的显现。但不管何种美,都是感性的呈现,审美教育首先激起的是感性。如优美,它在形式上具有稳定、协调、柔和、细腻、光滑等特征,给人一种和谐感,使人陶醉;而壮美也有着体积、数量、规模等感性显现,但重要的是它表现的是一种冲突、对抗,这让我们恐惧与惊赞。
“美”现在是以一种高高在上的姿态接受人们的仰视与膜拜,审美渐渐被用来意指高雅、杰出与独特。对于美和美感而言,我们认为,美感似乎比美更重要。“由于美具有感性之物质,审美始于感知。”[6](P248)席勒“让美在自由之前先行”,我们应让美感在美之前先行。感受性是美感活动的最基本特征。由于美学研究与我们所接触到的是活生生的人性体验,与感触密切相关,与人类的生存方式及生存状态息息相关,我们由美感让美回到人间,回到我们的生活。只有美感才是对美的真正凸显。这与我们为什么把审美教育的内涵之一定为美感教育有内在的联系。审美教育一定要引导人自己去感受,去得出自己的结论。
二、审美教育目的的感性规定性
教育首先要培养人,要使人首先获得生命。审美教育也应培养人。如果说智育培养的是“聪明人”,德育培养的是“德性人”,体育培养的是“健康人”,那么审美教育培养的则是“审美人”。审美人是审美感受活动的主体,是能对现象进行介入式观照的主体,是体验的主体。审美人的感性发展应该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感性开掘,即发掘人的内在感官,通过自身的感官,通过审美知觉的形成,而不是凭借“延伸的肢体”去确认生命的存在;二是拯救人的感性沉沦,即避免陷入一种本能主义的泥潭,从媚俗中升华。
审美并非与功利无涉,审美行为属于超越行为,它是超功利行为,是去功利行为。康德在此意义上使用“审美无功利”。功利行为培养出的是“经济人”,超越行为培养的是“审美人”(含自律的“德性人”),只有审美人才是完整的人。审美教育要使人获得真正的审美体验,从而能自己进行审美观照。由于审美教育的对象和审美的对象之间有一种差距,我们必须以审美活动为中心,审美活动是审美教育的依托与参照。
我们站在事物面前总是显得过分矜持与理智,不信任自己的感官或偏离了自己的直接知觉,撇开知觉而妄求理解,在还没有真切感受事物之前就过快的用思考取代了感受。我们总是先去寻求隐藏在形象之中的“深刻的思想”或“时代内涵”,过快地考虑了事物与外界的联系,对外界的功能。在这一点上,我们的感觉已经自动化了,我们对自己的感官是不信任的,总是在以别人的经验为经验,感觉被忽视了。应该记住:“唯有感觉使我们像向一个独特的存在物开放那样向审美对象开放,唯有感觉使我们在思考引起的那些破坏或至少推迟传递经验的所有问题之外,同这一对象建立接触。”[7](P510)
审美教育就是要倡导一种感觉的“陌生化”,从而维持人类感性世界和感官经验的活力。审美教育就是要使人养成“感受形式美”的眼睛和有“音乐感的耳朵”,并通过对各种感官能力的开掘,以获得一种“共通感”。总之,审美教育就是要使人能“以全部的感觉在对象中肯定自己”,要使“人的感官成为人性的,并且能创造出能适应人类存在和自然界存在的全部财富的人性的感官”[8](P126)。彻底的人化是审美教育的理想。
审美教育对感性的开掘具体表现在敏锐丰富的审美知觉的形成。审美知觉的侧重点是事物的外观、形象而不是事物的自然属性,不是认识论意义上的观察,而是领悟,是对情感和想象的领悟。它的目的并不是指向概念性的认识,而是注重事物的完整的形象与生动的外观的直接呈现。它使整个世界刻满了新的意义,从而超越那种“囿于粗陋的实际需要的感觉”,那种只具有“有限意义的感觉”。
当代社会是一个“技术关联”的社会,是一个形象恣生的时代,这种形象是市场与技术联姻的自我幻影。其中的审美文化呈现为一种泛审美意识与伪审美精神。在这种审美文化氛围中,技术吞并了艺术,文化和艺术变成了包装,大众审美提供了种种表现感性冲动的形式、时间与内涵。人尽管已不是“工作的机器”,却成了享乐的机器,“跟着感觉走”,“游戏人生”成了另一种形式与意义上的“单面人”。
因此,通过审美教育开掘感性实际上所进行的乃是一种审美人生观的培养,是一种世界观的教育,是一种人生态度的熏染,是一种人性的拯救,其目的是要使人生活在美的世界中,使人生活在平和而不是平庸之中。审美教育强调美感教育,强调批判与判断力培养,强调体验,强调审美主体的形成,就是要让学生处处都能感受到美,以一种美的感官去形成美的世界。
三、审美教育中介的感性规定性
各类教育中介(物质中介、意识中介、行为中介)中都显现出感性的呼唤,感性是教育的通道。在这里我们主要讨论审美教育最特殊的中介——形象的感性规定性。
智育以“文字”为中介,德育以“规范”为中介,体育以“技巧”为中介,而审美教育则以“形象”为中介。德智二育中都涉及或关注形象,但形象处于辅助地位,形象是手段,目的是为了更好的进行理性教育:在体育中,形象不得不依附于技巧,只有在审美教育中,形象才既是手段又是目的。在众多的审美教育论述中,都承认形象性是审美教育的一个最显著特点。形象一直是美学中的一个重要范畴,前面论及的美、美学的感性特质与此有共通之处。形象是形式的第三层含义,指外观、形状、表层等,因而形象是美的寓所,形象性是美的重要特性,在美感教育中,不管是体验浅易的美还是领悟艰奥的美,都离不开形象。
在中国传统美学中“意”与“象”常是联在一起的,并形成了一种意象(意义与形象)一体的思维模式。“意象”、“形神”、“意境”、“直觉”等学说中都贯穿着“形象”这一基本范畴。在意象论中,形象的把握是优于语言文字方式的——“书不尽言,言不尽意”;而形象则因“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而成为一种重要的认识与言说方式。西方美学中的“形象”是作为本体地位被加以关注,“形象”是贯穿西方美学史的一个重要概念。“摹仿”是亚里斯多德对此的看法,“美只能在形象中见出”[9](P126)是黑格尔的明确界定。这种以形象为工具与目的的方式在维柯那里演变成了“诗性智慧”。
鉴于此种理解,如果说智育所要的是一种抽象能力,是要“得意忘形”,那么审美教育则要的是一种意象能力,是要“立象尽意”。
审美教育中的形象中介是感性的、生动的,审美教育就是要以“美的形象”(审美外观的活形象)作为教育手段,使人达到一种形象下的直观。由于这种形象能激起一种“普遍情感”,从而具有了一种共通性。情感在形象中栖息,无形象则情感无从依附,形象在情感中永生,无情感则形象没有灵气。这是为什么众多的审美教育论著中把审美教育称为情感教育的一个重要原因。审美教育中的“情感教育是一种非功利非认识而以自由和创造力为特征的情感教育”[10](P123)。因而它与智育、德育中的情感不一样,不是关注形象与外界的功能关系,而是考虑形象本身的价值,是为了“诗性智慧”本身,正是在这一点上,形象既是目的又是手段得以成立。审美教育中的情感是具有感性特征的,它指向的是感性外观,而不是感性实体。
形象作为审美教育的中介,其基本的实现条件与途径,已在前面有所论述,在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审美教育必须为“形象”提供条件,创造机会。而且这种形象是整体的形象,是一种整体意蕴,而不是被肢解了的要素,亦不是形式的原则。因此,在审美教育中一定要注意对形象的整体感受。审美教育中的形象不是分析,而是感受。
四、审美教育反馈的感性规定性
审美教育活动的反馈可以说是一种审美教育成果的表现。审美教育活动的反馈形式之一就是在审美冲动支使下的一种创造品,这种反馈的感性规定性是无须赘言的。因此,我们把思绪集中在另一种反馈形式上,即审美主体的反应,这具体地表现为审美情感的流露,审美力的形成。审美活动是审美教育的参照与依托,审美教育的反馈必须放在整个审美活动中来考虑。
在审美活动中,审美主体必须对外界环境的限定性作出反应,因此,呈现出一种外在目的;审美教育的独特性又使审美主体对自己的需要作出反应,即同时亦具备了内在目的。因而,审美主体的反应也就是针对这两种目的的反馈:注重对外在目的的表演性反应,注重内在目的的愉悦性反应。表演性反应把重心放在了如何调整自身,从而使自己与外界和谐;愉悦性反应把重心放在了如何享受自身,从而使自己身心和谐。这两种反应是审美情感的两种外显方式,二者的一个共同目的就是为了使人“诗意的栖居”。
在表演性反应中,审美主体的情感表达程度以外界的需求为标准。这种表演性反应(跳个舞、唱个歌)所获得的掌声与激励,使审美主体获得了一种被认同感,继而强化了这种表演的欲望。事实上,这种表演已转化成了一种被迫的表演。尽管“人只是在表演”[11],但我们所需要的只是自愿的表演,那才是一种真诚的表演,是在表演真诚。因此,我们认同这种表演性,因为它亦是一种言说方式,是一种对审美感受的表达与确证。这种表演不是为了达成共识,而是为了表现,是为了被理解,被接受,是为了审美情感的流露与宣泄。审美活动反馈的表演不应使人意识到在被迫表演,不存在不真诚的自愿表演,真正自愿的表演就是在表演真诚,在真诚的显露出真实的感受。
如果说表演性反应是“延时”性的,那么愉悦性反应则是“即时”性的。在审美教育中,我们必须注意对审美主体愉悦性反应的强化,这是审美主体情感形成最直接的途径,也是唯一途径。“美就是一种在场的关系。”[6](P219)它首先强调的是对个体的意义。在审美中,不允许“不在场”,没有“缺席”的权利。必须体验,体验是生命意义的瞬间生成。每获得一次真切的体验就是生命可能性的一种实现。
审美主体的愉悦性反应决不是由于因果关系而引起的,它是一种对事物本身的自由的想象与领悟,是体验时的一种情感流露。它是超功利的反应形式,它所面对的是感性外观而不是实体,所注重的是外观与外观的接轨,而不是被视为放在环境中的对象,即不应是被视为装饰品,而应是一种“交流”的对象,是它的存在本身,不是与环境的关系,而是“我”与“你”的关系。审美主体在审美活动中所获得的那种愉悦、轻松、和谐的感觉就是一种美,就是一种享受,就是一种审美情感。它通过审美力而表现出来。”
审美力就是借助于形象的一种特殊情感判断能力,它是一种情感本身的判断,而不是藉道德情感而作出的道德判断,亦不是借认知情感而作出的认知判断。道德感是一种典型的评价性体验,其评价标准是有参照系的。它所关心的主要不是一种快乐,而是“更为关心避免痛苦”[12](P16)。而且,道德判断是否定的,首先是对不良方面的感知,而审美判断则是积极的,它是对好的方面的感知。理智感受客观物理法则的约束,认知判断是一种事实判断,它的分析性(与对象的“若即若离”性)扼杀了审美情感的生动与圆满性;其实证性亦抹平了在审美情感驱动下的不着边际的想象力。美感指向客体的感情形式,它是超功利的,又是丰富的,它执着于感性对象,却又溶有理性。
五、审美教育实践形式的感性规定性
我们总是说审美教育对其他几育有促进作用而很少谈及其他几育对审美教育有什么作用,这说明审美教育在享受一种“殊荣”,审美教育有一种统摄力,也就是说审美教育是教育的一种境界。审美教育不只是培养理智,也不仅仅培育心灵,而是培育一个完整的人,它所注重的是“把人的各种能力统一起来的一种整体心成”[13](P173)。
西方有艺术教育的传统,且艺术教育几乎是审美教育的代名词,但审美教育绝对不仅限于艺术教育。有研究认为审美教育可分为作为感性教育的艺术文化教育与作为理性教育的美学教育[14](P48-52)。这种划分虽然有些机械,但也有其合理性,尤其是它强调了艺术教育的感性教育性质。艺术是人类情感符号形式的创造,艺术不诉诸概念而诉诸具体可感的形式。艺术深切的涉及知觉、思想与有形动作的实际过程,艺术的形式直接引起感官的共鸣,艺术的表象是另一种复现或符号化这个世界的方式。审美亦不是以概念为中介,而直接地把握生动的感性形式。
尽管我们不认同“艺术教育应为教育的基础”[15](P7),但也认为音乐、绘画、舞蹈等艺术形式不应该是在教育之余进行的,而是教育的重要内容,而且人的感性的丰富发展既是作为人生存的基本能力,亦是作为人类个性培养的基础。因此,把艺术教育视为感性教育的核心也未尚不可。但这只是一种小美育观,现在我们倡导的是一种大美育观,自然美、社会美、人自身的美等各种形式的美都进入到审美教育的领域中来了,这使审美教育的实践形式更加丰富起来,而且这几种形式中直接涉及到人的感性。
人是被抛入传统中的,人被文化笼罩着,教育亦被理解成主体间的文化传承[16](P111)。现在有许多学者认为当代大众即审美文化,是一种在泛审美意识的追求中片面地发展以商品性为前提但缺少了等价性、以技术性为媒介但缺少了复杂性、以娱乐性为中心但缺少了神圣性、以形象性为主体但缺少了意义性的审美文化。我们在某种意义上承认这种观点,对于考察教育的背景、审美教育的目的、审美教育的氛围与环境以及发现审美教育在实践中存在的失误等方面有重要意义。
审美教育通过对审美文化的审视、反省与改造,以期形成一种高尚的审美趣味,并承担起构建审美文化的重担。因为审美文化毕竟实现了美与生活的公开拥抱——“美成为了人生活的唯一证明”。审美文化就是使生活审美化,使人“艺术化生存”,它广延了审美对象,扩大了审美教育的范围。审美教育一方面必须在审美文化批判、时代反思的基础上重建主流审美文化,以精英文化统领大众文化;另一方面又必须从个体身上着手,使审美教育成为自我实现的理想形式与根本途径,从而实现各种能力协调发展的“完全之人物”。
通过自然美进行的审美教育所实现的肯定是一种感性教育。当年卢梭把他的爱弥尔带到乡村,就是因为他反对“臆造的美”,而认为“一切真正的美的典型存在大自然中”[17](P482)。大自然中的美要靠自己去看、去听、去感受、去发现、去判断。
人作为审美对象,其具体的审美结构包括人的形体美与精神美(人格美)。形体美即一种健美,它能被人的视觉所捕捉到,所显露的是生命的活力与激情,它所激起的是人的一种和谐的状态的美,而不是畸形的“健美”。由于“主体就是他的一连串行为”[20](P126),因而,我们把人格看成是一个人在社会生活中所表现出来的整体形象。对于人格美的追求所表达的就是主体对“怎样生活”及“如何存在”的看法。
六、审美教育实践中的误区及其感性转向
以往的审美教育是作为一种有意识的心理准备状态,是一种去欣赏别人告诉你是“美的”事物的活动,是一种认识的累积,它要我们去承认美,也就是说审美教育出现了一种认知化倾向。而美感则是面对现象所产生的直接的感动,这是一种感受的成果,它是在发现美。诚然,在“承认”的意义上使用“审美”,的确不能把审美教育和美感教育并列起来,但我们可以在另一个意义上,即在“审美”的本源的意义上使二者等同起来,那就是在判断的意义上使用“审美”,即回到“审美”这一词本身。有了这种判断,才能有直接面对时的感触,才能去激动,这种审美(美感)活动才是一种真正美好的生态态度,因为它使你无时无刻不发现美。总的来说,我们更倾向于接受审美教育是美感教育这种表达方式,因为我们承认重要的是美感。它所关心的是感性本身,感性在审美教育中既是目的又是手段。感性是审美教育中的关键概念之一。
一般的审美教育理论都强调发现美、欣赏美、创造美,认为这些是审美教育的主要内容。按理说,发现美和美感的获得,与感性的开掘应该是有比较密切的联系,但在审美教育实践中,“发现美”也只是对审美活动进行逻辑分析的产物,在实践中亦不具操作性。学生并不能发现自己生活在一个美的世界中,并没有“因为没有美就不能生活”(苏霍姆林斯基语),并不能感受到生活中的美,而只是认同一条:在展览馆里陈列的作品是艺术品,是美的;著名(权威)批评(评论)家的理解(选择)是正确的。而评论家也不过是因为多了解一些作者的生活背景、创作时的心境及通过与作者交流从而把握了作者想在作品中“表现”什么的意图。他们因为这种关联性的阐释而成为了作品的权威解释者。
当学生面对现象、事物时,他不是在感受,而是在分析;不是在判断,而是在接受;不是在想象,而是在回忆。这主要是因为审美教育忽视了人的感性开掘,忽视了美感形成的最直接途径,忽视了人的审美体验的重要性。因而,他不会选择,不会欣赏,更不用说创造了。
另外,当前的审美教育主要囿于艺术教育范围之内,尽管提出了“大美育观”,把自然美、社会美、人本身的美等丰富的感性存在都纳入到审美教育,由于这几种美基本上不能进入教育而在审美教育实践中不能获得一席之地。就算把学生领到外面去参观,去游览名山胜水,也并没有收到好的审美教育效果,因为审美教育的观念仍没有改变,仍是以一种解释美——它为什么是美的,而不是让学生自己去领略,去感受。但它们不能进入教室,并不表明它们不能进入课堂,不能起到好的效果。只是我们要注意方式,要有一种审美教育意识。这几种美是不能“借”的,即我们不是在“借美育人”,而是要把它们转化为一种教育理念,进行深层次的渗透。
在审美教育中,正在进行着审美经验的“传授”。而事实上,我们都承认审美体验是个人的体验,总是个人的美感,这种体验感受是“妙不可传”的,它不能教,只可导,只有领悟。在音乐、美术等领域中的“经典名作”的欣赏中,这种审美经验的“传递”显得尤为突出。个人的审美体验与感受最终臣服于评论家的一己之见或历史赋予作品的意义,最终达成一种共识。有些教师尽管在陈述自己(所代表的被接受的普遍意见)之前,也先让学生描述自己的感受,但最后一个“总结”性的发言,却又导致了“共识”,殊不知艺术的魅力就在于个性化的生命表达。
我们以前过分地关注作者要在作品中表现的是什么,以作者的意向为评价标准,由于这种“标准”的存在,因而导致“共识”的必要性。一般的艺术教育所强调的都是技巧训练,所遵奉的信条就是“技之极者近乎道”,其最高水准、最理想状态也就是游刃有余的“疱丁”。但这是一条危险的道路,很容易使人成为“匠人”——有技法,无思想。这种审美教育方式所注重的是感性的,但是却偏离了方向,它太注重“说”和“做”,而忽略了“视”和“听”。对于审美教育的逻辑而言,人只有先去感受美(发现美、欣赏美都是一个意思),后才能创造美(表现美),才能以另一种言说方式去言说不可言说之感受。
在审美教育中,这种观念必须转变。“文本”概念的出现,解释学、接受美学的发展对审美教育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我们更应该重视理解过程的创造性,把作者的意向作为文本的一种存在状态。学生、教师、教材、环境都是一种开放着的“文本”,我们从自己的角度出发去理解或面对文本,实现其有效性,从对话中获得“创造的快乐”[19](P362)。
审美教育要培养审美感受的主体,首先就要使学生回到感性,要使学生自己面对现象、事物去进行美的分析,去想象,去领悟。审美教育的感性转向是“回到事物本身去”理念的体现:一方面回到人本身的生物体的感觉本身去,通过培养敏锐的“视”“听”等感性器官去与文本“碰撞”、“交谈”;另一方面回到对象本身去,关注对象的实在,对象的感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