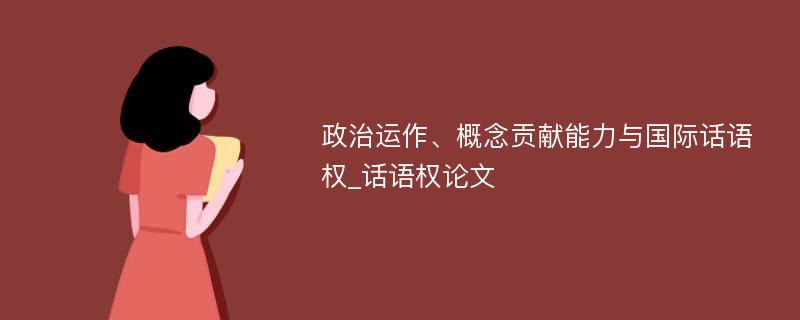
政治操作、理念贡献能力与国际话语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话语权论文,理念论文,贡献论文,能力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国际话语权体现的是一国的政治操作能力和理念贡献能力,同时也是国家软实力要素之一。一国国际话语权的提升与该国的政治和学术资源性实力相关,更与该国的政治和学术精英在国际政治和学术舞台上的活动能量大小有关。因此,要提升中国的国际话语权,我们就必须大力提高中国的政治操作能力和理念贡献能力。
一、国际话语权是个好东西
国际话语权是个好东西。说它好,是因为它能以非暴力、非强制的方式改变他人的思想和行为,并使一国之地方性的理念和主张成为世界性的理念和主张。《孙子兵法》所谓“攻心为上”,说的就是这个意思。攻下别人的心,不就是使攻者之思成为被攻者之想吗?可见,国际话语权古已有之,只是没用这个现代词汇而已。
在国际政治领域,人们通常崇拜和颂扬物质性实力(军事实力和经济实力),但对以思想和理论为核心的话语权这类软实力不算特别重视,即使谈论它,也多将其当作物质性实力的附属品。事实并非如此。在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中,成功地通过话语和观念来改变和塑造他人(国)的例子屡见不鲜。《尚书·虞书·大禹谟》中就曾记载过一个以话语权“征服”他者心灵的故事:三苗部落叛乱,舜命令大禹前去征伐。大禹领兵镇压却成效不彰。伯益就让大禹放弃武力,而建议舜改修文德,结果三苗来服。由于古文简约,我们不知舜当年提出了什么政治或文化话语,并成功地使三苗接受这些话语,但这件事告诉我们,话语的力量,或者更通俗地说,思想的力量有时并不亚于物质的力量。
一个以话语权塑造国家的当代实例是南非。南非曾长期实行种族隔离制度,国际社会曾对其施以除战争之外的一切必要手段,包括政治和经济制裁、武器禁运,等等,但均未能迫使白人种族主义者改弦更张,反使南非在禁运状态下实现了经济现代化。冷战结束后,国际社会掀起一股民主化浪潮。当这股浪潮横扫南非之后,结果种族隔离制度顷刻间土崩瓦解,所以正是民主这个话语塑造了一个新南非。
如果我们以能力来定义国际话语权的话,那么国际话语权可体现在政治操作能力和理念贡献能力两个方面。政治操作能力主要体现为议题设定和规则制定能力,以及国际动员能力;理念贡献能力主要体现为提出并推广新思想和新观念的能力。政治操作能力和理念贡献能力是两种独立而又密切相关的能力。如果一国政治操作能力强,那么就有助于推广自己的理念。比如,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中拥有强大的政治操作能力,那么像“华盛顿共识”这样的经济发展理念就更容易得到推广。如果一国理念贡献能力强,那么也有助于促进自己的政治操作能力。比如,北欧国家长期以来专注于和平研究,提出过不少解决国际和国内武装冲突的概念与设想,因此北欧政治家常有机会操刀斡旋国际冲突之重任。
二、中国的国际话语权:从波峰到谷底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和改革开放30周年,各行各业都在总结60年或30年的成就与经验。具体到国际话语权,近期历史表明中国经历了一个从波峰到波谷的曲线变化过程。1949—1972年,中国虽然处于孤立状态,并被排除在绝大多数国际组织之外,但那时中国的理念贡献能力很强。中国向国际反帝反殖运动提供了自己的革命理论,向世界爱好和平的国家提供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向国际关系学界提供了“三个世界”概念,因此,那时中国的国际话语权相当突出。1972年,任凭政治操作能力超强的美国如何操作,联合国内的第三世界国家就是不为所动,硬是把中国“抬进”了联合国,而中国当时还不是联合国成员国,没有任何议题设立和规则制定能力。
从1979年改革开放至今,中国眼光向内,专注于国内经济的发展,自1989年之后又执行以“韬光养晦、有所作为”为核心的外交政策,我们的国际话语权从波峰逐渐走向低谷。中国虽然已经成为绝大多数国际组织的成员国,而且在绝大多数外交和国际性场合也有中国人的身影,但由于我们在议题设立和规则制定等方面的能力有限,因此中国在制度性和非制度性国际场合的话语权并不突出。也就是说,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国际话语权的增长与其综合国力增长并不同步,后者的增长幅度远高于前者。
近一两年来,关于中国国际话语权的讨论日渐热烈,但不少人似乎认为经济实力的增加能够自然带来话语权的增长。比如,有人认为这次金融危机对提升中国的国际话语权是个良机,只要我们愿意出钱,就能在IMF这样的国际金融机构内换取更多的话语权,其实这是一个误区。这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权力要素,两者之间的可转换性并不强。这次G20伦敦峰会的结果证明,即使中国愿意出钱,发达国家也不肯稀释自己在IMF中的股份额。实际上,像IMF和世界银行这样的国际组织表面上是个经济组织,而其内在决策机制反映的是国际政治权力的分配。美国在这两个组织中拥有的绝对话语权是其在二战中以数百万将士的生命和鲜血换来的,绝非是其他国家可以用钱买来的。如果能用钱买到话语权的话,那话语权早就落在沙特这样的OPEC成员国手中了。
话语权,顾名思义,就是这种权力表现在你的话语当中。如果你不说出来,怎么去说服别人呢?如果你不作为,怎么运用政治操作能力呢?然而,“韬光养晦、有所作为”原则在今天不利于中国国际话语权的快速提升,虽然它曾经帮助我们回避了很多国际矛盾和负面事件的影响,为中国创造了一个比较有利的国际环境。首先,这一原则要求中国在遇到国际矛盾和国际冲突时尽量少出头并低调面对,在国际组织和国际会议等场合少成为议题的发起者、议程的设立者和文本的起草者,因此,中国总是在国际场合主动成为一个沉默寡言者、被动参与者或中立弃权者。我们的有所作为通常局限于与我切身利益高度相关的事务(主要是领土主权问题),在其他事务上少有高调介入之时。总的来说,如果从加入的国际组织和国际制度的数量来看,中国的确融入了国际社会,但从政治操作能力来看,中国的参与质量不高。
其次,这一原则要求中国实行不结盟政策,从而阻碍了中国的国际规则制定能力。在联合国体系下,有无盟友和盟友多少是一国国际规则制定能力的重要指标。制定和修订国际规则通常非一国之力所能办到,而需要一个团结与协作的国家集团。中国当年能加入联合国,就是靠第三世界盟友的无私帮助,迫使联合国违反美国的意愿而修订了有关规则。如果中国继续执行“韬晦”外交政策,那么我们在制定和修订国际规则时就难以组织起一个以盟友为主体的国家集团,制定(修订)于我有利的规则,或阻止对方制定(修订)于我不利的规则。
第三,这一原则不利于中国增强自己的战略信誉,从而阻碍中国的国际动员能力。“韬光养晦、有所作为”说白了就是见机行事,而一个战略信誉强的国家在很多时候就不能见机行事,因为只有这样,它才能在其他国家心目中形成一个稳定的行为预期,从而在必要之时能够动员起足够多的国家帮助自己。
另外,虽然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巨大,物质性实力(特别是经济实力)迅速膨胀,但我们未能像建国头30年那样,向世界提供具有普遍意义的思想、理论和概念。相反,受苏东集团解体等种种复杂国际因素的影响,中国在国际话语方面通常处于守势。我们常常以中国特色、中国国情或“民族的就是世界的”这样的“特色”话语来抵挡某些国际强势话语的冲击。这种作法虽然使我们能够理直气壮地抵御某些国际性话语的冲击,但这反而使我们难以向世界贡献普世性的理念。一个话语是地方性的还是国际性的,就看它能为多少国家所接受。一国提出的、能为世界所接受的话语越多,那么这个国家的国际话语权就越强。如果我们单纯强调“中国特色”,那么就意味着这些话语只适用于中国,而难以向世界推广。
我们以中国的“发展话语权”为例说明这一点。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的发展与改革道路与所谓的“华盛顿共识”大相径庭,我们的确可以说中国的改革开放模式是具有“中国性”的发展道路。但是,如果这条道路只有中国人可以通过,而其他国家过不去,那么中国人把这样的“发展话语权”总结并贡献出来就缺乏普遍意义,因为别的国家学不了。如果我们能从中国的发展模式中总结出一些具有普遍意义的东西,就像当年毛泽东提出的“农村包围城市”革命理论一样,那我们的“发展话语权”就有世界性的意义,因为其他国家、特别是一些第三世界国家是可以学习和借鉴的。所以,中国提出的话语应当是中国性和普世性的结合,即基于中国经验而具备世界价值。
三、中国怎么办?
基于以上分析,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的策略就显而易见了。中国必须从政治操作能力和理念贡献能力两方面入手,提高中国的国际话语权。
首先,我们应当适度调整“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外交政策。这一政策仍有其现实意义,但今后应更加突出有所作为。有所为,有所不为,但“为”的范围和力度应大于“不为”的范围和力度。在很多场合,中国的立场宣示很鲜明,但政策措施却很圆融,这实际上不利于树立中国的战略信誉。在战略信誉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能只看眼前一时的得失,因为从长期来看,国家间关系是一种多轮博弈,所以向他国发出明确的政策信号,为他国树立稳定的政策预期是很重要的,它也是我们争取盟友的重要前提和基础。
其次,我们应当在各类国际场合努力成为积极的参与者。中国要有声音、有主张、有方案、有位子。有位子这一点最为重要。如果中国或中国人当选为某一组织、委员会或机构的主席,或成为领导成员之一,那么我们的声音、主张和方案就更有被关注和被接受的可能。
第三,我们有必要重新考虑不结盟政策,通过发展实质性的盟友关系,扩大我国的盟友数量和提高盟友质量,特别是与周边国家的战略友好关系。如能加强和扩大与周边国家的军事战略合作,中国则能较快地增强国际动员力。如果我们有更强大的国际动员力,则中国的政治操作能力就能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第四,我们要以“立足中国、胸怀世界”的精神向国际社会贡献话语。我们虽然理直气壮地以“中国性”来反对某些西方的“普世性”话语,但就没想过自己能为世界贡献一点普世性话语吗?中国在历史上向来不乏普世性话语。比如,儒家思想数千年来一直就是“东亚世界”的普世性话语。上文提到的“农村包围城市”、“三个世界”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等都是普世性话语。今年是新中国成立60周年和改革开放30周年,我们应当好好总结60年和30年的经验,并从中精炼出一些具有普遍意义的话语贡献给世界。
中国的迅速崛起意味着中国在实力上与美国差距的减少,以及与诸强差距的加大。展望未来的国际体系,有可能出现美、中两极并立的格局。但这是指硬实力要素而言,像话语权这种软实力未必会与硬实力的增长同步。一个大力士的思想就出类拔萃吗?话语权的独特性就在于它与人的思想有关,与理解、交流、接受和塑造这些无形的交往过程有关。近三四个世纪以来,西方思想一直是人类思想的主流,西方的话语因而也在人类话语体系中拥有“霸权”地位。你可以质疑西方话语有种种的不合理性,但不能否认它们在大体上仍能切合近三四个世纪以来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与现状。因此,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以及其他新兴国家仍不具备挑战和替代西方话语霸权的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