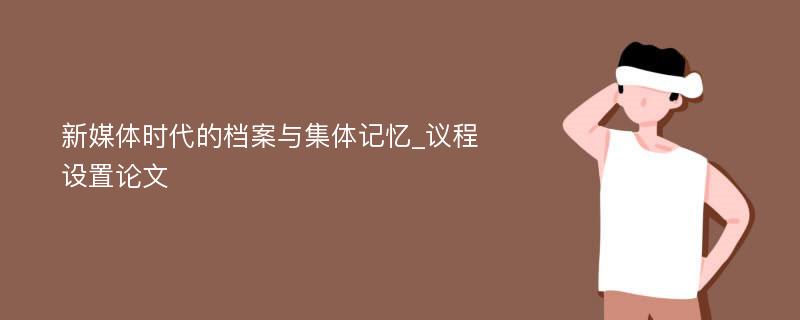
新媒体时代的档案与集体记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集体论文,记忆论文,档案论文,媒体论文,时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集体记忆概念最早由法国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于1925年在《记忆的社会框架》一文中提出。哈布瓦赫将个体记忆放大至社会群体层面进行考察,提出集体记忆乃是一个特定社会群体之成员共享往事的过程和结果,保证集体记忆传承的条件是社会交往及群体意识需要提取该记忆的延续性[1]。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社会学家保罗·康纳顿在哈布瓦赫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人类的身体实践和仪式之中保存着集体记忆或曰社会记忆。他强调,“任何社会秩序下的参与者必须具有一个共同的记忆”,“我们对现在的体验,大多取决于我们对过去的了解;我们有关过去的形象,通常服务于现存社会秩序的合法化”[2]。 当我们的视角从现在跨越到未来,未来对过去的集体记忆,正是来源于对当下的了解。当下形成并留存什么样的记载,决定了未来拥有什么样的记忆素材。当下既可以由康纳顿所说的身体实践和仪式所记载,也可以由刻写实践所记载。人类历史上每一次记录与交流技术的跃迁,从结绳记事到岩画,从口述传说到文字记录,从文稿、书籍等印刷媒介到电视、广播等大众传播媒介,再到当下的网络论坛、博客、微博、微信、社交网络等新媒体,在改变人类交往方式的同时,也为人类的刻写实践提供了不断革新的方式,由此重塑了集体记忆的方式、载体和内容。 当下,新媒体技术以其鲜明的交互性、平等性、及时行、共享性等特征已经越来越深入地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也不可避免地渗透到集体记忆中去,影响集体记忆的形成、维护和存续。本文考察新媒体应用对集体记忆的影响,探讨档案在集体记忆建构中的价值,并探索构建新媒体时代档案记忆的方式。 1 新媒体环境下的集体记忆 德国民俗学者沃尔夫冈·卡舒巴称互联网乃是“全球集体记忆的档案馆”[3],这个集体记忆正是由于大众书写才如此丰富、多元,既宏大而又细微。新媒体技术开启了大众书写时代,为大众广泛、深入地参与当下社会的公共事务、重大事件提供了史无前例的机会和平台,给大众书写当下现实留存未来记忆提供了期待。然而,“技术既无好坏,亦非中立”,克兰兹伯格第一定律如是说。新媒体技术因其自身的特点,也为集体记忆带来了一系列风险。 1.1 集体记忆进入大众书写模式 法国思想家雅克·德里达曾指出,“从过去到现在”的记忆建构就是一个权力运作过程[4]。这里所说的权力主要体现在根据谁在当下的理念、利益和期待去建构和叙述过去,即哈布瓦赫所言,集体记忆定格于过去,却由当下所限定。然而,“从现在到未来”的记忆建构何尝不是一个权力运作过程?这个权力的核心是当下的话语权,“话语意味着一个社会团体依据某些成规将其意义传播于社会之中,以此确立其社会地位,并为其他团体所认识的过程”[5]。话语权掌握在谁的手里,谁就有权在社会中传播与其利益一致的意义,创造并书写当下的实践,为未来留下记忆素材,塑造未来的记忆。 传统媒体时代,话语权往往掌握在权力精英手中,社会大众只是扮演受众的角色。而新媒体颠覆了精英在传统媒体生态中的话语垄断态势,重新配置了话语权关系,大众借由新媒体从精英手中争得话语权,得到形式上的言论赋权。大众利用网络论坛、博客、微博、微信及社交网络等新媒体平台实现了对社会公共事务和重大事件的大众书写。 大众书写促进了公共舆论空间的构建,社会公众在此空间针对社会事务自由发布信息,述说观点,甚至宣泄情绪。在这个空间,个体被看见,群体被展现。公共舆论空间为未来留下的集体记忆素材呈现了复杂现实的原貌,不仅有粗描的政策,还有鲜活的人物,写实的细节,这也意味着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有了书写“完整历史”、“完整记忆”的可能。 更重要的是,大众书写重构了议程设置模式。议程设置过程包括媒体议程设置、公众议程设置和政策议程设置[6]。传统媒体环境下,媒体议程影响公众议程,后者反过来又影响政策议程,即媒体议程设置→公众议程设置→政策议程设置[7]。在此过程中,民间话语有可能被精英话语、官方话语排斥在外,以致民间话语基本上湮没无闻。而新媒体环境下,事件的发生可以通过新媒体的传播快速上升为公众议题,引导大众媒体的议程设置,并对政策议程产生影响和推动,即,突发事件在新媒体平台首发——传统媒体跟进——政府作出回应。在这种新的议程设置模式里,新媒体拥有相对独立的议程设置自主权,并影响传统媒体议程、甚至政策议程的设置。微博打拐、“7·23”动车事故、郭美美事件等一系列网络重大事件表明,大众书写已经深深介入社会公共事务以及重大事件的发生、发展过程中,缓慢但坚实地推进着国家新语境、国民新思维和社会生态变革。由大众参与并推动的当下变革应当被历史铭记,而只有将新媒体平台上的这些经验留存下来,未来才可以回望得见这一段由大众参与书写的记忆。 1.2 集体记忆面临的风险 因于新媒体技术自身的特点,新媒体环境下集体记忆的记录、沉淀、保存和传承处于一种相对以前更为开放、更加不确定的空间中,面临一系列风险。 (1)集体记忆失存的风险 信息存储设备以其疯狂增长的存储能力不断印证着摩尔定律,人类社会拥有的数据也不断从ZB向下一个指数级冲刺。这给了我们一种错觉,似乎那些记载了大众在新媒体时代角色与价值的记录会被理所当然地留存下来,等着我们或后人需要的时候轻而易举地检索到、浏览到。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新媒体平台运营商少有在记录保存方面做出专门规定,而网站关闭、网址变更、链接失效、发帖记录被随意或故意删除等屡见不鲜,这意味着那些未被有意留存下来的集体记忆面临永远失去的风险。 (2)集体记忆被遗忘的风险 新媒体平台信息具有内容快餐化的特点。绝大多数信息被淹没在信息的海洋中,通常引不起任何的关注或影响范围非常有限。而引起关注成为热点的信息,往往不是在得到社会充分关注和讨论后结束的,而是被另外一个热点所取代,即所谓“替代式消亡”[8]。在这样的环境中,大众始终处于一种“追风”的状态,难以对值得铭记的社会事件进行深层思考,沉淀更多的意义。 (3)集体记忆价值被消解的风险 新媒体平台信息过载导致注意力“疲劳”。微博上“随手拍照解救乞讨儿童”曾引起广泛关注,然而随着一张又一张照片的发布,大众的疲劳感也随之上升,最后反倒难以引起多少反应。对过往经验中高尚或丑陋的记忆本应使集体或者被鼓舞前行,或者牢记前车之鉴,然而,新媒体平台上类似的观摩经历一而再再而三,大众反而变得越来越麻木,越来越“宽容”,对身边的丑陋司空见惯,集体记忆本应起到的积极力量被消解。 另外,新媒体平台不可避免地滋生网络垃圾文化,甚至产生信息的劣币驱逐良币现象,即泛滥的琐屑无价值信息使受众变得麻木,失去了对信息价值的判断能力,以及对重要信息的识别能力。各种网络炒作和网络热点与公众一呼一应,加之商家的投资包装,一个网络垃圾文化时代彻底到来了[9]。这种网络垃圾文化导致人们习惯于浸泡在娱乐信息里,而难以对关涉到族群认同、身份认同的话题和史实进行严肃认真地思考,这最终只会侵蚀集体记忆。 (4)集体记忆失真的风险 新媒体让每个人参与到信息的制造和传播过程中,而公众参与的背后又意味着信息极容易被捏造和篡改。以微博信息为例,美国新闻学者克雷格·西尔弗曼提出“原始微博法则”:人们倾向于转发包含错误信息的原始微博,而选择忽视随后发出的更正信息。这是因为原始微博包含更多吸引人眼球的新闻元素,而事情的真相则索然无味。另外,许多人对事件并不真正了解,就匆匆发表议论,这也易造成对事件真相的扭曲与误判。信息失真只会造成集体记忆偏离甚至背离历史事实,蒙上更多迷雾。 (5)集体记忆碎片化的风险 尽管新媒体平台为大众参与社会公共事务以及重大事件提供了交流和记录功能,它本身并不承担对这些记录进行有意义地组织的功能。在网络热点事件的发生、发展过程中,微博、微信、网络论坛、博客、各类社交网站等往往是一齐涌上,各显神通,推波助澜。它们共同参与并见证了网络重大历史事件,但是没有一种平台拥有该事件的完整记录。集体记忆材料呈碎片化散落在各个新媒体平台上,未能被提炼、汇集。更重要的是,各类社会事件在新媒体平台酝酿、发酵后,往往由传统媒体接手将其推向新的高潮,并最终有可能引起官方机构制定政策或发表声明作出响应。是故,集体记忆的碎片除了分散在各种新媒体平台上之外,还分散在传统媒体上、官方文件中。 2 档案之于集体记忆 在古希腊神话中,记忆女神谟涅摩绪涅常常被描绘成一位身披绿色常青柏,手持记录工具——书和笔的年轻女性,这一文明启蒙时期塑造的形象后来成为记忆的象征。在人类漫长的发展过程中,档案的历史和记录的历史一样悠久,档案正是凭借对人类社会活动的独特记录在集体记忆的建构、传承中占有一席之地。 2.1 档案是建构集体记忆的重要媒介 正如哈布瓦赫所言,集体记忆不是一个既定的概念,而是一个社会建构的概念,它不是某种神秘的思想,而是人们根据当下来对集体的过去进行理解与建构、回忆与再现[1]。集体的过去既可能留存于神话传说、民间故事、体化实践、操演仪式、器物建筑,也可能留存于文献记录中。康纳顿明确肯定了文献记录所代表的刻写实践在集体记忆建构中的价值,即“用刻写传递的任何记述,被不可改变地固定下来,形成记忆的人工制品,简化了记忆的处理过程,并有利于记忆进入公共领域”[2]。美国学者肯尼斯·富特则专门强调了文献记录大家族中的重要成员——档案在集体记忆中的价值,他指出,“档案可以被视为一种延展人类交流时空范围的重要手段,与其他交流手段(如口述和仪式传统)一起,实现信息传递,从而维持记忆的世代相传”[10]。 档案是人们在社会实践活动中形成的原始记录,它自身所具有的真实、可靠等属性使其在传承记忆的文献记录中具有无可替代的优势。我国档案学者冯惠玲对于档案作为集体记忆建构媒介的价值进行了深刻阐述,她指出“在这个建构过程中,档案资源是一种经过沉淀的最基本、最稳定、最深层的要素,它给关注者提供事实、关联、依据和理性,通过这种方式浸入每一个时代的集体记忆当中”[11]。 实际上,档案自诞生之时起,就被打上了记忆的烙印。法国历史学家雅克·勒高夫在《历史与记忆》中提到,在中世纪,“记忆”被当做档案的代名词,人们用一份“记忆”来指代一份行政公文[12]。而作为系统收集并集中保存档案的场所,档案馆更是被有意识地作为集体记忆的存储器。档案馆因而被赋予“记忆的宫殿”、“记忆的宝库”等美誉。档案界对档案是构建集体记忆的重要媒介已形成了基本共识。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采纳通过的《档案共同宣言》向全世界宣告了档案在集体记忆保存、维护、唤醒中的独特、专有、不可替代的地位,也为档案工作者提供了“记忆”这个颇具说服力的概念阐述其职业使命,扩大其社会影响。 2.2 档案承载的是有选择的集体记忆 对于个人而言,有记忆,就有遗忘。对于集体而言,同样如此。集体记忆是选择性的记忆。作为集体记忆的重要媒介,哪些记录能作为档案留下来,哪些档案能够进入档案馆永久保存,甚至为谁建立档案馆,同样也是选择的结果。因而,档案呈现的是有选择的集体记忆。 美国密歇根大学本特利历史图书馆馆长弗朗·西斯布劳因把档案背后存在的选择明确地归于权力,他指出“档案涉及权力,这就意味着权力借助档案而留存于史”[13]。雅克·勒高夫在《历史与记忆》一书中记述了档案馆曾被君主当作记忆制度来铭记自己的功绩[12]。而法国大革命之后建立起来的国家档案馆则是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产物。“史书出,史料亡”,这种描述我国历朝历代修史方式的表述也从反面印证了这种说法。新王朝统治者所畏惧而要销毁的史料,往往正是典章制度、表册诰命等档案。它们凝固的是前朝的记忆,正是忌惮于此,新统治者才会在根据自己的利益需要对过往的历史做出“合法性”说明的同时,将这些承载真实历史记忆的档案史料彻底销毁。 即使在既有档案体制下,记录什么,保存什么,销毁什么,同样也是选择的结果。在档案领域,这个选择主要由档案鉴定这项专业工作来完成。鉴定工作是档案人员手中的尚方宝剑,决定档案的生死存亡。也正是因为如此,档案工作者被批判为“肯定现行的政治结构和权力关系的共谋”[13]。 3 构建新媒体时代的档案记忆 新媒体所代表的传播技术和传播方式正显著地改变着世界,它对当下的影响将沉淀为明天的记忆,汇入人类历史长河的经验累积。作为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原始记录,档案亦应凝结社会在新媒体时代的发展和变迁,并将其作为档案记忆跨时空传承。 3.1 档案工作者的权力与职责 一直以来,档案工作者习惯将自己定位为“记忆的守护者”,这个隐喻暗示了档案工作者和记忆的形成与构建无关。正如加拿大档案学者特里·库克所言,“固有的观念认为,档案工作者记录过去而非未来,处理历史事件而非现实或未来事件,他们不构建历史和记忆,因为这是史学工作者和其他档案用户的角色”[16]。然而,若档案工作者身处受新媒体技术影响发生深刻变革的当下,却对发生在新媒体平台上的重大事件无动于衷,对活跃于新媒体上的普通大众在推动社会进步中的价值与意义无动于衷,目睹这些承载未来集体记忆的新媒体记录散乱、失存或被随意删除而无动于衷,这又何尝不是在“记录”未来、构建记忆?只是,所记录的是空白的未来,构建的是记忆的黑洞。 当档案工作者从事收集、鉴定、保存档案的专业实践时,正是在决定着“什么被记忆什么被忘却,谁能够声名远播,谁最后无声无迹”[14]。档案工作者就像“一只看不见的手在操控社会记忆”[15],手中的这份权力既可以无意地造成历史的偏见、缺漏与空白,也可以有意地去记录更广阔的人类经验,“既记录国家也记录公民,既记录中心也记录边缘,既记录主流声音也记录异见声音,既记录国家政策也记录文化表达”[16]。 新媒体时代,档案工作者应以流淌在血脉中的历史责任感为导引,规约手中的权力,让无意识的偏颇成为权力自觉,勇于担当新媒体档案记忆塑造者的职责,通过档案收集、鉴定、整理、保存等一系列专业化实践,为未来留存尽可能完整的集体记忆素材。 3.2 构建新媒体档案记忆平台 留存并维护新媒体时代的档案记忆,需要探索可行的方法与渠道。构建一个中国新媒体档案记忆平台,是一个可能的解决途径。冯惠玲曾提出建设基于互联网的以档案数字资源为主体的“中国记忆”数字资源库的构想[11],而新媒体档案记忆平台可以作为该资源库的一个组成部分,反映新媒体环境下多彩的社会生活。 档案工作者可以在该平台上开展集体记忆素材的鉴选、提炼、汇集和保存。具体来讲,档案工作者可以网络重大历史事件为依托,建立一套新媒体档案识别及鉴定方法,挑选出能够尽可能全面反映公众在社会公共事务中价值与意义的各种新媒体记录,将其以专题、年度、事件、媒介类型等形式组织起来,并建立关联。该平台的建设需要以档案工作者为主体的信息资源管理专家、计算机技术专家、新媒体平台运营商等多方协作、共同完成,实现新媒体档案资源的长期保存、开放利用。 档案是建构集体记忆的重要媒介,但档案并不等同于集体记忆。如果档案被尘封,它就始终处于德国埃及学者扬·阿斯曼所说的文化记忆潜在模式,只有被使用者在新的社会背景和历史背景中采用,并被赋予新的含义的时候,它才出现在文化记忆的真实模式之中[17]。因而,新媒体档案记忆平台发挥其价值的唯一方式即是向社会开放,由公众去诠释、解读,建构集体记忆,激活集体记忆,并将其传承下去。 4 结语 新媒体技术深刻改变了中国社会发展现实,为大众提供了参与形成、书写集体记忆的机会,也提供了为未来留存更完整集体记忆的期待。然而,新媒体技术也为集体记忆带来了失存、遗忘、消解、失真、碎片化等风险。档案在集体记忆的建构、维护、存续中发挥独特的作用,档案工作者有责任通过自己的专业实践为未来馈赠一个由新媒体刻画的当下社会图景的记忆,并通过档案识别、鉴定、组织、保存等专业技能降低集体记忆面临的风险。新媒体档案记忆平台即是一个可能的解决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