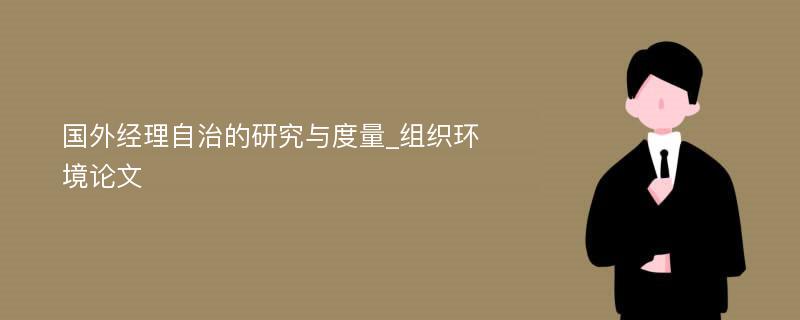
国外经理自主权研究及测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自主权论文,测量论文,国外论文,经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现代企业演变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所有权日益分散,经理职业化也越来越普遍。当控股股东逐步将公司日常管理工作交给职业经理负责后,公司治理的焦点就转向如何监督和约束经理。面对实际控制权越来越大的经理,公司利益相关者必须权衡经理应该拥有多大的自主权,以便既能促使经理有足够的自主性激励投入工作,又不至于产生过高的代理成本,这就产生了如何合理安排经理自主权的问题。
经理自主权(managerial discretion),有的学者直译为“经理自由裁量权”。在20世纪50~60年代,经理自主权现象已经颇受学者们的关注,例如马奇和西蒙(March和Simon,1958)、威廉姆森(Williamson,1963、1964)、汤普森(Thompson,1967)与莫利斯(Morris,1967)等的研究,主要反映经理追求自身利益的行为。70~80年代现代企业理论兴起以后,经理自主权常常被用来解释机会主义、代理成本或败德行为的成因。直到80年代末格罗斯曼、哈特和穆尔提出企业的所有权—控制权经济学分析模型后,学者们才全面认识到经理自主权对公司价值的成本效应和收益效应。现将主要的理论研究成果及观点概述如下。
一、经理自主权研究的三个阶段
1.现代厂商理论中的经理行为。自伯利和米恩斯(1932)揭示了现代公司中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的事实后,经理行为就成为企业理论研究的焦点。在伯利和米恩斯看来,经理及经理阶层是“不掌握任何有意义股权情况下的‘自我永存的团体’”,伯纳姆(1941)和钱德勒(1987)称之为经理主义或者经理革命。经理主义理论的贡献在于发现了现代企业中经理获得自主权的必要条件——所有权与控制权的分离。此后的许多文献主要集中在对经理行为方式的研究,并相继提出三种假说,即鲍莫尔(Baurmol,1959)的销售最大化(sales maximization)假说,马利尔斯(Marils,1964)的成长最大化(maximizing growth)假说,以及威廉姆森(1963和1967)的经理效用(managerial utility)最大化假说。在这三种假说中,为股东提供满意利润是约束经理自主行为的必要条件。作为结果,经理自主行为能够获得各种效用,包括更好的声誉、更多的报酬、安全的职位、合意的在职消费,并增强经理权力和影响力。后来,Jensen和Meckling(1976)将这些通过自主行为获得的效用统称为经理代理成本。对于经理而言,它们是自主权收益(Burkart和Gromb,1997)。这一阶段理论研究的贡献在于发现了经理自主行为有悖于股东利润最大化目标的现象,提出了经理与股东利益不一致的问题,为此后兴起的代理成本理论作好了铺垫。其缺陷在于过分关注经理自主行为的负面效应,而忽视了经理自主性对增加股东财富的积极作用。
2.战略管理理论中的经理自主权。汉姆伯瑞克和芬克斯坦(Hambrick和Finkelstein,1987)从组织战略管理的角度研究了经理自主权的内涵及其影响因素,他们将经理自主权定义为经理的行为空间(latitude of actions),并强调这一空间是在经理与利益集团之间就其行为的合理性进行动态博弈的复合过程中形成的。作为结果,经理自主权反映了在既定权力分享状态下,经理对赖以生存的环境的控制程度。在这个过程中,经理的行为受任务环境、内部组织结构及其个人特性三方面因素的影响,经理自主权是这种复杂过程的综合结果。
该研究的贡献在于明确提出经理自主权概念,并解释了战略管理理论与组织生态学理论关于组织是否有能力支配自身命运的观点分歧。(注:组织生态学家认为,由于组织惯性的原因,企业行为实际上是被动的环境选择的结果(Hannan和Freeman,1977),不是主动适应环境变革的结果;而早期的战略管理学者则认为,组织内部充满有目的的自主行为(purposive actions),企业有足够的空间实现自我塑造和发展(Andrews,1971;Child,1972)。)汉姆伯瑞克和芬克斯坦(1987)认为,企业行为的本质是经理行为,经理对企业行为及其产出效果的影响因环境变化而异,这些变化包括不同的任务环境,不同的组织结构,或者不同的经理个人特性等因素。在经理自主权较大的公司里,经理对公司绩效的影响就比较显著;而在经理自主权较小的公司里,经理对公司绩效的影响则比较微弱。典型的例子是公用事业公司与计算机行业公司的经理自主权差异较大。
从现有文献来看,该学派的研究已经验证了来自行业层次、企业层次和个体层次的许多理论推断,例如解释了影响经理自主权的行业因素(Hambrick和Abrahamson,1995),经理自主权对经理报酬的影响(Mueller和Yun,1997;Finkelstain和Boyd,1998)等。然而,由于这方面的研究根植于战略管理理论,比较关注组织外部任务环境因素的影响作用,而忽视了从组织的内部结构与治理角度来分析经理自主权,因此该研究对经理自主权的认识仍处于抽象的概念阶段,尽管指出了经理自主权对公司绩效影响的强弱关系,但却没有回答这种关系是正向关系还是负向关系;仅仅指出经理自主权是一个有效的经理行为空间,而没有挖掘经理自主权的实质内涵。
3.现代企业理论中的经理自主权。随着交易费用经济学、委托—代理理论、产权理论的兴起,现代企业理论对经理行为的研究发生了质的飞跃。由于信息不对称、契约不完全及环境不确定性,经理行为不可避免地具有机会主义的特征,并由此产生代理成本,其原因主要在于经理对企业获得的外部股权资本或者债务融资,具有资源配置方面的自由裁量权,可以在项目投资机会,以及具体用途方面作出选择(Jensen和Meckling,1976)。在詹森看来,自由现金流(free cash flow)是经理自主权引致代理成本的必要条件。阿洪和梯若尔(Aghion和Tirole,1997)在研究了组织内部的权力配置问题以后指出,提高代理人的实际控制权有助于激励其投入工作的主动性,但结果必然是以委托人的控制权损失为代价。委托人的监督程度越高,经理努力以及经理与委托人的利益一致性系数会越小;而若委托人的干预变小,经理的自主性将提高,经理的私人收益则会增加,在此基础上,布卡特和格罗姆(Burkart和Gromb,1997)借助格罗斯曼与哈特(Grossman和 Hart,1986)以及哈特和穆尔(Hart和Moore,1990)提出的企业所有权—控制权分析模型进行研究后发现,由于分散所有权而导致的经理自主权对公司价值既有成本效应,也有收益效应,而且即使严密的大股东控制在事后看是有效的,但在事前会对经理构成一种压迫,致使其自主性降低,减少对企业的非契约性投资。至此,企业理论对经理自主权的认识日臻完善。尽管如此,但现有文献在分析经理自主权对公司价值的成本效应和收益效应时,使用经理努力和大股东监督两个变量的复合作用来间接表示,其不足之处在于没有将经理自主权作为一个独立的变量进行直接分析,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对该理论推断的经验检验。
二、经理自主权的影响因素
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是经理自主权产生的前提条件。在现代厂商理论的三个假说模型中,约束经理行为的基本条件是为股东提供满意的利润。这些都不足以系统反映经理自主权的影响因素。检索已有文献表明,比较系统地论述经理自主权影响因素的理论有两种:一是以汉姆伯瑞克和芬克斯坦(1987)为代表的战略管理理论。该理论系统地提出了影响经理自主权的因素,包括任务环境因素、内部组织因素和经理个性特征因素。其中,任务环境因素包括产品差异性、市场成长性、产业结构、产品需求稳定性、各种制度和规章约束,以及其他外部强制力量;内部组织因素包括组织的惯性力量(如组织规模、寿命、文化和资本密集度)、资源可利用程度及其他内部强制力量等;经理个性特征包括认知能力、对组织的承诺程度、组织的内部控制水平、权力基础以及其他政治人际关系等。这三方面实际上涵盖了企业的外部生存环境、内部组织结构和经理本人三个层次。二是公司治理理论。公司治理理论认为,制约经理行为的约束机制包括大股东监督、董事会、代理权竞争、公司接管市场、经理人才市场和产品市场等(哈特,1995),这些因素最终可以归结为公司外部治理环境和内部治理结构两个方面。
由于公司治理的内部监控机制与高层管理者的战略策划过程紧密结合(田志龙,1999),因此经理行为实际受公司治理系统和公司管理系统的综合影响。经理是联系公司管理系统与公司治理系统的核心,应将公司治理与公司管理综合起来研究(巴纳盖,1995),因此经理的行为空间必然跨越公司管理系统和公司治理系统而存在。由此,李有根(2002)提出,从公司治理与公司管理系统化的角度看,影响经理自主权的因素包括:外部环境因素、治理结构因素、管理结构因素和经理特性因素。治理结构是经理参与决策的活动空间,包括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以及旧体制下的老三会等权力机构;管理结构是经理实施决策的组织工具,包括组织资源、组织规模、组织文化和管理层级构造等;经理特性反映来自经理个体方面的影响其决策行为的各种非正式因素,特别是人际关系敏感性、领导风格、忍耐性、认知能力、权威影响力,以及年龄等。外部环境因素包括政府、公众、顾客、供应商,以及产品市场、资本市场、法律制度等,是经理决策的客观约束或依据。
三、经理自主权的测量方法与指标
概览现有研究文献,测量经理自主权的方法主要有四类:一是直接资料考证法,主要途径有:(1)考察经理在经营活动中的审批权限;(2)考察董事会对经理主动提议事项的通过率;(3)查询经理工作日记,通过分析经理在日常经营决策中所开展的沟通和联系工作,来确认经理在特定决策中面临的自主空间有多大。例如,登勃和纽勃尔(1996)直接考察了数百名董事日常工作记录,以研究分析各类董事的权力与职能。二是访谈/问卷法,被调查对象可以是经理本人,也可以是董事会成员、监事会成员、主要股东代表,以及经理的直接下属等,通过相关人员的评价来判断经理自主权大小。比较忌讳的是直接要求被访问者对经理自主权给出判断,因为这样可能会导致无法克服的内生误差。例如,哈里森·郑等(2001)借助我国企业家调查系统考察了我国乡镇企业经理的经营自主权情况。三是管理实验模拟法,例如Carpenter和 Golden(1997)曾模拟一家食品企业的战略管理决策过程,研究经理自我感知的自主权差异及其原因。情景模拟实验的优点是可以控制决策背景,但外部有效性可能受到怀疑,且实验控制难度较大。四是间接指标测量法。由于经理人员的角色比较复杂,经理行为及其自主空间难以准确观察,因此研究人员更倾向于采用间接指标来测量经理自主权。
现有文献中测量经理自主权的间接指标包括以下四类:
1.职位结构方面的自主权指标。经理因在董事会中兼任职务而获得的权力统称为结构性自主权(Malekzadeh、McWilliams和Sen,1998),如经理是否兼任董事长或者副董事长。此外,董事会中的非执行董事比例也会影响经理自主权(Adams和Hossain,1998)。
2.所有权方面的自主权指标。首先,大股东股权集中度。股权越集中,则控股股东越有能力行使经理选择权,对经理自主权构成强烈约束(Aghion和Tirole,1997;Burkart和Gromb,1997)。其次,经理持股比例。为了激励经理努力,或者防御敌意收购,经理的持股水平会有所提高(Mock等,1988),但同时也会提高经理持股的自主权效应(李有根,2002)。可见,所有权结构安排是权衡经理自主权的有力工具。
3.资源运作方面的自主权指标。首先,可自由支配利润。威廉姆森(1963)指出,可自由支配利润是经理自主权的源泉,是满足经理“消费偏好”的“基金”。计算方法为实际利润减去股东的最低满意利润。其次,自由现金流的规模及其变动。詹森(1986)认为,自由现金流是导致经理代理成本的主要原因之一;而斯图尔茨(1990)也认为,自由现金流的变动反映了经理或者投资不足,或者过度投资。由此,斯科迪斯和普瑞彻特(Scordis和Pritchett,1998)使用自由现金流的规模(FCF)及其变动(ADMFCF)来度量互助保险基金经理的自主权成本。结果表明,为了防止客户因防范经理的自主权成本而退出保险,基金经理会向保险客户支付尽可能多的保险红利。再者,全部资本的加权投资回报率。穆勒和郧(Mueller和Yun,1997)在研究经理自主权对经理报酬的影响时,使用全部资本的加权投资回报率(C)来间接测量经理自主权。假定经理行为是追求成长最大化,C的计算方法为单项投资收益率按投资额加权平均后的收益率。穆勒和郧(1997)认为,加权投资回报率大于1,则表明经理没有过度投资的自由空间,因此自主权D为0;反之,则不失一般性,令经理自主权D等于(1—C)。穆勒和郧(1997)的研究再次揭示了美国大公司经营效益低下而经理人员获取高报酬的矛盾现象。最后,即时可利用资源。芬克斯坦和汉姆伯瑞克(1990)在研究高管人员任期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时,使用年营运资金占销售收入比来度量经理自主权。
4.任务环境方面的自主权指标。汉姆伯瑞克和芬克斯坦(1987)提出了测量不同行业的经理自主权的6个指标,芬克斯坦和鲍德(1998)进一步使用市场成长性、研发投入度、广告投入度、资本密集度、产品市场占有率和管制程度等6个指标来测量经理自主权与经理报酬之间的关系。Adams和Hossain(1998)在研究新西兰保险公司经理自主权与自愿披露经营信息行为的关系时,也使用由8个变量构成的一组指标来间接反映经理自主权,包括企业类型、资产构成、产品集中度、再保险率、经营本地化、非执行董事比例、公司规模和销售网络等。
四、对我国国企改革实践的启示
经理自主权是所有权与控制权相分离的产物,如果所有者缺位,且经理在企业中没有多大的利益,经理自主权就会产生许多代理问题,如利润转移和资产侵蚀。这些代理问题就是通常所说的“内部人控制”问题(张维迎,1997)。与之相反,如果大股东过分干预经理的正常经营行为,那么就难以保证企业行为为全体股东利益负责,如恶意关联交易和大股东掏空上市公司等,这些是通常所说的“一股独大”的委托人问题。适当的经理自主权安排是并行解决委托人问题与代理人问题的突破口。
随着我国国企改革的深入,“下放的经营决策权使经理自然成为部分控制权的拥有者”(张维迎,1999)。掌握实际控制权意味着,公司内部的经营决策程序由经理负责“提议”和“贯彻”,董事会负责“认可”和“监督”,变成了股东会或董事会只是批准经理提议的“橡皮图章”,而经理则成为事实上操纵公司事务的核心机关。现有《公司法》对股东、董事会和经理三方之间的权力划分“部分关系是非常清楚的,但大部分是很模糊的”,“在控制权公共所有部分,谁进一步,谁退一步主要靠彼此的默契来解决”(张维迎,1999)。面对这种变化,公司股东、董事会以及其他利益相关者必须重新认识经理行为的实际空间,建立有效机制来合理安排经理自主权。
完善公司治理结构,适当安排经理自主权,寻找公司运作的最佳绩效,要实现这个逻辑的良性循环,关键是正确认识经理自主权的成本效应和收益效应。由于企业是一个不完全契约集合,经理投入企业的人力资本多少取决于其自主权水平,当经理自主权受到抑制时,其对企业的非契约投资必然降低,其人力资本贡献也必然减损。另一方面,严密监控经理自主权的代理成本也是确保实现公司价值最大化的重要因素,尽管从事前来看,可能会降低经理对公司经营的自发性非契约投资,但在事后是有效的,如何权衡这两种效应,需要更多的实证研究去寻找有助于解决问题的正确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