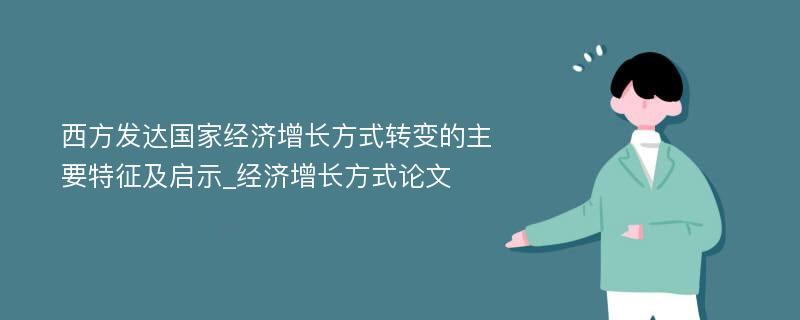
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主要特征及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发达国家论文,经济增长方式论文,主要特征论文,启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建立起现代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基本完成由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向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这就是说,中国现时在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上准备实现的东西,正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实现或基本实现的东西。因此,深入研究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对我们有着十分现实、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的主要特征
1.经济增长速度经历了一个由快转慢的过程。
仅仅从产业革命以来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实践看,追求经济增长速度一直是人们关注的中心。恩格斯曾指出,产业革命以后,英国的生产力出现了“前所未闻的速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08页)。率先完成工业化的英国成为“世界工厂”。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工业高速发展,使其经济实力大为增强,美国超过英国居世界第一。战后,从1948年至1973年,日本工业增长速度为世界之最,年均增长率高达15%。其次是德国,年增长率超过8%。于是,美国经济实力地位相对衰落,美、日、德成为西方国家的三大中心。然而,70年代特别是8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经济增长速度普遍不高,不要说两位数,就是4%以上的速度都不多见了。
2.从货币投放看,持续实行紧缩政策。
面对30年代大危机,凯恩斯主义者采用了扩大货币投放量,扩大政府开支,甚至“赤字财政”的办法。80年代以后,西方各国普遍控制货币供应量增幅。
1950-1980年,美、英的货币紧缩持续期没有超过两年的;而1980年以后,紧缩期有时持续5-9年以上。
3.产业结构、产品成本构成呈软化趋势。
直到本世纪中叶,即使是产业结构最先进的国家,其国内生产总值中“硬产业”(农矿、工业、建筑业)的比重都超过“软产业”(服务、信息等业)。然而,最迟到1970年,美、英、意、加等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中软产业比重第一次超过了硬产业。1983年,最后一个西方大国——法国也实现了这种超越。发达国家产业结构的软化成为一种重要的社会经济现象。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产品的软件成本比重上升极为迅速。以电子产品为例,60年代,硬件比重高达80%,软件仅20%。80年代末,这种情况便完全颠倒过来,硬件比重下降至20%,软件上升到80%。产品成本构成软化成为又一种重要的社会经济现象。
4.从劳动力构成看,脑力劳动者所占比重不断上升。
西方国家国民经济各部门就业人口中,体力劳动者的比重日趋下降,脑力劳动者的比重日益上升。以美国为例,1930-1968年期间,蓝领职工增加60%,工程技术人员却增加了450%,科研人员增加了900%。终于,1977年,脑力劳动者所占比例达50.1%。70-80年代,西方国家脑力劳动者在数量上超过体力劳动者,劳动力构成软化了。
5.从生产、制造特点看,自动化技术水平不断提高。
60年代以后,由于控制技术的发展,电子计算机的崛起,工业机器人的问世,以及柔性制造系统的诞生,西方各国自动化技术发展进入集成化阶段。这样,使没有人直接参与的生产控制自动化和经营管理自动化提升到更新更高的水平。
90年代初,主要在西方国家,已有1500条以计算机为中心的自动完成加工、装卸、运输、管理的柔性制造系统。生产、制造柔性化方兴未艾。由此,产品制造周期大为缩短,机床利用率大为提高(可达80%),库存和在制品数量大为减少,劳动力、机床数量、占地面积、生产成本进一步减少50%左右。
6.从资源耗费看,逐渐建立起资源节约型的国民经济体系。
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生产、流通和消费领域,在杜绝资源浪费,降低资源消耗,提高资源利用率、生产率和单位资源人口承载力诸方面,已经和正在取得巨大成功。它们正在建立一种资源节约型国民经济体系。这个体系包括以节地、节水为中心的农业生产体系,以节能、节材为中心的工业生产体系,以节省运力为中心的综合运输体系和适度消费、勤俭节约为特征的生活服务体系。
7.从工人劳动时间看,当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工人劳动时间普遍趋于缩短。例如,美国实行5天40小时工作周,有些企业每周工作35小时。欧洲经济共同体平均每周工作36.9小时,其中,荷兰仅31.5小时。
以上,我们从七个方面描述了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的主要特点。由此,我认为,如果我们摈除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不把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与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看成绝对对立的东西的话,那么,似乎可以把当代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概括为一种速度和投入适度,产业、产品、劳动力结构和生产制造方式柔软,资源(物质资源、劳动资源)节约的经济增长方式。
二、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的启示
启示之一: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
经济增长方式转型表现在许多方面,本文显然远未能全面描绘。可是,有一点能够肯定:这一切方面决不是、也不能孤立存在。因此,把握经济增长方式及其转型,必须坚决拒绝两个层次的形而上学。
其一,必须反对孤立地、片面地、静止地看待经济增长方式及其转型的个别方面,而要把它看成为一个有机整体,其各个方面相互联系,不可分割。例如,速度和货币投入问题。集约型经济增长的确以质量和效益为中心而不盲目追求高速度,集约型经济增长的确着重生产要素质的提高而不刻意追求生产要素量的扩张。然而,能否认为速度高、投入多就一定是粗放型,速度低、投入少就一定是集约型,因而,只要把速度降下来,或只要把投入降下来,就实现了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呢?显然不能这么简单。现实生活中,高速度高效益、低投入高产出很难追求,而高速度低效益、高投入低产出却屡见不鲜。于是,适度速度的高效益、适度投入的高产出成为人们经常的和可以实现的最佳选择,而低效益的高速度、低产出的高投入则成为众矢之的。可见,我们只是从这些意义上反对高速度、高投入的。我们只是说,1千吨木材在芬兰产出纸制品164吨,在前苏联仅产出27.3吨。因此,前苏联的这种速度和这种投入与芬兰的那种速度和那种投入都不是抽象的速度和投入,而是具体的速度和投入,不可同日而语。
50-60年代高速增长后,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增长速度普遍不高,人们说,那是因为西方陷入了“滞胀”。然而,80年代中期走出“滞胀”以后,4%以上的速度都极为罕见。原因恐怕不宜简单化。80年代中叶以来,西方各国政府为经济转型而调整了各自的经济政策目标,即从凯恩斯主义的充分就业的高速增长转为货币学派、供给学派追求的低通货膨胀下的适度增长。这种目标的转变,说明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增长速度不高具有某种主动性质和自觉性质,反映了某种必然性。实践证明,当代世界各国,凡实行粗放型增长方式的几乎都追求高速度,凡实行集约型增长方式的几乎都不追求高速度。仍以前述纸制品生产为例,既然西方国家的生产率高达前苏联5-6倍,假定它们需求相近,苏联不可能不追求5-6倍于西方的速度,西方国家却只需苏联1/5-1/6的速度。
由此可见,我们有些同志将我国经济增长速度与西方作简单对比,是不科学的。我国数量型增长的高速度与西方质量型上升的低速度之间缺乏可比性。以此证明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也不妥当。
其二,必须反对孤立地、片面地、静止地看待经济增长方式及其转型,而要把它与它的外部环境统一起来。任何一种经济增长方式都是其特定的自然和人文环境的产物。这种环境是多方面的,其间,一国的资源丰度、科技水平和经济体制对增长方式的影响就十分重要。前苏联生产的耐用消费品是出名的“傻大粗”,这自然与它矿产、电力等资源十分丰富,特别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关系密切。为什么现代集约型增长首先出现在西方?为什么中国当前才把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提到战略高度?显然,市场经济的发展呼唤集约型经济增长。
总之,经济增长方式本身是一个系统,是一个由若干相互作用、相互依赖的部分按一定秩序组成的具有特定功能的有机整体,而经济增长方式与其外部环境又构成一个更加复杂得多的大系统。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是一个系统工程,宜从多方面入手,整体推进。
启示之二:教育、科技的大发展既是集约型经济增长的基础,又是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化的决定因素。
只有在教育、科技大发展的前提下,劳动者素质(主要是智力素质)才能大提高。脑力劳动者地位的上升,产品成本软化、产业结构软化、制作柔性化才有可能。产品成本软化、产品结构软化、制作柔性化,才能在减少资源耗费、劳动工时及投入、速度适当的条件下大幅度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
邓小平同志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我理解,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后的生产力是集约型生产力。这种生产力显然不同于以往那种体力劳动者依靠简陋的生产工具作用于自然物或经简单加工的原料而产生的粗放型生产力。
由此,我们更理解党中央“科教兴国”战略的及时和正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