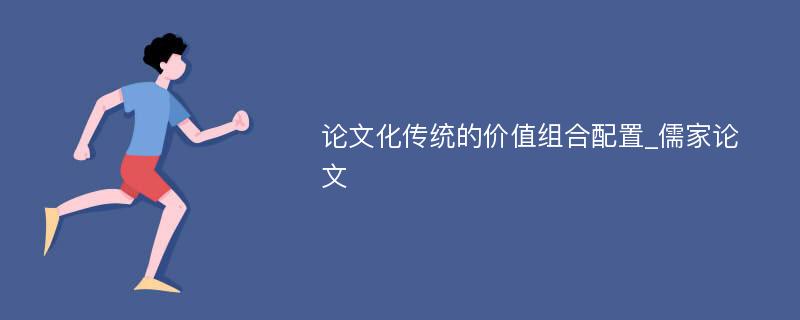
文化传统的价值组合配置刍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组合论文,传统论文,价值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文对文化的价值多样性进行多元的理解,集中阐述和讨论“文化的价值组合配置”(cultural configurations of values)概念。主要包括以下几个要点:(1)在世界的各种文化中,人类的价值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但其基本价值是相似的,甚至相同的。(2)人类的各种基本价值之间不但有互相促进的关系,也有相互矛盾、相互竞争、相互冲突的关系。(3)一种文化类型提供对相互冲突的价值的一种处理方式。不同的文化形成其各自的价值组合与配置。这种价值的配置与其社会环境相适应,是其文化的核心部分。文化差异性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尽管所有文化共有这些基本价值,但是他们会给予这些价值不同的权重,形成不同的价值配置形式。(4)有时在同一个社会里,会存在若干“亚文化”,会有不同的价值配置。随着时间的推移,文化和社会都会有改变。虽然它们在价值组合配置普世化上可能永远无法达成一致,但是它们之间的共同价值为和平共处提供了基础。
这种观点可以支持一种温和的价值普世论,也可以支持一种温和的价值相对论。一方面,不同的社会共有一些相似的、甚至同样的价值;另一方面,不同的实践形式又有各自存在的合理性。这种现象可以从相似价值的不同配置上得到解释。在价值方面,人类既是相似的又是不同的。而方面的不同,又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表现出来。一方面,我们之间有足够的共性使得可以彼此互相理解、协作;另一方面文化差异的存在有其价值配置上的合理根据。理解文化的这一重要维度,对于处理当今世界中的文化差异和各文化间的和平共处是非常关键的。
人类的基本价值
价值的本质以及其本体论状态是哲学争论的一个主题。有人认为价值是主观的,也有人则认为它是客观的。有些价值被认为是内在的价值,其他被认为是工具性的价值。有些价值是道德的,而其他的则无关道德,例如经济价值和美学价值。本文对价值的理解是基于一般层次的理解,并不涉及这些争论。尽管其关注点是道德价值,但是我们在这里提出看法也适用于非道德的价值。
价值代表人们在生活中的追求,并引导和刺激人们的追求。价值并不是人们追求中所要得到的特定东西,而是人们的追求之动因。我们用价值来解释人们追求事物的行为,例如,有人做慈善事业,是因为他认为慷慨是好的价值,而贫穷和苦难则不是。当我们赞扬人们的勇敢行为时,我们用“勇敢”这一价值去对有关行为进行评价,并且鼓励与之类似的行为。价值以各种方式相互连接,为实践理性网络之链接。例如,仁慈,同情和慷慨,是相互关联的概念。我们通常将体现在一个人身上的正面价值称为“美德”,表现了一个价值或多个价值的某一特性。
本文的第一个主张是,一般地说,人类的基本价值在世界上的主要文化传统中是相似的。跨文化价值研究的难点之一是不同文化中的价值术语及其使用是不严格的。在特定文化中形成的价值不具有“自然种类”那样的同一性。为了避免不必要的争端,我们可以说跨文化的价值是相似的,而不说它们是相同的。(这一主张也同样适用于亚文化群,不过本文并不会对文化群与亚文化群作出区分)由密歇根大学的罗纳德·F.英格哈特组织的“世界价值调查研究”(网址链接:http://www.worldvaluessurvey.org)可以为以上的观点提供根据。他们的研究表明,在不同的国度和文化区域可以找到同样的价值。其实,这并不意外。事实上,人类的价值适应于人类需求,而且总体说来人类的基本需求在不同的文化间是相似的,这些需求的特殊形式或许是有文化特定性的。很多中国人喜欢喝茶,然而很多美国人喝咖啡;贫困山村中的人或许会将白薯作为食物的主要来源,而在欧洲比较富裕的社会的人们惯于吃小麦或牛肉;为了心理需求,有人找牧师,有人看精神科医生。然而,总体来说,基本需求仍然是相同的,人类基本价值是与这些需求相对应的。
人类基本价值表现人类生活中的基本追求。例如“知识”,“仁慈”,“健康”,“财富”,“勇敢”,“友谊”,“尊重”,“节制”,“力量”,“自由”,等等。基本价值表现在一般性的概念之中。尽管它们可以被翻译成为文化中的特定术语,并且它们没有文化特定性。在某种程度上,基本价值可以与迈克尔·沃尔泽的“薄的”道德理想相类比。他认为这些“薄的”道德理想是普遍的(Walzer,1994)。另外,这一观点与休谟的观点相近。休谟在《道德原则研究》(第Ⅱ部分,第Ⅱ章节)一书中表明,美德之所以得到人们的认可是因为它们有对人有利的倾向,即促进人类的利益和赐福人类社会。
人类拥有共同的基本价值的主张也可以从进化论的角度加以论证。进化论观点认为,人类是进化至今的一种生物性存在。作为一生物物种,生存是我们最高目的,并且我们基本的活动都可直接或间接地在这唯一最终的目的中得以解释。根据这一观点,人类基本的生理和心理需求都是在这同一进化过程中形成的,所以这些需求在不同的社会中也是相同或相似的。如果不能满足这些需求,人类将无法生存。生存的需要是人类价值的最终来源。比如,人们珍视“勇敢”这一价值,是因为它有助于保卫自己和家族。人们取悦于花朵的美丽,一个合理的解释是因为花朵象征着茂盛的植物,而茂盛的植物又意味着多产的动物,这些都是我们祖先的食物来源。盛开的野花自身是可食用的,或者表明其周围有其他可食用的植物。从这个意义上看,美丽的鲜花对人类的生存(曾经)有着重要的作用。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各个文化中的每个个人或团体都持有所有的价值。由于种种原因,个人会有价值的盲点。有些人在社会中是“反常”的,比如,一个连环杀手可能不会珍视生命,极端的孤独者或许不会珍视友谊,某些特殊思想流派中的人或许不会珍视财富。然而作为一个整体,一个社会在基本价值上是不能有盲点的。否则,它就很难生存下去。不同文化中的社会实践也是有变化的,其中有些差异可以通过不同的价值诉求来解释。再者,相同的价值或许会有多种表现方式。在某一个社会中,做一个好的社会成员意味着要定期参加教会的活动,然而在另一个社会中却不一定是这样。在一种文化里,父母会将生病的孩子送到医师那里,然而在另一种文化里,父母则是将他们送给宗教仪式中的巫医。尽管他们对此的追求方式是不同的,这两类社会中的父母都共同珍视他们孩子的健康。西班牙的斗牛深得某些人的喜爱,但是有时又很残酷。有人可能会问,人们怎么会喜欢虐待动物?一个合理的解释是,西班牙人并不是喜欢虐待动物,他们珍视勇敢、娱乐和自己的文化传统。在斗牛中,他们看到了这些价值并和世界上其他人们共享这些价值,而不是虐待动物。他们或许不会否认斗牛给动物带来痛苦,但是考虑到这一礼仪运动实践中所实现的积极价值,他们认为这一痛苦代价是值得的。所以,不同文化间不同的道德实践并不能证明文化不共享基本价值。
价值之间的竞争和冲突
本文的第二个主张是,基本价值之间会存在冲突,至少会相互竞争。也就是柏林在《扭曲的人性:人类思想史章节》中所说的,“价值可以碰撞”(Berlin,1991,第12页)。这是因为价值有其向量的性质。如果我们想象一个“价值的空间”,各种价值相对于彼此而言都有各自的力量与方向。价值的这一向量特性促使人以特定的方式行动。因为有些价值在同一维度上,所以它们或许会相互竞争。每个价值指向一个方向,以促动人的行动。当一个人向一个方向行动时,他就不能以相同的力度向另一个方向行动。例如,一个人自身的自由与对其他人的忠诚或许会冲突。“自由”和“忠诚”在所有社会中都是珍贵的,尽管其实践的方式与程度有很大不同。有些人或许不认为个体的自由与忠诚间会存在紧张或冲突,认为一个人可以自由选择对某人忠诚。但是,只要忠诚表现其约束力,它与自由之间就会有冲突。假使张三服务于政治领袖李四很长时间,在一段儿成功职业生涯之后,李四事业开始下滑,张三考虑开始他自己独立的政治生涯。由于李四对张三一直很好,而且很明显也还需要张三的帮助,所以张三会受到两个方向的压力:“忠诚”于李四和自身的“自由”。这两者很难相容。另一个例子是,同一个人不可能同时过一种充满激动人心的、冒险的而同时又安全、安宁的生活。这种在个人身上的冲突也存在于社会中。根据柏林所说,“狼的完全自由对羔羊来说是致命的;强者的完全自由、天赋,与弱者和少天赋的人的有尊严的存在权是不相兼容的。……平等或许需要对那些希望主宰的人的自由进行限制。”(如上)有些情况下,价值的冲突是由于它们在实现的过程中会互相争夺时间和资源。同一个人就很难同时完全发展他的学识潜力和体育运动潜力,很难同时既是合格、模范的母亲,又能如特蕾莎修女一样,到处去帮助全世界的穷人。这也就是柏林在《自由四论》中所说的:“在日常经验中我们遇到的世界里,面临的选择是同样终极和同样绝对的,一些追求的实现必然涉及牺牲其他的可能性”(Berlin,1969,第168页)。我们可以这样理解由价值冲突而产生困难:一个人的行为涉及相交的两个或两个以上似乎同样重要的价值,追求一个价值就会破坏对其他价值的追求。在《从人的自由到社会的自由:政治价值的建造》一文中,伯纳德·威廉姆斯讨论了“自由的代价”这一概念,即为了平等或正义,有时我们必须对自由进行限制(Williams 2001b,第3-26页)。可以说,在一个价值系统里,任何价值都会有其损益。当我们允许大幅度的自由言论时,其他价值如公众礼俗就会付出代价。在生活中,节俭和优雅可能会把我们拉入相反的方向——追寻“此”可能会引发“彼”的损失。这种损失之所以发生,乃是因为价值是相互关联的,在一个价值框架里它们会为实施空间而竞争。
一些作者同意柏林关于的价值冲突的观点(比如,Taylor,Williams,Negal等),而其他人则否认此种冲突。罗纳德·德沃金(Dworkin,2001)主张,如果表达方式恰当,自由主义价值是没有冲突的。他说,自由主义者应该把“自由”定义为有自身限制的一具体种类,而不是无限制的一张空白支票。其实,德沃金看到了对自由要有“限制”的需求,正是因为自由是和其他价值有冲突的。我们需要给这些价值指定其各自的位置,否则它们彼此会越位。德沃金有时暗示道,价值之间可能冲突是因为一种价值或许会被其他价值推翻(Dworkin,2000,第2页)。其实,这种认为一价值会有推翻另一价值之可能的观点暗含的意思即是这些价值在同一维度上相互竞争,相互冲突。
价值的组合配置
很明显,如果社会要保留各种价值,就必须把它们以一种有意义的方式组织在一起。这种组织通过文化里的价值模式得以实现。价值模式反映了不同价值间建立起来的关系,这包括相互竞争和相互冲突的价值。本文的第三个主张是关于各文化传统中的“价值组合与配置”。“价值组合与配置”是复杂、漫长并且持续的过程。通过这种过程,各种价值被以系统化的方式确定优先次序并组织起来,达到一种在一特定文化里的理想的平衡状态。价值配置有其结构。它的结构大体上由两模块组成。首先,价值在彼此优先次序方面有其规定。不同的文化可以用不相同的方式为价值排序。例如,尽管两种文化都认可“忠诚”和“个人自由”这两种价值,一种文化可能会将忠诚看得比个人自由还高,而另一种文化则可能相反。儒家认为遵循“礼”要高于“自然无为”这一价值,而道家则相反。其次,相同的价值配置对同一系列中的各个价值的规定的程度也会有所不同。可能两种文化都认为x价值比y价值重要,但是在得以区分两种价值的重要性程度上,两种文化可能会有分歧。例如,虽然美国与西欧其他国家都认为言论自由比公共礼俗更重要,美国给言论自由的分量要高于欧洲许多国家。在德国,否认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对犹太人的大屠杀是违法的,在美国由于言论自由的至高价值,则不可能有这样的法律。
当然,一种价值高于另一种价值并不意味着前一种价值永远绝对地胜过后一种价值。例如,儒家认为对父母的责任高于对工作的责任,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当对父母的义务与对工作的责任冲突时,人们就什么工作都不能做。这取决于具体情况,取决于在行为中两种义务的筹码的多少,等等。如果某人的父母想要一起看电影,而同时又有一个重要的工作会议要参加,那么理性的儒者会说这个人应该去参加会议。但是,如果父母不舒服需要送医院,那么或许这个会议就可以跳过。这如同说,尽管金子比银子珍贵,但是一万盎司的银子仍然要重于一盎司的金子。这里的要点是,当牺牲父母与牺牲工作之间存在终极冲突时,儒家的价值配置倾向于履行对父母的义务。
价值配置体现了一种文化对良好生活的理解和理想,是对社会生存与需求的系统化、概念化的回应。阿拉斯代尔·麦金泰尔在《德性之后》一书中讲到,一个文化传统就是“关于组成那一传统的各种善的理念的论证”(MacIntyre,1984,第222页)。在表达其特殊的价值配置时,文化传统提供为什么某些的价值比其他价值要重要的理由。作为概念的配置,价值配置不能被精确量化。在价值配置中价值间的关系是很松散的。在很多情况下,不同的文化会共用一种相似的价值配置,却以不同的习俗形式表现出来。人类学研究表明,不同的习俗文化形式是价值的体现,比较道德哲学则阐明不同的价值配置。道德哲学和社会科学的各种尝试往往表达、证明或试图改革某种价值配置。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可伦理学》中提出的人生理念即是价值配置的一个好例子,约翰·罗尔斯的《正义论》是另一个例子。社会科学中的研究,如“世界价值调查”,不但很好地说明了不同文化间不同的价值配置,并且反映了社会中现有的或正出现的价值配置。在同一个社会里常常存在不止一种价值系统,所以也存在不止一种价值配置。中国古代的两种价值配置就分别体现在儒学与道家中。在当今美国,某种程度上说,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之争便体现了不同的价值配置之间的争论。
在通常情况下,价值配置的形成并不是一个社会有意识的决定,而是一个自然的、往往是漫长的过程。这个过程常常受地理环境因素和历史突发事件的影响。艰难物质环境中的人可能会将“忍耐”看做是很重要的美德,因为这事关他们自身的生存与延续。狩猎社会的人们或许会更看重身体的力量的价值。一个强大而有魅力的领袖或许会抓住一个历史性的时刻去发展和明白地阐说新的价值配置,并由此改变民族方向。“9·11”恐怖袭击事件为美国人民提供了一个机会,将他们的价值关注点从个人自由向安全和社会控制方面转移。比如,现在,美国公民如果在海外有一万美元以上的银行账户,就必须每年按时向政府报告他们每一个账户的存款额。这种对个人隐私的赤裸裸的侵犯,在“9·11”之前是很难想象的。我们可以预言,如果针对美国的恐怖行动继续存在,那么价值配置的转变就会变成长久性。这即是价值重构的例子。①
不同的文化中常常嵌有不同的价值配置。古希腊哲学在他们所有的基本价值中更重视智慧、勇敢、节制和正义。儒家则将仁、义、礼、智、信作为文化的核心。简单地认为希腊人不重视相当于“仁”的价值,或儒家不重视“正义”都是不对的。他们也重视这些价值,只是他们各自对这些价值的地位判定不同。同样地,不是如今的社群主义者不重视个人自由,他们也重视,只是不像自由主义者那般重视。不是自由主义者不重视公益,他们也重视,只是不像社群主义者那般重视而已。人们可能会怀疑,如果希腊人重视仁爱多一些,或者儒家重视了正义多一些,是不是会更好?如果社群主义者重视个人自由多一些,或者自由主义者重视,公益多一些,是不是情况会更好一些?毕竟,他们都认为这些价值是好的价值。他们当然可以更重视一些相关的价值。问题是,这些价值的偏移会影响同一价值配置中各种价值的优先顺序。由于一个文化中的各种价值是联系在一起的,所以各种价值得到的重要性是相互依存的。因此,增加一个价值的重要性不可避免地就会影响其他价值的分量。如果社群主义者更加重视个人自由多,就意味着它在向自由主义倾斜。如果自由主义者更重视公益,就意味着它更加向社群主义倾斜。到了一定的程度,这种倾斜的持续则会导致丧失原来的立场。
同时,追求一个价值会不可避免地带来在某些其他价值方面的损失。这种性质意味着不可能存在绝对的单一价值。也就是说,没有任何可以永远高于一切的价值。人们或许会认为某些价值,比如人的生命,是绝对的。但是并不是这样。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人死于艾滋病或癌症,如果社会能投资更多以加强医疗研究,很多生命就会获救。然而,这样做会付出经济和道德上的代价。这会给我们也同样珍视的其他的东西带来负面影响。如果我们把公路上的行车速度降到现在的一半儿,也许可能大大降低交通事故率,从而节省大量生命,可是由此带来的结果也会让我们不能不在其他方面付出代价。很多人认为人权价值是绝对的,其实不是。我们的社会每年都无意地把不少无辜者送进监狱。这当然是对人权的严重侵犯。如果社会能在培训警力和法务人员方面投入更多一些,在司法过程中投入更多一些,就会减少这种对人权的严重侵犯。但是我们并没有这么做。并不是因为我们不珍视无辜者的人权,而更多的是因为那样会损失其他我们也珍视的东西。比如,我们也渴望国家的安全,资助穷人,健全的医疗保健等等,也必须在这些方面做适当的投入。“9·11”恐怖袭击事件后,美国政客们的言论有“国家安全的成本再高也不为过”之说。他们错了。国家安全的成本会太高。这是因为安全方面的价值成本会影响到我们珍视的其他重要东西。在价值配置中,有些价值被看的比其他价值重要得多,我们从而为追求这些重要的价值付出更多的代价。但是,没有任何单个价值会绝对胜过所有其他价值。人类不可能在单一的价值上生存,无论那个价值有多么重要。
一个价值系统的特性和重要性表现于它特定的价值配置。一个社会或者文化里的价值配置旨在满足该社会的特殊情况和需求。由此原因,合并而“平均”不同价值系统并不是文化进步的好方法。柏林的《自由四论》说明,当人们憧憬理想生活时,他们希望不会失去或牺牲任何一个价值,希望所有的理想都能够被满足。然而,这样的愿景不只是空想的,也是不合逻辑的。它之所以不合逻辑,是因为一些基本价值必然地会冲突,我们不可能满足一个而不去负面地影响另一个。例如,有人可能会认为道家强调自然无为就如儒家强调循规守礼一样,都是好的追求,因而两者都想要。然而,在这两者之间存在着不可避免的紧张关系。由于一种价值系统以一定的方式构成,它可以重视自然无为多一些或重视循规守礼多一些,或者两者都同等重视。但不可能存在一种价值配置使两者彼此优先。在这个意义上,儒道合一的价值配置就是矛盾的,至多,人们可以在两者之间徘徊往返。在儒家与道家两者之间产生一种折中的价值配置不是不可能的。然而,此系统既不会是儒家的,也不是道家的,会缺少各自系统中的力量和特性。
文化改革涉及其中的价值配置的变革。这常常是通过文化内的对话达成的。马丁·路德改革运动的一个重要方面即是通过挑战教皇权威,将宗教权威的来源从教皇转向了信徒个人。换句话说,路德运动的后果之一即是削弱集权——集权在当时的基督教那里的表现即是教皇(或者其核心成员)独揽大权——而更注重个人自决。孔子、孟子将仁作为核心价值,并以此与强力(军事力量)这样的价值相对,试图以“仁”政取代“霸”政,也是要改变当时当权者所遵循的价值观。
改变价值配置是有相应的成本的。试图“改进”一文化传统时,人们有时就会将一价值抬至一更高的位置,或者引入新的或异质的价值,以应付新的挑战(“新”的价值其实往往只是到目前为止在其自身价值配置中仍处于较低位的原生价值,或者是经过重新阐释、重新包装的价值)。这样做,当他们看到变化的积极方面时,他们就会常常不注意到这种变化所带来的其他价值损失。例如,当前儒学民主化的尝试中,一些学者试图提升儒学内部的“民主价值”。事实上,儒学的民主化是会有代价的。过度把儒家民主化,必然造成对儒家传统价值的损失。由于这个原因,儒家的民主化必须有其限度。②如果在一个价值系统里我们不能两者兼得,那么我们需要决定采取哪种方式。一些人不意识到这种“价值系统改变的代价”。他们希望既保存自己的蛋糕又把它吃掉。其实既不现实也不明智。
当今世界,文化间的道义方面的争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不同文化的价值优先取向导致的,而不是关于价值自身有无之争。就是说,是集中在某一价值对于其他价值的优先性方面的争论。当今之世,对抗普世价值主义的主要来源是不同文化间的异类价值配置,而不是异类价值。人权问题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第一代”人权宣言注重人的社会以及政治权利,而“第二代”人权所宣扬的权利主要集中在经济和文化权利上。大多数人同时接受这两种人权思想。但是他们各自的优先考虑点或着重点并不相同。人权问题方面的重要分歧往往在于是优先人的社会以及政治权利,还是给予经济、文化的权利同等的、甚至更大的关注。1993年曼谷人权宣言第10章主张,“经济、社会、文化、民众以及政治权利的独立和不可忽略性,及有必要对所有人权思想的范畴给予同等关注”。某些“第一代”人权思想的倡导者拒绝或是看低“第二代”人权思想的合法性。这说明,跨文化(或者跨“主义”)的道德观碰撞经常是由不同价值观系统中不同价值的优先取向造成的。
不同价值配置的持续性
本文的第四点是,不同文化传统之间的价值配置不会消失,但是它们可以和平共存。价值配置的合理性主要基于具体社会的需要。因此,世界上会存在不止一种合理的价值配置。不同价值配置的共存可由以下两点来解释和论证:第一,之所以有不同价值配置的原因之一是因为价值体系的形成并不是一个纯粹的逻辑过程。价值体系和价值配置从来都不仅仅是由理性决定的,而是包括感情和传统在内的各种各样的其他因素。理性主义者认为理性是道德价值的基石。比如,在康德看来,一个人仅基于理性就能形成道德规范。至少,理性主义包含了一部分真理。我们经常以理规劝自己和相互以理性规劝以去确定一条道德之径。一位美国哲学家曾经跟我说过,她在阅读完彼得·辛格“动物解放论”的有力论证后,降服于他的理性论证,一下子变成了素食主义者。在道德价值的形成中,理性的力量是显而易见的,道德价值的理性手段(或态度)处处可见。黄金律就是一个例子。尽管在运用黄金律时也会涉及情感,但是主要还是依靠理性制定出恰当的处理方式。一个人可能倾向于做某件事,但是对黄金律的深思熟虑可能导致他去做另一件事。
另一方面,情感主义者认为情感决定道德价值。例如,大卫·休谟在《人性论》中主张“道德特质并不来自理性”。他认为,我们的感受最终决定道德上的对与错。休谟主张,道德不是我们理性推理的结果。而且理性也不能激发道德的、善良的行为,因为理性本身是惰性的,并不影响我们的激情和行动。休谟所说也有其道理。在人们做有关道德的思考时,情感主义也有其依据。我们经常跟随着情感来做道德决定。上面提到的那位美国女哲学家也告诉我,辛格的哲学说教对她的子女根本不起作用。而在她把孩子带到附近的一个屠宰场,让他们亲身经历了那里的惊心动魄的一幕幕之后,情感的变化促使孩子们不再吃肉了。再如堕胎问题。在改变一个人关于堕胎的立场上,理性几乎不起作用。最终是某人对堕胎的感受决定其立场。我们对诸事的情感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家庭及社会环境所影响的。这些影响往往是跟我们的共同情感联系在一起的。
与理性主义和情感主义相对,传统主义者认为我们的道德在传统中形成。麦金太尔主张,离开了传统,人们将不能确定道德与善。他认为一个人的历史只能在他所生活的环境中才可以理解(MacIntyre,1984,第206—207页)。对于麦金太尔来说,人的生命是传统的一部分。只有在传统的语境中才能定义和实现美德(同上,第222页)。麦金太尔主张,我们需要找出体现在传统中的推理这一概念。根据这一概念,理性的辩护来源于历史,是历史的一部分(MacIntyre,1988,第7页)。因此,传统是理性的源泉。不同的传统有不同的理性思维,或者说,所有的推理都是在某一个传统的思考模式下进行的(MacIntyre,1984,第222页)。
本文认为,人类的价值观有很大可能是由以上三个要素共同塑造的,即理性、情感和传统。人类既是理性的动物,也是情感的动物,又是传统的动物。我们以理规劝人们以使他们意识到某事比其他事情更重要。我们根据自己的感受对某一事件的道德意义作出回应。同时,生活在传统中的我们从上一代继承价值并对其有所改造,又将之传给下一代。在传统中,我们了解和把握理性;在传统文化的熏陶下,我们形成和培养自己的情感及其表达方式。我们的价值配置尽管随着时间总是在变,但却是上述三个过程的合力的结果。除了理性、情感和传统之外,价值配置的形成还涉及其他因素,如地理条件和特殊历史事件等。所有的这些与价值配置有关的因素使得不同的价值模式的存在成为很自然的事。
全球化已经极大地促进了跨文化运动对各个文化的价值配置的影响,但是并没有消除本土性因素。全球化(globalization)的过程也是全球地域化(glocalization)的过程。不同文化传统的人们可能会以不同的方式思考。他们对某些事物的感受可能也不同,并在各自的传统中遵循着不同的途径。不同的价值配置很可能会继续存在。
第二,除了社会环境等原因,不同价值配置的继续存在也可以由道德生活中的另一个重要元素来解释,这便是人们的道德行为的价值功效的不确定性。这就是说,由于人类社会中各种事件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尽管人们在行动中追求这些价值,但成形的价值观并不总是能决定人们行为的结果。事实上,除了极端的事例,由于这种不确定性,证明一种价值配置优越于其他的同样经历了历史考验的价值配置几乎是不可能的。
有些哲学家,如柏拉图,寻找人类生活的确定性。在柏拉图的真实世界中,理念以逻辑的方式就像数学符号那样“配置”在一起。在《智者》篇中,柏拉图借陌生人之口告诉我们:理念就像字母表中的字母一样排列在一起,对于这些字母来说,语法决定了它们之间的结合与否(253a)。对于理念,逻辑决定了它们相互间的协调或不兼容(253c)。合理排列的理念形成了一个等级配置。哲学家的工作就是确定理念排列的知识或逻辑。对于柏拉图的理念世界,有两件事应该注意。第一,根据他的观点,正确的理念排列方式只有一种,同时,“善”位于理念等级配置中的顶端。第二,柏拉图的理念世界并没有区分事实和价值。所以,对柏拉图来说,在理念世界中使价值体系化只有一种正确的方式,或者说,只有一种合理的价值配置。在《普罗泰戈拉》中,柏拉图向我们表明为了消除生活中的不确定的“运气”,人们的知识应该以理解“技术”(techne)为目标。这种知识和技术的把握使人们能有条不紊地掌控自己的生活。换句话说,因为只有一个客观正确的价值配置,所以有德之人必须知道这一事实并相应的掌控自己的生活。
可是,柏拉图错了!不仅理念世界并不存在,一个客观正确的普遍价值配置体系也不存在。人类永远无法逃离道德生活的不确定性。我们经常选择做某些事,尤其是有道德意义的事,这是因为我们想获得一个想要的结果。但是,我们经常不知道我们的行动,尤其是从长远来看,能否产生我们所想要的结果。如果一个学生没能考入法律学校并对此而感到悲伤,他应该继续尝试吗?如果他停止努力,他也许会错过这班车并毁掉他的成为一名优秀的律师的未来。但是,如果他放弃,那有可能是一件好事,因为他可能会找到一个更适合他的工作,并过着幸福的生活。托马斯·内格尔在《道德运气》(Nagel,1993,第61页)中视在不确定中作出的决定为一种道德运气。在此,道德运气是指我们的道德行为的结果的不可预测性和不确定性(关于广义的道德运气的讨论,可参见William,1981)。这一含义并不同于亚里士多德使用此术语时的含义。在亚里士多德看来,道德运气包括一个人的出生、体貌,甚至是他的孩子的出息。内格尔主要关注的是道德的责任和价值。但是他讲的道德运气却有更深的意义。由于不可控的因素促成了我们行动的结果,那么对于所期待的结果而言,一个道德的选择是好还是坏便至少部分的取决于运气。具体事件有运气的因素。理想的生活则更具有不确定性。
对于一个社会也是如此,由于这些不确定性,我们不能确切地知道在特定的事件中哪一价值或哪一个价值体系将使我们获得想要的结果。在某一事件中,听从自由的声音可能会获得一个好的结果,而在另一事件中,听从社群主义的声音则会获得好的结果。在进退两难的道德困境中遵循一种价值可能不会总是获得想要的结果。因为我们是人而非上帝,因为生活中有不可摆脱的运气的因素,我们不得不挣扎并摇摆于不同的价值之间,有时甚至是在不同的价值体系之间。中国人以并行儒、释、道三教而著称,他们遵从不同的价值体系。对道德幸运在人们的道德决策过程中的作用的理解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中国人的这种实践。
由于价值的不确定性等原因,我们不可能找到一个单一的价值体系来解决我们的所有道德问题。但是。这并不是说所有的价值配置都同样的合理。极端的价值配置,如弗里德里希·尼采所论述的那种极端的价值组合配置,既不能有助于人们的生存,也不能有助于社会,其本身也不能持久存在。现存的主要的文化传统已经历过时间的检验。尽管它们得以形成的过程不尽相同,价值配置也有所不同,它们在解决人类的需求上都达到了相对好的平衡。我们可以以工具主义的视角来看待价值配置。在这种视角下,好与坏更多的是功效问题而不再是对与错的问题。由于价值配置深为传统和历史事件等当地因素所影响,所以在不同的环境中有不同的价值配置,这些价值配置有其存在的合理性。
最后,如果本文对文化价值多元化的论述是正确的,那么,一方面,人类的基本价值是普世的,另一个方面,这个世界将不会最终接受一种单一的普遍的价值配置。上个世纪西方的巨大成功使人们想到人类是否会走向“历史的终结”。即,西方的自由民主的价值配置是人类仅有的切实可行的普世的价值体系(Fukuyama,1989,第3—18页)。如果这意味着整个世界将接受同样的价值配置的话,那是不会发生的。影响价值配置的环境在不同的地方从来都不是一样的。不同的地理、社会和历史环境为价值的多样性提供了条件,也使得用一个单一的价值配置去满足所有的不同社会和文化环境下的人们的需要成为不可能的事。随着时间的推移,文化会有所改变,但是它们并不会以相同的方向和相同的方式而发生变化。因此,它们从来都不会在普适的价值配置上达成一致。
对于多样的价值配置来说,世界是足够大的,可以容纳多种价值配置体系。如果有不同价值配置的文化不融合为一个单一的配置,当它们相遇时会怎么样呢?根据约翰·格雷的观点,不相称的生活方式的冲突可以通过它们间的相互妥协来解决(Gray,2000,第85—102页)。这种妥协就是不同的生活方式或价值配置相互容忍对方,即使它们在重要问题上的看法并不一致。儒家学说与自由民主的价值体系就是这样的例子。只要儒家不能提供普选领导人的民主方式之外另一种更好的方式,它就必须接受事实,尽管它认为民主有严重的缺陷。
根据柏林的观点,我们很早就应该从浪漫主义那里吸取有关的教训。“弄清了多元价值的存在,就在[柏拉图式的]理想概念上打了个缺口,在关于所有问题都有简单答案的信念上打了个缺口,在把所有事情理性化的努力,在认为所有问题的有完全的回答,以及所有的拼图式生活概念上打了个缺口”(Berlin,1999,第147页)。也就是说,由于多元价值的存在,所有这些理想化的理念都不能成立。柏林的结论是:“如果这些理想是不相容的,那么人们迟早会意识到他们必须使之相适应,他们必须妥协。因为如果他们试图去破坏其他人,其他人也将会破坏他们。因此……我们认识到容忍其他人的必要性、认识到维持不完美的平衡的必要性,认识到驱赶其他人到我们目前所设立的囚栏中的不可能性,或者是进入包含我们在内的唯一途径的不可能性。”(同上)。也就是说,现在我们要最终明白:文化的价值配置会继续是多种多样的,达到并维持世界和平的唯一方式就是为不同文化的彼此共存而寻找道路。③
注释:
①除价值配置的改变外,文化改革的另一重要方面是改变其表现形式或者代表符号,改变体现价值追求的习俗形式。当年负荆请罪,而今则是登报致歉。两者的形式完全不同,但是表现的价值则大致相同。这方面的研究主要是人类学的研究主题了,这里不赘述。
②有兴趣的读者可参见我的《道与西方的相遇:中西哲学主要问题比较研究》第7章。
③本文是在纪念北京大学哲学系建系一百周年的“华人哲学家会议”的发言稿。其基本想法曾表达于2005年的《道与西方的相遇:中西哲学主要问题比较研究》一书中。其论证与作者2008发表的“Cultural Configurations of Values”(World Affairs:Th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Issues)大体一致。在写作中,作者受到南洋理工大学哲学博士生李记芬小姐的协助。在此表示感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