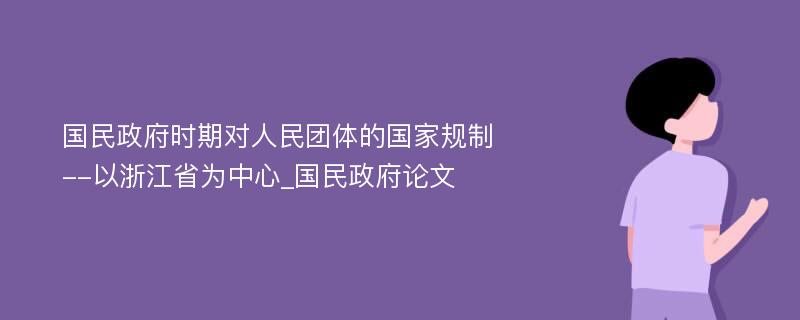
国民政府时期国家对人民团体的管制——以浙江省为中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民团体论文,国民政府论文,浙江省论文,管制论文,时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团体政治是近代以来以各种社团组织参与政治过程为主要特征的一种政治形式。它特别强调介于国家与个人之间的社会团体在政治过程中的作用。民国时期国家为了便于控制社会,按照职业及地域关系组织各种团体,以控制团体的形式来达到控制社会的目的。费孝通认为“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存在着一种以‘己’为中心的差序格局,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处理各种关系就是基于这种差序格局,“以‘己’为中心,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和别人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不象团体中的分子一般大家立在一个片面上,而是像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藉此,费孝通认为正是由于这种差序格局的存在导致了中国乡土社会不存在团体。[1](P26)从这个意义上讲国民政府对各社会团体的管制不仅仅是国家对社会的控制的一种方式,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国民政府对社会,尤其是乡土社会的一种改造与重构。关于民国时期国家同社会团体关系的研究,主要以下成果:蔡勤禹、姚群民对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对工商业团体的管制做了研究,他们认为在抗战时期国民政府为了完成抗战,加强动员力量,管制经济,加强了对工商业团体的管制。这种管制“一方面使工商业团体数量大量增加和素质提高,也打击了囤积居奇,对于集中全国物质与人力,发动抗战起了积极作用,但另一方面这种管制未能同工商业团体事业相配套,压制了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导致官僚资本膨胀。”[2]此外学者还对明清时期诸种慈善团体进行了研究(注:对慈善团体的研究,学者主要集中于明清时期民间慈善团体的研究,其中最有影响的当数梁其姿:《慈善与教化——明清的慈善组织》,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因其与民国时期慈善团体关系不大,在此不一一列举。),蔡勤禹以抗日战争为线分战前、战时、战后对民国时期的慈善团体进行论述。[3]
以上这些成果主要有两方面特征,一是主要集中在战时对工商业团体的研究,他们多把国家对工商业团体的管制看作是一种战时国民政府的经济政策。二是主要集中在对作为“公共领域”的慈善团体的研究上。实际上民国时期国家对团体的控制与管理范围极其广泛,不仅包括工商业团体与慈善团体,还包括各种职业团体,甚至于一些地域性的社会团体。
在时间段上,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国家自始至终都以控制社会团体的方式从而达到控制社会的目的,国民党政府将社团作为控制民众的一种手段,强迫民众按职业或其他标准来组织各种团体。因此以民国时期大量社团的出现而断定民国时期市民社会的发展,从这一方面讲是有一定的片面性。本文以浙江省为中心试图对民国时期国家对社会团体的管制进行论述,并以此为出发点对民国时期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进行探讨。
一、国民政府对人民团体管理权限的演变
人民团体按照国民政府的规定主要包括以下几种:农会、渔会、工会、商会、工商同业公会、学生会、妇女会、文化团体、宗教团体、公益团体、慈善团体、自由职业团体及其他经中央核准之人民团体等。[4](P195)民国时期人民团体系由民众自行组织,根据团体性质上划分可为社会团体与职业团体两种,但多数民众团体都是国民政府出于管理的需要强令组织。国民政府规定“各人民团体须接受党部之指导与协助及政府之监督,对于管理的层级,国民政府规定在中央为中央执行委员会民众运动指导委员会,在省为省党部,在市为市党部,在县为县党部,县党部未成立或因故撤消者应直接受该省党部之指导与协助”。[4](P195)后来国民政府为了加强党部在基层的力量,增强区党部与区分部的力量,制定了《区党部区分部指导民众运动方案》,要求区党部、区分部加强对民众运动的领导,遵照上级党部之规定训练所属党员,指导党员直接参加人民团体,在团体内指导民众思想行为及组织的训练,同时党员要因地制宜协助团体兴办各种社会事业。[4](P439-441)
由于党部与各级政府的分立,如何处理各级党部同同级政府之间的权限是整个国民政府时期一个难于解决的问题。对人民团体管制权限也是党部与政府两者之间争夺的一个方面,党部利用中央所赋予的“指导与协助”之权,政府利用“监督”之权对人民团体进行激烈争夺。
在此情形之下国民政府制定了《训政时期民众训练方案》,对党部与各级政府在人民团体管理权限方面做出了以下规定。(1)党部对于人民团体不受指导而予以处分时,须呈准上级党部以命令行之,但对于人民团体之解散并须转请当地政府依法执行之。(2)政府对于人民团体认为须解散时须依法办理,但事前须知照当地党部后执行。[4](P209)从这一规定就可以看出各级党部对人民团体的管制上,具有很大的权限。领导民众运动,指导人民团体,便成为各级党部尤其是各地方党部在战前政治活动一个的重要方面。对于领导民众运动,指导人民团体的目标,国民政府标榜:“改善民众生活,提高民众知识,促进生产力与生产额,提高民众之民族意识,以增进民族之自信力,然后可以御侮自卫,民治之基础树立。然后可以完成训政,国民经济发展乃可以救生产落后困苦已深之中国。”[4](P195)由此可见,国民政府在很大程度上是以人民团体的形式来作为对人民进行训练的手段,以达到其训政的目的。
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为了适应战时需要,加强了对人民团体的控制与渗透。鉴于地方党部虚弱,不足以达到掌控各人民团体的实际情形,李宗黄指出:“过去各级民众团体,往往在县城空挂招牌,很少发生作用者,其原因固多,而指导人员未能深入下层工作,积极扶植发展,实为主因。”[5](P204)国民政府也深刻检讨道:“党部有无法责令党员指导民运之苦,而党员亦因无所遵循,每多忽视自身之责任”,乃规定人民团体之主管官署,在中央为社会部,在省为省社会处,未设社会处之省,为民政厅,在院辖市为社会局,在县市为县市政府。[4](P435)这样就将省县党部主管人民团体许可组织事宜移送同级政府接管。各级政府与各级党部在人民团体管制方面的关系就变为:省县政府于接受人民申请许可组织团体后,应即派员视察,同时函知省县党部;省县政府指导团体组织完成后,向省县党部备案;省县政府与省县党部对于督导人民团体发生意见时,应分别报请上级党政联席会议决定,如再不能解决时,其最后决定权属于中央社会部。[4](P437)人民团体管辖权限由党部到各级政府,一方面反映了党部在各地方势力的软弱,无法达到国民政府对各人民团体监控的目的,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国民政府在战时加强了对人民团体管制的力度。自战时人民团体管理权限转移到各级政府后,党部就处于政府与人民团体之间相对尴尬的位置。自此以后,各级国民党党部对人民团体的领导权就体现在人民团体内部建立党团,协助人民团体之建立与督导。(海宁档案馆藏档M2-21-4)此时国民党党部由原先在人民团体管制方面的主导地位逐步变为辅导与协助地位。
由上分析可以看出,整个民国时期国民政府都没有形成一个独立的机构来对人民团体进行管理,其管理机构不是从属于党部便从属于政府。这样,就形成了党部、政府、人民团体三者之间纠缠在一起的情形,党部与政府在人民团体管制权限方面没有明确的划分,两者之间时常发生冲突。
二、国民政府对人民团体的外部监控
按照国民政府制定的人民团体组织方案,凡欲组织团体者须具有该团体法规所规定之规定资格,由发起人连署向当地高级党部(后来是政府主管官署)申请许可方可成立。人民团体必须遵守以下原则:(1)不得违反三民主义之理论与行为。(2)接受中国国民党之领导。(3)遵守国家法律,服从政府命令。(4)团体会员以法律所许可之人为限。(5)有反革命行为被告发有据或受褫夺公权之处分者不得为会员。(6)除例会外,各项会议须得当地高级党部及主管官署之许可方得召集。[4](P196)如,浙江省海宁县民营电业联合会成立之时,交通部长朱家骅派国际电讯局长温毓庆和浙江电政管理局长朱重光、中央建设委员会派黄辉、浙江省建设厅派主管科长吴竟清、海宁县政府派建设科长张文明、县党部派总干事吴观澜等列席指导。[6]国民政府为了管理需要还制定了《人民团体指导办法》,规定了对性质不同的人民团体采取不同的指导方法。[4](P197)
国民政府为了便于管理,规定在同一区域内不得有两个性质相同之团体存在,其目的就在于:“使同一区域内同一职业或同一志趣者均纳入一个组织之中,而免团体组织重复与分歧。兹查本省各县市间有两个以上同性质同级之团体存在,致组织力量分散,团体内容空虚,业务无法开展,自应由各级县市政府切实查明依法分别予以合并组织或解散。”[7](3-2-456)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国民政府为了清除中国共产党在人民团体中的影响,解决同类团体之间的纠纷及健全人民团体组织起见,决定对人民团体进行整理,并且要求在各级党部及政府的指导、监督与协助下进行改组,其目的就在于使各人民团体掌控在国民政府所能达到的范围之内。[4](P198)
人民团体成立后,当地高级党部及主管官署或监督机构对人民团体理事监事就职宣誓进行监誓,人民团体理事监事之誓词犹如国民党党员誓词,如下:余谨以至诚实行三民主义,遵守国家法令,忠心努力于本职,如有违背誓言愿受严厉之制裁。[8]国民政府为了便于了解各人民团体的活动及日常动态,规定人民团体必须每月向主管党部及政府主管部门提交动态月报表。[7](P3-2-471)浙江省政府为了保证人民团体的活动不致于发展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游行,制定《人民团体游行注意事项》,对游行宗旨、集会地点、游行日期及时间、游行路线、游行标语及旗帜都做了详细的规定。[7](3-5-539)国民政府对人民团体种种规定及各种指导与监督,其目的就在于运用政府及党部的力量从外部对人民团体施以监控,避免人民团体的活动与国民政府的政治统治发生冲突。
国民政府对人民团体外部的监控还表现在对“非法团体”的取缔上。杭州市党政联席会议秘密决定各党派如有外围组织各种人民团体之情事,依法应一律予以取缔,以重法纪,[7](3-2-456)杭州市这一规定意味着国民党党部及地方政府为人民团体唯一合法组织者。1946年11月,董时进领导的中国农业协会发动各省市县分支会组织征集会员,浙江省社会处令各县市党政机关切实注意健全省市县农会党团之组织,加强活动,尽可能防止该会之发展,对其以有效之打击。最后浙江省政府以其内容确含政治之企图,且不无欺骗作用为由[7](3-2-456),将其取缔。平湖县政府以妖言惑众为由将同善社、灵学会两非法团体予以取缔,将其财产查封交由党部处理。[9]
总之,国民政府采取种种措施从外部加强对人民团体的管制,最根本的目的就在于确立各级政府及各级党部对人民团体的领导地位,排斥其他党派对人民团体组织与领导,尤其是对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种人民社团。
三、国民政府对人民团体的内部渗透
民国时期,国民政府还采取了诸多措施加强对人民团体内部的渗透与控制,并将其作为国家对人民团体实行管制的一种最为有效的方式。
以党团的方式对人民团体加以控制,是现代国家政治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国民政府为了对人民团体进行有效地渗透,制定了人民团体组织实施的详细计划。浙江省国民政府要求各人民团体应在团体成立一个月内成立党团组织;各人民团体应积极吸收该团体内优秀分子加入党团;已有党团组织的人民团体,应分别召开党团干事会议,切实检讨工作计划及改进方法;各人民团体的党团应视工作需要定期开会,除讨论本身工作外,并得检讨时局问题及国内党派关系,以增进工作同志的政治认识,在开会时应请当地的党团部及政府派员出席指导。[7](3-2-200)战前各级国民政府党政机关就与各人民团体建立了各种联席会议。
国民政府将人民团体管理权限由党部转移到政府以后,各级党部就在人民团体指导方面就处于政府的协助地位。此时,各级党部对人民团体的领导与掌控就表现在以建立党团为核心。海宁县党部秘密制定了在人民团体内加强党团活动、巩固领导权的方案,规定各人民团体内部限期成立党团组织,党团分子负建立该团体分组核心的任务,县执行委会按月拟订党团活动中心工作,督促党团执行并考核。
战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鉴于人民团体的管辖权限让位于各级政府的情形,制定了加强党团组织办法以协助政府对人民团体管制的方式来对各人民团体进行渗透。各级党部调查所属地区人民团体之组织及活动情形,要求党员应按其职业与兴趣、专长及知识程度等情形,分别参加人民团体,其在团体内之工作活动应受该团体之党团指导;无党员参加之人民团体当地党部应即会同团部选派优秀党团员参加并组织党团积极活动;凡重要之群众集会或群众运动,当地党团部得事先指定优秀党员团员组织临时党团,以策划并指导之;各党团应择定同志一人至三人担任情报组织工作并指定一人任宣传工作。[7](3-2-200)
吸收人民团体内部的优秀分子参加党团,不仅是国民党扩大其组织的一种重要手段,也是其直接参与人民团体内部活动,加强对人民团体内部渗透,扩大其在人民团体内部发言权的最直接、最有效的途径。国民党执行委员会要求各党团应尽量吸收所在团体之优秀分子入党,并争取中立分子使其同情国民党。[7](3-2-200)浙江省海宁县党部要求:“本县人民团体,如县乡镇农会、县乡妇女会、县镇商会及各种同业公会……职员皆就党员中介绍担任各级理监事。其无党籍者随时物色入党,并培植核心党员,计划成立人民团体之党团组织。”(海宁档案馆藏档M1-1-51)吸收人民团体内部优秀分子参与国民党党团是民国时期,尤其是战时及战后国民政府对人民团体渗透的最重要的方式。
国民政府对人民团体内部的渗透与控制还体现在对其人事方面的控制上,这主要体现在对人民团体指导员的任用、人民团体书记的派遣及人民团体职员选举上。1933年国民政府就制定了《人民团体指导员任用规则》,规定人民团体指导员任用以当地高级党部民众运动工作人员为原则,人民团体指导员之职责主要为指导人民团体,指导、监督人民团体干部之选任与人民团体成立前日常活动的组织等方面,人民团体指导员于所指导的团体完成经当地高级党部认为健全即可解除职务。[4](P202)尽管人民团体指导员非人民团体正式成员,但其对人民团体的领导人选起了极为关键的作用,尤其是对人民团体成立之初的领导权的控制起了重大的作用。
人民团体书记由政府派遣是战时国民政府为加强对人民团体控制所采取的一特别措施,为战后国民政府所延续。1940年国民政府指定了《职业团体书记派遣办法》,国民政府规定以下情形之职业团体须由政府指定,(1)团体无财力任用书记者。(2)团体性质重要而尚未任用书记者。(3)现有书记思想不纯正或能力薄弱者。(4)由团体向政府请求者。(5)团体经济充裕,而无适当书记人员者。(6)政府认为有其他必要指派情形者。职业团体属于中央直接主管团体者,由中央主管部会指派,属于省县市之团体者,由省市政府主管厅局及县市政府指派。职业团体书记以曾经特种训练合格之人员为限,其由政府指派者,以派遣至原属职业团体服务为原则,其薪给得由各级政府支给。[4](P442)这一非常措施便于强化国民政府对职业团体的控制,对职业团体内部渗透的效果甚为明显,浙江省国民政府逐步把其推行至社会团体,这样整个人民团体的书记大多就由国民政府派遣。
人民团体书记派遣后国民政府为提高其业务水平,对其进行调训,1946年杭州市政府就鉴于各人民团体“于抗战时期内多数未离陷区,对于政府所颁法令,殊为隔膜”,且“大多非属训练合格人员,知识程度,高低不一,攸关会务推进甚巨”,首批调集各团体书记予以训练一个月,再依次抽训各团体理监事及会员,[10](P307-308)。国民政府定期对人民团体书记进行甄审,留良去劣,1946年7月杭州市政府就对杭州市人民团体书记全部进行甄审,计合格者三十八人,由市府加委,准予任用,不合格者七人,予以免职。[10](P307-308)这样国民政府就把人民团体书记变为国家的一种公职人员,由国家的公职人员来对人民团体进行管理,其对人民团体的渗透程度与效果是不言而喻的。海宁县政府曾指出:“白县派书记呈撤离后,人民团体联系渐趋疏淡”[11](P41),要求主管当局加紧对人民团体加以辅导。
人民团体职员是人民团体得以运转的重要保证,国民政府对人民团体职员进行严格的监选。各地人民团体职员之选举须由当地高级党部指定人员出席指导,并由主管官署或监督机关指定人员监选方得举行。[14](P204)国民政府对人民团体职员选举的监控,其目的就在于使人民团体得以顺利执行政府的法令与政策。
国民政府为了便于对人民团体从内部进行渗透,还采用给予人民团体经费补助的手法来控制人民团体。对于这一做法,国民政府解释道:“人民团体之组织系以民众自由意志为基础由民众自行发起,故其经费应以各该团体会员之会费及捐款充之为原则。惟现在训政时期各地民众有因经费而无力组织者,有已经组织对于本党主义颇能真实接受推行,且奉公守法为民造福而无力维持者。为推行训政,制止反动,建设民权政治之基础计,在此特殊情形之下本党尚有予以经济上补助之必要,惟此项补助并非常例,不可未具严密之规定。”“补助费之决定除因特殊情形由党部秘密执行者外,其补助费之决定应会同当地政府统筹办理。”[4](P204)各地受本党补助之人民团体,其经费预算应由各该团体按照实际需要及各该团体事务之繁简,呈请当地高级党部核定后再呈请政府备案。[12]国民政府以补助人民团体经费的手段得以插手团体内部事务,便于向人民团体内部的渗透。
四、国家政权与人民团体之间的互动
国民政府为组织人民团体顺利起见,给予了人民团体种种政治权利,其中最主要的为职业团体职员可参加县参议员、乡镇民代表候选人选举及甲、乙两种公职候选人选举两种。这些权利的赋予使人民团体政治地位在法令上得以确立,当然这也是国民政府控制人民团体的一种措施。
按照战时国民政府颁布的《县各级组织纲要》规定,由县内乡镇民代表会选举县参议员,以每乡镇选举一人为原则,并得酌加职业团体代表,但不得超过县参议会总额十分之三。浙江省政府制定的《修正县参议员及乡镇民代表会候选人考试暂行条例施行细则》中明确规定具有县参议员及乡镇民代表会候选人职业团体或人民团体系指农会、渔会、工会、商会、同业公会、文化团体、公益团体、自由职业团体等依法成立的团体。[13]
1942年国民政府考试院考选委员会颁布《县参议员及乡镇民代表候选人考试声请检复须知》,对人民团体的县参议员及乡镇民代表候选人资格做了详细的规定:曾任职业团体或其他人民团体职务三年以上,著有成绩者得参加县参议员选举;曾任职业团体或其他人民团体职务一年以上者得参加乡镇民代表选举。浙江省政府对此解释道:“规定职业团体应以县参议员之名额不得超过总数额十分之三为限,以每一职业团体为一单位,各自由职业团体合为一单位,按会员多寡比照分配其应出之名额,但至少每一单位应分配一名,不足分配时由各单位分别选出初选人,会同复选之各单位初选人名额比照其会员人数定之。”同时浙江省政府还根据实际情形规定:区域选举之当选人以本乡镇内之公民为限,其由数乡镇合选参议员一人时,以参加选举各乡镇内之公民为限,职业选举之当选人以各该团体之会员为限,会同复选时以参加复选各团体之会员为限。浙江省政府并规定:“乡镇保长及保队附当选为乡镇民代表会代表者,应即辞去一职。至农会等系属民众团体,其正副干事长当选为乡镇民代表会者,得兼任之。”[14]
国民政府规定曾任职业团体或其他人民团体主要职务且年满二十五岁者,得应甲种公职候选人检复。[7](3-1-49)浙江省各县也规定曾任职业团体或其他人民团体职务一年以上且年满二十五岁者,得应乙种公职候选人之检复。(湖州档案馆藏档312-8-3)1946年嘉兴县规定职业团体人员参与甲种候选人检复须于4月30日完成,同时得参加县参议员选举。[15]
浙江省鉴于训政时期“人民运用四权能力尚属薄弱”之情形,赋予人民团体职员以担任乡镇保甲干部人员之权利。浙江省政府规定曾任职业团体职员一年以上得参加乡镇长选举;曾在认可之初级中学或其他同等学校毕业并曾在各机关团体(包括人民团体)学校服务二年以上者可担任乡镇干部人员;曾在认可之高级小学毕业,并曾在各机关团体(包括人民团体)或学校服务二年者可担任乡镇保甲干部人员。(嘉兴档案馆藏档304-4-25)国民政府赋予人民团体政治上的种种权利固然是处于对人民团体渗透与控制的需要,但同时也是在很大程度上把人民团体作为训练人民、改良社会的一种手段。
各种人民团体组织成立后,国民政府对其加以渗透与控制,其目的就在于利用人民团体加强对社会的管制,尤其是人民团体内部成员的治理。民国时期国家对社会控制力的薄弱,以人民团体的形式来对社会来加以控制,不失为一种有效的途径,这也是现代国家政权控制社会的一种方式。
1936年浙江省政府发布训令:查僧道如确系不守法规,所属教会知情不举,或饬查仍词偏袒,县政府得本监督职权,召集当地多数僧道公决,依该教教规予以惩处。如无法取得公决时,得直接将该僧道驱逐,并得呈请上级机关,转行该教总会饬令该教会纠正,如该教会不予纠正,得再请上级机关转饬另行改组,或撤消该教会。[16]阮州市茶馆业商业同业公会鉴于战后“杭州开设茶馆者竟有风起云涌之概,不顾一切法令擅自营业者比比皆是。既不遵章入会又不声请登记……虽有受劝告而经左右同业保证加入本会者数甚寥寥,在本会惟有酌情变通以息意外纠纷,似此漫无限制,隐患堪虞”,要求“对有新开设茶馆在未经核准,创设登记以前未有本会之证件者不准擅自营业。”[7](ll-l-30)
在战时国民政府还指定了《非常时期职业团体会员强制人会与限制退会办法》,规定职业团体法定会员资格之从业人员或团体,均应加入当地业经依法设立之各该团体为会员,非因废业或迁出团体组织区域或受永久停业处分者,不得退会;拒绝入会之各从业人员或下级团体,应由各该业团体限期劝令加入,逾期仍不能遵办者,应予警告,自警告之日起十五日内仍不接受者,得由该机关团体呈请主管官署分别予以下列处分,各从业人员以罚款与停业之处罚,而各业下级机关则予以整理与解散。[17]这是为了应付战时非常环境的一项非常措施,但也反映了国民政府试图以团体的形式来加强对人民的控制与管理,这一做法也为战后国民政府所延续。1946年杭州市政府令娱乐业职业公会劝导国际戏剧院工人入会无效后,令警察局强行令其入会。[7](12-2-33)国民政府以人民团体作为控制其本身所控制的行业及人员的一种手段,从而达到控制社会的目的。
人民团体在国民政府的指导与监督下,在不违反国民政府法令前提下可参与各种政治与社会活动。嘉兴县政府于1930年2月召集各民众团体,及各公团代表,组织国货提倡筹备会。[18]嘉兴县米业公会决定取缔黑市交易。1946年浙江省社会处要求各人民团体协助推行抗战复员工作:策动组织及指导各级原有之慈善、宗教、公益及社会、事业团体协助政府办理各种复员救济工作;督导各地同乡会联合协助政府办理难民还乡工作;督饬各工商、自由职业及社会团体办理调查登记各种专门技术人才,以应收回复员之需要。[7](11-1-30)
人民团体一方面代表本团体会员的利益,但另一方面又执行国家的法令政策,执行国家对团体会员的管制,正是因为人民团体的两面性,人民团体常常处于国家与社会“中间人”的角色,它常常与国家及其所属会员发生冲突。1933年12月,嘉善县农会应县政府所定之缴租标准,违背二五减租原则,增加佃农负担,要求县政府遵循1927年之实际租额。[19]嘉兴县商人统一组织委员会全体委员,因县政府诬控拉夫一案而全体辞职。[20]海宁县商会要求县政府减轻商人负担,提高商人待遇。嘉兴人力车公会与三轮车队发生冲突,从而导致人力车公会各理事总辞职[21],此类事例举不胜举。
国民政府赋予人民团体种种政治权利,利用人民团体加强对所属团体会员的管制,而人民团体也得以参与国家的种种政治活动,从而形成了国家与人民团体之间的互动关系。人民团体一方面是其团体会员的代表,其与会员之间的利益息息相关,但另一方面人民团体也代表国家对其所属会员进行管制,处于国家与社会的“中间人”地位,正是由于人民团体这种两面性,造成了国家、人民团体、所属会员三者之间的互动。
五、结语
中国传统社会里,家族思想颇为浓厚,阻碍了人民团体意识的发展,“吾国民众,虽号称四万万五千万,惟因缺少团结,一如散沙,致所有蕴藏民力,未能充分发挥”。[22]国民政府以团体的形式把民众组织起来,其根本目的在于改变过去那种民众散漫组织形式,加强国家对社会的控制。“所以本党的同志,对于乡镇保甲和职业团体,都要领导,不但要注意乡镇保甲,也要注意职业团体。”[23](P71)以团体的形式来加强对社会的控制,不仅可以减少政治投资成本,同时也可以大大增加行政控制效率。“乡镇公所应随时宣传鼓励民众加入各种人民团体,与人民团体负责人取得联系与合作。”(嘉兴档案馆藏档304-4-34)
国民政府对人民团体的管制同行政机构结合在一起:“至中国家族思想,本来是浓厚的,颇足以阻碍人民团体意识的发展,因此又把保甲组织严密起来,使每一个家族的产生,应透过保甲的关系,与整个国家生活发生联系。同时更规定组织妇女会,少年团,职业团体与民众组织,使每个人除家族生活外,各个内参加一种社会组织。这样久而久之,人民的思想自然会随着生活的变化,由家族主义进到国族主义。”[24](P9)人民团体同国家行政机构相结合,以树立现代国家形象是民国时期国家对人民团体管制的最根本目标。
我们不应简单地把国民政府时期国家所控制的人民团体作为“黄色某某会”,人民团体实际上是国民政府对传统社会改造的一种手段,它是国民政府对社会重构的一种措施。“要使人民熟练会议技术,俾得运用四权,必需其他农工团体以及其他经济文化团体的发达,健全的地方自治,必依存于社会自身的繁荣,所以自治组织的演进,决不是一蹴可就的。”[25](P238-239)以人民团体的形式来训练人民行使四权,尽管有国民政府自我标榜的成分,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国家以人民团体的形式来改造社会的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