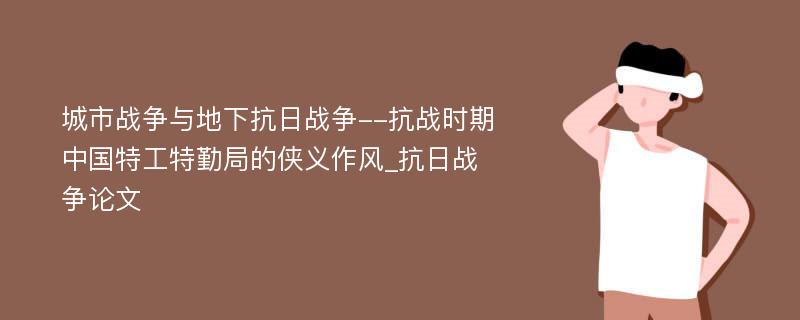
城市中的战争与地下抗战——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特工秘密机构的侠义之风,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抗日战争论文,侠义论文,之风论文,中国论文,特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873(2004)03-0098-10
1930年代末和40年代初,尽管人们渴望公共租界依然能为所有逃避日本占领军残酷统治的人提供一片安身的乐土,但孤岛还是成了动乱之地。前上海工部局属下的英美行政当局已根本无法抵御日军的苛求,日本军队行将进入并占领公共租界。在爱国情绪的激励下,上海市民不得不把孤岛作为发起抗日运动的基地。国民党和共产党都利用租界来进行抗日宣传,收集情报,获取军事物资,密谋暗杀,进行抗日的神经战。在汪伪警察的协助下,日本人也以牙还牙,大肆报复。尽管号称中立,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实际上成了各方争斗的战场。在这场城市战争中站在最前列的是国民党情报机构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军统)的特工人员。军统的首领便是在重庆的戴笠将军,戴笠发誓绝对效忠于蒋介石个人,西方的媒体有时将他称为“中国的希姆莱”。为了恐吓投敌分子,从1939年到1940年间,军统在上海进行了一系列暗杀汉奸行动,其主谋就是戴笠。
回顾民国历史,戴笠和军统组织可谓是两大背景下的产物,它是国民党和共产党内战的产物,也是中日战争的产物。军统,行动诡秘,令人生畏,是蒋介石对付政敌的利器,所以长期以来一直是人们热衷于揭露的对象,也是左派进行反国民党宣传攻击的靶子。然而,有关戴笠和军统在抗战时期的史料在60年代前并不多见,自60年代起,海峡两岸开始出版大量个人的回忆录和史料集。在冷战的氛围下,留在大陆的前军统成员受共产党之邀所撰写的回忆大多对自己的这段经历加以谴责,而他们在台湾的老同事却发表回忆录对军统的历史加以颂扬。这些资料描绘了军统中的重要人物,构画了军统的组织机构,讲述了军统历史上的一些重大事件,探讨了军统在国民党政治中所起的作用。可以想见两岸发表的东西大相径庭,或褒或贬,黑白分明。然而,这些相悖的叙述所惯用的语言却极为相似,他们所用的语言源自《三国演义》和《水浒》之类的通俗古典历史小说,以此来描述他们所想象的抗战历史。用这样的语言所描述和想象的军统历史意义何在?军统组织和人员在抗日战争中起过如此重要的作用,而他们利用这段历史又是想告诉我们什么呢?怎样才能帮助我们把握上海街头国民党抗战的性质?本文试图通过审视1939年这一关键时刻的军统历史来回答上述问题。当时,敌对的特务头子正企图赢得军统特工的效忠而与戴笠较劲。他们用历史小说豪侠之风中仁义忠孝之类的语言来激励无名的特工进行生死之战。
戴笠和军统的创建
戴笠首创军统,他白手起家,使之成为个人权力的强大据点。与此同时,这位将军自视为蒋介石的个人工具,利用军统为其主子和领袖的意志服务。这样,戴笠所创建的组织就存在着一种根本的矛盾,这是一个权力极大的机构,在民国政治中举足轻重。同时,这种权力来自戴笠对蒋介石个人权威的绝对依附和效忠。戴笠与蒋介石的关系始于1924-1925年,当时,祖籍浙江江山的戴笠来到广州,被黄埔军校六期录取。在军校,他受到中国国民党创始人孙中山任命的校长蒋介石的训导。在以后的岁月里,戴笠把自己既看作导师蒋介石传统意义上的弟子,又把自己视为近代革命党最高领袖的政治追随者。在创建军统时,戴笠既运用流行的儒家的忠义观,也引进孙中山的革命理念,在军统的训练计划、组织规则和个人准则里打上其特定的印记,使军统的纪律与对领袖的个人崇拜结合起来,在军统内部培养了一种特殊的政治文化氛围。戴笠的情报工作始于20年代中期孙中山去世(1925年)后的岁月里,当时他是黄埔军校的士官生。孙中山的去世引起国民党和共产党的领导权之争,最终导致了国共联合这一脆弱同盟(1923-1927年)的分裂。这场争斗也使黄埔和广州成为政治竞争的热土,在这场争斗中,可靠的政治情报机构自有其可贵的价值,而这正是戴笠所热切追求的。
从一个独立的情报人员到一个专业的特务部门头子,戴笠的转变发生在30年代初日本军队占领满洲之后。1932年初,一批黄埔军校的毕业生出于爱国激情创办了力行社,旨在促进国民党的改革,使中国政府更为强大。他们宣誓遵守党的纪律,无条件地效忠于蒋介石。力行社组建了以戴笠为首的特务处。1932年,在南京近郊的富有象征意义的中山陵,蒋介石亲自将这项任命授予戴笠。蒋以黄埔军校前校长的身份教导戴笠在组建特务处时不妨读读《三国演义》和《水浒》这类传统的历史小说,以便从中得到启发。戴笠立刻明白这项特殊的任命生死攸关责任重大。(注:国防部情报局编《戴雨农先生全集》(2卷本),台北,国防部情报局,1979年,第1卷,第316页。)他向蒋介石发誓:“从今后雨农将置生死于度外,为完成我们的使命与敌人作殊死的斗争。如若失败,甘愿被领袖处死。”戴笠的部下常把他的誓言与战国时燕国的刺客荆轲相比,荆轲临行时对焦虑不堪的燕太子丹唱道:“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注:《戴雨农先生全集》,第21章,第316、349页。)从此以后,尽管特务处从克格勃和盖世太保那里借鉴行动方法和组织技能,特务处的成员却从不把自己视为社会主义者和法西斯分子。戴笠坚持必须建立与忠孝仁义传统信念相吻合的组织体系,用中国式的语言来表述这些观念,他对部下说:“同志即手足,团体即家庭。”“我们的同志以仁义而相聚,我们的关系以互忠互信为纽带。”(注:魏大铭:《评述戴雨农先生的事功》,《传记文学》第38卷第1、2期,1981年,第44、45页;刘培初:《浮生掠影集》,台北,正中书局,1968年,第58、59页。国防部情报局编《戴雨农先生全集》第1卷,台北,国防部情报局,1979年,第314、323页。)特务处的核心组织为蓝衣社,由“十人团”组成,其成员几乎是清一色的黄埔六期同学。从1932年到1937年,这些老同学在戴笠的领导下,靠一笔经费在南京一个特别的办公室里共同生活。他们把这当作家庭的延伸,大家都是结拜兄弟。这个团体带有平等主义色彩,戴笠虽然是领导,也不过是平等兄弟中的一个带头人而已。
1936年的西安事变使戴笠对蒋介石的忠诚受到一次非同寻常的考验。1936年12月12日,在张学良将军的指挥下,东北军军官发动军事政变,将蒋介石扣押在唐代古城西安的东北军司令部内。张学良是被刺杀的东北军阀张作霖之子。起事者要求国民党政府停止进攻撤到陕北的中国共产党,向外来的日本侵略者宣战。这些军官威胁道,他们的要求若得不到满足,就要杀蒋。西安事变使南京政府陷入混乱,蒋介石可能遭到不测,当其他人正忙于争权夺利之时,戴笠却不顾个人安危,陪同蒋夫人从南京飞往西安。他曾秘密处决过不少共产党员,一旦落到共产党的手中自然性命可虞。然而他还是义无反顾地陪同蒋夫人前往,有意要重演历史。早在1922年,孙中山被他的同志抛弃并遭到广东军阀陈炯明部队的进攻时,蒋介石陪同领袖一起登上泊于广州城外珠江上被围攻的“永丰号”巡洋舰。孙中山最终安然逃离。蒋介石在这一事件中崭露头角,在危难之际,他是唯一坚定地站在领袖身边的信徒,从而成为孙中山革命遗产的合法继承人。(注:中国国民党党史委员会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台北,1984年,第10页。)戴笠1936年的慷慨“赴难”重演了领袖和导师蒋介石当年的壮举。西安之行被许多人目为戴对蒋绝对忠诚的表现。戴笠因此不仅赢得了蒋夫人的友谊,也赢得了蒋介石的完全信任。事变之时蒋的许多副手和以前的学生都躲在南京偷安。(注:《戴雨农先生全集》第1卷,台北,国防部情报局,1979年,第46、48页。文强:《戴笠其人》,见沈醉、文强编《戴笠其人》,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0年,第196、197页。)
西安事变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它标志着中国对付日军侵华的官方政策发生了根本变化,从而为战争搭好了舞台。次年夏,北平近郊爆发了七七卢沟桥事变。特务处工作量大增,其机构大为扩张,到1938年就变成了军统组织。军统的总指挥部在国民党的陪都重庆,其成员多为军统训练班的毕业生,军统已成为蒋介石军事委员会得力的臂膀。军统局聘用了越来越多的军人报务员和情报分析人员,准军事的秘密特工部队均配有美式装备。结拜兄弟之间的习惯用语和古代武士的悲壮气概依然激励着敌后地下特工站英勇奋战。与此同时,重庆总局科层化和专业化的情报分析员和技术人员则认为“义气”之类用语是时代错置。军统局的科层化使工作关系得以正规,但是它并没能取代以往的兄弟义气,也没有改变戴笠的政治文化观念。戴笠给军统内刊题名为《家风》,俨然以家长的身份办理局务,军统组织要求绝对的服从和彻底的献身精神,对个人行为严加约束。他援引《汉书》中的名言“匈奴不灭,何以家为?”禁止部下在抗战时期结婚。他制定纪律严禁吸烟、赌博、打麻将之类的不良行为。违犯内部纪律的人通常被单独关禁闭,而且每年都有不少人因违犯局规遭到处决。这种死刑称之为“殉法”,是一种“殉难”的形式,以确保军统局内部严刑峻法的完整性。(注:《戴雨农先生全集》第1卷,台北,国防部情报局,1979年,第265、266、311、312、319、320页。章君谷:《戴笠的故事》,《传记文学》第14卷第1期,第8至19页。)戴笠要求军统的同志们具备刻苦、坚定、奉献、忍耐这样的品行,他不断提醒他们,加入秘密组织目的是为国家为人民做出特殊的贡献。因此,为了维持军统“家教”的纯洁性,其成员必须随时准备做出完全的牺牲,(注:《戴雨农先生全集》第1卷,第397至405页。《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11卷,第336页。)就像蒋介石亲自领导的力行社“革命战士”那样。戴笠承认他对蒋介石的个人忠诚高于一切。他刻意渲染自己个人忠于领袖蒋介石的绝对重要性。(注:魏大铭:《评述戴雨农先生的事功》,第43、44页。)这样,戴笠就可以要求部下绝对效忠于他。在戴笠看来,军统的任务就是当蒋介石的“耳目手足。”军统局的成员不能有独立思考的想法,必须满足主子的要求,甘为领袖效犬马之劳。(注:《戴雨农先生全集》第1卷,第262、367、368、382、383、398、399页。沈醉、文强编《戴笠其人》,第58、59、149页。)如此强调上下级之间这种垂直的忠诚,也就意味着同志之间横向的手足情义要大打折扣,甚至在特务处内部也是如此。(注:《浮生掠影集》,第53、54页。)虽然家族内的父子之道与兄弟之情在一定的条件下未必相悖,但考虑到像这样一个中国秘密机构的性质,要在垂直的忠诚和横向的义务关系之间摆正轴心的位置自有其重要的含义。忠孝之道,走向极端就会在领导和集体面前彻底抹杀自我。兄弟情义,则允许一定程度的自我判断,乃至于自主。虽然自主未必总是正义感的先决条件,个人献身一项事业是出于自己的判断和决心还是出自义务和责任,其性质是完全不同的。而且,在个人与集体之间的关系上,是允许还是禁止人们在行事时超越领导限定的范围独立思考,其性质也是完全不一样的。戴笠和他的部下所崇奉的观念其潜在的自相矛盾看来是理不清的。
戴笠希望他所标榜的一套既可作为权宜之计,也可充当普遍的原则。他的有些训令直截了当,如“同志们要吃苦耐劳,努力工作。”有些则引经据典,援引历史上的格言。在戴笠所作的许许多多的口号、演讲、典礼、姿态中自有其一以贯之的东西,足以反映出军统局的精神状态。(注: J.J.Linz,"An Authoritarian Regime:Spain,"in Eric Allard and Stein Rokkan,eds,Mass Politics:Studies in Political Sociology,New York:Free Press,1987,pp.281-3.)但是讲话思维习惯于引用历史典故也会导致另一种复杂的情况,历史事件有其特定的背景,往往带有多重含义。借古喻今,其含义有时难以捉摸。经常发生这样的事,戴笠讲话时引经据典,部下却吃不准他的真正意图。正是因为自我抹杀(有时甚至是自我贬斥)戴笠才成功地赢得了蒋介石的完全信任。蒋介石曾要求部下必须甘当革命事业的“无名英雄”。(注:邓元忠:《三民主义力行社史》,台北,世间出版社,1987年,第281至283页。)似非而是的结果是,自我抹杀,乃至于完全丧失自我却使戴笠通过掌有秘密权力,反而为他打开了自我扩张的大道。这种做法所付的代价和所得的补偿都相当大。结拜兄弟之间的行为准则与家规族法的内在矛盾,横向的义气与垂直的忠孝的内在矛盾会导致一种模糊的关系,产生不同的秩序问题。
总之,戴笠是利用这种模糊关系的高手。他是军统局内务的主要仲裁人,他对局规的解释对部下可谓是生死攸关。但是兄弟义气本身对他那种生死予夺的权力也有一定的约束。其约束力体现在戴笠不能为了权宜之计而背信弃义。这就是为什么一方面有充满神秘色彩和英雄主义的刘戈青事件,另一方面又会发生双重或三重的叛逆行为。这一事件使戴笠处理部属行动的能力受到了严峻的考验。
1939年发生在上海的刘戈青事件
刘戈青是军统最成功的刺客之一,他在1939年冬刺杀汉奸陈箓后英名远扬。刺杀陈箓虽非小事,但刘戈青事件的意义更在于他对戴笠的忠贞不渝。刘戈青事件发生之时,军统上海站正被其对手和敌人搞得濒临崩溃,军统特工对组织的忠诚正受到严峻的考验,刘在上海的顶头上司王天木已经叛离组织投奔敌方。与王相反,刘戈青以自己的行动表明了他忠于组织决不动摇。在后来官方所写的军统历史中,刘戈青是间谍和反间谍的黑暗世界里真正的英雄,他是戴笠所称道的仁义之士。刘对戴笠的忠诚就像古代所推崇的游侠之士对结拜兄弟和上司的忠诚。他的作风光大了领袖的风采。在30年代末上海城市战的腥风血雨中,特工们继承侠士遗风,通过历史的传奇,扮演了领袖、信徒、对手、英雄、叛徒这形形式式的角色。
招募刘戈青
刘戈青是一个福建华侨的儿子,家道殷富,他毕业于上海暨南大学,获学士学位。1935年夏,他偶然碰到戴笠,在28岁那年加入了军统。(注:乔家才:《戴笠将军和他的同志》,台北,中外图书出版社,1981年,第1卷,第2至5页。)刘的背景比较特殊,因为在抗日战争开始之前,军统局内几乎没有大学毕业生。(注:《戴雨农先生全集》,第1卷,第22页。)军统官员大多受过传统教育,他们来自一些省份,那里与发生在大城市的五四运动相当隔阂。戴笠曾就读于浙江第一师范,1919年前,一师的课程还是传统的文史科目。从上层到中层,军统的官员从小读的都是经史之学。传统的通俗文化赞美战国时刺客,歌颂三国时的英雄,他们便是在这种文化氛围中长大的。(注:邓元忠:《三民主义力行社史》,第61至71页。)军统参谋官戴经元(译音Dai jingyuan)1940年在南京刺杀汪精卫未遂。人们看到他常与朋友一起饮酒,为国难而扼腕叹息。他会大吼道:“荆轲、聂政今何在?拨乱反正,攘除奸凶,所托何人?”(注:《戴雨农先生全集》,第1卷,第117页。)1939年,军统香港站的联络员袁连楚(译音Yuan Lianchu)在上海被日本宪兵逮捕后在牢中写道:“易水空自流,侠士无限愁。”(注:《戴雨农先生全集》,第1卷,第107页。)这些都是指《史记》所载的战国时期那段悲壮的历史。
20世纪中国高等教育制度发生急剧的变化,北京和上海的高校入学考试强调英语和数学成绩,这些来自各省“中农”家庭的学生没法与人竞争。他们也看不惯五四一代西化的社会精英,后者鼓吹打破旧习,进行社会革命。像戴笠这样在谍报部门的军官往往沉浸于传统的英雄传奇和历史类比的天地之中,由此派生出他们自己的一套行为规范。在网罗第一线的特工时,戴笠要找的对象是受过国术训练的人,就像《史记》和通俗小说所描述的那种放浪不羁敢做敢为的游侠。(注:魏大铭:《评述戴雨农先生的事功》,第42页。沈醉:《我所知道的戴笠》,见沈醉、文强编《戴笠其人》,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0年,第78页。国防部情报局编《中美合作社史》,台北,国防部情报局,1970年,第15、46、56至60页。)他把功夫大师请到军统局内,作为活生生的典范,就像《江湖奇侠传》(当时在小市民中十分流行的武侠小说)中的英雄豪杰。(注:沈醉:《我所知道的戴笠》,第132、133页。平江不肖生:《江湖奇侠传》,上海,上海书局,1923年。P.Link,Mandarin Ducks and Butterflies:Popular Fiction in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Chinese Cities,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1,p.22.)为了寻找江湖好汉,特务处深入穷乡僻壤,在浙江的山区嵊县和汉水上游的襄阳等地招兵买马。这些地区以穷山恶水土匪游民而出名,流传着武侠豪杰绿林好汉仗义行道的故事。(注:魏大铭:《评述戴雨农先生的事功》,第41-2页。)戴笠在组织特工核心成员时往往注重其出身籍贯,然后工于心计地利用其亲朋好友同学老乡的关系来扩招特工。抗战之前还没开办军统训练班前尤其讲究这种关系。(注:沈醉:《我所知道的戴笠》,第87页。)由于戴笠十分倚重这些亲友老乡关系,他的男女部属主要来自浙江、广东和湖南三大省份。但是这种关系网最终也导致了谍报机构内部的分裂。1946年,戴笠死于飞机失事,在接班人的问题上,军统分裂成浙、粤、湘三大派。(注:魏大铭:《评述戴雨农先生的事功》,第48、49页。《戴雨农先生全集》,第1卷,第8页。文强:《戴笠其人》,第173、174页。)抗战爆发之时,军统的这种基于个人忠诚和特殊关系的团结受到严峻考验。戴笠的部下发现他们不仅要和日本人作战,还得与汉奸汪精卫(1883-1944年)手下过去的国民党弟兄作战。刘戈青的背景与军统中的大多数同僚不同,他既不是黄埔系的,也没有什么老乡关系,从各方面看都不是军统核心圈内的人。可见刘对军统的忠诚不是派系的产物,而是基于他真正地倾心于戴笠所推崇的侠义之道。
刘戈青在行动
1939年2月18日,刘戈青和两个同伴暗杀了“维新”傀儡政府的外交部长陈箓。那天正好是中国的除夕日。陈被杀时正在法租界的寓所内祭祖。刺客开枪,陈箓倒在地毯上,被一阵弹雨射死。为了警告想当汉奸的人,刘戈青留下“签名”,用毛笔在白纸上写道:“共除奸伪,永保华夏。蒋委员长万岁,中华民国万岁!”在陈箓的家属叫来的租界警察抵达之前,刘戈青一行已逃离现场。次日,在上海倾向抗日的报纸头版纷纷用大标题刊登了刺杀事件,称其为重庆政府对汉奸的第二次打击。一家报纸模仿武侠小说中章节标题写道:“汉奸陈箓夜登鬼录,飞快将军从天而降。”(注:乔家才:《戴笠将军和他的同志》,第11、12页。)
刘戈青是奉军统上海站站长王天木的命令行动的,王随后就将情况向重庆的戴笠做了汇报。(注:乔家才:《戴笠将军和他的同志》,第14-至17页。)为了挫败日本与中国达成部分和平的企图,军统展开了系统的活动,威胁要刺杀那些想当汉奸的人。在刘戈青行刺的半年前,军统曾在租界杀死过另一个汉奸高官,这些都是军统这一政策的体现。1938年10月,前大使和内阁部长唐绍仪在租界寓所内被化装成古董商的军统特工用斧头砍死。军统当时得到情报,唐绍仪已被日军情报头子土肥原贤二相中,将出任被占领区的傀儡政府首领。为了将谈判扼杀在萌芽之中,军统便除掉了土肥原看中的候选人。(注:Masui Y.,History of the Trial of Chinese Collaborators,Tokyo:Misuzu Shobo,1977,p.198;金雄白:《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2卷本,香港,春秋杂志社,1965年,第1卷,第62页。黄美真、张云:《汪精卫国民政府成立》,2卷本,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卷,第297页。)军统在这一时期所从事的暗杀活动是有目共睹的。据估计,从1937年8月到1941年10月,戴笠的人在相对安全的上海外国租界进行至少了150起暗杀行动。1941年后两年,伪政权的特务组织再次搞掉了军统上海站。在同一时期,军统特工向日本军官发起过40多次攻击,50多次破坏敌人包括机场和军火库在内的军事设施。(注:陈恭澍:《北国锄奸:英雄无名第一部》,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10页。黄美真、张云:《汪精卫国民政府成立》,第1卷,第297页。)他们的行动极大地鼓舞了重庆的支持者。亲重庆的报纸对每次事件都大加渲染,有关社论把刺客比为替天行道的当代奇侠。
对手
为了报复军统的攻击,日本人就在上海滥杀无辜。军统每次行动过后,日军立刻处决一大批无辜的中国人。处决散播了恐怖气氛,但并不能有效地还击军统的挑战。陈箓被刺事件使日本人感到有必要建立一个相应的特务机构,来保证大汉奸的安全,消灭上海的军统特工,压制上海租界内中国报纸的反日宣传。结果便是汉奸特务组织的产生,该机构以所在地极司非而路“76号”而闻名,创始人是李士群(1907-1943年)。早在1939年2月,李士群和丁默村在土肥原的上海司令部“小东京”谒见土肥原,然后就开始筹办这个汉奸特务组织,他们两人过去都是中统特务(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注:黄美真、张云:《汪精卫国民政府成立》,第1卷,第259-62,267,293页。)丁和李表示可以帮助“召集国民党同志以促进和平进程。”日本人自然乐意有这么一个工具来帮助他们打入似乎难以渗透的中国社会关系网。重庆的特工机构过去巧妙地利用中国相当复杂的个人社会关系,来开展工作。(注:Masui Y.,History of the Trial of Chinese Collaborators,p.198;黄美真、张云:《汪精卫国民政府成立》,第1卷,第298页;晴气庆胤:《我所知道的76号》,《书林》,第4期,第45-8页。)1939年2月10日,日本东京军部批准土肥原关于扶持傀儡特务机构的计划。从3月1日起,丁和李正式开始工作。(注:J.H.Boyle,China and Japan at War,1937-1945:The Politics of Collaboration,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2,pp.238-9.)丁和李同意他们将事先向日本宪兵汇报行动详情。他们也同意每天向日本人作汇报。日本人则提供武器弹药和金钱。6月初,机构设立在上海西区前安徽军阀陈调元将军的寓所。丁和李给房子装上电网铁门,搞得就像一座碉堡,并开始为76号组建“行动”(绑架暗杀)的力量。丁默村和李士群干这一行绝对是高手。两人在20年代是共产党的叛徒,30年代是国民党中统特务。陈果夫、陈立夫兄弟利用其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举足轻重的影响,组成强大的政治派别CC,作为CC情报机构的主要人物丁默村也是1938年蒋介石武汉军事委员会三处主任,与一处(中统)的徐恩曾、二处(军统)的戴笠是同事关系。1938年末,军事委员会重组情报机构,三处被解散,其组织被戴笠的军统接收。机构重组反映了黄埔系与CC派在重庆的权力斗争中占了上风,对蒋介石的抗日政策也不无影响。重组的结果,丁默村自然而然地被解除了职务,他心怀不满,便于1939年春和李士群一起在上海投靠了日本人。(注:黄美真、张云:《汪精卫国民政府成立》,第1卷,第266、267页。)
76号真正的后台老板是李士群,30年代初起,他便活跃在沪宁地区,加入了杜月笙为首的青帮,是青帮小头目季云卿的徒弟。(注:有关青帮和杜月笙可参见Brian G.Martin,The Shanghai Green Gang:Politics and Organized Crime,1919-1937,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6.)李士群富有创业精神,1938年到上海后他便努力组建情报网,准备待价而沽。开始只有他一个人搞情报,他从过去的中统同事那里收买情报。后来他的情报来源扩大到国民党上海支部的中层干部,还有青帮成员。到丁默村抵沪时,李士群已经组成了一个7人核心小组,其成员大多数是前中统和CC派的特务。(注:黄美真、张云:《汪精卫国民政府成立》,第1卷,第262至268、281页。)1939年5月8日,汪精卫带着随从抵达上海。李士群招募以青帮头目吴世宝为首的一帮地痞流氓,由他们确保汪精卫一行在上海的人身安全。(注:黄美真、张云:《汪精卫国民政府成立》,第1卷,第272、276页。)李士群拉拢的人其背景与戴笠的军统干部极为相似。为了宣布76号在租界的存在,李士群采取了一种双重的策略。他要在租界破坏军统组织,将军统最老练的特工招募到自己的麾下。他要利用自己对重庆情报网的了解,以威胁利诱的手段来达到目的。1939年夏秋时节,李士群着手行动。到同年9月,他成功地收买了许多军统要员。(注:黄美真、张云:《汪精卫国民政府成立》,第1卷,第299页。)李对这个结果十分满意,在年末访问东京时,他告诉日本主子他已经破坏了江苏、浙江、安徽、上海和南京地区的全部军统组织,戴笠手下的人不是被他除掉,就是投到他的门下。军统的主要人物如林之江(曾刺杀唐绍仪)、王天木(上海站站长)如今都听他的使唤。他吹嘘76号不仅战胜了蓝衣社的军统特务,也打倒了CC派的中统特务。(注:黄美真、张云:《汪精卫国民政府成立》,第1卷,第286,279、280、294页。)
王天木的叛逃
1939年夏末,李士群向军统上海站发起决定性的攻击。首要目标便是军统上海站站长王天木。李士群的手下光天化日之下在公共租界的商业街南京路绑架了王天木,将他押到极司非而路76号,关了三个星期才释放,关押期间,王受到相当的礼遇。(注:晴气庆胤:《我所知道的76号》,第47、48页。)然而,不久王天木就差点在军统同僚的子弹下丧命。他侥幸逃脱,愤愤不已,怀疑是“老板”戴笠下令除掉自己的。另一个军统人员给王看了所谓戴笠从重庆发来的下令处死王天木的电报,(注:乔家才:《戴笠将军和他的同志》,第11、12页。)这更加深了王的疑心。他气得发抖勃然大怒,大骂戴笠无仁无义,声称从此脱离军统。
1938年3月,戴笠一察觉到李士群开始与自己作对,便孜孜不倦地提醒特工不可背信弃义。(注:《戴雨农先生全集》,第1卷,第551-2页。乔家才:《戴笠将军和他的同志》,第17-18页。)同时,他对部下的举动严加监察,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惟恐部下临阵动摇,叛变倒戈。王天木安然无恙地从被重庆称为“阎王殿”的76号归来,这自然会影响到军统内部对他信任,人们对他的忠诚也产生了深深的怀疑。(注:《戴雨农先生全集》,第1卷,第114页。)这正中李士群的下怀,他精心策划这个局面,迫使戴笠做出两难的选择,这使人想起《三国演义》中的故事。(注:晴气庆胤:《我所知道的76号》,第48页。)李士群和戴笠都熟悉《三国演义》的故事:刘备的结拜兄弟关羽勇武过人,不幸落到对手东汉末代皇帝的丞相曹操手中。曹操对关羽精心款待礼遇备加,但关羽“身在曹营心在汉”,只愿暂时听命于曹操。当他得知刘备的消息后,便挂印封金,冲出曹营,去会大哥兄弟。关羽不顾个人安逸,拒绝高官厚禄,可谓是忠义双全。(注:罗贯中:《三国演义》,香港,中华书局,1970年,第200至203,210至213页。)然而关羽曾苟安曹营毕竟有损英名。他的另一个把兄弟张飞就心存疑窦,关羽只得当着张飞的面,斩杀曹操的追将,用他们的血来证明自己的忠诚。(注:罗贯中:《三国演义》,香港,中华书局,1970年,第225至227页。)在戴笠的特工看来,王天木滞留76号的经历好比当年关羽在曹营,为证明自己的清白,王天木应该去刺杀头号大汉奸汪精卫。但汪精卫的住处戒备森严,刺客无从下手。王刺汪不成是可想而知的,也就不能因此而肯定王的不忠。论江湖义气,首领不应露出一丝怀疑部下不忠迹象,尊重兄弟情义是首领团结部下的纽带,轻易生疑便是对兄弟情义的玷污。《三国演义》中,要求关羽证明自己清白的是小弟张飞而不是大哥刘备。王天木回来后,戴笠如果生疑,就会显得他自己太“小人”,不配忠勇之士的效忠。然而,要有战国和三国时的首领那样用人不疑的气度,对一个20世纪的特务头子来讲风险实在太大,因为他深知今日的江湖义气与古代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语。有意思的是,在台湾情报局所作的戴笠传记中对这件事避而不谈。(注:《戴雨农先生全集》,第1卷,第112页。)如果戴笠下令处死王天木,这就有损于他重视仁义的领导形象。但是,当时王的同僚都怀疑确是戴笠下的命令。可见是戴笠先有负于王,其它军统特工也就认为王的公开倒戈情有可原,(注:乔家才:《戴笠将军和他的同志》,第17至19页。)王天木也是这样来为自己辨白的。
对部下的忠诚与背叛,戴笠在处置时还是相当谨慎的,这从他对王天木和陈明楚两个同时投敌的叛徒的处理中可见一斑。与王天木不同,陈明楚投敌完全是出于自愿。很可能就是陈明楚后来出卖了刘戈青,使刘落到汉奸特务的手中。(注:乔家才:《戴笠将军和他的同志》,第25、26页。《戴雨农先生全集》,第1卷,第114页。)戴笠毫不含糊地下令处死陈明楚。1939年圣诞夜,3个军统特工在上海西区兆丰公园附近的夜总会与陈明楚搭话。时值圣诞夜,一批汪伪的主要支持者带了20个保镖在夜总会的酒吧舞厅里饮酒作乐,军统特工向人群一阵扫射,陈明楚当场毙命,刺客乘混乱,跳上备好的汽车迅速逃逸。王天木是否是这次刺杀的目标尚不清楚,特工开枪时,他正巧离开舞厅。汉奸难免要对他有所怀疑,他被再次带到76号,详加审讯。但不久就被放出来继续为李士群效力。(注:《戴雨农先生全集》,第1卷,第66页;金雄白:《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第1卷,第66页;陈恭澍:《北国锄奸:英雄无名第一部》,第134至136页;乔家才:《戴笠将军和他的同志》,第1卷,第28、29页;《汪逆特工总部内幕》,桂林,国防书店,第12、13页;黄美真、张云:《汪精卫国民政府成立》,第1卷,第287页。)与此同时,作为对陈明楚之死的报复,76号在1939年圣诞日,将被他们关押的3名军统成员拖到大院里实施枪决。(注:陈恭澍:《北国锄奸:英雄无名第一部》,第262-3页。)在1939到1940年期间戴笠所处罚的军统叛徒中,陈明楚夜总会被杀是比较典型的事例。李士群阴谋引诱军统要员倒戈之时,戴笠也开始加紧严惩汉奸。刺杀事件引起报复,不久两个特务帮派之间的争斗在上海激化成一场全面的城市战。1939年秋,李士群声称端掉了军统上海站。而军统方面也声称干掉了十多个傀儡特务机构中的要人。(注:金雄白:《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第1卷,第64页。)李士群的部下就将目标对准那些忠于蒋介石的社会名流和抗日积极分子。上海亲重庆的报纸编辑和记者是他们攻击的首要目标。这些人被迫闭门关窗转入地下,以避免恐怖分子的攻击。与重庆有关联的银行收到了邮包炸弹和手榴弹。(注:参见叶文心编《战时上海——中日冲突,1937-1945》,第一章。)谣诼纷起,说什么伪政权的特务机构有一张黑名单,上面包括100多名上海的教育工作者、作家、出版商、记者、金融家、企业家、法学家。这一时期,上海市民中不少头面人物在街头遭到伏击和枪杀,沪江大学的校长刘湛恩就是其中之一。(注:金雄白:《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第1卷,第66至80页;黄美真、张云:《汪精卫国民政府成立》,第1卷,第294页。)
虽然军统特工在上海街头英勇抗战,打击了汉奸分子,但是军统在敌后各大城市的情报点却遭受了1937年抗战以来最大的损失。(注:《戴雨农先生全集》,第1卷,第105、106页。)军统上海站的叛徒把该地区特工名录、地址和组织联络图都交给了日本宪兵。日本宪兵和公共租界与法租界的特务一起紧急搜捕了军统13个办公点和藏身处。更有甚者,上海的军统叛徒陈明楚曾负责军统南京站的人事安排,他向日本提供的情报极为精确,涉及面也很广。1939年8月12日,军统安庆站站长蔡胜楚(译音Cai shenchu)在南京被捕,遭到严刑拷打。8月19日,军统南京站的办公点和藏身处遭到袭击。南京站副站长谭闻知(译音Tan wenzhi)答应与敌人配合。9月11日,军统在南京的秘密电台落到敌人手中。王天木在北平和天津有不少老关系,日本宪兵根据他提供的情报在华北展开大搜捕。9月27日,军统在天津地区27岁的负责人曾澈在天津大街上被认出,随即被捕。次日上午,在英法租界警察的帮助下,日本宪兵袭击了军统在天津的办公点和藏身处,抓获了不少特工,其中有41岁的天津站负责人陈资一。曾、陈两人马上就被枪决了。王天木在上海的叛变促使青岛站的军统头目赵刚义起而效尤。赵曾在办理军统局务时在上海与王有过合作。11月15日,赵刚义带领日本宪兵在青岛大肆搜捕。军统青岛站的代理站长交出了特工名单、地址和电台。1939年11月24日,军统在北平的办公处和电台陷入敌手,副区长周世光被捕,随即遭到枪杀。(注:《戴雨农先生全集》,第1卷,第106至109页。陈恭澍:《上海抗日敌后行动》,台北,正中书局,1984年,第127页;乔家才:《戴笠将军和他的同志》,第1卷,第103页。)从北平地区办公处军统特务那里索取的情报使日本宪兵对张家口、察哈尔、绥远、丹东、内蒙等地进行了系统的搜捕,国民党情报员、积极分子、游击队长纷纷入网,电台被毁。(注:乔家才:《戴笠将军和他的同志》,第1卷,第95至97,103、104,107、108页。)王天木和戴笠之间的猜疑导致了王的叛变,到太平洋战争爆发,由此引起的雪球效应几乎使军统在敌后的情报体系毁灭殆尽。
忠义的语言和戏剧
在这个时期,刘戈青被李士群抓进了极司非而路76号。就像曾对王天木那样,李对刘戈青可谓是礼遇备加。刘被捕的当晚,就允许他和同志联络。李士群还允许刘戈青的女朋友陆谛进来陪他。陆谛过去曾为刘送信并照顾过他。戴笠的传记上写道,李士群摆出一副“君子”风度,表示他对英雄好汉的宽宏大量。(注:《戴雨农先生全集》,第1卷,第114页。)他甚至答应刘戈青可以会见来客,保证客人来去自由。刘的两个朋友包天擎(刘的私交)和朱山猿(刘的军统同事)得到消息便马上来到极司非而路76号,探视朋友。戴笠写道:“在落难之际,同志间的这种牢不可破的友谊连李士群这样的人也不得不为之佩服。”(注:《戴雨农先生全集》,第1卷,第502页。)刘戈青请朱山猿带个条子给戴笠,发誓在任何情况下决不会为个人安危而改变对戴笠的忠诚。(注:乔家才:《戴笠将军和他的同志》,第1卷,第23、24页。)1940年1月10日,戴笠下令将刘的字条当作教材来教育各种训练班的学员。刘坚决拒绝投降,朱山猿身入险境看望朋友,戴笠把这种行为称之为“我们集体的侠义之举,我们将为之自豪。”戴笠评论道:这是对军统和同志的一片赤胆忠心,这种大义凛然的精神连李士群这等叛逆也为之感动。(注:《戴雨农先生全集》,第1卷,第502页。)
戴笠尤其赞赏刘戈青在这关键时刻所体现的忠诚,因为当时正值王天木叛变不久。王天木毕竟还是“十人团”的元老之一。王的两个女儿与戴笠的独子关系很好,两家甚至曾打算要结儿女亲。(注:陈恭澍:《上海抗日敌后行动》,第6页。)按照上海站后继者的说法,王的叛变不仅使军统在敌后的地下组织遭到毁灭性打击,更使得同僚间的相互信任荡然无存。(注:陈恭澍:《上海抗日敌后行动》,第8页。)王天木这个核心人物的叛变使军统局为之震惊,刘戈青出于对戴笠个人的仰慕而刚刚加入军统,他的忠贞不渝显得尤为难能可贵。但是,有些军统成员反对将地下情报战的惨败归咎于一个心怀不满的老特务的叛变。在陈恭澍(上海站新站长,曾任江苏地区的联络官)这样老练的特工看来,有足够的线索表明存在着为人不知的谜团。陈后来回忆道:“虽然只有两三个人叛逃,但是出卖行为却是空前的。我们面对着极为复杂难解的形势……会不会是反间谍部门精心策划旨在长远的韬晦之计,天木只不过是这场悲剧中的一个主角?”(注:陈恭澍:《上海抗日敌后行动》,第9、10页。)戴笠是否参预其中,心照不宣地任凭部下流血牺牲?他是否将自己的真实意图瞒着上司?他是否会策划如此残忍的阴谋而置仁义于不顾呢?李士群将王天木和刘戈青尊为“上宾”,表明他赏识真正的英雄,是一个值得英雄好汉为之效劳的仁义之人。他效法《三国演义》中曹操款待关羽的做法,对刘戈青礼遇有加,而且在刘被76号关押6个月后,还让刘最终在南京成功地“越狱逃跑”,也可能是“释放”。(注:乔家才:《戴笠将军和他的同志》,第1卷,第31至34页。)1940年初,刘戈青回到重庆。戴笠把他当作大英雄来欢迎,在军统总部为刘大摆宴席。(注:乔家才:《戴笠将军和他的同志》,第1卷,第1页。)军统内部有人写诗将刘的行为与荆轲相比,刘携带着女友安然归末更使人们想起战国时范蠡告别越王,带着绝世美女西施泛舟五湖的逸事。有一首诗将刘的归来比作范蠡退隐,“居然匕首戮神奸,易水重歌壮士还。载得西施仍许国,肯随范蠡五湖间。”(注:乔家才:《戴笠将军和他的同志》,第1卷,第35页。)戴笠似乎对刘戈青的忠诚没有丝毫的怀疑,刘戈青也对戴笠坦诚相见。他要求戴笠允许他给敌酋李士群寄一封信,戴笠慨然允诺。刘在信中将李誉为“天涯知遇,至感平生……自当图报于他日。”戴笠颔笑置之,由于军统局禁止重庆与敌占区通信,他破例安排人将这封给汉奸特务头子的信带到香港转寄。(注:乔家才:《戴笠将军和他的同志》,第1卷,第34页。)
结论
当戴笠这位军统家族的首领容忍了有可能危及垂直忠诚的横向义气时,他所获匪浅。《三国演义》中,关羽最后在华容道知恩报义高抬贵手放走曹操。(注:罗贯中:《三国演义》,第400、401页。)戴笠当然也不能对仁义这类话语的份量置之不顾。他的组织成员便是在这种英雄史诗般的文化背景下出来的,历史小说中所推崇的为人准则,也是他们在实际生活中的行为规范。戴笠看重仁义这类象征性词语,最终他也不得不面对历史的重演。戴笠对刘戈青的事情大加渲染,目的是向人们表明他就像古代的明主贤相,能赢得忠义之士的拥戴。只有一个仁至义尽的首领才会如此宽宏大量,允许部下与自己的仇敌共叙友情。戴笠没让自己的忌心阻碍刘戈青与朋友的交往,这种姿态有助于加强人们的信念,即可以向人们表明,王天木的叛逃并没有动摇军统内部上下级之间的忠信。军统在敌后的实力可谓是损失惨重,由于错误、出卖、失算,许多人牺牲子自己的生命,另外一些人受到严刑拷打,被投入大牢。乔家才曾继任为军统北京站负责人,还当过军统华北各站的督察员、重庆军统内部纪律督察员。1939年秋,他回到河北老家,发现妻子因上吊自杀未遂,喉头留下了一条很深的疤。她已经精神失常,都认不出他了。这是因为日本宪兵怀疑乔的身份,抓住他的妻子严刑审讯的结果。(注:乔家才:《浩然记》,台北,中外图书出版社,1981年,第3卷,第129、130,135至137页。)在王天木叛逃后继任上海站站长的陈恭澍也曾于1941年10月被捕。4年后,他仍不敢相信自己是怎样熬过这场大劫的,“时至今日,听到敲门声,我的心就会怦然而动。听到电话铃响,肌肉就会不停地抽搐。”(注:陈恭澍:《北国锄奸:英雄无名第一部》,第22页。)
戴笠告诉他的部下,军统的历史是用同志们的血汗和泪水写成的。重要的是,死亡临头之时,要甘为事业献出自己的生命。他把军统局比作一个大家庭,满口仁义道德,以传统伦理来团结特工。戴笠向死亡的军统特工的父母支付丧葬费,照顾他们的孤儿寡妻,送他们的孩子上学。戴笠有意把他创办的军统办成一个仁慈的机构,同志们为组织付出血汗泪水,组织也将以德相报。但是,戴笠为这家长式的集体中所塑造的英雄形象不是浪漫的侠士,而是无名英雄,这将有助于加强上下级的垂直关系而不是个人之间的横向联系。无名英雄坚持“纯正的家族传统”,将忠于“国民革命的理想,而不计个人名利得失。”戴笠声称军统将“继续孙中山和革命烈士未竟的事业。”为了继承革命事业,他和部下庄严地表示“在清除一切私心杂念,甘当无名英雄。”(注:《戴雨农先生全集》,第1卷,第409、410页。)“古人云:一将功成万骨枯。”戴笠对部下说:“千百万无名英雄的牺牲才换来历史短暂的辉煌……历史记载丰功伟绩,白纸黑字一目了然……你我的历史地位在于为这些丰功伟绩作出无声的贡献。我们为其他人的成就作辅垫,我们是无名英雄。”(注:《戴雨农先生全集》,第1卷,第409、410页。)戴笠继续说,无名英雄就要随时准备作出牺牲。他们是坚韧不拔忍辱负重的典范。(注:《戴雨农先生全集》,第1卷,第401页。)他们是领袖的工具,而只有领袖才能创造伟业名留青史。(注:《戴雨农先生全集》,第1卷,第399页。)戴笠树在重庆军统局后面山坡上的石碑就是献给无名英雄的,碑的两面一字不刻。这座石碑集中体现了戴笠军统组织氛围内的主要矛盾:要求个人通过家族式的组织关系来追随先辈,继承遗志,求得不朽。而这一切都是抽象的,非个人化的。它既需要英雄偶像,强调个人牺牲,但又完全缺乏历史上游侠所必备的自主和勇猛。
戴笠要求个人放弃独立思考,乃至放弃个人的道德自主,他所谓的符合特务组织要求的无名英雄归根到底就是充当领袖的驯服工具。然而,这与特工们所推崇的历史传奇中的游侠精神相抵触。军统成为正式的情报组织后,作为这个秘密组织核心的兄弟之道仍然很有市场,戴笠也非常想利用这一点来笼络人心。但是,在赞美传奇式的英雄和无名英雄时,戴笠混淆了两者的目的。他想利用这两种象征,任意上下其手。虽然他常常不得不对这些文化象征强有力的制约屈服,为了自己的利益,他还是尽可能地利用其中的矛盾和含糊之处。他的部下也多少看出他的口是心非。尽管他们公开声称敬佩戴笠的人格,却也在不停地揣摩他的阴暗心理。戴笠不是中国的希姆莱:他的所作所为颇具象征性,那是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铸就的产物。但他也根本不是一个仁至义尽的儒将,并不是某些崇拜者后来所想描绘的那种形象。戴笠公开声称推崇仁义之道,又对由此产生的矛盾巧加利用。他的内心深处是个异常矛盾的世界,其阴暗面也存在着迫害和出卖这类可怖的可能性。戴笠的部下后来把军统美化成一个英雄辈出的世界,把自己描绘成保国安民奋勇抗战的当代奇侠。为了表明他们对其理想化的首领的忠诚,他们把戴笠描绘成“一家之长”。这种企图使这些圣徒传的作者把自己放到了小说家的范畴。道义上的暖昧不清是戴笠操纵军统的关键所在,刻意美化终究是徒劳的。
译者附记:本文译自叶文心编《Wartime Shanghai:Sino-Japanese Conflict,1937-1945,Routledge 1998》。受资料限制,文中个别人名、地名的译音复原为中文时采取音译的方法,特此说明。
标签:抗日战争论文; 李士群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1939年论文; 历史论文; 台湾国民党论文; 蒋介石论文; 戴笠论文; 汪精卫论文; 刘戈青论文; 国民党论文; 世界大战论文; 太平洋战争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