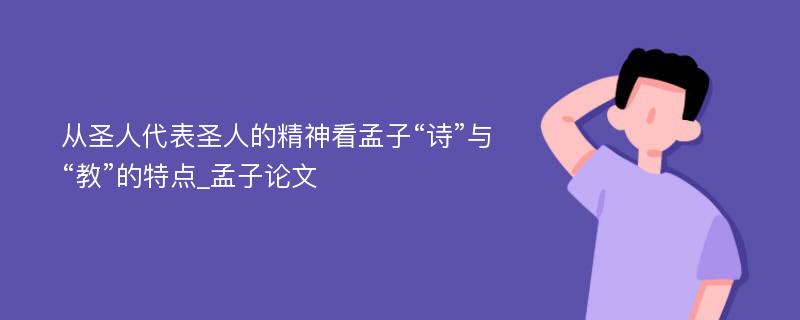
代圣人立心——孟子“《诗》教”的特征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孟子论文,圣人论文,特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诗》教”自孔子创立遂成为儒家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孔子将“诗三百”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化典籍,充分肯定了它在思想道德、文化传统等各个方面的教育教化功能。在此基础上,儒家的“亚圣”孟子进一步将“《诗》教”提升到代圣人立其心的高度,并提出了“以意逆志”“知人论世”等意蕴深长的“《诗》教”方法论,不但使先秦儒家“《诗》教”发展到一个新境界,而且为“《诗》教”的进一步发展开辟了道路。
一
孟子“《诗》教”代圣人立心的特点,首先表现为它以学为圣贤作为“《诗》教”的目标。
孟子将历史上的教育活动概括为人伦之教,他说:“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1]上古三代的学校虽名称有别,但“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1]在他看来,所谓“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人伦教育意义重大,如果社会上人人都能行仁义,恪守既定的伦理规范,那么这个社会也就能够成为太平的治世了。生活在战国时代的孟子希望通过倡导“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1]的人伦教育,使社会从新走上安定而秩序化的轨道。但是,现实社会去圣久远,怎样才能推广这样的人伦教育呢?孟子的做法,就是将弘扬仁义之道的人伦教育具体化为学为圣贤的教育。孟子认为,历史上的人伦之教为“圣人”所施,圣人,即尧、舜、禹、汤、周公、孔子这样的人,他们“出乎其类,拔乎其萃”,(注:《虞东学诗·迹熄诗亡说》曰:“洎乎东迁,而天子不省方,诸侯不入觐,庆让不行,而陈诗之典废,所谓‘迹熄而诗亡’也。”语出清·焦循.《孟子正义》)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1]同时,他们“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1],所以,他们既是人伦教育的主体,也是人伦教育的理想,因此孟子说:“圣人,人伦之至也。”[1]其中,孟子特别推崇孔子,认为他是圣贤中之“集大成者”[1],所谓“出于其类,拔乎其萃,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并明确表示:“乃所愿,则学孔子也。”[1]既然教育的根本目的是“明人伦”,圣人又是人伦的最高境界,那么求学受教所追求的,就应该是学为圣贤。
孟子的性善论为他学为圣贤的教育目标奠定了理论基础。孟子所谓之性善,是说人人具有与生俱来的“善端”。孟子所谓之善性,对群体而言,是人人都要自觉恪守伦理道德规范;对个体来说,是具有“大丈夫”的品格和意志。所以,教育的过程是将“善端”培养为成熟的善性的过程,是体认、实践伦理规范并完善人格的过程。在这个逻辑前提下,孟子指出,圣贤的境界是可以实现的。他认为“人皆可以为尧舜”[1],“圣人与我同类者”[1]。因为“尧舜之道,孝悌而已矣”[1]。所不同之处在于“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1]。所以,“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觉后知,使先觉觉后觉也”[1]。
以学为圣贤作为教育教化的基本目的,“《诗》教”的经典意义与价值就得到了明确和提升。
关于“诗三百”的价值,孟子曾说:“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1]赵岐在《孟子注》中解释说:“王者,谓圣王也。太平道衰,王迹止熄,颂声不作,故《诗》亡。”这是因为,在儒家的传统观念中,诗与政教有着内在的统一性。
“诗言志”在先秦是带有普遍性的认识,据朱自清先生考证,“这种志,这种怀抱,其实是与政教分不开的,非关修身,即关治国”[2]。而二者之间的统一性在于:“其哀心感者,其声噍以杀;其乐心感者,其啴以缓。”[3]《毛诗序》亦有言曰: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对此,孔颖达作疏曰:“治世之政教和顺民心,民安其化,所以喜乐,述其安乐之心而作歌,故治世之音亦安以乐也。”“乱世之政教与民心乖戾,民怨其政教,所以忿怒,述其怨怒之心而作歌,故乱世之音亦怨以怒也”。“国将灭亡,民遭困厄,哀伤己身,思慕明世,述其哀思之心而作歌,故亡国之音亦哀以思也”。“诗述民志,乐歌民诗,故时政善恶见于音也。治世谓天下和平,乱世谓兵革不息,亡国谓国之将亡也。乱世谓世乱而国存,故以世言之。亡国则国亡而世绝,故不言世也。乱世言政,亡国不言政者,民困必政暴,举其民困为甚辞,故不言政也。亡国者,国实未亡,观其歌咏,知其必亡,故谓之亡国耳,非已亡也。若其已亡,则无复作诗,不得有亡国之音。”[4]
在孟子的观念里,“诗三百”的经典意义就在于圣贤以诗喻后世以人生大道。若以圣贤人格塑造人,《诗》则能够以其独具的特性发挥无可替代的作用。
二
从《孟子》中有关“《诗》教”的内容来看,他以“温柔敦厚”作为“《诗》教”的目标,以“诗三百”有关圣贤人格的内容为“《诗》教”之源,以读者对圣贤人格的感悟为“《诗》教”的基本途径,从而使他的“《诗》教”在教学论的层面上也体现出代圣人立心的特色。
(一)“温柔敦厚”——实践“《诗》教”的本质意义
《礼记·经解》云:“入其国,其教可知矣。温柔敦厚,《诗》教也。”这是先秦有关“《诗》教”的经典性的定义。据孔颖达注疏曰:“温,谓颜色温润;柔,谓情性和柔。《诗》依违讽谏不指切事情,故云‘温柔敦厚’,是《诗》教也。”[3]意思是说,观一国之民性,即可知其教化。如果百姓性情柔和,待人接物态度温厚,说明是深受《诗》之教化的缘故。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诗》教”的宗旨在于化民之品格。
“《诗》教”的核心目的是教人养成温柔敦厚的品性,它的理论基础,则在于合乎中庸之道。《礼记·中庸》云:“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是人所固有的一般意义上的本性,按孟子的说法,就是“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1]。“和”是指当人性在现实中展开后,能够合乎礼义道德规范。所以说,“《诗》教”在学为圣贤的人伦教育中,发挥着教化人性的作用。温柔敦厚,正是圣贤人格博大胸怀的反映。在“《诗》教”中,受教育者要以温柔敦厚作为修养原则,不断地学习圣贤之道。
这个教化过程,不是法家金刚怒目的强制过程,而是通过熏陶习染使受教育者日渐心向往之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诗》教”以其比兴讽喻的特点而发挥了独特的作用,所以孔子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5]
然而,现实生活是纷繁复杂的,真正能够以礼义道德为旨归,做到言行不逾矩,需要大智慧。为此,孟子在“《诗》教”中作出了很大努力。他引导学生深入探求诗歌主体的精神世界,体会古圣贤王的博大胸怀、崇高境界。例如《孟子·万章上》记载:
万章问曰:“《诗》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信斯言也,宜莫如舜。舜之不告而娶,何也?”孟子曰:“告则不得娶。男女居室,人之大伦也。如告,则废人之大伦以怼父母,是以不告也。”[1]
表面上,舜“不告而娶”有违娶妻必告父母的规范,与他的圣人形象有矛盾。而孟子则引导学生进行更为深入的分析:“舜父顽母嚣,常欲害舜。告则不听其娶,是废人之大伦,以怨怼于父母也。”[1]告而不得娶,就更违背了人伦的大节,因此,两害相权取其轻,只好不告而娶。这样一番分析,就可以令学诗者更加深刻地体会到何为仁义之道,以及圣贤何以为理想化的人物。
(二)“王者之迹熄而《诗》亡”——选择“《诗》教”的典型内容
就《诗》的特点和发展历史,孟子说过“王者之迹熄而《诗》亡”的话[1]。虽然至今人们对这句话仍有不同的理解[6],但从孟子的思想逻辑来看,“王者之迹”当是指古圣贤王的仁政德化之道,也即传统意义上与“霸道”相对而言的“王道”;“《诗》亡”则是就《诗》昭示王道的功能日益衰落来说的。因此,历代的阐释中比较合理的有两种:一是以朱熹为代表,将“王者之迹”解释为伦理道德规范。“《诗》亡”是指“诗三百”所蕴含的精神由以“二雅”为代表的对王道的歌颂,变而为以《黍离》为代表的离乱之伤[7]。二是以清代学者为典型,将“王道”坐实为西周的政策措施,包括“采诗”之风,“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变为“礼乐征伐自诸侯出”,“采诗”风衰,王道不振(注:《虞东学诗·迹熄诗亡说》曰:“洎乎东迁,而天子不省方,诸侯不入觐,庆让不行,而陈诗之典废,所谓‘迹熄而诗亡’也。”语出清·焦循.《孟子正义》)。总而言之,孟子是以“王道”作为选择“《诗》教”内容的标准的。
首先,从《孟子》对风、雅、颂的选取比例来看,取《鲁颂》2次,各一首;《商颂》1次,一首;引自《大雅》者20次,凡15首;引自《小雅》4次,各一首;引《国风》3次,各一首。师生论诗,涉及《小雅》二首,《国风》三首(注:《孟子》七章共引.诗.26次,凡30首;论诗3次,涉及诗5首。其中,只有6首取自“国风”,分别是《豳风·鸱鸮》《豳风·七月》《邶风·柏舟》《邶风·凯风》《齐风·南山》《魏风·伐檀》徐复观先生在长篇论文《中国经学史的基础》中提到《孟子》“引《国风》者仅四次,二次出自他的学生”,但在注释中说“此处所列数字,恐稍有遗漏”.所遗者,为《七月》和《伐檀》,分别见于《滕文公上》“民事不可缓”章和《尽心上》与公孙丑论“不素餐兮”一节)。显然,反映西周王道的《大雅》是孟子引《诗》的主要来源。
其次,从《孟子》涉及的《诗》之章句来看,也可略见一斑。《孟子》所引的诗句,大体可分为三类:
第一,记载古圣贤王躬行仁义的事迹。《孟子·梁惠王上》“孟子见梁惠王”一节中,孟子引了《诗·大雅·灵台》的诗句来论证“贤者而后乐此”的道理:“《诗》云:‘经始灵台,经之营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经始勿亟,庶民子来。王在灵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鸟鹤鹤。王在灵沼,于鱼跃。’文王以民力为台为沼,而民欢乐之,谓其台曰灵台,谓其沼曰灵沼,乐其有麋鹿鱼鳖。古之人与民偕乐,故能乐也。”[1]诗章所描写的欣欣向荣的社会生活景象烘托了文王与民同乐的巨大价值,因此,对这一段诗章的引用不但有力地支持了孟子与民同乐的思想,也使讨论、教化的对象感受到古代圣贤博大的精神境界,激发他们的向往之情。
第二,概括古圣贤王施行仁政的方针。孟子用于“《诗》教”的诗句中,有一些是直接反映社会伦理规范的,像“周虽旧邦,其命惟新”。“周道如底,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视”。孟子以之作为分析评价现实的标准,同时也就是在传递一种价值取向和行为准则。
第三,反映古圣贤王修、齐、治、平的处世原则。像“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永言孝思,孝思惟则”,都是较为典型的例子。孟子对这类诗句的引用,多是结合具体事件或情境,使后学者能够更深刻地领悟行王道的内涵与策略。
(三)“以意逆志”——实施“《诗》教”的基本策略
“以意逆志”出于《孟子·万章上》,是孟子“《诗》教”最主要的方法论:
咸丘蒙曰:“……《诗》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而舜既为天子矣,敢问瞽瞍之非臣如何?”曰:“是诗也,非是之谓也;劳于王事而不得养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独贤劳也。’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如以辞而已矣,《云汉》之诗曰:‘周余黎民,靡有孑遗。’信斯言也,是周无遗民也。孝子之至,莫大乎尊亲。尊亲之至,莫大乎以天下养。为天子父,尊之至也。以天下养,养之至也。诗曰:‘永言孝思,孝思惟则。’此之谓也。”[1]
在这里,孟子指出,读诗既要由辞句入手,又不能因片面地或表面化地理解辞句,蒙蔽了对诗歌主旨的把握。学《诗》的关键,是探求诗人之“志”。
传统意义上的“志”不是一般的思想感情。闻一多先生曾说:“志有三个意义:一、记忆;二、记录;三、怀抱。”朱自清先生进一步推断:“到了‘诗言志’和‘诗以言志’这两句话,‘志’已经指”怀抱’了。”“这种怀抱,其实是与政教分不开的。”[2]所以说,“以意逆志”是要求读者以自己对伦理道德的认识与圣贤之“志”相比照,从而更深入地体会圣贤人格的境界,探究其实践策略。
孟子的“以意逆志”,特别强调读者要通过对诗歌的涵咏达到对意义的体悟,这是十分值得我们深入研究的。例如:
公孙丑问曰:“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诗也。’”孟子曰:“何以言之?”曰:“怨。”曰:“固哉!高叟之为诗也。有人于此,越人关弓而射之,则己谈笑而道之,无他,疏之也。其兄关弓而射之,则己垂涕泣而道之,无他,戚之也。《小弁》之怨,亲亲也。亲亲,仁也。固矣夫,高叟之为诗也。”曰:“《凯风》何以不怨?”曰:“《凯风》,亲之过小者也。《小弁》,亲之过大者也。亲之过大而不怨,是愈疏也。亲之过小而怨,是不可矾也。愈疏,不孝也。不可矶,亦不孝也。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1]
那么,读者之“意”与诗歌之“志”如何相“逆”呢?在此,孟子提出了“知人论世”的原则:
一乡之善士,斯友一乡之善士。一国之善士,斯友一国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以友天下之善士为未足,又尚论古之人。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1]
正所谓“不问其世为何世,人为何人,而徒吟哦上下,去来推之。问其所逆,乃在文辞而非志也,此正孟子所谓害志者”[8]。只有深入分析古代圣贤在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的思想和行为,才能真正理解并揭示出其“出于其类,拔乎其萃”之处,从而得到借鉴譬喻之教;只有体悟到圣人以何为道、何以为道的境界,才能称得上以圣人为友。这便是孟子所谓“善教”——得民者,得其心也;如能使百姓心怀仁义,向往圣贤,则化民成俗也好,治世安民也好,就变得易如反掌了。
三
孟子“《诗》教”观的形成,是与他的历史观念和《诗》学观念有直接联系的。
(一)圣贤救世的历史观
圣人,最初是指聪明人,例如《尚书·洪范》云:“聪作谋,睿作圣。”传云:“于事无不通谓之圣。”春秋后,圣人的内涵逐渐变得崇高神圣[9],特别是在儒家学者的观念中,圣贤人格成为最合乎道德规范的理想人格,圣人的事业就是理想的政治。而孟子正是这一思想的典型代表。他不但指出圣人是“人伦之至”,而且系统阐发了“圣贤救世”的历史观:
当尧之时,水逆行,泛滥于中国,龙蛇居之,民无所定;下者为巢,上者为营窟。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驱蛇龙而放之菹。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汉是也。险阻既远,鸟兽之害人者消,然后人得平土而居之。尧、舜既殁,圣人之道衰,暴君代作。坏宫室以为污池,民无所安息;弃田以为园囿,使民不得衣食;邪说暴行又作。园囿污池,沛泽多而禽兽至。及纣之身,天下又大乱。周公相武王,诛纣伐奄,三年讨其君,驱飞廉于海隅而戮之;灭国者五十;驱虎豹犀象而远之:天下大悦。世袁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1]
在孟子看来,历史就是圣贤之道在现实中的展开。这颇具儒家道统色彩的历史观反映了他对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即圣贤以仁德王天下、以行仁政创历史。
因此,“诗三百”作为“王道之迹”的反映进入到孟子的教育视野,自然要发挥以圣贤为教的功能。
(二)习染于“诗言志”的传统,对“赋诗断章”之风加以修正
孟子以“《诗》教”作为实践其教育理想的重要内容,与他对“诗言志”传统的继承、发展也有直接关系。
《尚书·舜典》云:“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也有“诗以言志”的话。如前所论,《诗》之“志”不是一般的思想感情,而是关乎社会政治与道德教化的追求。因为“《诗》以言志”,所以学《诗》是优入圣域最好的途径。以《诗》为教,重心也应该放在体悟圣心上。
那么,战国时出现的“赋诗断章”现象是不是“《诗》言志”传统的失落呢?
“赋诗断章”出自《左传·襄公二十八年》:
齐庆封好田而耆酒,与庆舍政,则以其内实迁于卢蒲癸氏,易内而饮酒。数日,国迁朝焉。使诸亡人得贱者,以告而反之,故反卢蒲癸。癸臣子之,有宠,妻之。庆舍之士谓卢蒲癸曰:“男女辨姓,予不辟宗,何也?”曰:“宗不余辟,余独焉辟之?赋诗断章,余取所求焉,恶识宗?”癸言王何而反之,二人皆嬖,使执寝戈而先后之。[10]
根据这段史料,人们基本上都将“赋诗断章”理解为根据主体的需要断章取义地用《诗》。但是,《左传·定公九年》又有云:
苟有可以加于国家者,弃其邪可也。《静女》之三章,取彤管焉。《竿旄》“何以告之”,取其忠也。故用其道,不弃其人。《诗》云:“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思其人,犹爱其树,况用其道而不恤其人乎![10]
以“苟有可以加于国家者”为标准反观《左传》引《诗》、用《诗》的情况,则可以看出,“赋诗断章”并非尽可以随自己的意思断章取义地用诗,而是要以言“志”为准则。例如,《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记载的“季札观乐”,就表现出当时是以反映王政德化的水平作为《诗》的鉴赏标准的。又如《左传·襄公二十七年》记载的赵孟请七子赋诗以观志,都是围绕家国天下的主题。像伯有赋《鹑之贲贲》,是偏离了这一主题的,于是就受到指责。类似的还有《左传·昭公十二年》“宋华定来聘”,也是由于未能理解赋诗者关乎政教的深意而遭到指责的例子。
所以说,“赋诗断章”作为诗之为用的一种新方式,并未脱离“《诗》言志”的传统。但是,就当时的情况来看,应该说它扭曲了这一传统。
诗是人类的表达与所表达最完美的结合,对此的割裂预示着危险的倾向,所以孟子在“诗言志”的基础上强调“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促进了儒家“《诗》教”的正常发展——在面对社会生活的新变化时,既要坚持自身伦理教化的本质,也要使它在新的解读方法论中不断得到新生。
人是在文化的继承与创新中追求着自我的价值。在这个过程中,教育的责任不仅是传授知识和技术,更重要的是要让受教育者心怀理想地生活,有智慧地生活。这是孟子的“《诗》教”观念给予我们的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