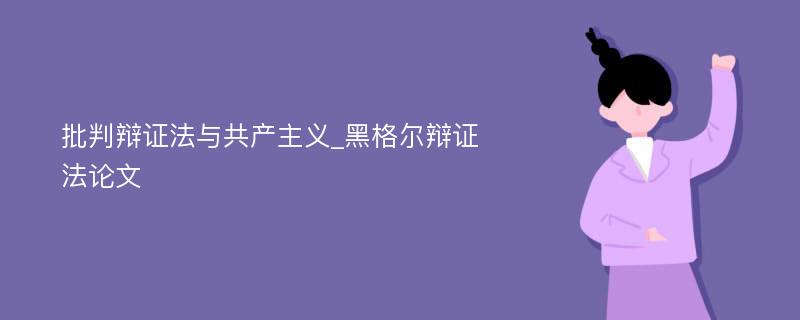
批判的辩证法与共产主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辩证法论文,共产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1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8862(2013)07-0026-06
“共产主义”是马克思全部思想中最有魅力的概念之一。近年来,西方一些激进左派思想家主张放弃社会主义,重回共产主义。“共产主义的回归”成了当今一些左派用来标榜自己激进立场的新政治话语。西方右派的思想家们则将20世纪共产主义政治体制的命运等同于马克思思想的失败,因而宣告“历史的终结”的到来。无论左派还是右派,都将关注点聚焦于“共产主义”,“共产主义”逐渐成为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一个关键问题。如果我们要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合法性辩护,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尤其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就必须重新审视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概念。而这种重新认识必须在一种更新了的、对于马克思思想的后苏联式的理解中展开。这就要求我们理解马克思主义社会批判的辩证法,既要立足于马克思的经典文本,又要立足于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在双重视域中推进对共产主义的理解。
关于共产主义,罗素从辩证法的视角对马克思提出了一个质疑和诘难。罗素认为,“黑格尔是以普鲁士国家来结束他对历史的辩证叙述的。按照黑格尔的说法,普鲁士国家就是绝对观念的完美体现。对于普鲁士国家毫无感情的马克思,把这种说法看作是一种站不住脚的和软弱无力的结论。他说,辩证法在本质上应该是革命的,似乎暗示辩证法不可能达到任何最后的静止状态。然而我们却没有听说共产主义建立之后还要再发生什么革命”。①根据罗素的论述,如果说马克思的辩证法是批判的、革命的,那么就不可能达到任何最终的静止状态,而共产主义似乎正是这样一个终极状态。因此,罗素接着指出,“马克思的辩证法并不比黑格尔的辩证法更革命些。况且,按照马克思的说法,既然一切人类的发展都是由阶级冲突所支配的,而且既然在共产主义之下将只有一个阶级,由此可见,就不能有更进一步的发展,人类就必然永远都处于拜占庭式的静止状态中”。②可见,在罗素看来,马克思的辩证法并不比黑格尔的辩证法更革命,因为共产主义在马克思的思想中是一个最终的静止状态,在这个意义上,共产主义也就依然是黑格尔意义上的绝对观念的完美体现。
罗素把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社会比照为黑格尔的“普鲁士国家”,一个“拜占庭式的静止状态”。然而马克思却声明自己的辩证法是批判的、革命的,批判的辩证法意味着对任何终极静止状态的消解。因此,罗素在这里企图揭示的是马克思思想当中的一个矛盾:批判的辩证法与共产主义之间的矛盾。如果说,马克思的辩证法是批判的、革命的,那么共产主义就绝不是一个拜占庭式的静止状态。如果说共产主义是一个终极的绝对观念的完美体现,那么马克思的辩证法就与黑格尔并无二致,绝不是批判的、革命的辩证法。马克思方法和体系之间存在着矛盾。
我们可以发现,罗素对马克思的批判在某种意义上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对黑格尔批判的翻版。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版跋中强调,“辩证法,在其神秘形式上,成了德国的时髦东西,因为它似乎使现存事物显得光彩。辩证法,在其合理形态上,引起资产阶级及其空论主义的代言人的恼怒和恐怖,因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③在马克思看来,他的辩证方法与黑格尔之间的辩证方法不仅是不同的,而且和它截然相反。马克思要发现黑格尔辩证法神秘外壳中的合理内核。这一合理内核就是辩证法的否定性。马尔库塞曾经就此明确指出,在黑格尔最高水平的著作《逻辑学》中,“黑格尔反复强调,辩证法具有‘否定’的特征。否定‘构成了辩证理性的本质’。‘趋向理性的真正概念’的第一步是‘否定的一步’;否定‘构成了真正的辩证过程’”。④黑格尔的辩证法本质特性就是否定性。“对于马克思来说,如同对待黑格尔一样,辩证法注重于这一事实:内在的否定实际上就是‘运动和创造的原则’,辩证法就是‘否定的辩证法’。”⑤马尔库塞确实看到了辩证法的否定的理论本性,但同时也抹杀了黑格尔辩证法与马克思辩证法之间的本质性区别。虽然黑格尔辩证法也是一种否定的辩证法,但与马克思的否定的辩证法之间存在着本质的不同。
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不仅指出了黑格尔辩证法的理论贡献,同时也指出了黑格尔辩证法的局限,并且表明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与黑格尔辩证法之间根本性的不同。恩格斯指出,“黑格尔哲学的真实意义和革命性质,正是在于它彻底否定了关于人的思维和行动的一切结果具有最终性质的看法。哲学所应当认识的真理,在黑格尔看来,不再是一堆现成的、一经发现就只要熟读死记的教条了;现在,真理是在认识过程本身中,在科学的长期的历史发展中,而科学从认识的较低阶段向越来越高的阶段上升,但是永远不能通过所谓绝对真理的发现而达到这样一点,在这一点上它再也不能前进一步,除了袖手一旁惊愕地望着这个已经获得的绝对真理,就再也无事可做了”。⑥黑格尔辩证法作为否定性的辩证法终结了“人的思维和行动的一切结果具有最终性质的看法”,但同时在“绝对精神”面前不能前进一步、袖手旁观、无事可做。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恩格斯批判了黑格尔,指出黑格尔的体系和方法之间是矛盾的。“黑格尔体系的全部教条内容就被宣布为绝对真理,这同他那消除一切教条东西的辩证方法是矛盾的;这样一来,革命的方面就被过分茂密的保守的方面所窒息。”⑦
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与黑格尔辩证法的本质性区别正在于此。恩格斯站在批判的辩证法的立场上指出,“历史同认识一样,永远不会在人类的一种完美的理想状态中最终结束;完美的社会、完美的‘国家’是只有在幻想中才能存在的东西;相反,一切依次更替的历史状态都只是人类社会由低级到高级的无穷发展进程中的暂时阶段”。⑧完美的社会状态和完美的国家同批判的辩证法之间是格格不入的。从辩证法的角度来看,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一个无穷的过程,包括资本主义在内的任何一个社会阶段都是一个暂时性阶段。当马克思和恩格斯批判黑格尔方法和体系之间存在着矛盾的时候,意味着他对这个问题有了充分的理论自觉。显然,他不会重蹈覆辙,从而把共产主义理解为黑格尔意义上的绝对完美观念的体现。也就是说他不会在自己理论中支持他所批判的东西。如果批判的辩证法对共产主义无效的话,那就违反了马克思辩证法的批判本性,而重新沦落为黑格尔哲学的翻版。批判的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方法,共产主义是马克思想要实现的理论旨趣。我们不应该仅仅把批判的辩证法看作是共产主义实现的理论途径,共产主义本身也应当在批判的辩证法的意义上获得理解。
在批判的辩证法的意义上去理解共产主义,最重要的就是要破除对共产主义进行一种静止的、完美的理想状态的解读。熊彼特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宗教,而马克思本人是一位“先知”。“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人间天堂的学说,对于千百万人的内心意味着一道新的光线和新的生活意义。”⑨在熊彼特的理论视域中,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就是一种完美的人类社会的理想状态,是一种“人间天堂”。因此,马克思主义不过是人类的乌托邦之梦。它将希望寄托于一个完美的社会,那里没有艰难,没有痛苦,没有暴力,也没有冲突。在共产主义的世界里,没有对抗、私利、占有、竞争或者不平等。物质产品极大丰富,人人平等,毫无贵贱之分。共产主义是一种完美理想状态,是一种乌托邦,而马克思本人是一位先知。这是绝大部分当代西方思想家对马克思的评价。实际上,马克思与传统的乌托邦式的思想家有着根本的不同,马克思从来不热衷于对未来社会的描述和建构。正如伊格尔顿所指出的:“马克思对那个没有痛苦、死亡、损坏、失败、崩溃、冲突、悲剧甚至劳动的未来根本不感兴趣。事实上,他根本不关心未来会怎样。众所周知,马克思根本无法描述出社会主义社会或者共产主义社会究竟是什么样子。”⑩
马克思不仅对描绘未来不感兴趣,并且他认为对未来的描绘会陷入一种教条的抽象概念。马克思在1843年致卢格的信中指出,“我不主张我们树起任何教条主义的旗帜,而是相反。我们应当设法帮助教条主义者认清他们自己的原理。例如共产主义就尤其是一种教条的抽象概念,不过我指的不是某种想象的和可能存在的共产主义,而是如卡贝、德萨米和魏特林等人所讲授的那种实际存在的共产主义。这种共产主义本身只不过是受自己的对立面即私有制度影响的人道主义原则的特殊表现。所以,私有制的消灭和共产主义决不是一回事,除了这种共产主义外,同时还出现了另一些如傅立叶、蒲鲁东等人的社会主义学说,这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因为这种共产主义本身只不过是社会主义原则的一种特殊的片面的实现”。(11)可见,马克思绝不主张对共产主义作一种固定的、僵化的、教条主义的理解,因为这会使共产主义成为一种教条的抽象概念。
马克思主义即使是一种乌托邦,也不是一种对未来社会的空想,而是一种吉登斯所谓的“乌托邦现实主义”;马克思即使是一位先知,也不是作为预言家的先知。“《圣经》中的先知也从来没有试图预知未来。恰恰相反,先知的伟大之处在于他们谴责现世的贪婪、腐败和权力欲,并向我们发出警告:如果不能做出改变,人类将根本没有未来。马克思正是这样的一位先知,而不是什么预言家。”(12)实际上,马克思对预言未来充满了警惕,马克思从来“不想教条式地预料未来”。在马克思的时代,充满了各种对未来的预测——而几乎所有这些预测都出自不可救药的理想主义激进分子之手。先知的伟大不在于预测未来,而在于谴责现世。因此,“对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变化的分析,才是马克思的真正遗产和他的研究工作的旨趣所在”。(13)
马克思指出,“实际上,而且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14)对于共产主义的理解首先在于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去理解共产主义,不是去把它当作本质上与资本主义分离开的东西而同资本主义相对照。去理解共产主义就是去理解资本主义本身,因为资本主义的动态变迁或演化包括着共产主义的出现。”(15)共产主义是什么?共产主义就是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对资本主义的研究也就是对共产主义的研究。马克思将资本主义作为其一生的研究课题,其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此。未来不是与现在相割裂的状态,在当下中孕育着未来。因此,对于马克思来讲,重要的任务不是对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进行多么精细的描述,关键在于对当下的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深刻的剖析,找到一条通往未来的现实道路。
伊格尔顿指出,“马克思认为,重要的不是对于理想未来的美好憧憬,而是解决那些会阻碍这种理想实现的现实矛盾。而为人们指引解决问题的合理方向,正是马克思和所有马克思主义者的历史使命”。(16)要想实现这一真正的历史使命,就必须把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所掩藏的剥削关系揭示出来,在此基础上找到一条通向未来社会的通道。未来不是一个既定的现实状态,未来所意味的正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扬弃。“马克思正是在现实逻辑的自相矛盾中找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未来的轮廓。现实的溃败就是未来的真正形象。”(17)在《法兰西内战》中,马克思充分地表达了革命工人阶级的这一历史使命:“工人阶级并没有期望公社做出奇迹。他们不是要凭一纸人民法令去推行什么现成的乌托邦。他们知道,为了谋求自己的解放,并同时创造出现代社会在本身经济因素作用下不可遏止地向其趋归的那种更高形式,他们必须经过长期的斗争,必须经过一系列将把环境和人都加以改造的历史过程。工人阶级不是要实现什么理想,而只是要解放那些由旧的正在崩溃的资产阶级社会本身孕育着的新社会因素”。(18)如果要使这种希望超越无聊的幻想,就应该采取行动让那个令人心动的美好未来成为可能。共产主义的理想就是对现实的无情的批判,就是积极促使资产阶级社会本身的不断地崩溃。因此,无产阶级的任务就是解放新的社会因素。
马克思指出:“新思潮的优点又恰恰在于我们不想教条地预期未来,而只是想通过批判旧世界发现新世界。”(19)马克思的这句话对我们理解共产主义至关重要。马克思不想把共产主义作为一个完美的固定社会状态进行预言,共产主义社会是在批判旧世界过程当中发现的新世界。因此,共产主义要求我们必须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批判。“如果我们的任务不是构想未来并使它适合于任何时候,我们便会更明确地知道,我们现在应该做些什么,我指的就是要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所谓无情,就是说,这种批判既不怕自己所做的结论,也不怕同现有各种势力发生冲突。”(20)这意味着对马克思共产主义的理解不是从与资本主义相割裂的角度去阐释,而是与资本主义相联系的角度去理解,去实现。正如劳拉所指出的,“对于资本主义消失之后而来到的截然不同的社会制度,马克思的确着墨不多。不过,这并非因为马克思的更大的兴趣是批判资本主义而不是描绘他认为‘应当’取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共产主义社会。真正的原因在于,马克思根本不是以这种方式来看待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的差别”。因此,“与唯心主义和空想家的虚无主义途径相反,理解共产主义的唯一科学道路,就是辩证地理解资本主义,把它理解成一个在其‘母体’中孕育着共产主义的发展过程”。(21)一种真正艰难的未来局面不是对现在的单纯延续,也不是与现在的彻底决裂。真正的未来是对现在的批判。马克思的批判的辩证法是对现实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是在批判旧世界当中发现新世界,因此,共产主义就是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对不公正社会的反驳。在批判的辩证法的意义上,共产主义不是一种完美的、理想的社会制度,它所表达的是人类对美好事物的向往。这样,共产主义就是共产主义运动。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非常明确地表达了对共产主义的这一理解:“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22)这一现实的共产主义运动,在理论的意义上,是人向人的本性复归的运动;在实践的意义上,则是扬弃私有财产从而消除资本逻辑的运动。
在《巴黎手稿》中,马克思指出,“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和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生成的”。(23)马克思把共产主义看作是人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是向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而这一运动过程需要通过私有财产的扬弃来实现。“对私有财产的积极的扬弃,就是说,为了人并且通过人对人的本质和人的生命、对象性的人和人的作品的感性的占有,不应当仅仅被理解为直接的、片面的享受,不应当仅仅被理解为占有、拥有。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就是说,作为一个总体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24)马克思把对私有财产的积极的扬弃和人作为一个总体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本质看作是一个过程。这一扬弃过程在马克思看来就是人类自由解放的过程。“对私有财产的扬弃,是人的一切感觉和特性的彻底解放;但这种扬弃之所以是这种解放,正是因为这些感觉和特性无论在主体上还是在客体上都成为人的。”(25)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进一步把共产主义对私有财产的扬弃转化为对资本的批判,具体而言就是对资本逻辑的批判。可见,马克思并不仅仅想在理论的意义上把这一扬弃过程揭示出来,换言之,马克思扬弃的不仅仅是私有财产的观念,而且也是现实当中的私有财产。“要扬弃私有财产的思想,有思想上的共产主义就完全够了。而要扬弃现实的私有财产,则必须有现实的共产主义行动。历史将会带来这种共产主义行动,而我们在思想中已经认识到那正在进行自我扬弃的运动,在现实中将经历一个极其艰难而漫长的过程。”(26)
因此,在政治哲学的意义上,马克思的共产主义作为“运动”就绝非一种理性政治,而是知性政治。理性政治是一种宏大的政治。理性政治把历史总体化,把所有问题综合起来,对未来社会做出一个完美的理性规划,从而一举解决所有问题。这对人类历史而言是一个崭新的开端,人类借此得以重生。柏拉图的理想国、康帕内拉的太阳城、莫尔的乌托邦都是一种理性政治的谋划,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社会与它们的区别正在于此。知性政治并不企图一劳永逸地解决所有问题,它逐个地解决问题,它永远在解决问题的途中。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并不是理性政治的完美谋划,而是作为知性政治的共产主义运动。与此相应,在社会理想的意义上,共产主义是一种调节性理想,而非建构性理想。共产主义社会就是对现存社会的反驳,就是现存社会的反义词。它作为人类的一种价值诉求引导着人类向更加美好、更加符合人性的社会迈进。共产主义作为共产主义运动,在现代社会的条件下,就表现为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共产主义是作为否定的否定的肯定,因此,它是人的解放和复原的一个现实的、对下一段历史发展来说是必然的环节。共产主义是最近将来的必然的形态和有效的原则,但是,这样的共产主义并不是人类发展的目标,并不是人类社会的形态。”(27)正是由于共产主义社会是“最近将来的必然的形态和有效的原则”,共产主义永远都是社会下一阶段发展的目标,共产主义总是作为历史发展的必然环节而存在的。因此,共产主义是社会状态与价值诉求的统一。如果说共产主义是一种社会状态的话,那么这一状态并不是静止的,而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然而,西方右派对共产主义运动的理解往往等同于经验事实意义上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从而也就把苏联与东欧共产主义政治体制的瓦解等同于共产主义运动的失败,进而等同于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的破产。正是基于此,当代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也就自然而然地被看作是资本主义的彻底胜利,看作是历史的终结。实则不然,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在某种意义上确证的恰恰是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运动的胜利。我们透过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可以发现,共产主义运动并没终结,而是活生生地存在于这样的现实当中。“在马克思逝世后的一个世纪里,工业化国家的政府采取了大量改革措施来改善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准:劳工法、最低限度工资法、社会福利和保障、平价住房、公共卫生体系,遗产税、累进所得税,等等。如果在马克思的时代,这些措施就会被贴上‘社会主义’的标签;马克思甚至在《共产党宣言》里描述过许多这样的措施,而且,难以理解,不采取这些措施,资本主义怎么还能存活下来。”(28)可见,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马克思所设想的共产主义的某些重要方面,正是在此意义上,它们的确是发达的。与其说马克思的遗产已经被苏联自封的共产主义遮蔽了,不如更准确地说,它已经被20世纪资本主义的主要发展证明了。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确证了社会主义的现实性,体现着追求共产主义价值诉求的发展态势。
另一方面,在发达资本主义消极界限的意义上,也更加确证了马克思思想尤其是共产主义思想的正确性。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主义本身所固有的矛盾和问题在发达资本主义时代被放大,更加尖锐地表现出来。人在非神圣形象中的异化被膨胀为整个社会的现实。资本运行的逻辑由工业资本主义时代的“G-W-G'”发展为金融资本主义时代的“G-G'”。这种“以实在货币为起点和终点的流通形式G-G',最明白地表示出资本主义生产的动机就是赚钱。生产过程只是为了赚钱而不可缺少的中间环节,只是为了赚钱而必须干的倒霉事。因此,一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国家,都周期性地患一种狂想病,企图不用生产过程作媒介而赚到钱”。(29)这使得资本逻辑所支配的现代人没有国家概念,没有道德底线,也无所谓社会责任。因为,现代社会的金融资本主义已经不再需要传统意义上的“勤劳和努力”等美德了,它的“美德”是“机会主义”。正像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指出的,“在每次证券投机中,每个人都知道暴风雨总有一天会到来,但是每个人都希望暴风雨在自己发了大财并把钱藏好以后,落到邻人的头上。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这就是每个资本家和每个资本家国家的口号”。(30)以金融资本主义为主要标志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把资本拜物教放大到了极致。只要资本主义存在,作为资本主义批判的共产主义运动就不会过时。
作为共产主义运动的共产主义更多地昭示的是一种道德理想或价值诉求,而非社会制度的建构。共产主义运动就是对共产主义价值诉求的无穷无尽的指向性。关于共产主义,海德格尔的与众不同之处就在于,他不是从党派斗争或世界观的角度,而是从存在论的角度出发来解读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学说的历史意义的:“人们可以以各种不同的方式来对待共产主义的学说及其论据,但从存在的历史的意义看来,确定不移的是,一种对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东西的基本经验在共产主义中自行道出来了。”(31)共产主义永恒的人类性意义就在于它是对人类存在状态的本质性道说。正因如此,作为道德预言家的马克思将与世长存。
用伊格尔顿的话来说,“马克思对解放的认识既反对平稳的延续,也反对彻底的割裂。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是那种世间少有的奇才,一个能保持清醒现实主义头脑的理想主义者。他将注意力从未来的美好幻想转移到枯燥的现实工作中。但正是在这里,他找到了真正丰富多彩的未来。他对过去的看法比很多思想家都更为阴郁,但他对未来的憧憬与很多思想家相比都更具希望”。(32)共产主义之所以是一个谜一般的概念,因为这个概念是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统一,它是价值诉求和社会批判的统一。正是在这种统一之中,才能在批判的辩证法的意义上理解共产主义,才能把握共产主义概念的本质性内涵。共产主义就是共产主义运动,这一命题中蕴涵着马克思共产主义概念的全部秘密。即使这一命题告诉我们,共产主义的理想状态永远无法完全实现。但我们必须得有共产主义,如果没有对共产主义的追求,世界就变得缺乏希望。虽然我们永远在途中,但我们永远在回家的路上。
注释:
①②罗素:《论历史》,何兆武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第167页;第167-168页。
③(3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22页;第311页。
④⑤马尔库塞:《理性与革命——黑格尔和社会理论的兴起》,程志民等译,重庆出版社,1993,第112页;第256页。
⑥⑦⑧《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2009,人民出版社,第269-270页;第271页;第270页。
⑨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吴良健译,商务印书馆,1999,第46页。
⑩(12)(16)(17)(32)伊格尔顿:《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李扬等译,新星出版社,2011,第69页;第71页;第73页;第83页;第80-81页。
(11)(19)(2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7-8页;第7页;第7页。
(13)(15)(21)(28)詹姆斯·劳洛:《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共产主义》,《当代英美哲学地图》(欧阳康主编),人民出版社,2005,第628页;第644页;第644页;第629-630页。
(14)(22)(2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527页;第539页;第197页。
(1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159页。
(23)(24)(25)(26)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第81页;第85页;第85-86页;第128页。
(29)柄谷行人:《跨越性批判——康德与马克思》,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第117页。
(31)海德格尔:《海德格尔选集》上卷,孙周兴选编,上海三联书店,1996,第384页。
标签:黑格尔辩证法论文;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论文; 黑格尔哲学论文; 共产主义社会论文; 共产主义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本质主义论文;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唯物辩证法论文; 理想社会论文; 资本论论文; 罗素论文; 哲学家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