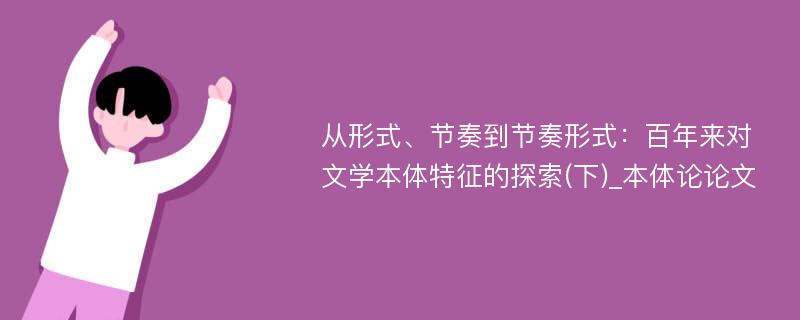
从形式、节奏到节律形式——文艺本体特性百年探寻轨迹扫描(下篇),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形式论文,节律论文,下篇论文,本体论文,轨迹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 I206.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342(2001)03-31-06
在对二十世纪中国文论和美学关于文艺本体特性的百年探寻轨迹进行扫描的上篇,我们把王国维、鲁迅、郭沫若、康白情等现代诗人群和朱光潜、林语堂等人的观点作为前五十年间的重要坐标点,并简要地说明了这些坐标点之间的联系。这里的下篇,则是对二十世纪后五十年的探寻轨迹进行扫描。
我们可以把二十世纪的后半期分为两段。前段的近三十年从总体上说对文艺本体特性的探寻在态度上是拒斥的,在理论观念上则限定在俄苏文论模式的“形象”范畴之内,并在内容与形式二分的结构中消泯了文艺的本体问题。文艺理论所重视的,几乎只是文艺与生活和人民的关系,而且拘囿于文艺与政治的关系。这期间,前五十年间的探寻成果被集体性地遗忘,遭到历史性的抹煞。“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两三年间,对文艺特性的认识也还只在作为“最高指示”的“形象思维”论的圈子内进行,实际上依然是重复俄苏文论的观点。直到社会主义新时期的到来,在思想解放大潮中,人们对文艺特性问题的讨论才逐步落到本体层面上。从这时起到世纪末的二十年间,人们恢复了对前五十年的探寻成果的记忆,并在西方现代美学(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大量引进和对中国古代美学的深入发掘中得到参照和启示,从不同的角度对文艺本体特性问题作出了各种不同的回答,其中包括具有综合意义的“节律形式”说。这种对百年探寻具有综合意义的观点到了世纪末还在生态思维所昭示的终极性大综合和还原性视点下得到进一步的深化。这里,仍然以展示若干重要坐标点的方式对这后五十年间的探寻进行扫描,是为下篇。
坐标点之六:主流文论的“形象—典型”说
在文艺本体探寻经历了二、三十年代的高潮后,由于文艺与现实政治的关系问题空前突出,革命权威中心的几乎全部注意力都放在如何推动和调控文艺为革命政治直接服务的功利目标上,并逐步成为主流文论。进入四十年代以后,文艺本体及其特性问题已不为主流文论所注意。到五十年代,随着当时苏联文艺理论(从季摩菲耶夫的《文学原理》到毕达可夫的《文艺学引论》)的引入,被粗陋阐释的别林斯基的“形象思维”说成了对文艺特性的唯一诠释,形成至今仍被广泛认同的“形象”本体说。到六十年代初,这种观点在分别由蔡仪和以群主编的两种全国统编文艺理论教材中被作为权威结论凝结下来,并在八十年代初以来的各种“新编”教材中仍被沿袭。
这种观点认为,文艺的本源是生活,文艺自身即其本体是具有感性具体性的形象,而真正的文艺不仅形象是生动的,还要以独特的个性概括社会生活的本质,即成为典型。因此,严格一点说,这种文艺本体特性观应概括为“形象—典型”说。后来,对这种观点长期存在的“反映—再现”论阐释受到质疑并补充了“表现”内涵后,甚至在“典型”说也遭到种种非难和改造之后,形象作为文艺本体的观点依然保留。再后来,人们以“意象”取代形象,或者将典型与意境互补并列,或者在典型和意境之外还加上意象而同为“艺术至境”,都还脱不了形象这个基本点,足见此说影响之深。当然,这也说明此说确实蕴含着某种合理的内核,因为绝大多数的文艺确实都有形象,也离不开形象。
但是,这毕竟是一种肤浅而又粗疏的认识。第一,任何形象都表征着一定的意旨,许多思想都可能用形象的方式来传达。作为此说理论基础的别林斯基的形象思维论如果孤立起来看,本来就隐含着误读为思想图解的可能。为了避免这种误读,他特坦强调文艺表现“情致”(或“激情”)的重要性。这个思想,苏联的一些美学家(如波斯彼洛夫等)曾经给予阐释并引起国内某些学者注意。还有的学者如王元化则直接从刘勰和黑格尔的观点阐述情志(情致)问题,并为一些新编文艺理论教材所吸取。尽管如此,文艺以什么样的本体特性与情致这个特殊对象相对应,情致何以能够为文艺形象所表现而成为其意蕴,这些与文艺的本体特性密切相关的问题并未得到理睬。基于这种认识,文艺创作中长期存在的“形象化”以至观念图解的误解一直得不到根本纠正。第二,生活中无处没有形象,也不乏生动而典型的形象,而且任何形象都含蕴或或指向一定的意义内容,它们与作为审美对象的艺术形象的基本区别何在?换个角度说,为什么文艺要以生动以至典型的形象为本体?文艺究竟是看中了形象身上的什么特性,而正是这种特性经过艺术的提练和强化才使其成为文艺的审美本体的呢?显然,还应从形象和典型中区分出具有审美特性的文艺形象来。第三,正如八十年代中期就有论者指出的,形象思维作为从原始的意象思维发展而来的一种一般性的思维方式,在人类的实践中普遍存在,而不能把它等同于艺术思维。后来又有论者指出,形象思维要正确掌握世界也必须遵循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道路,艺术创造和欣赏也离不开抽象。于是,依托于形象思维的“形象”说同时从两面遭到怀疑:一面是形象性并不能涵盖所有的文艺作品,比如文学中大量的抒情和论说作品;另一面是文艺中的形象不应只是诉诸思维的认识中介。建立在认识论文艺观基础上的“形象”说,因此面对尖锐的质疑。对于主流文论所说的“形象”,需要既在其中同时又在其外寻求文艺本体的真正特性,把被“形象”所屏蔽的文艺本体特性揭示出来。
坐标点之七:宗白华的“活力—节奏形式”说
正如本文上篇所说,这决不只是一个坐标点,而是贯穿了二十年代到八十年代的一条线索。由于这条线索的存在,文艺本体特性百年探寻的思理重点和特色才得以明晰,而且为其他各种见解的学理定位提供了一根轴线。
在宗白华看来,中华民族很早就发现了宇宙旋律及其生命节奏的秘密,而他正是以对这宇宙旋律及其生命节奏的深刻体验来感悟文艺本体的审美奥秘的。
早在1920年冬,宗白华在德国留学时就写了《看了罗丹雕刻以后》,表达了他的“活力”说美学观。他说:“这大自然的全体不就是一个理性的数学、情绪的音乐、意志的波澜么?”“这个世界……乃是向着美满方面战斗进化的世界。”“大自然中有一种不可思议的活力,推动无生界以入于有机界,从有机界以致于最高的生命、理性、情绪、感觉。这个活力是一切生命的源泉,也是一切‘美’的源泉。”“自然无往而不美。何以故?以其处处表现这种不可思议的活力故。”而“艺术的目的是表现最真实的自然”。在宗白华看来,这种表现了世界之“动”的活力,贯穿于物质与精神并把两者沟通起来,使物质具有生命而精神化。他说:“动者是生命之表示,精神的作用;描写动者,即是表现生命,描写精神。自然万象无不在‘活动’中,即是无不在‘精神’中,无不在‘生命’中。……这种‘动象的表现’,是艺术最后目的,也就是艺术与照片根本不同之处了。”显然,这种表现了动象的活力正是物质与精神之间共有的中介,也是自然与艺术之间共有的特性与中介。有了它,艺术才得以把物质精神化、生命化,自然的真实即自然的美才得到表现。(注:《宗白华全集》第1卷,第309-313页。)
1943年,宗白华在《中国艺术意境之诞生》中从《庄子·养生主》对庖丁解牛的描写引发议论说:“‘道’的生命和‘艺’的生命,游刃于虚,莫不中音,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经首之会。音乐的节奏是它们的本体。所以儒家哲学也说:‘大乐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易》云:‘天地氤氲,万物化醇。’这生生的节奏是中国艺术境界的最后源泉。”“音乐和建筑的秩序结构,尤能直接地启示宇宙真体内部和谐与节奏,所以一切艺术趋向音乐的状态、建筑的意匠。”(注:《宗白华全集》第2卷,第332-333页。)“尤其是‘舞’,这最高度的韵律、节奏、秩序、理性,同时是最高度的生命、旋动、力、热情,它不仅是一切艺术表现的究竟状态,且是宇宙创化过程的象征”。(注:《美学与意境》第217页。)在这里,宗白华明确指出节奏是艺术的本体,并且把节奏的概念扩展到旋律以至秩序。1947年,他在《艺术与中国社会》中又说:“中国人感到宇宙全体是大生命的流行,其本身就是节奏与和谐。人类社会生活里的礼和乐,是反射着天地的节奏与和谐。一切艺术境界都根基于此。”(注:《宗白华全集》第2卷,第413页。)他虽然谈的是中国艺术,却与二十多年前的见解相呼应,实际上贯通地揭示了中西艺术共同的本体特性。
到1957年参加当时的美学大讨论,宗白华在主张美是客观存的《美从何处寻?》一文中,仍然通过具体的例证明确肯定节奏对于艺术之美的本体性意义,指出“这节奏,这旋律,这和谐等等,它们是离不开生命的表现”(注:《宗白华全集》第3卷,第270页。)。到六十年代论中国书法艺术的论著,依然一以贯之地体现出他的“活力”论的基本精神。直到晚年他还说:“中国的书法,是节奏化了的自然,表达着深一层生命形象的构思,成为反映生命的艺术”(注:《宗白华全集》第3卷,第611-612页。)。
宗白华为什么如此看重节奏对于艺术的本体意义呢?这是因为,正是这表现了活力的节奏才能激发欣赏者相应的活力,并启示对生命精神的象征。尽管他没有象郭沫若早年那样明确地指出文艺欣赏就是“节奏相互变换”的“感应”,但他们诗心相通,实际的认识是一致的。在写于1921年的《艺术生活——艺术生活与同情》中,他用“同情”来指称由感应而物我同一、人我同一的境界,认为“艺术的作用,即是能使社会上大多数的心琴,同入于一曲音乐而已”。在这篇文章开头的题诗中,他写道:“你想要了解‘光’么?/你可曾同那疏林透射的斜阳共舞?/你可曾同那黄昏初现的冷月齐颤?/你可曾同那蓝天闪闪的星光合奏?”(注:《宗白华全集》第1卷,第316-317页。)这里所描述的,正是以节奏为基础的“感应”状态。1933年,在《哲学与艺术》中,宗白华评述了毕达哥拉斯(毕氏的“数的和谐”说就包含着“大宇宙”与“小宇宙”相感应的思想)的美学观点,指出:“音乐是形式的和谐,也是心灵的律动,一镜的两面是不能分开的。心灵必须表现于形式之中,而形式必须是心灵的节奏,就同大宇宙的秩序定律与生命之流动演进不相违背,而同为一体一样。”(注:《宗白华全集》第2卷,第54页。)在分析中国古代绘画的“三远法”时,他说,这种“诗意的创造性的艺术空间”“趋向着音乐境界,渗透了时间节奏”,“由动的节奏引起我们跃入空间感觉。直观之如决流之推波,睨视之如行云之推月。全以动力引起吾人游于一个‘静而与阴同德,动而与阳同波’的宇宙。”(注:《宗白华全集》第2卷,第432-434页。)艺术形式之所以能使人的心灵与大宇宙的秩序定律“同为一体”,其秘密就在以节奏以基础的感应。宗白华尽管没有象郭沫若那样明确地提出“感应”说,但他们确实诗心相通,诗学的感悟惊人地一致。应当说,当郭沫若还信奉着泛神论诗学时,宗白华就已经用“活力”和“节奏”来揭示大自然生命化和艺术与心灵同一的根源了。
在宗白华看来,也正是具有“活力”和“节奏”的形式才成了艺术象征的本体。在《中国艺术的写实精神》,他引王船山论诗话说:“君子之心,有与天地同情者,有与禽鱼草木同情者,有与女子小人同情者,悉得其情,而皆有以裁用之,大以体天地之心,微以备禽鱼草木之几。”他认为:“这是中国艺术中写实精神的真谛。”“写实、传神、造境,在中国艺术上是一线贯穿的”,“窥探宇宙之秘,是艺术家最后最高的使命”。(注:《宗白华全集》第2卷,第323-325页。)这就是说,正是具有“活力”和“节奏”的形式,才因表现了“道”的节奏而成为“道”的象征。
宗白华的“活力—节奏形式”说的文艺本体特性观,不仅贯穿他的一生,而且贯穿在他对几乎一切艺术的美学分析之中,也贯穿在他对东西方艺术的鉴赏和对东西方美学的比较研究之中。在他那里,这种观念决不只是抽象的理论,而是融合在艺术鉴赏家的真切细腻的感受中从而得到切实验证的。作为文艺本体特性的孜孜不倦的探寻者和阐释者,他以一生的坚守和深化对这一重大的美学课题的贡献迄今无人可以企及。也有美学家触及到了,但是没有他的阐述明确和深入,更没有他那样融合着审美经验的真切和生动。宗白华的“活力”说美学观,必定是永葆活力的。
坐标点之八:李泽厚的“情感—形式”说
当“文化大革命”结束,主流文论在关于形象思维的讨论中仍然坚持“形象—典型”说时,李泽厚从其人类学本体论的实践哲学(即主体性实践哲学,又称实践本体论)出发提出了“情感本体”说,后来又深化为“情感—形式”说。
1979年,李泽厚在《谈谈形象思维问题》中指出,当时在形象思维问题上针锋相对的两派“在一个基本问题上是一致的,就是把艺术看作是认识,认为这是一种定论”,而“把艺术简单地看作是认识,是我们现在很多公式化概念化作品的根本原因”。他认为,艺术包含有认识的成分,认识的作用,但是不能把它归结于或者等同于认识,它是以情感来感染人的;形象思维也是在情感逻辑的支配下进行的。(注:《李泽厚哲学美学文选》,第339-341页。)后来,在《华夏美学》的结语中,他更明确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认为“本体只能是人”,“人性也就是心理本体”,而“心理本体的重要内涵是人性情感”,艺术就是表现这个本体的。(注:李泽厚:《美学三书》,第428页。)在阐释王国维的意境论时,他说:“诗词是各种常人、诗人所能感到的人生,予以景物化的情感抒写,才造成艺术的境界。所以,‘境界’本来自对人生的情感感受,而后才化为艺术的本体。这本体正是人生境界和心理情感的对应物。”(注:李泽厚:《美学三书》,第416页。)这就是说,情感本身还并不就是艺术的本体,而艺术的本体指的是文艺作品中作为情感对应物而展现的景物等形象。也就是说,只有当情感获得恰当的艺术形式时,它才成为艺术的本体。显然,李泽厚是把艺术形式的情感内涵视为文艺本体特性的。
1981年,李泽厚在《审美与形式感》中主要依据格式塔心理学的“异质同构”学说阐释形式感,从人与自然相同一的高度说明包括艺术形式在内的一切审美对象之所以能引起美感的原因,这实际上是在艺术与自然的同一性上寻求艺术本体的特性,即艺术何以能对应自然(参宇宙之奥秘,写天地之辉光)的原因。(注:《李泽厚哲学美学文选》,第441-447页。)遗憾的是,他没有深究下去,而是忙着以他的实践积淀说去弥补同构对应说的缺陷。
在后来的《美学四讲》中,李泽厚把艺术剔析为形式层、形象层和意味层三个层次。在文艺的现实存在方式中,其实形象和意味都是存在于形式之中的。何况,在文艺审美活动中,不仅所谓形式层,而且形象层和意味层都可以是具有更加深远的象征功能的形式。参照他的美即“自由的形式”的说法,建立在情感本体上的文艺本体的特性就在于它是情感的形式。然而,艺术形式究竟凭什么特征而能与情感相对应从而能表现情感呢?对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却依然没有明确的回答。后来,李泽厚明确宣布自己是不讲自然本体论的,这就堵死了对文艺本体特性的探秘之路,因为正如宗白华所反复阐述的那样,这个秘密本来就在实践得以生成的自然的运动中。
坐标点之九:王一川的“中介—活动—作品”说
八十年代后期文学人类学兴起,对文艺本体特性的探寻又有了新的视点。其中,比较系统的观点是王一川以人类学文艺学的名义提出的。
1987年,王一川发表《本体反思与重建》,对文艺本体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阐发。他借兰色姆的话指出对艺术进行本体反思的重要性,认为对艺术本体进行本体反思,弄清艺术本身究竟是什么,乃是文艺学、艺术批评的起点和归宿。他说:“艺术何以存在?在于何处?为何而在?追溯这类问题便进入到真正的本体之思领域。”针对认识论文艺学中本体的失落,他提出从三个方面来理解艺术的本体,即“作为人类感性的超越与解放的中介的艺术本体”、“作为在活动整体中才生成的艺术的本体”和“作为上述两层本体义的集中包蕴的作品的本体”。把这三义联系起来,他给艺术本体下了一个一般的定义:“艺术本体是在活动整体中通过作品亮相的使得感性的超越与解放成为可能的体验,要言之,是体验。”
所谓本体,应是实有的存在,“作为人类感性的超越与解放的中介的艺术主体”为什么会有这种功能?“作为在活动整体中才生成的艺术本体”究竟具有什么特征?“作为上述两层本体义的集中包蕴的作品的本体”何以能将其集中包蕴?凭什么特性而能这样集中包蕴?归结为体验,这体验又是怎样的生命活动?艺术靠什么特性来实现这体验?这些问题不能不予回答。在王一川构建的人类学文艺学体系的形式论部分,他说:“艺术是形式的艺术(或符号的艺术,语言的艺术)。正是在形式中体验得以亮相,超越与解放得以实现。因而形式的研究十分重要。……人类学文艺学将摈弃把艺术形式仅仅看作内容的附庸的作法,而强调形式本身的超越意义、体验意义。形式意味着体验的亮相,形式在本质上就是诗”。(注:王一川:《通向本文之路》,第62-98页。)看来,艺术的本体还是在于它的形式,但是,什么样的形式或者是形式的什么特征才使它具有超越和体验的意义从而成为诗的呢?他没有回答。在从体验论美学走向语言论美学、修辞论美学之后,这个问题更是被语言本体论屏蔽了。
坐标点之十:余秋雨和林兴宅的“象征形式”说
从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象征”论是文艺本体阐释中又一个值得重视的坐标点。
最先明确地把象征与文艺本质相联系并展开深入论述的是余秋雨。他在1987年出版的《艺术创造工程》中,从艺术创造的角度阐述了自己对艺术本质的看法。跨过大半个世纪的话语隔离,他对形式的关注和认识与王国维的“形式”说遥相呼应。在论及意蕴的开掘时,他指出:“意蕴在艺术作品中如同能源,层层散发开去,层层体现出来:凭借着形象,凭借着情节,凭借着结构,凭借着语汇,凭借着各种外部呈现方式,渐次获得实现。对于意蕴来说,其他一切都是形式——不同层次的形式。”对于意蕴与形式的关系,他以火为喻,认为“艺术作品的意蕴,也就是艺术作品的精神内核。它在艺术作品中并不单独、直捷地显露在外,但又在作品整体的每一部分都可发现它的踪影”(注:余秋雨:《艺术创造工程》,第51页、188页、第194-195页、第210页。)。显然,形式之显示意蕴犹如火之发出光芒,它就是艺术的本体。
从这个认识出发,他对形式的创造特别重视,认为艺术创造工程无非艺术形式的凝铸。他从感性直觉的角度来揭示艺术形式的特征。对于感性直觉,他引用了柏格森的描述,强调这是“使我们置身于对象的内部”的体验,是“与对象中那个独一无二、不可言传的东西相契合”。他这样描述艺术欣赏中的“感应”:“这里有视听上的本能的颤动,这里有浓郁的感官气氛,这里的生命都流泻为气貌,这里的气貌都包含着生命。”(注:余秋雨:《艺术创造工程》,第51页、188页、第194-195页、第210页。)他借克罗齐的话说:“心灵只有借造作、赋形、表现才能直觉。”因此,“艺术形式也就是一种直觉形式”(注:余秋雨:《艺术创造工程》,第51页、188页、第194-195页、第210页。),也就是能引起感应的形式。为了强调形式对于艺术的本体意义,他还借重了卡西尔关于“艺术家是自然的各种形式的发现者”和“在艺术中我们是生活在纯粹形式的王国中”的观点。他说:“是形式使内容走向普遍,走向长久。”(注:余秋雨:《艺术创造工程》,第51页、188页、第194-195页、第210页。)正是基于此,艺术的形式才成为象征,而“艺术,就其本质而论便是一种象征”,“只有承认象征,再现、摹仿才有艺术意义”。(注:余秋雨:《艺术创造工程》,第51页、188页、第194-195页、第210页。)在余秋雨看来,无论是感性直觉即感应,还是象征,都离不开形式;没有这样的形式,也就没有艺术。既然如此,形式作为感应和象征的本体,也就是艺术的本体。
但是,艺术的形式究竟是凭借什么特征才能引起感应并建立象征呢?余秋雨已经意识到“这里的生命都流泻成气貌,这里的气貌都包含着生命”,却终究没有说出这与生命融为一体的“气貌”是什么。在抵达终点仅一步之遥的地方,他没有继续探寻。
到90年代初,林兴宅陆续发表了关于文学本质思考的系列文章,并于1993年出版了《象征论文艺学导论》。在这本书中,他明确地指出:“艺术作为审美的对象,它的物质载体不是初被当作符号来掌握,而是被当成本质存在来掌握”。“只有把艺术品的物质载体当作艺术的本体存在,直观它的形象,才是把艺术当成艺术来对待。”(注:林兴宅:《象征论文艺学导论》,第64页。)而艺术品的物质载体之所以是艺术的本体,能成为审美对象,则是因为它呈现为一个独特的“结构”。“艺术作品的这种‘审美结构’是严格意义上的艺术的本体。”(注:林兴宅:《象征论文艺学导论》,第65-75页。)这个“审美结构”也就是艺术的形式,而“艺术作品的形式……就是艺术存在的本体,形式是一切艺术审美之谜的谜底”。“艺术审美对象就是这个融彻着内容的形式,说得极端一点,审美对象就是形式,除了形式便一无所有了。”“艺术作品的形式是艺术审美的真正起点。”“艺术作品的生命特征归根到底就是艺术形象的生命表现性,是与人的生命同构契合的效应。”(注:林兴宅:《象征论文艺学导论》,第113-119页。)由于“在文学作品中,真正有价值的东西是作家通过创造性的表现所揭示的特征”(注:林兴宅:《象征论文艺学导论》,第369页。),他进一步指出艺术形式的结构应是“特征图式”,即“艺术形象整体的特征所表现的人类普遍性的‘心灵图式’”(注:林兴宅:《象征论文艺学导论》,第323页。)。
形式作为“结构”为什么如此重要呢?在林兴宅看来,这是因为“艺术作品作为审美对象在本质上必须是表现的。”“而‘形式表现’的内在机制就是象征。”因此“象征”乃是文艺学的核心范畴,“是艺术的性质、特征、功能和规律的概括”,“文艺学应该围绕着‘象征’范畴重新建立自己的体系。”(注:林兴宅:《象征论文艺学导论》,第259页。)
在论及艺术表现的三个层次时,林兴宅注意到了曾永成在80年代中期提出的关于“节律形式”和“节律感应”的观点,但他只把这看作是生物层次上的表现。他也注意到了郁沅在1990年提出的“文学感应”说,但他认为“感应”只能说明这审美关系的性质,而无法说明艺术自身的功能特性,不能作为艺术价值的本质的范畴。
林兴宅对作为艺术本体的形式从“结构”和“特征图式”作了更深入具体的阐释,余秋雨则注意到艺术形式的“气貌”特征及其感应之间的功能关系,把艺术的本质定位于象征却并不限于意蕴认识。他们的观点虽有不同,但他们都认为艺术的本体是具有象征功能的形式,因此将其归入同一个坐标点。这种观点,与30、40年代的现代诗人群的观点遥相呼应,并且把象征从诗歌扩展到艺术,这一学理上的进展是值得重视的。但是,他们都没有明确地把艺术的象征同其他的象征区别开来,没有揭示出艺术象征的艺术特性,因此离文艺本体特性终究还隔着一层。
坐标点之十一:王岳川的“人类本体”说
为了打破艺术本体长期被屏蔽的状况,王岳川在1994年推出了以《艺术本体论》为名的专著,以使艺术本体得以敝亮。
王岳川是基本“艺术与人类具有一种同构关系”,(注:王岳川:《艺术本体论》,第2页。)“艺术本体论与人类本体在历史的走向上达到同一”(注:王岳川:《艺术本体论》,第45页。)的基点来考察艺术本体的。他在追溯了“摹仿”说的古典本体论、“表现”说的浪漫本体论、“形式”的语言本体论和“文化”说的批判本体论之后,提出“新本体论”即“艺术活动价值论”是艺术本体论的当代形态的观点。从书中对艺术形象的超越性的本体论、审美感悟与艺术创造的体验本体论和文学意义审美生成的解释本体论的论述看,作者的视点并不在艺术自身本体,而是在于全面揭示艺术对于人的生命存在和生成的本体论意义,亦即文艺价值本体论。这个意图,作者在绪论中就已点明。他说:“文艺本体论是对艺术存在的反思,是对艺术的意义和价值的领悟和揭示。……艺术本体被遮蔽,但它通过沉默而言说,通过呈现而被揭示。艺术与存在之间那种命中注定的不解之缘,使对艺术意义的探索成为对人类审美活动的整体揭示和敞亮。”(注:王岳川:《艺术本体论》,第1页。)在作者看来,艺术的本体意义就在于“标示出人的本体的超越之维”。(注:王岳川:《艺术本体论》,第3页。)这种价值论视角所得出的本体论,显然已不是本来意义的本体论。
但是,该书以专章阐述了作品本体,指出作品“作为艺术本体的重要层次——艺术的存在形式,是人的精神创造超越性存在”。(注:王岳川:《艺术本体论》,第197页。)作者认为,对艺术作品本体的重视,表明美学对艺术的研究已从外在研究走向内在研究,而且“作品的深层意蕴是艺术具有永恒魅力的关键所在”(注:王岳川:《艺术本体论》,第251页。)。显然,艺术对于人的一切本体价值和意义都基于艺术作品,艺术作品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艺术本体。同时,在阐述艺术审美体验的本体意义时,王岳川还注意到“气”,认为“气在审体验中有决定意义”(注:王岳川:《艺术本体论》,第191页。),正是基于气的作用,真正的艺术才是“一种充盈的生命气息的律动”(注:王岳川:《艺术本体论》,第192页。)。
尽管王岳川对艺术本体的思路与众不同,不是直指艺术本身,但他从与人类生命超越性本体同构的角度作的阐释,仍然提供了一个带根本意义的参照,即从人的生命本体特性去认识文艺的本体特性。
坐标点之十二:曾永成的“节律形式”说
在文艺本体特性百年探寻的途程中,曾永成于80年代中期提出的“节律形式”说具有综合和总结性的意义。这一观点虽然形成于对中国古代感应论审美观的现代阐释,参照了西方近代以来美学的重要见解,实际上也融会了王国维、鲁迅、郭沫若、宗白华、林语堂等人的思维成果,符合现代诗人们的诗学感悟,而且还能包容或切入80年代以来的探寻所取得的相关成果。
对文艺审美本体特性的探寻贯穿在曾永成二十年来的美学和文艺学研究中。“节律形式”这个观点,在1982年的《运用系统原理进行审美研究试探》一文中就已萌生。1986年的《审美特性“初感”再思》明确指出“审美活动是一种节律感应活动”,并从现代科学的角度揭示了“节律”作为普遍存在的中介并引起节律感应的事实。(注:见《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2期。)分别于1989年和1991年出版的《以美育美》和《感应与生成》,进一步系统阐述了以节律为基础的感应论审美观,正式提出了“节律形式”这一概念。作者说:“任何一种审美的形式实际上都以其秩序结构显示出运动的本性,具有某种力度、气势、节奏、韵律和张力结构,这一切可统称之为节律。我们把审美对象的具有节律特征的形式,称为‘节律形式’。”(注:曾永成:《文艺的绿色之思》,第44页。)作者认为,包括舞蹈、音乐、造型艺术和文学在内的一个审美活动都是以节律形式引起节律感应而产生美感的。(注:曾永成:《文艺的绿色之思》,第13-41页。)对于节律形式的类生命特性,它对意义表征和生命体验以及整合与超越的价值和功能,还有功利内容如何被赋与节律形式而转化为美等问题,都进行了阐释。
在1995年的《文艺政治学导论》中,作者用节律形式去阐释政治活动的审美性质。到2000年的《文艺的绿色之思——文艺生态学引论》,更以专章考察文艺审美活动的生态本性,明确地把文艺审美活动的生态本性定位于以节律形式为条件节律感应,指出“气韵作为节律形式或形式的节律特征,是审美对象本体的特性所在”(注:曾永成:《文艺的绿色之思》,第66页。)。作者指出:节律形式的普遍中介作用,“贯穿了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全部领域,也贯穿于人的身心整体的生理,心理和意识的各个层次,这就造成物物之间、物人之间、人我之间、心物人间,身心之间乃至天人之间多维度生态关联中的对应。这样一个多维多层而又纵横错综的对应网络,就是审美形式意蕴生成的生态基础。”(注:曾永成:《文艺的绿色之思》,第83-84页。)而且由节律形式表现的意蕴非常丰富、广阔而深厚,即于通达天地之道,也可表征心灵之秘,它可以在无际无涯的宇宙生命世界中纵横对应,于万取一收之中映照出无穷的意义来(注:曾永成:《文艺的绿色之思》,第82页。)。为了把文艺的审美象征同其他象征进一步相区别,作者还特地阐述了审美形式的生命动力性,认为:“还是在符号(意义能指)性和动力(生命构建)性的结合与统一中,审美形式的生态本质及其生命目的性才得到全面的揭示。”“在节律感应中感悟意义并在生命体验中享有意义,就是使意义生命化……由节律感应导致象征,才是审美的象征与其他象征的区别所在”。(注:曾永成:《文艺的绿色之思》,第92页。)在对节律形式生命动力性进行阐释后,作者还进一步指出:在人类的生态系统中,“节律形式作为信息所具有的对物质实体的超越性,使它能映照、网罗、聚焦和沟通大千世界整个生态之网。凭借这种超越性,节律形式才成为生态系统中特殊的普遍中介,从而赋予文艺审美形式生态整体性”(注:曾永成:《文艺的绿色之思》,第93页。)。对于节律形式作为感应中介的作用,还从生命体验中介、生命象征中介、生命整合中介、生命生成中介以及实践中介诸方面加以展开和深化,从生态功能的角度强调了节律形式作为文艺本体特性的意义。
生态学被人们视为终极的科学,生态思维从人类与世界的生态关联对文艺审美活动的本体特性的探寻也当以其巨大的综合性而具有终极探寻的意义。主要综合了“形式”说、“节奏”说和“感应”论与“象征”论的“节律形式”说,作为百年探寻的一个总结,同时也应是一个新的起点。以这个理论“细胞”为原点,新世纪的文艺理论和文艺美学应有一个新的面貌,上升到一种新的境界。
收稿日期:2000-02-19
标签:本体论论文; 宗白华论文; 艺术本体论论文; 西方美学论文; 艺术论文; 中国形象论文; 文化论文; 本体感觉论文; 生命本质论文; 美学论文; 李泽厚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