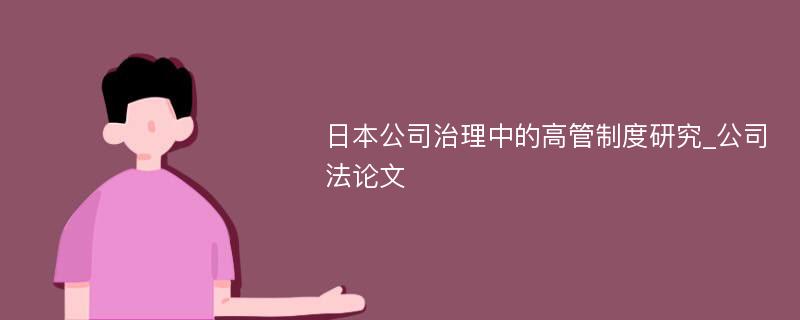
日本公司治理中的执行官制度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日本论文,执行官论文,公司治理论文,制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引言
近几年,公司治理问题成为全球关注的热点。在公司法学领域,公司治理主要围绕以下两个问题展开讨论:第一,谁是公开上市公司的所有者?即公司主权论;第二,应该如何构筑公司经营管理机构?即经营者监管体制论。① 后者是有关公司经营机构改革的问题,为了实现股东利益的最大化,如何在最大限度发挥经营者能力的同时,有效地确保对其进行监督是这一问题的中心。因为公司是法人,公司的经营是通过经营者来实现的,所以要确保公司经营的效率性和健全性,就必须建立一套能够合理有效监督经营者的体制。
在这一问题上,日本也不例外。公司治理论在日本流行的主要背景是:频繁出现的企业丑闻、经济不景气带来的企业倒闭问题、经济竞争的全球化② 以及美国法的影响。③ 在此背景下,2002年5月,日本对商法及商法特例法中有关公司经营机构的部分做了重大调整,针对大型公司引进了美国式公司治理中的委员会制度,选择采用委员会制度的公司将由执行官取代董事执行公司的业务,董事则作为董事会的成员进行经营决策并监督执行官的业务执行。原先公司的经营者——代表董事、业务执行董事转变成了经营监督者,而执行官则成为公司法制上新的经营者。2005年6月日本新公司法对此予以了确认。
二 日本股份有限公司业务执行机关的历史变迁
(一)商法规则及1950以前股份有限公司的业务执行机关
1890年,由德国人赫尔曼·劳埃斯勒(Carl Friedrich Hermann Roesler)起草的商法是日本最早具有近代意义的系统商法典,通称为“旧商法”。④ 然而,由于当时日本法学界法英两学派的法典论争等原因,⑤ 该法几乎未施行就被“新商法”所取代。⑥“新商法”颁行于1899年,现行的日本商法就是指这部法典。
1950年以前的日本商法要求股份有限公司必须具备三个机关,即作为公司意思决定机关的股东大会,作为业务执行、公司代表机关的董事以及作为监督机关的监事。除此之外,还可根据需要临时设置检查员。⑦ 股东大会不仅有权审议决定法律及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事项,对除此之外的事项也可进行审议决定,是公司最高且万能的机关。⑧ 此外,就公司的业务执行,规定在公司章程中没有特别规定时,以董事的过半数表决决定。第261条第1款就公司的代表权规定:原则上由董事各自单独代表公司;第261条第2款规定:公司也可通过公司章程或股东大会决议决定应代表公司的董事,或基于章程的规定,通过董事的互选决定代表董事。因此,在1950年以前的商法中,股份有限公司的业务执行机关不是董事会这样的合议制机关,⑨ 而采独任制,即公司董事各自具有业务执行权和公司代表权。而监事则作为股份有限公司唯一的监督机关,具有对业务全盘的监督权。⑩
(二)1950年商法修改对股份有限公司业务执行机关的重组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为了应对经济的高速发展以及经济民主化的需求,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纷纷对公司法进行了大幅度的修改,(11) 日本也不例外。1950年,在美军占领下的日本对商法中有关股份有限公司的部分进行了大幅度修改。此前的日本公司法深受德国影响,基本属于德国法系的立法,而这次修改则在此基础上大量引进了美国法的制度。(12) 1950年的商法修改被认为是符合了当时大型企业所有与经营分离的世界趋势,促进了日本公司法制的近代化与民主化。(13) 现在日本股份有限公司法制中有关业务执行机关的基本框架,就是在1950年商法修改时形成的,此后基本上都是在这一构架上进行的修补作业。
效仿美国进行的1950年商法修改基本上维持了股份有限公司三机关鼎立的形式,但为了谋求公司经营机构的合理化,对各机关构成以及机关之间权限的分配进行了重大调整。这主要可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对原先作为公司最高及万能机关的股东大会的权限做出限制,股东大会只能就商法或公司章程所规定的事项进行决议(《商法》第230条之10)。这样,股东大会就不能再被称为万能机关,然而有关公司经营的基础事项以及董事、监事的选任、解任,依然属于股东大会的权限。因此,股东大会作为公司最高机关的地位并没有改变。(14) 第二,规定由全体董事构成董事会,即合议体体制,由董事会决定公司的业务执行以及其他不属于股东大会决议的事项(《商法》第260条)。与此同时,确立了代表董事制度,规定代表董事是代表公司及执行业务的专门机关(《商法》第261条)。通过这一修改,董事本身就不再是公司的机关,而只是公司业务执行决定、监督机关(即董事会)的成员了。(15) 第三,在该次商法修改之前,监事的监督监察权限针对的是董事业务执行(即业务监察)以及公司财务(即会计监察)两个方面,而且业务监察是重点,而在该次修法之后,业务监察权被划归为董事会,监事只具有会计监察权了。
1950年商法修改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业务执行机关的分化,在法律上明确规定了股份有限公司的业务执行机关由全体董事组成的董事会及董事会选任的代表董事两方面构成。然而,关于董事会与代表董事的关系一直存在着争议,争论的焦点在于:能否由股东大会选任代表董事?派生机关说(有力说)认为,在理论上,董事会本来具有公司业务执行的全部权限,但由全体董事执行公司业务难以实现经营的机动灵活性以及效率性,作为应对这一实际问题的方法,商法规定,由董事会选任代表董事来行使业务执行权,即代表董事是从董事会中派生出来的机关。因此,代表董事的选任是董事会固有的权限,即使动用公司章程,也不能将此权限划归股东大会。(16) 并立机关说(通说)则认为,将并非时常处于活动状态的董事会解释为公司的业务执行机关是不切实际的;(17) 董事会是决定公司业务执行的机关,即意思决定机关,而代表董事是担当执行本身以及公司代表行为的机关,即执行机关,董事会与代表董事并立构成股份有限公司的执行机关,因此代表董事不是董事会的代表机关,而是公司的代表机关。(18) 基于上述理由,在理论上将代表董事的选任划归为股东大会的权限是有可能的。
(三)1981年商法修改对股份有限公司业务执行机关的调整
1981年商法修改是在企业丑闻频繁发生的背景下,为防止企业的不正当行为、强化企业自主监督机能而进行的。为强化董事会对代表董事业务执行监督的手段,此次修改对以下四点进行了改善:1.明确了董事会的业务监督权限(《商法》第260条第1款);2.明确了董事会的决议事项(《商法》第260条第2款);3.规定了代表董事须向董事会进行报告的义务(《商法》第260条第3款(19));4.明文规定了董事召集董事会的权限(《商法》第259条第1款)。
1981年以前,《商法》在规定由董事会决定公司业务执行(《商法》第260条前段)的同时,在其他各条文中还具体规定了董事会的决议事项(《商法》第231条、第261条第1、2款、第280条之2第1款本文、第296条、第260条后段、第265条、第293条之3第1、2款等)。1981年的商法修改在此基础上又明确规定了五项董事会决议专属事项,即:1.重要财产的处分与受让;2.大额借款;3.重要使用人的选任、解任;4.重要组织的设置、变更及废止,以及5.除此之外的重要业务执行。上述事项只能由董事会而不能委任代表董事决定(《商法》第260条第1、2款)。这样做的目的在于,鉴于业务执行机关的实权向代表董事集中的现实,通过增设上述规定来挽回日渐形式化的董事会机能。(20)
三 企业自主引进执行官制度
在上文中我们看到,日本围绕股份有限公司业务执行机关的改革主要是在经济形势变化以及发生企业丑闻的背景下,为应对公司经营机构合理化的需求而进行的。它的改革内容可概括为两个方面,即对业务执行机构进行合理化调整以及强化对业务执行的监督。然而,尽管在立法上做了各种努力,实际收效却差强人意。因此,一部分企业开始自发探索实践新的制度,其中就包括执行官制度的自发引入。
执行官制度的原初模式是美国的经理制度,(21) 将其最先引进日本的是索尼公司。(22) 尽管在当时它还不是商法上的法定制度,但自1997年起,自发引进该制度的日本企业开始急剧增多,(23) 这对此后2002年商法正式引进该制度产生了巨大影响。
(一)商法制度偏离了公司业务执行机关的应有状态
1950年商法修改之际设置董事会制度的宗旨在于,通过董事之间在董事会会议上的讨论及交换意见,以期能够达到慎重、妥善行使董事会权限的目的。(24) 然而,在日本很多股份有限公司中,董事这一地位被用于对职工工作业绩优秀的一种奖赏,因此董事的职位就越设越多,有些公司的董事更是达到数十名。(25) 而董事会人数过多,势必导致无法对议题进行实质性的讨论,也无法进行灵活机动的意思决定。因此,有些大公司为了确保意思决定的机动性,除了在公司中设置法定的董事会之外,还自发设置了由特定少数董事组成的常务会。(26) 然而,由于有关公司经营的重要事项多在常务会上讨论及决定,这就很容易架空董事会的权限,使董事会沦为一个仅仅在形式上追认常务会决定的机关。而且,由于董事会的成员多为本公司职工出身,实际上都有赖于代表董事的提拔,所以根本无法期待由他们形成对代表董事的有效监督。(27) 董事作为公司的职工处于被代表董事指挥领导的地位,这就使经营主体与监督主体之间的关系变得十分微妙。(28) 在上述问题不能解决的情况下,日本商法中的董事会无论作为意思决定机关还是监督机关,都无法实现该制度设计的初衷。
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些上市公司开始尝试在商法允许的自治范围内对董事会进行改革。具体的措施包括:1.削减董事的人数;2.采用执行官制度;3.引进独立董事制度;4.缩短董事的任期。(29)
(二)索尼公司率先自发引进执行官制度
索尼公司是日本乃至全球著名的电子产品生产制造商,因其技术先进、产品精良,在世界各国拥有庞大的消费群,该公司的股票也早就在全球主要的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公司效益以及对股东的回报,在日本企业中也是名列前茅的。但由于受到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日本泡沫经济破灭的影响,该公司的股票一度急剧下跌,引起海外特别是美国机构投资者的青睐,外国投资者的持股比例曾超过40%。(30) 1997年6月,该公司对经营机构进行了改革,(31) 将当时为数38名的董事削减至11名(包括3名外部董事),解任了原18名董事,将其他9名董事改任为执行官。(32) 很多知名公司以此为契机,纷纷引进该制度,执行官一度成了日本经济界瞩目的对象。2002年,《日本经济新闻》进行了一次企业问卷调查,其中60%的受访企业表示已引进或预定在2002年以后引进该制度。(33)
(三)对企业自发引进执行官制度的评价
对于企业自发采用执行官制度,正面的评价认为:这一制度的采用削减了公司董事人数,由此可能促使董事会发挥其作为合议体的(决策)机能,不仅如此,由于采用执行官制度,减少甚至杜绝了职工兼任董事的现象,也有可能强化董事会的监督机能。(34) 的确,上述2002年《日本经济新闻》实施的企业问卷调查结果中也显示,绝大多数引进该制度的公司认为引进后产生了正面的效果。比如,近六成公司称本公司董事会的意思决定变得迅速了,进而有四成以上的公司称公司的部门负责人可专心自己所负责的业务,因此,基本上可以达到引进该制度的目的。
然而,也有专家指出了如下的问题:(35) 1.董事与执行官兼任较多,易造成业务执行机能分离的不彻底;2.由于商法上没有直接规定执行官制度,各个公司就执行官的名称及定位不统一,容易导致董事职责模糊;3.很多引进了执行官制度的公司并未建立起针对执行官的业绩评价体系及报酬体系;4.还有一些公司引进执行官制度只是在赶时髦,目的性不明确。除此之外,还有学者提出应该将执行官能否作为股东代表诉讼的对象作为探讨课题,(36) 当执行官与公司代表董事、业务执行董事同样参与业务执行时,应该考虑通过法律修改使其能够成为股东代表诉讼的对象。(37)
四 商法正式确立执行官制度
(一)2002年通过修改商法等法律引进设置委员会公司
在要求立法改善公司治理的呼声下,日本分别于2001年、2002年4次修改《商法》及《商法特例法》。其中,2002年5月的修改对股份有限公司的业务执行机关进行了重组。
2002年2月13日,日本法务省法制审议会公司法部会经过多次审议,发表了有关公司法修改的法律案纲要。该纲要的宗旨在于,进行以公司机关为核心的改革,为公司经营的合理化提供法律制度上的支持。(38) 该纲要在法务省成文后提交国会,并于2002年5月22日通过、2003年4月1日开始实施。2005年新《公司法》在相应的有关条款中,进行了重申及确认。
通过此次修改,股份有限公司的机关设计出现了三个选择。即满足一定法定条件的股份有限公司既可继续沿用以往的公司机关,也可通过修改公司章程成为设置重要财产委员会公司(39) 或设置委员会公司。其中影响最大的是设置委员会公司体制的建立。(40) 因为它为大型公司(资本金5亿日元以上或负债额在200亿日元以上的股份有限公司)或被视为大型公司的公司(资本金1亿日元以上但不足5亿日元,且在公司章程中注明就公司的会计报表、附属明细表接受审计员审计的股份有限公司)采用业务执行与监督分离的美国式公司治理结构提供了制度上的可能性。
具体而言,大型公司或被视为大型公司的公司可通过公司章程规定,接受适用有关设置委员会公司的特例(《商法特例法》第1条之2第3款/新《公司法》第2条第1款第12项),即成为设置委员会公司。设置委员会公司的董事会中必须设置三个委员会:提名委员会、审计委员会及薪酬委员会(《商法特例法》第21条之5第1款/新《公司法》第2条第1款第12项),各委员会由3名以上董事构成、其中过半数须为外部董事(《商法特例法》第21条之8第4款/新《公司法》第400条第1-3款)。设置委员会公司中不得设置监事(《商法特例法》第21条之5第2款/新《公司法》第327条第4款)。此外,设置委员会公司必须设置1名以上的执行官(《商法特例法》第21条之5第1款第4项/新《公司法》第402条第1款)负责公司的业务执行(《商法特例法》第21条之12第1款第2项/新《公司法》第418条第1款第2项),就一定的业务执行事项,还可委任执行官决定(《商法特例法》第21条之7第3款、第21条之12第1款第1项/新《公司法》第418条第1款第1项、第416条第4款本文)。此类公司的董事不执行公司业务,而是作为董事会成员参与业务执行的决定并监督执行官及其他董事的职务执行(《商法特例法》第21条之6第2款本文、第21条之7第1款/新《公司法》第415条、第416条)。
(二)设置委员会公司中的执行官制度
1.执行官的意义
执行官是设置委员会公司实施业务执行的必要常设机关,执行官本身不具有公司代表权(《商法特例法》第21条之12第1款第2项、第21条之5第1款第4项/新《公司法》第418条、第402条第1款)。设置委员会公司以外的股份有限公司也可任意设置执行官(执行经理),但它的法律地位或是董事(兼任董事时),或是使用人即职工(不兼任董事时),而在设置委员会公司中,除作为董事会成员的董事之外,必须设置作为法定业务执行机关的执行官。
2.执行官的选任、解任、任期、人数、资格等
执行官的选任、解任只能由董事会决定(《商法特例法》第21条之13第1、6款/新《公司法》第402条第2款、第403条第1款),该决定权限不能授予执行官(《商法特例法》第21条之7第3款第4项/新《公司法》第416条第4款第9项)。在设置委员会公司中,董事的选任、解任议案由提名委员会决定,但执行官的选任、解任不能由提名委员会决定。这是因为,董事会同时还决定执行官之间的职务分工、指挥命令关系以及执行官之间其他的关系(《商法特例法》第21条之7第1款第3项/新《公司法》第416条第1款第1项),这些事项与执行官的选任、解任权限密切相关,所以有必要将其作为业务执行决定的重要环节划归为董事会专属。(41) 针对这一点,有学者指出,应该将执行官选任议案的决定权限交给提名委员会。其理由是,作为董事会的成员,董事可兼任执行官(《商法特例法》第21条之13第5款/新《公司法》第402条第6款)(42),且可兼任执行官的董事人数没有限制。(43) 但也有专家指出,由于法律并没有禁止提名委员会的成员董事(即提名委员)兼任执行官,因此,若允许提名委员会决定执行官的选任、解任议案,且由提名委员兼任代表执行官,就很容易产生实质上由代表执行官决定执行官的危险。(44)
执行官的任期截止到就任后1年之内召开的有关最终决算的股东大会年会之后最早召开的董事会结束之时(《商法特例法》第21条之13第3款/新《公司法》第402条第7款本文)。
因为董事会为合议体制,所以作为其成员的董事需在3名以上(《商法》第255条/新《公司法》第331条第4款),而执行官为独任体制,故一人或数人均可(《商法特例法》第21条之5第1款第4项/新《公司法》第402条第1款)。即使有数名执行官,在法律上也无需规定必须组织类似董事会的合议体。当然,为实施董事会授权的业务决定及业务执行,也可以组织类似执行官会议的合议体。(45) 在设置数名执行官时,应避免“无所任执行官”,即没有特定分管领域的执行官,因为这样会使第三者产生该执行官拥有全部业务执行权限的错觉。(46)
3.执行官的薪酬
执行官的薪酬由薪酬委员会决定(《商法特例法》第21条之11第1款/新《公司法》第409条)。这是因为,董事会的成员董事可兼任执行官,且兼任人数未做限制,若将执行官的薪酬决定权限划归董事会,将会有“自己给自己发薪”的危险。(47)
4.执行官的地位
执行官的地位大都准用董事的相关规定。执行官与公司形成委任关系,因此向公司承担善管注意义务及忠实义务(《商法特例法》第21条之14第7款第4、5项/新《公司法》第330条、第419条第2款、第355条;《民法典》第644条)。就执行官与公司的竞业交易、利益冲突交易,采取与董事同样的规制(《商法特例法》第21条之14第7款第5项/新《公司法》第419条第2款、第356条),即此类交易均须征得董事会的同意(《商法》第264条、第265条/新《公司法》第356条),就此类交易给公司带来的损失,执行官需与同意该交易的董事向公司承担连带清偿或赔偿责任(《商法》第266条/新《公司法》第423条)。
5.执行官的权限
(1)一般权限
执行官的一般权限为:①基于《商法特例法》第21条之7第3款(新《公司法》第416条第4款本文)规定的董事会决议,决定董事会委任的事项;②执行设置委员会公司的业务(《商法特例法》第21条之12/新《公司法》第418条)。执行官业务决定权限的范围是:除法律上规定的董事会专属决定事项之外由董事会委任的事项。董事会不能将下列事项交由执行官决定(《商法特例法》第21条之7第3款/新《公司法》第416条第4款但书):①有关经营基本方针等的基本事项;②决定组成各委员会的董事;③决定公司与审计委员间诉讼的公司代表人;④选任、解任执行官;⑤决定代表执行官;⑥基于公司章程的规定,应由董事会决议的董事、执行官责任的免除;⑦认可公司的财务会计报表;⑧在股份转让限制公司中,认可股份转让及指定受让人;⑨有关公司收购自己公司股份的事项;⑩决定招集股东大会;(11)决定向股东大会提交议案;(12)决定公司营业转让及受让;(13)决定事后设立的内容;(14)决定应召集董事会会议的董事;(15)认可董事、执行官与公司的竞业交易及决定行使介入权;(16)认可董事及执行官进行的与公司利益冲突的交易;(17)认可转让限制新股预约权的转让;(18)金钱分配;(19)决定股份交换合同书的内容;(20)决定有关股份转移时股东大会认可的事项;(21)决定公司分立计划书的内容;(22)决定公司分立合同书的内容;(23)决定公司合并合同书的内容;等等。
(2)执行官的董事会召集请求权
执行官被赋予董事会召集请求权(《商法特例法》第21条之14第3、4款/新《公司法》第417条第2款),但该权限并非直接召集董事会的权限。执行官需首先向特定董事,即由董事会决定的、专门接受董事会召集请求的董事(《商法特例法》第21条之7第1款第4项/新《公司法》第416条第1款第1项)提交记载会议审议事项的书面请求,在该书面请求提出后5日之内,董事会没有发出以自书面请求之日起2周之内的日期为开会日的召集通知时,提出该书面请求的执行官可自行召集董事会(《商法特例法》第21条之14第4款、《商法》第259条第4款/新《公司法》第417条第2款)。执行官被赋予董事会召集请求权的理由在于,执行官在执行业务时,常需要股东大会的决议,例如股份的交换与转移、公司分立、合并等(《商法》第353条、第365条、第374条、第374条之17、第408条第1款/新《公司法》第309条),而股东大会的召集决定需要董事会的决议,因此法律赋予了执行官这项权限。不过,执行官并非董事会成员,另外出于防止代表执行官控制董事会的考虑,法律没有认可执行官的董事会出席权。
(3)提起各种诉讼的权限
就以下几项诉讼,执行官被视为董事,具有诉讼提起权(《商法特例法》第21条之14第6款/新《公司法》828条第2款):股东大会决议撤销之诉(《商法》第247条/新《公司法》第831条)、股东大会决议无效或不存在之诉(《商法》第252条/新《公司法》830条)、新股发行无效之诉(《商法》第280条之15/新《公司法》第828条第2款第2项)、股份交换无效之诉(《商法》第363条/新《公司法》第828条第2款第11项)、股份转移无效之诉(《商法》第372条第2款/新《公司法》第828条第2款第12项)、公司新设分立无效之诉(《商法》第374条之12第1款/新《公司法》第828条第2款第10项)、公司吸收分立无效之诉(《商法》第374条之28/新《公司法》第828条第2款第9项)、减少公司资本无效之诉(《商法》第380条第1款/新《公司法》第828条第2款第5项)、公司合并无效之诉(《商法》第415条第1款/新《公司法》第828条第2款第7项、第8项)以及公司设立无效之诉(《商法》第428条第1款/新《公司法》第828条第2款第1项)。
6.执行官的报告说明义务
执行官有义务出席股东大会并就股东要求的事项进行说明(《商法特例法》第21条之14第7款第3项、《商法》第237条之3/新《公司法》第314条)。执行官需每3个月至少1次向董事会报告其职务执行情况(《商法特例法》第21条之14第1款前段/新《公司法》第417条第4款前段),在有生病等正当事由的情形下,可由其代理人代为报告(同条同款后段)。在董事会提出要求时,执行官需出席董事会并就被要求的事项进行说明(《商法特例法》第21条之14第2款/新《公司法》第417条第5款)。但应注意,执行官并没有出席董事会的法定当然权限,而只是应董事会要求出席董事会,并就相关事项进行说明报告。(48)
在各委员会提出要求时,执行官还有义务出席该委员会并就要求的事项向委员会进行说明(《商法特例法》第21条之9第1款/新《公司法》第411条第3款)。此外,当执行官发现有可能会给公司带来严重损害的事实时,应立即向审计委员会报告该事实。
7.代表执行官与表见代表执行官
设置委员会公司须通过董事会的决议规定代表公司的代表执行官,执行官为一人时,则该人自然成为代表执行官(《商法特例法》第21条之15第1款/新《公司法》第420条第1款)。在日本,因为公司代表权一般被解释为公司业务执行权的对外表现,(49) 所以法律规定公司代表人从执行官中选出。代表执行官的“代表”不是指执行官的“代表”,而是指“公司代表权”,因此可以选任数位代表执行官。这样,将全体执行官都选任为代表执行官也是可能的。(50)
代表执行官行为的效果归属于公司,其权限基本上与传统公司中的代表董事相同,即涉及有关公司营业的一切诉讼内及诉讼外的行为,公司对代表执行官代表权施加的限制,不能对抗善意第三人(《商法特例法》第21条之15第3款、《商法》第78条第1款、《民法》第54条/新《公司法》第420条第3款、第349条第4、5款)。在此意义上,代表执行官与传统公司中的代表董事具有同样的功能。(51)
代表执行官在原则上单独代表公司,不过为防止滥用公司代表权,可通过董事会决议规定由数名代表执行官共同代表公司(《商法特例法》第21条之15第2款/新《公司法》删除该规定(52))。不过,即使在此情况下,第三人对共同代表执行官中的一人进行的意思表示,也将对公司产生效力(《商法特例法》第21条之15第3款、商法第39条第2款/新《公司法》删除该规定)。
设置委员会公司对无代表权的执行官赋予易使第三者误认为具有代表权的名称时,为保护信赖该名称的善意第三人,有必要使该执行官基于该名称实施的行为效果归属于公司。因此,《商法特例法》设置了相当于表见代表董事制度的表见代表执行官规定(《商法特例法》第21条之16/新《公司法》第421条)。
8.执行官、代表执行官的责任
(1)对公司的责任
在设置委员会公司中,经营责任的核心为执行官的责任,而董事的责任则主要是监督责任。(53) 执行官对公司的责任由以下几个方面构成:其一,任务懈怠责任。执行官怠于履行职务时,必须赔偿由此对公司产生的损害(《商法特例法》第21条之17第1款/新《公司法》第423条)。这一责任基于执行官债务不履行的一般责任发生事由,属过失责任。没有全体股东的同意不得免除该责任(《商法特例法》第21条之17第2款/新《公司法》第424条),不过,可基于《商法特例法》第21条之17第6款(新《公司法》第425条第1款第1项),以执行官4年的薪酬、代表执行官6年的薪酬为限予以减轻。其二,违法盈余分配的责任。在设置委员会公司中,执行官就违法盈余分配行为对公司承担以下清偿责任(《商法特例法》第21条之18第1款/新《公司法》第462条):①执行官向董事会提交违反《商法》第290条第1款(新《公司法》第461条)规定的议案,且董事会基于该议案的决议进行了违法盈余分配时,就基于该决议进行盈余分配的金额;(54) ②执行官进行违反商法第290条第1款规定的盈余分配时,就盈余分配的金额;执行官向董事会提交违反《商法》第293条之5第3款(新《公司法》第461条)规定的议案,且董事会基于该议案的决议进行了违法盈余分配时,就基于该决议进行盈余分配的金额;(55) 执行官进行违反《商法》第293条之5第3款规定的盈余分配时,就盈余分配的金额。不过,上述责任并非无过失责任,只要执行官证明了就上述行为并未怠于注意,即不承担该责任(《商法特例法》第21条之18第1款但书/新《公司法》第462条第2款)。此外,以上责任的免除须经全体股东的同意(《商法特例法》第21条之18第2款、第21条之17第2款/新《公司法》第462条第3款但书)。其三,利益冲突交易责任。就得到董事会认可的利益冲突交易给设置委员会公司带来损失时,进行该交易的执行官以及基于董事会的授权决定该交易的执行官对公司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商法特例法》第21条之21第1款第1项/新《公司法》第423条第1、3款)。不过,执行官如能证明其就该职务执行并未怠于注意时,可免除责任(《商法特例法》第21条之21第1款但书/新《公司法》第423条第3款)。其四,有关股东权利行使的利益提供责任。《商法》第295条第1款(新《公司法》第120条第1款)规定,公司不能就股东权利的行使向任何人提供公司或子公司的财产利益。违反该规定的董事或执行官向设置委员会公司承担与该利益相应金额的清偿义务(《商法特例法》第21条之20第1款前段/新《公司法》第120条第4款本文)。此责任为无过失责任,无全体股东的同意不得免除(《商法特例法》第21条之20第2款/新《公司法》第120条第5款)。此外,现行商法也不认可减轻该责任。(56)
(2)对公司第三人的责任
与董事一样,执行官的职务履行存在恶意或严重过失时,必须向第三人承担责任,赔偿由此产生的损失(《商法特例法》第21条之22第1款/新《公司法》第429条第1款)。此外,由于执行官就股份认购证、财务报表等规定中应记载的重要事项进行虚假记载、登记或公告而使第三人产生损失时,执行官也必须向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商法特例法》第21条之22第3款/新《公司法》第429条第2款第1项)。
(3)董事与执行官的连带责任
在董事或执行官对设置委员会公司或者第三人造成损失负有赔偿责任的情况下,若其他董事或执行官也对该损失负有赔偿义务,他们为连带债务人(《商法特例法》第21条之23/新《公司法》第430条)。
(4)和股东代表诉讼的关系
法律认可设置委员会公司的股东采取股东代表诉讼的方式追究董事及执行官对公司的责任(《商法特例法》第21条之25、《商法》第267条至268条之3/新《公司法》第847条)。
(三)设置委员会公司体制的采用状况
2003年4月,设置委员会公司体制开始正式实施,至同年6月的股东大会年会为止,正式采用该制度的公司共有55家,包括四类:1.重视集团战略的公司(例如日立制作所,该企业集团有18家企业采用);2.鉴于海外投资者的增加而采用该制度的公司(例如索尼、三菱电机);3.控股公司及其旗下公司(例如野村控股公司及其旗下的公司);4.由于加入到海外企业旗下而采用该制度的公司(例如西友公司、日本电信控股公司等)。(57) 也有一些公司虽继续沿用传统治理结构,却也设置了任意执行官(例如丰田汽车、松下电器产业等)。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采用设置委员会公司体制的公司中,董事长不兼任首席执行官(CEO)的现象比较多,(58) 看来很多公司都意识到应将业务执行与监督分离。
五 日本公司治理论中的执行官制度
(一)如何看待公司治理问题中的执行官制度
如上所述,公司治理的目的是为了排除不正当经营及促进经营的效率性,前者是经营健全性的问题,后者是经营效率性的问题。一般认为,日本公司治理长期以来未能充分发挥作用的原因在于,未明确划分董事会的监督机能与经营团队的经营机能、没有采用类似美国的执行官制度(59) 以及监事地位不够独立。日本公司法制也一直想通过代表董事、董事会以及监事之间的协调与制衡来改善治理结构,但效果不佳。为此,日本在法制上做了多种尝试,近几年更是相继采用了外部监事(1993年)、外部董事(2002年)与执行官(2002年)制度,前者限于传统公司,后两者限于设置委员会公司。同时,前两者的目的在于强化监督,而执行官制度的采用则更多是为了促进效率。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日本国内外商业竞争激烈、市场瞬息万变,将企业经营决策的大权都交给人数相对较多、需以一定程序召集的董事会并不现实,故有必要视公司自身情况,将一部分经营决策权交给执行官来应对上述局面。具体来讲,日本通过效仿美国采用设置委员会公司体制,代表执行官只要接受了董事会的授权,就可自由进行资金调配,决定新股发行、处分库存股、新股预约权及公司债等。此外,代表执行官还可单独决定使用人的选任、解任,这样就提高了业务执行及业务重组的灵活机动性。
(二)设置委员会公司体制与执行官制度存在的问题
从整体上来看,尽管设置委员会公司体制没有强制性地要求股份有限公司经营机关(即业务执行机关)的决策、执行与监督彻底分离,但相对明确地划分了董事、董事会以及执行官在经营机构中所扮演的角色,在这一点上,也许比日本传统公司治理结构略胜一筹。但是,从对业务执行监督的角度来看,设置委员会公司的董事会能否扮演好监督的角色,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外部董事作用的发挥,而外部董事制度的采用是否必然会提高董事会的监督机能还有待考证,(60) 外部董事的独立性是否能够得到保证也受到一定的质疑。(61) 在美国,对外部董事的独立性要件甚至涉及排除公司业务执行者的亲属及公司的交易相对人,而在日本,对于外部董事只要求其现在或过去未担任公司或该公司子公司的业务执行者或使用人(《商法》第188条第2款第7项之2/新《公司法》第2条第1款第15项),似嫌不够。除此之外,还有学者担心,采用设置委员会公司体制会弱化对经营的违法性监督。(62) 因此,设置委员会公司能否提高监督实效,还需要通过实践来检验。
如何处理法定执行官(即设置委员会公司的执行官)与任意执行官(即非设置委员会公司的执行官)的关系,也是一个有必要解决的问题。两者虽有很多共同点,但却分属于不同的法律层次,由于外观、名称相似,因而容易产生混淆,作为实务对策,应在命名时设置一些差异。此外,法定执行官的责任原则上为过失责任,而非设置委员会公司的董事原则上为无过失责任,对此有学者指出,各委员会与董事会监督权限的明确划分,不能成为减轻执行官责任的必然理由。(63)
(三)如何看待公司治理模式的选择制
通过2002年商法等的修改,日本大型公司可在传统式(即设置监事公司)与美国式(即设置委员会公司)两种治理模式中进行选择。设置委员会公司体制也许会在某种程度上改善日本公司经营机构现存的一些问题,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一定优于传统治理模式。如上所述,该体制的成功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外部董事作用的发挥,而即使在美国,外部董事制度也有很多问题有待克服。(64) 美国新经济神话破灭所引发的以安然事件为代表的公司财务丑闻,表明主要由外部董事组成的大型上市公司董事会在公司的内部监督机能上并无优势。同时,在日本,采用传统治理模式的公司也有非常出色的业绩表现,例如丰田汽车、松下电器产业、佳能等。日本没有废除传统治理模式而是采用选择制,这本身就说明根据日本立法机构的考量,没有足够的理由证明美国式治理模式优于传统治理模式。因此,选择制并不是向将来全面采用美国式治理模式的过渡措施,而应看作是针对不同历史、不同个性企业在制度上所采取的不同应对办法。决定公司治理模式优劣的不应是法律,而应是市场,公司法的作用应该是给企业发展排除障碍,创造更大的发挥空间,这也许是选择制给我们带来的最大启发。
注释:
①参见[日]末永敏和:《公司治理与公司法》,中央经济社2000年版,第3页。
②参见[日]末永敏和:“公司治理”,《法学家》1999年第1155号,第122页。
③参见[日]川口幸美:《外部董事与公司治理》,弘文堂2004年版,第1页。
④参见[日]伊藤纪彦:“近代公司法的出发——劳埃斯勒商法草案与明治23年商法”,载滨田道代编:《北泽正启先生古稀祝贺论文集——日本公司立法的历史展开》,商事法务研究会1999年版,第46页。
⑤关于法典论争,详参见[日]今井洁、浅木慎一:“法典论争与国产公司法的成立”,载滨田道代编:《北泽正启先生古稀祝贺论文集——日本公司立法的历史展开》,商事法务研究会1999年版,第79-124页。此外,高仓史人的论文“商法典的成立”也对日本新、旧商法典的成立及法典论争有所介绍。参见高仓史人:“商法典的成立”,《法学家》1999年第1155号。
⑥旧商法颁布于1890年,原定于1891年1月1日起施行,后由于法典论争而延期,延期理由为:过于照搬外国法,不符合日本实情。该法的一部分于1893年7月1日开始施行,其余部分于1898年7月1日施行,但由于1899年6月开始实施新商法,即现行商法,旧商法除破产篇外被全部废除。参见平井宜雄、新堂幸司、金子宏等编:《新版法律学小词典》,有斐阁1996年版,第176页。
⑦参见[日]大隅健一郎:《新版公司法概说》,有斐阁1967年版,第102页。
⑧参见[日]谷川久:《股东大会》,载竹内昭夫、鸿常夫、上柳克郎主编:《新版注解公司法(5)》,有斐阁2002年版,第15页。
⑨然而,在当时公司的实际运作中,通过章程规定设置相当于董事会机构的公司也很多。参见[日]河本一郎:《现代公司法》,商事法务研究会1999年版,第365页。不过,在当时,这些都是公司自发组织的机构,并非商法上的法定机关。
⑩参见[日]片木晴彦:“监事的适法性监察与妥当性监察”,载北泽正启、滨田道代编:《商法的争点I》,有斐阁1993年版,第166页。
(11)例如,英国于1948、1967、1976、1980、1981、1985、1989年对公司法进行了重大修改。美国于1946年由美国律师协会起草了《示范商业公司法》,纽约、加利福尼亚等很多州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公司法修改,其后的多次修订也影响了极大部分州的公司法修改。德国于1965年制定了新的《股份法》,法国于1966年制定了《商事公司法》。详见大隅健一郎:《新版股份有限公司法变迁论》,有斐阁1987年版,第226-227页;铃木竹雄:《新版公司法》(全订第三版),弘文堂1991年版,第36页。
(12)例如授权资本制度、董事会制度、股东代表诉讼制度等。
(13)参见[日]上村达男:“被占领与公司法修改——今天的意义”,《法学家》1999年第1155号,第22页。
(14)参见[日]本间辉雄、谷濑村邦夫编:《公司法》(第6版),法律文化社1999年版,伊藤纪彦执笔部分,第179页。
(15)然而,对于这一解释,也有反对意见认为,董事依然是股份有限公司的机关。参见[日]加美和照:“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董事会与代表董事”,载加美和照编:《董事的权限与责任》,中央经济社1994年版,第10-11页。
(16)参见[日]户塚登:“美国股份有限公司中的业务执行”,《阪大法学》1961年第39号,第84-86页;[日]中井宏、大隅健一郎:《新版公司法(中卷1)》,有斐阁1983年版,第131页。
(17)参见[日]弥永真生:《公司法》(第4版),有斐阁1999年版,第159页。
(18)参见[日]石井照久:《公司法》(上卷),劲草书房1967年版,第300-301页;田中诚二:《公司法详论》(上卷)(三全订),劲草书房1993年版,第610页;[日]铃木竹雄、竹内昭夫:《公司法》(第3版),有斐阁1994年版,第265-266页。
(19)2002年商法修改后,改为商法第260条第4款。
(20)参见[日]北泽正启:《股份有限公司法研究3》,有斐阁1997年版,第41页。
(21)日本的公司治理结构中原来没有法定的经理职位,在日本公司实务中自行设置的“社长”,相当于英文中的manager,我国通常翻译为“经理”,与美国公司中的执行官有所不同。
(22)参见[日]吉田春树:《执行官》,文春新书2000年版,第8页。
(23)参见[日]神田秀树:“公司法的现代化与公司治理”,载《商法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中央经济社2005年版,第37页。
(24)参见[日]田边光政:《公司法要说》(第五版),税务经理协会1998年版,第249页。
(25)参见[日]近藤光男:“董事会制度的改革:有关设置监事公司”,《金融商事判例》第1160号(2003年2月增刊号),第136页。
(26)公司自发设置“常务会”的现象在20世纪60年代的日本就已非常普遍,上市公司尤为显著。注册资本金在50亿日元以上的股份有限公司约九成设有“常务会”。其设置的理由在于克服董事会规模膨胀影响经营的灵活机动性问题。由“常务会”讨论的问题主要包括:1.向董事会提出的议案;2.董事会决议的实施;3.有关代表董事业务执行的重要事项;4.公司日常业务的执行;5.公司各部门业务的实行方针与计划;6.公司各部门之间的联络与意见协调等。“常务会”所决定的事项,几乎不会被董事会否决或变更。详见京都大学商法研究会:“股份有限公司经营机构的实态”,《商事法务研究》1963年第289号,第13-18页。
(27)参见[日]田村达也:《公司治理》,中公新书2002年版,第99-100页。
(28)参见[日]宍户善一:“公司治理的日美比较与对商法修改讨论的启示”,《民商法杂志》1998年第117卷4、5号,第609-610页。
(29)参见[日]河和哲雄:“董事会改革的现状与课题——有关设置委员会公司等的公司治理”,载《公司法修改的基本问题》,商事法务股份公司2003年版,第102-104页。
(30)参见吴建斌:《最新日本公司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49页。
(31)索尼公司当时经营机构改革的主要内容包括:1.在商法规定的基础上,将董事会定位于决定索尼企业集团经营基本方针的机构;2.从本公司内外挑选善于集团经营的人选作为董事候选人;3.为强化对业务执行的监督,增加外部董事人数;4.为使董事会能够切实有效地进行审议及意思决定,确保董事的合理人数(将来逐渐将董事人数减至5到6名);5.在引进执行官制度的同时,配套推进经营意思决定机能及监督机能与执行机能的分离。参见[日]森本滋:“公开公司的经营机构改革与执行官、监事制度(一)”,《法学论丛》1999年第145卷第1号,第19页。此外,关于索尼公司在1997年实施的经营机构改革以及索尼公司执行官制度的实际状况,在前索尼董事会副董事长桥本纲夫、索尼经营业务室课长西村茂的“索尼的机构改革”一文中有较详细介绍,参见《商事法务单行本》1998年第214号,第1-14页。
(32)参见[日]河本一郎、岸田雅雄、森田章、川口恭弘:《日本公司法》(新订第三版),商事法务研究会2000年版,第38页。
(33)该企业问卷调查内容载于2002年6月20日《日本经济新闻》早刊。
(34)参见[日]末永敏和:“公司法与日本的特殊性:世界标准与日本标准”,载《21世纪的法与政治——大阪大学法学部创立50周年纪念论文集》,有斐阁2003年版,第244页。
(35)参见[日]藤川信夫:“经营机构的制度设计”,载末永敏和、长谷川俊明、稻叶阳二编:《转型为设置委员会公司及引进重要财产委员会的法律实务》,中央经济社2003年版,第209-210页。
(36)参见[日]森田章:《公司法的规制缓和与公司治理》,中央经济社2000年版,第148页。
(37)参见[日]江村信行:“关于执行官制度的立法论考察”,《企业法学》2002年第19号,第106页。
(38)参见[日]始关正光:“平成14年商法修改的概要”,《法学家》2002年第1229号,第6-8页。始关正光当时任法务省大臣官房参事官,直接参与了2002年商法修改的起草和审议。
(39)设置重要财产委员会公司的起因:《商法》第260条第2款规定,公司重要财产的处分、大额借款等事项必须通过董事会决议。因董事会的召开势必影响到经营的机动性,故2002年通过修改商法规定,自2003年起,在满足法定条件的前提下,可由少数董事构成的重要财产委员会来替代董事会行使上述权限。可设置重要财产委员会的公司为大型股份有限公司或《商法特例法》上被视为大型股份有限公司的公司,其董事人数应在10名以上,且其中有1名以上的外部董事。重要财产委员会由3名以上的董事构成,委员由董事会决定(《商法特例法》第1条之3),不必须是外部董事。重要财产委员会制度是法律对实际生活中存在的“常务会”的追认,同时也明确了对其的规制。参见[日]早川胜:“特集:2002年公司法修改全貌(二):重要财产委员会与大型公司以外的公司—审计员的设置”,载《法学教室》2002年第265号,第25页。
(40)参见[日]落合诚一:“特集:2002年公司法修改全貌(二):概观2002年商法修改”,载《法学教室》2002年第265号,第6页。
(41)参见[日]前田庸:《公司法入门》(第9版),有斐阁2003年版,第447页。
(42)审计委员会的成员董事(或称审计委员)不能兼任执行官(《商法特例法》第21条之8第7款)。
(43)参见[日]末永敏和、吉本健一:《解读新公司治理》,中央经济社2002年版,第179页。
(44)参见[日]长谷川俊明、水谷嘉伸:“设置委员会公司的运营”,载末永敏和、长谷川俊明、稻叶阳二编:《转型为设置委员会公司及引进重要财产委员会的法律实务》,中央经济社2003年版,第292页。
(45)参见[日]神田秀树:《公司法》(第6版),弘文堂2005年版,第166页。
(46)参见[日]武井一浩:“向设置委员会公司转型的实务应对”,《商事法务》2003年第1659号,第64-65页;[日]上村达男:“大型公司运营机构的选择”,《判例Times》2002年第1093号,第88页。
(47)参见[日]弥永真生:《2002年商法修改解说》,有斐阁2002年版,第84页。
(48)参见[日]加美和照:《新订公司法》(第8版),劲草书房2003年版,第324页。
(49)参见[日]山口幸五郎:“代表董事”,载竹内昭夫、鸿常夫、上柳克郎编:《新版注解公司法(6)》,有斐阁2002年版,第131页。
(50)参见[日]泽口实:“法定执行官的选任、权限等与任意执行官的关系”,《商事法务》2002年第1643号,第40页。
(51)参见[日]岸田雅雄:《公司法入门》(第5版),日本经济新闻社2003年版,第343页。
(52)关于共同代表制度的删除:现行共同代表制度的宗旨在于,利用共同代表人之间的制衡来防止代表权的滥用。该制度在现实中几乎无人利用,即使被利用,也常常引发公司与交易相对人之间的纠纷。此时,交易相对人一般都能通过表见代表董事规定(《商法》第262条)的类推适用得到保护,因此,共同代表的登记制度在实际中基本发挥不了作用。鉴于此,新《公司法》把共同代表定位于公司内部对董事等代表权进行的限制,并将其从登记事项中删除。参见[日]相泽哲(法务省大臣官房参事官):《新公司法一问一答》,商事法务股份公司2005年版,第124页。
(53)参见[日]上村达男:“特集:2002年公司法修改全貌(二):设置委员会公司”,《法学教室》2002年第265号,第24页。
(54)《商法》290条第1款规定:(股份有限公司)可以资产负债表上的净资产额扣除下列金额后所得的金额为限进行盈余分配:(1)资本额;(2)资本公积金及盈余公积金的合计额;(3)该决算期中需积累的盈余公积金的金额;(4)其他法务省令规定的金额。
(55)《商法》第293条之5第1款(中期分配)规定:会计年度为1年的公司可在公司章程中规定,在1个会计年度内以1次为限,基于董事会决议,在一定日期向股东进行金钱分配……第3款:第1款的金钱分配可以从年终资产负债表上的纯资产额中扣除下列(1)至(4)项的金额后,加入(5)至(7)项的金额为限进行:(1)在最终决算期的资本及公积金的合计额;(2)在有关最终决算期的股东大会年会上进行累积盈余公积金及金钱分配时,需累积的盈余公积金的合计额;(3)在有关最终决算期的股东大会年会上决定的从盈余中分配、支付的金额或转入资本的金额,以及依第210条第1款的决议决定的股份取得总价额的合计额;(4)除前3项之外的法务省令规定的金额;(5)在公司最终决算期后减少的资本公积金、盈余公积金的金额中扣除有关该资本公积金、盈余公积金减少的《商法》第289条第2款第1项所规定的金额;(6)从最终决算期后减少的资本额中扣除有关资本减少的《商法》第375条第1款第1项及第2项规定总额的金额;(6之2)在有关最终结算期后损失处理议案认可决议时,《商法》第289条第1款中所规定的应填补资本亏损的金额;(7)除前3项之外的法务省令规定的金额。
(56)预定于2006年5月起施行的新公司法已将该责任改为过失责任,董事、执行官只要证明自己就此业务并未怠于注意的,就可免除责任(《公司法》第120条第4款但书)。
(57)资料来源:“采用设置委员会公司体制的主要公司一览及采用公司的动向与倾向”,《商事法务》2003年第1669号,第33页。
(58)参见[日]江头宪治郎:“日本开放式公司中董事的义务:特别针对监督义务”,《商事法务》2004年第1693号,第6页。
(59)参见[日]川滨升:“董事会的监督机能”,载森本滋、川滨升、前田雅弘编:《确保企业的健全性与董事的责任》,有斐阁1997年版,第41页。
(60)2001年的“安然事件”使我们看到了即使在外部董事制度发达的美国也存在很大的经营监督问题。安然公司当时是名列全美第5位的大公司,一直被作为公司治理的楷模,其董事会共有17名董事,其中15名是外部董事,包括美国会计学权威的斯坦福大学商学院长、原联邦期货交易委员会委员长、原英国资源大臣等重量级人物,结果还是没有实现有效的监督。
(61)参见[日]吉本健一:“外部监事及外部董事之外部性的意义与功能”,《阪大法学》2002年第52卷第3、4号,第93页。
(62)2002年、2003年日本大阪大学法学院末永敏和教授在清华大学、华东政法学院、上海社会科学院等的公司法讲座中多次提到:对公司经营的监督分效率性监督与违法性监督,董事会的监督来自于经营机关内部,更适合效率性监督,而监事的监督来自于经营机关的外部,更适合违法性监督,因为设置委员会公司中不设置监事,所以势必会弱化对经营违法性的监督。
(63)参见[日]滨田道代:“验证:公司法修改之(六):董事、执行官的义务、责任、责任减轻、代表诉讼、和解”,《商事法务》2003年第1671号,第36页。不过,预定于2006年5月起施行的新日本公司法已就这一问题做了调整,非设置委员会公司的董事将与设置委员会公司的董事、执行官一样,原则上承担过失责任(《公司法》第423条、第428条)。
(64)参见[日]山城将美:“公司治理论中董事会的定位”,载《21世纪的企业法制——酒卷俊雄先生古稀纪念》,商事法务股份公司2003年版,第844-845页。
注释:
说明:第一,“执行官”一词的日文为“执行役”以及“执行役员”,尽管译成中文时均为“执行官”,但两者在法律意义上分属不同层次。前者是指“设置委员会公司”中法定的、必要的业务执行及代表机关(《商法特例法》第21条之12第1款第2项、《商法特例法》第21条之5第1款第4项/新《公司法》第418条),后者是公司任意设置的业务执行机构,其与公司的关系主要是雇佣关系,法律上的意义为使用人。两者在本文中都将涉及。“设置委员会公司”是指:通过2002年日本商法、商法特例法的修改以及2005年新公司法的确认,“大型公司”可在两种公司治理结构中进行选择,分别是日本传统治理结构与在董事会中设置提名、薪酬、审计三委员会、由执行官取代董事执行公司业务并废除监事制度的治理结构。采用后者的公司就是所说的“设置委员会公司”。因该制度效仿美国,与美国公司治理结构相类似,因此采用该模式的公司又被称为“美国式公司”,与此相对应,称维持日本传统治理模式的公司为“传统公司”。此外,又因两种公司形式上的最大区别在于是否设置监事,所以“传统公司”又被称为“设置监事公司”。“大型公司”是指,在有关公司最终会计年度的资产负债表中,作为公司资本金记入的金额在5亿日元以上,或在负债部分记入的总额在200亿日元以上的股份有限公司(《商法特例法》第1条之2第1款/新《公司法》第2条第6项)。第二,本文中所出现的法律主要有《商法》、《商法特例法》及《公司法》,因2005年法律修改的结果使日本公司法的法律形式出现巨大变化,故在此特别说明。在2005年之前,日本并无形式上统一的公司法(或称公司法典),一般所说的日本公司法主要是指日本《商法典》第2篇(公司篇)、《商法特例法》、《有限公司法》、《商业登记法》等的总和。由于有关公司的法律十分分散,近几年接二连三地修改又造成条文剧增,原有体例根本无法承载。在此背景下,作为“公司法现代化”改革的一个重要环节,新公司法聚散为整,将分散在商法各单行法中的法律汇整为一部统一的公司法典,于2005年6月29日国会上通过,并于2006年5月起施行。本文中所标注的《商法》及《商法特例法》的条文名称序号是截止到2006年4月底的现行法,标注为“新公司法”的是与现行法相对应的、自2006年5月起施行的新法条文序号,前者与后者之间将用“/”符号隔开。第三,本文中出现的法律均为日本法律,文中将不再重复注明“日本”二字。第四,本论文标注中的参考文献,除吴建斌教授的《最新日本公司法》之外,其余均为在日本出版发行的日文文献,为便于读者理解,文献资料名称及出版发行单位名称等均采用中文标注。此外,如无特别注明,本文讨论的公司均指股份有限公司尤其是上市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