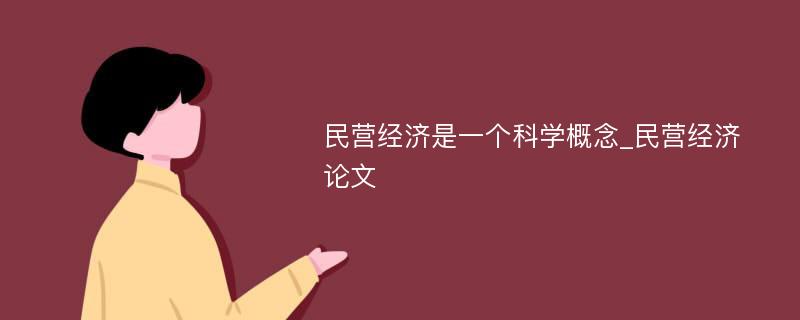
民营经济是一个科学的概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是一个论文,民营经济论文,概念论文,科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江泽民同志在十五大报告中指出:“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一切反映社会化生产规律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都可以大胆利用。要努力寻找能够极大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公有制实现形式。”这既是对改革开放以来行之有效的企业经营方式的充分肯定,又是鼓励人民群众继续“大胆利用”和“努力寻找”新的公有制实现形式。
改革实践上的突破创新要求从理论上作出新的概括。在国有大中型企业经营方式的改革上,我们已经打破了“国有只能国营”的僵化模式,采用了承包经营、股份经营、中外合作经营等经营方式。国有小型企业、城镇集体企业和乡镇企业广泛采用了承包经营、租赁经营、出售即通过改变所有制而改变经营方式、股份合作制等经营方式。面对公有制经济多种多样的实现形式,作为经济理论工作者,理应作出新的理论概括,创造出与现代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涵盖面广的经济概念和范畴,丰富社会主义经济理论。1995年5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已经指出:“民营科技企业是发展我国高技术产业的一支有生力量,要继续鼓励和引导其健康发展”。在这里,党中央把近年涌现出来的科技企业中的非国家举办的部分,如集体的、合伙的、个人的、私营的、中外合作的、中外合资的科技企业,高度概括为“民营科技企业”。这一理论概括十分准确,据此推论,还可以概括出“民营工业企业”、“民营农业企业”、“民营商业企业”、“民营物资企业”等概念,进而将各类民营企业再概括为“民营经济”,则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但是白永秀、马晓强先生发表在某刊1997年第3 期上的《“民营经济”的提法质疑》(以下简称《质疑》)则认为,“民营经济”的提法“模糊不清”,“不科学”,“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有害无益”。其理由,一是这一提法“不能准确反映包含在其中的各种类型的所有制性质,模糊了人们的视线”;二是“模糊了相同所有制经济成分之间的具体区别及其运行特征,使国家很难有针对性地采取对策,进行有效管理”;三是“没有对‘民营’中的‘民’作出明确界定”。基于上述理由,《质疑》认为“应及早摒弃这一提法”。笔者读后,对文中观点及其结论不能苟同,现提出商榷,向二位作者并借此机会向经济工作者、经济理论工作者求教。
笔者以为,《质疑》一文所持观点的方法论值得研究。
第一,党的十五大明确把“减少”国有经济比重作为“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的主要内容。随之而来的是:国有国营的企业数量又将有较大幅度下降,而非国营企业的数量将大幅度上升。面对改革实践的这一大手笔,迫切需要有一个与“非国家经营”同义的经济概念来表述,以便和“国营”概念相对应。十几年来,随着改革实践的深入发展,已经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创造了“混合所有制经济”概念(见十四届三中全会文件),作为对股份制、股份合作制、中外合资、合伙制等企业的理论概括;在个人收入分配方面,我们有了“按要素分配”概念(见十五大报告),作为对按劳分配以外的分配有了“多种分配方式”(见十三大报告)的理论概括。既然在所有制和分配方面都有新的概念创造出来作为对改革实践的理论概括,那末作为表层经济关系的经营方式,在打破国营模式多年以后,为何不能使用“民营”这一概念作为对90%以上企业多种经营方式的理论概括呢?事实上,“民”是相对于“国”而言,既然有“国营”提法,自然也应有“民营”提法,当这一提法和经济学融为一体时便成为经济概念,成为经济理论大厦上的一块砖石。如果说,“国营”是指国家经营的话,那么,“民营”则是指“民间经营”,其外延就是:全社会所有各类企业中,除了国家经营的企业以外,均系“民间经营”的企业,具有质的规定性。显然,“民营经济”的提法既能客观反映社会经济现实,又符合形式逻辑有关集合概念的要求。“民营”和“国营”两个提法在外延上互相排斥,其外延相加之和为最邻近的一种概念——经营主体,二者之间的关系是矛盾关系。《质疑》只允许“国营经济”提法存在,而不允许“民营经济”提法存在,也是不合逻辑的。
第二,“国营经济”和“民营经济”都有一个“所有”问题,即经济学范畴的生产资料所有制,二者是处于微观经济中的不同层次:“经营”处于表层关系,“所有”处于深层关系,它们在法律上的表现便是经营权和所有权的关系。所有权和经营权是可以分离的,同一种所有制的企业可以有不同的经营方式,同一种经营方式也可以为不同的所有制企业服务。我国正处在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过程中,已经创造了除国有国营以外的所有制形式及其经营方式,诸如国有私营、国有集营、集有集营、集有私营、合伙经营、承包经营、租赁经营、委托经营、私有私营、私有国营(如中船公司向外商租借商船投入运营、私营企业家牟其中从俄罗斯购回民航飞机出租给四川西南航空公司投入运营)等等。可见,“民营经济”提法是以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这一产权理论为前提条件的,是市场化改革、打破全民所有制国有企业只能实行国营模式的必然结果,应当给予以充分肯定。《质疑》断言“民营经济”提法不科学,其原因是混淆了“所有”与“经营”是两个不同的经济学范畴。不仅如此,作者受传统观念影响,认为只能谁所有就谁经营,而否认了所有权与经营权是可以分离的这一基本经济现实。
第三,民营经济产生于市场经济,是市场经济中的企业经营方式。党的十五大指出:“一切反映现代化生产规律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都可以大胆利用。”作为反映现代经营方式的理论概括,“民营经济”概念在市场经济国家早已广泛流行。我国正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市场经济中的企业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企业,显然是一无级别、二无上级的市场主体。国家对这样的企业是不存在直接管理问题的,而是通过调节市场,让市场影响企业活动。这同计划体制下的企业活动情况有着根本性区别,那是国家直接管理到企业活动的经济,企业的产供销活动都受到政府部门的直接干预。《质疑》所说的“民营经济”“提法模糊了相同所有制经济成分之间的具体区别及其运行特征,使国家很难有针对性地采取对策,进行有效管理”,显然就是作者混淆了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区别,模糊了两种不同体制下的企业运行特征。既然是国家对市场经济中的企业不直接管理,怎么还会存在“有效管理”的问题呢?!
第四,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企业所有制性质往往被十分看重,是“唯成分论”,凡国有企业就是“长子”,便可获得“政策倾斜”及其优惠。相反,凡是非公有制企业则被打入“另册”,只能另眼看待。十五大明确肯定“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非常科学的,符合真正的市场经济中各类所有制企业都享受国民待遇,处于同等地位而不存在“长子特权”和“所有制岐视”之惯例的。这就是说,作为资源配置方式的市场经济并不看重处于深层经济关系的企业“成分”的,相反,企业所有制性质在趋于淡化。诚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的市场经济,而公有制形式包括国有经济,城乡集体经济、基金会、职工持股会、股份制经济中的公有资产部分等,其中国有经济居主导地位。若主导部分即国有企业中1000家大企业由国家掌握,企业数量占预算内工业企业的0.8%,资产占46.44%,销售收占52.64%,利税占67.3%,则已足以控制、支配国民经济,若加上公有制经济的其他部分,如集体经济、股份制企业中的公有股本,则产值肯定超过GDP的60%, 足以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即使1000户大企业都按国营模式(这是极而言之,其实大多将改制为股份制企业,亦属民营经济之例), 则民营企业在国有企业中就占 99.2%。由于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各类企业处于平等竞争地位,所以企业“成分”主要体现在注册登记的时候。只要“主导”部分一能保值增值,二能占居主导地位,就能保证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
总之,如何对待“民营经济”的提法,涉及方法论问题,如果是站在传统计划经济的立场看“民营经济”,则横看竖看不顺眼;如果是站在市场经济的立场上看“民营经济”,则这正是市场经济所要求的,它就象市场经济一样不存在姓“资”姓“社”的问题。
《质疑》一文反对“民营经济”提法的几点理由始终隐含着的前提是:“民营经济”姓“资”,无异于“私有化”的另一种提法。《质疑》说:“民营化就是私营化、私有化”。江泽民同志在庆祝建国40周年讲话中指出:我国实行坚持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发展多种经济形式的方针,“不是要实行‘私有化’”。这里所使用的“私有化”是加了引号的,含有“所谓的”的意思,即指并非搞私有化。这和有的同志随意使用“私有化”一词给人扣帽子、打棍子完全不是一回事。显然,对待“私有化”概念,不能从教条出发,望文生义,断言其社会制度属性。我们对待国有企业中的通常作法,即把股份制、股份合作制、兼并、租赁、出卖、合资嫁接、破产、委托经营、加强管理,以及无偿划拨、裂变剥离、先售后股、退市进郊等等这些市场经济国家通行做法运用到改革实践中,并不含有“抛弃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意思,相反,由于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主体条件下的改制形式,其结果必然是加强和巩固社会主义公有制,笔者因此以为,只要是在坚持公有制主体在国有经济起主导作用的前提下,吸取市场经济国家的通常作法,用于改革国有企业的实现形式,以激发其活力,都属正常现象,决不能轻易扣上“私有化”帽子,加以鞭挞。
《质疑》一文把不能反映“各经济类型的所有制性质”作为反对“民营经济”提法的一条重要理由,在方法论上是不足取的。经济学上有不少概念并不存在单一的“所有制性质”,如“市场经济”、“现代企业制度”、“财产混合所有的经济成分”(见十四届三中全会文件)、“资本组织形式”、“股份制”(见十五大报告)等等,这些提法为不同类型的所有制所共有。人们在使用“混合经济”等提法时并不担心会出现丧失阶级立场问题。经济学的这种理论概念,正像人们对“人”的不同划分方式一样:人,固然有“穷人”和“富人”,“好人”和“坏人”的区别,但还有许多不存在社会阶级属性的概念,人们并不能作出“好人”和“坏人”的区分。自从1979年以来,人们对阶级成分已经趋于淡化,中央决定,对干部填写的履历表上也不再设“成分”栏目。入党、参军、提干时也不再计较本人成分问题。“人”是如此,为何对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还要搞“唯成分论”呢?
我们既然是搞市场经济,那么只要在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坚持共产党领导的前提下,按照邓小平同志的三个有利于的原则,具体作法则可以探索。《质疑》作者把“民营经济”的提法斥之为“在理论上与实践上都有害无益”的。党中央、国务院早已使用了“民营科技企业”的概念,对于这样一个有“红头文件”为依据的提法,《质疑》作者竟斥之为“有害无益”,显然不能算是一种严肃慎重的行为。既然党中央、国务院已经率先在科学技术领域提倡“民营”,那么将其由个别上升为一般——“民营经济”,又有何不妥呢?上述分析表明,《质疑》否定“民营经济”提法的所谓理论依据是经不住推敲的。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推广使用“民营经济”提法,有利于国有企业改革中大胆实行多种经营方式,加速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进程;有利于各类不同所有制企业开展平等竞争,享受国民待遇;有利于中国企业同国际上市场经济国家的企业接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