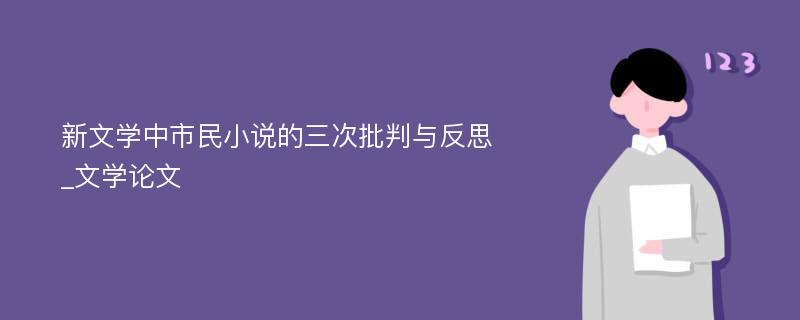
新文学对市民小说的三次批判及其反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文学论文,市民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市民小说又称为民国旧派小说,或鸳鸯蝴蝶派小说。三个名称以市民小说最为贴切,它最能说明这一小说流派的基本性质和基本形态。从文化取向和美学取向上说,市民小说是传统小说的延续,是传统小说在20世纪的一种改良体。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新文学对市民小说进行了三次批判,一次是“五四”时期,一次是30年代初,一次是40年代前期。这三次批判的内涵实质、是非得失以及它们之间的互动关系,是本文所分析的问题。
一
民初的文坛是市民小说的一统天下。新文学一登上文坛,就开展了一场对市民小说的批判运动。这场运动声势浩大,鲁迅、周作人、沈雁冰、李大钊、罗家伦、郭沫若等人都写过大量的批判文章。
“五四”新文学作家对市民小说的批判集中在两个问题上。
首先他们认为中国市民小说是“非人”的文学,代表性的文章是周作人的《人的文学》。周作人在文章上说:“我们现在应该提倡的新文学,简单的说一句,是人的文学。应该排斥的,便是非人的文学。”他还从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对“人”做了界定,他说:“我们要说人的文学,须得先将这个人字略加说明。我们所说的人,不是世间所谓天地之性最贵,或圆颅方齿的人。乃是说从动物进化的人类。其中有两个要点,(1)‘ 从动物’进化的,(2)从动物‘进化’的。”从这样的观点出发,他对中国传统小说进 行了批判。他说:“中国文学中人的文学,本来极少。从儒教道教出来的文章,几乎都 不合格。”他不仅这么说,还将眼前的市民小说归纳为“色情狂的淫书类”、“迷信的 鬼神书类”、“神仙书类”、“妖怪书类”、“奴隶书类”、“强盗书类”、“才子佳 人书类”、“下等谐谑书类”、“黑幕类”、“以上各种思想和合结晶的旧戏”共10种 。他认为这些都是非人的文学,应该加以排斥。
从以上的批判文字可以看出,新文学与市民小说的分歧主要在文化观念上。“人的文学”的核心是人道主义和人本主义。人道主义和人本主义来自于西方,用周作人的话来说,是用欧洲的“人的发现”给中国文学“辟人荒”的。因此,新文学的文化观念具有的是“世界的眼光”。市民小说是中国传统小说的延续,它表现的是中国传统的文化精 神,其中做人的道德规范是核心内容。因此,市民小说实际上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道德小 说,具有的是“中国的眼光”。在新文化运动的文化背景下和赶上世界发展潮流的社会 心态中,市民小说代表着陈旧、落后和僵化,被新文学作家所指责也就理所当然。
第二个问题是新文学作家认为市民小说是一种“记账式”小说,对此问题分析得最为透彻的是沈雁冰的《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注:沈雁冰《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载《小说月报》1922年第13卷第7号。)。沈雁冰在文章中指出了市民小说的两大缺陷:
一、他们连小说重在描写都不知道,却以“记账式”的叙述法来做小说,以至连篇累牍所载无非是“动作”的“清账”,给现代感觉敏锐的人看了,只觉味同嚼蜡。
二、他们不知道客观的观察,只知主观的向壁虚造,以至名为“此实事也”的作品,亦满纸是虚伪做作的气味,而“实事”不能再现于读者的“心眼”之前。
应该说,沈雁冰对民初市民小说的分析相当到位。是描写还是“记账”看似仅是一种小说的叙述方式的选择,其核心却是小说的叙述中心的不同。描写强调的是文学性,强调的是以写人为叙述中心的创作模式。“记账”强调的记载性,它是以记事为叙述中心的创作模式。清末民初外国小说被大量地翻译到中国来,市民小说的创作明显地受到外国小说的影响。惯于用传统文体进行创作的市民小说开始发生变化,在小说结构的布局上,倒叙成为了常用文体;在叙事视角上,第一人称叙述已经普遍使用。但是市民小说家没有认识到外国小说的这些叙述方式是为了更好的写人而设置的,他们仅仅就事论事地对外国小说简单地模仿,小说的叙事模式还是传统的写事模式。以写事为中心,无论小说的结构和叙事视角发生怎样的变化,只能是“记账式”的冗长而琐碎地描述,因为要把事情说清楚,只能这么写。这样的小说反映问题自然显得肤浅而表面化。问题还在于,民初的市民小说家为了弥补“记账式”所带来的记叙的敷陈和阅读的沉闷,就更加追求情节的离奇。这些离奇的情节由于常常缺乏生活根据,显得漏洞百出,使人们怀疑他们除了才力的不逮之外,还有创作态度的粗疏和随意。(注:此时市民小说粗制滥造的情况十分严重。例如标为“惨情小说”的周瘦鹃的《留声机片》。小说写一个失恋的男青年到恨岛独居了8年。临死之前将自己对女友的爱恋之情灌在留声机片上寄给女友。女友听到这样的遗言竟然在激动和惭愧中死去了。像这样的胡编乱造弥漫于当时的市民小说创作中。)
其实,对传统小说的批判从“晚清小说界革命”就开始了。梁启超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就将中国传统小说看作为“中国群治腐败之总根源”,将它们斥之为“诲淫”“诲盗”。但是梁启超的批判并没有取得好的效果,他所渴望的“新小说”并不多见,倒是他所否定的那些传统小说在新时期有了进一步地发展。“五四”新文学作家不同,他们对市民小说的批判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在他们批判市民小说的同时,新小说登上了文坛,并且成为了中国小说的“正宗”,这就是最大的实绩。“五四”新文学能够取得成功,其原因就在于:与梁启超空泛地批判不一样,新文学作家在批判的同时,还以外国的思想理论和文学理论作为参照系,建立了新的文学观念,那就是“人的文学”。
“五四”新文学作家不仅开展文化批判,还对市民小说的艺术模式作了精到的分析。面对新文学作家的文化批判,市民小说作家们还能嘀咕几声,(注:在当时的小报《晶报》上有一些对新文学的批判不满的文章。这些文章主要从道德层面上嘲讽新文学宣扬“不孝”,攻击他们的“自由恋爱”是“自由性爱”,说新小说是“外国小说”,看不懂。文学观念和美学层面上的应对几乎一篇也没有。)面对新文学作家的艺术分析,他们只能默默地承受,他们不得不承认,新小说作家的分析是有道理的,新小说的创作模式的确比他们高明。
梁启超是一个思想宣传家,他创作的小说《新中国未来记》还只是一则政治寓言。说这样的小说就是“新小说”,从创作文本上说,它根本无法说服那些传统的文人们。“五四”新文学作家就大不相同了,他们是思想宣传家,同样他们又是作家。他们在提出新的文学观念和批判市民小说创作文本的同时,拿出了“新小说”的实绩。鲁迅、郁达夫、叶绍钧、冰心等人用他们的作品告诉读者小说应该怎样写。无论是思想深度上还是美学表现力上,与这些“新小说”的实绩相比,市民小说都相形见绌了。
这是一次压倒性的批判,也是一次绝对性的批判,新文学作家对市民小说采用的是非 你即我的完全排斥的态度。这种态度在破坏阶段特别有效,取得了明显的效果。但是, 这种态度有没有缺陷呢?还是有的。它不能承认对方的优势,更不愿接受对方的特长, 所以一到达建设阶段,其弊病就暴露出来了。
二
30年代初有两件事轰动一时。一是向恺然的《江湖奇侠传》中的部分章节被改编成电影《火烧红莲寺》;二是张恨水的小说《啼笑因缘》的发表。从下面的两段文字中可以看出这两件事在当时的影响之大:
《火烧红莲寺》对于小市民层的魔力之大,只要你一到那开映这影片的影戏院内就可以看到。叫好、拍掌,在那些影戏院里是不禁的,从头到尾,你是在狂热的包围中。( 注:沈雁冰《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载《小说月报》1922年第13卷第7号。)
《九尾龟》、《广陵潮》、《留东外史》之类的东西,也至今还占领着市场,甚至于要“侵略”新式白话小说的势力范围,例如今年出版的张恨水的《啼笑因缘》居然在“新式学生”之中有相当的销路。(注:瞿秋白《鬼门关外的战争》,载《瞿秋白文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
这上两段文字摘自于新文学作家当时的两篇批判市民小说的理论文章。我之所以摘录 它们主要说明两个问题,一是说明新文学对市民小说批判的起因;二是要说明新文学作 家文学创作定位上的某些失误。
这一次批判的起因看起来是《火烧红莲寺》和《啼笑因缘》在社会上产生的影响,其深层的原因是新文学虽然自“五四”以后取得了“正宗”的地位,但没有得到广大的市场,而失去了“正宗”地位的通俗小说还是有着广大的读者群。瞿秋白此时说了这样一段话:“新文学尽管发展,旧式白话的小说,张恨水,张春帆,何海鸣……以及连环画小说的作家,还能够完全笼罩住一般社会和下等人的读者。这几乎是表现新文学发展的前途已经接近绝境了。”(注:瞿秋白《鬼门关外的战争》,载《瞿秋白文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话虽说得过分些,却反映了一个事实:“五四”以来的新文学虽然发展着,但它只是知识阶层的读物,“一般社会和下等人的读者”则“完全”被“旧式白话小说”笼罩住,这样下去新文学将“接近绝境”。看到了问题,但是怎样将读者从市民小说那里争取过来呢?30年代的新文学作家还是采取的“五四”时期的态度,对市民小说采用了一股脑儿地批判的态度。除了瞿秋白以外,鲁迅、沈雁冰、夏征农、钱杏邨、郑振铎等人此时都发表了批判市民小说的文章。这一次批判虽然炮火十分猛烈,但是收效甚微,并没有改变新小说阅读面狭小的局面,更没有瓦解市民小说的读者群。
这种局面形成的根本原因是新文学作家对市民小说的读者群、市民小说的文化观缺乏科学的分析。沈雁冰对市民小说的读者作了这样的分析:“这些小说的读者大部分是小市民——即所谓小资产阶级。”(注:沈雁冰《封建的小市民文艺》,载《东方杂志》1933年第30卷第3号。)将市民小说的读者定位于小市民并不错,市民小说主要表现的是市民阶层的思想和愿望;广大小市民是市民小说的主要的读者层,问题是如何评价这些小市民。在中国人口中农民占绝大多数,市民占有的比例并不大,然而在当时的中国,真正能读文识字的也只是市民阶层,他们的人数虽少,却是文学作品的主要读者群。城市的范围当然不能和农村相比,但它是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它代表着社会风气的迁徙和时代心理的变化,是整个社会的动脉。如此重要的读者群,新文学作家却不屑一顾,将他们斥之为“小资产阶级”“封建意识的小市民”“游离不定的小市民以及一般闲者”(注:见沈雁冰《封建的小市民文艺》;夏征农《读啼笑因缘》,载《文学问答集》,1935年10月生活书店出版。)。这么重要、有如此庞大的读者群就在他们的斥责声中被轻轻地推到一边去了。相反,市民小说作家却在这个领域里如鱼得水,他们主要以都市为创作背景,写出了发生在城市中的各个重大事件:“五四”运动、“五卅”事件、军阀混战、工厂罢工、金融危机、“一·二八”事变等;写出了城市中的各种人物的生活状态和心理状态,有买办、政客、商人、金融家、军阀,也有工人、店员、学生,甚至白相人,混混儿、妓女等等;同时他们也表现出城市的人文景观,有交易所、银行、跑马场、游艺场、大饭店,也有工厂、作坊、街道和弄堂。市民小说作家很多本身就是小市民,他们把发生在身边的事诉诸于文字,即使是简单的事件描述,市民阶层都感到亲切,容易产生共鸣,市民阶层自然就成为了市民小说稳定的读者层。新文学作家把当时中国的最主要的读者群都否定掉了,其作品又怎么能走向大众呢?
除了表现市民的生活以外,二三十年代的市民小说还表现出中国传统的人文精神。除暴安良、因果报应、慈悲为怀、尊老爱幼、赤胆心肠……中国这些传统的人文精神是有不少封建糟粕,但更多的是作为优良的道德标准融化于中国人的是非判断和行为规范之 中了,而且随着时代的发展传统人文精神的内涵也在不断地进行着调整和改良。中国的 现代化的过程属于被迫的形态,是在一次次对外战争的失败和一次次民族屈辱之中被迫 走向现代化的,物质的落后是承认的,是客观事实所证明的,传统的人文精神虽然受到 了冲击,但始终就没有承认失败过,始终是中国社会的基本的精神力量。清末民初以来 ,西方现代文化观念进入中国,也影响了一些社会精英分子的理论思维,但始终没有变 更中国社会主体的文化形态。在二三十年代,国内军阀连年混战,国外日本对中国的侵 略日益加深,民族的自尊心受到了极大的损伤,传统的文化精神作为中华民族的基本精 神被极大地激发起来。此时的市民小说所宣扬的传统的人文精神符合中国大众心目中的 价值判断,又由于他们的作品特别注意表现现实社会和反映现代情绪,作品或正或反、 或直或曲地反映出了时代的要求,如武侠小说并没有直接反映现实生活,但作品宣扬的 除暴的精神和尚武的精神同样具有着客观的时代意义。但是新小说作家对他们的文化观 念却不是这样认识,他们从阶级论的观点出发,对他们的作品采取了一概否定的态度, 言情小说、狭邪小说、武侠小说自不必说,就是思想意义和艺术表现均不俗的“国难小 说”,他们也是全盘否定,说这些小说只是“在国难的事件中打打趣而已”,是“封建 余孽作家在小说方面的活动的成果”。(注:钱杏邨《上海事变与鸳鸯蝴蝶派文 艺》,载《现代中国文学论》,1933年6月出版。)这种说法显然是缺少客观分析的态度 ,其根本所在是对中国的传统文化精神缺少科学的认识。对传统的文化精神缺少科学的 认识就不能使作品接近人民大众,瞿秋白此时对新小说与读者的关系作出这样的评价: “社会上的所谓文艺读物之中,新式小说究竟占什么位置呢?他实在亦只有新式知识阶 级才来读他。固然,这种新式知识阶级的读者社会比以前是扩大了,而且还会有更加扩 大些的可能。然而,比较旧式白话小说的读者起来,那就差得多了。一般社会不能容纳 这种新式小说,并不—定是因为他的内容——他们连读都没有读过,根本不知道内容是 什么,他们实在认为他是外国文的书籍。”(注:瞿秋白《鬼门关外的战争》。)不注意 到传统的文化精神,只是一味地阐述“新思想”、“新观念”,这样的小说只能被“一 般社会”视作为“外国文的书籍”。
与“五四”时期的默默承受不同,在这一次的批判中,市民小说作家开始有所反击。1932年《珊瑚》杂志创刊,创刊号上,主编范烟桥提出了“新旧兼容”的口号:“以艺术的文学为中心不分新旧,有掌故的记载,有文艺的研究,有新思潮的介绍,有旧文学的整理,深入各个阶级得到读者的满意,广及边塞域外有一致的好评。”(注:范烟桥《过去的回溯》,载《珊瑚》1933年第24号。)范烟桥的这段话还仅仅说明一个态度。在该刊上发表众多的理论文章的“说话人”就说得更明白了,他说:“新文学派里,确有当得起‘新’,够得上‘文学’的作品。《礼拜六》派里,也有极‘新’,极‘文学’的作品。”(注:从第13号开始《珊瑚》开辟“说话”栏目,由署名“说话人”对当前作家作品进行评论。至48期《珊瑚》停刊时共发表文章18篇。“说话人”显然是笔名,真名不详。)他对当时的“爱国小说”和“国难小说”作出了评价,他说:“《林家铺子》确是一篇观察极深刻的小说,但是《往哪里逃》和它的姐妹篇《食指短》,实在是一·二八背景下很有意义的写实小说,我们似乎不应该因着他署名‘卓呆’而不拉上新文坛去。否则这个‘新’字,不过是一层面幕,还有她的庐山真面在里面呢?”(注:《说话(三)》,载《珊瑚》1932年第15号。)从这些言论可以看出,所谓“新旧兼容”是指小说的价值是“读者的满意”,只要能得到“好评”,新旧文学都应该存在;至于怎样分小说的新旧,不能根据作者的姓名,而应看作品的内容。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受到批判的市民小说作家说话似乎很有底气,这个底气就是他们的作品很受读者的欢迎。
三
对市民小说的第三次批判是四十年代初,主要的文章是叶素的《礼拜六的重振》和佐思的《礼拜六派新旧小说家的比较》。与此同时通俗小说作家也开展了“通俗文学运动”。这次批判和前两次不同,不再是双方的互相排斥,而是在“同一阵营”的认可基础上的客观分析,所以与其说这是一次批判,不如说这是一次讨论。
叶素和佐思的文章主要是两个观点,一是“我们是依然热望礼拜六派在今日民族的共同责任下重新振奋起来的,尤其是那些曾经建下过许多优秀成就,为巨万大众所热爱的有能之士,我们的整个国民文艺依然对他们具有极大的期待”。新文学作家第一次对市民小说采取了认同的态度,这是抗日战争的背景下统一战线的建立而要求的。二是以客观的态度分析市民小说,他们认为市民小说的“新人”是孱弱的,“即使是从文字技巧的方面看来,这些新人的无力也是可惊的。”“时间会使某些新文学家(指市民小说的 年轻作家,引者注)衰败,也会使某些旧小说家新生。”在对市民小说的“新人”批评 的同时,他们肯定了张恨水、包天笑“老人”的小说,认为他们的作品“充满了民族解 放的精神”(注:佐思《礼拜六派新旧小说家的比较》,魏绍昌编《鸳鸯蝴蝶派研究资 料》第127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从市民小说四十年代的创作实绩看,他们 的批评是有一定道理的。
新文学作家一直称市民小说为“鸳鸯蝴蝶派”小说或“礼拜六”小说。对这两个称呼,四十年代的市民小说作家都不满意,他们提出了通俗文学的口号。1942年通俗市民小说作家在《万象》第2年第4期和第5期上推出了“通俗文学运动专号”。这两期专号上 共发表了6篇文章,它们是陈蝶衣的《通俗文学运动》、丁谛的《通俗文学的定义》、 危月燕的《从大众语说到通俗文学》、胡山源的《通俗文学的教育性》、予且的《通俗 文学写作》。这些文章在总结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的同时,提出了“通俗文学”的美 学原则。
首先他们就否认自己是“鸳鸯蝴蝶派”或“礼拜六”作家。《万象》主编陈蝶衣说:“从我开始‘操觚’的时候起,就根本没有赶上鸳鸯蝴蝶派’那个时代,所以我对于所谓‘鸳鸯蝴蝶派’实在是很隔膜的。”(注:陈蝶衣《编辑室谈话》,载《万象》1943年第13期。)这段话基本上代表了四十年代市民小说作家的态度。在他们的眼中,“鸳鸯蝴蝶派”是指民国初年的作家作品,是“旧派”小说。那他们是不是新小说作家呢?也不是,他们认为新小说作家是鲁迅、茅盾、巴金等人,这些人的作品是“新派”小说。那他们是什么作家呢?他们自认为是超乎“旧派”和“新派”的通俗文学作家。他们的“通俗文学运动”也就是从这样的思路出发的。
他们认为当前阻碍中国文学发展的根本原因是由于中国文坛上出现的新旧文学两军壁垒造成的,而这种两军壁垒的状况又是人为的。“中国的文学,在过去本来只有一种,自古至今,一脉相传,不曾有过分歧。可是自从‘五四’时代胡适之先生提倡新文学运动以后,中国文学遂有了新和旧的分别,新文学继承西洋各派的文艺思潮,旧文学则继承中国古代文学的传统。虽然新文学家也尽有许多在研究旧文学,填写旧诗词,旧文学家也有许多转变成新文学家,但新旧文学双方壁垒的森严,却是无可否定的事实。”他们认为,新旧文学双方都不能使得文学大众化。新文学具有新的思想和意识,但欧化的形式使得普通大众望而生畏;旧文学的表现形式在中国虽然具有较强的适应性,但有些思想意识明显地落伍于时代了,现在应该将新旧文学的优点结合起来,建立中国通俗文学的体系,只有通俗文学才能真正做到文学的大众化。“我们提倡通俗文学的目的,是想把新旧双方森严的壁垒真正打通,使新的思想和正确的意识可以藉通俗文学而介绍给一般大众读者。”(注:陈蝶衣的《通俗文学运动》,载1942年《万象》第2年第4期。)从这些言论中可以看出,他们是想在“新文学”和“旧文学”之上建立一个“通俗文学 ”,并让中国文学统一在“通俗文学”的旗帜下,这显然是他们的一种理想。从文学渊 源和他们的创作实际来看,他们都是从民初的“鸳鸯蝴蝶派”发展而来的,按照他们的 话来说,是“旧”派文学,只不过他们在新的时期有了新的变化罢了。但他们对中国文 学的现状的分析还是有道理的,对中国文学发展的意见还是有积极意义的。历史证明各 据一垒的新旧文学都不能创作出既有时代气息又具有中国作风的文学作品来,要使文学 大众化,真正地得到发展,打破新旧壁垒的确是一个必要的前提。
这些“通俗文学运动”的倡导者们还对通俗小说的写作做了具体的要求。他们提出通俗文学的创作应该是:“在生动的故事中,更应注意下列数点:(1)题材忠于现实;(2)人物个性描写深刻;(3)不背离时代意识。”(注:予且《通俗文学写作》,1942年《万象》第2年第5期上。)从这样的表述中可以看出,市民小说实际上是以新小说的模式提 出创作标准的。
四十年代初的这场批判之中,市民小说作家的声音似乎比新文学作家的声音高,这与当时的文学格局有关。在战争的背景下,随着新文学作家的纷纷撤离,上海、京津地区等中国文化的中心又是市民小说一统天下。包天笑、张恨水、周瘦鹃等市民小说老作家 佳作不断;张爱玲、苏青、梅娘、予且等市民小说新作家异常活跃;胡山源、丁谛、徐 轩等新文学作家也加入了市民小说作家的队伍。市民小说一时声势浩大。理论上的张扬 来自于创作实践的厚实。
四
新文学对市民小说从坚决地排斥、严厉地批判到基本认可;市民小说从惶惶不知所措 、不满与反驳到理论的张扬,新文学对市民小说的三次批判各有特色、各有得失。在相 当长的时间内主流和次流、批判者和被批判者,新文学与市民小说就以这样的关系存在 于中国现代文坛上。你写你的,我写我的,各不相干,这个局面首先是由市民小说打破 的。张恨水在其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张恨水曾对《春明外史》的结构作了这样的表述:
《春明外史》,本走的是《儒林外史》、《官场现形记》这条路子。但我觉得这一类社会小说犯了个共同的毛病,说完一事,又递入一事,缺乏骨干的组织。因之写《春明外史》的起初,我就先安排下一个主角,并安排下几个陪客。这样,说些社会现象,又 归到主角的故事。同时,也把主角的故事,发展到社会的现象上去。这样的写法,自然 是比较吃力,不过,这对读者,还有一个主角故事去摸索,趣味是浓厚些。(注:张恨 水《我的创作和生活》,载《文史资料选辑》第70辑,中华书局1980年版。)
对中国市民小说作家来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认识。“说完一事,又递入一事,缺乏骨干组织”,这是那些市民小说长期以来一直进行着的以写事为中心的创作模式。这样的创作模式曾被茅盾先生批评为“记账式的叙述法”。(注:沈雁冰《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载《小说月报》1922年第13卷第7号。)张恨水认识到写小说应该有一个“主角”,并且围绕着“主角”写“陪客”和“社会现象”,说明他已经认识到小说创作应该以写人为中心,认识到小说中的其他人物和事件应该围绕着主要人物展开。从这样的认识出发,张恨水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就十分生动,杨杏园(《春明外史》中的人物)、金铨、金燕西、冷清秋(《金粉世家》中的人物)、樊家树(《啼笑因缘》中的人物),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小说的结构也相当的完整,故事的叙述、细节的描写都围绕着主要人物的感情起伏而展开,小说的线索无论怎么复杂,主角既然决定了,它都是一个整体。到三十年代初张恨水写《啼笑因缘》明确地表示“必须赶上时代”,(注:张恨水《我的创作和生活》,载《文史资料选辑》第70辑,中华书局1980年版。)把社会的黑暗和统治者的压迫引进到小说中来。张恨水对小说创作有这样的认识,并在小说中做出了卓有成效的实践,当然不是他有什么独特的高见,显然是受到新文学“写人模式”和“启蒙意识”的影响。张恨水的小说实践给市民小说开创了一个新的天地。从三十年代开始到四十年代,写人的命运、写人的思想情绪已成为了那些优秀的武侠小说、侦探小说和社会小说的创作中心。市民小说向新文学靠拢提高了市民小说的艺术品位,促使了市民小说走向了繁荣。
新文学是否融进市民小说的要素呢?也还是有的。新文学明显的变化从四十年代开始。 如果我们把巴金的《寒夜》与《家》进行对比,把茅盾的《腐蚀》与《蚀》进行对比, 把老舍的《四世同堂》与他二十年代的小说进行对比,就会感觉到这些新文学作家四十 年代的小说中的故事性明显地加强了。既然是说故事,而且是说中国的故事,以血缘关 系和伦理道德来展开矛盾和纠葛就少不了;既然是说故事,就要讲到故事发生的社会、 自然环境,浓厚的生活性和世俗性也就少不了。说故事、血缘性、道德性和世俗性是中 国传统小说的特色,是市民小说赖以生存的文化基础和社会基础。四十年代新小说中的 这些市民小说的要素使得新小说更好看了,“中国化”的色彩也明显地加浓。
新文学一直批判着市民小说,但是批判和被批判的双方却在创作实践中产生了互动,起作用的是文化背景的变化和市场的需求。
中国传统文化毕竟是和中华民族的民族性结合在一起的。抗日战争是民族战争,民族情绪的高昂使得“五四”以来的“世界文化”的观念受到了削弱,使得中国传统文化的地位得到了提高。对新文学作家来说,他们不再把中国传统文化视作为阻碍社会进步的文化观念,而是从民族意识的角度开始接受中国传统文化。(注:“五四”时期,新文学作家是把传统文化作为新文化的对立面来批判的。陈独秀在此时说过:“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孔法,贞节,旧伦理;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见《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独秀文存》第242页,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重印本。这样的批判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这种接受使得中国传统文化与“五四”以来的新文化互相交融,交融的结果就是将中国传统文化和“五四”新文化 中那些不合时代或不合中国国情的内容排除出去,形成了一种既讲求人性的价值又讲求 传统伦理道德的新型的文化形态。这种文化形态是符合中国国情的,也说明了自“五四 ”以来中国文化经过震荡和整合之后,正逐步地走向成熟。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国新 文学与市民小说出现的一些新的变化正是这种文化观的体现。以传统的伦理道德规范规 范人性的发展,以人性的发展修正传统的伦理道德,这样的文化观在以后的中国得到了 进一步强化,并被称之为中国特色的文化观,成为了主流意识。在这样的文化观念的观 照下,传统的伦理道德中如果摧残人性,这些伦理道德就被视为落后,视为凶残;而那 些不顾中国起码的伦理道德一味地为所欲为的行为举止,同样被视为异类,视为不合中 国国情。既要人性健全的发展,又要合理地做人,这就是中国小说价值判断的是非观。 经过数十年的文学创作,新小说与市民小说美学上的各自的优势和劣势已相当明确了, 作家们对新旧文学的创作特征及其优缺点有着相当的了解。加深小说的思想性和加强小 说结构的完整性,是新小说写人模式的优势,故事情节生动和世俗性浓厚,这是市民小 说写事模式的优势。为什么不能既保持故事生动,又坚持以写人为中心呢?有了这样的 要求新小说与市民小说自然要融合在一起。如果我们将眼光放远一点看,出现在四十年 代的新旧小说的互动意义深远。金庸、琼瑶、莫言、王安忆以及八十年代以后那些标着 “新”的名称的小说,在美学上实际上都走的新旧交融的道路。既有思想的深刻性,又 有情节的生动性,交融中的中国小说在探寻着一条中国小说的创作之路。
标签:文学论文; 小说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文学分析论文; 火烧红莲寺论文; 张恨水论文; 啼笑因缘论文; 珊瑚论文; 读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