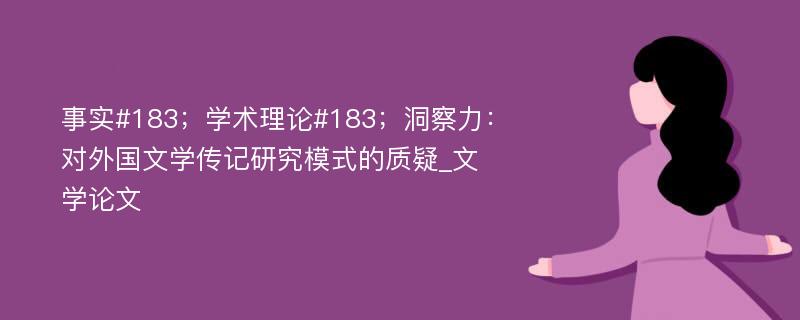
事实#183;学理#183;洞察力——对外国文学传记式研究模式的质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学理论文,洞察力论文,外国文学论文,传记论文,事实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外国文学持续进入中国学界的视野。尤其是新时期以来,外国作家及其作品的翻译、介绍和研究更是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文学作为某一文化区域历史阶段中生活样式的独特表述,其迁移和旅行无疑会丰富其他文化区域的人们对这个世界的了解和认识。在学术领域,亦会起到文本形态和理论资源双重的借鉴作用。
然而外国文学研究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样,是一种严格意义上的学术研究,其学理性涉及到研究对象、范围、命题、文献、材料、分析、论证、方法论和结论等全过程。但是长期以来,虽然人们对外国作家作品尤其是外国名家、名作进行了大量的译介和各类研究,但单就研究模式而言,有相当一部分则是停留在传记式研究模式之上,即依据作家所在国或国外的参考书、作品、自传或传记、国外学者的评论材料或研究成果,按照作家的生平、时代、文学思潮、同时代文学创作或流派、主要作品的结构、主旨、意蕴和艺术手法等方式,将材料进行分类整理,意译转述为中文,在此基础上进行阐释,由此成为国内了解该作家的研究成果。(注:由于一篇文论容量有限,在此不能提供具体的统计数据。读者可以参考1980年以来国内有关外国文学专论性的出版物以及主要外国文学期刊对于作家的研究文章。另可参见“中国学术期刊网·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这种模式对于不了解该作家、不熟悉该作家所在国语言和文学背景的一般读者而言,无疑是十分必要的。这种研究加上有关作品的翻译,可以使中国读者具体地了解该文化区域民族精神的探索样式和作家的艺术生命历程。
然而学术研究是要得到不断推进的。对于外国文学或一位外国作家的研究领域而言,中国学者的研究与其他国家学者的研究应当是同一层面上的学理性研究,但其意义在于,中国学者处于不同的文化区域和历史时段,可以透视出差异的缘由并能够提供一种中国的视角,从而推进学术领域,尤其是激发理论想象的方式。这种研究方式是否可以对于这一作家的所在国或文化圈起到文化互动作用、以及对于中国汲取异域文化有何种借鉴等问题,无疑是我们在研究外国文学,包括对作家和作品研究时应当面对的。而以适当的眼光将何种意义带出与研究模式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如果不对学界长期采纳的某种主要的模式适时加以审视,对其中的学理性不进行追问,显然不利于该领域的深入。
文学研究一般指以某一文学现象,包括作家、作品、思潮、流派、手法等作为研究对象,对其形态、本质、特征、规律和功能进行探讨,并按照一定的理论观点和审美尺度进行不同角度的分析和评价。它可以是内部研究也可以是外部研究,可以是纵向研究也可以是横向研究,或是二者的有机结合。而且,这种研究总是随着时代的变化在观念、角度、方法等层面,激发了新的思考而拥有了新的思路,由此使研究得到深化。由于文学是某一文化区域的人利用自身的语言和文化传统对其内心世界和外在世界的独特表述和艺术编码,因此它受制于该文化区域历史时段的生活样式,即处于个性系统(personality system)、社会系统(social system)和文化系统(cultural system)三者的关系中(劳思光136)。(注:该系统是帕森斯(Talcott Parsons)用以论述行为系统,并非专指文学研究。但笔者认为文学书写实际上也处于该系统之中。参见劳思光:《文化哲学讲演录》(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2年)136。)而且这三种互为关联的要素在文化交往和技术革命中不断呈现出新的影响模式。因此,每一文化区域中的历史时段都有其相对应的文本形态和文本内涵,其中也必然包含了文本环境、文本生产体制、文本传播以及文本接受等相关环节。外国文学是异域文化语境中的文学书写者的精神表述和艺术编码,牵涉到我们所不熟悉的语言指涉、文化传统和背景以及社会图景,即一种由多种力量综合作用而成的文化产品。因此,这种源自不同文化区域的文学文本总是内涵着复杂的历史因素和与之相关的观念表征(conceptual representation)符码。虽然这些因素有时涉及到人类的本质或表现了人类的一些共同问题,而大多都不能进行表层的直接迁移,而尤其应对其中存在文化误读的观念系统加以认真考察。因而福柯认为,“当我们要谈论‘作品’时,在此处和彼处的意义并不相同。作品不能被看作是一个直接的、确定的或一个同质的单位”(Foucault 24)。这一点也正如2001年出版的《诺顿文学理论与批评选集》的主编利奇教授针对当代文学文本的变化所指出的那样:
但是理论本身所内含的东西还不止这些。它超越了早期新批评对“文学性”的探索,而形成了一种问题和分析模式(mode of questioning and analysis)。由于后结构主义、文化研究以及新的社会思潮,特别是妇女及民权运动的影响,文学理论日益对体系(system)、体制(institutions)和规范(norms)等进行质疑,对其采取某种批判或反抗的立场,对理论盲点(blind spots)矛盾和由一些根深蒂固的观念掩盖的曲解感兴趣。日益将个人或地方性实践与更为广阔的经济、政治、历史以及文化的伦理力量结合起来。这种带有“文化批评”的理论不再关心可能性的论述条件,而对文化文本和体制中所内涵的价值、实践、范畴和表征的调查和批判更加感兴趣(Leitch xxxiii)。
20世纪后半期以来,由于社会生活和思想世界的巨大变革,西方文学研究的思想资源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思潮为理论支撑点。在此影响之下,人们首先对先前业已建立的观念形态和经典文本所内含的指意系统重新审视,将某一文化区域的文学观念纳入历史发展的进程和社会文化表征系统中加以透视和考察,而不是静态地将那些文学中的若干命题作为自足的系统简单地看待,或将大量的新的文本作为证实这些观念或命题的注脚。从文本生产的总体过程来看,每一历史时段中拥有资本和支配权力的社会阶层掌握了文艺生产、市场和传播的方式,并通过体制和媒体影响受众,形成自身意识形态所需要的观念系统,并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决定表征的形式和内容。因而社会表征诸种形态中所隐含的权力话语、种族意识、社会性别观念等,均是权力通过社会文化表征系统的再现。而内化在艺术和文学作品中所谓的“普遍常识”和“客观真理”则通过人们已经认可的符号和观念逐渐得到深化。因此,由资本和政治权力集团控制的表征系统的目的,实际上是输出观念,影响文化消费,即通过物化的过程达到观念的强化,并由此带动物化的消费和文化产品的再生产。一位作家,他或她本人在具体书写时或许并不清楚,自己要表达怎样的含义(赫施29),然而他或她却不是历史真空中的存在,其先在的观念无意识往往发挥着隐性作用,在不自觉中迎合文化市场的需求,使其写作成为历史时段中的文化表征系统中的附属品。
人们在外国文学研究中一般要依据文本事实,建立命题、筛选事实以及对文本内部的诸种构成性因素进行具体分析,但是这种分析却脱离不了与命题和自己所选择的事实相互关联的因素。就是一般的读者,也自然会将自己的价值观与文本中所隐含的价值观联系起来,形成一种期待视野。因此,文学文本并非是一个与历史、社会、文化无涉的独立净土。对文本的理解,无论是作者内心世界的所谓私人写作,还是对社会现象或历史进程进行的总体的艺术再现,从广义上说,均是一种社会性和文化性的理解,亦是一种历史性的理解。如前所述,这种文化产品的生产受制于历史时段中的观念系统和社会文化语法系统的制约。因为,凡是进入公共消费空间的文化产品均被一系列相关条件所支配,即由资本和权力机构所控制的生产、传播与市场的形式,文化产品再生产的方式,由主流意识形态所规定的述说边界,由支配性表征系统所逐渐形成并不断强化的审美观念和接受心理;由文化符码的外部迁移到边缘区域,性别和群体的文化内外殖民化等等因素所制约,并由此成为了文学社会化的整体过程中难以忽略的关联点。而一种文学文本在不同的文化区域中旅行时,并不是在一种审美共同体或普遍价值体系下的等值迁移,而必然受制于传播者或接受者的文化意识和立场、语言能力、传播和接受区域的文化政策和文化传统等合力因素。作为文化中重要分支的文学体制本身、文学文本(包括经典)本身、文学研究模式本身以及从事该门学科进行教学和研究的人群等,均难以在这一整体过程中独立而中性地存在。那种预设或认定一种超越差异的审美共同体的存在方式,即是一种乌托邦。那种声称自己的书写或研究是脱离了意识形态的个人行为,这本身亦是一种意识形态的显现(Kavanagh 306)。
赛义德认为:“迄今还没有人发明一种方法,能使学者脱离生活环境,脱离他(有意或无意)参与的某一阶级、某一信仰、某一社会立场的事实,或脱离作为某一社会的一个成员所从事的纯粹活动”(10)。而当一个文本迁移到或在其他文化区域“旅行”时,文本在语言的转换过程中,我们虽然不排除由于翻译的原因,原文中的有一些因素会丧失,但语言背后主要的文化符码会成为文本附加物,其中所内含的观念系统也大多会随之进入到异文化区域中。这中间,翻译者和研究者的文化立场显然是非常重要的。因而,在进行文学文本的研究时,应当对源自异文化区域的文本所内含的观念有所意识,透视出文本符码背后的观念系统,将这一观念系统对应于具体的历史境遇并看到问题所在。赛义德对文学文本中的问题性有着深刻的见解:
我坚信,批评家们在评论卡莱尔或拉斯金,甚至在评论狄更斯和萨克雷时,常常对他们有关殖民扩张、劣等种族或“黑鬼”的看法置若罔闻,认为这些看法与文化毫不相干,因为文化具有清高的性质,而清高的文化才是这些作家们的天地。……我并不是要说,是小说,或更宽泛意义上的文化,“引起”了帝国主义,但是,这种小说作为资产阶级社会的文化产物,不可能与帝国主义没有联系。(赛义德230)
虽然我们很难认定外来文化产品和外国文学文本都与帝国或殖民意识必然有关,但将这种异文化区域的文化产品仅仅进行平面的、非研究性的翻译或转述行为不仅缺乏学理性,而且缺乏文化责任。如前所述,中国近现代以来所引入的大量的外国文学作品中不乏优秀的经典之作,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国人的精神世界、思想文化以及中国文学的书写和接受。然而,在新时期引进高潮中,在对这一领域进行的学术研究中,学理的重要性是不可回避的。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应当在原有的基础上得到不断地推进。笔者认为,外国文学作家和作品以及相关理论并非是“清高”于生活世界之外的事物,因而对外国文学和文学理论的研究也就并不存在一个中性立场,而在客观上有一个文化立场的问题,有一个如何接受、如何研究的问题。其中一项工作就必然要探索有效的研究模式。因此,如何通过研究模式使人们深入地解读这些舶来的作品、如何了解外国作家对生活的写照、如何透视异文化文本所隐含的观念系统,如何使这种文本真正有助于学术界尤其是中国学界的文学研究,就成为我们必须正视的问题,而这一学术研究的意义也就内含其中。而反观外国文学领域中大量的产品,几乎没有形成这样一种意识,更不要说以中国角度对某一核心问题或视点进行强有力的论证了。在许多传记式的研究中,或对文本艺术特征分析、形象分析、思想影响等进行的平面剖析时,在很大程度上是在认定有一种普遍价值观和审美意识形态的条件下,在那些被预设的、被经典化的作品、观念、概念、界说的基础上进行的,即在对那些至关重要的观念系统未加清理的前提下进行的,也有一种简单化的研究,其一是跟风译介,将一些“新”东西介绍给国内,然而又缺乏系统和相关的跟进研究;其二将某些作家置于“主义”之下进行的主观或想像性的评议。更有甚者,直接将国外的研究材料中有洞见的原创思想稍加改编,转述为中文,而不指明出处。这种低重复的研究不仅不能在该领域的基础上有所超越,而且有违学术良知的基本操守。
所以,外国文学传记式研究模式提供了一种“事实性知识”,然而“事实”本身却不能决定理论意义。对于一个异文化区域中的作家,我们不仅需要了解有哪些事实,其中又有哪些事实需要我们研究,而且需要了解这些事实之间的相关性是什么。这就需要中国学者在进入该领域后,在全面解读和分析已有成果的基础上获得自身的洞察力。传记式研究的方法论基本是属于翻译——阐释法,即依据国外现存的文本材料,也包括国外的未整理的档案材料进行中文意译和阐释。如果这种研究对于某一作家的研究领域有意义的话,笔者认为,中国学者所挖掘出的新材料可以算是一种。但是,一般而言,中国学者限于条件的限制,要挖掘出新的材料是比较困难的。这一模式大多呈现为一种平面形态:
传记式研究模式
现存材料—时代与作家生平—主要作品/同时代文学思潮或流派—文本艺术手法—意义
主要方式:翻译—解释—归纳
研究一个外国作家的学者,在理论上一般都应具备解读该国文字的坚实基础。许多欧美大作家,已经在国际学界形成了一个个具体的分支之“学”。所以,有关这些大作家和作品的工具书、评论集、作品分析和指南是非常丰硕的。因此对于国内学界而言,重新研究和了解这些作家的学者并不需要去读用中文重新转述的材料,而仅仅依靠转述的材料所建立的研究成果本身也是有问题的。有研究能力的学人会直接查阅、研读第一手原文材料,即作家本身的著述,以及第二手原文材料,即学界对该作家的研究成果,其结果往往比中文转述的材料要准确、全面、精要得多。人们在这种研究中所需要的是,一个新的研究成果的出现,它采纳或挖掘出了何种新的材料、采纳了何种新的方法、提供了何种新的视角,即这一成果以何种方式重新进入到该领域之中,为人们带出了何种新的意义,即人们需要了解的该分支学科领域所获得的启示,而非是停留在、甚至低于原有研究成果上的中文转述或平面译介。其实,一位文学家,特别是文学大家,其思想境界、对生活的认识和智慧以及对语言的驾驭能力往往都在常人之上,其书写总是一种文化的复合体。任何一种单一的方式,或非严格意义上的研究不仅根本不能进入有效的研究过程,而且很可能由于水平的限制而引发负面误读。因此,在此种研究中对相关的问题没有清醒的意识,对基于文本的理论述说没有进行历史还原,对相关的材料并没有全面把握,对作家和作品的解释只是停留在转述之上,那么,长此以往,这种单一的传记式研究模式不仅难以对文本内含的观念形态进行系统分析,还将导致原创性的麻木和缺失,在一种平面译介中也就自然缺乏学理的深度和力度,建构起某一作家研究领域中国学界所应有的理论想象和学术话语,也就无从谈起。
所以,评判一种研究模式主要是看其是否具备内部理论的一致性和该理论所声称的有效力。换言之,这种模式对于该领域而言,可以揭示出何种问题、可以提供何种述说问题的方式。对这种复杂的、包容万象的文本进行研究,尤其是以跨文化的视野对不同文化区域的文本进行研究时,其研究的一般规律总是从单一走向综合。笔者认为,在外国文学研究中,还可采纳问题式研究模式:
问题式研究模式
作家作品中所涉及的核心问题
——问题本身的意义与研究对象的确立
该作家研究领域中迄今对该问题的探讨范围、方式及缺陷
——问题的忽略、缺失及原因
该问题在相关领域中的呈现
——文本外部因素:生产、传播、接受、翻译、跨文化阐释等
该问题在作品中的展开方式
——文本内部因素:艺术手法、叙述策略、互文性等
该问题研究对该领域的理论意义和借鉴意义
较之“传记式研究”,“问题式研究模式”在纵向和横向两个层面上均以核心问题展开,使人们以一种问题性看待材料、艺术手法、叙述策略、观念、传播、接受和翻译等相关过程和问题,其中亦不排除对新材料的挖掘或发现。这种研究模式在方法论上可以打破平面论述,使人们在集中关注某一作家在其作品中所反映出的基本问题中,为该研究领域提供一个中国的视点,可以为学界提供一个题域,使人们能够深入下去,因此更有学理意义和理论价值。笔者在此并无意否定传记式研究,而且肯定了传记式研究的某些功能作用。但笔者认为,对于丰富的文学现象本身,研究模式亦可以呈复数形式,此处仅提出一个思考和讨论的建议。而对于文学研究而言,西方学界也有着大量的严格规范性、旨在推进学术的指南。(注:文学研究学理规范性可参见两本重要的指南:Bonnie Klomp Stevens and Larry L.Stewart,A Guide to Literary Criticism and Research.3rd Ed.(Fort Worth,PA:Harcourt Brace College Publishers,1996);John A.Goldsmith,John Komlos,and Penny Schine Gold,The Chicago Guide to Your Academic Career:A Portable Mentor for Scholars from Graduate School Through Tenure(Chicago and London:The U of Chicago P,2001).)简言之,国内外国文学研究已经进行了多年,我们确实需要理论意识和洞察力,超越那种平面译介的层面,在迁移异文化文本时考虑汉语经验层面上的提升和回应,走向理论的建构。在外国文学研究领域倡导学理性意识,进行一种多元探讨显然是有意义的。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Foucault,Michel.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 & the Discourse on Language.Trans.A.M.Sheridan Smith.New York:Pantheon Books,1972.
赫施:《解释的有效性》,王才勇译。北京:三联书店,1991年。
[Hirsch,E.D.Validity in Interpretation.Trans.Wang Caiyong.Beijing:The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Ltd.,1991.]
Kavanagh,James H.“Ideology.”Critical Terms for Literary Study.Ed.Frank Lentricchia and Thomas McLaughlin.Chicago and London:The U of Chicago P,1990.
劳思光:《文化哲学讲演录》。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2年。
[Lao,Siguang.Lectures on Cultural Philosophy.Hong Kong:The Chinese U of Hong Kong P,2002.]
Leitch,Vincent B.et al.eds.The Norton Anthology of Theory and Criticism.New York and London:W.W.Norton & Company,2001.
爱德华·赛义德:《赛义德自选集》,谢少波 韩刚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
[Said,Edward.Selected Essays.Trans.Xie Shaobo and Han Gang,et al.Beijing: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1999.]
标签:文学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文本分类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艺术论文; 中国模式论文; 文本分析论文; 外国文化论文; 文化论文; 读书论文; 作家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