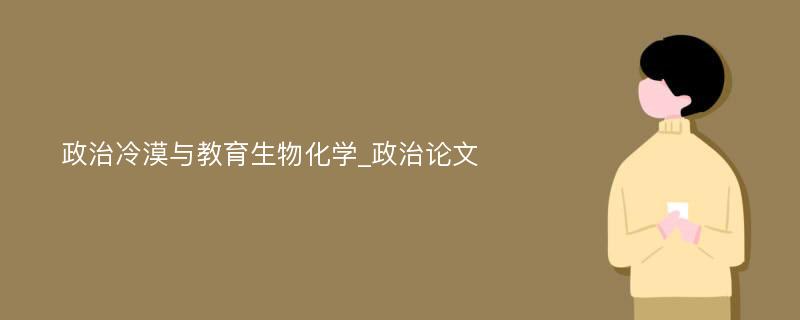
政治冷漠与教育的谋生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冷漠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代社会同时发生着两类值得关注的现象,一类是政治冷漠,一类是教育的谋生化。这两个现象之所以值得关注,在于政治和教育是人类事务中两个主要的、核心的领域,且这两个领域与所有人都相关,即所谓“每一个人的政治”、“每一个人的教育”。那么,这两类现象是孤立发生的,还是相互作用的?这是一个需要思考的时代性大问题。
政治冷漠与追求自由的悖论
政治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这种重要性首先在于政治关联着人的本性。人是政治的动物,因为人是唯一会说话的动物,说话能力可以用来表达什么有益,什么有害,什么是正义,什么是非正义。政治生活使人趋于完善,一旦脱离政治生活(法律和公正),人就可能堕落成最“恶劣的动物”。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亚里士多德才认为,生活在政治组织中是人性实现的必要条件,而本性上脱离城邦(政治组织)的人,要么是神,要么是“鄙夫”。[1]当然,人性多维,政治不是人性实现的全部条件,人性也可以在其他活动中得到实现。但在政治领域里实现的人性,是人性的卓越或卓越的人性,因为本来意义上的政治是公共、公开的领域:一方面,在这一领域里活动就是一种“冒险”,需要巨大的勇气,这是对人性弱点的克服与超越;另一方面,在这一领域展示的是正义等值得追求和敬重的人类价值。
政治的重要性还在于政治是人类对自身命运的一种主要把握方式。人是有限的存在,对这种有限性的认识构成了命运意识。人的存在就在于人有命运意识,但不屈服于命运的安排。比如,单个的人是不自足的,这是人的命运,但人通过共同体实现了自足进而能够把握自己的命运;人可以是“最为优良的动物”,也可以是“最为恶劣的动物”,正是政治使人趋于前者而避免走向后者。
政治对人来说如此重要,但如今的人对政治却是那样的冷漠。鲍曼对此有深切的观察:“对大写‘政治’的兴趣(即对直接的政治运动、政党、政府的构成和方案表现出的兴趣)、强烈的政治信念以及对所谓的传统政治活动的积极参与,所有这些都在越来越快地消失。”[2]这种对政治的冷漠,不是一时一地的现象,而是卷入现代化进程中的全球多数国家的现象,是一种“现代性的后果”(吉登斯语)。
当代人的政治冷漠有多种层次和维度的表现。首先是对政治的信念和信心的丧失。如今的时代被称作“反政治”(anti-political)、“无政治”(un-political)、厌恶政治的时代,弥漫着对政治的怀疑和排斥。对糟糕政治的怀疑与排斥自有其合理性,问题是这种排斥“并非是针对某个特定的政党或政治家的拒斥,而是一种深切得多的对‘政治本身就是无用’的确信”[3]。在学术与知识领域,“政治终结论”甚嚣尘上。政治已经终结的说法,有多种“版本”,包括历史的终结、民族国家的终结、权威的终结、公共领域的终结等,反映的是对政治作为一种改变人类命运实践的信心的丧失。大众的“反政治”情绪与学术领域的“政治终结论”交相辉映,共同折射出我们这个时代人们对政治的失望心态。
与人们对政治丧失信心相辅相成的是政治本身的迷失、退却与变形。富里迪分析了政治迷失的多种形式,包括语言迷失和方向迷失。语言迷失是指政治人物已经很难找到合适的政治用语来表达自身,他们不再言说自己的信仰、原则与追求,而是代之以“议程”、“计划”等社会性、经济性的语言。政治语言的贫乏与衰落,折射的是人们在谈论政治时已经无法找到合适的言辞。方向迷失表现为政治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失去了建构重大议题的能力,攸关人类或民族生死的重大议题从“政治的雷达里消失了”,政治“不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能够做什么,总是纠缠于与必然性密切相关的所谓“民生”问题。[4]
与政治迷失相关联的是退却。鲍曼认为在过去时代,政治是人类行为的主要“立法者”,其机制是设定“选择议程”(agenda of choice)(实际选择的范围)和“选择法则”(code of choosing),但“现今的政治制度正置身于这样的一种过程之中:或明或暗地放弃在议程与法则之设立中的作用。……设定议程与法则的功能,愈来愈从政治制度那里让给了各种势力”[5]。代替政治设定议程和法则的所谓的“各种势力”是什么呢?不外乎经济与市场以及科技这些“新兴力量”。作为政治实体的国家已经越来越承认市场与经济法则对政治与法律的优先性和优越性。退却之后的政治躲在经济和市场之后,沦落为为市场和经济服务的工具,政治的变形不可避免地发生了。诸如民生、安全、医疗、养老等与经济、利益相关的话题已经主导了政治领域,政治徒有其表,内里已经被填入了经济性的内容。
人们越是对政治无信心、不抱期望,政治存在的合法性就越低,政治衰落的程度就越大;而政治越衰落,政治就越不可信,人们对政治的信心就会越不足,这是一个恶性循环。
对政治的犬儒主义和怀疑论,为当代人逃离政治生活找到了理由。既然政治这么无用、无聊,那么作为个体,不参与政治、远离政治就是明智的选择,因为与其将有限的精力浪费在一些毫无意义的事情上,不如去做些对自身有益的事情,这大概就是当代人逃避政治生活的典型心态。在当代社会,这种心态已经演化为这样一种“意识形态”:政治越少,自由越多。也就是说,对很多人来说,逃避政治已经不再只是一种心理取向,而是一种权利要求,一种“政治自由”(political liberty),即“脱离政治的自由”(freedom from politics)。“政治存在的理由是自由”,而自由的本意则是摆脱生物必然性的束缚走向公共生活(政治),即参与政治的自由,而如今的自由则变成了脱离政治的自由,这难道不是对人类追求自由的反讽吗?
更糟糕的是,人们对政治的逃避得到了现代国家这一政治实体的认可与鼓励。国民不再对政治生活感兴趣,不再期待国家的拯救,而国家则认为只要不干涉自由,就不再有其他公共之善,对国民也就无所亏欠。也就是说,公民对政治不感兴趣,作为政治实体的现代国家,不仅鼓励这种冷漠,实际上其自身也对本来意义上的政治(公共之善)不感兴趣,“公民对政治的无兴趣与冷漠,国家撤回了推动公共之善的义务,都是市民社会的令人不快而又正当的产物”[6]。
当代人不仅不参与政治,甚至已经不再认可自己的政治身份,不再视自己为政治主体。如前所述,当代政治徒有政治之表,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被市场和经济力量裹胁而去,运作形态则是与商业机构并无二致的科层制。科层制或官僚制实际上就是制度化的机器形态,对个体的人有天然的胁迫,使之客体化。“一旦参与行为衰减了,一旦作为媒介的横向联合体萎缩了,个体公民就会独自面对巨大的官僚国家,就会感到无能为力。”[7]一方面是参与政治的意愿缺乏,这使得政治变成了少数人的事情,变成了官僚体系的内部事务;另一方面,作为个体,即使偶尔有意愿参与政治,也会发现自己是政治所统治、所排斥的对象,已经无从下手,只能体会到一种被支配的客体感和无从着力的无力感。
作为政治动物的人不再对政治感兴趣,那么他对什么感兴趣呢?当代人最感兴趣的莫过于物质财富与物质利益了。阿伦特说,“自现代肇始以来,由于生命安危成为人们的首要关切,结果,所有行动都根本上屈服于必然性之轭下”[8]。在这个时代,很多人认为,谋生最重要,财富最可靠,其他的一切都无关紧要。几乎每个人都从公共政治领域逃逸,不愿意在那里浪费生命,都埋头于私人生活与私人关系。在消费社会里,科学家居于“不胜寒的高处”,俨然成了上帝的化身,但在阿伦特看来,这些人也是在“干一份活儿”的群体,在政治上并不可靠。[9]如今艺术品也成了商品,艺术家(如果还配得上这一称号的话)也是通过自己的作品谋生的人,也是在“干一份活儿”。更具讽刺的是,专门从事政治活动的人,用褒义词说是政治家,用贬义词说是政客,他们也是在“干一份活儿”,也是谋生者。本来是“每一个人的政治”,现在越来越专门化,专门从政的政客越来越职业化,政治也变成了一个谋生的职业领域。
教育的谋生化
如上所述,在一个物质极大丰富的时代,如今的人,其所有活动似乎只有一个焦点,那就是如何生存,如何活下去,如何活得更好。我们身处消费社会,每个人都被认为、自认为是劳动力,都在挣钱糊口,都在为满足或真实或想象的必然性需求而挣扎。人们从事不同的职业,表面上有天壤之别,实际并无二致,都是在“干一份活儿”。
在整个社会走向谋生化的时代里,本来应该具有理想性和行动性的教育也谋生化了。教育的谋生化既是社会谋生化的结果,因为教育是整个社会系统中的一个环节,被整合进了谋生化的链条之中,又是社会普遍谋生化的原因,因为人人都要受教育,谋生化的教育强化了每一个受教育者谋生的欲望与习性。教育的谋生化“转型”虽然不是一夜之间实现的,而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但其谋生化的特征已经显露无遗。
教育谋生化首先表现在如今的教育已经成了国家谋生的手段。现代教育脱胎于资本主义经济需要,一开始就是为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服务的,“在当时,一群企业巨头认识到,公共教育培养和驯化的作用会给他们带来巨大的财富”[10]。在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教育的贡献无可置疑,尝到甜头的现代国家,对教育的经济回报期待越来越高。在一个全球化时代,各国之间的经济竞争如此激烈,政府花在教育上的每一分钱都应该有助于在竞争中获胜。现代国家在办教育的时候,往往将这一功利目的隐藏起来,隐藏在一些冠冕堂皇的目的之后,但只要稍加留意,我们就可以发现这一被掩盖起来的真正目的。正如诺丁斯所言,美国教育目的的公开表述总在变换,但其潜在的目的一直是:保持美国在经济上的强大和给每个孩子以经济上成功的机会。[11]
教育不仅是国家谋生的手段,更是个人谋生的手段。我们身处一个矛盾的时代,一方面是科技发达、物质丰富,另一方面又到处充满了不确定性,似乎每个人都有生存之虞。我们生活在一个最好的时代,因为我们这个时代物质前所未有的丰盛;我们又生活在一个最坏的时代,因为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风险时代,每个人都没有安全感,内心都充满了失败的恐惧。“年轻人微不足道的个人志趣——‘成功’,也就是说,给自己找个落脚的地方——贯穿了他的一生。”[12]接受教育,只不过是“给自己找个更好的落脚的地方”的一种方式,因为在这个时代,出身虽然依然重要,“爹”还有得可“拼”,但谁都阻挡不了的趋势是,“个体在社会劳动分工中占据何种位置并不取决于其出生时就确定的特征,而取决于其后天获得的特征,尤其是受教育水平”[13]。在我们这个时代,对个体来说,上学、接受教育不是为了其他什么目的,而是为了谋生,“任何超越个体的教育目的,哪怕是有法律效力的教育目的,也要拿到个体理性的法庭上接受审判。不过,这些个体理性是有限的,并为自我利益所主导”[14]。
作为谋生手段的教育,其现实形态就是“为了就业的教育”(education for employment)、“为了工作的学校”(school to work)(阿普尔语)。所谓就业,就是获得“一份活儿”,这是在我们这个物质时代活下去的最可靠的依凭。也就是说,如今的教育虽然还有“浓妆艳抹”的一面,但如果褪尽铅华,我们看到的只能是在为“干一份活儿”的技能做准备的粗糙面孔。
“为了就业的教育”或“为了工作的学校”与作为行动的教育性质完全不同,形成了自身的显著特征。首先,教育是面向就业市场的,市场需要什么样的从业者,教育就培养什么样的人,迎合市场需要成了现代教育的“金科玉律”。面向市场和社会需要本身并不是问题,问题是教育应该有自身的坚守和尊严,失去自我,教育与那些迎合市场需要的物质产品的生产者又有什么区别呢?与就业市场离得较近的高等教育,如今已经越来越显露出职业培训化的特征,以“找到好工作”作为吸引学生、获得良好谋生回报的优势与长处。更可怕的是,为了就业的思想已经延伸到基础教育阶段,甚至到了幼儿教育阶段,整个教育过程都被就业压力所绑架。
什么样的知识和内容有利于谋生和就业呢?显然是实用性知识和技能。学校教育的重点和焦点就是这些知识和技能,至于人文艺术学科,无论人文学者如何强调他们在人的想象力、创造力和批判性思维发展中的作用,在教育中均处于可有可无的尴尬境地。因为这些知识在为了谋生的教育中已经失去了存在的基础,它们既无法为国家带来经济上的进步,也不能为个人找到好工作增加筹码。从事人文学科的学者在这种为了就业的教育系统中生存,有时候甚至会油然而生一种愧疚感,因为他们找不到自己的专业知识的有用性。
为了就业的教育不但突出实用知识和技能,还在受教育者身上塑造受欢迎的“社会性格”。我们这个时代大多数人所共同拥有的、为现代教育所推崇并塑造的性格是什么呢?物质、自我、冷漠。这种性格的核心是对物质的追捧,以消耗物品作为生活方式,所谓“我消费,我存在”。与物质化相联系,社会性格的另一个特征是自我,即以自己为中心,将自己作为衡量一切事物好坏的尺度,将生命力全部投入到自身的安逸和舒适上,除此之外,一切都无关紧要。这种社会性格的另一个特征是冷漠,即每个人都心安理得地旁观他人的命运起伏,甚至幸灾乐祸,因为他人的不幸既可以为自己提供消遣与娱乐,又是自己成功的良机。现代教育正在不遗余力地塑造现代社会所需要的这种性格。学校通过自身的“私利化”暗示、怂恿受教育者追逐物质财富,学校自身也变成了“消费场所”,许诺给学生及其家长以物质与利益回报;学校变成了“个人奋斗的场所”,在这里,病态竞争成了家常便饭,同伴之间的关系被染上了“你死我活”的色彩;学校生活的利益化、竞争化同时也在塑造着人的心灵冷漠,潜移默化中造就了一批冷漠旁观他人苦痛的人。
教育谋生化还表现在教育的运作模式上。根据佐藤学及很多研究者的观察,20世纪学校改革与构造,受产业主义思潮与运动的控制,其特征就是把工厂企业生产与管理的原理引进学校的组织与运作,借以提升学校教育的“效率”与“效益”。[15]学校的基本框架,包括学校的管理体制、管理制度、学年安排、班级编制、学科与课程设置、教师组织与管理、学生的组织与管理等都是按照工厂与产业的模式来建构的。这样的运作模式,以所谓的效率为追求,以制度与纪律为手段。在所谓的效率面前,学生成了追求效率的工具。问题在于,学校是教育机构,不能把人当作工具,只能把人当作人,一旦把人当作工具,就走向了教育的反面。现代学校的管理,最重要的是铁的纪律。在铁的纪律面前,任何个性都会被碰得头破血流,学生成了被铁的纪律所管制的一个个非生命化的存在。以这种模式运作的现代学校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变成了与现代工厂或企业“同质同构”的存在,二者配合默契,朝着一个共同的谋生目标努力。
教育谋生化的另一个表现是上学变成了一种“工作”,学生变成了一种“职业”,即“学生职业”。柏拉认为,“学生职业”的说法只是一种隐喻,不是一种真正的定义,因为从事这一职业没有报酬可拿。[16]学生当然不是一种真正的职业,但学生也并不是没有报酬可拿。只不过,真正的职业得到的报酬是金钱,而“学生职业”拿到的报酬则是分数。如前所论,谋生化的学校许诺给学生的是未来利益,这种利益的缺陷是不能即刻兑现。但学校发明了分数这一绝佳的替代品,“在学校里,分数纠缠着学生,如同工资纠缠着计件活的工人”[17]。也就是说,分数之于学校,犹如货币之于社会。首先,货币作为标准,将社会上异质的、多样的劳动与财富均质化,打通了人与人之间、物与物之间的通道,使每一个人及其劳动都可以相互换算。同样,分数将多样的、个性的、异质的教学活动均质化,成了衡量一切教和学的通用标准。其次,分数与货币一样,是一种交换手段。拥有货币可以直接购买自己希望拥有的物品,分数虽然不能直接用于购买,但在校内却可以换来尊重、羡慕、荣耀、尊严,能够起到货币在社会上所能起的同等效用,更何况分数还可以换取将来好的职业。再次,分数与货币一样,是一种“储蓄手段”。一次分数虽然不足为凭,但一次次的分数积累犹如银行存款的累加,却可以使自己的价值直线提升。正如成年人整天上班挣钱一样,学生则是整天上学挣分数。因此,学生即使不是一种真正的职业,起码也可以算做一种“准职业”。也就是说,在他们尚未走向社会去干一份谋生的活儿之前,早已经预演了很多年。
政治冷漠与教育的谋生化
政治冷漠与教育的谋生化显然不是两个相互孤立的现代现象,一方面,它们有共同的社会基础,或者说二者都是“现代性的后果”;另一方面,二者又相互关联、相互作用,即政治冷漠促使教育的谋生化,教育的谋生化也滋生着政治冷漠。
政治冷漠和教育的谋生化可以说是现代性诸多后果中的两种。“现代性是在复杂的技术条件下由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制度和文化上的一系列伴随物。”[18]也就是说,如果政治冷漠和教育的谋生化是所谓的“伴随物”的话,那么现代技术和经济增长则是背后的社会根源。阿伦特指出,望远镜的发明在现代科技史、甚至是人类史上都是一个“大事件”,因为在此之前,感官告诉我们太阳围着地球转,而望远镜等科技发明却证实这只不过是一种蒙蔽人的错觉或幻觉。在此之前,人类事务的诸多领域都是建立在感官功能及对感觉进行抽象与理性思考的基础之上的,比如政治就是建立在人的言谈和行动之上的。政治之所以可能,就在于人有基本的“同感”或“常识”(commonsense),“同感”为言谈和行动奠定了可理解的人际基础。基于“同感”的言与行的共享既是政治生活本身,又是人类建构共同世界的方式。“同感”就是架在人们中间的那张“桌子”,正是因为它的存在,人们才有了一个可靠的联系和一个共同的世界,“桌子”消失了,共同世界也就随之坍塌。科技发现使得感官不再可信,对政治及作为“准政治形态的教育”(教育其实也是一种以言与行的共享为特征的行动,在这行动的意义上,教育本身就是政治,但因为教育场域中的人主要是未成年人,严格说来教育只是“准政治”)起到了釜底抽薪的作用:既然感官不可信,那么以此为基础的政治和教育也就不那么可信。
感官不可信,人曾经引以为豪的理性也就不那么可靠,不确定性的深渊就在眼前。但人作为有限存在物,对确定性的寻求一刻也不会停歇,一定要抓住真相,否则就没有安全感和确定感,人有根深蒂固的“求真意志”。现代科技不同于以往的理性沉思,不同于那种透过现象去把握存在和真理的方式,而是以实验为基本样态,所谓实验就是利用工具和仪器“逼迫”自然“说出”自身的秘密。在求真意志的驱使下,科技成了唯一的依靠。这种对现代科技的绝对信任具有多重效应。首先,科技的范式泛化,被运用到人类事务的一切领域。政治也按科技的基本精神进行了改造,变成了以“手段—目的”为基本结构的关于人的管理实验。霍布斯的哲学就顺应了这种趋势,将自然科学中的实验与制作观念引入政治领域,从而开启了“政治科学化”的大门,政治由原来的在共同世界里的行动逐步变成了“管理科学”。教育同样被现代科技所“调教”,由古代主要面向人自身的人文教育转向面向自然与宇宙的科学教育。与古代教育基本上是为人生不同,在科技范式的主导下的现代教育基本上是“逼迫自然说出自身秘密”的科技过程的一个组成部分,至少是一个准备性部分。与政治一样,教育也采取科学化的方式,其日常运行与组织架构遵循的也是工具理性(手段—目的)逻辑。
其次,现代科技的突飞猛进还引发了人们世界观的改变。人是地球生命,地球是人类生存所依赖的基本境况。地球作为有生命的肌体,具备人所不具备的永恒性。人正是通过在不朽的地球上建造自己的人造家园、创立伟大的功业来超越自身的可朽性。因此,在人类历史的绝大多数时期,地球是先于人的,是先于有灵的生命存在。但现代科技改变了历史,也改变了人们看待地球和世界的方式。在现代科技的逻辑里,地球只是科技施加自身作用力的承受者,是改造的对象,是需要加工的工具。哲人惊呼“地球死了”、“自然死了”,而杀死地球和自然的“凶手”正是现代科技。有朽的人追求不朽正是政治存在的根基,如今连作为人存在之基本境况的地球和自然都是有朽的了,人所追求的不朽也就成了虚空。不朽性的消失,意味着拔掉了政治存在的根基。同样,教育也是有世界观基础的,不同的世界观有不同的教育。现代教育的世界观是对象化、物质化、工具化的,将地球和自然视为谋生的工具、资源和手段,整个现代“教育叙事”讲述的都是人类如何征服自然、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故事。
阿伦特说,现代社会有一个基本的假设,那就是“生命作为至善”、“生命作为最高善”[19]。过去时代先于、高于、大于人的神明、超越性价值,甚至自然和世界都不再重要,人被抛回他自身,“水落则石出”,生命的价值一下子彰显出来。在我们这个时代,无论我们做什么都是为了“谋生”,都是为了照顾作为至善的生命。在这种社会趋势的推动下,政府已经不再是政治自由的守护者,不再是公民共同行动的制度化机构,而是生命(生命需要、物质利益和安全)的照看者,“民生”问题成了政治的头等大事。教育也被裹进生命必然的洪流之中,成了满足生命必然性需要的手段,成了“谋生”的准备与训练。
贝克基于对现代社会的洞察,指出现代人已经“生活在文明的火山上”,即进入“风险社会”阶段,“不明的和无法预料的后果成为历史与社会的主宰力量”[20]。身处“风险社会”中的人,无论富贵还是贫穷,都要面对不明的、无法预知的危险,不确定性的幽灵到处游荡。这样的现实,使得社会的所有阶层,包括那些所谓精英和高端,终其一生都面临着解雇、破产,以及与此相伴随的丧失社会地位、社会承认和人格尊严的威胁。这是一种暴力,一种结构性的暴力,内在于现代社会本身。
风险社会对政治和教育的影响显而易见。在这样一个“朝不保夕”的时代,每个人自顾不暇,都有“惶惶不可终日”之感,哪里还有“闲情逸致”去操心政治和公共事务,政治冷漠是必然的结果。国家也因势利导,“让臣民相互竞争,并在梦想无法实现时责怪他们自己”[21]。现代国家之所以纷纷标榜自己是“有限政府”,实际上就是告诉自己的国民,不要对政府有过多、过分的期待,“一切都得自己扛”。而这样的做法,又强化了人们对政治的不信任感。学校教育无法将“风险社会”隔离于有形或无形的围墙之外,或者说学校教育本身就是“风险社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风险社会”里的个体无依无靠,只能到劳动市场去谋生,成则意味着财富、地位、尊重,败则意味着贫穷、苦难、没有尊严。进入劳动市场是有前提条件的,而这种条件由教育提供。现代社会的学校教育之所以如此重要,就在于其给个体提供了进入劳动市场谋生的资格。因此,我们甚至可以说在“风险社会”里,教育的谋生化是一种无法避免的宿命。
政治冷漠与教育的谋生化不仅有共同的社会基础,而且相互作用、互为因果,形成一种双向循环。从政治冷漠的维度看,政治冷漠为教育的谋生化提供了政治基础和便利,或者说政治冷漠是教育谋生化的直接推动力之一。从本性上说,教育是一种行动,是本来意义上的政治活动或准政治活动,在这个意义上,教育是政治的一种预备和预演。当今政治的本性发生了变化,但教育的政治预备与预演功能依然存在,只不过是为顺应政治的需要而变换了型态。如今的政治,其关注的焦点变成了以“民生”为核心的生存与消费问题,作为政治预备与预演的教育,其关注的重心相应也转到了谋生与消费上。在谋生化的道路上,教育随着政治起舞,双方密切配合,跳的是一曲合拍的“双人舞”。
教育随着政治一起跳谋生的“双人舞”,那是别无选择的选择。冷漠时代的政治是变形的政治,这种政治一方面以国家利益为核心,将所有其他活动都视为实现这一利益的工具。如前所述,教育不可避免地成了国家谋生的工具,国家对教育的投入不是为了其他,而是为了“集体生存”,即在国家间的竞争中获得胜利。另一方面政治又以满足个人或现实或想象的必然性需要为合法性基础,将其他人类活动,包括教育都纳入到奠定自身合法性的链条之中。在现代国家,教育其实都是一项“民生”工程,衡量教育的标准不再是其自身品性,而是人们是否满意,所谓好教育就是“人们满意的教育”。“多数人的所思所想就构成了公共舆论”[22],由于现时代多数人的所思所想都是谋生,都是必然性的满足与再满足,那么,人们满意的教育不可避免地就变成了谋生的教育。当然,对教育满意不是目的,最终是通过对教育的满意进而实现对政治的满意。现实政治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来为自己统治的合法性辩护的。
政治冷漠的另一个表现是政治让位于经济和市场,使经济和市场力量成为设定议程和法则的力量。相应地,经济和市场力量也成了主导、左右教育的力量,在这股终极力量的牵引下,教育也变成经济活动,学校成了市场的一个环节。鲍曼指出,作为市场的一个环节,教育也被赋予了选择法则的工具性功能,即教育通过自身活动,“告诉”进入教育场域的人什么是“值得要的、可取的、适宜的”[23]。在一个一切以市场为导向且又充满风险的时代,教育所“告诉”受教育者的选择法则,无外乎富有、获胜等于安全和幸福,谋生胜过一切!
反过来,教育的谋生化也加剧着政治的冷漠。谋生化的教育培养的是以谋生为目的的人,“现代教育总体上说为年轻人准备的是‘生活’而不是‘世界’,因而也就把他们交付给必然性的铁掌去控制了”[24]。现代教育所培养的被必然性铁掌所控制的人是谋生者,不是公民,公民是倾向于通过共同体的安康来寻求自身幸福的人,看重公共事业和普遍的善,而谋生者、消费者则埋头于自身利益,对公共事业、公共善、良好社会、社会正义没有兴趣,而这恰恰是政治冷漠的典型特征。当然,教育的日常言说少不了冠冕堂皇的语言,比如公平正义、人类价值等,但在这些华丽辞藻之下的真正法则则是个人生存高于一切。也就是说,谋生化的教育通过自身活动暗示或明示受教育者唯一重要的是个人的前途和幸福,政治则是无用与无意义,对政治抱有热情和信心是幼稚和愚蠢的表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