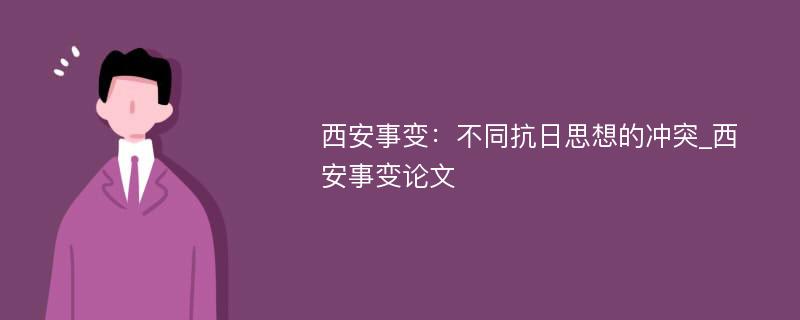
西安事变:不同抗战观念的冲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西安事变论文,冲突论文,观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36年底发生的西安事变,长期来人们已习惯于把它看成是抗战与妥协两种不同观念冲突的结果,是由妥协走向抗战的重要转折。近年,随着越来越多史料的公诸于众,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这一观点的基础有所动摇。本文认为,导致西安事变发生的关键因素不在于是否抗战,而在于如何抗战,蒋介石与张学良、中共之间最根本的分歧在于两条抗战道路,即全面抗战和片面抗战观念上的冲突。
一
西安事变前,国共两党及国内各政治力量间在对日抵抗态度上逐渐趋于一致。作为执政党的国民党和国民政府越来越痛感日本侵略的巨大威胁,维护政权及民族的生存权利,成为具有浓厚民族意识的蒋介石无法忽视的任务。1934年,蒋介石曾做出判断:“第二次世界大战——即中国生死存亡的关头……临到我们头上!……现在可供我们准备的期间,恐怕最多也只有三年。”[1](p.388)强调:“现在国家的长城已经为外人所占了,今后就是要靠我们全国的军人能够做国家的长城,我们要能尽到长城的责任,就务必随时随地用尽我们的心力、体力,一刻不停,丝毫不苟地来准备一切。”[1](p.448)次年召开的国民党五大上,蒋明确谈到,民族运动,“对外应向国际为吾民族求独立平等,对内应向民族为吾国际求自立自强”。两个方面“必须同时平衡进展,方有成功之望”[2](p.657)。
1935年华北事变后,国民政府继续加强对日抗战准备工作,在外交、内政、经济、社会文化、国防军事等多方面均采取了较为积极的措施。这些措施包括:改善与苏联关系,谋求与中共接触,政治解决中共问题;政府实施改组,将主张对日节节妥协者逐渐排除出政府;实行币制改革,法币与英镑挂钩,加强与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联系;开展民族文化宣传运动,提高中国民族的自信力和凝聚力;1936、1937年度国防计划把对日抵抗列为最急迫问题,进行了详细研究和规划;各地江、海防及作战阵地均开始着手整顿、加强,全国军队实行整编,提高、加强军队的素质和战斗力;尽力扩大武器装备生产,积极向国外洽购军火;加紧铁路、公路等基础设施尤其是西南后方根据地的建设等。所有这些,为后来的持久抗战发挥了不可低估的作用。1936年1月,蒋介石在与全国中等以上学校学生代表见面时表示:“如果和平交涉不能成功,最后当然只有一战,政府方面正在努力准备最后的牺牲,我们全国国民在这个危急的非常时期中,都应该在中央政府领导之下一致作最后牺牲的最大准备,才能达到我们和平的目的。……我决不怕战争,不过我要做有准备有计划的战争!我们和日本不战则已,战则必胜。”[3](p.108)
明示中国忍耐限度是国民政府对日逐渐强硬的明显标志。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有关最后关头的说法并不鲜见,但对“最后”的界限没有一个明确的限定,留下寻求妥协的活口和退路。1936年7月,根据不断变化的内外形势,蒋介石首次在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上对退让限度做了较为明确的说明:“假如有人强迫我们签订承认伪国等损害领土主权的时候,就是我们不能容忍的时候,就是我们最后牺牲的时候”,“从去年十一月全国代表大会以后,我们如遇有领土主权再被人侵害,如果用尽政治外交方法而仍不能排除这个侵害,就是要危害到我们国家民族之根本的生存,这就是为我们不能容忍的时候。”[2](pp.666~667)这一表态,向全国做了交代,不能不对国民政府产生一定的约束力。中共方面敏锐地注意到了这一变化,认为:“蒋委员长的这种解释,较之过去是有了若干进步,我们诚恳地欢迎这种进步。”[4](p.109)
事实上,西安事变前夕,在中日间的一系列交涉中,国民政府态度已明显强硬,表明了维护国家主权的原则立场。张群曾谈到对日基本方针:“一切交涉,都要取一定的外交方式,不作枝节谈判,同时在军事上,自己竭力准备……如果能够调整,固然是我们的希望,否则惟有一战以求解决。”[2](p.664)1936年9月,蒋在主持处理成都、北海两案时,态度强硬,指示:“此时外交应目无斗(全)牛以视之”[2](p.673),并要求:“京沪汉各地立即准备一切,严密警戒,俾随时抗战为要”[2](p.675)。随后,在国民政府支持、组织下,中国军队在绥远对进犯敌军展开反击,蒋在有关电文中,多次表示“不顾一切”维护华北主权,不惜与日破裂,准备做“任何牺牲”[2](pp.681~680)之意。正是由于国民政府和蒋介石的大力支持、督促,傅作义率部取得了百灵庙大捷[5]。对此,中共内部也做出了积极的判断:“汤恩伯准备援绥抗日,南京对日本采取强硬态度。总观各方情况,目前时局正处在转变焦点,我应不失时机,善于运用,争取国内和平,转向对日抗战。”[4](p.159)
当然,当时国民政府对日强硬并不意味着其准备迅速选择对日全面作战,毕竟,中国是弱国,是处于被侵略的地位,从根本上说,中国的因应必然是被动的而不可能主动。因此,在准备抗战的同时,国民政府始终在寻求和平解决中日间问题的出路,始终在努力拖延与日本最后摊牌的时间,蒋介石更将这一方略比诸列宁的布列斯特和约[6],这也就是我们看到的国民政府抗日准备和对日妥协往往并行的原因所在。而且,在政策的显性层面,更多显示的是其妥协的一面,这也是其政策往往不为舆论谅解的重要原因。更重要的,在将抗日准备主要定义为军事准备的前提下,蒋介石及国民政府对民众的抗日宣传相对忽视,甚至怕影响到其拖延策略的执行而持压制态度,对团结各地方实力派也没有表现出充分的的诚意。沈钧儒等谈到:“蒋先生在二中全会报告救亡御侮步骤与限度……在这个限度里面,尽可能的进行准备,我们是可以同意的;但是我们得再提出,除了这对外的限度之外,对内的停止内战和开放人民的抗日言论自由和救国运动自由,也是极端必须的。”[7]认为国民政府对日抵抗准备存在的重大问题,即在准备抵抗同时,没有最大限度地集中、发挥抗日力量,没有通盘考虑运用与实现全民抗战。
二
作为西安事变主角之一,中共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不可忽视的一支重要力量,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后,反蒋抗日是中共当时的基本方针。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中共对国民政府及蒋介石的立场也在逐渐发生变化。1935年8月,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帮助下,发表八一宣言,呼吁全体同胞摒弃政见分歧,“集中一切国力(人力、物力、财力、武力等)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8](p.522)。12月,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会议,确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指出:“不使一个爱国的中国人,不参加到反日的战线上去。这就是党的最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总路线。”[9]当然,这一时期,中共公开文件中对国民政府高层的判断还是悲观的,八一宣言就将西安事变的两个主角蒋介石、张学良与汪精卫一起,并列为卖国贼[8](p.519)。
但是,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最高政治决策者们,当然能够看清,蒋介石乃是国民党现实的最强有力领导人,与国民党的联合战线难以离开蒋介石,而且,蒋介石在日本压迫下逐渐表现出的民族主义立场中共领导人也并不陌生,因此,统一战线的现实道路离不开对蒋介石的团结、争取。1936年3月,博古在致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电中,说明蒋介石在南京政府抗日、投降两派中,“尚周旋两者之间之上”[4](p.31),注意到蒋介石有向抗日倾向转变的可能。而张闻天、毛泽东等则在复电中明确表示:“十分欢迎南京当局觉悟与明智的表示。”[4](p.35)6月12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言指出:“我们的口号,我们的重心是抗日,请蒋出兵。”[10](p.551)同时,中共与国民党在不同地点已经从多个渠道进行接触。1935年下半年,蒋介石授命陈果夫、陈立夫、宋子文、邓文仪等从多方面寻求与中共联络。次年1月,中国驻苏使馆武官邓文仪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两次会谈,邓转达了蒋介石的两党合作条件:中共取消苏维埃政府,其成员参加南京政府工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统一指挥;两党或党内合作,或共产党独立存在,南京政府可向红军提供军事装备和食品;红军可到内蒙参加抗日[11]。最初的谈判,虽未达成任何协议,但双方对彼此立场有了初步的了解。随后,国共了间展开多次接触,方式和层次也不断升级。1936年6月底,双方形成了共同的《谈话记录草案》,确认:“为求民族之生存,须立即实现民族革命之联合战线,共同抗日”[12](pp.823~824),同时,双方进一步讨论了实现联合战线的具体步骤和方案。11月,国共两党代表陈立夫与潘汉年实现高层接触,此后,直到西安事变前,双方始终保持接触。8月下旬,共产国际的指示进一步促进中共开展对南京政府的工作,并逐渐将这一政策公开化,确定“联蒋抗日”的统一战线方针。关于这一点,张闻天、周恩来在“致红四方面军电”中有扼要说明:“中国最大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抗日反蒋并提是错误的,我们从二月起开始改变此口号。三月南京有人来接洽,我们提出一般的条件,再往南京。六月、八月南京又有两次来件。八月上旬政治局讨论了对南京的方针……然而,我们的估计还是不足的。八月下旬国际又进一步指示。”[4](p.132)循着这一思路,1936年8月,毛泽东在有关电文中指出:“因为南京已开始了切实转变,我们政策重心在联蒋抗日。”[4](p.117)9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党内指示,明确指出:“目前中国的主要敌人,是日帝,所以把日帝与蒋介石等同看待是错误的,‘抗日反蒋’的口号,也是不适当的。”“我们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4](p.125)中共中央判断:“在日本帝国主义继续的进攻,民族抗日运动继长增高的基础上,国民党的政策有趋向于抗日的可能,有争取蒋军全部或其大部参加抗日战争的可能。”[4](p.137)征诸当时实际,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这一判断是符合国民党和蒋介石的发展趋势的,联蒋抗日政策本身也表明中共对蒋介石的判断已由卖国贼转向抗日的同盟者。正如西安事变善后过程中中共所指出的:“要发动全国性的、大规模的抗日战争,就一定需要全部中央军或至少是大部分中央军的参加。”[13]
此时,国内各政派及不同政治力量也逐渐注意到蒋介石和国民政府的对日抵抗立场。30年代以来一直与蒋对立的胡汉民于1936年初改变其一贯的反蒋抗日立场,提出:“余今日之工作,为如何促进政府之觉悟,并如何团结全国之抗战力量,俾中华民族最后之自救。”[14](p.57)长期对蒋抱批评态度的冯玉祥也认为:“介石确有救国之能力及心田。”[15](p.858)救国会领导人沈钧儒等在1936年明确指出:“政府对日外交,最近也比较地采取强硬态度。塘沽协定的正式披露,浪人走私的严重抗议,至少这两件事,表示政府不甘心屈辱到底。”[7]国民政府和蒋介石也不再在公开场合对抗日立场讳莫如深,1936年6月两广事变中,蒋致电陈济棠表示:“国家处境如斯,已无瓦全之理,中央救亡决心,与兄等初无二致。”[16]公开表露其迫不得已将起而抗战的立场。正由于此,毛泽东在1936年10月乐观地指出:“目前情势,日寇侵绥如箭在弦上,华北长江同时告急。但国内统一战线粗有成就,南京当局亦有转向抗日趋势。”[4](p.161)应该说,这一判断是全面和客观的。
历史是复杂的,在中国各政治力量殊途同归、逐渐走向抗战的历程中,1936年底,却发生了以要求实行全民抗战为主旨的西安事变。这一在历史发展线索中稍显突兀的事件,如果放到两种抗战观念冲突激化的过程中去考察,可以在相当程度上得到更顺理成章的解释。酿成这一重大事件的原因固然很多,但蒋介石的片面抗战立场和全面抗战要求之间的冲突,是其发生的最根本原因。
三
大量的事实证明,西安事变中张学良、蒋介石冲突的根源不在于是否抗日,而在于如何抗日,这一点,从张学良的态度上可以看得很清楚。1936年4月,张学良与周恩来见面之初,张对蒋介石的抗日态度做出了较为乐观的估计,认为:“在国民党要人中,只佩服蒋尚有民族情绪,领导大得力”,“相信帮蒋能抗日”[17](p.155)。以致周在信中含蓄地劝告张:“为抗日固足惜蒋氏,但不能以抗日殉蒋氏。”[4](p.61)周的这一说法本身就是中共开始调整对蒋政策的反映,也反证了张在这一问题上的态度。张的这一认识至西安事变爆发也没有迹象证明发生了重大变化。两广事变后,张学良受到蒋介石很大压力,但他仍然认为:“尽管在蒋的幕僚中有亲日派,蒋仍然是抗日的。”[18](p.90)
但是,张学良对蒋的抗日期许并不意味着双方的融洽,事实上,蒋张始终保持着一种微妙的关系。曾几何时,张学良曾是一方霸主,对蒋介石并不真心臣服。1934年,张学良甫回国内,在与胡汉民代表密谈时就表示:“已下决心为将来北方之主动,目前则仍与汪蒋敷衍,免其猜忌。”[19]此后,他和国内各地方实力派始终保持着密切的接触。热河失守前后,张在致手胡汉民函中谈到,九一八“负最终之责任者当别有人在”[19],暗示东北沦陷的责任应由蒋承担。30年代曾参与反蒋各方密谋的徐永昌,在日记中数次留下张学良参加活动的记载。1935年6月,两广方面代表携陈济棠白绫传书,策划请蒋下野,称:“张汉卿早已同情。”[20](p.271)刘定五则告诉阎锡山:“今日一通电报蒋即下野,张汉卿已与西南同意,至时电蒋同引罪下野,再由西南政会留张逐蒋。”[20](p.296)张蒋间已大有貌合神离之态。
导致张学良对蒋不满的原因很复杂,蒋自我中心的安内政策无疑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作为地方实力派首领之一,张有自己的生存需要,蒋的消融异己政策对他始终是一个威胁。而丧失东北的家国之恨,尤使张痛切希望掌握一支复地雪耻的力量。但是,张的这一愿望并不为蒋所谅解,东北军奉命参加“剿共”战争后,迭遭失败,蒋介石并没有安慰的表示,反而借机撤消了两个师的部队番号。连作壁上观的徐永昌也为此不平:“何立中、牛元峰两师进剿失利以致于覆没,他军何尝关怀一顾,且也责其无能,轻其将宪。宋如轩至截扣其两师底饷,中央也以为应当,似此情形,纵张汉卿顾全大局不之较,其如部下不平何?”[20](p.453)切身之痛,加上其他诸因素,使张对蒋的信心不断下降。
从1936年初开始,张学良和中共之间频繁接触,由于双方都有迫切寻找出路的要求,立场很快接近,中共从张学良那里得到了不少的物资援助,而张学良也对中共尤其是通过中共与实力大国苏联接近抱有厚望。在共同对日的旗帜下,同时也是为与南京政府抗衡,以张学良和中共的结合为基础,西北渐渐形成了一个松散的联合局面,中共致电共产国际时提到:“许多方面经常向我们提出苏联是否援助他们的问题,近来问得更加多了。打通国际路线已成了张学良、杨虎城、阎锡山、傅作义一班人的口头语了。”[21](p.232)在张学良看来,在对日问题上与中共、苏联有很强的结合点,完全可以相互结成一根链条。所以,张学良曾明确向中共建议:“红军应立即开始实施打通苏联,以便推动西北国防政府的建立。”[21](p.143)对建立一个有着苏联背景的西北对日联合体抱有厚望。
在与中共进行接触后,张学良对蒋介石的自我中心政策表示出越来越多的疑虑。1936年6月,他在王曲军官训练团演讲时提出:“我们要想全民动员,长期抗战,马上就要积极努力于唤起民众,组织民众的工作。”强调:“抗日与统一,统一与抗日,这两件事情是具有不可分离的连环的关系。”[22]这其中包含的集中民众力量的要求及抗日统一必须有机结合的判断和蒋介石单纯强调集中统一及服从的基本立场已有所区别。他后来总结:“良对中央同志怀有不满,因之更加忿恨,加深必须实现良之幻想。即:(1)促请蒋公登用良心目中所谓之贤哲。(2)容纳共产党,如总理北伐时然,给政府添新刺激,以图耳目一新,挽回国人之观念。(3)停止内战,团结作抗日工作,以免把有为之青年优秀自相牺牲。”[23](pp.1199~1200)1936年9月,他致电蒋介石,提出全国一致抗日救亡主张:“就各方言,欲救亡必须抗日,欲抗日必须全国力量之集中。”[24](p.147)在稍后致陈诚电中,更明确表示:“欲图救亡,必须抗日,欲谋抗日,必须统一。但统一力量,不应偏重军事,统一全民力量,乃是坚固之武力。”[24](p.149)集中全国力量,一方面是充分发挥民众的爱国力量,如同情支持“七君子”的抗日爱国主张;同时政治解决中共问题,发挥中共力量,尤其是借此充分利用苏联的力量也是题中应有之意。正如与张颇有接触的徐永昌在日记中所反映的:“张汉卿对抗日热烈极,大有宁为玉碎不顾一切之慨,甚至不主张剿共。以为在我抗日下共匪必无如我何。”[20](p.430)
从张学良的态度说,西北的联合固有对抗蒋介石之意,但并不必然把蒋介石作为假想敌,尤其是在共产国际指示联蒋抗日,国共两党间又颇有接触的情况下,尤其如此。张学良希望实现全国一致的团结抗日,把联合中共尤其是争取苏联支持作为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出发点,同时也希望自己在西北站住脚。满足他这两个要求,张学良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因此,如果蒋介石善用力量的话,西北大联合未尝不可为蒋所用。张对蒋的劝谏,其实也就是围绕着这一中心进行的。
四
蒋介石本能地把这种联合当成针对他的力量联合。陕西是西北首省,也是国民政府经营的重点。蒋1935年进入西南后,逐渐以西南为中国抗战的战略后方,而西北背靠苏联、屏障西南及其本身纵深广大的地理特征,使其在蒋的对日战略中占有不可动摇的重要地位。蒋介石将陕西俾予张学良,初意不无借重张学良,控制陕西以安西北之意,但他事必躬亲、惟我独尊,陕西作为其寄予厚望的西南大后方的重要屏障,势必要将其最终控制在自己手里。如他在西安事变善后时所说:“中央无论如何决不能放弃西北。中央数年以来,确认西北尤其陕西为北方国防之根据。关于开发西北与建设西北之事业,无不本于国防之见地,按照计划尽力进行……中央如放弃西北,即无异放弃国防,亦即无异于自弃其职责,故无论任何困难牺牲,势不能不确实掌握此重要之国防根据。”[4](pp.133~134)对这样一个战略要区,蒋不可能将其长期交给张学良。正因如此,张、杨的逐渐接近,尤其是张、杨与中共之间接触,形成“三位一体”局面,为其始料未及,在他看来是严重的失控局面,对其西北及整体战略形成巨大威胁。因此,他深为戒惧,两广事变时曾在日记中写到:“东北军之隐患,所谓:‘联共抗日,自由行动’之企图,乃因桂事和平解决而消乎?如果对桂用兵,则不测之变,不知伊于胡底。”[24](p.144)对张表现出相当警惕。蒋介石开始向张施加压力,西北的局面终于向着冲突激化的方向演进。
1936年8月,中共就注意到:“蒋介石有于西南问题解决后分化东北军撤换张学良之企图。”[4](p.121)毛泽东甚至致函提醒张学良:“不要再去南京了,并要十分防备蒋的暗害阴谋。”[10](p.567)杨虎城也告诫部下:“大批中央军进入陕西之后,一纸命令,甚至几句话,就会把我们和东北军调到河南、安徽那些地方,三天一改编,两天一归并,很快就会被肢解消灭。你们必须注意提高警惕,不要认为蒋介石的目的只是为了对付共产党,要看到这里暗藏着蒋介石排除异己的祸心。”[25](p.147)杨虎城这一说法,从西安事变事前事后一些情况看,并不完全是无根据的。蒋介石一再督促张、杨全力“剿共”同时,通过陈立夫主持的与中共谈判也一直在进行中,直到12月初,中共代表潘汉年与国民党方面代表陈立夫还举行了会谈,由于中共的让步,双方在政治上事实已不存在多大障碍,关键问题是军队改编和领导人的出处,陈在谈判中答应红军可保留三万人[4](p.174),中共则坚持“红军不能减少一兵一卒,而且需要扩充之”[4](p.175),双方未能达成一致。不管对谈判的结果做何种判断,可以肯定的是,这种幕后谈判的继续,和蒋在张面前表现出的对中共的强硬态度显然并不完全一致。
其实,蒋介石对不同的人的表态也有很大不同。当10月下旬张学良向他委婉进言劝其和中共抗日时,蒋断然拒绝,甚至表示即使“共党当面以手枪拟之,亦不与之妥协也”[20](p.486)。而仅在前几日,当冯玉祥向蒋提及与中共妥协问题时,蒋则轻松表示,除军队问题不易解决外,人的问题、党的问题都好办,以致冯玉祥乐观地在日记中总结与蒋谈话结果:“红军的事,得了三条结论,虽不十分清楚,亦倒还好。”[15](p.816)蒋的表态及冯由此得到的印象,从中共当时对与国民党谈判的乐观估计看,当不是毫无根据的。10月17日,中共判断“与南京谈判有急转直下势”,准备打破此前一直坚持的谈判没有进展不派领导人直接出去谈判的原则,“交涉由蒋派飞机到肤施接恩来到西安与蒋直(接)谈判”[4](p.158),并乐观谈到:“我应不失时机,善于运用,争取国内和平,转向对日抗战。”[4](p.159)蒋对张、冯在中共问题上完全不同的表态,无论哪一种代表了他的真实态度,或者两者都在其考虑范围之内,其所体现的心态颇值注意,在对张学良与中共联络有所察觉,又对张抱相当戒备心理的情况下,蒋介石对张的严厉态度,不无以中共问题向张示警之意。
张学良奉令入陕“剿共”,除刚刚到任时与红军有过激战外,实际一直态度消极,而蒋介石的督促也并不严厉。但是,恰恰是在获悉张学良与中共接触形成三位一体局面后,蒋对张的督促明显加紧,这一结果固然不排除形势变化的原因,但以压张进攻中共来破坏张与中共联络的意图是可以想见的,而且在局部地区也确实发生了效果。蒋至少可以期望如下结果:一是张对中共作战获胜,蒋可以牢牢把握处理中共问题的主动权;一是张作战失败或拖延进攻,蒋可以考虑把张调离陕西,趁机控制陕西。而无论哪种结果,张与中共的联系都可以借此破坏。蒋介石这种心态的变化及政策的变动,也就是中共在谈判时感觉困惑,不知道蒋“确实企图”的重要原因。
蒋介石一再进逼,使张面临着极其困难的选择。1936年12月4日,蒋亲自来到西安,继续逼迫张“进剿”红军,并做了将东北军调离陕西的准备。12月9日,蒋致函邵力子:“可密嘱驻陕《大公报》记者发表以下之消息:蒋鼎文、卫立煌先生皆到西安。闻蒋委员长已派蒋鼎文为西北剿匪军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为晋陕绥宁四省边区总指挥。陈诚亦来谒蒋,闻将以军政部次长名义指挥绥东中央各部队云。但此消息不必交中央社及其他记者,西安各报亦不必发表为要。”[26]12月12日,西安事变当天,《大公报》在要闻版以《陈诚指挥绥东军事》为题刊出这一消息,且称:“蒋鼎文对剿匪总司令职表示谦辞,但愿短期内在陕帮助进剿。据闻残匪之消灭仅属时间问题。”[27]蒋介石此举,显然有利用非官方报纸为撤换张、杨制造舆论,向张、杨施加压力之意。而此前蒋会见东北军将领等一系列举动也使张心怀疑惧,“思蒋公对良不加信任,已不重视矣”[23](p.1201)。这一切,终于使张、杨铤而走险,直接引发了西安事变。
五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发动兵谏,扣押蒋介石。事变后,张、杨立即发出通电,宣布其八项主张。通电对蒋介石的具体指责是“弃绝民众,误国咎深”,八项主张的中心内容则是: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停止一切内战;释放被捕之爱国领袖和一切政治犯;开放民众爱国运动;保障人民政治自由;立即召开救国会议[28](pp.3~4)。这一通电的主旨在于国内政治的改革,改组政府、停止内战、开放政治等要求,实际都是对南京政府实行的专制政策的反对,指向的是南京政府片面的、自我中心的对日政策,所以张学良说:“良等此举,意在促成全国真正之觉悟,全体动员;盖对日作战,必须军民并用,仅恃徒知服从之军队,绝不足以济事也。”[29](p.173)也就是说,虽然南京政府的政策也具有走向抗日的可能和条件,但由于其“弃绝民众”、排斥异己,“未能将抗日力量十分发扬”[28](p.82),实际仍然是误国的。这一判断,正是为什么张、杨要扣蒋,而又从一开始对蒋安全即注意保证的根本原因。后来,毛泽东谈到事变时,在肯定“国民党进步虽极缓慢,但一致抗日的前途是存在的”[30](p.3)基础上,明确指出:“西安事变是国民党内部在抗日问题与国内改革问题上,因政见不同而发生的。”[30](p.1)此所谓政见差异,结合此前中共对国民党认识的变化及事变后国共关系的新形势看,实际也即指南京政府自我中心的内外政策与全面抗日的抗战政策之间的冲突。
当然,出于宣传、策略等方面的原因,张、杨发动事变后,也有种种指责南京政府对日妥协的言论。但是,正如阎锡山所说的:“前在洛阳时,汉卿曾涕泣而道,以为介公有救国之决心而方法上有所矛盾。”[28](p.72)双方争持的焦点是具体方法而不是根本立场。所以,事变后,张、杨多次强调,事变的目的在于“增加抗战力量”[24](p.162),在致宋哲元电解释扣蒋动机时谈到:“我们必须联合各党各派一致抗日,方足以救亡图存。学良迭将此意面呈蒋公,未蒙采纳。不得已将蒋公抑留西安,促其觉悟。”[23](p.1061)重心是放在反对蒋介石自我中心的安内攘外立场上。而事变后孔祥熙通过张学良转蒋电中也颇具深意地谈到:“抗敌御侮,国人皆同此心。中枢同人,初无二致……中枢之措施,汉兄尽所稔知,此次之事,当出迫不得已,别有苦衷。弟意任何主张,苟利国家,无不可从长计议。”[23](p.1078)此所谓“别有苦衷、“任何主张”,在孔祥熙之意,当然不是指是否抗日问题,综合文意及当时实况判断,当是指改变自我中心的安内政策、团结各地方实力派、容纳共产党而言[15](p.816)。可见,当时当事各方对西安事变的实际目标都有着心照不宣的认识。
作为西安事变的另一重要当事人,蒋介石在代表其对事变回应的《对张杨训词》中也强调:“中央数年以来之政策方针,亦唯在和平统一、培养国力、团结人心,不忍毁损民族之力量。”[31](p.21)这既是为自己辩护,其实也委婉回答了张、杨集中力量一致抗日的要求。而中共中央的判断则更为明确:“这次发动是为了要抗日救国而产生的,是要以西北的抗日统一战线去推进全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开始。”[4](p.222)
西安事变的谈判结果进一步明白显示了发动者的目的。根据周恩来的报告,双方最后达成的谈判结果主要内容是:改组政府和国民党、中央军撤离西北、释放被捕之爱国领袖及分期释放政治犯、停止“剿共”、联俄联英美法[4](p.272)。可以看出,这一结果大体实现了张、杨的八项主张,是南京方面及蒋介石,而不是张、杨及中共让步的结果[4](p.275),基本代表了张、杨发动西安事变的意图。同时,谈判结果明显是以国内政治的改革为中心的,体现着国内团结一致的基本观念,和张、杨发动事变时集中全国力量全面抗战的要求相符合。和八项主张相比,谈判结果增加了确定联俄、联英美法外交政策一项,但这本身就是国民政府正在致力的工作,并不代表着外交政策的转向。
正是由于西安事变存在着上述这样一些特点,有论者提出,西安事变中无论是张、杨的八项主张或是最后的谈判结果并未直接涉及到对日抵抗问题,因而怀疑张、杨发动事变的动机[29](p.64)。其实,这和把张、杨与蒋冲突看成是抗战和投降两种原则立场的区别一样,都是对张、杨与蒋之间冲突的本质有所误会。张、杨的八项主张针对着蒋介石片面的自我中心的内外政策,目标在于集中全国力量一致抵抗外敌侵略,即所谓“八项主张不过发动抗日必备之条件”[23](p.1100),中心在如何抗日而不是是否抗日。所以,抵抗侵略的原则立场,未列入谈判条件之中,实属顺理成章。
这也是事变和平解决的基础。了解了西安事变的这一性质,对于我们继续解开研究中的一些疑点,相信都会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收稿日期】2003年12月
标签:西安事变论文; 抗日战争论文; 国民政府论文; 张学良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历史论文; 蒋介石论文; 南京国民政府论文; 国民党论文; 世界大战论文; 太平洋战争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