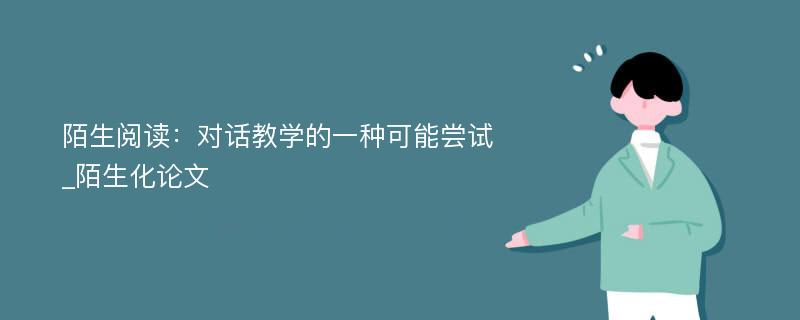
陌生化阅读:对话教学的一种可能性尝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可能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年来,很多文章强调了教师在教学对话中要积极营造民主的氛围,要有平等的态度,真诚和爱,彼此精神世界的敞开、相互接纳等等,这些无疑都是教学对话展开的前提。但是,只有这些显然还不够,我们应该看到教学对话对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提高阅读教学对话的质量,首先要求语文教师自身对文本的更高水平的解读。在阅读教学对话中,存在两种意义的对话:第一种是师生与文本对话,阅读过程是一个对话的过程。这是阅读学意义上的对话;第二种是师生之间、生生之间的对话,教学中要展开平等的对话。这是教学意义上的对话。第一种对话,是阅读教学对话的基础,师生间、生生间的对话,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展开,又把第一种对话引向深入的。阅读教学对话,包含了较为复杂多样的对话形式。既有教师、学生与文本的对话,也有师生、生生之间的对话,还有教师学生的自我对话;阅读教学的文本,既包括文选系统的各类课文,还包括与之相关的导学系统、练习系统、知识系统,还有教科书以外的教参、教案、多媒体课件、网络资源、课外读物等等。阅读教学最基本的教学目的在于培养学生的阅读能力,教师作为阅读教学对话的引导者,首先应该具有较好的阅读能力。
阅读是由多种心理因素参与的心智活动。阅读教学是比一般个体阅读更为复杂的活动。因为在阅读教学中存在多个阅读主体,阅读主体间的地位、水平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作为第一阅读主体的教师,在阅读的感知、理解、鉴赏方面理应优于学生。不然拿什么来引导学生的阅读呢?阅读教学又从何谈起呢?从阅读教学的角度看,教师与文本的对话,是阅读教学中对话良好地展开的前提和基础。所以,阅读教学中对话水平的高低,教师的因素仍然是关键,所以笔者认为提高教师的阅读鉴赏水平乃是当务之急。在此,我们不妨尝试借鉴陌生化的文学理论,并把它运用到阅读教学中。我们不妨把自己熟知的解读暂时“搁置”起来,通过追求对熟悉的文本的陌生化阅读效果,达到对文本的个性化解读。
“陌生化”这一原理是由俄国形式主义理论家什克洛夫斯基在《作为技巧的艺术》中最先提出来的。“陌生化”正是一种重新唤起人们对周围世界的兴趣,不断更新人对世界感受的方法。它要求人们摆脱感受上的惯常化,突破人的实用目的,超越个人的种种利害关系和偏见的限制,带着惊奇的眼光和诗意的感觉去看待事物。由此,原来司空见惯、习以为常而毫不起眼、毫无新鲜感的东西就会焕然一新,变得异乎寻常,从而引起人们的新颖之感和专心关注,使人们重新回到原初感觉的震颤瞬间,“陌生化”就是不断打破人们的接受定势,使人们从迟钝麻木中惊醒过来,以一种新奇的眼光,去感受对象的生动性和丰富性。表现在文学作品中就是打破文学语言正常节奏、韵律和构成,通过语言形式的强化、重叠、颠倒、浓缩、扭曲、延缓等打乱正常顺序,使文学语言与熟悉的语言形成相互疏离、相互错位,以此产生令人耳目一新的功效。这样就可以把读者从迟钝麻痹的状态中唤醒以增加阅读的效果。
阅读教学中的陌生化,包括阅读文本时的“陌生感”和教学方法上陌生化的追求。我认为在阅读的意义上有两层含义:其一是指阅读文本时,找到作者用陌生化的手段创作的句段;其二是有意识地对于阅读主体很熟悉的课文,用陌生的眼光去阅读。从某种角度看“陌生化”是美感产生的条件和前提。这能够解释为什么当我们到某处去登山,面对眼前的自然美景会激情澎湃,感慨万端;而常年住在山脚下的人或每天上山的挑夫却没有这种感觉。在诗歌写作中为了表达的效果,经常运用通感的修辞手法,甚至有不合逻辑、不合语言规范的句子,而这些词句恰能构成诗歌触动读者神经的敏感部分。请欣赏下面19世纪英国诗人的这句诗:
野鸽孵着自己悦耳的啼声①
这里诗人没有直接写野鸽的啼声多么悦耳,野鸽“孵着”一个声音,这看似不合情理的话语恰是富有诗意的语言。在诗人华兹华斯看来有了“孵着”这个词后,就使读者的想象力更能注意到野鸽一再柔和的啼叫,野鸽“仿佛很喜欢倾听自己的声音,带着孵卵的时候必然有的一种平静安闲的满足”② 请注意诗人华兹华斯作为诗歌鉴赏者,他把野鸽完全人格化,在他眼里野鸽仿佛喜欢倾听自己的声音。在这里,诗人运用了陌生化的手法,使我们从野鸽的啼声想象到它的形象,我们试图接近诗人写诗时的感觉:也许是一个春日的早晨,诗人正是听到了远处传来的几声柔和悦耳的野鸽啼声,想象到在湖畔草丛中也许有个野鸽巢,也许有一只正在孵卵的野鸽,怀着一种抑制不住的欣喜,心中涌起这句诗。这句诗带给我们如此美妙的的想象,这样阅读也许就可以算作完成了一次感觉的还原。如果我们阅读文学作品时,超越时间和空间的局限,试图找到作者写作时灵感飞动的瞬间,让我们的心和作者的心灵“相遇”,就有可能还原作者的感觉,有可能使阅读与欣赏成为一种美妙的沉浸或超越。
我国现代诗人戴望舒,以一首《雨巷》闻名于世,《雨巷》中用了中国读者熟悉的“丁香”意象。他的另外一首诗《我用残损的手掌》恰当地运用了读者陌生的意象:残损的手掌。它表现了戴望舒诗歌的另外一种风格。
我用残损的手掌
摸索着广袤的大地:
这一角已经变成灰烬,
那一角只是血和泥;
……
这里“残损的手掌”让读者想象到被外族侵略的祖国,遍体鳞伤,血迹斑斑,而作为她的儿女也饱受凌辱与伤害。“残损的手掌”这一意象,有一种悲怆感,让我们仿佛看到,一个受伤的士兵在充满“血和泥”的土地上,用残损的手掌摸索爬行,又好像看到他在抚摸一张被炮火烧残的中国地图……正是这“残损的手掌”,给读者的视觉以强大的冲击力,胜过诸如“男子汉的手掌”“坚强的手掌”“遒劲的手掌”等惯常的用法。
这种言语陌生化的手段被广泛运用于各种题材的文学作品中。拉丁美洲魔幻现实主义的代表作《百年孤独》,其突兀的开头就运用了这种手法:“许多年之后,面对刑警队,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将会回想起,他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这句著名的开篇,一下子就预示了许多年以后的事情,开拓了故事开展的时空,像一幕电影镜头,给人以时光倒流的感觉。“见识冰块”把熟悉的事物写成为陌生,“冰块”,我们人人熟悉,为什么作者却说要“见识冰块”?这个开头确实不同凡俗。那个遥远的下午,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什么许多年后还将会想起?那个下午为什么如此重要?那冰块又意味着什么?《百年孤独》中运用了大量的陌生化手法。
陌生化,本来是文学创作上的概念,我们在这里借用作对文本阅读时的一种感觉状态。阅读文本要有独到的见解,没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就谈不到对话。我们在阅读时不仅要捕捉作品中的这种言语陌生化的表现手法,更要主动寻求阅读的陌生化的效果。我在这里所说的“陌生化”指教师对文本要保持新鲜感,尤其对熟悉的文章而言。这是一种良好的阅读状态,我们要把前人的、他人的、甚至自己的对文本的种种解读暂时“搁置”起来,仿佛第一次接触这篇文章,重新对熟悉的文本进行陌生化的处理,只有这样才可能有新的感悟,才能有独到的见解。
语文教师面对的课文文本不外乎两种情况:一种是新的篇目,甚至以前都没有接触过的,例如《等待戈多》(节选)《百年孤独》(节选)《人生的境界》《人是什么》《米洛斯的维纳斯》《花未眠》等新选进教材的课文;另一种是长期保留在教材中的篇目,例如李健吾的《雨中登泰山》,朱自清的《荷塘月色》,恩格斯的《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鲁迅的《故乡》《祝福》《记念刘和珍君》等。还有些即使前几年没有在中学教材里出现过、近几年新选入的篇目,却也是教师们熟读多遍的文章。如何在这么多遍的阅读之后,仍然对作品保持最初阅读时的感觉,而不让一直以来阅读的思考与理解来打扰教学思路与对话?对于前一种新篇目,不妨先不要看任何参考书,仔细阅读,写下自己初读时的问题及感想,然后了解其作者、写作背景后,再多读几遍。对这类课文我们很容易产生初读的新鲜感受,也就更容易想见学生阅读的心理;但是对于熟悉的课文,教师面对的困难是:因为多次的阅读反而感觉迟钝,从而影响与文本对话的兴趣,对其评论的教学语言也有可能有格式化的倾向,这正是阅读教学中成功对话的障碍。我认为,如果面对这种状况,就需要我前文所谓的“陌生化”处理了。请你清空你以前阅读的他人的评论及自己以前的阅读体会,静下心来调动你的想象力、你的感知力,细细阅读原文,最好把那本你写满各种评论文字的课本放在暂时找不到的地方,把熟悉的课文变成陌生的,——如第一次阅读一样。把熟悉的文章读陌生,是比较困难的,但是只有这样,才能从中发现新的东西,有新的感悟,这也是教学的创造性的体现。很多优秀的语文教师不断重新备课,推翻以前的教案,其道理就在于此。
在阅读教学中,有意识地陌生化的效果追求,意味着不重复自己。不重复自己的教学思路,不重复自己的教学言语。如今上网查找资料如此便捷,给教师备课带来很大的方便,但是也有负面的影响,独立思考问题的时间少了,在阅读文本之前,经常看他人的言说,重复他人(教材编撰者、教参)的阅读,久而久之,忘记了自己的独立思考,丧失了独立解读文本的能力,丧失了自我的话语权。我们提倡教师备课充分,并不意味着尽可能多地照抄别人。其实不仅仅是语文教师,在学术界普遍存在重复他人的阅读的现象,比如赫尔巴特如何如何、杜威如何如何,几乎都是在重复他人的评价、他人的阅读。很多人几乎没有亲自阅读过这些教育大师翻译过来的原著。《课标》中提出了阅读教学中要赋予学生“倾听”作品的权利。笔者认为,首先教师要拥有和行使这个权利。如果一个教师他自己对文本的理解都来自教参,或者是别人的阅读体悟,把这些东西抄在自己的教案中,视作珍宝,甚至作为解读课文的标准,势必把本应该有不同阅读感悟的内容忽略过去,而把那些所谓标准预设到自己的教学框架之中。独立解读文本,意味着教师在阅读课文时要有自己的见解,能和作者作一番对话,而这个对话的程度的深浅直接影响到教学对话水平的高低。因为如果一个教师不能感悟作品,不能质疑文本,就很难引导学生去这样做。正如李镇西老师所言:“没有语文能力或者语文能力不强的教师,是很难培养好学生真正的语文能力的。这是不言而喻的。在这里,‘培养’同样首先意味着教师本人语文能力的示范。教会学生阅读,教师本人就应该善于阅读,特别善于在阅读中发现问题。”③
任何艺术之所以存在并且有生命力,就在于它的独创性。阿炳的《二泉映月》之所以打动人心,成为我们民族音乐的瑰宝,就因为它有不同于别的乐曲的特点,它凄婉、柔美的旋律,触动了我们心灵中最柔软的部分。日本教育学者佐藤学先生提出了教学中的“原创性”问题,他认为“在‘原创性’得到维护的课堂里,摒弃外来的知识、谈论自己的真实的教师出现了,同时,每一个儿童也作为意义的主体建构者出现了。这样,就可以建设起每一个儿童——他们的认识与表达那是不可置换的个性的文化——都受到尊重的课堂。”④ 阅读教学的课堂,只有师生双方对文本个性的解读,才能构成其课堂的“原创性”。在这点上教师应该堪称表率。
当然,陌生化阅读不是唯一的阅读状态,而个性化阅读也不能脱离阅读的社会性,因为阅读是个性化行为,阅读又是社会化行为。“知人论世”也是阅读不可或缺的,这要求语文教师具备必要的文史知识,及关于作家作品的文学知识。另外,在阅读教学的对话中,我们要高度警惕把对文本的多元解读变成任意解读,变成任何理解都有道理却没有答案。阅读教学中的经典文章,大多是人类思想的精华部分,对它们的阅读学习,很多时候就是经受心灵的净化。于漪老师说,语文教学是通过与智者、圣者的对话,提高学生的境界。教学论专家杨启亮教授也指出,对语文选文中体现着作者特定背景下的特定感情、态度、价值观,必须予以尊重,惟其尊重才有语文。“教者和学者对语文还应持有虔诚、敬畏之心,虽不必像故人那样宗教般地对待文化经典,正襟危坐地运笔写字,但以待人、待文化、待天下之心教学语文还是很有必要的”⑤,尊重,这也是对话精神的精髓吧。注释:
①②华兹华斯《抒情歌谣集》1851年版序言见《西方文论》(下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
③李镇西《对话:平等中的引导》《人民教育》2004年第3—4期
④日]佐藤学著《课程与教师》教育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
⑤杨启亮《困惑的语文:一种回归本体的教学期待》《语文教学通讯》2005年第9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