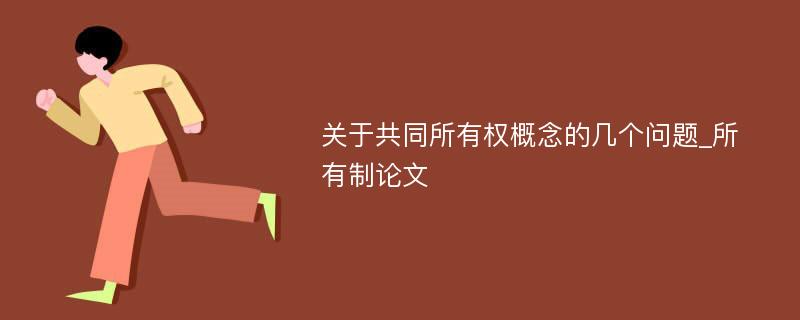
关于共有制概念的几个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几个问题论文,概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共有制理论是80年代中期以来兴起的一种所有制改革理论,但由于以往改革实践的积累有限,加上人们对这种初步实践经验的认识方法又不同,这就使共有制问题的研究一直处在初步探索阶段,仅共有制概念本身的含义,理论界至今仍存在很大分歧。党的十五大在所有制问题上的重大理论突破,为共有制问题的深入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指导。笔者就目前共有制概念界定上仍然存在,以及人们可能达成的共识谈点个人意见。
误区之一:共有制本是所有制关系中“一般”范畴的概念,却要给它定性、定位;仅凭“共有”的含义是共同占有,就能认定它是姓公、姓社,这是符合马克思关于公有制设想的改革模式
共有制概念是80年代中期一些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在大胆探索集体经济新的产权制度模式的过程中率先使用的。使用这一概念的初衷是要强调自己独特的改革模式既不同于私有制和传统的公有制模式,又同其他地区产权制度改革做法有区别,并要使自己的实践模式从马克思的公有制理论设想中找到根据。但是,这样一来就使自己陷入了一个自相矛盾的境地:一方面使用一个跨越历史时空、带有普遍性的所有制“一般”概念,另一方面却要赋予它特定的性质、内容与任务。关于“共有”不等于公有,理论界已作过不少探讨。笔者要强调的是,既然共有制这个概念的内涵是定为“共同占有方式”(从词义本身看也只能如此),那么它的外延就极其宽泛,至少可以包括“劳动者的共同占有”、“剥削者的共同占有”、“劳动者和资产者的共同占有”等,而单就“劳动者共同占有”而言,又分古代公社的共同占有,私有制社会劳动者的共同占有、社会主义社会劳动者共同占有、共产主义社会共同占有等不同社会历史状况。可见“共有制”不是今天改革才有的新事物,而是古今中外所有制关系的历史上早已有之,并继续存在的现象,仅凭“共有制”这顶帽子,实在难以承担为今天的改革模式“正名”的重任。
其实,只要对共同占有方式这种所有制关系的“一般”范畴作点具体的、历史与逻辑的分析,就不难理解将共有制当作一种特定性质的新的所有制概念,难以得到人们一致认同的原因。首先,共同占有方式同非共同占有方式一样,都是所有制形式范畴,同所有制基础的社会性质没有必然联系,只有同具体的社会历史内容结合起来,才能同所有制性质和社会制度挂上钩,仅从形式本身不能区分姓“公”姓“私”、姓“社”姓“资”。正如十五大报告所讲的不能笼统地谈论股份制是公有还是私有一样,不能笼统地讲“共有”就是公有。其次,“共同占有”是相对于“单独占有”而言,属于社会化占有方式,但社会化不等于集中化、公有化,也包括分散化、非公有化占有,是社会化占有方式的各种所有制形式的总和。从人类历史上迄今为止的所有制形式看,共同占有方式的所有制形式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作为单一主体占有、权利不可分割的公共占有制(公有财产制),包括国有制、集体(社区、社团)所有的公共财产等,其中,国有财产又包括不具有权利排他性的社会公共产品和可以在市场流通的经营性资产。另一种是多个主体共同占有同一财产,权利可以分割的财产共有制(或叫共有财产制)。所谓权利可以分割,是指各个财产共有人享有共有财产所有权的份额明晰,共有人可以通过收回或转让自己所占份额的财产权而退出这种共有财产关系。显然后一种情况因财产权主体结构是多元,财产所有权的性质便不确定。构成共有财产关系的各方性质各异,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法人组织,可公可私,可中可外,这种财产共有制不过是各种性质主体构成的混合所有制。复次,无论公有财产制还是共有财产制,本身都没有姓“资”姓“社”之分,国有制、集体所有制可以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本形式,也可以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成分。公有财产制和共有财产制是否能成为社会主义公有制,关键看劳动者是否从经济到政治上成为社会财产的主人。具体说,关键看代表全体劳动者根本利益的国有制在国民经济中是否起主导作用,国有、集体所有和混合所有制中国有成分与集体成分的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是否占优势。最后,共同占有方式作为社会化占有方式,它是生产社会化历史发展的产物,随着社会化生产力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具有不同的历史内涵与社会形态。马克思、恩格斯设想在未来社会化生产力高度发达的条件下,共同占有方式将达到这样一种历史境界:全部生产资料已成为人人平等、直接占有和使用的社会公共产品,那种旧式社会分工与传统的财产关系及财产观念同国家、商品、市场经济一起走向消亡。马克思将这种未来社会形态的共同占有方式的历史内涵称为“劳动者的自由人联合体”,同一切以往的所有制形式比较,这种未来社会共同占有方式在不同角度上可以有不同概念:“社会所有制”、“共产制”(完全的公有制)、重新建立的“劳动者个人所有制”等等。马克思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包括它的第一阶段)共同占有方式所达到的社会化历史高度,显然是今天社会主义共同占有方式不可同日而语的。今天的社会主义共同占有方式架起了通向未来社会的历史桥梁,但桥梁远不是彼岸。
误区之二:把共有制概念界定为一种新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或一种特定的公有制实现形式。在十五大以前,称共有制是区别于私有制和传统公有制的“第三种所有制”,一种公私兼容的“综合性所有制形式”;十五大以后,称为公有制的一种实现形式
正如上述分析所指出的,如果共有制作为社会化占有方式的一般概念可以成立的话,那么就不是社会主义特有的,也不只有一种所有制形式,更不只一种所有制实现形式。这里还必须搞清楚,所有制形式同所有制实现形式是所有制形式范畴中两大不同层次的概念。所谓所有制形式是指作为单一主体占有、权利不可分割、所有权归属性质明确的占有关系,通常称某种所有制或经济成分,个人所有制是这样,国有、集体所有等各种公有制也是这样。所有制实现形式其实是所有制的派生形式(再生形式),即原有的所有者主体不变,而所有权的实现过程可以通过不同企业财产组织形式而变得多样化,表现出多种形式。同一所有制可以有多种实现形式,同一实现形式可以为不同所有制所有,或包容各种不同所有制成分与利益主体。
所有制实现形式之所以不反映所有制的财产归属性质,而只反映企业财产权主体结构状况与财产组织形式,这是经济运行中资源配置的不同方式与要求所决定的。经济社会化市场化程度低,所有制实现形式简单,只采用那种财产权主体结构单一、所有权同经营权(实际占有权)不分的传统企业组织形式。经济社会化、市场化越发达,所有制实现形式则越加多样化,除了个体户、独资企业,更多的是由多元主体的财产组成的混合所有制企业(法人团体),包括从传统的合伙制、合作制到实行现代企业法人财产制度的股份公司、股份合作制、各种社会基金等财产组织形式。我们看到,在生产社会化、市场化推动占有方式社会化、市场化的过程中,各种所有制属性不变,所有制结构相对稳定,而所有制实现形式则是最活跃的因素,成为把各种经济成分、各个产权主体的财产纳入社会化、市场化大生产过程共同发展的产权运行机制。
所有制形式范畴两大层次的联系与区别表明,所谓财产共有制(混合所有制)正是共同占有方式的所有制实现形式(产权制度)层次。共同占有方式的形成、发展不仅要有财产公有化成分(公有化程度取决于生产力具体水平、公有财产的社会性质取决于整个社会经济基础的性质),更要有财产共有化(产权社会化、市场化)的财产权主体结构与产权组织形式。财产权主体结构宏观上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微观上则大多是多元化。各个所有者通过不同产权组织形式结成各种不同的财产利益共同体,并且在市场机制作用下不断进行产权流动与重组,实现各种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作为生活资料的财产共有关系,古今中外早已有之,而作为生产资料(资本)的财产共有化则是市场经济的产物。市场经济越发展,财产共有制关系越发达,企业财产组织形式越多样化,各种社会化程度较低和非共同占有的所有制成分日益纳入共同占有方式的所有制实现形式的体系。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不仅要让公有财产占主体地位,而且要构建、发展财产共有制关系,使各种公有财产同非公有财产共存互补,通过多样化的现代企业组织形式,各个不同主体的财产融合一体,共同发展。社会主义共同占有关系的传统体制是一种纯粹公有、产权集中统一的所有制模式,它扼制了经济社会化、市场化过程,也阻碍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发展壮大。近20年的市场取向改革,不断调整所有制结构,改革创新所有制实现形式,说到底就是遵循市场经济条件下共同占有方式发展的客观规律,构建、发展与完善以公有财产为主、与多种非公有财产并存,融合一体、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财产共有制关系。
误区之三:认为共有制就是深圳万丰村创造的劳动者共同所有制
80年代初兴起的股份合作制经济是我国农村继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又一场产权制度大变革。作为又一项群众性的制度创新,从一开始就带有鲜明的地区特色,形成各自不同的股份合作制发展模式。80年代中期一些沿海发达地区兴起的社区型股份合作制模式中,以深圳万丰村、横岗镇、广州天河及浙江东阳集团为代表的深圳模式(万丰模式),在各种实践模式中很有特色。这种模式在产权上社区合作制因素浓厚,又具有股份制资本联合要素,企业财产归社区集体占有经营,又折股量化到个人,只作分红依据,不得转让、继承,一般也不退股。在分配上,按股分红的资本回报率高于合作制。深圳模式的重要意义在于它为社区内劳动者个人所有同集体占有相结合、发展社区经济、实现共同富裕提供了一条可资借鉴的思路。深圳万丰村在制度创新过程中一个可贵之处,就是不仅勇于实践,大胆探索,而且勤于理性思考,自觉地将自己的实践经验总结上升为理性认识,再用来指导实践。然而,股份合作制作为一项根本性的制度创新,实践时间不长,模式的多样性,制度形成的复杂性和不规范性,使这一新的产权制度的理论研究起步后具有很大难度。在近十几年产权制度改革的观念、政策、法规都滞后的环境下,理论研究中各种观点的探索性与不成熟就不可避免。用共有制或劳动者共同所有制这类概念来界定万丰模式,正代表了股份合作制理论研究中一种尚不成熟的观点。这种观点仅仅从微观企业形式上,并且只以万丰模式为典型依据,为公有制设计一个劳动者共同占有与个人所有相结合的理论模型,因而对公有制实现形式的分析带有一定的片面性。同时为了满足“所有制性质取向”,力图将股份合作制的劳动联合与资本联合、共同占有与个人所有统一到一个带有公有制色彩,但内涵与外延都过于宽泛的概念上来,结果概念的不确定性反而模糊了万丰模式本身的制度内涵。
提出一个新的范畴或概念,必须从内涵到外延都能把握它同其他事物相区别的质的规定性,否则难以成立和为大家所普遍接受。对共有制概念界定问题提出以上三点质疑,并不表明笔者反对使用这一概念,否定这一理论研究,而是要指出,共有制这一概念在什么情况下可以成立,而在什么情况下不可以使用。
共有制作为一种研究所有制形式的方法,即研究所有权社会化历史发展规律的理论,才成为有特定含义的独立概念。共有制理论首先是研究占有方式社会化一般规律,其次是研究人类社会商品——市场经济时代财产权社会化一般规律,最后要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财产权制度的特殊规律。根据近20年来我国所有制改革实践的基本经验,笔者主张确立社会主义财产共有制关系这一新的范畴与法权概念(参阅拙文《关于社会主义财产共有制关系的历史思考》,载《中共中央党校学报》1997年第3期), 以反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所有制结构与所有制实现形式的基本特征。共有制理论的现实意义就在于此。至于股份合作制(无论它有多少模式)企业产权制度与经营方式,按照“三个有利于”标准,在改革实践中被证明可以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一种实现形式(显然并非唯一的实现形式),但决不要因此而认为这些本属于中性范畴的产权制度与经营方式本身就姓“公”、姓“社”,非得要对它们定性定位,用共有制一类概念来重新界定,甚至取代原有的国有制与集体所有制概念。因为这只能造成理论上的误区,也不利于政策上的规范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