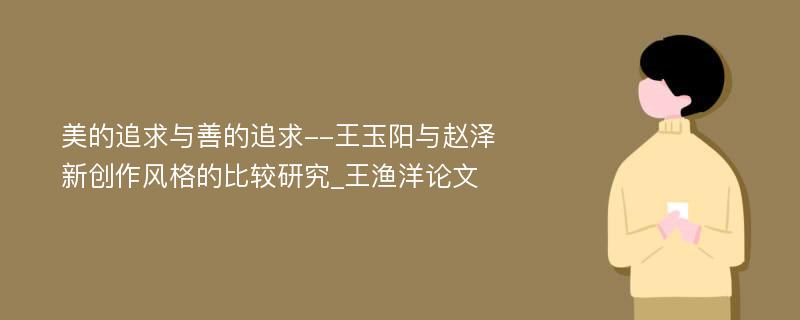
美的追求与善的追求——汪渔洋、赵执信创作风格比较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风格论文,执信论文,汪渔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同一时期(清初)、同一地区(今山东省淄博市),迭出三位文学巨擘,王渔洋、蒲松龄、赵执信,恰应了那句人杰地灵的话头,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罕见稀闻的佳话。不过,三人的艺术道路相去甚远,蒲氏以短篇文言小说名世,姑置勿论,王、赵同为诗人,差异却亦十分明显,所以然者何?即本文将要讨论的问题。
一、两种风格的诗
首先让我们来看两组短诗,目的在于通过一斑见一般,从感性上了解王、赵二人诗作的差别,并非轩轾甲乙之意。左侧为王作,右侧为赵作:
第一组
江 上 暮行湖上
吴头楚尾路如何?寒光滟滟泛光湖,
烟雨秋深暗白波。灵蚌深潜定有无?
晚趁寒潮渡江去,闻道天龙贪采拾,
满林黄叶雁声多。寄言休炫月中珠。
第二组
真州绝句吴江夜泊即事戏题
江干多是钓人居,沽酒穿林寻远火,
柳陌菱塘一带疏。买鱼和月过邻船。
好是日斜风定后,自知不及乘轩鹤,
半江红树卖鲈鱼。得向松陵乞料钱。
第一组中的两首诗,均是写的舟行观感。然而《江上》纯系写景功夫,通过“烟雨”“寒潮”“黄叶”“雁声”等意象的组合,传达出极富江南水乡野况凄迷味道的那种清秋嫩寒的境界,谓之“长江秋韵图”可也。作之者得于心,览之者会其意,妙造自然,化景物为情思,信歌诗之精品,艺术之上乘!《暮行湖上》却不然,该诗系雍正二年(1724),作者自苏州还乡,行经泛光湖有所感而作。泛光湖在江苏宝应县西南,当地传说湖中有一含珠蛤蚌,夜晚辄出,照耀湖面,光华万顷,故名泛光湖。诗歌因借这一神话传说,告诫灵蚌不要炫耀自己的夜明宝珠,以免被天龙抢去,从而对封建统治者(天龙)的贪婪本质进行了尖刻的讽刺。可见写景并非意旨所在,作者的用心乃在于揭露与批判时政。
第二组诗中两首,虽然入眼景物(江岸、树林、日月)、情事(买鱼卖鱼)类似,然而立意绝然不同:《真州绝句》画的是一幅宁静、舒缓、融和骀荡的渔村小景,在这里,自然不是原生的自然,而是与人类亲善的人化自然,是人的精神的无机界,如费尔巴哈在《基督教的本质》中所说的,“是客观的‘我’”;《吴江夜泊即事戏题》却是通过自己与在职官僚的生活对比(一者清苦但闲适;一者有钱而仰人鼻息),表达作者对封建官场的鄙弃。
以上两组诗,体现着两位诗人各自创作的主导倾向,如果将其与其他代表性作品联系起来观照,便会使我们获得如下的认识:(1)从诗作体现的思想意义来看,王诗远离政治而关注自然,因情依景而发,体现人与自然的和谐;赵诗靠拢政治而关注社会人生,为时缘事而作,体现人与社会的冲突。(2)从诗作流露的感情格调来看, 王诗情怀淡远,表现的是封建士大夫的闲情逸致;赵诗心肠热切,反映的是儒家正统文人的郁愤不平之气。(3)从语言及表达特点来看,王诗清雅流利、 自然本色,珠圆玉润、天然音节,含蓄空灵、一任白描,因而十分耐人品味,作者大类一位旁观者,身影隐而不显;赵诗俗近质直,兼用典实,稍带人工痕迹,笔法既有敷陈,亦入议笔,作者介入其中,,胸次露而不藏。(4)从阅读效应上看,王诗重在虚处生情,意境鲜明, 诗味浓厚,足人讽咏赏玩,以至当人们还不明白为什么喜爱它时就喜爱上它了,然而倘无正确态度,也易将人导入消极静观一途;赵诗重在实处生根,意境缺乏,诗味相对淡薄,难以引发强烈的美感和无尽遐思,然而却能激发人们产生一种紧迫的、付诸行动的力量。总之,王诗体现出作者尚美(特指优美)的艺术倾向,易于于承平“盛世”流布,从长久的观点看,又具有超越时限的永恒性的特点,其价值在于审美意义;赵诗则体现出作者向善的艺术追求,易于于兵燹播迁之乱世取得共鸣,其价值在当时体现为社会批判意义,时过境迁则每为认识价值所取代。
二、诗论溯源
创作风格的形成,是与一定的文艺思想密切关联的,王、赵二人的诗歌创作,便是他们各自诗歌理论实践的结晶。
王渔洋是“神韵说”的倡导者,他在自己大量的论著中一贯标举“神韵”,以为诗家三味即在于此。什么是“神韵”呢?照字面理解,当指“风神”“韵致”之类的意思。王氏本人在《师友诗传续录》第28则中就是这样解释的。不过“风神”仍然是相当抽象的一个概念,要想把它落实得更加具体,恐怕王渔洋也讲不清楚。其实,“神韵”也好,“风神”也好,与前人所讲的“风骨”、“风力”、“神骨”、“气韵”等并无太大的差别,起码在内涵上有一部分重合,因此,我们将它们统同理解为“精神”“意趣”,大体不致离谱太远的。那么,怎样才能使自己的作品具备“神韵”呢?这有赖于孕育逼真传神的形象、创造情景交融具有空间美感的意境、含蓄吞吐的表达才能实现。其实,这也是前人早就注意到了的问题,诸如“意在言外”“境生象外”“意长笔短”“弦外之音”“意到笔不到”“虚实结合”等等,都是讲的这一问题。欧阳修“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六一诗话》)、梅圣俞“诗有内外意”(《续金针诗格》)、王夫之“以显函微”(《诗广传》卷五论《周颂·清庙》),则是人们为说明这一问题而常常征引的名言。尽管如此,王渔洋拈出“神韵”二字仍然是很有意义的,因为它较之“气韵”“风骨”“风力”“神骨”等说法,对诗的本质特征概括得更准确、更鲜明、更富有美学意味,而且直接开启了后来王国维的“境界”诗论。神韵说很快为清初的诗坛所接受,以至于形成了赵执信所说的很有势力的宗派门户,便是它生命力的事实上的证明。
渔洋神韵说本诸严沧浪(羽)、司空表圣(图)。沧浪以禅喻诗、主张妙语,他所说的“羚羊挂角,无迹可求,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王氏赞谓先得我心。对于司空表圣“美在酸咸之外”“不著一字尽得风流”,渔洋更是佩服,因而力宗其说,在编选他的《唐贤三味集》时,即据以为准的“录其尤隽永超旨者”。应当说这是极有见地的,因为它抓住了诗歌艺术最根本的特征——美,意境之美。有人说:诗人只服从感情的命令。实际上这话说得并不妥当,黑格尔讲:“艺术作品之所以为艺术作品,既然不在它一般能引起情感(因为这个目的是艺术作品和雄辩术、历史写作、宗教宣扬等等所共同的,没有什么区别),而在它是美的。”(《美学》卷一第42页)人们之所以需要科学,是出于求真的本性;人们之所以需要道德,是出于向善的本性;人们之所以需要艺术,是出于尚美的本性,因为艺术能向人们提供高级的审美享受。在神韵美的创造上,渔洋、沧浪、表圣共同的特点是强调“出虚”“用无”,因为神韵意境的产生关键在于虚化部分,必须充分发挥抒情诗虚写部分(志、意、情、理、趣等)之主导作用,而不可拘泥于具体事物描写的实在部分,否则就谈不到什么神韵或意境了。
如果我们的溯源就此止步,那还是远远不够的,因为沧浪、表圣的观点也是渊源有自,并非凭空从天上掉下来的。严氏与司空的观点来源于道、释两家的哲学思想。中国道家的世界观是一种比较典型的自然天道观,它认为宇宙万物的本源在于一种至高无上的自然之“道”,至于各种各样的事物——“器”,只不过是“道”的种种具体表现形态罢了。“道”是虚无的、形而上的;“器”是实有的、形而下的。然而,虚无的“道”又无时无处不存在于各种实有的“器”中,庄周说的“道在屎溺”便是这层意思。基于此,便产生了道家一系列的审美观点:“道”不可言,“言不尽意”;崇尚自然,否定人工;“物我混同”“天人合一”。(参见《齐物论》)中国古典美学史上的形神、意象、言意、虚实、有无、风骨、气韵、情景、韵味、意境、神韵等等范畴与概念,无一不是由此派生或引发出来的。至于释家之影响文学理论,乃是东汉以后的事情:由天竺东渐的释教,出于在华传播的需要,特别是由于内在宗旨的相契相通(“空寂”与“虚无”、“明心见性”与“修心炼性”,同属于消极出世的人生态度),遂与道家之变种——玄学结合起来,以发挥其精神渗透作用。至后来禅宗所谓佛理至高、不可言喻,“不立文字”只靠心解妙语,益发见出释道合流的倾向。司空图是个虔诚的佛教徒,严沧浪以禅喻诗,王渔洋则声称“诗禅一致,等无差别”,这就向我们提示了“神韵说”更深沉的思想根源所在。
接下来谈读赵执信了。赵执信的诗论集中地见之于《谈龙录》,此外还散见于一些论诗诗。如《题程松皋舍人诗卷》、《七夕雨饮松皋舍人分韵得九佳》、《深秋偶作》、《题大木所寄晴川集后》、《论诗二绝句》等。其。诗歌理论,源自明末清初的二位诗人兼文艺评论家——昆山吴桥(修龄)、常熟冯班(定远),主要观点有:(1)诗以言志;(2)诗中须有人在,即要让读者能够想见出作者的心性、行藏、 学问、修养等方面的情形来;(3)诗之外要有事在, “事”即“道”“理”,意指不能失去教化作用;(4)文以“意”为主,语言为役, 主强而役弱,则无令不从。(参见《清史·赵执信传》)赵执信的诗歌创作正是他的这些诗论主张的实践与体现,其于草野涂炭、生民疾苦三致意焉,显示出强烈的现实批判精神。赵执信的诗论主张显然是对传统的儒家诗教理论的继承与发扬。儒家以经世为宗,提倡存心养性,从孔夫子的“苛政猛于虎”“仁者爱人”、孟夫子的“民贵君轻”,中经汉代大儒综理,至于杜工部的“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白香山的“以天下心为心”“以百姓欲为欲”……一脉相传,代表了正统儒家积极入世的政治思想与人生态度。与此相联系的便是对文学艺术社会政治功利性的强调,例如“诗言志”,“文以载道”,“为时而著”“为事而作”,“唯歌生民病”,“不关风化体,纵好也枉然”,“实录”“写真”,“道胜文至”……全是搞的“政治第一”,要求文学艺术自觉而主动的向政治靠拢,以充分发挥“兴观群怨”补察时政的作用,以达到“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利国利民的政治目的。
由上所述不难看出,在文艺理论上,儒家的观点与道、释两家的观点是有着重大区别的,在儒家那里,“善”是标准,“善”是落脚点;而在释、道两家这里,“美”是原则,“美”本身即是目的。儒家的文艺观点侧重反映的是文艺的外部规律,诸如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文艺与现实的关系,文艺与时代变迁的关系等等:释、道两家的文艺观点侧重反映的是文艺自身的内部规律,诸如构思、创作、风格特点等等。儒家与释、道二家的文艺理论之间,具有一种内在的互补性,过分地抬高或排斥任何一方都将失之于片面而给创作带来不利影响。
三、风格即其人
按照封建时代文人人生的常规逻辑,凡政治上的得意者,一般宗儒,其诗文创作相应地便注重教化实用,如王渔洋那样位望通显之人,似乎不当写出那等冲淡清远之作;而政治上的失意者,一般说来,其思想感情每常向道向佛,如赵执信那样被排挤出统治者圈子、政治上绝望的人,似乎不当写出那等执着于社会人生的诗作。为了弄清这个问题,我们有必要对二人的生平轨迹作一番追踪考察。
王渔洋生于明崇祯七年(1634),卒于清康熙五十年(1711)。其生活时代恰值明清易代之际,即“满州”这一少数民族凭借军事实力取代汉人政权,建立起以满族贵族为主体的满汉地主阶级的联合专政,并使之逐步巩固的时期。这一时期总的特点,一方面是社会矛盾的复杂化(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统治者内部的矛盾错综交织),一方面是封建专制主义的强化。为了在思想文化方面加强控制,统治者对汉族知识分子采取了高压与怀柔相结合的政策:倡孔孟、抬理学、开科举;禁“淫词”、毁图书、大兴文字狱。怀柔使其不致与统治者产生二心,高压使其不敢与统治者产生二心。王渔洋正是具有这种双重心态的文人的典型。他出身于明季官宦世家(祖辈有数人死于国难)自幼受到良好的文化教养与仕进熏染;弱冠登第,官职直做到刑部尚书。他深得顺、康二帝的赏识、信任和优待,曾先后四次被任命为考官,两次奉使远行祭告山海之神(南海、西岳),多次接受御赐:赐食、赐宴、赐墨宝、赐匾额(“带经堂”、“信古斋”即康熙手书),他的祖、父、母、妻三番得到诰封,致令他“感激国恩,不禁泫然”,表示要子孙辈永志不忘(《居易录》卷二十)。他为官公正廉洁,处事谨慎得体,洵属那个时代难得的循吏。然而,即使如此,在那种特定的政治大气候中,在那种险恶的官场旋涡中,王渔洋仍然被罢免、降级处分过三次。就在他第一次被免官的前一年,与他同在京城为官的长兄士禄先他而获罪,原因是典试河南乡试时,试题语句被指责为有疵,经吏部审查移送刑部,终致削职。王渔洋艺术修养甚高,加之性情谦和、奖掖后进,故而交道颇广、友朋众多。在这些文朋诗友中,许多他认为极有才气的人,都因文被祸,例如洪升、孔尚任、查慎行、朱彝尊等遭遇都是很不美妙的。毫无疑问,这等于一次又一次地给他敲响了警钟。那么,作为既“识时务”又具文学眼光的王渔洋会选择什么艺术道路呢?空洞无物的颂圣应酬之作,前朝已有台阁体失败的覆辙为殷鉴;规模汉唐的前后七子之剽窃、“公安派”末流之俚俗伧陋,俱不能挽救诗歌之穷;感时伤世忠愤怨刺之词,一者不能为(缺乏生活),二者不愿为(审美观点与李白、杜甫本不相谋),三者更不敢为。于是,既能展露才情,又不致招灾引祸的“神韵”一途,自然便成为他的“必由之路”。《香祖笔记》卷一有段话流露了他的心曲:“释氏言羚羊挂角无迹可求,古言云羚羊无些子气味,虎豹再寻他不著,九渊潜龙、千仞翔凤乎?此是前言注脚,不独喻诗,亦可为士君子居身涉世之法。”据此看来,从处世态度方面考察,王渔洋吹鼓神韵说,实质上是一种“莫谈国事”的逃避现实而隐身于朝廷的手段,它反映了汉族士大夫中的一种卑怯心理,是适应(起码不会妨碍)新朝统治秩序的需要而产生的一种颇具缓冲效应的理论学说。
再读赵执信。赵执信生于康熙元年(1662)卒于乾隆九年(1744),一生是在所谓“康乾盛世”度过的,于渔洋氏称伯岳父。他也是一位早慧的诗人,十七岁中举,十八岁中进士,应鸿博试得官在京与修明史,并且较顺利地得到提拔。公元1689年,因在佟皇后病逝的“国恤”期间宴饮与观看洪升所著《长生殿》传奇演出,为人弹劾,以“大不敬”的罪名被革职罢官。其时其事尚可回旋,赵执信不肯夤缘,独任其咎,维护友人很多。经过这场风波,赵执信对官场的险恶、龌龊有了清醒的认识,他决心退隐,不再与世俗同流合污。从此他便返还乡里并开始了多次漫游活动。他东至大海,西抵嵩岳,南到广州,北达天津。漫游使他开阔了视野、认识了社会、接近了人民。他写下大量同情劳动人民疾苦、揭露统治者罪恶的现实主义诗篇,如《道傍碑》、《大堤叹》、《碧波行》、《后纪蝗》、《甿入城行》等, 都是悲愤激烈的放歌,具有一种痛快淋漓的气势。特别是《甿城行》一诗, 简直是歌颂农民拿起锄头来造贪官污吏的反,在当时那种历史条件下,这是颇需一点胆量的。赵执信生性傲岸,耻于依人,在矛盾错综的统治者圈子里,遭受打击是必然的。然而他不入消极颓废的途路,而是屈其身不屈其道,注重名节、粪土富贵,关心民生痛痒,敢讲真话,敢于揭开封建“盛世”的画皮,这是十分可贡的品格,是王渔洋远远弗如的。所以,倘从诗作的思想内容方面考察,王诗可说是“盛世”外表假相的反映,赵诗才是“盛世”内部实质的揭示。
王、赵二人诗风的差异,除了习学、淘染不同使然外,更与在那个时代里,二人不同的生活道路、人生态度、道德人格、气质禀性等有着密切关系。这里用得着人们常说的那句话了:风格即其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