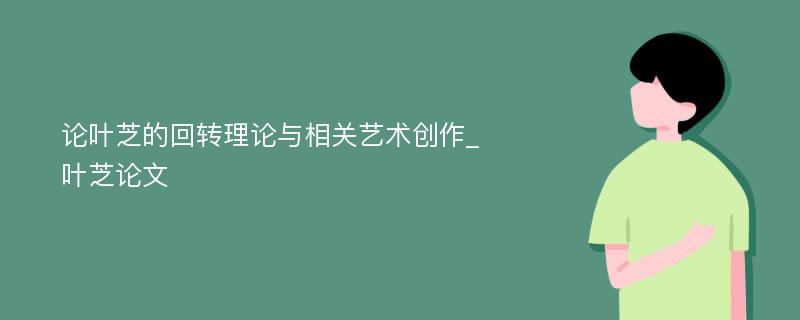
论叶芝的GYRE理论及相关的艺术创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叶芝论文,艺术创作论文,理论论文,GYRE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英语文学界,W.B.叶芝是与庞德和T.S.艾略特齐名的现代诗巨匠,但由于他的诗歌涉及到他高深晦涩的历史观、社会观、艺术观和哲学观等,国内鲜有人对他的诗歌创作,尤其是其晚期的哲理诗进行研究和评论。因此,为其众多的晦涩难懂的哲理诗寻找出通向理解大门的路径是十分必要的。
纵观叶芝玄奥的历史观、社会观、艺术观和哲学观,不难发现其核心是二项对立,而他的二项对立理论又可以通过他的关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Gyre理论得到充分展示。他的Gyre理论不仅可以说明他的历史观,而且还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他的社会观和艺术观,更好地理解他的诗作主题。
一、叶芝的GYRE理论
格瑞格里夫人( Lady Gregory) 曾暗示,“叶芝的《幻象》( A Vision) 中的哲学系统使叶芝的诗作的意义模糊、复杂”。实际上,“《幻象》以及叶芝的20世纪20和30年代的诗作构成了一种启示,一种由现代主义文学奇特地构成的启示”,“一种对无法辨识的、无以言表的事物的昭示”[1]。而《幻象》中的主体意象是Gyre,即社会和历史发展的漩涡状缩影。所以,研究其Gyre理论的内涵不仅是理解其晚期诗作的关键,也是理解其整个诗歌体系的有益参照。
在其重要诗作《幻象》中,叶芝形象地将历史的发展历程比作由两个以相反方向旋转的正圆锥体组成的漩涡体,一个正圆锥体的顶点恰好在另一个正圆锥体的底面的圆心上。因此两个圆锥体的中轴线是共同的。每时每刻这两个圆锥体都在绕着共同的中轴线作互为反方向的旋转,也就是说,历史上的每一刻都是这两个互为反方向旋转的圆锥的一个横切面,都包含两个互为反作用、互相穿透的运动。在这种运动中,一个圆锥体的横切面正在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越旋越大,而另一个的横切面则越旋越小。两个圆锥体共同组成一个Gyre。当其中一个圆锥体的横切面旋转缩小至一个点时,整个漩涡体则改变运动方向,即那个横切面为一点的圆锥体的横切面开始越旋越大,另一个则相反。每当其中一个圆锥体的横切面旋转缩小成一点而另一个圆锥体横切面旋转扩大到最大值时,即漩涡开始改变运动方向时,历史上便会出现一次大混乱。历史上这种混乱出现的周期约为两千年。
在整个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中,两个呈圆锥状的螺旋体相互交错,这就意味着在每一个历史时期,总有一个法则处于主导地位,同时另一个相反的法则起着对抗和制约作用。例如,主观总受客观的制约,客观也会受主观的制约。随着历史的发展,处于主导地位的法则总会让位于处于从属地位的相反的法则。在叶芝的诗作中,这种历史法则的转变被形象地通过关于海伦和基督的出世的传说所暗示。丽达被化成天鹅形状的宙斯诱奸而生下海伦,而圣母马丽亚则被化为鸽子形状的上帝昭示而生下基督。给人类带来混乱和灾难的海伦与给人类带来福祉和救赎的基督构成鲜明的二项对立。
与他的Gyre理论相呼应的是叶芝的关于历史发展的月亏月盈观。叶芝还把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比作是月亏月盈的变化。月亮的亏盈是有规律、有周期的,人类历史的发展变化同样是有规律、有周期性的。在人类历史的月盈期,即从月亏到月盈这个时期内,人类的主观法则处于主导地位,人类致力于发展自己的思想,致力于用自己的行为改变客观世界;而在人类历史的月亏期,即从月盈到月亏的时期内,人类的客观法则处于主导地位,人类屈从于客观世界,为客观世界所奴役,人类被物化和异化。我们的现代主义文学即是人类被物化和异化的产物。但是,正如叶芝的Gyre旋转至一个圆锥体切面缩小为一个点时漩涡体要改变运动方向一样,当人类历史发展到月亏至极时,即没有月亮的那一刻,人类历史又从客观法则占主导地位向主观法则占主导地位的方向发展。无论是人类历史还是人类个人的生活,均是由互为对立的两个漩涡状圆锥体构成,一个漩涡代表着理智、知识和客观,另一个代表着情感、直觉和主观,无论是个人生活的某一刻,还是人类历史的某个时期,两个漩涡所代表的因素总是处于对抗状态,一方处于主导地位时,另一方则处于反主导地位,而且一旦二者的对抗力量达到平衡,人类的艺术创造便达到黄金时期。公元前5世纪的希腊和公元六七世纪的拜占庭时期均是这种主观和客观、理智与情感达到平衡后的文化繁荣的黄金时期。在《驶向拜占庭》( Sailing to Byzantium) 一诗中,叶芝把令人失望的现代爱尔兰和拜占庭相对比,并称赞拜占庭时期的艺术是一种“永不衰老的知识的纪念碑”和“永恒的艺术”。而且,在他对《幻象》的评论中,他认为拜占庭时期乃是人类历史上分别代表主观和客观的两个漩涡达到对抗平衡的最佳时期,这个黄金时期或许在历史上既是空前的,又是绝后的,因为在拜占庭文化早期,“宗教生活、艺术生活和现实生活是统一的,建筑学家和工匠表达的既是大众的品味,也是少数人的品味。画家、马赛克工匠、金银匠、宗教典籍的插图画师几乎都是不受个人感情影响的,或许几乎从没有个人设计意识,他们全身心地投入到他们的主题和整个民族的想像之中。”[2]
二、Gyre理论中的社会观
叶芝认为,在历史的漩涡中,社会在两个朝着相反方向旋转的漩涡中不断地变迁,由兴旺走向衰亡,再由衰亡走向兴旺;在历史的大漩涡中,个人的命运如同浪中浮萍,个人的努力微不足道,甚至努力的初衷和结果恰恰相反;人,就如同一个演员,口中说着无名作者的台词,做着无名导演规定的动作。
在题为《超自然之歌》( Supernatural Songs) 的组诗中,叶芝表达了他对现代社会命运的深切担忧,在第八首诗《他们因何而来》( Whence Had They Come) 中,叶芝对人类深信不疑的一些观念也提出了质疑。深陷于爱河和性爱欢愉的恋人总是情不自禁地说要爱对方“到永远的永远”,但是当他(她)们从情感的热潮中清醒过来时,他们甚至不知道那个说出“爱你到永远的永远”的声音究竟属于谁。人类的其他行为也大抵如此。外向的“被感情激发冲动的人唱出/他从未想到过的词句”,而内向的人则从不知“什么样的剧作家……/什么样的大师”主宰着他的痛苦。个人绝不是他行为和痛苦的主宰,他的命运掌握在一种超自然的力量的手中。人类总是忙忙碌碌、不辞辛劳地朝着自己设定的目标努力,但他们却很难发觉,他们努力的结果却总是事与愿违。
具有杰出军事才干、似乎无所不能的拿破仑横扫欧洲,试图统一欧洲,建立强大的法兰西帝国,但结果却是让他的老对手英国钻了空子,使英国成了世界的霸主。这从个人的角度看似乎是事与愿违,但从历史的角度而言却是一种逻辑的必然。正如叶芝的Gyre理论所说明的那样,对抗中的二项中的任何一项发展到极至的那一刻也就是它开始衰亡的那一刻。叶芝在他的组诗《超自然之歌》中就援引了历史上的数个与拿破仑失败相似的例子。罗马帝国强盛一时,最后却消失在被称为野蛮人的日耳曼人手中;而法国的查理曼大帝,其祖先恰恰是摧毁了罗马帝国的“野蛮人”,但却在公元八世纪将分裂的欧洲数个小国统一为一个大帝国,为现代的欧洲版图奠定了基础。尽管此组诗写于1934年,叶芝在其中却准确地预言了当时欧洲社会的走向。他在诗中暗示欧洲的下一个拿破仑就是希特勒。希特勒与查理曼大帝和拿破仑一样,都是“野蛮人”的后裔,都具有统一欧洲的野心。因此,他要带给现代文明的也必将是一场混乱。当然,“混乱”对于处于日趋腐朽的现代文明之中的人类来说未必是一件坏事,它至少可以说是人类第二次被救赎的先兆。现代文明的旧秩序需要由全新的新秩序所代替。
在《青铜头像》( A Bronze Head) 中,叶芝表达了他对现代社会的看法,他认为现代社会乃是一个“处于衰落和颓败期的邪恶世界”,只有“大屠杀”才能除旧存新,建立新的社会秩序。现代社会的混乱也好,战乱也好,都只是一种新秩序建立的前奏,都是耶稣第二次圣临的序幕,这正如英雄或圣人的母亲的怀胎之苦恰恰是英雄或圣人降临的先决条件一样。
摧毁坚不可摧的罗马之手
和鞭源自何处?
当改天换地的查理曼坐胎成形
怎样的神圣戏剧在他母腹中形成?
实际上,早在他的中期诗歌《第二次圣临》( The Second Coming) 中,叶芝就预言:20世纪是失控的猎鹰,在历史的漩涡中盘旋,一点也不听驯鹰者的呼喊;未来要到这个世界上建立新秩序的,是那头在荒漠中沉睡了数千年的狮身人面的怪物。它一旦苏醒过来,倘若人性复苏,就会建立一种和平博爱的美好秩序;倘若兽性大发,就会为法西斯力量创造生存的合适土壤,助纣为虐,使世界变成人间地狱。
总的来说,叶芝对未来社会的看法还不算太悲观。他在《革命后的爱尔兰》( Ireland After the Revolution) 中指出,“某些悲剧性的巨变会改变欧洲和人们的观念”,从而使一种新秩序的建立成为可能,这种新秩序很有可能使文明进入一种荷马时期式的和谐状态。
三、Gyre理论中的艺术观
在他的历史漩涡理论的框架内,叶芝发展了他的艺术观,即酒神规则和太阳神规则的二项对立理论。我们知道,叶芝的历史漩涡理论的实质乃是二项对立以及对立项在对立中的消长。他的艺术观实际上是他的历史漩涡理论和尼采的历史观的综合产物。尼采对叶芝的影响在叶芝1903年的信件中可见一斑:“我经常感到人的灵魂主要有两个倾向。一种是要超越形式,另一种则是要创造形式。尼采将这二者分别称作酒神式的和阿波罗式的。”
在这里“形式( Form) ”既代表艺术领域的秩序,也指社会中的秩序。“酒神规则”( The Dionysian Principle) 因希腊酒神Dionysus而得名,代表一种无政府主义力量,它同时具有破坏力和创造力,是一种本能的、情感的、潜意识层面的力量,与人的本性和种族记忆密不可分。而“太阳神规则”( Apollonian Principle) 则因希腊太阳神Apollo的名字而得名,代表一种秩序、理性的力量,是诗和口才的化身,是由意识控制的规则,具有秩序化、和谐化的倾向。在艺术领域,太阳神规则可将经验和初始材料转化成美、和谐和形式,使初始经验升华为新生的完整系统观点。在社会领域,太阳神规则则将人类情感的混乱状态控制在理性的框架之内。
在历史的某些短暂时期,太阳神规则和酒神规则可以达到完美的平衡。在这样的时期内,大量的由对立的二项平衡产生的伟大艺术品层出不穷。在尼采眼里,这种和谐时期的典型是公元前五世纪的希腊和拜占庭早期。在历史漩涡的大框架内,这种平衡和谐很快就会为历史的两个漩涡的反向旋转所打破,或是酒神规则占上风,或是太阳神规则占上风,因此艺术就会颓废或僵化。酒神规则占上风会导致艺术的颓废和混乱,太阳神规则占上风则会导致艺术僵化和教条化。当以情感为主的酒神规则发展到极至,艺术的各种规则和原型均要消解,此时历史的漩涡则反向运转,以理性为主的太阳神规则就会逐步增强,而酒神规则则趋于减弱。
四、与Gyre理论相关的主要象征
叶芝认为,象征是诗歌内涵的重要基石。“象征实际上是惟一可能的表达某些抽象的实质的方式,是可映照出精神火花的明灯。”[3] (P22)文学批评家凯恩斯·克莱格( Cairns Craig) 指出,要理解叶芝诗歌的内涵,关键是“准确地追寻那些被强加给了许多意义的东西的具体的、单一的意义”[4]。因此,要理解叶芝后期的诗作,除了必须了解他的关于历史、社会发展的Gyre理论外,理解一些与Gyre相关的象征的准确意义也十分重要。
1.猎鹰、鸽子和天鹅
这一组象征与叶芝的历史漩涡理论紧密相关。在《第二次圣临》中,猎鹰是一种挣脱了人类理性控制的暴力的象征,它在历史的漩涡中盘旋,伺机将自己的暴虐施加在人类的命运之中。当然,根据叶芝本人的一贯看法,任何象征都不可能局限于某一种简单的解释中。[3] (P58)从历史的角度而言,猎鹰还可代表一种自由和力量之美。从理性的角度而言,猎鹰似乎是邪恶的暴力;从浪漫的角度而言,它代表一种自由的优雅,这与叶芝的关于历史漩涡的二项对立不谋而合。
和平鸽在《幻象》及叶芝的一些重要诗作中通常与人类救赎的希望密切相联。根据《圣经》传说,上帝以鸽子的幻象出现,使圣母玛丽亚受孕,从而生下耶稣。耶稣替人类洗清罪孽,并给人类留下他再次圣临的希望。而天鹅则与人类文明的潜在毁灭相关。根据希腊神话传说,宙斯化作天鹅的形状诱奸了丽达,使她受孕生下了两个蛋,其中的一个蛋就孵出了海伦。海伦引发了特洛伊战争,使高度文明的特洛伊被野蛮的希腊人毁灭。因此,在叶芝的诗作中,和平鸽和天鹅往往构成二项对立,一个是人类被救赎的先兆,一个是人类文明行将毁灭的先兆,但二者都预示着历史漩涡的逆转。
当然,天鹅还有其他的寓意,在叶芝的某些诗歌中,天鹅还代表孤独的灵魂。在他的《1919》( Nineteen Hundred and Nineteen) 中有这样的诗句:
一些道德家和神话诗人
将孤寂的灵魂比作天鹅
实际上,在叶芝的笔下,天鹅独立超然的特性如此突出,以至于孤寂的灵魂反而成了天鹅的象征。
2.房子、塔和面具
在叶芝笔下,盎格鲁—爱尔兰式的农家房舍是常出现的象征,它通常代表一种历史遗产。它由有权有势的主人雇佣建筑师和艺术家所建,主人试图通过建造它来享受日思夜想的幸福,但是,其结果是,这种房子却成了一种文化的纪念碑,这种文化源于暴力,但却永远不被暴力所玷污和占有。
塔是叶芝自创的神话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盘旋的古老楼梯”在他的诗作《自我和灵魂的对话》( A Dialogue Of Self And Soul) 中象征着自我从历史中获取知识和经验的必由之路。同时,它也与 Gyre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有螺旋上升的特点,与历史发展的轨迹相吻合。塔本身又是富于哲理思维的、冷眼看世界的叶芝本人的自况象征。在《内战时期的冥想》( Meditations in Times of Civil War) 中,他站在塔的城垛上,放眼看世界,看到的全是“仇恨、魇足和即将来临的空虚的鬼影”。在《月期》( The Phase of the Moon) 中,日渐破损的塔顶成了半死的时代的象征。当然,在许多与爱尔兰历史相关的诗篇中,塔则成了爱尔兰遭受异族血腥入侵和压迫的纪念碑,甚至是每一个政权的象征,因为“每一个现代国度”均建立在血腥之上,“政权/就像所有沾有血污的东西一样/是活人的财产”。
面具也是叶芝关于艺术创作的理论中的重要象征。叶芝认为,要成为一个伟大的诗人,首先应该放弃个性中的某些琐碎的因素。他必须戴上面具,将自己的个性隐藏起来,装扮成他本来不具有的“反自我形象”( anti-self) 。戴上这个面具,他就可以扮演与正常自我相反的一些角色,这个面具实际上就成了诗人或英雄的内在自然情感的对立项,它使诗人或英雄具有了普遍的悲剧色彩,使诗人的诗作也具有普遍意义。戴上这个面具,莎士比亚就成了李尔王、罗密欧、奥赛罗或哈姆雷特,他所爱的女人也不再是那位“黑女士( Dark Lady) ”,而是朱丽叶、苔丝特莫娜和奥菲丽娅等等。
3.特洛伊、拜占庭、爱尔兰、英格兰
特洛伊主要是被野蛮人摧毁文明的象征,而拜占庭则是在历史的进程中对立的二项达到平衡时文化繁荣的象征。因为在前面的论述中已经涉及到了特洛伊与拜占庭,所以在此不再赘述。
爱尔兰和英格兰在叶芝笔下是另一组二项对立。爱尔兰虽被英格兰奴役,但她融合为一体的团体却在爱尔兰的西部存留,只有这种半传说式的纯朴善良的团体才可以被称作是“民族”,而英格兰的那些只认金钱没有人情味的、建立在一个阶级对抗另一个阶级的人群则只能被称作“群氓”。爱尔兰代表着“由共同想像力凝聚在一起的、因在共同生活中产生的诗歌和故事和因依旧可以刺激人们的心灵和激发想像行为的充满伟大情感的过去而凝聚在一起的民族”,而英格兰则代表着拥有“都市曲调”和“学院品味”而没有任何古老传统的“群氓”国度。[3] (P129),一旦爱尔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脱离了英格兰的统治,它将步入一种拜占庭时代,全面复兴自己的民族文化。
综上所述,叶芝的关于历史发展的Gyre理论是理解其晚期诗作的关键之一,它不仅涉及叶芝晚期创作的社会观和艺术观,也与其晚期诗作的许多重要象征和意象紧密相连,是理解其晚期诗作的关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