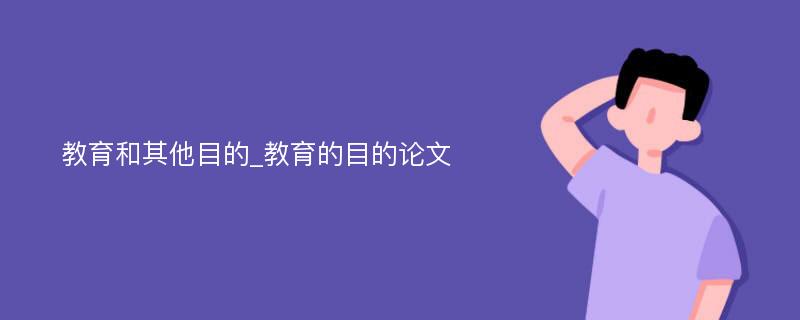
教育的目的及其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目的论文,及其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教育的目的
教育应该给人什么?教育的目的——不仅仅是大学教育,而是教育可以一以贯之的目的——是什么呢?如果说,教育的责任是培养人,随之而来的问题是,我们的教育所追求的是培养什么样的人?有多少人,经过了小学、中学、大学甚至取得了更高的学位以后,在人生的旅途上仍茫然不知自己应走向何方,不知在这茫茫宇宙间,人又是怎样的一种存在。这些终极问题不是时隐时显地叩问着我们的心灵么?
在我看来,教育就是启发每一个人对“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的问题做出自己的回答,教育的目的就是启发人不断地去“认识你自己”——古希腊巴特龙神庙的神谕,成为多少西方圣哲探讨人生的起点。
哲学、宗教、科学、艺术都在各自的领域探索着它的答案。而对于每一个人来说,这是人生的终极问题,逃避不了。
天地鸿蒙,宇宙何时诞生?人起源于何时何地?于是有“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张若虚:《春江花月夜》)的叩问天宇;意识到每一个人都是茫茫天地间、浩淼人类长河里一个有限的、独立的、孤独的个体,了解到每一个生灵都经历着生命千回百转的幸福与悲哀,于是有陈子昂登幽州台的慨叹: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每当这首诗蓦然闪现在脑际,我眼前总是浮现出一个背负行李,在荒凉苍茫的天地间踽踽独行的人的形象——这个人不仅是你,也不仅是我,而是每一个人的生之际遇——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独立的世界,背负着对自己生命的责任,这责任是任何其他人都无法代替的。于是,一种对旷世的寂寞和根本孤境的感触也许就会在某一个未曾预约的时候突然袭上心间,如同陈子昂不自禁的怆然之泪。人多么像莎士比亚笔下那个忧郁的因理性而徘徊的王子哈姆雷特,在生命的纷纭歧路上一次一次做着艰难的选择——to be or not to be?to be or not to be?(“生存还是死亡,这是个问题啊。”)每一个人需要追问的,岂止生死问题。我,连同在我身边匆匆走过的人,不都在人生旅途大大小小的选择来临时,追问自己:我在往何处去?我应该如何选择?——to be or not to be?在时间织就的经线上,我们用存在的勇气,以自己的所思所为为纬,勾画着人生的坐标,一个一个坐标连接起来,便成为自己生命历程的屐痕点点,在这种过程中,人永远不会成为一件已经完成的定型作品——除了死亡这个终结者雕塑家刻上最后一道印记,人只是在不断"to be"——成为——他(她)自己,而使自己成为什么样的人,是每个人的自由选择以及基于选择的责任。
从这种意义而言,我想,教师应该成为学生的一面镜子,在启发学生追求真善美的理想的过程中,鼓励学生通过反思不断认识自我,养成独立思考与独立行动的能力,由此确定自己的生活道路,并担负起对自身与社会的责任。我以为,教育的目的即在于培养自我认识、自我塑造、自我负责并具有社会责任感的和谐发展的人。如果将孩子们比作卫星,那么,成功的教育就如同运载火箭,让孩子们在星箭分离后自主地在求知的轨道上运行。
自由的精神
在我读小学与初中的时代,家庭的学校对孩子的要求往往是“做一个好孩子”:父母的好孩子、老师的乖学生。那时,在我们眼里,老师说的话、书本上印刷的字句,都是亘古不移的真理,我们将之记诵在心,仿佛真理在握,从来没有对它们产生过任何怀疑——直到我在十四岁那年遇到两位启迪我用自己头脑思考的老师。
十四岁,正是对人生、对社会充满了疑问、寻索答案的时候,而那时的中国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对于经历数度劫波的中国人而言,那是一个令人神往的年代:思想文化界开始文化修复的努力,人们以道德、良心与理性反思着文化和社会问题。那时,正在学医的我和我的同龄人正处于开始自觉关注社会问题并希望由自己决定生活方式、试图拒绝家长和“大人”干预的时期。两位老师启迪我独立思考,鼓励我坚持自己信仰的真理。那时,我们常一同讨论鲁迅,探讨人文主义的精神,思考我们关注的各种社会问题,我为自己所坚持的理想辩护,只服从于让我认同的思考,从不因为他们的老师身份而自甘“屈服”,我们一起度过了许多心灵充实而快乐的日子。当我在纷纭的世事中,用自己的头脑思考,用自己的心灵体验,用自己的理想支持人格与尊严时,我欣喜而又欣慰地发现,思考使我感到有力了。就在这种独立思考中,我一步一步寻找着自己人生的道路。现在的我常说,如果中国的很多问题要回到“五四”时期重新思考,那么,我的所有选择、思索就要回到十四、五岁的历程的起点。
我曾问其中一位老师:你是在塑造我吗?他回答:“即使是塑造,也只能体现自由的涵义。”十余年过去了,这句话我一直忘不了。正是对生活中遇见的优秀老师的感恩之情,使我希望将生活给予我的惠泽转赠给我身边的人和比我年轻的一代一代,所以在医学与教育学之间,我选择了后者作为毕生投入的事业。对教育中自由精神的思索也自此开始。
提到教育与学术自由,就不能不令人怀念蔡元培先生对北京大学的改造。在“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的未名湖畔,既有陈独秀、李大钊、胡适、周作人等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又有背后拖着长辫的辜鸿铭等传统辩护士,百家争鸣的学术氛围蔚然成风。我以为,这种坦荡、开放的胸襟不仅给老师以讲授的学术自由,给学生以选择的空间,更是对学生独立思索与判断能力的培养与信任,学校与教师相信学生可以通过独立的思考,在尽可能多的思想交锋中,了解认识世界有多种视野,从而祛除偏狭的观念,并最终形成自己所认同的观点与信念。
具有自由精神的教育必是尊重个体差异并相信每一个人都有发展潜能的教育。我曾听到一位老师提到体罚的必要时说:“我也爱孩子,但对有些学生,你就是恨铁不成钢,不能不打。”在我看来,每个人的资质不同,发展的方向也会有所差异,如果你的学生可以成为一块好铁,为什么你一定要逼他去做一块劣质钢呢?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其实,己所欲,即当施于人吗?整齐划一的思想无疑将以“削足适履”为强制方法。现实中,父母、教师以自己的意愿强加于孩子,不知已造成多少悲剧。我以为,己之不欲与所欲,均无权“施于人”,涉及到他人的一切,都需要以尊重他人意愿为基本态度,这是明了自由精神的父母对待孩子的基本态度,也是明了自由精神的教育者对待学生的基本态度。在尊重学生个性及潜质的基础上,且让我们相信学生将有他们的自我塑造。正如同森林“鸟语花香”之美,美就美在“每一只鸟都歌唱,而不只是百灵才歌唱;每一朵花都开放,而不只是牡丹才开放”。所以,对于你的学生——
如果他(她)是一只鸟,就让他(她)尽情歌唱;
如果她(他)是一朵花,就让她(他)尽力实现花的芬芳。
科技教育与人文精神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人文精神的滑落成为中国文化界颇为关注的问题。当科学及其物化形式的技术越来越显现其认识和改造物质世界的威力并携带着丰厚的物质利益时,中国的文科教育愈益显现出“门庭冷落”的尴尬景象,学习哲学、文学的大学学子们在课堂上问老师:毕业后找工作难,工资低,学习这些究竟有什么用?
文化、教育界探询着融合人文与科学技术教育的途径。如果说,这一次,我们是在为人文教育寻求价值的话,那么,回顾历史,往昔的图景很有意思,就在百年以前,人们还曾孜孜以求,为科学与技术教育正名,以求得与人文教育同等的地位。
曾几何时,人文精神曾被视为教育的灵魂,在古希腊的自由教育中,由贵族子弟与自由公民享用。这种教育被认为与精神性、理性和高尚相关联,通过非功利的科目如音乐、哲学、文法、修辞等,训练学生完善身体和心灵,解放精神和思想;而接受职业与技术训练的是奴隶与工匠,他们的活动被视为物质的与低级卑贱的。在古代中国,亦一直存有“道器”之分,所谓“道成而上,器成而下”;又有“劳心劳力”之别,所谓“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都试图在人文与技术之间,划出一条泾渭分明的分界线。人文与科技教育的分裂最初就是这样以技术教育受到轻视为特征的。
二十世纪颇具影响的美国哲学家与教育家杜威认为这种区分阻碍了人道和自由的发展,故而毕生致力于打破这种反映在教育中的政治、经济的不平等及精神与物质分裂的二元论。在他生活的年代,科学已在众多领域取得进展,而在文化、教育界,科学与技术教育仍然不能取得与人文学科同样的地位。他提倡广泛开展技术教育,在实验学校里开设商店、车间,让孩子们在做中学,倡导从生活中学习,将学校作为一个简化的雏形社会,孩子们在这样的环境中学习的一切,将有助于他(她)们自身的自由发展,成为能有效促进民主的社会公民和能承担责任的家庭成员。杜威的这些常被视为“标新立异”的激烈反传统思想与行为,实际上只是他试图在学生学习的内容与其社会生活之间建立联系的一个尝试,使学校不再是与生活隔离的场所,而学生所学习的不再是脱离人生的高高在上的内容,藉此打破人文教育与科学技术教育的鸿沟,打破由这种区分带来的不平等的阶级之别。
随着二十世纪科学与技术的飞速发展,人们不必专门劳神为科技的重要性奔走呼吁了,人们在一次次科技革命带来的新的世界里尽情享受着它带来的福祉。但是,二十世纪两次世界大战的降临打碎了人们的梦想。以科学技术为先导的武器成为屠戮生命的刽子手,原子弹的蘑菇云冲破了科学与伦理的屏障,科学领域还可以保持“伦理中立”的价值观吗?二十世纪的人们忧郁地意识到,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它既可能扫除无知的愚昧和黑暗,为人们带来前所未有的福祉;也可能刺破和谐,成为人类毁灭自身的工具。让科学促进生存与死亡,在于人类的选择。学生——尤其是理工科学生——应当具有对于人类终极价值的关怀,而这种关怀正是人文精神所系。
科技与人文的关系是什么呢?如果说,科技是一辆飞奔的汽车,那么,它将驶往何方,它的方向是助益人的幸福还是给人类带来灭顶之灾,则由人文关怀决定。
现代似乎是一个需要为人文精神与教育寻求生存理由的时代,幸耶悲耶?
那么,在科技教育中,如何融合人文精神呢?
让我们听听二十世纪有着传奇色彩的大科学家爱因斯坦怎么想的吧。爱因斯坦在论教育的演讲中表达了他的观点:学校的目标应当是培养和谐发展的人,而不是专家(《论教育》),技术学校的培养目标亦当如此。他反对学校直接教授那些在以后生活中直接用得到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在他看来,生活所要求的东西过多,学校不大可能采取这样那样的专门训练,何况单纯的专业知识教育,只能使人成为有用的机器,不能成长为和谐发展的人。他认为学校应当把发展学生独立思考和独立判断的一般能力放在首位,需要使学生理解社会伦理准则并对之产生热烈的感情,需要养成对美和善的辨别力,同时还必须学习去了解人们的动机、幻想与疾苦,以此获得与别人和集体的适当关系。他认为,这些价值观主要不是通过教科书传授给年轻一代,而是通过“人文学科”,通过同教育者亲身接触得来的。过分强调竞争制度,以及依据直接用途而过早专门化,会扼杀包括专业知识在内的一切文化生活所依存的那种精神(《培养独立思考的教育》)。他认为,如果一个人掌握了他的学科的基础理论,并且学会了独立地思考和工作,他必定会找到他自己的道路,而且比起主要以获得细节知识为其培训内容的人来,他一定会更好地适应进步和变化。
与专业科技知识及人文教育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两者是否必然为教育中对立的内容呢?我以为,如果将人文精神的最高境界视为对真善美的追求,那么,科学知识、科学精神与科学方法教育融汇而成的科学教育,正需要以人文精神为其价值内核。人文与科技教育实可互为促进。
科学教育启真。在诸多领域,强调“科学性”似乎已经成为人们衡量其正确性的标准。人们似乎忘了,科学研究发现本身也许并非是终极真理,它们可能有所局限。对此,英国哲学家波普尔倡导用“证伪法”对科学发现加以检验,将所有科学定理、定律均视为暂时的假说,时刻等待着新的发现来否定它。这种开放的科学研究态度将疑问和批判视为科学的基本态度和基本精神。事实上,科学史上的许多伟大发现都建立在对某些被认为是经典结论的怀疑和检验中。在科学知识教学中,使学生了解探索科学的过程中一个不断发现新的领域、原则的过程,了解理论是可错的,从而对科学问题产生探究和质疑的态度,甚至对伟大科学家的方案也不盲目崇拜,有可能为他们进行新的探索奠定自由思考与开放视野的心理准备。
科学教育启善。科学的应用不再是一个可以回避“善恶”的问题,战争中用搀杂了科技高含量的武器杀人是一个最为极端的例子,而当计算机病毒以“爱(love)”的名义来传播时,科技带来的阴影已成为当代人心中抹不去的忧虑。也许我们可以说,科技带来的问题——环境污染是另一个例子——只能用科技来解决,但科技本身不能回答解决的方向和价值取向,回答来自于对人文精神的关怀,甚至冲破以人为本的意义,而上升到对于整个地球上的一切生命的关怀——这是对“善”的尊崇。
科学教育启美。在学校教育中,科学一直是以严谨、抽象和纯理性的形象出现的。而在许多科学家眼中,追求科学真理的过程,就是追求自然世界的简洁性、对称性与和谐性,也即追求美的过程。缺乏艺术的熏陶,缺乏诗人般的想象力和气质,就不会成为独创性的、第一流的大科学家。
在科学教育中,通过对科学知识、科学精神、科学方法的教育的平衡,对教材作史论结合的改进,对各种促进学生思维、情感发展的教学方法的应用,我们才能有望造就将人类的幸福,将“真善美”的追求作为起点和终点的科技人才。因为科学之真、道德之善、艺术之美的理想原是不可分的“三位一体”,正如拉丁箴言所说的那样:“简单是真的标志,美是真理的光辉。”而善——“适用于道德经验的东西,必然在更高的程度上也适用于美的现象。”(席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