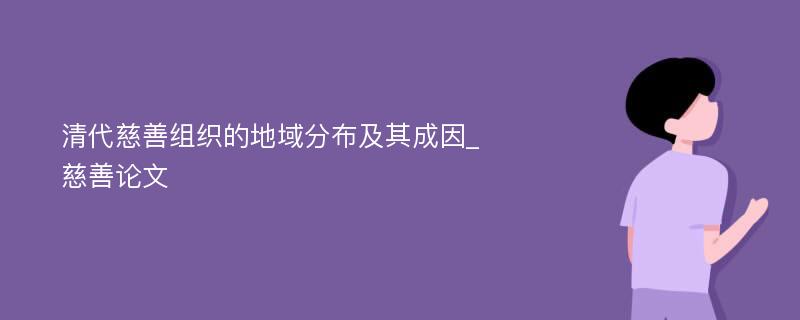
清代慈善机构的地域分布及其原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清代论文,地域论文,慈善机构论文,原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5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2359(2007)05—0162—04
清代是慈善活动比较发达的一个时期,大量慈善机构纷纷设立,它们所开展的救助活动涵盖了慈幼、养老、恤婺、助葬和疾病救助等。从救助主体的角度来看,清代慈善机构大体可分两类:一类是官方为主导的养济院、育婴堂、普济堂等;另一类是民间力量为主导的地方善堂、宗族义庄和工商业者的会馆公所。清代慈善问题,近年逐渐引起学者们关注,尤以夫马进、梁其姿、王卫平的成果最为丰硕。但是,从整体上对清代慈善机构地域分布特征进行研究尚未引起足够重视,本文拟从这一角度进行探讨。
一
在官方为主导的慈善机构中,养济院完全由政府办理。养济院最早出现在南宋,制度化始于元代,世祖至元十九年(1282年),诏“各路立养济院一所”[1]。明洪武五年(1372年),“诏天下郡县立孤老院,凡民之孤独残疾不能自立者,许入院,官为赡养,……寻又改孤老院为养济院”[2],进一步将养济院推广到州县一级。清承明制,随着清政府对全国统治的建立与巩固,养济院制度也逐步得到恢复和发展。养济院是前代比较成熟的救济制度,各州县大都有现成的设施,对以少数民族身份入主中原的满清政权来讲,这样一个行“仁政”、奠定自己统治合法性的机会,它自然不会放弃。顺治五年(1648年),清政府下诏“各处养济院收养鳏寡孤独及残疾无告之人,有司留心举行,月粮依时发给,无致失所。应用钱粮,察明旧例,在京于户部、在外于存留项下动支”[3](卷二六九,户部,蠲恤)。养济院制度在清代的发展首先体现在其救济覆盖范围的扩大上。由于清代统治区域的扩大,边疆一些地区也被纳入这一救济体系。如广西镇安府,在清初为流府时,“向未有孤贫口粮”,雍正七年(1729年)改府,领州二县一土州四,到十三年“准其各设四名”。
清代养济院制度的救济对象,在《大清律例》中有明确规定:“鳏寡孤独及笃废之人,贫穷无亲属依倚,不能自存”[4],要求受救济者必须同时满足三个条件:丧失劳动能力、没有私人财产并处于家庭赡养之外。这个群体处于社会的底层,失去了生存能力,最需要外来帮助,在政府实施的有限救助活动中,得到了优先考虑。养济院皆有定额,按省确立,各省名额从数百到数千不等。乾隆初年,河南省额为1990名,山西省额设孤贫人数为1148名,陕西省额内2191名,额外498名[3](卷二六九,户部,蠲恤),各省再将名额分配给所属州县。为收养这些人,基本上每州县设立一所养济院。可以说,清代的养济院是平均分布于全国各地的。
从明末开始,民办的慈善机构逐渐出现,清初政府并没有太多介入。雍正年间,官方逐渐渗透其中,使其变为官民合办机构,这些慈善机构以育婴堂和普济堂为代表。雍正二年(1724年)闰四月,雍正发布上谕:“京师广宁门外,向有普济堂,凡老疾无依之人,每栖息于此。司其事者,乐善不倦,殊为可嘉……尔等均有地方之责,宜时加奖励,以鼓舞之。”[3]同时,对育婴堂也要求“行文各省督抚,转饬有司,劝募好善之人,于通都大邑人烟稠集之处,照京师例,推而行之”[3](卷四零六,礼部,风教),并向北京广渠门内育婴堂颁赐“功深保赤”匾额一方和银一千两,以示鼓励。育婴堂和普济堂本来是由地方社会主持创设的民间慈善机构,自雍正二年诏谕发布以后,情况开始发生变化,其官营色彩日趋浓厚,各堂在经费来源和日常管理上受官方的影响较多,逐渐转化为官督民办的机构。雍正还只是鼓励民间力量在大城市设立普济堂、育婴堂,而到了乾隆年间,官办趋势则进一步增强。乾隆元年(1736年)议准“各省会及通都大郡,概设立普济堂,养赡老疾无依之人,拨给入官田产,及罚赎银两、社仓积谷,以资养赡”[3](卷二六九,户部,蠲恤)。用地方公产来保证普济、育婴二堂的设立,进一步将两者推向全国。从此以后,不少地方即由官方担负起创设、管理普济堂和育婴堂的责任。各级地方政府奉旨纷纷建堂,一时间形成“由京师达郡县,育婴堂乃遍天下”[5] 的局面,普济堂也大抵如此。就全国而言,不仅各省的省会,而且各府、州、县治,都置有相应的机构。
政府对普济堂、育婴堂的介入体现在清政府财政拨款上。如“福建省城育婴堂经费,岁拨存公项下银五百两,又拨盐道库羡余剩充公银一千二百两,并以岁收田租、生息等银凑用(岁无定额),与普济堂各半分支,报部核销”[6]。太仓普济堂,“清雍正二年奉旨劝谕开设。乾隆四年,知州江之炜、知县平其政奉文将入官房屋改为一州四县医赡老疾之所,计屋四十九间半,续又奉文拨给入官田产暨绅士前后捐田充用”[7]。政府对普济堂、育婴堂拨入了公款,自然会参与其中的管理,太仓普济堂于乾隆“五十五年,奉两江总督孙士毅行令,停止董事,官为经理”[7]。在实际运营中,育婴堂、普济堂带有强烈的官方色彩。
二
从清中叶开始,全国人口出现了迅猛发展的局面。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达到了3亿,到鸦片战争爆发前,全国人口总数达到了4.128亿[8](P251—252)。伴随着人口的增加的是社会的整体贫困化和贫富分化,从而使社会的救济需求大大增加。与此同时,清政府的财政日趋匮乏,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时,曾有结余7000余万两。但自嘉庆元年(1796年)至九年(1804年),为镇压白莲教起义,所耗军需饷银多达2亿两之巨,相当于清政府5年的全部财政收入,国库极度空虚,政府已很难再为社会救济支出更多的经费。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开展慈善活动的主体开始由政府向民间转变,民间为主导的慈善机构逐渐增多。一方面,主要依靠民间力量的综合性善堂在一些大城市开始兴起;另一方面,完全由民间办理的宗族义庄和会馆公所(以互助为主要职能的)在江南迅速发展。
综合性善堂开展的活动覆盖面广,规模较大。嘉庆九年(1804年)设立的上海同仁辅元堂,开展的救济活动主要有“一恤婺,凡旧族孀居,贫苦无依者,月给钱七百;一赡老,凡年过六十,贫苦无依或残疾不能谋生者,月给钱六百;一施棺,凡贫无以殓者,予之棺并灰沙百斤;一掩埋,凡无主棺木,及贫不能葬者,一例收埋。后又建有义学,施棉衣,收买字纸以及代葬、济急、水龙、放生、收瘗路毙浮尸等事。它如栖流、救生、给过路流民口粮悉预焉。”成为上海“诸善堂之冠”[9]。广东最著名的善堂是创办于同治十年(1871年)的广州爱育善堂。据记载,当年邑中绅富设爱育善堂于广州城西十七铺,官方在批准的同时,又“先后赀助四千金为之倡”,并“普谕绅士及各行店量力认捐,以成善举”,得到了富商们的积极响应,“赀助者三万两有奇,各行认捐者每年六千两有奇”。资金齐备以后,绅董们制定了章程,将所筹资金除用于建堂外,余款皆“分别治产生息”。其活动主要有“开设义学、施药施棺、捡拾腐骼、栖养废疾诸善事”。爱育善堂在当时“规模之大,积储之厚,捐输之广,施济之宏,尤前此未有…其惠几遍于全省”[10]。创设于光绪四年(1878年)的天津广仁堂“分设六所,一曰慈幼所,收养男孩,初时则为涤垢治病,继则分拨各所授事。二曰蒙养所,设义学整斋,择聪俊者,延师课读。三曰力田所,于堂之左右购置地亩,种植木棉稻黍菜蔬,择笨者雇老农教习。四曰工艺所,择不能耕读者,令习编藤织席刻字印书,俟年长业成,听其出堂自谋衣食。五曰敬节所,收养青年节妇及无依幼女,无家可归,俟长成为之婚择配。六曰戒烟所,广延良医,妥置方药,疗治鸦片瘾病,俾吸食者有自新之路庶烟禁不致徒设”[11]。综合性善堂适应了城市发展需要,弥补了官办慈善机构的不足,同时也有助于地方士绅更多地介入地方事务的管理,从而得到士绅的青睐。松江府“道光以来,郡邑村镇递次兴建,几于靡善不便”[12]。这些善堂,政府仍然参与监管,只不过已不占主导地位。
至于完全由民间办理的宗族内社会救济和工商业领域的救助活动,发展更不平衡。清代宗族内的救济设施主要是义田、义庄。义庄以义田为主体,以赡养贫困族人为宗旨,作为赡族组织机构的义庄拥有庄屋、义庄田、墓祭地、宗祠等。北宋皇佑二年(1050年),范仲淹在苏州创建了全国最早的义庄——范氏义庄。范氏义庄对后世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陈奂《济阳义庄记》中说:“范氏设义庄以赡族之贫,至今吴人效法者颇众。”[13] 义庄和义田主要分布在江南地区,苏松常三府较多,以苏州最为集中。据潘光旦、全慰天在“土改”时的调查,苏南地区吴县、常熟两县义庄较多,吴县有64家,常熟有88家,其他各县除无锡、武进外,义庄却不多见[14](P49—51)。
工商业领域的互助活动通过工商业者的组织会馆、公所实现的,会馆、公所主要分布于各城市和商业巨镇。其职能很多,但救助功能较强的却集中在苏州、上海地区,开展救助活动是两地会馆公所主要甚至是唯一的职能。如嘉庆八年(1803年)在沪宁波人的四明公所以从事同乡救助为其唯一职能。进入民国时期,在其章程第一条中,仍规定以建殡舍、置义冢为公所宗旨。又如苏州漆作业,在这一时期创立性善公所,“以备同业贫苦孤独、病残无依者生养死葬等事”[15](P148)。
苏州、上海民间救济活动发达,当时人就注意到了。冯桂芬说:“今世善堂义学之法,意犹近古。能行之者,惟我江苏为备,江苏中又以苏州、上海为备,虽都会如江宁、膏腴如扬州,弗逮也。”[16] 苏州“城内外善堂可偻指数者,不下数十。生有养,死有葬,老者、废疾者、孤寡者、婴者,部分类叙,日饩月给,旁逮惜字、义塾、放生之属,靡弗周也”[17](P368)。上海“善堂林立,甲于他邑。而资斧亦皆充足”[18]。两地民间慈善活动的发达程度,远远高于全国其他地区。
三
从总体上看清代的慈善机构的地域分布,其平衡程度与政府介入程度成正比:完全由政府开展的救济活动,其地域分布最均衡;政府起主导作用的,其分布比较均衡;民间自行开展的,则最不平衡。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我们可以从政府政策和各地经济文化差异等方面进行探讨。
清政府的政策由各州县等地方政府来执行,所以政府起决定作用的慈善活动,其分布便比较均衡。救济需求是慈善活动存在的基础,无依无靠的孤老、寡妇、残疾人是一个社会的普遍现象,清代自然也不例外,因此对这个群体进行救助的养济院、普济堂、清节堂应运而生。随着人口的增多、商品经济发展和社会的贫富分化,这个群体的数量逐渐增大,而清政府受其财力的制约,仅靠自身无法解决这个问题,只能号召民间力量的参与。清政府宣布:“凡士民人等,或养恤孤寡、或捐资赡族、或捐修公所及桥梁道路、或收瘗尸骨,实与地方有裨益者,八旗由该都统具奏,直省由该督抚具题,均造册送部。其捐银至千两以上,或田粟准值银千两以上者,均请旨建坊。”[3](卷四零三,礼部,风教) 由于各地的经济、文化情况的巨大差异,民间社会主导的慈善机构分布极不平衡,集中在江南一带。
清代江南地区社会慈善事业的兴盛,与商品经济的发展有一定关系。晚清上海慈善机构数目的大量增加,与这一时期上海人口膨胀不无关系。鸦片战争之后的上海发展迅速,人口剧增,带来各种社会问题。又如晚清工商业领域的互助活动将广设义冢作为重点,与这一时期各大城市商品经济迅速发展,城镇地价不断增值有很大关系。再加上交通不便和土葬风气的盛行,工商业者帮助安葬死者作为最重要的救助内容。另一方面,商品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城镇繁荣、商业的兴盛,开展慈善活动需要大量的金钱,拥有雄厚经济资源的商人及其帮助必不可少。晚清上海的善堂领导阶层有越来越多商人参与,如上虞商人经元善等,都是清末上海著名的“善人”。相对而言,内地的救济活动较少,与当地经济实力较弱也有一定联系。
在民间盛行的儒、释、道三教中均有大量社会救济的思想观念,儒家认为仁者应超越自我去关心他人,这样才能达到仁的境界。佛家讲求因果报应,把布施救济、济贫恤困作为人生价值实现的途径。道家认为行善可使子孙得到福报。江南文化发达,善书传播广泛,行善的思想相应也得到了广泛传播。从清初开始,好善风气逐渐在长江三角洲一带盛行。“生长是邦,耳濡目染,因视善善为分内事”[17](P368)。一地有了慈善活动,就会带来善行的模仿。苏州肉店同业设立公所进行互助的理由是“苏郡建设各善堂,恤养老幼贫病,施舍棺药,收埋尸柩等项善举,无一不备”[15](P259)。其最终结果就是“东南好之义之名称天下”[12],形成了民间慈善机构分布的不平衡局面。
收稿日期:2007—04—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