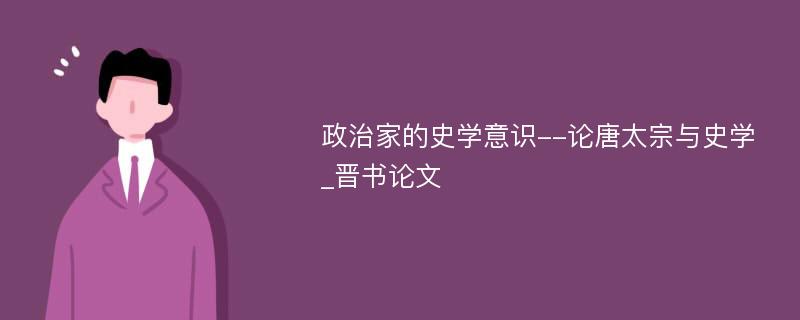
一个政治家的史学自觉——略论唐太宗和历史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学论文,历史学论文,政治家论文,太宗论文,自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57(2003)04-005-09
这里说的“史学自觉”,至少包括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是:对史学的功用有深刻的认识,并能以这种认识运用于一定的社会实践。第二层含义是:对史学活动给予关注,并在史学工作上作出积极的努力以至于作出相应的(直接的或间接的)贡献。一个人具备了这两层含义的要求,可谓之“史学自觉”。在中国古代的政治家中,唐太宗是一位“史学自觉”的突出代表。
一 政治家需要历史学吗?
这个问题,不止是一个理论问题,对于政治家来说,它更是一个实践问题。因此,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必须从认识和实践两个方面进行考察。在中国古代政治生活中,尤其是在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生活中,唐太宗是从认识和实践两个方面对这个问题作出了很好的回答的政治家。唐太宗认识历史有一个特点,即他十分重视认识历史的途径。具体说来,他认为人们通过读史才能了解古代历史的面貌,了解历史上的人和事,从而从历史中得到启示和智慧。反之,离开了史书,这一切都成了不可能的事情。他曾这样写道:
朕拯溺师旋,省方礼毕;四海无事,百揆多闲;遂因暇日,详观典府。考龟文于羲载,辨鸟册于轩年;不出岩廊,神交千祀之外;穆然旒纩,临睨九皇之表。是知右史序言,由斯不昧;左官诠事,历兹未远;发挥文字之本,通达书契之源:大矣哉,盖史籍之为用也。自沮诵摄官之后,伯阳载笔之前,列代史臣,皆有删著。仲尼修,而采《祷杌》;倚相诵,而阐《丘》《坟》。
降自西京,班、马腾其茂实;逮于东汉,范、谢振其芳声。蕞尔当途,陈寿覆其国志;眇哉刘宋,沈约裁其帝籍。至梁、陈、高氏,朕命勒成;惟周及隋,亦同甄录;莫不彰善瘅恶,激一代之清芬;褒吉惩凶,备百王之令典。[1](卷八一《修晋书诏》)
这里说的“神交千祀之外”、“临睨九皇之表”,是强调通过阅读史书,可以使人的思想和视野超越时间与空间;所说“右史序言”、“左官诠事”,“发挥文字之本,通达书契之源”,是指出了史官制度和文字的结合所产生的社会作用和无可替代的特殊意义。惟其如此,唐太宗得到一个明确而极有分量的结论,这就是:“大矣哉,盖史籍之为用也。”
在唐太宗以前,有许多人都曾讲到过对于历史经验的重视及其意义,归结起来,大意都近于“前事之师,后事不忘”、“彰往察来”等等。但如何认识“前事”?“彰往”的途径何在?大多没有作出明确的表述。在这个问题上,唐太宗的认识之所以显得重要,正是因为他指出了人们对历史的了解、认识,是通过“史籍”而得到的。他对于史学工作的重视,就是建立在这样的思想基础之上,而较少狭隘的实用的色彩。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唐太宗的这一认识,比起唐代史学批评家刘知幾的论述,还要早五六十年。刘知幾在他的名著《史通》中指出:
向使世无竹帛,时阙史官,虽尧、舜之与桀、纣,伊、周之与莽、卓,夷、惠之与跖、硚,商、冒之与曾、闵,但一从物化。坟土未干,则善恶不分,娴媸永灭者矣。苟史官不绝,竹帛长存,则其人已亡,杳成空寂,而其事如在,皎同星汉。用使后之学者,坐批囊箧,而神交万古,不出户庭,而穷览千载,见贤而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若乃《春秋》成而逆子惧,南史至而贼臣书,其记事载言也则如彼,其劝善惩恶也又如此。由斯而言,则史之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务,国家之要道。有国有家者,其可缺之哉
这一段话,非常清晰地阐明了人们之所以能够认识历史上的人和事并进而作出自己的价值判断,正是因有史官的存在和史书的撰述;揭示出“史官不绝,竹帛长存”对于社会和人类进步的意义,从而揭示出史学的真正价值。
我之所以要引证刘知幾的这些话,是为了说明作为政治家的唐太宗,在刘知幾之前已经有了大致相近的认识,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当然,唐太宗的史学自觉,无疑会反映在他对历史撰述事业的重视。这突出地表现在梁、陈、齐、周、隋“五代史”的修撰和《晋书》的修撰方面。
梁、陈、齐、周、隋“五代史”的修撰,始议于武德四年(621年)令狐德棻的上书建议。他指出:“近代已来,多无正史”,“当今耳目犹接,尚有可凭,如更数十年后,恐事迹湮没”,“如文史不存,何以贻鉴今古?”[3](卷七三《令狐德棻传》)唐高祖赞同他的建议,并于次年颁发了《命萧瑀等修六代史诏》[1](卷八一),令诸大臣分工撰述。此次修史动议,由于以下原因,历数年而未果:一是当时全国政局尚未安定,诸大臣无暇顾及修史;二是有的大臣离职或辞世,任务落空;三是缺乏大规模修史的组织经验,无人统筹规划,撰写工作难以有实质性的进展。这是皇家修史的一个重要教训。但是,这次修史动议也展示出了一个事实:唐皇朝建立伊始,即十分重视修史活动,而“修六代史诏”则显示出史学上的宏大气度,为后来的修史活动奠定了思想基础。
八年后,即贞观三年(629年),唐太宗建史馆于禁中,命诸臣修撰梁、陈、齐、周、隋“五代史”。诸臣认为,后魏(即北魏)史已有魏收《魏书》、魏澹《魏书》,“以为详备”,不必重修,故由“六代史”变为“五代史”。经过七年的努力,至贞观十年(636年),五史皆成,为一代盛事[4](卷六三《史馆上·修前代史》)。此次修史成功,同唐太宗的决策有极大关系。一是他设立了史馆,并给史馆以很高的地位,为皇家修史开创了新的局面,在中国史学上是一件里程碑的事件。二是他以房玄龄监修,魏徵“总加撰定”[3](卷七一《魏徵传》),令狐德棻“总知类会”诸史[3](卷七三《令狐德棻传》)。正是有了修史的专门机构,又有了明确的分工合作,加之比较安定的社会环境,才可能出现中国史学上的这一盛事。显然,唐太宗是这一盛事中的关键人物。
唐太宗晚年提出了撰写新的《晋书》的要求,这是他在皇家修史活动中的又一重要决策。对此,学术界曾有这样那样的猜测和推论,似也不无参考价值。但我认为唐太宗的这一决定,在他于贞观二十年(646年)下达的《修晋书诏》里本已阐述得清清楚楚,足以表明他的意向和宗旨,舍此而作其他的猜测和推论,恐怕都难以反映历史真相。唐太宗指出:
唯晋氏膺运,制有中原,上帝启玄石之图,下武代黄星之德;及中朝鼎沸,江左嗣兴,并宅寰区,各重徽号,足以飞英丽笔,将美□书。但十有八家,虽存记注;而才非良史,事亏实录。[1](卷八一)
诏书对十八家晋史一一作了评价,究其根本来说,一则不能称为“实录”,二则不是完全意义上的晋史。他希望写出一部超出现存十八家晋史的《晋书》,其具体要求是“铨次旧文,裁成义类,俾夫湮落之诰,咸使发明”。当然,诏书中所批评以往晋史之缺陷的一些方面,无疑都是应当避免的。因有诸家晋史作为参考,新修《晋书》进展较快,于贞观二十二年(648年)撰成。新修《晋书》的总面貌是:
以臧荣绪《晋书》为本,捃摭诸家及晋代文集,为十纪、十志、七十列传、三十载记。其太宗所著宣、武二帝及陆机、王羲之四论,称制旨焉。房玄龄以下称史臣,凡起例皆(敬)播独创焉。[3](卷六三《史馆上·修前代史》)
以一家为本,参考诸家之长,并吸收晋人文集之与史事相关联者入史,可见唐初史家在撰述路径与方法上的成熟,确为后人修史提供了有益的启示。有一点必须指出:令狐德棻在近二十人的《晋书》修撰者中被推为首,“其体制多取决焉”[3](卷七三《令狐德棻传》),而非敬播一人“独创”。今天我们读到的《晋书》,就是唐太宗下诏新修的《晋书》;加上上面已经讲到的“五代史”,总共有六部“正史”撰成于唐太宗在位期间,这占了“二十四史”部数的四分之一。对这六部“正史”,我们不必重复人们已经作过的许多评价,而是要从中窥见唐太宗在史学自觉方面所达到的高度。他创立了比较完备的史馆制度而为后人沿袭一千多年,在他的号召下一举撰成六部“正史”且流传至今,仅此两件事情,他的史学自觉以及他在中国史学上的位置已足以令人赞叹。然而,他的史学自觉还表现在他的政治实践方面,这一点更值得人们关注。
二、史学自觉与政治实践
唐太宗在政治实践上成功的主要标志,是“贞观之治”局面的形成。用今天的眼光来看,“贞观之治”是当时综合国力的表现,它在经济、政治、文化、军事、民族关系、中外关系、民风民俗等方面,都呈现出一种盛世气象。
“贞观之治”局面的出现,是多种原因促成的。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唐太宗和他的大臣们非常重视对历史经验的总结和借鉴。作为最高统治者,唐太宗在这方面起了表率的作用,其他如房玄龄、魏徵等这些最高统治集团中的核心人物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唐太宗对历史经验教训的重视,反映出他对史书以至史学的高度重视,换言之,这是他的史学自觉之光折射在政治实践上的光彩之处。
关于唐太宗重视历史经验教训并使之与自身的政治实践相结合的问题,我们要感谢唐玄宗时期的史学家吴兢(670-749年)所撰写的一部历史名著《贞观政要》。这是一部全面记述唐太宗君臣论政之书,对于唐太宗及其决策核心的大臣们如何重视历史经验并竭力从中吸取借鉴有详细的论说。本书含十卷四十篇,可以说篇篇都离不开讨论历史经验及其与现实的关系。其篇目是:君道、政体;任贤、求谏、纳谏;君臣鉴戒、择官、封建;太子诸王定分、尊敬师傅、教戒太子诸王、规谏太子;仁义、忠义、孝友、公平、诚信;俭约、谦让、仁恻、慎所好、慎言语、杜馋邪、悔过、奢纵、贪鄙;崇儒学、文史、礼乐;务农、刑法、赦令、贡赋、辩兴亡;征伐、安边;行幸、田猎、灾祥、慎终。[6]对于如此丰富的、涉及异常广泛的内容,这里不能作详尽的阐述和评论。因此,只能就笔者认为是尤为重要的几个方面作扼要评述。
第一,关于为君之道。贞观初年,唐太宗曾向魏徵提出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何谓明君、暗君?”魏徵回答说:
君之所以明者,兼听也;其所以暗者,偏信也。诗云:“先民有言,询于刍荛。”昔唐、虞之理,辟四门,明四目,达四聪。是以圣无不照,故共、鲧之徒,不能塞也;靖言庸回,不能惑也。秦二世则隐藏其身,捐隔疏贱而偏信赵高,及天下溃叛,不得闻也。梁武帝偏信朱异,而侯景举兵向阙,竟不得知也。隋炀帝偏信虞世基,而诸贼攻城剽邑,亦不得知也。是故人君兼听纳下,则贵臣不得壅蔽,而下情必得上通也。[5](卷一《君道》)
唐太宗对于魏徵所说,十分赞成,故而“甚善其言”。魏徵的回答,是以先贤的言论和历史的事实为依据,并概括出“君之所以明者,兼听也;其所以暗者,偏信也”的认识,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至于使这一问对成为中国政治史上的千古佳话。当然,问题的重要性并不在于这一出色的问对,而在于当事人特别是唐太宗在自己的政治实践中贯彻了作为“明君”的原则。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唐太宗不仅是“名君”,而且也是“明君”,与此有极大关系。一般说来,在唐太宗的政治生涯中,他是努力地按照“兼听”的原则行事。唐初,大乱之后,应实行什么样的国策?这是治国安邦的大事。他自己认为,短时期内难以达到至治。于是他征询大臣们的意见。魏徵认为:“凡人在危困,则忧死亡。忧死亡,则思化。思化,则易教。”唐太宗颇有怀疑地反问道:“善人为邦百年,然后胜残去杀。大乱之后,将求致化,宁可造次而望乎?”魏徵进而论道:“此据常人,不在圣哲。若圣哲施化,上下同心,人应如响,不疾而速,期月而可,信不为难,三年成功,犹谓其晚。”唐太宗表示赞同魏徵的看法。这时,大臣封德彝等提出不同的认识,认为:“三代以后,人渐浇讹,故秦任法律,汉杂霸道,皆欲化而不能,岂能化而不欲?若信魏徵所说,恐败乱国家。”魏徵反驳说:“五帝、三王,不易人而化。行帝道则帝,行王道则王,在于当时所理,化之而已。考之载籍,可得而知。昔黄帝与蚩尤七十余战,其乱甚矣,既胜之后,便致太平。九黎乱德,颛顼征之,既克之后,不失其化。桀为乱虐,而汤放之,在汤之代,即致太平。若言人渐浇讹,不及纯朴,至今应悉为鬼魅,宁可复得而教化耶?”[5](卷一《政体》)
封德彝等虽无言以对,但终认为魏徵的主张不可施行。这一场激烈的辩论,对于后来“贞观之治”局面的出现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几种不同的意见中,唐太宗毅然采用魏徵的主张,“每力行不倦,数年间,海内康宁”,“华夏安宁,远戎宾服”,唐太宗无限感慨与幸慰,对魏徵给予极高的评价,把自己比作“玉”而把魏徵比作“良工”,他说:“玉虽有美质,在于石间,不值良工琢磨,与瓦砾不别。若遇良工,即为万代之宝。朕虽无美质,为公所切磋,劳公约朕以仁义,弘朕以道德,使朕功业至此,公亦足为良工尔。”
第二,关于认识民力。在中国历史上,不可能产生对民力有完全正确的认识,甚至存在着认识上的很大差别。这种差别,又直接涉及到社会的治乱、朝代的存亡。对于这一点,唐太宗君臣屡屡有所讨论。这些讨论,集中到一点,可以概括为水舟关系之论。贞观六年(632年),魏徵对唐太宗说:
自古失国之主,皆为居安忘危,处治忘乱,所以不能长久。今陛下富有四海,内外清晏,能留心治道,常临深履薄,国家历数,自然灵长。臣又闻古语云“君,舟也;人,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陛下以为可畏,诚如圣旨。[5](卷一《君道》)
此处所谓“人”,即是“民”的代称。贞观十四年,魏徵在一次上疏中又指出:
《礼记》曰:“爱而知其恶,憎而知其善。”若憎而不知其善,则为善者必惧。爱而不知其恶,则为恶者实繁。诗曰:“君子如怒,乱庶遄沮。”然则古人之震怒,将以惩恶,当今之威罚,所以长奸,此非唐、虞之心也,非禹、汤之事也。《书》曰:“抚我则后,虐我则雠。”荀卿子曰:“君,舟也。民,水也。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舟。”故孔子曰:“鱼失水则死,水失鱼犹为水也。”故唐、虞战战栗栗,日慎一日。安可不深思之乎?安可不熟虑之乎?[5](卷三《君臣鉴戒》)
对于魏徵所强调的这些道理,唐太宗都表示赞同而“深嘉纳之”。他也用这个思想来教导太子。他在晚年所著的《帝范》一书中,突出地论述了这个思想。
第三,关于民族关系。唐太宗在位期间,重视密切各族间的关系。前文说到的“华夏安宁,远戎宾服”,以及“胡越一家”、唐太宗获得“天可汗”的尊号等等,都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民族大融合的反映。对此,唐太宗以历史与现实作过比较,故而也有十分的自信。贞观二十一年(647年)唐太宗同大臣们讨论他在政治上获得成功的原因,史载:
上御翠微殿,问侍臣曰:“自古帝王虽平定中夏,不能服戎、狄。朕才不逮古人而成功过之,自不谕其故,诸公各率意以实言之。”群臣皆称:“陛下功德如天地,万物不得而名言。”上曰:“不然。朕所以能及此者,止由五事耳。自古帝王多疾胜己者,朕见人之善,若己有之。人之行能,不能兼备,朕常弃其所短,取其所长。人主往往进贤则欲置诸怀,退不肖则欲推诸壑,朕见贤者则敬之,不肖者则怜之,贤、不肖各得其所。人主多恶正直,阴诛显戮,无代无之,朕践祚以来,正直之士,比肩于朝,未尝黜责一人。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此五者,朕所以成今日之功也。”[6](卷198)
这五条经验都很重要,其中最后一条关于民族关系的认识,尤为可贵。
第四,关于善始慎终。“鲜克有终”,这是历史上历代统治者的一个教训。唐太宗统治集团创造了“贞观之治”的局面,作为最高统治者,唐太宗能否善始慎终,当是这个统治集团十分关注的问题之一。在这方面,唐太宗依然是一个关键人物。应当承认,正如唐太宗晚年自省的那样,在“盛世”之下,他本人也滋长了骄奢之风,因而屡屡受到大臣们的诤谏。但是,作为一代英主,唐太宗自己是不曾忘记“慎终”这一要求的。
关于善始慎终的政治目标,唐太宗着眼于两点,一是反复向大臣们致意,表明唐皇朝的功业,非其个人可以达到,“实赖诸公之力”;二是反复强调居安思危,即“安不忘危,治不忘乱”。他明确地指出,这都是他阅读史书所得到的启示。其中,秦、汉的经验教训尤为他所关注。吴兢《贞观政要》以卷末记唐太宗重视“慎终”之事,也表明了史家的深意。
贞观五年,太宗谓侍臣曰:“自古帝王亦不能常化,假令内安,必有外扰。当今远夷率服,百谷丰稔,盗贼不作,内外宁静。此非朕一人之力,实由公等共相匡辅。然安不忘危,治不忘乱,虽知今日无事,亦须思其终始。常得如此,始是可贵也。”魏徵对曰:“自古以来,元首股肱不能备具,或时君称圣,臣即不贤;或遇贤臣,即无圣主。今陛下明,所以致治,向若直有贤臣,而君不思化,亦无所益。天下今虽太平,臣等尤未以为喜,惟愿陛下居安思危,孜孜不怠耳!”[5](卷一○《慎终》)
贞观六年,唐太宗对大臣说:
自古人君为善者,多不能坚守其事。汉高祖,泗上一亭长耳,初能拯危诛暴,以成帝业,然更延十数年,纵逸之败,亦不可保。何以知之?孝惠为嫡嗣之重,温恭仁孝,而高帝惑于爱姬之子,欲行废立;萧何、韩信,功业既高,萧既妄系,韩亦滥黜,自余功臣黥布之辈,惧而不安,至于反逆。君臣父子之间悖谬若此,岂非难保之明验也?朕所以不敢恃天下之安,每思危亡以自戒惧,用保其终。[5](卷一○《慎终》)
贞观九年,唐太宗又对公卿们说:“朕端拱无为,四夷咸服,岂朕一人之所致,实赖诸公之力耳!当思善始令终,永固鸿业,子子孙孙,递相辅翼。使丰功厚利施于来叶,令数百年后读我国史,鸿勋茂业粲然可观,岂惟称隆周、炎汉及建武、永平故事而已哉?”房玄龄因而进言说:“陛下撝挹之志,推功群下,致理升平,本关胜德,臣下何力之有?惟愿陛下有始有卒,则天下永赖。”唐太宗回答道:“朕观古先拨乱之主皆年逾四十,惟光武年三十三。但朕年十八便举兵,年二十四定天下,年二十九升为天子,此则武胜于古也。少从戎旅,不暇读书,贞观以来,手不释卷,知风化之本,见政理之源。行之数年,天下大治而风移俗变,子孝臣忠,此又文过于古也。昔周、秦已降,戎狄内侵,今戎狄稽颡,皆为臣妾,此又怀远胜古也。此三者,朕何德以堪之?既有此功业,何得不善始慎终耶?”[5](卷一○《慎终》)这一番谈话,意味深长,今天读来,仍可令人三思。
贞观十四年,唐太宗和魏徵有一番对话。吴兢写道:
[太宗曰]平定天下,朕虽有其事,守之失图,功业亦复难保。秦始皇初亦平六国,据有四海,及末年不能善守,实可为戒。公等宜念公忘私,即荣名高位,可以克终其美。”魏徵对曰:“臣闻之,战胜易,守胜难。陛下深思远虑,安不忘危,功业既彰,德教复洽,恒以此为政,宗社无由倾败矣。[5](卷一○《慎终》)
从这些言论和思想来看,唐太宗确是认真阅读史书的,他对于秦汉史事尤为关注和再三思考,他所提出的问题也都是政治实践中的重大问题。由此可见,唐太宗不是一个狭隘的、只讲实用的人,他是把历史和现实联系起来进行思考,并力图从中寻找到正确的路径,以求长治久安。不仅如此,他还致意于有唐一代在历史上的位置,希望“丰功厚利施于来叶,令数百年后读我国史,鸿勋茂业粲然可观”。应当说,这并不是一个奢望或幻想,事实表明,有唐一代的历史不仅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是辉煌的一页,即使在世界历史上也有它的崇高地位。唐太宗的史学自觉,使他能够想到“数百年后读我国史”的景象,亦足以见其自信之坚、气度之大。
诚然,唐太宗是有自知之明的,他在恢弘的事业成就的道路上,也在不断地自省。他希望这些反思和自省能够成为一笔精神财富,使其后人可以从中得到教益。于是,他把历史经验和政治经验融会起来,写成一部《帝范》传给后人。这是他的史学自觉的最后的升华。
三、历史经验和政治经验的结合
把对以往的历史经验的理解和对现实政治经验的总结结合起来,著成一部“帝王论”即《帝范》留给后人学习、参考,可以看作是唐太宗把自己的史学自觉推向了他所能达到的高峰。
《帝范》是唐太宗辞世前的著作,一说作于贞观二十二年(648年),即他辞世前一年;一说作于贞观二十三年(649年),即他辞世的当年(注:《唐会要》,《册府元龟》二说不同,笔者以为当从《唐会要》作贞观二十三年为是。参见吴云等编《唐太宗集》,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05页。)。《帝范》凡十二篇,篇名为:君体、建亲、求贤、审官、纳谏、去谗、诫盈、崇俭、赏罚、务农、阅武、崇文。卷首有序,卷末有后序。唐太宗在《帝范》序中表明四层意思:一是再三致意创业维艰,“战战兢兢,若临深而御朽;日慎一日,思善始而令终。”二是指出太子李治从小养尊处优,“未辨君臣之礼节,不知稼穑之艰难。余每此为忧,未尝不废寝忘食。”三是历史上“经天纬地之君,纂业承基之主,兴亡治乱,其道焕焉”,是后人应当了解和思考的。四是指出撰写《帝范》的主旨,即“披镜前踪,博采史籍,聚其要言,以为近诫”[7](卷一○),希望太子认真学习,引以为戒,将来治理好国家。这篇序文,文字不多而含意甚深,表达了一位政治家对历史的洞察和对未来的关注。
《帝范》各篇所论,都要言不烦,切中本质。其《君体篇》,在“民者,国之先,国者,君之本”的思想指导下,全面阐述了“为君之体”。《建亲篇》从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入手,强调“众建宗亲而少其力”的做法,这是肯定西汉贾谊政治主张的正确和借鉴意义。《求贤篇》阐述了“国之匡辅,必待忠良,任使得其人,天下自治”的思想,对西汉皇朝在这方面的得失颇多论述。《审官篇》指出,明主当用人之所长:“智者取其谋,愚者取其力,勇者取其威,怯者取其慎,无智勇怯,兼而用之。”太宗朝人才济济,同他的用人之道是分不开的。尤其是他能做到“不以一恶而忘其善,勿以小瑕掩其功”的态度对待周围的人,实为难能可贵。《纳谏篇》指出:“王者高居深视,亏聪阻明,恐有过而不闻,惧有阙而莫补”,故必须“倾耳虚心,伫忠正之说”,以形成“臣无隔情于上,君能遍照于下”的政治局面。但是,“昏主则不然:说者拒之以威,劝者穷之以罪。大臣惜禄而莫谏,小臣畏诛而不言”,以致于“其为壅塞,无由自知”,“身亡国灭,岂不悲矣!此拒谏之恶也。”纳谏与拒谏所造成的两种不同的政治前途,如此分明。《去谗篇》是《纳谏篇》的进一步发挥,指出:“谗佞之徒,国之蝥贼也”,“故明主纳谏,病就苦而能消;暗主从谀,命因甘而致殒。可不诫哉!”《诫盈篇》阐述“俭则民不劳,静则下不扰。民劳则怨起,下扰则政乖”的道理,故应切记“骄奢之忌”。《崇俭篇》是《诫盈篇》的姊妹篇,进一步论述了“奢俭由人,安危在己”的思想。《赏罚篇》认为:“赏罚之权”应做到“无偏无党,王道荡荡”。《务农篇》说:“食为人天,农为政本。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乏则忘廉耻。”又说:“国无九岁之储,不足备水旱;家无一年之服,不足御寒温。”全篇反复致意于“务农之本”。《阅武篇》一方面指出“兵甲者,国之凶器也”,一方面又指出“土地虽广,好战则民凋;邦境虽安,忘战则民殆。”这里包含着对“兵甲”的辩证观点。《崇文篇》指出:“弘风导俗,莫尚于文;敷教训人,莫善于学。因文而隆道,假学以光身。不临深溪,不知地之厚;不游文翰,不知智之源”,“光于天下不朽者,其唯为学乎!”“文武二途,舍一不可;与时优劣,各有其宜”,全面强调“文”对于政治统治、“弘风导俗”的重要。
以上这十二篇的主旨所在,就是唐太宗在序中所说的,自古以来“经天纬地之君,纂业承基之主,兴亡治乱,其道焕焉”。当然,由于他自身的丰富而宏大的政治活动,在这些理解中渗透着他的亲身体验和经验教训。从这个意义上说,《帝范》一书可视为唐太宗在总结自身政治活动及体验的基础上所撰成的一部“君主论”。唐太宗在《帝范》后序中深自反省,他写道:
君子劳处其难,不能逸居其易,故福庆流之。是知祸福无门,唯人所召。欲悔非于既往,唯慎过于将来。择哲王以师,与无以吾为前鉴。夫取法于上,仅得为中;取法于中,故其为下;自非上德,不可效焉。吾在位以来,所缺多矣。奇丽服玩,锦绣珠玉,不绝于前,此非防欲也。雕楹刻桷,高台深池,每兴其役,此非俭志也。犬马鹰鹘,无远必致,此非节心也。数有行幸,以亟人劳,此非屈己也。斯数事者,吾之深过也。勿以兹为是而后法焉。[7](卷一○)
他的这种自我批判,几近于苛刻的程度,有的话或许后人中那些最严厉的批评家都会觉得过分。但是,我们对唐太宗自省的真诚之心和他对继承人的热切期望似不必有什么怀疑。反之,对暮年的唐太宗能够有这样的气度和胸襟,倒是应当给予高度评价的。可以说,《帝范》是他留给太子李治的一份政治遗嘱,也是他留给后世的一份政治思想遗产。
唐太宗的史学自觉,绝不是偶然的,而是在长期的政治生涯中学习、思考和体验的结果。早在他作为秦王的年代,秦府的学士们多是饱学之士。其中,虞世南同秦王李世民讨论历史问题最多。虞世南所撰《帝王略论》一书,以“公子曰”、“先生曰”的问对形式表述,当是他同秦王讨论历代帝王的事迹和得失而写成的[8](P131-132)。史载:
太宗重其博识,每机务之隙,引之谈论,共观经史。世南虽容貌懦愞,若不胜衣,而志性抗烈,每论及古先帝王为政得失,必存规讽,多所补益。太宗尝谓侍臣曰:“朕因暇日与虞世南商略古今,有一言之失,未尝不怅恨,其恳诚若此,朕用嘉焉。群臣若皆世南,天下何忧不理。”[3](卷七二《虞世南传》)
贞观十二年(638年),虞世南去世,唐太宗十分悲痛,说:“虞世南于我,犹一体也。拾遗补阙,五日暂忘,实当代名臣,人伦准的。吾有小失,必犯颜而谏之。今其云亡,石渠、东观之中,无复人矣,痛惜岂可言耶?”可见,秦王李世民从虞世南那里受到的史学熏陶是很深刻的。
秦王李世民的这种史学修养,在他即位之后又不断得到提升。按旧制,帝王不得亲览国史,但唐太宗却提出要观览国史的要求,他坦然地表明自己的意见。史载:
贞观十四年,太宗谓房玄龄曰:“朕每观前代史书,彰善瘅恶,足为将来规诫。不知自古当代国史,何因不令帝王亲见之?”对曰:“国史既善恶必书,庶几人主不为非法。止应畏有忤旨,故不得见也。”太宗曰:“朕意殊不同古人。今欲自看国史者,盖有善事,固不须论;若有不善,亦欲以为鉴诫,使得自修改耳。卿可撰录进来。”玄龄等遂删略国史为编年体,撰高祖、太宗实录各二十卷,表上之。[5](卷七《文史》)
贞观七年(636年)当梁、陈、齐、周、隋“五代史”纪传同时修成时,唐太宗十分高兴,他在奖赏修史大臣时说:
朕睹前代史书,彰善瘅恶,足为将来之戒。秦始皇奢淫无度,志存隐恶,焚书坑儒,用缄谈者之口。隋炀帝虽好文儒,尤疾学者,前世史籍竟无所成,数代之事殆将泯绝。朕意则不然,将欲览前王之得失,为在身之龟镜。公辈以数年之间,勒成五代之史,深副朕怀,极可嘉尚。[9](卷554《国史部·恩奖》)
“览前王之得失,为在身之龟镜”,这正是唐太宗史学自觉在政治实践中的格言之一。与此密切相联系的,是他还提出自己有“三镜”:“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3](卷七一《魏徵传》)对于唐太宗来说,所谓“以古为镜”,可以看作是史学自觉的又一种表述形式。唐太宗的史学自觉,还表现在他要求臣下认真读史,从史书中得到提高。他曾赠大臣李大亮《汉纪》一部,并嘱咐他说:
卿立志方直,竭节至公,处职当官,每副所委,方大任使,以申重寄。公事之闲,宜观典籍。兼赐卿荀悦《汉纪》一部,此书叙致简要,论议深博,极为政之体,尽君臣之义,今以赐卿,宜加寻阅。[5](卷二《纳谏》)
《汉纪》改《汉书》纪传为编年,记西汉一代史事,自不限“极为政之体,尽君臣之义”,但作为政治家的唐太宗对《汉纪》的这个评价,可谓切中要旨。
综上,我们是否可以得到这样一个总的认识:唐太宗的史学自觉,是“贞观之治”的思想基础之一;他的史学自觉在政治实践和史学事业中的作用及其产物是“贞观之治”积极成果的重要方面。历史发展了,时代特点不同了,但史学自觉对于政治家的重要,自有其一定之理,这仍然是值得今天的人们认真思考的。
收稿日期:2003-08-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