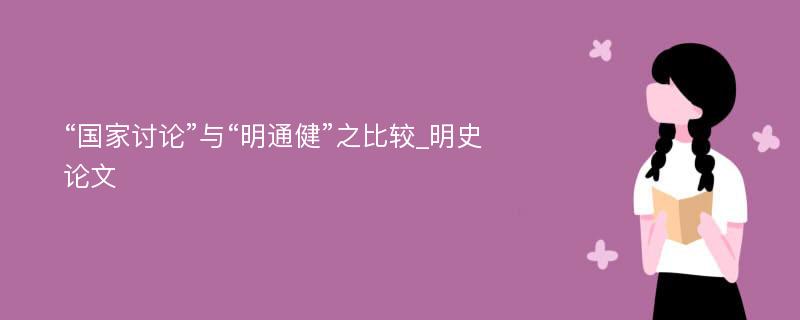
《国榷》与《明通鉴》之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通鉴论文,国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清人撰写的明史著作不下数十部,作为权威性的史书当推张廷玉主编的《明史》。而这是部奉敕编撰的官修史书,动辄忌讳,缺点不少,难以全面真实地反映明代尤其是明末的社会状况。因此,在研究明史时,参考私人著述就显得极为重要。本文拟对私撰的两部编年体明史著作——《国榷》和《明通鉴》作一比较研究,揭示出它们的异同和特点,以便人们更有效地利用这两部重要的史料。
一
有明一代,私人撰修国史之风盛行。嘉靖至万历年间,有邓元锡的《明书》,薛应旂的《宪章录》,郑晓的《吾学编》,陈建的《皇明通纪》以及稍后何乔远的《名山藏》等。明末清初易代之际,面对明朝的灭亡,满洲的入侵,许多明朝士民充满着哀怨,积愤于心,不吐不快,发愤写史以述先朝兴亡。《国榷》便是这个时代产生的一部杰出史著。
《国榷》的作者谈迁,“生平无他好,惟好书,故二酉五车,尽皆腹笥”①,“肆力于子史百家之言,尤谙列朝典故。”②谈迁在翻阅了众多史家著述之后,深感这些史书“拘忌文法,柱枝耳目,盲之诬,淑之短,赤之俗”③,存有许多缺点。尤令他气愤的是类似陈建《皇明通记》那类史书,见解肤浅,史实错误,观点荒谬,遗害不浅。同时,他在研读《明实录》的过程中发现某些记载并不完全可靠,甚至还有许多缺漏及掩饰之处,正如黄宗羲对《明实录》的评价那样:“见其表,其在里者已不可见,况革除之事,杨文贞(士奇)未免失实;泰陵之盛,焦泌阳(芳)又多丑正;神熹之载笔者多宦逆奄之舍人;至于思陵十七年之尤勒惕厉,而太史遯荒,皇成烈焰,国灭而史亦随灭,普天心痛”④。谈迁“窃感明史而痛之”,发誓要写出一部信史留传后世。他集群书,披阅采摘,一方面考诸皇明实录、宝训,以证《明实录》之是非;另一方面博稽诸家著作,订正群言。经过三十多年辛勤笔耕,终于“集海盐(郑晓)、武进(薛应旂)、丰城(雷礼)、太仓(王世贞)、临朐(叶向高)诸家之书凡百余种,苟有足述,靡不兼收,勒为一编,名曰《国榷》”⑤。明天启六年(1626年)初稿撰成后,谈迁继续收集史料,对原稿进行不断的修改和补充。不料,明朝灭亡后,《国榷》原稿被窃,谈迁不忍国亡史亦灭的悲惨结局,再一次投入全部精力进行《国榷》的重写,并前往北京查找崇祯朝的邸报,寻访故人旧事,补写崇祯、弘光两朝历史。“残编催白发,犹事数行书”,谈迁在有生之年终于写成了《国榷》这部内容丰富,首尾连贯的明代编年史。
《国榷》成书一百多年后,又诞生了一部私人撰写的明代编年体史书《明通鉴》。作者夏燮生活于清代中后期,这是个中国由封建社会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过渡时期,清政府在内忧外患的冲击下,已变得衰微不堪。鉴于国势陵替,许多仁人志士纷纷举起“经世致用”的大旗,号召人们从繁琐的乾嘉考据学的领域中走出来,把目光投向现实社会,以挽救危机日重的中华民族。他们大胆地闯入清政府严加控制的史学领域,尤其致力于明史的研究,希望通过对明季历史的研究,为清政府寻找一条治国之道,夏燮便是这些具有高度民族气节的学者之一。夏燮自幼便在他的父亲,清代著名学者夏銮的指导下研习传统经学。后来,他不仅精通音韵学,还“兼深史学,留意时务,持论宏通”⑥,即使在为宦地方之时,也是“公事暇,研心著述”⑦。夏燮一生勤于学问,著述颇丰,尤以史学成就为大。《中西纪事》、《忠节吴次尾先生年谱》、《明通鉴》便是其留给后代的史学著作。
官修《明史》被清政府视为圭臬,夏燮敢于对此书提出疑义。他在《与朱莲洋明经论修〈明通鉴〉书》中,将《明史》存在的问题归纳为十个方面,主要是:修《明史》者“半系先朝遗老,亡臣子孙,其中或以师友渊源,或因门户“嫌隙”,难以做到叙事公允,失实之处在所难免;编纂者摒弃私家著述,湮没了许多珍贵的史料;明朝历代《实录》多有失实之处,而修史者却未加详考,“率以窜改之实录阑入其中,殊非信史”;南明历史,《明史》缺而不书;《明史》还存在“叙事参错,而先后次第不明”等诸多问题。为此,夏燮认为:有明一代之事“非《通鉴》不足以经纬之”。于是,他倾注了“二十余年精力,实始于参证群书,考其异同,有疑则阙,择善而从,去取既明,然后敢下笔编次”,终于写成《明通鉴》。
谈迁初纂《国榷》,乃因明朝历代《实录》“作者非一人,繁简予夺之间,失得相伴”,而“野史家状……往往甲泾乙渭,左轩右轾”⑧,“见闻或失之竦,体裁或失之偏,记载或失之略,如椽阙焉”⑨。明亡后,他身谒明陵,继补明史,不忘故国之心,昭然可见。夏燮在《明通鉴》中,对有明一代的治乱兴衰,探本求源,全面展示了明代社会矛盾的发展过程,总结了明代兴亡的经验和教训,希望能为腐朽的清王朝提供治世之良策。二人写作目的虽不尽相同,但由于他们皆能发扬我国优秀的史学传统,客观公正地注视既往岁月,因而在他们的著作中所体现的求实求真精神,数百年来,一直熠熠生辉。
二
谈迁和夏燮在各自的著作中都投入了大量的心血,然而由于他们所处的时代不同,写作目的不同,尽管同是关于明代的编年体史书,却是长短互见,各有千秋。
首先,谈、夏二人在史书的编纂体例上各有创新。
《国榷》全书共一百零八卷,卷首四卷综述各项制度,分为大统、天俪、元潢、各藩、舆属、勋封、恤爵、戚畹、直阁、部院、甲科、朝贡等门,为人们阅读《国榷》提供了一条条较为清晰的线索。这种卷首开列全书主要脉络的方法,是以往编年体史书未曾使用过的,它完善并丰富了编年体的编撰。而夏燮在《明通鉴》中既注意完整地记录历史,又能巧妙地将清政府所忌讳的史实编入史书之中。为了详细记载朱元璋建立明王朝的经过,而又避免过多地涉及元代史实,《明通鉴》则以《明前纪》的形式加以叙述,成为该书的第一个组成部分,“凡此皆以元纪年,非关涉明者不书”⑩。《明通鉴》的第二部分《明纪》为全书的主体,记载了从洪武元年(公元1638年)朱元璋称帝至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的历史,整个明朝的兴衰治乱、政治经济无不囊括其中。1644年5月以后,隅居江南的南明政权仍坚持抗清,直到1661年才彻底失败,这段历史成为清朝统治者严加控制、禁止人们涉足的领域,夏燮则以《附编》的形式将其载入史册,“凡此皆取有关明事者书之,亦别为卷目”(11),以清纪年,避开了清王朝的禁忌。《明通鉴》由《明前纪》、《明纪》、《附编》三部分组成,完整地再现了明代历史。夏燮对自己的这一创新颇为得意,称之为“前此《通鉴》未有之创例”(12)。
谈迁、夏燮二人十分重视对史料的考证工作,而夏燮考辨尤勤,他借鉴胡三省注《资治通鉴》的方式,将《考异》注于正文之下,成为一种叙事与考据并举的写史方法。这里试以谈、夏二人述考明初一大疑案——建文帝下落为例,以显现出二者考证工作的异同点。
在明人所著的众多史学著作中,靖难之役结束后,对建文帝的下落有多种不同的观点,对于这个扑朔迷离的案件,谈迁在《国榷》中载道:建文帝获悉朱棣进入京师的消息后,“徘徊无所出,乃火其宫,马皇后自燔死,……而上(建文帝)急时欲自杀”,在此危急关头,太监王钺取出了太祖高皇帝置放于奉天殿的铁箧,内有剃发器具、度牒等物。于是,君臣数十人皆发出逃(13)。谈迁的这种剃度出逃之说主要依据是《致身录》、《从亡随笔》等书籍的记载。谈迁同时还罗列了崔铣、王世贞、李维桢、冯时可、袁懋谦、郭子章、何乔远、顾起元、陈继儒、高岱、朱国桢、钱士升、史继阶等十三人所持的不同观点,由于缺乏进一步的考辨,难以令人信服。夏燮在《明通鉴》中则作以下记载:“上(指建文帝)知事不可为,纵火焚宫,马后死亡。传言‘帝自地道出,翰林院编修程济、御史叶希贤等凡四十余人从’”(14)。在《考异》中,夏燮详细地考辨了几种具有典型意义的说法:《明史稿》依《明太宗实录》所载,认为帝、后俱崩;官修《明史》预为逊国张本,惟云“帝不知所终”;《御撰通鉴纲目三编》、《御撰资治通鉴辑览注》则两存其说;至于时人的看法,更达数十百种之多;各家之言,“皆历历可考”,难以定夺。在这种情况下,夏燮“不曰‘自焚’,亦不曰‘崩’,仍从逊位为词,而逊位以后之事悉阙焉,庶几纪实存疑为两得之”(15)。两相比较,夏燮对莫衷一是的观点所进行的严密考证及留有余地的记载,应当比谈迁简单的定论高明得多。
其次,谈迁、夏燮二人都十分注意广泛地收集资料,尤其值得称道的是他俩审慎取舍明季野史的态度。
喻应益在《国榷》序文中说谈迁“集诸家之书百余种”,以此足见《国榷》引用史料之广泛。吴晗先生在其《谈迁和〈国榷〉》论文中曾详细统计了《国榷》第一卷至第三十二卷所引书籍的作者,在这三十多卷中即达120余人,可见谈迁引用材料之丰富,以致《国榷》全书的字数比《明通鉴》多达一倍。《明通鉴》的史料主要来源于《明史》、《御撰资治通鉴纲目三编》,兼采其他稗官野史数百种。对于那些被统治阶级称为“多所污蔑,不可尽据为实录”的数量众多的私人历史著作,谈、夏二人都很重视,在应用这些资料时采取了谨慎的态度。谈迁将收集到的各种史料互相校证,信者从之,不信者弃之。夏燮曾说:“谓野史不可信,则正史何尝无采自野史而折衷之者,安见登之正史遂无传闻之误乎?”(16)因此,对于野史中“事有鉴于得失,义有关于劝惩,虽稗官外乘,亦择而书之”,“择野史之确然可信者,参之《明史》及《明史纪事本末》等书,入之正文,而以杂采稗乘疑相参者,夹行注于其下”(17),这就是《明通鉴》中的《考异》部分。关于甲申之变,由于“正史语焉不详,所谓殉难诸臣,亦多遗漏”,夏燮便“博采《北略》、《绥寇纪略》及甲申以后之野史”以书之(18)。在《附编》中有关南明史实的记载,他引用了计六奇的《明季南略》、钱澄之的《所知录》、王夫之的《永历实录》等多种私家著述,以求全面反映南明历史。
尽管谈迁和夏燮都知道众多的野史家乘之中,存有丰富而又宝贵的史料,也深知明季“野史如林,率多燕郢传讹之说”,且“明人恩怨纠缠,往往藉代言以侈怼笔”,因而在利用这些资料时都能坚持“芟其不可信者而信其所可信者”的态度(19)。总之,《国榷》和《明通鉴》的作者在引用史料、采摘史实时可谓英雄所见略同。
再次,史论评论皆为谈迁和夏燮所长。两者相比,谈迁更能客观地评价明代历史人物、政治制度及历史事件,这与其保存一部明代信史的写作目的是分不开的。明朝江南的粮长制至中后期破绽百出,危害日深。谈迁大胆批评道:“近县令入觐,例粮长二人随之,其实从役代应也。国初,每里令役,大邑且四五百人,费于何藉?虽上不时召对,间有旌拔,然民劳已剧,不若休息于田里也”(20)。夏燮则把《御批历代通鉴辑览》中对粮长制的评价作为自己的观点。因他作为清政府的官员,是不敢,也不可能彻底反对《御批历代通鉴辑览》中的官方意见的。尽管如此,夏燮对许多史实还是有他独到的见解的。如《明通鉴》卷九论解缙道,“明之解缙,其才有似于贾谊,其得君有似于魏征”,然仅“以冗散之恣,改授御史”,“然而十年著述,冠带来廷,则太祖方欲老其才以为子孙之用,而岂知知人之难,仅得之于方孝孺而不免失之于解缙乎?”此种评价实为寓论于史,史论统一。夏燮自称《明通鉴》“取记事而已,固不敢操笔削之权”,用“义取简明,不主褒贬”的手法对历史事件“考其事之本未,则事之是非自见;听其言之公私,则其人之清流浊流自见”(21)。
又次,谈迁、夏燮继承了我国史学秉笔直书的优良传统,并努力付诸实践。
黄宗羲在《谈孺木(迁)墓表》中曾赞扬谈迁“按实编写,不衔文采,未尝以作者自居”的写史态度。正是在直书思想指导下,谈迁在《国榷》中客观地记录了明太祖杀戮元勋宿将等官修史书所讳言的史实,并对《明实录》中那些开国功臣亡故的原因一一进行分析,指出了《实录》中的避讳之处。满洲贵族入主中原后,极力掩盖祖先的真实历史,而谈迁在《国榷》中详细记录了满族的发展过程。如:永乐元年(1403年)十一月条目下有“女真野人头目阿哈出等来朝,设建州卫军民指挥使司”的记载(22);永乐八年(1410年)八月条目下有“建州卫指挥使释家奴为都督指挥佥事,赐姓名李显忠”的记叙(23),而释家奴则为阿哈出之子;十二月条目下又有“设兀烈河、朵儿必河、木里吉、卜鲁、兀乞塔河五卫”的记录,而这五卫所管辖的民众则为“女直野人”(24),这些珍贵史料,道出了满洲祖先原为明朝附属的历史真象。夏燮在写《明通鉴》时,有关明史的资料已被大量发掘整理出来。他在《明通鉴·附编》中如实地记录下为清廷所严禁触及的史实,也表现了敢于秉笔直陈的气魄和胆识。夏燮多次强调“直书其事而得失劝惩寓焉”。他在《明通鉴》中引述了雍正皇帝评价史可法的上谕:“夫可法,明臣也,其不屈,正也。不载其语,不有失忠臣之心乎”(25),全面叙述了史可法在弘光朝的活动及史可法在顺治元年(1644年)九月致清睿亲王多尔的书信。此外,还大量记录了许多南明忠臣及抗清义士的反清之举,甚至对官修《明史》不为抗清义士张煌言立传提出批评:“(张)煌言之受命于杭城,与文信国(天祥)之就刑于西市,先后同揆,而《明史》不为之立传,宁毋贻刘道源失之瞠目之讥乎!”(26)寥寥数语,实、识均在其中了。
在浩如烟海的明代史籍中,《国榷》与《明通鉴》都占有极重要的地位,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洋洋洒洒几百万言的《国榷》所含内容十分丰富,尤详于明清易代之际及满族之祖先建州史实,后人在研究满洲的兴起及清军入关前后等诸多历史问题时,不能不参考《国榷》。夏燮坚持“年经事纬,此史例之大纲”的写史原则(27),对每一个历史事件都详考其时间先后。同时他身为清政府官员,又有条件收集到大量的诏令、奏折、文书等原始资料。因而,《明通鉴》中关于明代政治、经济、法律、文化、军事等各项制度的记载可信度较高,为后人研究明代的典章制度提供了宝贵资料。
注释:
①谈迁《枣林诗集》附录,钱韩伟《谈孺木先生传》。
②④黄宗羲《梨州遗著文集》卷三《谈君墓表》。
③⑧《国榷·自序》。
⑤⑨《国榷·俞应益序》。
⑥《清儒学案》卷一五五。
⑦《当涂乡土志》卷二。
⑩(11)(12)(15)(21)(27)《明通鉴·义例》。
(13)(20)(22)(23)(24)《国榷》卷十二、九、十三、十五、十五。
(14)《明通鉴》卷十三。
(16)(17)(18)(19)夏燮《与朱莲洋明经论修〈明通鉴〉书》。
(25)(26)《明通鉴·附编》卷一下、卷六。
标签:明史论文; 国榷论文; 明通鉴论文; 明朝论文; 中国古代史论文; 历史书籍论文; 明实录论文; 谈迁论文; 夏燮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