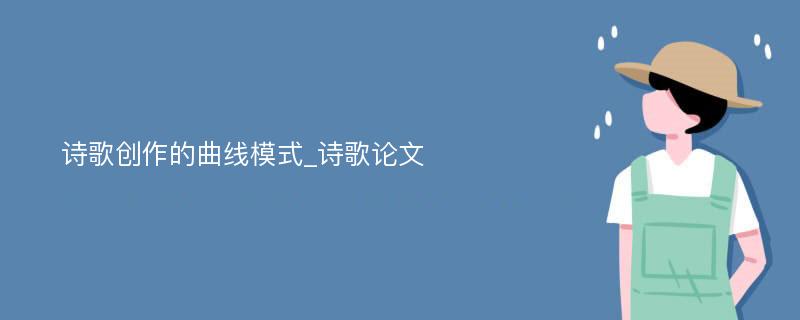
诗意创造的曲线图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图式论文,诗意论文,曲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诗歌是由语言构筑、在表意上具有很强空间性特点的艺术形式。从体制上着眼,这种看似简单的文体其内在构成却是相当复杂的。诗,不直接传达思想,这大概已是不成问题的定论。而情感因素居于主要地位的诗,一般说也不直接传达情感。中国古代的意境说为我们认识诗歌艺术规律拓开了一条新的路径,其实意境就是从空间的角度对诗意创造的解释。诗人是用语言材料造出境界,通过这种空间的方式作用于读者。情感的传达也是这样,有人称为“感染”很有道理,因为情感离不开艺术氛围,它是一种“物化”形态。诗歌表意不是直接的,过于直接就会损害艺术的效果,诗人必须充分认识这种特殊性。诗意的创造是由空间中的许多点构成的。这些点既不在一条直线上,也不在一个平面上,从总体观照,它是一种艺术的曲线图式。
一、诗歌语言的跳跃与曲线图式
一般的书面语言都具有表意词语的直线递接特点,词与词、句与句,甚至段与段之间的联系都是比较紧密的,这也是一篇文章中“章法”所要求的。诗歌的语言则不然,尤其是句子之间的递接常常因中断而出现较大的空白,从语言表达的角度讲,就是所谓的“跳跃性”,它在诗歌的思维方式中比较重要,具有鲜明的文体特性。
诗要创造意象、创造意境,与小说、散文相比有着特殊的语言方式。小说和散文虽然也是塑造形象,也要造情造境而形成一定的艺术氛围,但毕竟是以叙事为主,注重因果联系,直线递接特点比较突出。而诗歌的叙事性因素较弱,行文中多是描写、状物的成分,基本上属于描述性文体类型。长期以来,诗歌形成了自己的语言模式,不很好地了解这一点,就很难从根本上认识诗歌的思维逻辑规律。《诗经》开首中的“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前两句为一个整体,写的是鸟及与之相关的环境,两句的递接性比较强;后两句为一个整体,写的是人物之间的关系,也有比较强的递接性。但从前两句与后两句的关系看则是很微妙的,二者之间是由写鸟到写人的转化,不是直线的递接。杜甫那首有名的《绝句》更是如此:“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全诗不是围绕一个统一的核心意象来表述的,四句是四个方位,每一句中都有一个核心意象,“黄鹂”、“白鹭”、“雪”、“船”之间不存在着因果性的必然联系,更无语词间一线贯穿全诗的递接脉络。但是诗的表达却不因此而散乱,四句从四个方向构成了一个统一的立体空间,诗具有很强的整体性。我们说这首诗的跳跃性强,是从表述对象的转换来看问题的,一句一个主要对象,每句之间都留有空白。还有词与词的跳跃,象马致远的“枯藤老树昏鸦”,三个词就是三个意象,呈并列式,三者之间均有空白,标示确切关系的词语被略去了。诗歌语言的跳跃性,若从表征看是切断了表意整体间某些部位的直线递接,切割之后的各个部分具有相当的独立性,呈并列状态。若从内在意义讲是削减了某些表达程序,改变了语言的内在结构,拓展了诗意的空间性,反而进一步加大了语言的表意含量。
那么我们应当注意到,语言表达的直线序列被打破之后,意义的延伸已经不能保持原来的平稳状态,因断裂而处在不同的层面,出现了起伏和波动。仍以杜甫的《绝句》为例,这首诗语言跳跃性的标志是每句都有一个核心意象,因而失去直线联系而有了不同的空间,改变了直线语言序列表意的稳态局面。句内包含的意义与其他句没有必然联系,各处在不同的层面之上,于是意义的曲折波动造成一种回旋效果,整个思维过程所呈示的轨迹是曲线图式。一般说,诗歌的语言表意特性是取“象”造“境”,选取比较繁复的“象”构成诗意整体系列,又因“象”与“象”之间不同的组合关系,所以表意的过程就成为一种“波动式”,空间便开阔起来,诗意便有了更大的回旋余地。从曲线图式中,我们除了意识到的一些词、句间的鲜明并列关系之外,还必须注意到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每一句中的组合关系具有的起伏性;二是那些并列关系间的“空白”所形成的复杂性。
诗句中的组合关系是诗歌语言创造诗意的关键性因素,是万万不能忽视的问题。一个诗人语言内功、艺术思维潜能的强弱,很大程度上是看语词间精微组合关系的效果如何。在诗歌创作中,虽然这是一个近似于局部性的问题,但是它却可以相当充分地反映出诗人思想、情感、想象等许多方面的基本素质。比如“窗含西岭千秋雪”一句,在组合上诗人是调动了相当大的思维动势的积极性的。“西岭”之“雪”可以说是极为寻常的事物,从其自然性来看并无新异的特性,如果仅以这种自然性入诗就不会焕发出强烈的诗意光彩。杜甫不愧是伟大诗人,他在组合关系上动用了绝妙的艺术手段。他把“西岭”和“雪”均以主观的方式纳入的“窗”中,却在暗中不露声色地把“窗”变成了主动者,“西岭”、“雪”为“窗”所“含”。自然之物的“雪”一旦为“窗”所框住,一下子便升格进入艺术之境了。不仅如此,诗人在这种空间性沟通的基础上,还把诗意的维度引向了时间的境遇,“窗含西岭千秋雪”产生了强烈的灵视效果,真如刘勰所说“思接千载”“视通万里”了。巧妙的组合关系造成语言表达的起伏优势,使诗意空间进入多维而敏感的艺术美感的程控之中,更大幅度地提高了诗歌的美学品位。
诗歌语言跳跃所留下的“空白”,并不是诗意的真空地带,它是诗人在诗意创造过程中的一种表达技巧,是为读者凭借诗意内涵向更深远的理性感悟境界延伸所留下的“断”的余地。这种空白是诗歌表意复杂性的一个重要方面,它的优势是使意象之间意义的确切联系中断,造成一种模糊的艺术氛围,进而加大象征和暗示的强度。象“枯藤老树昏鸦”,从文字看是三个意象紧紧连接在一起,而实质三个意象间的“空白”是显而易见的,如果这样排列“枯藤老树昏鸦”或许更为合理。这三个意象的独立性很强,具体关系并不明确,因为它们中间并无关联的词语,这样更加大了读者审美判断选择的余地。
其实,不论是诗句中的组合关系还是语言跳跃所留下的“空白”,都是诗意创造曲线图式的组成部分,都是从各自不同的角度来实现对诗歌独特文体内涵的丰富和强化,这一点应当引起诗人的重视。
二、直觉感应的物质化与诗意表象
艺术直觉可以体验世界和人生的许多微妙性内容。直觉感应与灵感、想象等快捷性心理动势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诗意创造的曲线图式在任何时候都离不开直觉,这种用灵魂拥抱世界的方式可以为诗意的构成提供动人的表象材料。
从根本上讲,曲线图式是诗歌精神的物质化行为,是从诗人的内在思维形式到诗歌的语言表现形式的“外化”过程。这种由虚到实的转化,实质必然存在着诗人面对理性经验的过度介入的限制,否则诗歌艺术本质乃至整个诗歌文体都将陷入异化。所以诗人的创作必然要时时求助于直觉感应,向直觉寻求更多的可感性物质因素。
诗歌这种抒情性很强的文体区别于一般叙事文体的重要特征是对事物客观性的排拒。出于强化抒情的需要,一切表象内容都被纳入诗人的主观性范畴,并以此创造必须超越于客观现实的另一个世界。任何时代,诗都必须突破客观性物质现实的包围,而进入主体精神创造自由的高度,这决不是诗人狂放而漠视存在,这实在是诗歌文体特殊性的要求。诗从直觉角度对“物质化”青睐,又同时特别重视“感应”这一关键性环节。物质进入诗意的图式必须是“感应”之后的物质,其特征就是消解客观性,然后进入意象和写意的范畴。在此意义上讲,感应是一种严格的提取方式,是诗化过程所不能缺少的一关。在诗歌创作中,我们可以把诗人的物质性选择作为较宽泛的直觉内容来看待,这样就能很容易发现事物的客观因素被诗人主观情绪消解和重构的合理性。我们且不说李白的“白发三千丈”、艾略特的“荒原”,就是郭沫若的“炉中煤”、艾青的“太阳”、臧克家的“老马”都已经超越了客观的实在性,若在一般叙事文体中就是“荒诞”或“魔幻”之类,而在诗歌文体中只不过是惯常的方式。
强调直觉感应又必须注意到另一个方面:我们说诗对物质客观性的排拒并不是否认诗人原有的观念性内容在诗意创造中的作用。如果没有诗人原有的观念性内容而仅靠直觉感应,诗意的构成就是不可想象的,也就难以实现诗歌表意的深度。既然我们承认诗是一种创造行为,承认诗意的思维图式具有复杂性,那么我们就必须充分认识这种观念性内容是一切创造行为的基础。它的加入有着很强的必然性与合理性。我们只不过是反对诗人原有的观念性内容以理性的抽象形式“裸露”出来,反对破坏诗意创造的曲线图式。当我们强调直觉感应物质化重要性的时候,其实自然地包含着它对诗人原有观念性内容进行诗化整合的一面。在诗意创造过程中,二者缺一不可,而实质二者又是不可能截然分开的。许多诗人的创作都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下面引录卞之琳那首著名的《断章》来分析这个问题:
你站在桥上看风景,
看风景人在楼上看你。
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
你装饰了别人的梦。
这首诗读来不难感到一种强烈的哲学思辨意味,诗人的原有观念性内容在诗中的演绎是显而易见的。如果没有长期思想文化积累为底蕴,仅有瞬间的直觉感应是难于有这样的理性穿透力的。但是,我们之所以说《断章》是一首好诗,决不是因为看中了诗人的思想积累的深厚,更重要的是诗人在诗意创造的过程中,较为完美地建构了一个曲线图式,他把直觉感应的物质性内容与原有的观念性内容统一在一起,实现了直觉对理性的诗意整合。《断章》的强烈哲学思辨意味来自两个方面:一是理性的推论;二是意象运动的内涵。很明显,诗的表现借助了推论的方式,诗的整体框架其实是一个推导的过程。我以为这是诗意创造中一个十分危险的临界点,如果稍不慎重就会导致全面失败。但是反过来说,假如诗人不采取这种铤而走险的方式,在这样短的篇幅中很难实现哲学高度的提升。值得肯定的是,诗人在理性推导的框架中没有陷入“理论”的谷地,而是在意象的运动中又找到了艺术的自足。
在诗意创造的曲线图式中,优先强调直觉感应的“物质”意义,这是符合诗歌艺术规律要求的。关于“曲线”内涵的解释应当包括这样一个内容,这就是非理念的表达。诗绝然反对以理念的方式直奔思想的理论形态,而要竭力通过“物质”表象的具体呈现来创造一种艺术的空间“宽度”。这种“物质”是感应的结果,它们显像在诗中,就是所谓的诗意表象。在整个诗意图式中,“象”具有具体的直观性这一主要特点,但在表意上并不直通于抽象的理性,而是有一定的弯曲度,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曲线”的基本含义。又因这种“弯度”的作用,“象”不具有传达理念精神的确指性,所以“象”虽然来自传统的“概念”,但它实现了艺术的自足之后已进入了写意的状态,对传统的“概念”则是一种大幅度的超越。“象”具有了多义性的特征,对于“认识”来说它不是“确切”的,但对于诗意的构成它又远比“确切”更有意义。
直觉感应的物质化是诗歌构思及艺术表现的重要契机,诗意的创造,尤其是灵感的闪现及想象翅膀的飞腾都离不开直觉感应的“定影”,那么这种“物质化”过程的结果就是诗意的表象。诗意的表象不是诗的意象,意象是诗意聚结的核心,它具有很强的内在性。表象是诗歌作品中全部诗意外在的直观性具体事物,具有“可视”的特点,任何诗意的构成都不可能离开表象,它是曲线图式所依赖的最基本材料。诗人曹宇翔的《大河》─诗有两节是这样写的:
大河,我把你千古涛声披在身上
踏着黎明大道
继续流浪
用船歌中的一瓢清水养活我
把我的心
安顿在,河面滚滚而来的太阳里
前一节的诗意表象是“我”这个人身披涛声在路上行走(流浪);后一节的诗意表象是“我”这个人凭歌中的“水”活着,而且把“心”放在河水中的太阳上。从表象内容看,如果用一般的思维方式来理解就很难得其要领,但用诗的特殊思维方式就很容易理解了。诗人是用写意的方式把人的“我”与“大河”一体化了,由河的流动到人的流浪,是取形态之似。“船歌”则是渔人的生存方式的指代,而把“心”安顿在“太阳里”是一种深情的寄托和暗示。这两节诗的诗意创造确实相当曲折,意象间的联系是比较委婉的,这是比较明显的曲线图式。当然,诗意曲线图式的本质是由意象的内在意蕴构成的,从上例是不难看到这一点的。但是,意象的内在意蕴不可能独立进入图式,它不可能离开表象而存在。表象是意象的物质外壳,意象的内在意蕴是凭借表象的形态进入图式而完成表意的。象《大河》的内在意蕴无论多么深刻,如果不通过人与河流等一系列表象内容的实在性,都不可能以曲线图式进行表达。
诗意表象对于诗歌创作来说是特别重要的,表象也有一个积累的问题。诗人写诗所谓积累素材备创作之需,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积累表象。诗人要在生活历程的所见所闻中采撷直观的物质性内容以丰富自己,一旦进入创作,这些表象内容就会纷纷涌来撞击心灵,使想象的翅膀活跃起来,最后凝聚为整体诗意,进入艺术表现的曲线图式。
三、诗的变形与写意的空间维度
变形是诗歌文体的又一显著特征,是诗意建构的一种主观性强制手段。在诗学的范畴,变形至少包含这样两种形式:一是局部的变形,这主要是指诗意创造过程中的一种表现手法;二是整体的变形,这主要是指诗歌文体的一个鲜明特征,即诗人主观精神在诗意创造中的能动性。我认为更为重要的是后者,对于诗歌的发展来说,整体的变形具有深刻的哲学意义,它是一种宏观性的制导因素。
对于诗歌文体来说,表象的内容过于实在,就可能在一定程度上破坏诗意效果。诗歌的传达方式在本质上更接近于人的理想精神,变形正是适应了把诗歌由生活的物质性层面向理想的精神性层面提升的需要,可以说这是一种诗歌观念的确立。
从诗意创造的曲线图式角度看问题,变形是一种曲折的表达,是改变表意的由起点到终点的“直线”形态的作法。下面是台湾诗人余光中的名篇《乡愁》:“小时候/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我在这头/母亲在那头//长大后/乡愁是一张窄窄的船票/我在这头/新娘在那头//后来啊/乡愁是一方矮矮的坟墓/我在外头/母亲在里头//而现在/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我在这头/大陆在那头。”这是一首总体格局极为简单,而构思与表现又是特巧妙和精彩的诗。诗人居高临下,能够对“乡愁”进行宏观的俯视,并对其作了总体的变形处理。首先是由事物本体到喻体的变形,“乡愁”是一种情绪和心态,是无形之物,诗人的暗喻的方式把无形转为有形,把抽象之物变为具象之物,于是“乡愁”成了“邮票”、“船票”、“坟墓”和“海峡”等较为直观的意象。其次是诗人把渺渺茫茫、缠缠绵绵的“乡愁”情绪从思念这个角度变形为一种较为实在的“距离”。变形使“乡愁”这种情绪出现了艺术的弯度,不是由起点到终点的直线的“乡愁”表现,而是拐到了“邮票”、“船票”、“坟墓”、“海峡”等具体事物上去,使诗意的创造完全进入了艺术表达的曲线图式中去。从这里我们看到了变形是诗歌艺术的一个关键性运动机制,它把“乡愁”由虚变实,从生活层面推入了艺术层面。特别是诗人在变形的过程中以距离的变化反差来强化诗意,象“邮票”和“船票”。从物质实体看,“这头”到“那头”几乎不足方寸,但从与之联系的实际距离看又可能不止千里万里。这种内外反照即造成了强烈的艺术效果,使本来平常的“乡愁”变得这样优美动人,这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变形,是变形使诗获得了文体自身的美学价值。
从变形的表征看,变形具有时空位移的性质,由时间空间的变化来改变事物原有的形态。象李白的“黄河之水天上来”,就是把在地上流淌的黄河位移到了天上,空间发生了变化。北岛在《古寺》中这样写:“逝去的钟声/结成珠网,在柱子的裂缝里/扩散成一圈圈年轮”,历史在视觉中演进,这也是变形,这种变形的过程主要体现为一种时间的因素,是时间的位移。从余光中的《乡愁》看,这种时空位移的因素就复杂一些,从“乡愁”到“邮票”也有空间因素,“邮票”是中介,要把它落实在外地与家乡距离这个空间中,然后才有位移的可能。那么从“邮票”到“船票”则是一种时间位移,因为意象中含有“小时候”或“长大后”的时间因素,但这种时空的位移对于变形机制来说,不可能仅仅是一种物理性位移,而必然是一种心理性位移。物理性位移是表象,具有形式的意义;心理性位移是内蕴,具有精神的本质性意义。舒婷《镜》一诗中的句子:“女人可以摔落月的色斑,如/狗抖去水/拉上厚窗帘/黎明湿漉漉的舌头搭上窗玻璃”,如果从表象看,女人“摔落月的色斑”转为“狗抖去水”,从“湿漉漉的舌头”看,似乎是这“狗”与“黎明”又构成了联系,这其中不乏空间的位移因素。但是,我们只有从心理变化的角度才能把握诗的意象本质,诗人从变形的失态中揭示人、特别是女人生存状态的某种尴尬。何小竹《鸡毛》一诗中的句子:“你望着雪山的时候/想起鸡毛/那柔软之物/雪山便从鸡毛的背上/日日消瘦”。由“雪山”到“鸡毛”的变形过程,我们也可以窥到某些空间位移的因素,且不说诗人以此蕴含的象征暗示之意是什么,我们只注意变形所标示的心理过程就够了。从“雪山”、“鸡毛”与“日日消瘦”的联系可以看到一个心理过程的“空框”,诗人未必愿意在“空框”中加进确指性的涵义。
前面我们曾提到变形是诗歌文体的一个显著特征,它标志着诗歌思维的一种总体倾向,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诗歌观念确立的大事。从强化主体意识这一点看,选择变形这一艺术思维方式是诗意创造的明智之举,在简捷的篇幅中,如果尽是客观性内容的复写,那么就很难在一个思维的短距离内造成反差强烈的碰撞效果,就会产生一种惰性,而不能激起情感的大幅度波动。诗歌之所以具有很大的抒情优势,与变形所强化的主观性有直接关系。
在涉及变形这个问题的时候,不能不提到诗歌表达的写意性。二者虽不是同一个层面上的内容,但在诗意创造的范畴内却常常是难解难分的,因为很多时候写意是通过变形才得以实现的。变形的主要目的是求得强烈、新异的效果,写意的主要目的则是求得精度、深度以及以小见大的容量。从这个比较中,我们可以看到写意对于曲线图式的空间维度有着关键性的作用。
诗意创造的曲线图式非仅仅处在一个平面之上,意象的生成总是向着平面以外的空间伸展。当然,构成曲线图式的空间维度有各方面的因素,也包括变形在内。但由于写意的方式主要指向意义的内在涵量,它所起的作用相对说更大一些。艾青写:“在北方/乞丐徘徊在黄河的两岸”,这是大向度的概括,它的容量远远地超过了写实的内容本身,这是一种写意的方式。如果仅从表象看,它似乎只是关于“乞丐”的简单信息传递,但把它的写意内涵揭示开来,就会发现一种整体性的象征在向诗的深处扩张。这里“乞丐”的意象已不是单一的个体,而具有了群体的意义,“黄河的两岸”则是以黄河流经的地方指代一个民族生息的大片国土。诗的实质是表现一个特定时代人民流离失所而没有正常生存条件的悲剧。如果放在诗意的曲线图式上来考虑,除了方位、乞丐行为和地域等内容形成的轨迹之外,还有隐含在“乞丐”、“黄河的两岸”两个意象背后的一种空间性内容,它改变了事物的平面维度,实现了诗意的立体性空间维度的拓进。写意提高了诗歌美学的品位,因此可以说它是诗歌文体的又一重要性征。
有些诗歌理论把诗归为直接抒情一类,这种表述是很不确切的,这是对诗歌抒情性以及抒情方式的简单化或片面性理解,没有反映出诗歌抒情特征的本质和全貌。在诗意图式中,不但不允许理念由起点到终点的直线形态,就是抒情也不允许这样。长期以来形成的意象、意境理论所倡导的诗意传达,包括抒情在内,都是折射方式而排斥直线形态。古今中外的大量诗歌作品证明,越是优秀的诗就越重视意象或意境的创造,都具有以曲线图式来抒情言志的特点。看李白《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一诗中的两句:“我寄愁心与明月,随君直到夜郎西。”诗的情感确实强烈,容易引起共鸣。但这也不是直接抒情,诗中几乎见不到直接表达情感的内容,倒是意象递接极为曲折,是典型的曲线图式。尤其是“明月”这个意象悬在空中,被诗借来当做传递媒介,先把“愁心”交给“明月”,再由“明月”转给遭贬的王昌龄,诗人竟不肯直接交给王昌龄!天上地下三点成一大折线,这大概不能叫直接抒情吧。
以上关于诗意创造曲线图式的描述,是对诗歌独有艺术特性的理解。曲线图式反映了诗歌表意的曲折性和复杂性,我力求通过这种描述来揭示诗歌诗意构成及传达过程的内在规律,并尽可能从语言的跳跃性、直觉感应的物质化、变形及写意的空间维度等方面把诗歌从文体角度与其他文学形式区别开来,以加深人们对诗歌本质的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