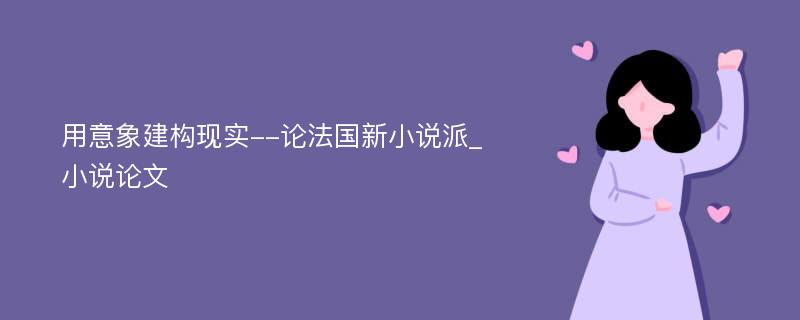
以图象构筑现实——论法国新小说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法国论文,图象论文,现实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提要】 描写作为无数可感性思维的形象实体的图象,是新小说派反映现实世界的独特方式,它打破了以往各文学流派在创作中形成的思维定势,深入抓住图象充分强调时空概念、增强对现实的表现力度这个核心,由此探究了新小说派以图象构筑现实的模式和内涵,给人以启示。
【关键词】 物体 图象 现实 时间 空间
在法国本世纪50年代,当阿兰·罗伯-格列耶的第一部小说《橡皮》由小说俱乐部和子夜出版社同时出版后,在这个对文学实验和文学演变一直持宽容态度的国度里,竟然引起了人们强烈的抵触;继而,他发表了《未来小说的道路》和《自然·人道主义·悲剧》等理论文章,更招致了公众持久的反对;同时,娜塔丽·萨洛特、克劳特·西蒙和米歇尔·布托尔的文学主张及其作品也在国内遇到很多反对派。在文学史上,这批作家被称为“新小说派”。虽然它的两个代表作家异乎寻常地取得了世界性声誉[①],但仍难以消除读者和评论家的责难之声。可以说,新小说派是本世纪争议最大的文学流派之一。一切的分歧实际上都是从所谓“读不懂”而开始并衍生出来的。新小说派作家致力于用20世纪中叶的艺术观念和小说读法去冲击那种从19世纪起,阅读小说中培养起来的欣赏趣味和阅读习惯,重新培养自己的读者群。因为,对这批作家来说,战后法国处于“怀疑的时代”,“资产阶级日益丧失他们的合法性和特权,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就抛弃这个阶级的有关本质的哲学依据。现象学逐渐进入所有哲学研究的领域,物理学发现了间断函数的重大意义,心理学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②]。社会现实是不稳定和浮动的,如同一个变化无常的迷宫,令人难以捉摸。故而,在他们看来,巴尔扎克时代的传统小说,只应作为继续创新的起点而不应再统治小说界。为此,他们就给自己的小说设下了一系列限制,并且有意识地拒绝通过艺术形式给读者提供某种明确、固定以至会滑向虚假的先验性意义。这种艺术革新——包括语言、形式和方法的革新固然是多角度的,但最终的革新仍然是文学原理中最难界定又无法逃避的基本问题,即文学与现实的关系以及如何表现现实的问题。笔者通过对无数次阅读体验的整理,认为理解图象、使用图象、掌握现实的图象表现,对研究新小说派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图象的现实表现
新小说派进行创作的契机和对象是图象,图象代替了艺术表现的对象——现实世界。小说家通过展现若干个经过精心选择的图象去完成对生活的诠释。
文学史发展演变的过程告诉我们,一个新的文学流派或思潮的形成,必然有其内外两方面的原因。因袭的文学观念和表达方式的反叛是其内因,外因则指文学所要描述和表现的客观对象,即现实生活。而现实生活又往往推动和促使作家对固有的文学观念进行重新深入的思考,最终嬗变成一系列新的文学形式和表达方式,新小说派的形成也莫能例外。我们有足够的理由认为,新小说派作家之所以运用以描述和展现图象为核心手段的新的表现方法和表现形式,除了主观上想创造一种新的写作手法外,对现实世界及其物体的重新认识和理解最终决定了他们的创新。
新小说派认为,由于时代错综复杂的发展,人们周围的现实状况失却了既往的确定性和明朗性,变得愈益晦涩游浮。因此,为了真实地表现生活,就势必采取一种有别于19世纪作家们把握世界的方式和眼光。新小说派着眼把握的是构成世界最为基本的单位,即客观存在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物体。他们认为,通过考察物体的存在形式,物体与物体之间的关系以及人观察物体时的精神活动,作家们有可能捕捉和更真实地把握现实生活。
在两篇被视为新小说派宣言的重要文章《未来小说的道路》和《自然·人道主义·悲剧》中,新小说派的首脑人物阿兰·罗伯-格列耶具体完整地阐述了他们这种把握现实的方式。
罗伯-格列耶从剖析传统作家所惯用方式的虚幻性入手,给自己和他的同道们指出了一条切实可行的道路。他认为,传统小说把种种“文学的外围心理学、伦理学、形而上学等等,自行强加于物体,掩饰着它们真正的陌生性质”[③]。这种陌生性质,就是物体的外形、运动和存在状况,是被一直漠视了的物体的“现实性”。无视物的真正属性,传统作家代之以人的“种种感情”,试图通过描述这些人为的感情来把握物体的现实性。比如,对于一片风景,不去描绘它的具体轮廓或基本成分,却大肆渲染它给人留下的庄严或宁静的印象。实际上,无论是庄严感还是宁静感,它们都不是物体的,而只能是属于人的,这恰恰是传统小说所认定的“深度”所在,这种小说的作用在于“开发”自然,以所谓挖掘物体的“深度”为基础。物我之间这种感情意义的交流,常常促使人将所有的感情都与物体联系起来,甚至延及一系列其它的感觉,于是,除了被我们所忽视的物之真正特性外,物似乎就可以容纳任何一种感情和特性。这种做法,“赋予任何事物以一种假冒的意义,也就是说,用一种或多或少带有欺骗性的思想感情的罗网,从内部去裹住某一种物体”[④]。在这种情况下,作家还怎么能真实地反映客观物质世界呢?更严重的是,这种方式也不利于真实准确地反映人类世界。连绵不断的以人易物渐斩地使人再也找不到有关自身感觉的真正起源。比如,是山庄严还是我庄严?庄严究竟是先在我之中还是先在我之外?这些问题都难以得到正确回答。
因此,新小说派已经不能在传统基础上来认识现在的世界了,必须从根本上否定那个“深度”。“事实上,今天有一种新的因素把我们和巴尔扎克,同样把我们和纪德、拉·法耶特夫人区别开来,那就是抛弃关于‘深度’的古老神话”[⑤]。有鉴于此,新小说派把握世界的独特方式,就是坚决拒绝任何形式的物我之间的感情交流,刷新描写物体的笔墨。要描写物体,作家“就必须毅然决然地站在物之外,站在它的对立面”[⑥]。摒弃任何自我幻想式的和物体接近的方式。对作家来说,他们面对的只是物体的光滑的平面,只有外形,既无灵魂,亦无价值,物就是物,而不是人的感情的对应物。同时,要注重“记录物与人的距离,物本身的距离,物与物之间的距离以及进一步强调只有距离,所有这些,也就是确认物是客观存在”[⑦]。在人的所有感觉器官中,只有视觉,特别是投向外形线条的视觉,才适宜于跟物体打交道。因此,小说家必须注重和信任自己的视觉效果,并将之在作品中准确地反映出来。
新小说派的这些主张,并不是像某些批评家所说的是在追求冷漠的“客观性”,恰恰相反,这是更高意义上的尊重人的表现,是“完全的主观性”。这种主观性体现在描述事物的不仅是“一个人”,而是这个人“在看,在感觉,在想象”,同时是一个“置身于一定的空间和时间中的人”,他“受着感情欲望的支配”,甚至“他的视觉常常变形,他的想象接近疯狂的境地”[⑧]。因此,事实上,新小说把物体的存在当作先决条件,以写物来表现人的复杂的内心世界,同时,新小说也关心和人在世界中的处境。尽管作家可以将物体描写得很仔细,但无论是真实的还是想象的物体本身,从未脱离于人的感知之外而显现出来。
由于尊重物体及其所属世界的原貌,新小说派就为其小说实验的图象表现提供了内在的必然性和广泛的可行性。无论是罗伯-格列耶的“物本主义”,萨洛特的“心理主义”,还是西蒙的“照像笔法”,最终都可以纳入带有总体创作特征的图象主义,布托尔也不例外。
“图象”一词,其实可以理解为一个合称,它包括作家们经常运用的照片、明信片、肖像、雕刻画、宗教画、群塑、连环画、画片、彩色说明书、风景等以及内心涌现出来的带有感觉和形状的心理幻影。这些东西,究其实质,是一种进入创作者内心的“符号”。德国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将符号界定为“所有在某种形式上或在其它方面能为知觉所揭示出意义的一切现象,尤其当知觉作为对某些事物的再现或作为意义的体现,并对意义作出揭示之时,更是如此”[⑨]。可以看出,符号有着两方面的内涵,其一,它是一种物质的呈现(能为“知觉”感知的“现象”);其二,它是一种精神的外观(能被揭示出“意义”)。用这一观点来审视频繁出现于新小说并不断流泻其中的图象,便可得出一个结论:这些经过作家挑选并作为无数可感性思维的形象实体的图象,并非无意义形式的体现,乃是以一种新的手段去揭示自然和生活,即追求“更高的真实意义”。
图象的物质性能触发作家的各种知觉,打动其创作欲望,并且作为一种实体的存在融入小说里;而精神上的意义则隐秘地藏匿其中,在各种片断的接续和生发中构成其独立的客观性,并与相应的世界意义呼应。对小说家来说,图象成了生活原型和创作者之间的中介,现实生活中的一切东西,都必须经过图象的过滤,再被组织进各种图象,然后以类似片断画的图象表现出来。实际上,被新小说派作为艺术表现对象的图象,代替了传统小说中的世界、生活、情景、人物和细节等等概念,也代替了连贯的情节和故事。图象汇聚了作家在创作状态中纷纭而至的各种各样的创作因子,是作家各种想象活动的触发点和落脚点。在布托尔的小说《变》中,传统意义上男女相爱的故事演化成了世界的一种无所不包的图象效果。这个世界在小说中是由罗马的景物、古典文化意象和火车等构成的,借助于这些有着图象效果的东西,作家找到了艺术通向生活的最佳形式。同样,这种现象在西蒙的创作中也大量存在,他几乎完全排除了传统小说中的叙事手法,几乎自始至终都是对画面的描述。他在总结创作经验时说:《弗兰德公路》、《华丽大厦》,还有《家史》,还有……下面这些篇幅,都是这样写出来的:产生于用我喜欢的某些画面编造点几故事的欲望。这些作品篇篇都是以我起初未曾料到的方式写成的,因为开头的少数几张画,在写作的过程中随着结构的需要经过了挑选和增补。”[⑩]
通过图象这种对现实的“零碎”的片断式的表现,新小说力图真实地去反映这个千变万化的世界的原貌。然而,零碎和片断并非等于杂乱无章和随意安排。实际上,每个图象的出现和安排都受制于作品最后的目标,受制于作品的内在联系。
为了对新小说派通过对物体图象化的描述来反映现实生活之方法有进一步的认识,我们不妨来具体分析罗伯-格列耶的代表作《窥视者》。
这部小说出版于1955年,获得当年的法国“评论家奖”,是新小说派作家的第一部获奖作品。它的故事情节十分简单:一个旅行推销员马第雅思回到他度过童年时光的小岛,兜售手表。在挨户访问中,他得知全岛居民几乎都对一个13岁的行为不端的牧羊女雅克莲感到不满。这天,雅克莲在海边悬岩处放羊,马第雅思骑自行车经过,将她强奸后推入海中。尸首被发现后,马第雅思回到出事地点毁灭罪证,却发现他的犯罪经过已被雅克莲的男友于连窥见。然而,马第雅思却继续若无其事地在小岛上又住了两天,并不断地自己欺骗自己,用自我意识把时间封闭起来,去涂抹凶杀的裂缝,然后乘船返回陆地。
分析故事情节包含的道德和法律意义并不重要,因为小说的着眼处并不在此。有别于传统的探案小说和犯罪小说的是:在《窥视者》中,作者并没有在作案动机和作案过程上着任何笔墨,甚至可以说,尽管小说有着所谓的探案或犯罪小说的故事框架,但是在具体描述中却少有侦探小说应具备的基本要素。作者有意在小说中舍去了那些传统成分而用图象化描写手法为我们构筑了一个真实的客观物质世界。这个世界是由这样几个层面组成的:第一层面是海、海浪、海鸥、轮船、汽备、码头、防波堤、灯塔,它们以其独立的存在组建了马第雅思3个小时的船上生活;第二层面是各种大同小异的房屋、家具、广场、咖啡店、酒店、各种大路、小路和叉路以及植物,它们构成了他在岛上两天零9小时的生活;第三层面是糖果、彩色糖果纸、香烟、香烟头、一段绳子、90只手表和手提箱以及租来的自行车,它们是马第雅思的身边物,时时提醒着他的行动和存在。作者对这三个层面的详细描述是贯穿整部小说的主线。整个小说内容是由对这些物体的反复描述构成的。物的重要性在小说中显而易见,它们存在着,并且印证着小说的情节发展和人物行动,把各种可能性的结果导向一个最终的归宿。比如,雅克莲是怎么死的?是自杀还是他杀?凶手是谁,是马第雅思,是于连,还是岛上另外一个居民?对此,国内外学者至今各执一端,而作者醉心于消灭故事,对犯罪的动机、场面甚至行动,在叙述上作了空白处理。而我们在此确认雅克莲是被马第雅思强奸后推入海中致死的,证据是作者反复着重描写的物品:遗落在出事地点的彩色糖果纸、三个烟头和手提箱中那丢失的绳子。尽管马第雅思用无数的心理幻觉来否定自己作了案,但这些作为证据的物品和它们之间的联系已经说明了一切。虽然作者从正面省略了作案经过,但这些物品却非常完整地连接起了读者思维的逻辑线条(这线条曾被作者故意扯断了)。
另外,作者对物的具体描述是将其融入绵延不绝的图象描写之中加以突出。而在每个图象中,出现最多的对物的描写文字是数字、几何学和物理学等方面的术语,它们限制、说明物体的存在。作者认为,这是表现物体的最好方式,最能赋予物体以本身的确定性。我们引用一段在全书中最不具“技术性”色彩的文字来增加点感性认识:
轮船似乎不再向任何方向前进。可是船尾传来水流被螺旋桨猛烈搅动的声音,离船已经很近的防波堤,比甲板高出12公分;现在一定是退潮的时候。轮船即将停泊的那个码头露出了下半截,这部分桥面比较半滑,被水浸成了褐色,一半印满绿色的鲜苔。只要注意观察,就能看出这个石块砌成的坡岸正在不知不觉地靠近轮船。
构成这幅笔融细腻的“静物画”的词汇,基本上是些不带任何感情色彩的中性词。这种与传统小说大异旨趣的描写方式,最符合新小说派对一个“更为客观和实在的世界”的追求。
二、图象的时间和空间
新小说以繁复的图象来包容、折射现实和人生的内容。在这个叙事和描写的基本单位里,由于作者引进和强调了时空概念,使得图象的表现力急剧增强,深化了作品的主题,并且使时间和空间在作品中具备了更加新颖的表现力。
对于新小说而言,时间的重要性再怎么强调都不会过分,因为,在这些作家看来,世界上没有整块的东西,它们都是镶嵌而成的,至于按照什么原则把那些零碎的块块镶嵌成为整体,大多要依赖于时间。对于时间的特性,布托尔总结出两点:双重性和间断性。[(11)]
所谓双重性,即指过去和现在。一般地说,时间的这两种特性,在新小说出现以前和以后的大多数小说中都已存在,而且很多作家对时间的安排也很讲究。那么,新小说派作家为什么要对此特别青眯呢?主要原因在于它有利于在新小说中随时不断地抽取并融合图象,而且按需要自由地赋予每个图象以时间。因此,必须以新的眼光去审视时间,抛弃按年代顺序铺展故事的传统手法。对此,布托尔解释说:“死板地按年代顺序铺展故事,严禁回忆过去,会带来使人瞠目的结果:无法对世界历史作任何引证,无法回忆遇见过的人,无法使用记忆,因而一切内心活动都不能写了,最后人必然变成了物。”[(12)]因此,必须通过回忆“过去”来进行叙事,并与“现在”的叙述相对照而共同产生心理上的“厚度”。这样,时间的过去和现在就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交错和重叠,而且,每个叙述的事件既可能作为起点,也可以看作是好几个叙述时间的汇合。更重要的是,叙述将不再是一条线,而是一个面,一个图象,在这个图象里,小说家可以自由地分别确定一定数量的点和线。
间断性的所指是时间线条的中断,是相对于连续性来说的。其实,在强调时间的双重性时,间断性已经隐含其中了。新小说既不可能按线性来进行叙述,也不可能在每个图象里把下文的内容一并叙述出来,只能采取在某些时候保持时间连续性的手法,让情节如潮水般涌现,而在两潮间歇之中,作者已经极其自然地安排了巨大的跳跃。之所以强调时间的间断性,是因为一方面现实生活往往不可思议地使间断性显得非常突出,造成突变;另一方面,作者在创作过程中,出于这样或那样的需要,有可能故意造成间断。故而,我们有必要梳理一下时间的连续性、间断性与图象的关系。时间在某一个图象里会出现连续性,但难以一直保持下去,有可能会出现间断;在几个图象之间,时间又会出现间断,但这种间断可长可短。至于在叙述过程中,何时连续,何时间断,怎样确定间断和跳跃的技巧?这些问题的处理既取决于叙述的节奏,也取决于由此产生的时间共鸣。对后者的考虑,主要是基于在每个时间刻度周围,都隐伏着一系列起和声作用的时间刻度。比如说,在进行某段叙述时,作者会突然中断现在时态而与以前某段回忆沟通、衔接,这样,间断性就出现了。
事实上,我们从时间的双重性和间断性来考察新小说派对时间的探索,并不能穷尽一切。作家们对时间的看法和要求以及特定的使用习惯,已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范围。比如,罗伯-格列耶在总结《嫉妒》的创作经验时说:“如果以为在它里面有一个含义单一明确的事件顺序……那就大错特错了。重建外部时序的任何尝试迟早都会遇到一系列的矛盾,因而会走入死胡同……对我来说,除了书中的时间以外,不存在任何可能的顺序。”[(13)]这里就提出了一个建立小说时间的问题。我们再来看布托尔,在他的每部小说,特别是《米兰巷》、《日程表》、《变》、《运动体》、《每秒钟六十八万一千公升水》等作品中,对时间性及其复杂的形式,都有极为明确和多种可能的追求。如在《运动体》里,时间就以两种几乎垂直相交的方式展开,一个是表面的时间,即描写的时间:作者逐次回顾美国的50个州,共50章,每一章的时间是1小时,结果是让读者在小说里度过了两天多一点的时间;另一个是与此时间垂直相交、逐步展开描写的美国的历史时间。现实时间和小说时间就这样交叉在一起。从举例来看,新小说派作家对时间性的探索虽然各有其貌,但对一个更广阔和更真实的时间形态的概括浓缩,却是作家们共同的特点,因而这些概括最终都被熔铸在各种各样的图象里。
新小说派同样关注图象的空间性,如同可以自由地调遣叙事时间一样。由于图象可以收缩集中随时奔涌于作家脑际的回忆,印象和感觉,而这些主观情绪又无不与特定的空间相维系,因此,新小说对空间的处理也是自由的。当然,这种切割、组合和汇聚的自由势必受到内在创作目标的制约。
新小说派怎样描写空间?从一个地点到另一个地点的空间位移说明了什么?对此,新小说派作家是这样考虑的:首先,在一个图象里,不仅应该指出这图象的空间中有些什么,而且更应该说明它们所处的状况如何。在这一点上,传统小说和新小说的区别应该是较为清楚的。比如,描写一所房子,单纯写出这里有一张断腿的椅子、路易十三时代的木床、被阳光映射着的大衣橱等是不够的,还要写出它们之间靠得是否很紧,中间是否可以过人,每件家具是否看得很清楚或者互相遮挡,处在什么方位,左面还是右面,有的是否构成一个孤立的角落,等等。做到这一步还不够,还需用数字来精确表达。这种视觉上的新现实主义的引进,给新小说带来了很大震动,读者常常会碰到一些描写类似照片、电影、绘画和技术书籍的片断,但这些是为在想象空间里树立准确而稳定的形象所必不可少的,特别是对赋予独立意义的物体而言。
其次,空间的位移常常与旅行的概念联系在一起。实际上有很多新小说是在不同地域之间的位移、闪回和交叉之间展开构思的。小说家认为,20世纪的空间不再是古典几何学的空间,而是充塞着许多莫名阻塞物的机械学空间,又重叠着因通讯工具的更新换代而被打乱了的想象中的空间。当作家叙述这些空间的状态以及主体从一个场所到另一场所之间的行程、速度和后果时,便可衍生出十分丰富的内容。于其中,不仅有人物在空间关系变化中的种种奇遇,而且各个地点以其历史性构织了另一个空间。因此,空间的位移意味着加深或修正作品的原有意义。在布托尔的《变》中,空间位移是从巴黎到罗马,表面上似乎在探讨伦理问题,其实,据作者解释,这部小说所要讲的,主要是巴黎与罗马这两个城市之间的“历史传统关系”。确实,当我们抛开习惯读法以后,就能越来越深地体味出小说中的历史诗情和象征韵味。这种带着历史印迹的空间位移所产生出来的重要性,超越了人物行动所带来的意义。
事实上,当作家构筑一个图象时,时间性和空间性这两个概念是难以分开的。要想显示空间,就必须把时间注入其中,将时间看作一个行程,一段路程。欲研究时间或连续或间断的运行特征,又必须以明确的想象空间为依托。这层意思,西蒙用一个词来界定:混合体。他的小说《弗兰德公路》,在代替了整篇叙事的图象里,时间和空间始终混合在一起。在介绍创作缘由时,他说:整部小说是在一次夜行途中一下子涌现在脑海中的,“我可以说,全部一起迅猛地一阵子卷来……德·雷谢克的祖代、战争、所有的一切……”[(14)]可见,这种混合体并非作者的刻意制造,它在作者萌生创作欲望时就出现了,而且作为一种创作的核心部分,已完美地体现在作品中。
对新小说派的研究,可以从许多的角度切入,而我们对图象问题的阐述,还不十分全面和准确。比如,与图象问题密切相联的语言创新和运用问题,我们就感到相当陌生。因为法语和汉语分属表音和表义系统的语言,所以使用汉语的我们,就只好对这个相当诱人而又极为关键的问题表示遗憾了。
注释:
①1984年东京国际笔会上,阿兰·罗伯-格列耶当选为“当今世界七大文化名人”之一;1985年,克劳德·西蒙荣膺该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
② ⑧阿兰·罗伯-格列耶(法)《新小说》,载《法国作家论文学》,三联书店,1986年,第400、399页。
③ ⑤阿兰·罗伯-格列耶(法)《未来小说的道路》,载《现代西方文论选》,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第312、315页。
④ ⑥ ⑦阿兰·罗伯-格列耶(法)《自然·人道主义·悲剧》,载《现代西方文论选》,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第319、334、335页。
⑨恩斯特·卡西尔(德)《符号形式的哲学》,引自朱狄《当代西方美学》,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22页。
⑩ (13)让·里加尔杜(法)《新小说派书目介绍》,载《新小说派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第659、645页。
(11) (12)米歇尔·布托尔(法)《漫谈长篇小说技巧》,载《法国作家论文学》,三联书店,1986年,第425、426页。
(14)克劳德·西蒙(法)《关于弗兰德公路创作经过》,漓江出版社,1987年,第26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