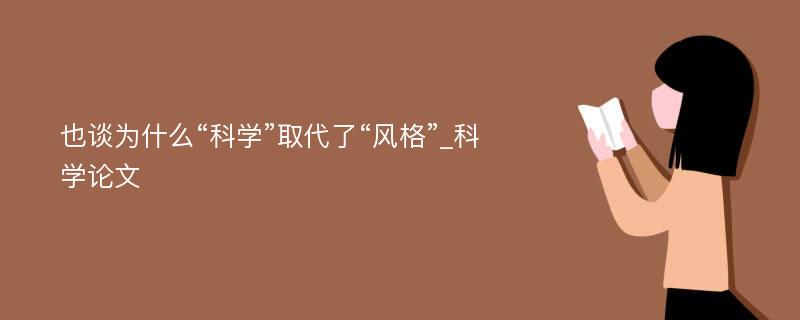
亦谈“科学”为何取代了“格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科学论文,取代了论文,亦谈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N0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934(2010)02-0101-05
自杨文衡[1]1981年、樊洪业[2]1988年著文提出了“格致”为何被“科学”取代这一问题之后,王果明[3]、李双璧[4]、朱发建[5]、金观涛[6]、张帆[7]、吴凤鸣[8]等人也先后著文讨论了这一问题。一个并非热门的学术话题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能够引起这么多学者的关注,而且其中还不乏大家,想必该问题比较重要,大有深入探讨之价值。“科学”取代“格致”应该是多方面的原因共同作用的结果。尽管上述作者所持的问题意识不尽相同,但他们都从各自的视角对“科学”取代“格致”的原因进行了分析。这些分析无疑有助于我们增加对“科学”取代“格致”问题的理解。不过,上述文章基本上都没有触及英文“science”语义的演变及其对“科学”取代“格致”的影响,而“格致”最终被“科学”取代与“格致”不能很好地对应“science”语义的变化不无关系。以下,笔者甘冒狗尾续貂之嫌,拟就这一问题谈些一孔之见。
1 英文“science”语义的演变
英语中的“science”源于拉丁语“scientia”,在中世纪,“scientia”的根本含义是“知识”[9]。弗兰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除将其翻译为“sciences”外,有时还将其直接翻译为“knowledge”(知识)、或者“learning”(学问)[10]。当时各类知识部门,即专门学科领域尚未完成独立,所有知识都还包含在哲学体系之内,故“scientia”与源于希腊语“philos(爱)”和“sophia(智慧)”的“philosophia”词义相近,以致在很多情况下,源于拉丁文的“science”和源于希腊文的“philosophy”在英语中可以互换使用[11]。陈启伟在研究1877年《格致汇编》所载英人慕维廉写的《培根格致新法》一文中的“Philosophy”译名时发现,慕维廉将培根《新工具》中的“Philosophy”和“science”都译成了“格学”或“学”[12]。这其实不难理解。因为在慕维廉看来,“Philosophy”和“science”根本就没有什么差别。后来英美等国的教会大学纷纷授予理科出身的毕业生以哲学博士(Ph.D)学位,与此也有很大的关联。
在近代以前,人们认识自然所获得的知识,不论是通过抽象思辨,还是通过经验观察所获得的知识,统统被纳入“自然哲学”的范畴。那时,拉丁语“philosophia naturalis”和“scientia naturalis”指的都是关于自然的知识,与希腊语中的“philosophia physice”同义[13]。即使是十六至十七世纪爆发的科学革命也未能改变这一状况。近代自然科学被认为诞生于十七世纪,其主要依据乃牛顿力学的形成。可是,牛顿(Isaac Newton,1643-1727)公开披露力学三定律的著作的名称是《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Principia Mathematica Philosophiae Naturalis)。尽管基于数学描述与经验观察的牛顿力学明显有别于传统意义上的自然哲学,但是牛顿仍将其称作为“自然哲学”。这意味着,近代自然科学虽然诞生了,但它还没有获得相应的名份,因此它不得不沿用“自然哲学”之名,继续寓居在哲学体系之内。这种情况至十八世纪末仍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例如,1808年,奠定化学原子论基础、被誉为近代化学之父的英国化学家、物理学家约翰·道尔顿(John Dalton,1766-1844)把他一生中最重要的著作命名为《化学哲学的新体系》(New System of Chemical Philosophy)。很明显,在道尔顿看来,基于分析实验提出的化学原子论仍只不过是自然哲学中的一个分支,自然科学和自然哲学根本就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差异。
自然科学与自然哲学分道扬镳,开始从哲学体系中分离出来,实际上是库恩(Thomas Samuel Kuhn,1922-1996)所言的“第二次科学革命”[14]爆发之后的事。经过英国工业革命和法国大革命的洗礼之后,自然哲学的面貌发生了重大变化。那就是,对自然进行经验与实证研究所获得的知识急剧增长,其中尤以化学、理论力学、热力学、光学领域的发展为甚。此时,不加区隔地继续将以数学和实验为两大支柱构建起来的知识体系统称为“自然哲学”已不合时宜,于是,英语中原本同义的“natural philosophy”和“natural science”的用法开始出现分化,人们越来越多地使用“natural philosophy”来指称对自然进行形而上学思考所获得的知识,也即狭义上的“自然哲学”;同时使用“natural science”,或其短缩语“science”来指称对自然进行经验与实证研究所获得的知识。结果,在十九世纪上半叶,关于自然的知识分化为两种类型,一种是现代意义上的“自然科学(natural science)”,另一种是现代意义上的“自然哲学(natural philosophy)”[15]。前者主要是基于“做(doing)”建立起来的,后者则主要是通过“想(thinking)”建立起来的。至此,原来在反对神学时结成同盟的两大致力于探寻世俗真理的知识领域便宣告彻底决裂了。
一般认为,直到英国科学促进协会(British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于1831年成立时,英文“Science”才获得了今日的确定含义[16]。此后,使用“science”来指称对自然进行经验与实证研究所获得的知识的情形有增无减。但是,即便进入十九世纪下半叶,使用“natural philosophy”来指称自然科学的现象仍然存在。如蒯肯波士(G.P.Quackenbos,)的《Natural Philosophy》(1859年初版,1873年再版)实际上写的都是以物理学为中心的自然科学方面的内容[17]。
肇始于十八世纪的科学的职业化与体制化,不仅使自然科学得以在十九世纪上半叶从自然哲学中分离出来,而且还使自然科学在十九世纪中期前后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以致自然科学在十九世纪下半叶呈现出了三大特征:一、专业化分工越来越细,涌现出了一批新兴学科,如生物学、生理学、有机化学、物理化学、电磁学、地质学等;二、科学与技术的关系越来越紧密,既出现了一批为了科学的技术,也出现了不少为了技术的科学,随着基于技术的科学和基于科学的技术的发展,科学技术对经济和军事的影响力大幅提升;三、科学的精神价值日益彰显,致使科学乃接受过严格检验的客观真理,科学方法具有普遍适用性,一切理论都必须接受理性的无情审视和批判等观念开始流行[18]。之后,科学不仅获得了崇高的社会地位,而且还获得了强势话语权。
工业革命后自然科学的快速发展,一方面为实证主义的兴起提供了土壤,另一方面则为社会科学的发展提供了范式。孔德(Auguste Comte,1798-1857)、穆勒(John Stuart Mill,1806-1873)等实证主义者认为,社会与自然原本没有本质上的差异,人们完全可以像自然科学家研究自然现象一样来研究社会现象,而且只有像自然科学家研究自然现象那样研究社会现象时,换言之,只有当社会现象研究建立在客观精确描述和系统逻辑分析基础之上时,所建立起来的知识体系才有可能称得上是“science”。孔德等人确信存在一种通用的科学方法,并试图用这种通用的科学方法来统一各门学科,进而主张没有必要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作出严格的划分。这种统一科学之思想对十九世纪中后期的社会科学的发展和“science”概念的形成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19]。
十九世纪后期,英文“science”除用来指称知识、学问(广义上的用法),以及自然科学(狭义上的用法)外,还衍生出了一种新的用法,即用来指称建立在客观精确描述和系统逻辑分析基础之上的有关自然、社会的知识体系。不难看出,这种“science”的概念,其外延小于广义上的“科学”,但明显大于狭义上的“科学”。依据实证主义科学观,“science”不仅包含自然科学中的各种专门学科,而且还包含正在西方兴起的社会学、经济学和政治学等社会科学学科,甚至包括介于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之间的历史学和文化人类学[20]。
2 “科学”取代“格致”的原委
黑船事件后彻底打开国门的日本,在与英美等国交往过程中接触到的主要是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之后兴起的科学。由于人们对十九世纪中后期科学的多元特征的把握不尽相同,故在翻译介绍“science”时不可避免地会按照各自对西方科学特征的理解选用不同的术语。一些人见到西方科学的专业化分工越来越细,分科化特征越来越明显,于是选用“科学”来表述之。这些人所言的“科学”明显带有分科之学”之意。另一些人见科学与技术的关系日益密切,实用化特征越来越明显,于是选用“实学”来对译之。“实学”者乃“实用之学”之谓也。还有一些人见“科学”强调对自然进行实证研究,理性化特征非常明显,于是将其称作为“理学”,意为“穷理之学”。此外,还看人将其翻译为“学”、或“学问”的[21]。
虽然中国古典文献中出现了不少“科学”用例,但它们都不是“science”意义上的“科学”[22]。作为“science”译语的“科学”传入中国,实际上是甲午战争之后的事。令人惊讶的是,“科学”传入中国后不到十年,其使用频度便开始超越当时用来翻译“science”的“格致”等词语,辛亥革命后则完全取代了“格致”[6]。为什么有着悠久历史的“格致”等译语遭遇“科学”这个刚从日本引进的新词之后没战几个回合就缴械投降了呢?
如众所知,“格致”一词源自于《大学》中的“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23]2。在儒家看来,格物、致知是为了诚意、正心,而诚意、正心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基础。问题是,何谓格物?如何致知?后来程颐(1033-1107)、朱熹(1130-1200)对其进行了解释。朱熹特别强调两点:一是“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23]6。二是“格物,须是从切己处理会去”[24]284。具体来讲,就是“如读书,便就文字上格。听人说话,便就说话上格。接物,便就接物上格”[24]286。很明显,儒家强调的格物致知,关键在即物穷理,即物穷理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明了事理或伦理,而不是物理。至于格物穷理的方法则是从身边的一草一木,一书一事格起,且主要依靠类推和顿悟[25]。
一些学者对西学东渐之初,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徐光启(1562-1633)等人借用儒家的“格致”等词来指称西学颇有微辞。确实,即便是十七世纪科学革命之前的西方“自然哲学”和中国儒家的“格物穷理之学”也有着很大的差异。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牛顿之前的西方“自然哲学”与中国的“格物穷理之学”并非完全没有相似之处。首先,双方都主张要即物穷理。其次,双方穷理的目的都不仅仅是为了探明物理。西方主张人们通过探究自然来了解自然的精妙,进而领略自然设计者的伟大,坚定对全能上帝的信仰。中国主张即物穷理则是为了明了事理,进一步加深对儒家伦理道德规范的认同,从而为“修齐治平”、“内圣外王”奠定基础。至于穷理方法,双方都强调观察思考,只是中国过于依赖类推和顿悟,西方更强调演绎推理罢了。那时,实验归纳法在西方尚未确立应有的地位,西方“自然哲学”的思辨色彩仍然比较浓。因此,西学东渐之初,中国的士大夫用“格致”来对译西方的“natural philosophy”甚至是“philosophy”并非毫无道理。
问题是,晚清时期的西学东渐在时空背景上已明显有别于明末清初的西学东渐。鸦片战争,特别是“亚罗号事件”之后,西方的自然科学已从自然哲学中分离出来。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人仍沿袭明末清初的做法,继续使用“格致”来指称十九世纪中后期的西方“自然哲学”和“自然科学”那就很容易引起混乱了,至少无法对“自然哲学”和“自然科学”进行有效区隔,更何况“格致”在儒家那里原本还有其特定含义。再者,十九世纪中期前,自然科学基本上是以物理学为中心展开的,那时生物学尚处于萌芽阶段,因此,把自然科学等同于物理学,将“自然科学”和“物理学”都称作为“格致”时,尚不至于引起严重的概念混乱。但是,当“自然科学”于十九世纪中后期急速分化为众多新兴学科之后,尤其是与生物学相关的学科获得快速发展之后,仍不加区分地将“自然科学”和“物理学”都称作为“格致”,必然会引起混乱。而事实恰恰是,洋务运动之后,在我国,既有把西方“自然哲学”称作为“格致”的;又有把“自然科学”称作为“格致”的;还有把“物理学”称作为“格致”的[1,2]。当然,仍有把西方的“格致”同中国的“格致”混为一谈的。
“格致”的用法如此复杂多歧,当然会引起人们的关注,乃至不满。譬如,先后出使英国和德国的刘锡鸿就不赞成人们借用“格致”一词来指涉西学。他认为,“大学之言格致,所以为道也,非所以为器也。”所谓“西学”,“盖工匠技艺之事也”。因此,他反对将设有外国科学仪器设备展览室的书院命名为“格致书院”,认为那是“殆假大学条目以美其号”[26]。当然,更多的人则看到了中学和西学的差异,认为有必要对西方格致和中国格致加以区别。如徐寿(1818-1884)在参与筹备格致书院时就曾指出了中西格致的差异:“然中国之所谓格致,所以诚、正、治、平也;外国之所谓格致,所以变化制造也。中国之格致,功近于虚,虚则常伪;外国之格致,功征诸实,实则皆真也”[27]。将格致理解为“自然科学”的林乐知(1836-1907)则提醒人们不要把对事物的抽象思考和经验研究混为一谈:“吾西国力学之士,每即物穷理,实事求是。自夫天文、地舆,以迄一草一木之微,皆郑重详审焉而不敢忽。……非如中国之奇方幻术,托于鬼神虚诞,令人茫乎莫凭,杳乎难索也”[28]。为了在自然科学与物理学之间作出区分,在翻译《格致启蒙》时,林乐知还特意把科学译为“格致”,把物理学译为“格物学”。
随着对西学了解的不断加深,人们意识到,用“格致”、或“西学格致”笼统指涉西学中的“自然哲学”、“自然科学”,甚至是“物理学”存在很多问题,有必要为西学中的这些概念另觅新的名词。特别是当实证主义科学观渗透进来之后,这种愿望变得更加迫切。此时,如果照旧把实证主义者们所言的科学纳入到“格致”的框架体系内,将会引起更大的概念混乱。因此,严复(1854-1921)在1903年出版的《群学肄言》中模仿日文译法,将“science”译为“科学”,并强调“群学”(社会学)是科学[29]。很明显,严复的“科学”泛指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这和梁启超的“科学”用法相似。梁启超(1873-1929)于1902年发表了多篇含有“科学”一词的文章。在这些文章中,梁启超把“格致”解作为“自然科学”,也即“狭义之科学”[30],把物理学称作为“物质学”[31]。在梁启超看来,一般意义上的“科学”,它不仅包括“天文学、物质学、化学、生理学”等“天然科学”[31],而且还包括“政治学、生计学(经济学)、群学”等“形而上学”[32]。
当西方用“science”、日本用“科学”来特指自然科学,以及泛指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时,我们一如既往地使用概念含糊的“格致”来指代自然科学,同时扩大“格致”的解释范围,使其能够用来泛指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显然不是上策。在精通英文的严复和精通日文的梁启超都接受,并提倡用“科学”来对译“science”的情况下,“格致”迅速被“科学”取代也就变成了情理之中的事了。
3 结语
英文“science”最初的含义是知识或学问;进入十九世纪后用来特指自然科学;实证主义兴起之后又开始用来泛指建立在客观精确描述和系统逻辑分析基础之上的有关自然、社会的知识体系,也即既包含自然科学,又包含社会科学。因此,“科学”在日本演变成“science”的定译词,并于十九世纪末传入中国之后,相应地被赋予了如下三层含义:
1.指知识或学问。人们在报章中常常能够见到“哲学是一门有趣儿的科学”、“伦理学是一门研究什么什么的科学”之类的表述。这类表述中的“科学”显然是指“知识”或“学问”,也即它是在最广义上使用的“科学”,并不具有对自然或社会规律进行客观描述的含义。
2.指自然科学。长期以来,人们为中国古代究竟有没有科学争得面红耳赤。如果此处的“科学”指的是基于数学分析和实验研究基础之上的自然科学,那么中国古代没有科学是不言而喻的;倘若指的是最广义上的“知识”或“学问”,那么说中国古代没有科学就很难站住脚了。不过,通常情况下,人们所言的“科学”主要是指“自然科学”。
3.指基于实证研究的有关自然和社会的知识体系。人们常说“马克思主义是科学”。这里的“科学”当然指的不是最广义上的“知识”或“学问”,而且也不是指狭义上的“自然科学”。我国的权威工具书《辞海》曾对“科学”作出了这样的解释:科学是“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的知识体系。它适应人们改造自然和社会的需要而产生和发展,是实践经验的结晶。科学可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大类,哲学是二者的概括和总结”[33]。不难看出,《辞海》中的“科学”词条作者受实证主义的影响比较大,在他们看来,“科学”乃是一种经受了经验检验乃至逻辑检验的知识体系。按照这种科学理解,虽然人文类学科称不上是“科学”,只能叫作“人文学科”,但是基于实证研究的社会科学被认为是“科学”家族中的正式成员。
在作为“science”译语的“科学”传入中国之前,中国主要用“格致”来对译“science”。这样,“格致”既具有了古典“science”意义上的“知识”和“学问”的内涵,又具有了与“natural philosophy”分离后的“自然科学”的内涵,甚至还被用来指代自然科学中的核心学科——物理学。加上,“格致”原本所具有的含义,即一种和“正心”、“诚意”相关联的修身、明德方法。在十九世纪中后期的中国,“格致”的语义可谓五花八门、莫衷一是。
恰巧,当时的“science”在实证主义的影响下,其概念又进一步演变为泛指基于数学分析和经验研究的一切学问,也即,既包括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自然科学,又包括诸如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之类的社会科学。这样一来,“格致”的概念要不要扩大解释以适应“science”概念的演变便成了一个必须面对的问题。熟悉西方科学发展情况的严复和梁启超等人意识到,有必要选择一个比较单纯的术语来对译“science”。也许从字面上看日文中的“科学”未必是“science”的最佳对译语,但是,无论是严复,还是梁启超,最终都选择了“科学”。于是,放弃“格致”,选用“科学”来指代“science”便逐渐演变成为一种潮流,以致1905年科举被废除之后“科学”迅速取代了“格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