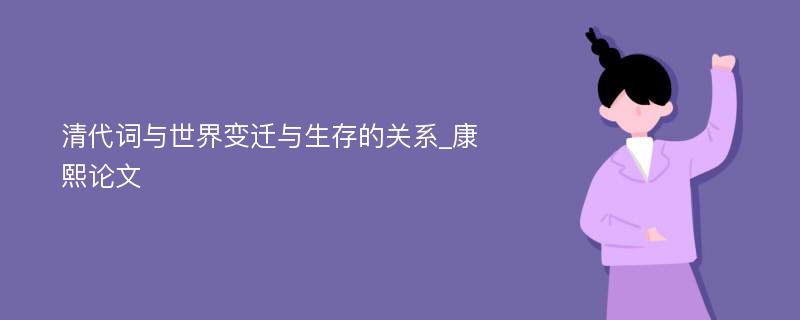
清词与世变、寄托的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寄托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清代词学,号称中兴,有人以为肇始于明清之际的陈子龙,与所谓“世变”有关;有人以为崛起于清顺、康之际的陈维崧、朱彝尊等人,与“阳羡”、“浙西”二派有关;也有人以为奠基于乾嘉之际的张惠言、周济等人,与常州派有关。各有各的根据,各有各的道理,但仔细推究起来,却也同样各有各的缺点,都有一些值得商榷的地方。
首先,是有关“世变”的问题。
所谓“世变”,盖有二义:一是指江山易主、朝代更替;一是指世风丕变,即政治环境和社会风气产生了大变化。二者互相关系,互相限制。大抵言之,江山易主、朝代更替时,政治环境和社会风气往往会随之而产生大变化,但是,世风的丕变,则未必由于江山易主、朝代更替。讨论文学与世变关系的人,有时候过于强调世变对文学的影响,难免有牵强附会之处,特别是把“世变”的意义囿限于改朝换代的解释时,几乎把文学都视为政治的附庸,而忽略了作家个人的情志和文学独特的生命。我们不能否认改朝换代之际,政治环境对文学的发展必然有所影响,但影响的多寡,也随时代和作家差异而有所不同。譬如说,六朝时江山频频易主,文学的风貌有什么重大的变化吗?晚唐五代前后,改朝换代之事,司空见惯,试问晚唐和北宋初年的文学风气又有什么重大的不同?进一步说,就词而言,《花间集》产生于戈戟纷扰之际,我们从中又能找到多少歌咏时代动乱的作品?可见,过度强调世变对文学的影响,未必正确,尤其是把“世变”囿限于江山易主的解释的时候。因此,认为清代词学的兴盛,肇始于明清之际陈子龙的说法,我个人是存疑的。谈清词史,自然可以从陈子龙谈起,但这未必表示身处乱世、写兴亡之感的陈子龙,对清词的兴盛起了什么必然的作用。
事实上,清初在顺治以前,词坛风气和明代是连系在一起的,都还在《花间集》、《草堂诗余》好尚成风的笼罩之下。陈子龙如此,王士祯、邹祗谟等人也是如此。清代词学风气的转变,严格说来,其实是在康熙年间。康熙年间,政治已趋稳定,已非江山易主、干戈纷扰之际。因此,就清词而言,把“世变”解释为政治环境和社会风气的改变,我是比较赞成的。
康熙年间,无论是词的创作、选辑或评论,都蓬勃发展起来。以孙默所编辑刊印的词选集为例,康熙三年(1664年)他选了王士祯、邹祗谟、彭孙遹词为《三家诗余》八卷,康熙六年(1667年)已增收曹尔堪、董以宁、陈世祥词为《六家诗余》十四卷,康熙七年(1668年)又增收陈维崧、董俞等人词为《十家诗余》二十四卷,到康熙十六年(1677年)更增收吴伟业、梁清标等人词为《十五家词》三十七卷,同年还增收龚鼎孳词另为《十六家词》三十九卷。我们由此可以想见此书风行及当时词学兴盛的一斑。不过,康熙词坛最受后来论词者重视的,仍是陈维崧和朱彝尊二人。
日本汉学者中田勇次郎,在《读词丛考》一书中有一篇论文,题曰《清初词选刻板考》,著录康熙朝的词选集刻本,就有几十种。(注:见中田勇次郎著《读词业考》,日本东京创文社,1998年12月初版;《清初词选刻板考》一文,见该书第299、316页。)以梓行于康熙十七年前的为例,比较著名的,除上述孙默所编选的以外,还有下列几种:
《今词苑》三卷,陈维崧等编,康熙十年(1671年)南涧山房刊本;
《今词初集》二卷,顾贞观、纳兰性德合编,康熙十六年(1677年)本;
《词坛妙品》十卷,张渊懿编,康熙十七年(1678年)原刊本;
《东白堂词选》十五卷,佟世南编,康熙十七年(1678年)刊本;
《词综》三十卷,朱彝尊、汪森合编,康熙十七年(1678年)初刻本。
其中最为后人注意的,自然是陈维崧的《今词苑》和朱彝尊的《词综》。因为他们二人分别是阳羡词派和浙西词派的代表作家。前者标榜苏辛,后者崇尚姜张,都对此后的清词坛有很大的影响。
同样的,在词学评论方面,像王士祯的《花草蒙拾》、邹祗谟的《远志斋词衷》、贺裳的《皱水轩词筌》、彭孙遹的《金粟词话》、纳兰性德的《渌水亭杂识》、刘体仁的《七颂堂词绎》、沈谦的《填词杂说》等等,也大都著成于康熙初年。(注:参阅拙著《清代词学四论》,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民国七十九年七月初版。书中《王士祯的词集与词论》一文,第1-68页。)陈维崧和朱彝尊二人虽然没有论词专著,但是陈氏的《陈迦陵文集》和朱氏的《曝书亭集》,集中的序跋题记等等文字,仍然常被论词者所征引。尤其是朱彝尊,更被视为康熙词坛的代表。连他《词综·发凡》里的一些话,像“词至南宋始极其工,至宋季而始极其变”等等,都一再被人援引申论。因此,特别标举陈维崧和朱彝尊,甚且只标举朱彝尊一人,来作为清词风气转变的关键人物,我都不反对。只是,我觉得还有一些人或事是不能忽略的。
例如,我们应该注意到康熙年间,颇有一些词论家用心辨别词与诗曲的不同,这是对元明以来词体混淆的一种反省。像李渔的《窥词管见》,约著成刊行于康熙十七年(1678年)(注:参阅拙作《李渔〈窥词管见〉析论》一文,原为国科会民国八十年获奖论文,先后发表于台北《国立编译馆馆刊》第廿四卷第1期及上海《中华文史论丛》第56辑,今收入拙著《清代文学批评论集》,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民国八十七年六月初版。),文章一开头就说:“作词之难,难于上不似诗,下不类曲”,这和同时刘体仁《七颂堂词绎》所说的:“词须上脱《香奁》,下不落元曲,乃称作手。”沈谦《填词杂说》所说的:“承诗启曲者,词也。上不可似诗,下不可似曲。”董以宁《与严绳孙论词书》所说的:“词与诗曲界限甚分,似曲不可,似诗仍复为佳”。(注:参阅拙作《李渔〈窥词管见〉析论》一文,原为国科会民国八十年获奖论文,先后发表于台北《国立编译馆馆刊》第廿四卷第1期及上海《中华文史论丛》第56辑,今收入拙著《清代文学批评论集》,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民国八十七年六月初版。)可谓契若针芥。他们所以有这样的论调,是有其时代背景的。因为词自南宋复亡之后,历经元明而日趋衰微,所谓缠令之体的“词余”,逐渐取代了词客文士的歌席案头之作,而腾之于歌者俗人之口。南宋词一向追求醇雅,讲求锤字练句、研声忖律的工夫,然而愈求醇雅,则愈曲高和寡;元曲小令虽然有时失之轻俗,但一般人却易于接受,喜欢它的清新浅易。因此,雅俗始则互相对立,互相影响,到最后,不但词有曲化的倾向,曲有词化的倾向,而且诗词曲之间,逐渐互相混合在一起,真的变成难分难解。这种情况,从元明一直到清初,都不能廓清,所以活动在顺康间的词人,在康熙年间才纷纷提出了辨别词与诗曲之间宜有分界的主张。因为有这样的主张,注意到了词体应该有别于诗曲,所以康熙间的词家,像陈、朱等人,才更有可能会注意南宋词与北宋以前词作的不同。浙派后继者王昶,继朱彝尊《词综》之后,编成《明词综》,序文中就说过这样的话:
“永乐后,南宋诸名家词皆不显于世,唯《花间》、《草堂》诸集盛行。”
《花间集》收录唐五代词,自不待言。而大约编成于南宋宁宗年间的《草堂诗余》,虽然表面上于唐五代两宋词并取兼收,实则重北宋而轻南宋,取北宋之周、秦,而弃南宋之辛、姜。因此,明人之崇尚《草堂诗余》,是间接反映了他们不喜欢南宋词,包括了辛、姜的豪雄和骚雅。就连陈子龙《幽兰草词序》中也说南宋词“寄慨者亢率而近于伧武,谐俗者鄙浅而入于优伶”,即可明白。而这个,正是身经时代变乱或早年曾经从事反清复明活动的一些清初词人,所期期以为不可之事。因此,陈维崧在他与友人合编的《今词苑》(一名《词选》)序文中即说:“东坡、稼轩诸长调,又骎骎乎如杜甫之歌行、西京之乐府也”,而且强调:“选词所以存词,其即所以存经、存史也夫”。
至于朱彝尊对南宋词的推崇,更不用说。他在中年学词之后,得到曹溶的鼓励、陈维崧兄弟的切磋,虽然也认为“小令当法汴京以前”,但他后来开始“崇尔雅,斥淫哇”(见《静惕堂词序》)、“去《花菴》、《草堂》之陈言”(见《孟彦林词序》),更在为陈维崧弟弟陈维岳《红盐词》所写的序文中主张:“善言词者,假闺房儿女子之言,通之于《离骚》、变雅之义。朱彝尊曾从曹溶处借阅了不少宋元词,他和汪森所编的《词综》,得力于此者应该不少。宋季元初的咏物之词,特别是周密所编的《绝妙好词》,和元初遗民王沂孙、张炎等人为“冬青六陵之役”所作的《乐府补题》,藉联吟龙涎香、白莲、莼、蝉、蟹等物,而寓故国之思,都是关乎比兴寄托,可以“通之于《离骚》、变雅之义”的作品。这两本集子,过去鲜人注意,他却在康熙年间,和友人合作借钞传印于世。其中最值得注意的,当然还是康熙十七年(1678年)他和汪森所合编刊行的《词综》一书。是书《发凡》所说的:“世人言词,必称北宋。然词至南宋始极其工,至宋季而始极其变。姜尧章氏最为杰出”,可以说是揭举了他标榜南宋姜、张的旗帜,也为后来浙西词派“家玉田而户白石”的风气开了先声。
不过,说到这里,我却也必须声明,我以上的很多论述,所以强调在康熙十七年以前的原因,是因为康熙十八年(1679年),陈维崧、朱彝尊和很多原来心存反清复明之志的博学鸿儒一样,都被荐举,应康熙皇帝之召,到宫中体仁阁应试,从此入翰林、修明史去了。这对于强调“不事二主”的古代读书人来说,多少是不堪之事。就陈维崧来说,过去的发扬蹈厉、标榜苏辛的气概,此后很难再宣之于口。就朱彝尊而言,过去所推崇的白石的清空、玉田的骚雅,过去江湖载酒时的身世之感、家国之悲,一下子也都可能变成了他人口中的腾笑之资。因此,从康熙十八年以后,他们二人的词学活动,很快就歇止下来了。陈维崧去世于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不说,朱彝尊在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为丁炜《紫云词》所作的序文中,对词的看法与前人已经大不相同。他在《紫云词序》中是这样说的:
自唐以后,工诗者每兼工于词。宋之元老若韩、范、司马,理学若朱仲晦、真希元,亦皆为之。由是乐章卷帙,几与诗争富。昌黎子曰:欢愉之言难工,愁苦之言易好。斯亦善言诗矣。至于词,或不然,大都欢愉之辞工者十九,而言愁苦者十一焉耳。故诗际兵戈俶扰流离琐尾,而作者益工,词则宜于宴嬉逸乐,以歌咏太平,此学士大夫并存焉而不废也。
可见,与过去的词学主张,已经迥然而异了。难怪他后来在《水村琴趣序》中说:“予既归田,考经义存亡,著为一书,不复倚声按谱”。虽然如此,他对浙西词派的开导之功已成,浙派后起有人,醇雅之词蔚然成风,已为清代的词学辟榛莽而别开一天地了。
因此,说康熙年间对清词有贡献的的词人,陈维崧和朱彝尊都是扭转元明以来柔曼词风的关键人物。尤其是朱氏,他让清词超轶元明而远绍南宋姜张的骚雅,使读者接触到宋元之际咏物之词的比兴之旨、寄托之义,真的是“指出向上一路”。我以为要谈清词与世变的关系,或者与南宋咏物词的关系,应当从此着眼。
至于清词与寄托的关系,易言之,清代词学与常州词派的关系,我的看法有很多已经呈献在《常州派词学研究》(注:原由嘉新文化基金会奖助印行,民国五十九年六月初版,后来收入《清代词学四论》一书,见注②。)一书中,另外有一些修正或补充的意见,最近几年正撰写一些论文,例如《温庭筠菩萨蛮“小山重叠金明灭”相关问题辨析》(注:见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中文学刊》创刊号,第121-149页,1997年6月。)、《温庭筠菩萨蛮十四首的篇章结构》(注:见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新第七期,第269-290页,1998年11月。)、《从诗的比兴到词的寄托》(注:见《首届宋代文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第543-555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6月。)等等,在此不想重复。这里只想就与本文有关者说明几点。
(一)陈维崧说:“选词所以存词,其即所以存经、存史”;朱彝尊说:“善言词者,假闺房儿女子之言,通之于《离骚》、变雅之义”。这些意见,都和常州词派张惠言等人的寄托说没有什么不同,但词的寄托之说至张惠言以后始告成熟的原因,与时代有关,易言之,与广义的“世变”有关。不仅有政治上的因素,如四库全书之开馆等等,而且也有学术上的因素,如乾嘉经学的昌盛等等,特别是张惠言和经学所谓“歙学”者金榜等人的关系,周济和史学的关系。除此之外,当然还有一些其他文学上的因素。
(二)常州词派倡言比兴寄托,用来推尊词体,所以成功的原因,是在于后继者大有人在,像董晋卿等人在创作上的推展,有声同气求之功,像周济、陈廷焯、谭献等人在理论上的不断补充,才真的使常州词派日益壮大,直至清末民初而未沫。
(三)常州派所以能风行一代,至清末民初而未衰的原因,是因为嘉、道以後,国势积弱,内乱外患纷至沓来,才人文士感念时世,每有难言之隐,此恰与常州词派的比兴寄托之说,有相通处。其中,同光间一些志士的感慨,鼎革时一些遗老的悲愤,俱托于词,更使常州派的寄托说在实际创作上得到了印证,因而能够久而不废。晚清词人,如文廷式、王鹏运、朱祖谋等人,他们有感于朝政日非,外患日亟,往往在词作中表现了“左袵沈陆之惧,尤生念乱之嗟”。有人说,在他们的词作中,只要小序中有标明年月日期的,往往都有其特定的“寄托”之意。像文廷式的《忆旧游秋雁,庚子八月作》,像朱祖谋的《丹凤吟秋半塘四月二十七日雨霁之作,依清真韵》,都是著名的例子。
这样说来,常州词派的寄托之说,真的又与“世变”密不可分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