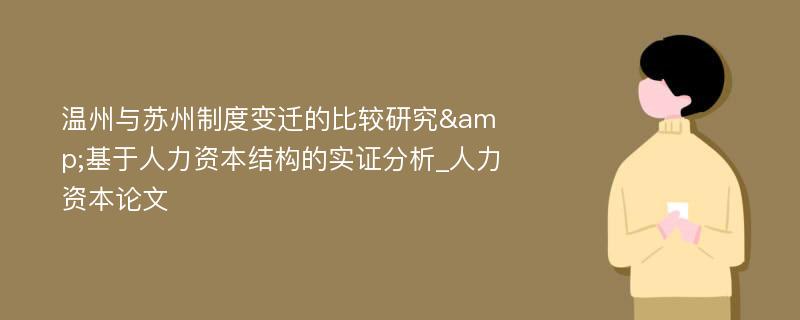
温州与苏州制度变迁的比较研究——基于人力资本结构的实证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温州论文,苏州论文,实证论文,人力资本论文,结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温州、苏州经济发展的制度变迁研究综述
温州经济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从经济制度变迁和经济转型的角度来深入研究“温州模式”。认为温州经济之所以具有如此活力,关键在于其制度的创新,是一种诱致性制度变迁。马津龙[1]在研究股份合作企业时,认为“温州模式”是中国改革过程中通过诱致性制度变迁建立市场经济的一种典型形式;施端宁、陈乃车[2]通过温州与苏南两种模式的比较得出结论,温州模式的制度创新是以需求诱致性制度变迁方式为主导的,制度变迁的主体是个体、私营企业和企业主,改革和创新的动力主要来自于民间的市场力量;金祥荣[3]也认为温州的制度创新是一种“需求诱致性”制度变迁方式,这种制度创新“正是温州和浙江省二十多年来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最大动力来源”。
对于苏州的制度变迁的研究,主要有施端宁、陈乃车[2]等认为苏南模式的制度创新是一种供给主导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方式,制度变迁的动力和主体主要来自于社区政府;周直[4]认为制度创新是苏南模式更新并更好地焕发活力的关键所在。苏州制度创新,主要包含企业制度创新与政府制度创新。由于政府过度参与企业决策加上政府规范市场秩序不到位,政府释放民间力量、整合民间资本与人力资源不够,这就使得民营经济的发展滞后于沿海其他一些地区。
上面的这些分析都有成立的理由,但这些研究并没有给出为什么会在相同的宏观制度环境下两个不同的地方会有不同的制度变迁路径。我们认为会有很多的原因导致这样的结果,但初始的人力资本存量结构的不同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在改革初期,温州具有富裕的企业家人力资本,而苏州却缺乏企业家人力资本。也就是温州是属于企业家人力资本富裕型,而苏州则属于专业人力资本富裕型[5],不同的人力资本结构模式决定了他们在制度变迁时的不同路径。
二、温州诱致性制度变迁的实证——企业家人力资本富裕的必然
在温州的制度变迁中,有很多的诱致性制度变迁的例证,我们将以其中的股份合作制作为主要案例进行分析。其他如挂户经营、民间金融、都市村庄、商会、城镇建设、旧城改造等就不一一说明。
(一)股份合作制——诱致性制度变迁的案例
到了80年代中期,温州以家庭工业为主体的经济格局悄悄发生了变化。1986年,除数量可观的个体、私营企业外,冒出了农民联户、合股、合作、集资等类似形式的企业10413家,年产值13.61亿。占当年全市14603个乡村工业企业总产值的71.5%,全市工业总产值的27.8%[6]。
显然这个时候原来的制度均衡需要被打破,因为如果不创造出一种新的企业组织制度,那么这些众多企业的“公”与“私”的问题就解决不了,企业的扩大再生产也成为一个问题。因此,制度选择集合要发生改变,需要创造出一种新的形式;其次,技术层面要求发生变化。马津龙[1]认为技术的不断进步要求企业迅速扩大投资规模,也需要一种新的形式。
由于在实践中遭遇到了这样的需求,温州企业家人力资本的创新功能就必然会释放出来。而这种制度安排的选择,是由个人或一群人,即初级行动团体,为了获取制度创新的利润而创造的。温州众多非公企业的企业家们作为初级行动团体,选择了创新的股份合作制的形式。首先,制度企业家们(创办企业或在企业中有投资的人们)要从技术上使这样的企业组织可以被认为是姓“公”的,其次能从新制度中获得更大的经济收益。因此,股份合作制就自然被发明出来。
这类企业分别吸收了股份制和合作制的合理因素,是介于两者之间的一种生命力很强的混合经济,在“政治”和“经济”两个方面都得到了保障。温州的企业家们就凭借他们所具有的企业家人力资本的功能,实行了制度的创新。有了这个制度以后,企业在政治上得到了保障,成为被现存制度所认可的“公有制”企业,而在经济上企业获得了比其他现存制度形式更多的剩余。
这种制度的开始实行是为了解决温州企业在发展中所遇到问题,并且是个别的企业自发组织实施的。成立于1982年的苍南毛纺厂是有记录的温州最早的股份合作企业;1986年温州第一家通过规范化的股份合作企业——苍南县桥墩门啤酒厂开业;同年10月5日,该厂股东大会全票通过全国第一部股份合作企业章程;1986年11月1日,温州商人杨嘉兴集资31.8万元,创办全国最早的“股份合作制信用社”——鹿城城市信用社。在这些股份合作制企业的带动下,许多企业纷纷起而效之,股份合作制就这样在温州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到1988年全市股份合作企业已有13469 家,到1998年达到高峰时全市股份合作企业达到36887家,其中工业企业27771家,工业总产值192.84亿元,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56.2%[7]。
(二)企业家人力资本在变迁中的作用
从温州股份合作制这个温州众多的制度安排之一来看,其过程完全符合林毅夫[8]所指出的诱致性的制度变迁。股份合作制从个别企业的制度创新,自发演变为群体行为,真正作到了“由个人或一群人,在响应获利机会时自发倡导、组织和实行”的制度安排的演进过程。
学者们在总结“温州模式”的成功时发现了一种机制:来自民间创新冲动和地方政府的支持默许。这种冲动就是源于企业家人力资本的作用。如果不具有旺盛的企业家精神,那么温州就不会出现这么多的中小企业;而如果不是具有良好的组织、管理和资源的整合能力,那么这些企业就得不到很好的发展,就不需要有新的制度安排使这些企业得到更快的发展。如果不是密集的企业家人力资本,那么就没有企业制度的创新。不能想象高居在办公室的人能够发明出股份合作制,“干中学”所给予的企业家人力资本增量,为股份合作制的创新提供了实践的经验。
这种诱致性的制度变迁,由于是在实践中所产生的,而且创新的制度安排比原来的制度更能促进了企业主剩余的增加,因此在这种利益的刺激下,更多的人会去模仿而不断地创办新的企业,制度鼓励了对企业家人力资本的投资。更多的企业家人力资本的产生,导致了可以促进企业发展的更多的诱致性制度变迁的产生,从而实现了循环累积效应。1980年10月13日,温州发放了改革开放后中国第一份私人工商执照,这个制度是国家供给的,是原有的一个制度重新恢复而已[6];但接下去的1980年开始的挂户经营和1981年开始的股份合作制,却是创新的结果,是诱致性制度变迁的结果。它们的出现,代表了对制度集变化的需求,而且是逐步演进的,每当出现了新问题就会产生新的选择,温州的制度变迁正是这样演化的。
在演进的过程中,温州政府不仅保护了各类企业的利益,事实上政府官员的利益也得到了保障——温州经济增长得到了保障,而地方官员的政绩也就得到保障,当时考核官员很注重地方的经济指标。这样,次级行动团体的利益也就得到了保证,所以这样的诱致性制度变迁就得到了实施。史晋川[9]认为温州经济发展已经对温州社会的组织结构及基层政府行为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这种影响表现为地方政府对致力于发展地方经济的企业家的重视。
“温州模式”本质是一种市场解决模式,或者说,是一种自发自生发展模式和自组织模式。其中政府的作用虽然重要,但主要是促进性的、辅助性的、倡导性的作用,而不是经济管理的作用。其动力来源于民间力量和浙江的传统文化,特别是温州的重商文化[10]。但为什么会在温州有自发的发展。一个解释是温州从古至今,包括即使在计划经济的严格控制的时代,其企业家人力资本一直处于不停的发展过程中,所以造成了在温州局部区域内企业家人力资本的高度密集。而企业家人力资本高度密集所带来的一个结果就是企业家精神的丰富,人们希望通过企业的成功而成为成功的标志,进而重复“古典工业化”的历程。在中国改革的初期就温州已经站在了一个企业家人力资本高度密集的起跑线上,改革开放的发令枪响之后,温州人就率先开始了市场经济的实践长跑。
三、苏州强制性制度变迁的实证——企业家人力资本的缺乏的结果
由于企业家人力资本的缺乏,因此在改革初期的苏州经济发展中的政府行为,在一定程度上代替了企业家人力资本的功能。由于苏州乡镇集体企业的产权不清晰,所有者缺位,企业的发展没有像温州那些个体、私营企业那样具有源源不断的动力。因此苏州的改革是自上而下的,动力源自于各级政府。
各级政府提供了制度变迁的设计和动力,然后通过层层的任务分解予以实施,苏州制度变迁的路径明显带有强制性制度变迁的特征。我们将通过一个典型的案例,即80年代初期苏南乡镇集体企业制度的制度分析加以实证。另外90年代初期苏州大规模外资引进、集体企业改制和大规模的工业园区建设等,也是苏州的强制性制度变迁的结果,但将不予以详细讨论。
(一)乡镇集体企业的发展——强制性制度变迁的案例
苏州乡镇企业起源于人民公社时代,但真正的发展却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农村改革之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使得农村分离出大量剩余劳动力,但户籍制度的束缚使得农民“离土不离乡”,进入乡镇企业成为问题的主要解决办法。同时,当时整体上分权改革思路以及地方财政包干制度的实施,刺激了地方政府兴办工商企业的欲望:它既有助于缓解关系社会稳定大局的就业问题,又可以增加发展地方经济所必须的财政收入。于是,出现了一批由乡村政府创办并直接管理的企业,形成了一个地方政府扮演推动角色的乡镇经济格局。其基本特征可概括为:创办和发展企业的资源动员依赖行政权力、产品竞争由市场导向、产权关系具有社区内“公有”的模糊性。企业产品的市场竞争会将市场原则传导到企业的内部关系里来,从而影响企业控制模式和产权模式的改变,是“苏南模式”变迁的基本线索。
这种制度变迁的第一个环节,就是来自于市场的压力使企业逐步从政府那里得到企业控制权的大部甚至全部。企业控制权包括任免企业经理、投资决定、工资奖金和利润分配等三个分项的控制权。在“苏南模式”下,早期这些权力无一例外集中在乡镇党政机构,然后开始向企业和企业经理转移,虽然各分项控制权的转移深度不同,并且在不同企业极不平衡[11]。
包括苏州在内的“苏南模式”,因苏南乡镇企业而生发,而苏南乡镇企业的核心特征是“地方政府公司主义”(Local State Corporativism)。转轨初期,市场秩序尚不完善,乡镇企业具有寻求政府及社区保护的内在需求,借以节约企业的外部交易费用。同时,地方社区政府多数还是乡镇企业发展的最初发动者和资金的提供者。由于乡镇集体企业的上缴利润是地方政府自筹收入的主要来源,而村镇办集体企业在很大程度上是村社区组织行政职能的经济基础。政府对企业超强干预,党政力量在市场领域溢出,集体财产社区“灰色私有”,造成企业经营机制退化,企业负担沉重,失血过多。苏南乡镇企业承担着多重政策目标,如用农村工业支援农业生产,以农民的工业收入补贴其农业收入;用发展乡村工业来巩固和发展集体公有制;提供农村公共产品乃至参与创建、随意摊派;离土不离乡,通过就地工业化避免农村人口向城市的大规模迁移等。江苏永钢董事长吴栋材曾说:“旧苏南模式耽搁了一代企业家的精力,也娇惯了一代农民的依赖性”[12]。
(二)企业家人力资本的缺失和政府的替代
洪银兴[13]认为,苏南乡镇企业的产生和发展离不开社区政府的推动。在当时苏南地区的大部分乡镇企业是由乡镇政府,或者利用原有的集体积累,或者利用政府的动员力量,或者由政府出面向银行贷款兴办的。利用政府职能全力兴办和发展乡镇企业。因此,苏南大部分乡镇企业的创业资本源自社区内的集体投入,其所有制的基本属性便是以社区政府为代表的集体经济。社区政府可以将从企业索取的一部分收入用于社区建设、举办公益事业,可以按规定的标准调度企业的一部分收入用于支农建设,促进社区范围内工农业的协调发展、务工者与务农者的共同富裕。
苏南模式的强政府现象,即政府推动,对于经济发展的作用具有两重性。一方面,“苏南模式”中的政府行为能够随着经济发展的要求而不断进行市场性调整。另一方面,过度的政府干预也可能产生“反市场约束”[14]。
苏南模式的制度创新是一种供给主导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方式,制度变迁的动力和主体主要来自于社区政府。在70年代末期至80年代初中期的中国分权化改革的前景下,中央政府下放了相当一部分管理权,地方政府获得了指导和推进区域经济发展的主动权,能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作出区域经济发展的决策,有了相对独立的经济利益。最终在地方政府的组织和引导下,形成了政府主导供给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
苏南模式的制度创新就始于此。由于地方政府控制了创办乡镇企业的资金、土地等主要生产要素,能借助行政、经济的力量,动员区域内的人力、财力、物力等资源发展本地经济,在动员和组织市场资源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它所形成的投资与发展能力也比乡镇企业自身的能力更大。因此,乡镇集体企业的实际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被社区政府所掌握,政社合一就成为必然。这一阶段,制度创新所带来的巨大效益得以充分发挥,苏南的乡镇集体企业得到迅速的、超常规的发展。
90年代初期,以集体所有制为主体的乡镇企业开始暴露出自身的弊端,如企业积累和发展动力不足,经营行为短期化,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经济实体。苏南模式进行了转换企业经营机制的改革。这时的改革方案,并不是一开始由政府利用强制性权力提出和实施的,而是由一些企业家、经济学家在现实中碰到各种弊端而向政府提出,促其接受这种方案。当然,从改革方案的酝酿、提出到实施,苏南各级地方政府始终扮演着主体的角色。同时,各级地方政府也继续在加大科技创新,引进外资等方面扮演着主要角色。
通过上面的一些学者的研究,可以发现包括苏州在内的苏南各级政府在乡镇企业的形成发展过程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关键的一点就是苏南的这些乡镇企业起源于社队集体企业,因此,在那个计划经济的时代,处于经济中心受到严格控制和存量较低的企业家人力资本使得苏州的私营、个体等非集体企业发展远远不如温州,企业本身只能通过社区的政府来行使企业家的权利。而这样的安排就更加抑制了企业家人力资本在苏州的生成和积蓄。
由于缺乏足够存量企业家人力资本,所以苏州改革开放初期只能通过政府的替代作用,举办社区的公有企业。这样的制度安排,解决了当时的企业家人力资本的短缺问题,但是政府承担了本来不应有政府承担的事项,造成了路径依赖,强化了选择的效应。企业家人力资本的发育被抑制了,于是更多投资于专业人力资本而不是企业家人力资本,造成了专业人力资本的不断的加强而企业家人力资本相对落后的局面[5]。当政府创办的乡镇企业,其利润水平开始下降,甚至出现亏损的情况下,乡镇企业的产权关系就需要明确。所以,苏州的乡镇企业经历了一段时间的发展之后,在2000年就开始了改制和转制,将原来由政府充当的角色还原给企业本身,标志着这种强制性的制度变迁的完成和终结。但随后开展的政府规定的乡镇企业的改制的幅度、比例、时间要求等,以及大规模的工业园区的建设和引进外资,又成为苏州的另一强制性制度变迁的开始。
当然这些制度的形成过程中,并不是由完全政府一手操办的,但是主要的推动力量还是政府。他们从乡镇企业的发展和工业园区的建设,以及大量外资的引进过程中,得到了诸如政绩肯定而获得职位上的提升等收益。因此,在企业家人力资本不够,不能进行诱致性变迁时,以政府为主导强制性制度变迁就有可能一直持续下去。
四、结论
我们从温州和苏州的制度发展中看到,温州诱致性的制度变迁是同温州所蕴藏的密集的企业家人力资本有关,是自下而上的一个过程;而且这个过程一直在持续,富裕的企业家人力资本不断地增加,又不断促进制度变迁;而苏州由于缺乏企业家人力资本,政府充当了企业家的责任,成为区域的经济增长的制度供给者,不断提供新的制度选择,并通过各级政府予以实施。
当然,这样的局面本身也是不断演变与发展的。随着两个地方的区域经济增长、人力资本结构模式的不断演进,制度的演变也会逐步产生变化。如现阶段温州大力推行引进专业人才和吸引外资,苏州则强调发展非公经济等,预示着温州和苏州均会有更多制度变迁路径的选择。
标签:人力资本论文; 温州论文; 苏南模式论文; 股份合作制论文; 制度创新论文; 企业经济论文; 企业创新论文; 实证分析论文; 社区功能论文; 经济学论文; 企业家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