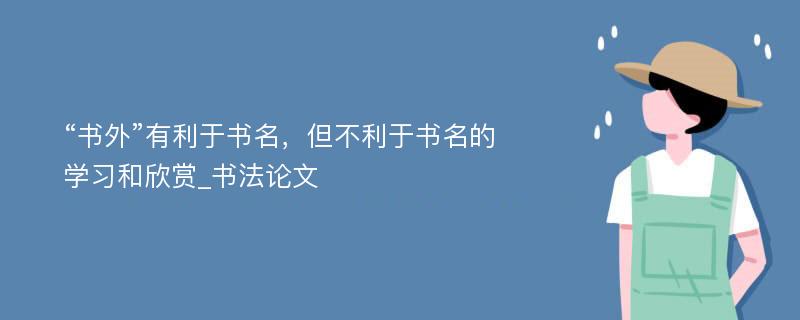
“书外功”有益于书名而无益于学书和赏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外功论文,书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陆游对他的儿子说:“汝果欲学诗,功夫在诗外。”历来论书者即引此来论书,所谓“书之功夫更在书外”,其实学书与学诗是不能相提并论的。
“外功”是指作者的阅历学识、思想修养,作品形式技巧当然是来自作者的“内功”。诗不管优劣,都不可能没有诗的形式,也不可能没有诗的内容。没有诗的内容不可能成为诗,而内容则来自作者的阅历学识。没有高尚的境界不可能成为好诗,而诗的境界则来自作者的思想修养。这样看来,陆游所谓的“诗外功”其实也还是“诗内功”。诗以言志,文以载道,文与诗一样,即必须有形式技巧,也必须有生活才能有内容,有思想才能有灵魂,所以,诗、文都离不开这种虽称为“外功”,而其实却是“内功”的“功”。
书法是诗文的视觉存在形式,它本身其实并无实际的思想内容,所以决定内容以及境界的阅历学识和思想修养这些“外功”也就不可能作用于书法。
历来论者之所以误以为“书之功夫更在书外”是学书之道,其原因是:一、将“人品高,书品自高”这种观者的“书外”感情现象误以为是学书之道;二、将“书以人重”这种“书外”的社会自然现象误以为是评书之道;三、将“书如其人”、“书如他人”、“书状万物”这种书论中描写书法形象的文学语言艺术的比喻手法误以为是书法作品中实际存在,并以此为赏书之道;四、“书为心画”,其实所“画”的是“书内”之心,却误以为“画”了“书外”之心,并以此为作书之道……总之将一切“书外”现象都误以为“书内”所有,因此就以为“书之功夫更在书外”了。
误以为“书之功夫更在书外”是学书之道,其原因除以上所说之外,还因为将书法本身的成功与书法在世人心目中获得的成功误以为是同一回事。沙孟海先生在《近三百年的书学》一文中指出:“艺术的真价值是一个问题,作者名望大小又是一个问题,本不能相提并论的。”
书法本身的成功——作书和赏书,全在于“书内功”。苏轼《论书》云:“笔成冢,墨成池,不及羲之即献之;笔秃千管,墨磨万锭,不作张芝作索靖。”这是说,“书内功”是提高书法作品水平的唯一途径。张旭对弟子也是“唯言倍加工学临写,书法当自悟”。这又说明“书内功”不仅是提高书法作品水平的唯一途径,同时也是提高书法鉴赏能力的唯一途径。
要使书法在“贵耳贱目”的世人心目中获得成功,则全在于“书外功”,而“书内功”简直无能为力。所以苏轼既说“书内功”是书法本身成功的唯一途径,又说“古人论书法,兼论其生平。苟非其人,虽工不贵也。”黄庭坚也说“学书须要胸中有道义,又广之以圣哲之学,书乃可贵。若其灵府无程,致使笔墨不减元常、逸少,只是俗人耳。”书法作品本身的实际水平已经与大书家钟繇、王羲之一样“工”,却因为作者的“生平”、“道义”、“圣哲之学”等“书外功”不及钟、王,其书遂被世人以为“不贵”,其人也被看作是“俗人”,而不是“书家”。这就说明,书名的获得,全在于作者的“书外功”。
因为观者“书以人重”,而不是“人以书重”,所以“书之功夫更在书外”虽然不是学书之道,但对作者获取书名来说却是千真万确,所以,历来凡是著名书家,一般来说都具有相当的“书外功”。从秦、汉始,李斯就是一个政治家,又是写《谏逐客书》的文学家,又是造《仓颉篇》的文字学家。蔡邕,是东汉时大文豪,工散文,善辞赋,通经史,精音律,晓天文,并有书论《九势》传世。王羲之是作《笔势论十二章并序》、《用笔赋》等书法理论家,又是作《兰亭序》的文学家。晋AI写作《平复帖》的陆机,是一位有《陆士衡集》行世的大文学家。唐初四家,也都是著名的学者。后来的孙过庭,是书法理论家和文学家。李邕是有《李北海集》行世的大文豪。草圣张旭,是一个有名的诗人。颜真卿,不仅是一个政治家,而且是一个有《颜鲁公文集》行世的文学家。宋以后的大书家,也大多是诗人、文学家。世传唐代郑虔,清代郑板桥为“三绝”才子。事实上宋以后,不乏“三绝”才子。如宋代苏轼、黄庭坚、米芾、赵佶等,元代赵孟頫、柯九思、倪瓒等,明代唐寅、文徵明、徐渭、陈道复、王宠、倪元璐、黄道周等,清代王铎、傅青主、金农、黄慎、汪士慎、陈鸿寿、赵之谦、吴熙载、赵之琛等皆长诗、书、画。宋以后其余有名的书家,也大多是文学家或大学问家。如宋代蔡襄,元代鲜于枢、杨维桢,明代祝允明、邢侗,清代王文治、刘墉、翁方纲、梁同书、邓石如、伊秉绶、包世臣、何绍基、康有为等等,或长于诗,或长于书文,或长于经史,或长于金石文字。而现代著名书家如吴昌硕、沈寐叟、鲁迅、齐白石、张宗祥、胡小石、高二适、沈尹默、陆维钊、邓散木、郭沫若等等,不是画家、篆刻家、文字学家、考古学家,便是文学家、诗人。以上书家的“书外功”,论者多以为是书法本身成功的阶梯,其实是获得书名的阶梯。不论是盛名之下,其实难副,或名实相符,要使书名家喻户晓都有赖于“书外功”。
然而,有“书外功”并不一定有益于书名,而只有当“书外功”具有一定的知名度,才有益于书名。当然,书名也同样有益于“书外功”的知名度。因“书外”的诗名、画名等等而有书名,或因书名而得“书外”的诗名、画名等等,都是屡见不鲜的。有不少“书外功”因为观者不存在知与不知的问题,所以作者也不存在遇与不遇的问题。所以,这些“书外功”一旦与书法结合就立即产生轰动效应,其人、其书也因此而声价陡增。例如巨型书、微型书、双管书、悬墨书、气功书、指头书、舌头书、以袖书、以头书等等。让观者满足于书写行为的视觉效果,淡漠或无视书迹本身的书法艺术效果,于是一举成了“著名书法家”,其实是“书写行为的艺术家”。
然而,一般所说的“书外功”,其实也与“书内功”一样,知名度的高低又并不等于“功”本身的高低。甚至“功”越高,知名度反而越低。“圣教难仰,曲学易尊”、“曲高和寡”、“至人晦迹”,这些古话所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所以,如果因追求书名而寄希望于尚未显之于世的“书外功”其实也难以遂愿。
不管是“书内功”或“书外功”,要获得一定的知名度,都必须有赖于另一种“书外功”。据说有一知书者当面这样质问一位颇有名声的书家:“像你这样的书法水平,社会上多得很,超过你的也不少,但为什么你的书名居然远在他们之上?”书家答曰:“我的实际书法水平虽然不及他们,但我的‘书外功’却远胜过他们。既然‘书之功夫更在书外’,我的书名远在他们之上又有什么可奇怪呢?”知书者忿然作色,于是想进一步证明其书并没有体现“书外功”,然而又实在无从着手——论字,字并没有写错;论文,文理也还可以;论书,时尚已经撕破了书法的统一标准,早就置历来所公认的共同意识于不顾,而唯以“主体意识”为贵,而“主体意识”如何,他人是无权干预的。于是这位知书者一时语塞,因为他还不曾悟出这位书家所说的“书外功”其实是另一种“书外功”,即如何用世的“书外功”。
“只知耕耘,不问收获”、“君子谋道不谋食”,这样的思想境界毕竟只有少数圣人才能绝对做到。作为大多数人来说,无论是名或实,无论是大道之名或小道之名,多少要体现人的争强好胜的本性。尤其是商品意识渗透一切领域,“竞争机制”不断被强调的今天,能“安贫乐道”的书家更是越来越难得了。必须指责的是只知收获不问耕耘、只谋食不谋道,而既收获也耕耘,既谋食也谋道,还不失是本分。况且,如何使学有所长者名实相符,这也是人类必须为之不断奋斗的理想之一。这种理想的实现,固然必须有合理的社会制度,必须有各行各业的伯乐,但本人能自用其才也是一个方面。即使在黑暗、乱世之中,能为国为民作出有益的贡献的人毕竟也不少,因为他们能自用其才。然而,以贾谊之才,况且又遇到了汉文帝这样的好君主,却仍然嗟叹“逢时不祥”。他无力改变“斡弃周鼎宝康瓠兮,腾驾罢牛骖蹇驴兮,骥垂两耳服监车兮”这样的现状,因而不能自用其才。所以苏轼感慨地说,学成一种本事并不难,而如何用这种本事才是难事。书法这种本事如何用世,当然同样也是难事。
其他“书外功”的工作对象是“物”,如何用世的“书外功”的工作对象却是“人”。书法赏鉴是人的一种行为,能诱导人的行为的“书外功”,当然是最利害的“书外功”。这种“书外功”又可分为如何管理书家和如何推销书法这样两种。
有管理能力者当然也可以同时具有“书内功”,但不具“书内功”,只具管理的“书外功”者也同样可以管理书家。张荣庆先生在《“书法热”中之思考》(《书法》一九九三年第二期第三页)一文中指出:“说实在话,对书法界担任领导工作的同志,人们的要求并不太高,只要能充分发挥其组织领导才能,把好关,把全国的或一个地区的书法事业搞上去,人们就会拍手叫好。这些领导同志如能同时有渊博的学识,又能写一手好字,那当然更好,写得不好,人们也会原谅。然而,现实当中令人感到不大正常的是,某些人字写得很一般,可是在一些重要展览中,总是少不了他们的大作,而且非要堂而皇之地挂在前面不可,这算怎么回事?不客气地说,这叫领导带头搞庸俗化。领导理论工作的,人品次、学术水平不高的也有;还有的人和字皆极俗,每次大展都落选,但因为是书协干部,就得照顾。这同样是庸俗化的表现。以上这种状况,眼下似乎也“不大好改变”。因具有管理书家的“功”而浪得书名,而且这种状况居然“不大好改变”,可见这种“书外功”的利害!
作为精神产品的书法,与物质产品一样,都有生产、推销、享用三个环节。物质产品如果是伪劣,即使在购买时眼睛上了当,但经使用后,迟早也必定被发现。譬如,要治病,吃了所谓的良药反而致死;要自杀,吃了所谓的毒品却仍然活着,于是伪劣就被证实了。书法作品则只有观赏的功能,而并无供使用的功能,所以如果不能在观赏中辨其优劣真伪,也就没有其他的鉴别办法了。因此,如何推销“书外功”对书名就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质量第一”反而很次要了。
虽说历史是一面镜子,时间将会作出正确选择,但也未必如此。正确与谬误无时不在较量,时而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时而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到底是谁压倒谁,就要看各自这种“书外功”的大小了。书名显赫的沈尹默先生对自己百年之后并不抱自信。他在《与豫卿(按:先师朱家济先生)夜话因赠》一诗中云:“豫卿誉我字,可当名迹看。长留一卷诗,百年谁能断。纸素非坚牢,时尚易昏旦。光光晋武迹,宋贤犹得见。知微不敢收,元常遂莫辨。就令尊王书,毋乃爱轻倩。传与不传同,右军无真面。寂寞身后事,真赏实亦幻。点染四十年,真欲弃笔砚……”书法名家谢世后,如果无人为他继续推销,或虽有人推销,但推销者的“书外功”不足以战胜对方,那末,原先的书法名家。其书名也就逐渐暗淡。沈先生的感叹正是这个意思。
推销书法,获取书名,可请经纪人,然而这是得益于他人的“书外功”;能自产自销、自我包装,才说明书家本人具备“书外功”。这种“书外功”通于用兵、经商之道。笔者以为可以先熟读《三十六计》、《孙子兵法》、《智谋大全》、《处世奇术》等书籍。这类书,因近年商品经济的发达,所以很畅销,也可到处买到。还可以借鉴近年发行的《行为科学》、《公共关系报》等报刊。《行为科学》主要有“创业指南、买卖趣谈、官场心得、关系探幽、处世技巧、名人行为……”等内容。《公共关系报》“突出企业公关,谨献科学实用的公关谋略,帮助企业塑造完美形象,解决经营难题,打开市场之门……”又广告曰:“订一份《公共关系报》,等于请一个公关顾问,可助事业成功。社会关系千变万化,人际关系错综复杂,要想关系和谐融洽,《公共关系报》期期到家,《公共关系报》属于大家”——当然也属于书法家!既知古典的奇术,又知眼下的新鲜谋略,并与书法具体情况相结合,然后付诸实践,达到运用自如,而不露任何痕迹,方是“书外功”。
浑身是“书外功”,却又不露任何痕迹,这一点是很要紧的,否则效果适得其反。当你准备向世人发出强大的“书外功”时,必须先将“书外功”加以伪装,然后发“功”。必须使受“功”者将你因强大的“书外功”而取得的显赫书名错以为是因为强大的“书内功”,这才是炉火纯青的“书外功”。如果你看了本文,对“书外功”有了新的认识,又因付诸实践,并获得可喜的书名,那么,对这一切,你必须懂得永远保守秘密。
随着“书外功”不断深厚,书法的知名度也就不断提高,最后达到家喻户晓,路人皆知。然而,要从“贵耳贱目”的书法外行心目中获得成功固然在于作者的“书外功”,而不在于“书内功”,但要从真手真眼的内行书法观众的心目中获得成功,却也与书法本身的成功一样,仍然只需“书内功”,而不必“书外功”。如果作者“书外功”大于“书内功”,因而名高于实,那末,内行的书法观众对其人其书反而产生厌恶,因而书名仍低;如果作者的“书外功”小于“书内功”,因而名低于实,那末,其人其书都必然为内行的书法观众留下良好的印象,因而书名自高。
我们绝不责怪书法外行,因为他们各自都埋头于比书法更为重要的工作,他们各自都是“书外”某些方面的内行;我们只能责怪我们自己——使书名家喻户晓,其实是一个并不美妙的愿望。书画家诸乐三先生刻有一方“宠为下”印章,刘熙载《书概》也说:“书非使人爱之为难,而不求人爱之为难。”这些话值得我们深思。他所指的“人”,当然是书法外行。
所有的书法外行都认为不是好书,所有的书法内行都认为是好书,这已经是最佳的状态了,又何必家喻户晓、路人皆知!
“书之功夫更在书外”,这是一句外行话——如果出于书法内行之口,但愿他所指的是获得书名之道,是社会自然现象,而并非他自己所遵奉的学书之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