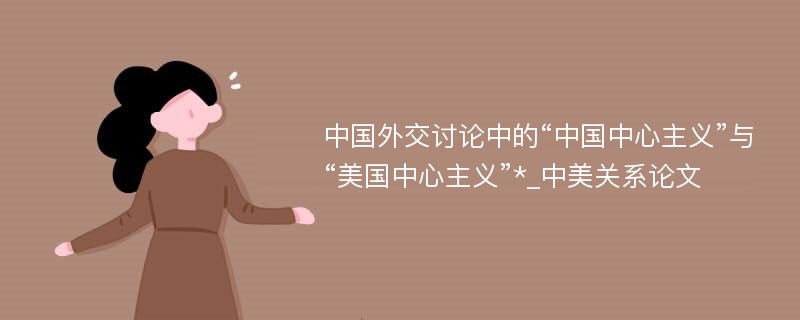
中国外交讨论中的“中国中心主义”与“美国中心主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主义论文,中心论文,美国论文,中国论文,中国外交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9550(2008)12-0062-09
一个国家的民众和精英对历史与现实的解读和对未来的期盼可以看成是这个国家国民心态(national psyche)的一部分。这种国民心态特别是外交精英的心态潜在且广泛地影响着国家对外交往的思维与行为方式。本文试图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①对目前较少研究但却深刻影响着中国外交讨论的两种心态——中国中心主义(Sino-centrism)与美国中心主义(U.S.-centrism)做个初步考察,探析它们对中国外交讨论的影响。笔者期望这一研究有助于我们对自身的心态有更为客观的认识,从而让中国的国民心态能够逐渐走向成熟和理性。同时,我们也希望这种讨论能够有利于推动社会心理学在政治学中的应用性研究。我们试图表明,即便是以社会心理学中一些众所周知的心理特征(traits)为出发点,社会心理学方法也能够为审视一些政治学的问题提供一些新的启发。
在进入实质讨论前,我们需要做几点说明。
首先,中国中心主义不等同于爱国主义。我们批评中国中心主义不是要我们放弃捍卫国家利益,恰恰相反,我们认为严重的中国中心主义不可避免地导致国家外交行为的失调,从而损害中国的国家利益。同样,中国外交讨论中的美国中心主义不是指我们对美国作为唯一超级大国这一现实的承认,而是一种对美国的近乎迷恋(obsession),即或者盲目崇尚、或者盲目敌视的心态。因此,我们批评中国的美国中心主义不是要求我们否定美国的超级大国地位,而是希望我们能够用更加理性和系统的眼光来看待美国对中国的影响。
其次,我们强调这两个重要的心态并不意味着没有其他的心态也在影响中国外交讨论。我们仅仅是强调这两个心态对中国外交有着重要影响(因而也就危害性越大)。此外,我们更不否认物质力量(比如国家力量)同样影响着国家的外交政策。
另外,我们批评中国外交讨论中的这两个重要的心态也不意味着只有中国才受到不健康心态的影响。比如,所有的国家(当然也包括美国)都受到自我中心主义的困扰,而且不同国家的自我中心主义在本质上是极其相似的,甚至是彼此的镜像。
再次,尽管本文会涉及这两个心态的起源,但我们在这里不对这个问题做深入的探讨,而将主要目的放在发现这两个心态并且探讨它们对中国外交政策讨论的影响上。
最后,尽管我们对这两种心态持批评的态度,但这不意味着我们否认中国的外交政策取得了长足进步。事实上,我们的目的是为了促进中国的外交政策取得更多的进步:只有意识到这两个几乎无时不在影响我们思维的心态对外交政策制定的可能危害,我们才能试图去克服这两种心态。
一 中国中心主义
中国中心主义心态是自我中心主义(ego-cen-trism)和自大主义(egotism)的奇特混合体。②
自我中心主义是一种普遍的心态,它是指习惯用自己的眼光来看待世界(包括自己),而不能用他人的眼光来看待世界。从社会进化的角度看,③每一个人和每一个群体必须是一定程度的自我中心主义者,因为这是进化进程中追求生存的选择结果。国家也是自我中心主义的,而在那些曾经一度强盛的国家,它们的自我中心主义心态往往更为强烈。中国外交讨论中的中国中心主义有两个要素,这两个要素相互依存,相互加强。④
首先,中国中心主义心态导致我们不能用他人的眼光来审视自己和外部世界以及中国和外部世界的交往,并且缺乏客观了解其他国家的动力。
比如,我们习惯把邻近国家说成“周边国家”。这一标签的潜台词就是我们是中心。我们对邻近国家的理解在相当程度上残留着许多过去中华朝贡体系的影响:我们天经地义地认为邻近国家也和我们一样,怀念或至少是相当认可中华朝贡体系。而事实上,邻近国家并不认同我们对历史上中华朝贡制度的正面理解。⑤
1978年,邓小平访问新加坡时意欲联手东南亚国家孤立“北极熊”,却发现这些邻国想共同孤立“中国龙”,他对此表现出极大的“错愕”。⑥这实际暴露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中心主义心态影响下的我们对邻近国家政府与民众的不了解,以至于产生了在中美准结盟情况下东盟会对中国要求一呼百应的错觉。这件事情虽然过去近30年了,但我们对邻近国家的研究依然停留在相当肤浅的水平,更没有有意识地去培养一批能够透彻了解邻近国家政治、经济、社会、历史、民族和宗教的专业人才。⑦因此,一些地区国家的领导人将美日同盟视为“地区公共财产”时,我们就难免表现出错愕、不解甚至愤怒。我们没有看到,尽管目前“中国威胁论”在邻近国家已不再有往日的市场,但是邻近国家对中国的疑惧心理还远没有消失。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有一段时间执行“输出革命”的外交政策,某种意义上也是有中国中心主义的心态在作怪:我们又可以为我们的邻近国家乃至远在非洲的兄弟国家做出表率了。正如章百家指出的那样,“在一个想象中以中国‘文化大革命’为起点的世界革命中,中国人似乎重温了那种中国是‘世界中心’的旧梦”。⑧
其次,中国中心主义使得我们的一些精英和民众有一种几乎是潜意识的心态:中国应当是伟大的,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未来,或者说是一种“天赋伟大(‘natural’greatness)”。事实上,国家无所谓“天赋伟大”:一个国家只能是伟大或者不伟大,而这一结果最终取决于人民的福祉是否得到充分保障和国家是否强大,而不是民众和精英们心目中对国家的想象。
“天赋伟大”最明显的体现是我们的精英和民众对中华文化产生的经久不衰的优越感:两千年中国在东亚地区秩序中的中心地位给这种心态提供了可供想象的基础。中华文化对外族武力入侵与统治所具有的巨大消化能力获得国内学界的广泛认可。历史上蒙古族、满族等民族统治被包容性极强的中华文化所融合,成为论证这一观点的范例。大众媒体上经常出现的对“汉唐盛世”的讴歌也是这种情怀的体现。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为中华文化复兴提供着更强的动力,这种文化上的优越感正在得到加强。有不少人相信据说是来自汤因比(Arnold Toynbee)的断言:“中国如果不能取代西方成为人类的主导,那么整个人类的前途是可悲的。”⑨
面对“9·11”事件后国际局势的混乱与美国在中东的困局,有学者提出,“解决民族冲突只有中华文化”,⑩“世界治理需要中医”,“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明模式——治理世界的西医出了问题”。(11)有学者已经开始建构全球化条件下新的世界政治哲学理论,否定西方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国际政治并试图以中国古代的“天下”观作为未来世界秩序构建的理论基础。(12)这样的理念在国内获得了相当的反响,因此有的学者就根据这一建构,提出“范式转移”而非“权力转移”正在成为国际政治发展的趋势,并力图证明中国在国际政治哲学上对美国的超越:美国的霸权不可持续,而中国的“王道霸权”却是有可能的。(13)而针对“到处都是你争我夺”的世界,“在北京奥运会上将孔子抬出来”的建议更彰显部分国人文化优越心态的上升。在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向西方学习之后,我们的一些民众和精英正在重温以中华文化的思维方式来实现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大同”的梦想。(14)
上述两个要素是相互强化而不是独立的,因此,除了这两个要素的“独立”体现外,它们之间的相互强化还会造就一些更加具体的体现。
首先是我们的精英和民众中强烈的文化和民族自卑感。在我们的精英和民众中,与中华民族“天赋伟大”心态并存的是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差距下形成的强烈的文化乃至民族自卑感。而强烈的文化和民族自卑感与中华文化优越感是“中国中心主义”这枚硬币的正反两面。
中国中心主义心态的存在使得我们在潜意识里不自觉地以历史上辉煌的国际地位来看待、衡量今天与未来中国的力量与影响。在世界范围内,当前超级大国与西方国家对中国崛起时隐时显的遏制行为,让我们无法超越中国从一个中心国家衰落到国际社会最低层的“百年屈辱”。在亚太地区,美国、日本对东亚区域一体化的掣肘以及一些邻国对中国的不信任情绪使我们难以找到大国乃至地区强国的感觉。在国内,大量政治、经济和社会的问题与矛盾以及台湾岛内的分裂主义倾向,也使许多人感到中国仍缺少成为强国的国内基础。在文化上,与历史辉煌时期的“八方来仪”情形相比,当前“中国的大学普遍成为西方高等教育体系的‘预科”’等现象,让我们感到“中国并不是世界知识生产的中心。在全球知识结构中,中国基本上处在一个劣势的地位……到目前为止,世界感受不到一个十三亿人口的大国对全球治理的重要思想、观念或者知识的贡献”。(15)这一距离中心国家的巨大现实差距不可避免地让我们的许多国民和精英产生了巨大的心理期待落差。
其次是“阿Q”式的自欺欺人。因为现实的中国和理想的中国之间差距是如此巨大,我们的国民和精英的优越感和挫折感就不得不靠“阿Q精神”来获得一点满足或安慰,这具体表现在对我们的发展成就时有陶醉,与此同时,我们又会对有的西方人不能承认中国已经是一个伟大国家感到愤愤不平,或是对有的西方人对中国已经是伟大国家的承认(许多时候可能只是虚伪的溢美之词)感到甚是满意。
显然,这一表现是建立在中国中心主义的两个要素之上:“天赋伟大”的自豪感必须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他人的承认才能被满足,而强烈的自卑感也必须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他人的承认才能被压抑住,(16)并且两个表现也是紧密相连的:别人的承认,哪怕是虚伪的,会给我们带来愉悦;而别人的不承认,哪怕是真实的,也会给我们带来不快。这种心态在申办2000年奥运会这一事件中得到了集中体现。我们的一些精英和大多数民众都将申办2000年奥运会的成功看成是世界对中国的(历史的,想象的?)大国地位的承认,而将申办的失败看成是世界对中国的(历史的,想象的?)大国地位的否定。而事实上,我们还远不是一个世界性大国。
最后是对中国自身地位的战略幻觉。20世纪80年代,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把中国定位于亚洲“地区力量”,引起中国的不满。(17)1999年,已故的英国学者杰拉德·西格尔(Gerald Segal)在发表的《中国重要吗?》一文中,(18)用傲慢的语言将中国定位为一个“二流国家”,激起了我们许多精英的愤慨。《人民日报》为此还发表了评论员文章予以驳斥。(19)学界主张把中国定位为“世界大国”者大有人在。直到近年,中国应该是具有世界影响的地区性大国的定位才为更多人所接受。(20)但是,忽视中国仅仅是国际体系的重要参与者而非领导者的现实而将中国视为一个世界中心国家的幻觉依然在一些人的心目中存在。我们对国内生产总值(GDP)数字上不断超越一些西方大国有着莫名的兴奋。一些学者在“北京共识”上的心态也同样折射出我们的一部分精英中的中国中心主义。许多人肯定乔舒亚·库珀·雷默(Joshua Cooper Ramo)提出的“中国发展模式”及其内容,(21)而在这种认同的背后则是对中国成为世界的一个中心国家(或者世界中心一部分)的期盼和想象。在我们对“北京共识”的讨论中,费正清对于中国中心主义心态的概括值得深思,“中国为各国做出表率,但别国是否走中国的道路则取决于它们自己”。(22)
二 中国的美国中心主义
1998年2月,奥尔布赖特在为美国向伊拉克发射巡航导弹的行动辩护时说,“如果我们不得不使用武力,那是因为我们是美国。我们是不可缺少的国家。我们站得高,看得远”。(23)这是美国人自我中心主义心态的一个例子。美国人的美国中心主义主要根源于美国长期处于国际体系中心这一政治现实,而中国人的中国中心主义主要来自于历史经历与未来成为世界中心一部分的渴望。美国人的自我中心主义与中国的自我中心主义只有程度和具体表现上的差异,却没有本质区别。
中国人的美国中心主义则是超越了对美国作为唯一超级大国现实的承认,而在美国全球权力引力下形成的一种对美国的近乎迷恋,即或者盲目崇尚、或者盲目敌视的心态。通俗地说,就是一种“又爱又恨”的心态。在这里,我们想强调,世界各国当中并非只有中国社会怀有美国中心主义的心态。英国要维持“英美特殊关系”,印度在谋求其他国家对其大国地位承认时更加重视美国的承认,都是这些国家的美国中心主义的体现。但是,美国中心主义在这些国家的存在并不意味着我们不应该反思我们的美国中心主义。
世界上部分国家产生美国中心主义的共同根源在于,一是美国在全球战略格局当中稳固的中心地位与持续的实力;二是与美国合作可以满足一些国家成为地区中心或是世界中心的一部分的心理需要。对于中国而言,其美国中心主义的产生还有两个特殊因素:一是美国在台湾问题上所具有的分量;二是美国和新中国一直在持续的意识形态对峙(尽管现在这种对峙没有美-苏/中在冷战时期的意识形态对峙那么强烈)。这些因素让美国在中国人心理上投下了巨大的阴影,而我们容易夸大美国对中国未来的影响力以及美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影响力。
中国的美国中心主义主要有以下三个基本特征:
首先,许多人认为“美国是宇宙的中心”。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扩大,我们逐渐意识到美国的强大。冷战后美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制度创新、技术创新、人才培养机制、研发投入、劳动生产率等继续领先其他发达国家,而这些都意味着欧盟、俄罗斯、日本、中国和印度等都难以挑战美国在全球战略格局中的主导地位,而且其差距可能还在扩大。
中国的美国中心主义却不仅仅停留在这些对美国力量的客观承认,而是我们几乎将美国看成中国国际环境的全部,或至少是唯一的中心。更具体地,它体现在这样一种简单的思维:只要搞好同美国的关系,中国的国际安全就基本上能够万事大吉,或至少不会出大乱子。因此,“当1997~1998年中美实现最高领导人互访后,中国学界安全战略研究呈现出一片歌舞升平的景象,仿佛只要中美关系健康稳定,中国就可以欢呼胜利,高枕无忧。而在1999年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后以及布什上台采取了一系列对华的强硬政策后,整个学界在震惊和哀叹后陷入一片黑暗的境地”。(24)这表明,中国的美国中心主义在20世纪90年代曾一度十分膨胀。
从根本上来说,中国的美国中心主义反映了我们不能用系统性的思维去理解国际政治。我们习惯了用一种简单的辩证法看待一个复杂体系的国际政治:许多人认为只要抓住中美关系的一个主要矛盾,其他的问题就都好办了。(25)而事实上,国际政治是一个复杂的体系,我们必须用一个系统的眼光去看待它。(26)主要矛盾无论多么重要,都不能决定一切。况且,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在很多时候是可以相互影响甚至是可以相互转化的。
其次,许多人的思维中有了潜意识的美国思维定式,不能够更加独立地思考。改革开放,向西方特别是美国学习先进的文化、制度理念和文明的生活方式,是中华民族追求国家强大、渴望进步、追求先进的需求。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一些学者(包括一些很“反美”的学者)却已经不知不觉地完全接受了美国思维定式。
一些学者认为,“从价值关系角度看,中国仍然没有完全融入‘国际社会’”,并且将“外部世界”(显然主要指的是美国和西方世界)对中国的猜疑和不信任的根本原因归结于中国与世界的价值冲突。(27)在这种思想里,中国自己应该坚持的一些道义标准和认同将不再有任何地位,中国的唯一出路是“美国化”。(28)因此,我们经常下意识地用美国的力量特别是行为和价值标准来衡量中国的力量和行为,用美国的国际政治逻辑来想象中国的国际政治逻辑。一些(非常“反美”的)学者不知不觉地接受了美国/西方的强权政治哲学,提出“全球化过程不能不包括军事自卫手段的全球化”,要军事保护国家利益(包括商业利益)边界。(29)这些人士似乎忘记了这种思想和我们一直以来都谴责的“炮舰政策”没有任何区别:鸦片战争就是英国用炮舰来保护其商业利益而直接造成的!
最后,“只有美国的赞美值钱”。前面我们提到,因为现实的中国和理想的中国的差距是如此巨大,我们的国民和精英的优越感和挫折感就不得不靠自欺欺人来获得一点满足或安慰。而这个时候,美国的赞美是最能够满足我们的“阿Q精神”的。因此,我们特别喜欢基辛格、布热津斯基等美国人物对中国的肯定与赞扬:他们对中国的肯定与赞扬,无论多么微不足道,一定是被详细报道的。这种中国精英对美国人的赞许和承认的极度需要和享受是如此之强烈,以至于连《中国可以说不》的作者都不能摆脱。(30)相比之下,许多其他国家对我们的评价在我们的眼里分量则轻多了,我们恐怕只有在需要这些国家在联合国的投票时才会想起来原来还真有些国家其实对中国并非无足轻重。
总之,世界上恐怕没有一个国家能像美国这样让中国人为两国关系的时好时坏而牵肠挂肚,或喜或悲。我们的精英和民众中都不乏随两国关系跌宕起伏而对美国时而憧憬时而愤恨者。外交讨论中对美国地位的过分崇拜不可避免地影响了学界与国内的新闻媒体,进而扩大了民众对于美国力量的过度感知。美国中心主义对中国外交的负面作用是多方面的。
比如,美国中心主义心态极大地限制了中国的外交视野。“中美关系是重中之重”的提法是这种心态的最显著体现。在这样的心态下,“我们在中美关系改善时,往往太过于陶醉,而忘记了这种改善给一些国家带来事实上的或者虚幻的压力,没有及时主动与这些国家改善关系,缓解它们的担心,避免其采取有损中国利益的反措施。而当中美关系回落到低谷时,我们才又想起其他国家的存在,急急忙忙寻求同这些国家改善关系。可这时候,这些国家开出的改善关系的价码又很高”。(31)美国中心主义的存在使我们忽视了对邻近国家及世界其他国家与中美之间的多边互动关系,丢失了系统思维的方法,把中国的外交环境看得过分简单化。
美国中心主义心态也是中国对美国不对称依赖背后的一个重要因素。比如在金融领域,我们认为美国是财富的象征和国际金融体系中最后的安全岛,中国的外汇储备在相当一段时间几乎全是美元。而中国国家投资公司的投资对象几乎都是美国的金融公司,这与中国国家投资公司成立时的一个目标,即使中国的外汇储备结构多元化背道而驰。这种对美国金融体系的过分依赖使美国获得了一种奇怪的影响中国的能力:中国是债权国,美国是负债国,美国却可以以此来给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等经济问题不断施加相当的压力。(32)在这种心态下,也许美国正在经受的次贷危机都不能够让我们对美国和它的金融体系有更加理性的判断。事实上,美国人也是人,同样会犯错误。
三 中国中心主义与美国中心主义的相互作用
“两个中心主义”在我们的国民和外交精英中是并存的,而且有着明显的互动关系。
一方面,对美国持迷恋心态的学者及国人相信,与美国这个世界中心国家的合作可以扩大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使中国迅速成为世界中心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对美国主要持否定心态的学者及国人则相信,美国是中国安全与发展的最大障碍(而不仅仅是潜在的最大外来威胁),因此中国要成为一个中心大国,必须要打破美国对华遏制才能有自己生存和发展的空间。总之,我们认为这两个“中心主义”几乎一直都是相互加强的,而这种相互加强对中国外交思想的形成和实践构成实质的危害。
首先是“中美共管”地区与世界事务的梦想。既然中国在国际体系绝不可能,或者至少暂时不能成为世界的唯一中心,那么推动地区与世界事务的“中美共管”同样可以缩小一些学者与国人想使中国成为中心国家的心理期许。当前中美在一系列地区热点问题上的有效合作以及某些美国人士提出中美成立“G2”或者是“战略联盟”,(33)似乎给“中美共管”的想法提供了某种现实的支持。
其次是“美国衰落后,舍我其谁”的心态。中国中心主义心态容易产生美国走向衰落的愿望思维。中国中心主义的心态使我们相信美国的世界霸权极不合理,极不可持续。美国内政外交出现的问题与困境成为一些学者认定美国走向衰落的证据,而对于美国经济优势和霸权力量的持续能力则愤愤不平或视而不见。因此,不少学者不自觉地将世界政治多极化的过程当做一种即将到来的多极现实,不愿承认美国在世界政治秩序中的中心地位在相当长的时间会保持稳固的可能性。
更有人认为,随着中国的不断崛起,中国可以甚至必定取代美国成为世界中心。当前,国内部分人士推崇历史上以中国中心主义为思想基础的所谓“王道”,认为其优于以美国中心主义为基础的美国“霸道”。其潜台词是,中国的“王道”霸权能够超越美国的“霸道”霸权。(34)这些人似乎从来不问为什么美国霸权不行,中国霸权就一定行?况且,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王道”与“霸道”之间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在大多数情况下,“王道”只不过是霸权国对自己“霸道”的粉饰。从本质上讲,任何国家的以文化优越论为基础的自我中心主义都是其追求全球或地区霸权主义的重要思想基础,也是一种“乌托邦”思想。(35)无论是“王道”还是“霸道”,无论是仁慈霸权还是强制霸权,都与中国提倡的国际关系民主化主张根本背离。
最后是“周边国家”是中美棋子的心态。我们几乎是无意识地将发展与地区国家的双边或多边关系当做了处理对美国关系的手段: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发展与地区国家的双边或多边关系在中国的外交中基本上没有它自己的独立价值。这种思维不可避免地对中国的睦邻外交带来负面影响,并且从根本上阻碍了我们与地区国家建立更加坚定的互信。
正如前文所述,“两个中心主义”均使得我们容易忽视研究近邻国家和加强与它们的关系。中国中心主义使我们不能从这些国家的角度来看待它们对中国的行为和思考。美国中心主义让我们从心里没有兴趣去多了解这些国家,仿佛只要中美关系一好,这些国家一定会对我们友好备至。这种心态集中体现在很多中国学者在讨论中国与近邻国家的关系时,都会花上大量的笔墨讨论美国因素特别是美国对其他国家对华政策的影响,仿佛我们的近邻国家也和我们一样迷恋美国。我们忽视了一些近邻国家认为发展与中国的关系有其本身的重要价值。因此,中国学者在许多地区内的国际学术会议上的发言让许多地区内的学者感到中国对地区的理解几乎是美国式地缘政治算计的翻版:“美国人心中只有反恐与预防中国篡夺地区领导权”,而“中国人心中只有‘中美共治’或者是取代美国”。在这样的心态下,中国的近邻国家很容易产生这样的认识:中国只是将它们视为中美地缘政治较量的工具,而中国随时都有可能在某种背景之下牺牲它们的利益。这样的认识将严重阻碍中国与地区国家建立更加坚定的互信。
这样的综合结果是中国给自己上了一个“美国套”。中国中心主义让我们从未仔细地去研究地区国家,从而也就不能从地区国家的角度来看待我们的外交行为(包括中美关系)。美国中心主义心态又使我们难以摆脱美国所设定的地缘政治游戏。一些学者与新闻媒体对于美国周边联盟的言辞挞伐和抛弃不结盟政策的所谓大国战略建议进一步加重了美国的对华防范意识,加深了邻近国家对中美战略较量与对抗的感知。在这样一种状态下,中国学界也就难以提出超越“中美核心之争”的建议,而“地区内国家则会真的围绕中美较量寻求力量平衡与自身利益”。美国的地缘政治游戏与我们的美国中心主义心态已经制造了这样一种心理困境:任何地区倡议,只要它出自中国,就会引起美国与地区国家的怀疑;如果它不是出自中国,但只要中国积极参加,美国与地区国家同样怀疑中国带有限制美国的意图。(36)这是一个我们给自己设定的“美国圈套”。
四 结语:塑造“普通民族国家”的国民心态
我们希望本文对中国中心主义和中国的美国中心主义的初步讨论是克服这两个不健康心态的开始。我们也高兴地看到在和许多同仁的交流中,大多数同仁都承认这两种心态的普遍存在。许多同仁也意识到中国中心主义并不等于爱国主义,迷恋或憎恨美国的美国中心主义也不是爱国。
值得肯定的是,这种状况目前开始得到一定的改善。“周边是首要,大国是关键,发展中国家是基础”的提法无疑是对“中美关系是重中之重”的一种积极矫正。
更重要的是,一些同仁已经能够自觉地注意摆脱“两个中心主义”的束缚和影响。比如,对于一些美国人士和媒体不断吹捧中国正在迅速崛起的“软力量”,(37)甚至对“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的提法有了一些相对冷静的认识。(38)有学者能够用更为冷静的心态来看待所谓的“北京共识”:他们明白将“北京共识”与“华盛顿共识”比肩之后,制造一个新的“中国威胁论”和中西不同价值观意识形态之间的冷战就变得易如反掌了。(39)尽管作为一个单独的国家,美国仍然是而且仍将在相当长时间内还会是中国外交考量中最重要的国家,但由于地区国家(或者说邻近国家)在中国外交中的分量增加了,所以美国在中国外交中的比重相对有所下降。(40)学界同仁已经注意到完全从美国角度看问题的危害,从而提出思维方式上的“去美国化”,或者“别再用美国视角看世界”。(41)
但是,在试图从其他国家特别是近邻国家的角度来看待中国的思维和行为这一点上,我们仍然有巨大的差距。要真正将中美关系放在国家对外关系的大系统中去把握,还需要在实践中更加彻底地摆脱中国中心主义和美国中心主义的影响。而只有中国中心主义有所淡化,我们才能更愿意倾听近邻国家的声音,才能使我们易于与地区主义、全球主义的思想共存与交流。我们还必须让发展与地区国家的双边或多边关系在中国的外交中有它自己的独立核心价值。在发展与地区国家的关系上,我们的准则应该是“善(对中国和地区国家而言),虽美国不悦仍需为之;恶,虽美国悦亦不能为之”。(42)
替代“两个中心主义”的应该是一个“普通民族国家”的国民和精英心态。一个普通民族国家是中国在国际政治中最恰当的国家定位和国际身份,而“地区性大国”应该只是一种对国家实力的恰当表述,“负责任的大国”则是我们对自己行为的期待和描述。这些标签都不应让我们的国民和精英的“大国心态”太过膨胀。否则,就与我们“坚持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的政治呼吁相悖离。我们也不要无时无刻想象中国已经是中心或者是马上就要成为中心了(无论是通过和美国共治或者是替代美国),这样反而可更加理性地和美国交往。
这样一种心态可以让我们更好地与近邻国家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平等交流,发现原来可能被双方忽视了的共同价值观,而不仅仅是重视我们和美国/西方价值观之间的差异和共性。显然,发现并拓展与近邻国家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共同价值观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探索发展中国家的各种发展模式,推动基于公正合理原则的国际关系和国际秩序,并在这个基础上,达成“加强同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和务实合作”,实现“加强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合作”(43)的目标。
这样一种心态可以让我们更好地以一种平和而不是自傲加自卑的心理与西方发达国家交往。包括中国、美国以及其他历史强国在内的国家的盛衰是世界历史中的事实。中国近代衰落与复兴也没有那么特别,中国不需要为此感到自卑和骄傲。中国作为一个普通民族国家对西方世界应该有这样的自信:既然中国的命运在于首先改变自己,那么中国就没有必要过度关注一些国家对中国的遏制,因为它们对中国的实际影响相当有限;它们也可以以接触的方式影响中国,中国应该借鉴吸收它们的经验。但最终中国应该有能力和权利寻求并决定适合自己国情的发展模式。这是中国作为一个普通民族国家需要不断锤炼的心理品格。
最后,一个“普通民族国家”的心态也能够让我们更好地处理中美关系。我们当然是希望也支持中国和美国建立一个更加良好的关系。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即便中美能够构筑起一个战略伙伴关系,那种中美能够共治整个世界的想法也是幼稚的、带着浓重帝国主义色彩,因而也是危险的。世界其他各国不会接受美国的帝国主义、中国的帝国主义,或者是中美携手的帝国主义。只有一个没有帝国主义色彩的中美伙伴关系才能是世界也包括中国和美国人民的福音。
章百家在研究20世纪中国外交历史所得出的基本结论是,“改变自己是中国力量的主要来源,改变自己也是中国影响世界的主要方式”。(44)实际上,人类历史上的任何一个强国对世界产生重要影响无不是以改变自己、发展强大的国家实力与政治精神文明作为前提的。这一思想对于中国来讲还有特别的意义:作为一个亚洲中心大国,中国改变自己比其他国家能够更大地影响世界。抛弃中心大国的历史迷思,接受普通民族国家的良好心态,无疑对中国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都有积极的意义。
[收稿日期:2008-04-14]
[修回日期:2008-10-21]
注释:
①将社会心理学应用到国际政治中的两部经典著作是:Robert Jervis,The Logic of Image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0; Robert Jervis,Perception and Mispercep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6。唐世平在这一领域做出了一些新的探讨,参见Shiping Tang,"Reputation,Cult of Reputation,and International Conflicts," Security Studies,Vol.14,No.1,2005,pp.34-62; Shiping Tang,"Fear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Two Positions,"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Vol.10,No.3,September 2008,pp.451-471; Shiping Tang,"The Evolutionary (Social) Psychology of Fear and Trust:Or Why Is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Difficult but Conflict Easy?" Paper presented at the 49th Annual Convention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Association in San Francisco,March 26-29,2008。
②更确切地说,这里讨论的自我中心主义是在群体/种族层面上的自我中心主义,即群体/种族中心主义(ethnocentrism)。“自大主义”,即“保护自己的自尊心”,一般被看成是自我中心主义的一个主要表现。在这里,我们将自大主义和自我中心主义区分对待,但同时强调自我中心主义包含自大主义。“自大主义”和“自恋症(narcissism)”经常是紧密相连的。
③关于社会进化范式的初步阐释以及在国际政治中的应用,参见唐世平:《国际政治理论的时代性》,载《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3期,第140~150页;Shiping Tang,"From Offensive to Defensive Realism:A Social Evolutionary Interpretation of China's Security Strategy," in Robert Ross and Zhu Feng,eds.,China's Ascent:Power,Interest,and Future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08,pp.141-162; Shiping Tang,"Social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Polities:From Mearsheimer to Jervis,"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forthcoming。
④[美]费正清著,张沛译:《中国:传统与变迁》,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第204~205页。
⑤卢武玄总统提出韩国要做“东北亚平衡器”。
⑥[新加坡]李光耀:《李光耀回忆录(1965~2000)》,台北:世界书局,2000年版,第694~695页。
⑦关于自我中心主义对中国的地区研究的影响,参见唐世平、张洁、曹筱阳:《中国的地区研究:成就、差距和期待》,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5年第11期,第7~15页。
⑧章百家:《改变自己 影响世界——20世纪中国外交基本线索刍议》,载《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第13页。
⑨这段话据称是源自汤因比和池田大作的对话。但是,在这本对话录的原文中,我们没有找到任何直接的证据表明汤因比确实说过这段话。Arnold Toynbee and Daisaku Ikeada,Choose Life:A Dialogue,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6,pp.246-254。
⑩李伯淳主编:《中华文化与21世纪 当代学者论人类未来百个方面的趋势》,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2003年版,第67页。
(11)张文木:《世界治理需要中医》,载《国际先驱导报》,2007年5月14日第15版。
(12)赵汀阳:《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秦亚青:《中国学者看世界[国际秩序卷]》,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7年版,序,第12~15页;Zhao Tingyang,"Rethinking Empire from a Chinese Concept,'All-under-Heaven' (Tian-xia,天下),"Social Identities,Vol.12,No.1,January 2006,pp.29-41。
(13)Zhao Tingyang,"Rethinking Empire from a Chinese Concept," pp.29-41; Wang Yiwei,"Why Is Pax-Americana Impossible? Comparing Chinese Ancient World Order with Today's American World Order," in Muzaffer Senel,ed.,Civilizations and World Orders,Boulder:Rowman & Littlefield,2007,chapter 16.
(14)我们要特别强调我们并不是要否定中国的古典哲学和治国之道有可以被借鉴的地方。我们只是指出在许多挖掘中国的古典哲学和治国之道的努力的背后是我们想建立一个以中华(中国)哲学为基础的王道“霸权体系”(或者“天下”)的梦想。
(15)庞中英:《政治意愿、国家能力和知识角色》,载《中国学者看世界[全球治理卷]》,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7年版,第348~349页。
(16)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来说,任何一个人的自我形象都必须一定程度地建立在他人对自己的认可之上。
(17)楚树龙:《全面建设小康时期的中国外交战略》,载《中国学者看世界[中国外交卷]》,北京:新世界出版社,第112页。
(18)Gerald Segal,"Does China Matter?" Foreign Affairs,Vol.78,No.5,September/October 1999,pp.24-36.
(19)古平:《贬低中国用意何在?》,载《人民日报》,1999年9月6日。
(20)参见唐世平:《再论中国的大战略》,载《战略与管理》,2001年第4期,第29~37页。
(21)Joshua Cooper Ramo,"The Beijing Consensus," http://fpc.org.uk/fsblob/244.pdf;赵晓:《“北京共识”的普世意义》,载《文汇报》,2004年6月14日。
(22)费正清:《中国:传统与变迁》,第627页。
(23)参见http://secretary.state.gov/www/statements/1998/980219a.html。某种意义上来说,美国的自我中心主义和中国的自我中心主义是极其相似的,几乎互成镜像。唯一的区别可能是美国的自我中心主义比中国的自我中心主义多了一些现实力量的资本。
(24)唐世平:《塑造中国的理想安全环境》,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77页。
(25)作者感谢翟昆指出这一心态的可能的辩证法起源。陈刚提醒我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中一直以美国专家为最多(最重要?)也许也反映了我们的美国中心主义。
(26)对系统范式的阐述,参见Robert Jervis,System Effects:Complexity in Social and Political Life,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7。中译本参见[美]罗伯特·杰维斯著,李少军等译:《系统效应:社会和政治生活中的复杂性》,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27)庞中英:《全球化、社会变化与中国外交》,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年第2期,第10页。显然,这是一种绝对的唯心主义思想。这种思想也没有意识到群体/种族中心主义(ethnocentrism)意味着中国不可能完全融入“西方”或其他。
(28)我们要强调,我们同样不认为中国应该只有自己的道义标准和认同,而不承认有任何普遍意义的道义标准和认同。这种思想是一种极端的自我中心主义的体现。
(29)张文木:《全球化进程中的中国国家利益》,载王逸舟主编:《中国学者看世界[国家利益卷]》,北京:新世界出版社,第210~211页。
(30)有趣的是,《中国可以说不》的作者同时承认我们对外国人的赞许和承认的需要是一个“心理病态”。宋强等:《中国可以说不》,北京: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1996年版,第202~205、285页。彼得·格里斯将这种中国精英对美国人的赞许和承认的极度需要和享受称为“基辛格综合症”。参见Peter H.Gries,"Identity and Conflict in Sino-American Relations," in Alastair I.Johnston and Robert S.Ross,eds.,New Directions in the Study of China's Foreign Policy,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6,pp.316-317。
(31)唐世平:《塑造中国的理想安全环境》,第278页。
(32)车耳:《外汇盈余的囚徒困境》,载《世界知识》,2007年第20期。在这里,我们当然不是反对金融体制必要的改革和开放。
(33)最直接的阐述参见Thomas P.M.Barnett,"The Inevitable Alliance," China Security,Vol.4,No.2,Spring 2008,pp.6-7; Fred Bergsten,"A Partnership of Equals:How Washington Should Respond to China's Economic Challenge," Foreign Affairs,Vol.84,No.4,July/August 2008,pp.57-69。但是我们要强调,我们是希望也支持中国和美国建立一个更加良好的关系的。
(34)赵汀阳:《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2005年版;Wang Yiwei,"Why Is Pax-Americana Impossible? Comparing Chinese Ancient World Order with Today's American World Order," in Muzaffer Senel,ed.,Civilizations and World Orders,chapter 16。
(35)William A.Callahan,"Remembering the Future:Utopia,Empire and Harmony in 21st Century International Theory,"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Vol.10,No.4,2004,pp.569-601.
(36)唐世平、张蕴岭:《中国的地区战略》,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年第6期,第12页。
(37)Joshua Kurlantzick,Charm Offensive:How China's Soft Power Is Transforming the World,No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2007; Joseph S.Nye,Jr.,"The Rise of China's Soft Power," Asian Wall Street Journal,December 29,2005.
(38)刘乃强:《中国本位的话语权争夺》,人民网,http://media.people.com.cn/GB/40606/6137138.html,2007年8月20日;王义桅:《借中喻美?审视中国“软实力”宜超越西方视角》,载《国际先驱导报》,2007年9月5日。我们当然同意“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相比“竞争者”是一个大的进步。
(39)庞中英:《“北京共识”:中国成为全球典范?》,http://www.china-review.com/gat.asp?id=11842,2004年8月16日;远山:《关于“北京共识”研究的若干问题》,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4年第5期,第17~21页;刘延棠:《“北京共识”的潜台词》,载《瞭望》,2007年第42期,第102~104页。
(40)唐世平、张蕴岭:《中国的地区战略》,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年第6期,第12页;楚树龙:《中国正日益“内向化” 美国对中国的重要性下降》,载《环球时报》,2005年7月25日。
(41)丁刚:《我国走向现代化必须应对的挑战:脱美国化》,载《环球时报》,2004年9月17日;王义桅:《别再用美国视角看世界》,载《环球时报》,2006年9月18日。
(42)在这里,我们套用刘备的名言:“不以善小而不为,不以恶小而为之。”但是,照顾到美国的敏感性,我们在解释中国的政策时也要兼顾到解释我们一些行为的“非故意的结果(unintended consequences)”。比如,中国参与的“10+1”、“10+3”其核心目标都不是为了排挤美国,而是为了向中国的近邻国家传达中国的善意。但是,客观上来说,这些行动的“非故意的结果”是美国的实际影响力确实有所下降。尽管美国不见得相信我们的解释,但否认这样的结果更容易让美国怀疑中国的意图。
(43)胡锦涛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十一部分,人民网,http://cpc.people.com.cn/GB/104019/104099/6429414.html,2007年10月25日。
(44)章百家:《改变自己 影响世界——20世纪中国外交基本线索刍议》,载《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第17~18页。
标签:中美关系论文; 自我中心论文; 精英主义论文; 世界历史论文; 世界主义论文; 美国史论文; 中国学者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中国军情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