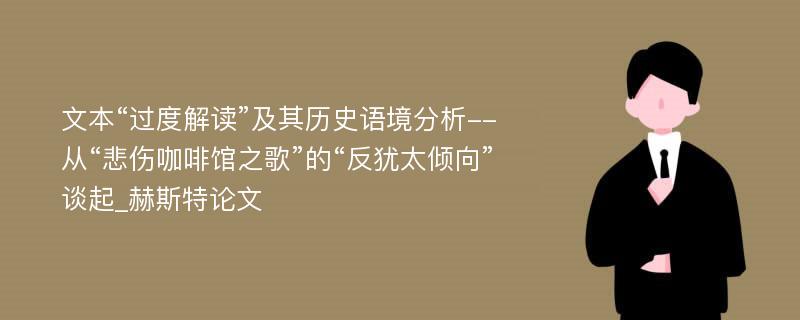
文本“过度阐释”及其历史语境分析——从《伤心咖啡馆之歌》的“反犹倾向”谈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语境论文,之歌论文,咖啡馆论文,倾向论文,文本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20世纪美国文学史上,卡森·麦卡勒斯(Carson McCullers 1917~1967)是一位成就 突出的现代南方女作家。1940年,年仅22岁的麦卡勒斯因为第一部长篇小说《心灵是孤 独的猎手》(The Heart Is a Lonely Hunter)的出版而一举成名,这部作品几乎包括了 她日后创作中的所有主题,其思想深度使人很难相信她此时的年龄。随后,三部杰作《 金眼睛里的映像》(Reflections in a Golden Eye 1941)、《伤心咖啡馆之歌》(The
Ballad of the Sad Café 1943)和《婚礼的成员》(The Member of the Wedding 1946 )相继问世。1961年,她终于推出了酝酿已久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没有指针的钟》
(Clock Without Hands),数月间在畅销书排行榜上成绩斐然。McCullers在1967年辞世 时年仅50岁,身后留下了五部长篇小说、两个剧本、20个短篇小说、20余篇散文和文学 评论、一部儿童诗集和若干零散的诗作以及一部未完成的自传。
其中,《伤心咖啡馆之歌》一直被誉为麦卡勒斯的一部扛鼎力作,情节引人入胜,到 目前为止是我国译介的惟一一部麦卡勒斯的中长篇小说,20年间李文俊先生的译本曾多 次转载于国内各个世界文学选集,深得广大读者的青睐。作品围绕沉闷的南方小镇上两 男一女之间的三角关系展开叙事。个性和外表颇为男性化的爱密利亚小姐是小镇上最富 有的女人,为人冷漠苛刻。几年前,镇上的恶棍青年马文·马西曾经迷恋上了爱密利亚 并决心为了她而痛改前非;不料,他在婚后十天内受尽了被冷落的屈辱并最终被赶出家 门,不久便因谋杀和抢劫罪坐牢。一天傍晚,丑陋的罗锅李蒙来到爱密利亚的杂货铺, 自称表兄与之攀亲,却意外地被爱密利亚收留,从此小镇的生活发生了变化:爱密利亚 为了取悦李蒙表兄,将杂货铺改成了咖啡馆,小镇居民们于是有了聚会娱乐的场所。直 到四年以后,李蒙被出狱归来的马西吸引,两个人联手处处与爱密利亚作对,爱密利亚 只得同马西约定日期在咖啡馆决斗。就在爱密利亚即将取胜的一刻,李蒙猛扑上来将她 打倒在地。随后,马西和李蒙两个人捣毁了咖啡馆,携财物离开小镇。幻灭的爱密利亚 过起了隐居生活,小镇重新恢复了原先的沉闷状态。
尽管《伤心咖啡馆之歌》的故事情节已经广为我国文学爱好者熟知,然而作品问世后 的一段插曲却多半鲜为人知:作者曾因“反犹倾向”的指控而一度遭受精神折磨。小说 于1943年8月发表后不久,麦卡勒斯就收到一封署名“一个美国人”的手写匿名信,信 纸上方印有飘扬的美国国旗衬托下的一组轰炸机,红、白、蓝三色图案下标有“让它们 永远飞扬”字样。信上说:“尊敬的年轻作家,我刚刚开始读你写的小说,但是你却在 第二页末尾拿犹太人开玩笑。等我看到是哪家出版商以后就不奇怪这样一篇小说得以发 表。你何不停止在种族问题上作文章,四下里看看那些心术不正的大政客和金融公司大 老板。或许还有你的朋友刘易斯先生和希特勒。(我)当然要严厉抨击《哈泼斯市场》
(Harper's Bazaar),直到你们这类人学会象犹太人一样有人性。”(Carr,1975:236—2 37)
这封信令麦卡勒斯深感意外,她在朋友圈子里到处写信求助,请求大家向她坦白各自 的看法或者为她广泛征集犹太裔读者的意见。同时,她还写了一封“公开信”为自己辩 护,信中指出:“当一个人对反讽意义反应不灵敏或产生误解时,作者很难解释清楚自 己的意图。”按照麦卡勒斯的解释,《伤心咖啡馆之歌》“是一个以谐谑方式讲述的轻 松故事,但是在它看似狭窄的语境背后隐藏着意味深长的痛苦内涵。她对待犹太人物时 与所有其他人物一样用的都是传统的轻描淡写手法。她无意拿犹太人开玩笑。这是一个 警世悲剧,谴责对象不是犹太人而是纵容种种堕落行径发生的社会”(Carr,1975:237— 238)。她相信读过她作品的人都了解她对国家体制中存在的法西斯因素深恶痛疾,对歧 视少数族裔的行为特别是南方地区肆意践踏民主的做法恨之入骨,但是她还是因为被人 误解而感到不安。她要求《哈泼斯市场》在十二月号刊登这封信,但是却由于赫斯特集 团总部的阻挠未能如愿:事实上,考虑到赫斯特报业在少数族裔问题上的立场,这似乎 不足为奇。无奈,麦卡勒斯只得私下里将这封信复制多份寄给友人,试图向公众阐明作 者意图。
关于这个事件,首先需要说明的一点是,麦卡勒斯的这部作品最初是由《哈泼斯市场 》杂志发表的,直到1951年才被霍顿·米夫林出版社(Houghton Mifflin)编入《伤心咖 啡馆之歌:卡森·麦卡勒斯中短篇小说集》。创刊于1867年11月2日的《哈泼斯市场》 杂志并不是一本专业文学期刊,一个多世纪以来一直是一份很有影响力的时尚杂志,它 主要面向中产阶级现代知识女性,集时尚美学和实用性于一体,提供时装、美容、家居 、健身、理财、旅行、娱乐、艺术等新潮信息,并以引领潮流的大胆风格为各类前卫艺 术家提供了展示才华的场所。其间,美国20世纪报业巨头威廉·伦道夫·赫斯特
(William Randolph Hearst 1863~1951)于20年代将该杂志收归赫斯特报业集团所有。 上文引述的匿名信作者对该出版社持有明显的偏见,原因多半与赫斯特本人的政治立场 及其办刊方针有关。赫斯特在上个世纪30年代表现出的亲纳粹倾向及其在40年代的反共 立场曾使美国左翼人士深感不安,公众甚至称之为美国“首席军国主义者”、“法西斯 主义的头号帮凶”。此外,赫斯特毫不掩饰对少数族裔的憎恨和排斥,他利用报刊杂志 不失时机地加剧种族间的紧张对立。《伤心咖啡馆之歌》发表其时,《哈泼斯市场》杂 志所遵循的正是由赫斯特本人于1933年为赫斯特报业制定的八条办刊方针,其中“为伟 大的中产阶级最优秀的成员办报刊”、“删除会冒犯有教养的人们的内容”等原则明确 无误地限定了刊物的服务对象,充分体现了当时盛行于美国白人中产阶级当中的精英意 识。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哗众取宠的失实新闻报道、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倾向、反自 由意志主义立场等种种原因,赫斯特报业在30年代的确招致了维护民主的左翼人士以及 少数族裔的不满甚至联合抵制。(注:详见George Seldes 1938年出版的Lords of the Press一书中第十七章“Farewell:Lord of San Simeon”。)根据评论家莱斯利·菲德 勒(Leslie Fiedler)的说法,以麦卡勒斯、杜鲁门·卡波特(Truman Capote)为代表的 《哈泼斯市场》圈内中人崇尚的是“一种新型理念,其主要标志是高级时装、古典芭蕾 、巴洛克歌剧、天主教仪式和法衣等——特别是既优雅精致又痛苦怪诞的文学——构成 的欣赏品味”,这个特点为该杂志狭窄地划定了一个特定读者群。Fiedler对此类作品 的时尚外表下隐藏着的“无政治或反政治”特性表示不满,并且在麦卡勒斯加盟《哈泼 斯市场》这件事上颇有微词。他认为这种做法尽管有助于作品得到认可却使评论界不能 不怀疑她本人具有“波希米亚式精英”倾向(Fiedler,1955:201—202)。可以说,
Fiedler的这一评论代表了一部分读者的看法。
其次,匿名信中提到的那个场景发生在罗锅李蒙前来投奔爱密利亚小姐的最初一刻, 他试图与爱密利亚攀一门远亲,见对方反应漠然便哭了起来。当时在场的一对双胞胎兄 弟里的一个评论道:“他要不是真正的莫里斯·范因斯坦,那才怪哩。”小说叙述者接 下来解释说“这是一个含有特殊意义的说法。……莫里斯·范因斯坦是多年前住在镇上 的一个人。其实他只不过是个动作迅速、蹦蹦跳跳的小犹太人,他每天都吃发得很松的 面包和罐头鲑鱼,你只要一说是他杀了基督,他就要哭。后来他碰到了一件倒霉的事, 搬到社会城去了。可是自此以后,只要有人缺少男子气概,哭哭啼啼,人们就说他是莫 里斯·范因斯坦”(p.173)。这个借喻立刻引起了旁人的共鸣,其中一个人随声附和: “唔。他很苦恼……这总有个什么原因。”可见,“莫里斯·范因斯坦”这个字眼已经 超越了某个具体人物的原型,成为一个文化符号,在特定的语境(封闭的南方小镇)中获 得了抽象的内涵,激发了“集体无意识”,其中至少包含了以下两层含义。其一,李蒙 “表兄”是身份不明的异乡客,范因斯坦的情况并不比他强:他一直被小镇居民视为“ 外来者”。其二,在小镇居民的眼里,范因斯坦爱哭的特点不仅与他的犹太人身份紧密 地联系在一起,而且还成为女性化乃至残疾的象征。这其中隐藏着一个危险的推论:犹 太人“缺乏男子气概”。如果将其置于历史背景中考虑,这种观念正是纳粹推行的“反 犹主义”的一个重要依据:由于民族宗教信仰的缘故,犹太男性出生后要行割礼,这个 仪式使他们的身体在白人眼里产生“异化”效果。其结果是,犹太人与肉体等同起来, 在“毒黄蜂”(WASP,意指White Anglo-Saxon Protestant)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中被 贬抑为“残缺不全的男性躯体”,与女性身体一样因为差异而被归为劣等。所以说,小 说中的这个细节折射出主流意识形态对犹太人乃至其他“外来”族裔的歧视。
然而,问题的关键在于上述一切是否足以说明匿名信中指控的麦卡勒斯“反犹”罪名 成立呢?事情似乎没有这么简单。可以说,任何作品都会在不同程度上对当时社会的意 识形态有所反映,但是作家与各种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却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其中 要涉及到文本意图、作者意图的分析。意大利作家、符号学家安伯托·埃柯(Umberto
Eco)在《阐释与过度阐释》中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仍然在世的经验作者对其书面文 本的某些阐释作出的反应是“不,我不是这个意思”,那么我们还能接受这些阐释吗? 在阐释他自己创作的作品时,经验作者是否享有特权呢?他的回答是:经验作者的特权 仅限于他有权排除掉某些阐释。更重要的是,在不可捉摸的作者意图和可论证的读者意 向之间存在着透明的文本意图,它会将一个站不住脚的阐释否定掉(Eco,1992:78)。也 就是说,文本中作者“潜意识”甚至“集体/个体无意识”的自然流露、阅读中读者主 体意识的自由介入分别对作者意图和读者意向构成了干扰因素,而文本的稳定状态决定 了文本意图的可靠性,使之成为给作品定性的惟一标准。
如Eco所讲,人类在寻求趋同性和相似性的基础上进行思维,作者会在自己的文化中发 现一些普遍认可的关联生成机制。但相似关联的两个不同境界会导致不同的结果:适当 的、有意义的关联是合理阐释的基础,而具有偶然因素的、主观臆断的相似性联想只能 造成“偏执的阐释”(Eco,1992:49)。而且,读者对文本的阐释是建立在自身的生活经 历和阅读经验基础上的,难免将个体意识形态的局限性强加给文本。如果说匿名信作者 对麦卡勒斯文本的解读不单单归因于“偶然因素”和“主观臆断”,那么这种阐释表现 出的“偏执”要追溯到三四十年代美国国内反犹主义情绪和犹太复国主义(Zionism)浪 潮的特定社会语境。30年代,已在美国政治和经济生活中占据了显眼位置的犹太人群体 从三K党对犹太人的迫害活动、民间反犹群体的增多连同抗议犹太人敛财掌权的呼声高 涨、美国政府重新修订的对欧洲犹太人不利的移民法、福特等公司以及哈佛等大学在人 员录用和学生录取上针对犹太人的歧视性规定等现象中敏感地觉察到了危险的信号。同 时,欧洲特别是纳粹德国对犹太人实施的残酷迫害和血腥屠杀更是加深了美国犹太人的 恐惧,从而导致了美国三四十年代的犹太复国主义浪潮。颇具讽刺意味的是,1941年, 珍珠港事件迫使美国最终放弃了“隔离主义”的外交政策而加入二战,就在美军在欧洲 战场上奋力抗击企图灭绝犹太人种的德国纳粹势力的同时,美国白人的反犹情绪却逐渐 升至历史最高点。这种紧张对立的局势于1944年达到高潮,直到二战结束后才有所缓解 。(注:Henry L.Feingold在The Politics of Rescue:the Roosevelt Administration and the Holocaust,1938~1945(New York:Holocaust Library,1982)中提供了相关背 景;另外还可参考It Can Happen Here?—Antisemitism,American Jewry and the
Reaction to the European Crisis,1933—1940”(Antisemitism Worldwide 2000/1,
http://www.tau.ac.il/Anti-Semitism/asw2000—1/feingold.htm)。)
这样看来,麦卡勒斯遭到的反犹指控可谓事出有因。与此不无关联,匿名信中提到的 “刘易斯先生”指的是1930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美国白人主流作家辛克莱·刘易斯(Sinclair Lewis)。反犹主义在20世纪20年代开始在美国白人主流社会的精英阶层中间抬头。这个时代推崇“优生学”和“人种净化”,因而反犹主义、反天主教思想在知识界猖獗一时。大部分移民被划为劣等人群,“WASP”精英阶层开始着手清理这些混进来的外来者,其中包括新教以外的暴发户。盲从的态度使大多数美国人极力维持因循守旧地固守一套僵化的白人中产阶级文化、政治、道德标准,不求变革,不思进取,仅仅满足于日常生活中平庸狭隘的乐趣。Lewis在他的代表作《巴比特》(Babbit,1922)中敏锐地捕捉到了这种以文化偏狭主义为标志的时代精神。此外,在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的纳粹统治时期,Lewis写了一本警世小说《不会在这里发生》(It Can't Happen Here 1935),虚构了一名希特勒式的美国人和他的追随者一起在经济萧条时期发动了一次法西斯政变的故事。小说刚一面世便在美国犹太人群体中引起强烈反响,其标题就被改写成耸人听闻的“会在这里发生!”并在犹太报刊中反复引用。犹太激进分子驳斥Lewis以达到警示犹太同胞的目的:如亨利·L.费恩戈德(Henry L.Feingold)在《它会在这里发生吗?——反犹主义、美国犹太人及其对欧洲危机的反应》一文中所说,“他们觉得,如果事情能在德国发生,那它也有可能在其他任何地方发生。于是,他们把国内高涨的反犹情绪看作事情正在那里发生的证据”。此间,媒体对犹太问题表现得极为谨慎:《纽约时报》董事会劝诫有犹太姓氏的撰稿人在署名时一律改用首字母缩写;三四十年代的报刊纷纷对有关犹太人的故事和报道作轻描淡写的处理,以免招惹“亲犹”之嫌。匿名信中将Lewis与希特勒混为一谈,这同麦卡勒斯的“反犹”罪名如出一辙,显然是文本“过度阐释”的产物。麦卡勒斯曾对阿尔弗雷德·卡津(Alfred Kazin)说,匿名信作者对《伤心咖啡馆之歌》中犹太人形象的误读就好像是契诃夫(Chekhov)作品中她最喜爱的一篇小说《罗思柴尔德的小提琴》(Rothschild's Violin)被当作反犹主义小说,或者如同《一个礼貌的提案》(A Modest Proposal)的读者指控乔纳森·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当真用婴儿烹饪一样荒谬。
回到麦卡勒斯的文本上,我们一方面不能否认所涉及到的文本片段反映了白人群体在 “莫里斯·范因斯坦”与李蒙表兄之间建立的具有反犹主义意味的相似关联,另一方面 也必须强调这并不能简单等同于作者立场。按照Eco的说法,文本的意图不浅浮于文本 的文字表面,只有有心要“看到”它的人才能看到。要想证明某个关于文本意图的推断 正确,惟一的途径就是把文本看作一个逻辑严密的整体来对待并在此基础上对其加以考 察:对一个文本的某一组成部分的阐释若在同一文本的另一部分中得到证实的话就可以 被接受,否则就必须放弃。在这个意义上,文本内在的逻辑是遏制读者任意联想冲动的 惟一机制。这样看来,关于作者对待犹太人的态度以及对当时白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中 普遍存在的种族主义的立场问题,答案仅有可能存在于文本意图的分析中;也就是说, 通过文本分析建构推导出“隐含作者”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惟一途径。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上文提到的有关“莫里斯·范因斯坦”的那个例证以外,文本中 还有其他种种迹象表明了南方小镇群体的种族主义政治倾向。无恶不作的恶棍青年马文 ·马西被塑造为邪恶的化身,他代表了种族主义的南方群体。故事叙述者在对往事的追 溯中轻描淡写地提到了从侧面证实马文种族主义立场的“三K党长袍”(p.197),语气中 似乎暗示了小镇人们对“三K党”的活动已然见惯不怪,习以为常了。同时,叙述者在 提到马文童年时被生性放荡的父母抛弃的时候说“不过这个镇子是不会眼看白种孤儿在 街头活活饿死的”(p.193),这种强调种族肤色的说法不自觉地流露出了小镇群体中根 深蒂固的种族界线观念。另外,文本中的群体所指显然是小镇上的白人男子,不仅爱密 利亚以外的其他女性很少被正面提及,而且黑人则同小孩一起被划在圈外:当一群人集 中在爱密利亚的后院里观看刑满释放回来的马文与爱密利亚会面时,“呆在院子外的小 孩和黑人大气也不出一声”(p.215)。甚至,尽管爱密利亚的咖啡馆“给小镇带来的新 的自豪感几乎对每一个人都有影响,连儿童也包括在内”,而且“对于单身汉、畸零人 与肺结核患者,咖啡馆更是个好去处”(p.219),但是在光顾咖啡馆的人群中似乎很少 出现妇女,也没有包括黑人。这一切使小镇成为以种族和性别划分等级的南方社会的一 个缩影。
那么,作者本人是如何看待这种“集体无意识”呢?事实上,许多评论家都曾指出,《 伤心咖啡馆之歌》在叙事声音上的复杂性给文本意图分析带来了一定的难度。所以,要 想搞清文本意图,首先有必要在叙述者、人物、小镇群体等构成的声音混响中辨别出隐 含作者的声音。许多评论家都在文本中辨别出了两种叙事风格。玛丽·安·戴泽(Mary Ann Dazey)从中观察到了“发出两种不同声音的同一个叙述者”,而且它们之间的问答 式交流使“从一个声音到另一个声音的转换很流畅,几乎不易察觉”。两个声音中的一 个是“客观”讲述故事的民谣歌手,另一个是引导读者注意力的“哀叹者”、对人物品 头评足的旁白;从句式上看,前者相对简单明快,多采用过去时态,后者复杂凝重,时 而转换成一般现在时。在作者的“指挥”下,“歌手的声音讲故事,第二个声音则为之 提供了忧伤的背景音乐”(Dazey,1986:117—124)。玛格丽特·B.麦克道尔(Margaret B.McDowell)认为“叙述者随意变换叙述声音,从与一群无所事事的工友业余闲谈的一 名纺织工人到以诗意、迂腐、正式化风格讲话的一名神秘的民谣歌手。民谣歌手的全知 视角及其原始直觉看似与纺织工人的口语体风格不甚谐调,尽管两者最终都出自民间” (McDowell,1980:76)。弗吉尼亚·斯潘塞·卡尔(Virginia Spencer Carr)也提出了与 之大体相似的看法:“叙述者与他(或她)所描述的小场景和大局面之间保持了相对客观 的距离……他不是任何事件中的某一个特定角色,但是他对即将发生事件的评论和暗示 起到了希腊戏剧中合唱的作用……他的全知叙述为后来的事件定下了基调和节奏,从正 式、规范化、诗意且时而迂腐的风格变成丰富多彩的口语化民间故事模式,后者是经常 光顾爱密利亚小姐的那些思想单纯的工人们所特有的风格。”(Carr,1990:57)总之,不 难判定,叙述者的身份是小镇上的居民,他对小镇生活的酸甜苦辣有着切身体会,对小 镇的风土民情和居民们的思想观念了如指掌。与此同时,叙述者又是一名旁观者,与群 体之间保持了一定的距离,这个距离使得他能够不动声色地观察和记录下小镇上发生的 一切并对其作出自己相对独立的评价和判断。例如,当“全镇在集体编造一个可怕、阴 森的[谋杀]故事”并沉浸在过节欢庆般的幸灾乐祸情绪之中时,叙述者从群体中区分出 了不肯轻易受谣言迷惑的“几个头脑清醒的人”和不忍心看到爱密利亚受法律制裁的“ 三个善良的人”(pp.178—179);当镇上长舌妇们组成的“狐群狗党”凭空猜测爱密利 亚和李蒙表兄的“苟合关系”并对此说三道四时,叙述者语气中流露出对这种侵犯他人 隐私的行为的不屑:“就让她们说去吧”,并且分别提到了“那些善良的人”和“一切 有头脑的人”在这件事上的看法:前者表现出宽容,“他们认为,如果这两个人在彼此 的肉体接触中能得到满足,那么这仅仅是涉及他们自己与上帝的事”;后者则表现出理 智,“他们直截了当地认为,这是无稽之谈”(p.190)。上述段落明显地体现了叙述者 不同于小镇群体的个人视角和价值观,是叙述者与群体之间叙事距离的具体体现。
可以说,叙述者混迹于群体之中,其视角却时而与群体相吻合,时而凌驾于群体之上 ,他对小镇群体行为和思维方式的态度也是或认同或讥讽。既然叙述者是群体成员却比 群体有其高明之处,那么他是否等同于文本的隐含作者呢?他又能在多大程度上代表经 验作者的立场观点呢?评论界在这个问题上多有争论。麦克道尔发现叙述者与镇民一样 虔诚地怀有一些迷信观念,如三和七两个数字的超自然神秘力量、马文归来与天象变化 的奇妙关联、马文身上的魔咒般邪恶力量;镇上流传的一些谣言显得夸张而恶毒,尽管 叙述者在有关爱密利亚谋杀李蒙的传言中表现出一定的判断力和同情心,他本人却似乎 对另一些涉及到爱密利亚的生活隐私的传言不假思索地接受,这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了 他的思想局限性。这种局限性使他成为一名“不可靠叙述者”,从而无法胜任“隐含作 者”的代言人角色。评论家苏珊娜·莫罗·保尔森(Suzanne Morrow Paulson)从女性主 义角度对叙述者的立场作出的分析颇有洞见:她认为“尽管自身充满困惑且令人感到困 惑的叙述者在为爱密利亚的谋杀指控辩解时流露出女性化的性格层面,但是他还是多半 采纳了属于大多数的劳动阶层男性主流视角。他像他们中的一员一样重复着某些男性观 念……”他对待妇女劳动的态度反映了群体的男权偏见。
他事实上不可理喻地摇摆在男权和女性视角之间、在不可靠的群体视角和可靠的作者 洞察力之间(Paulson,1996:191)。因此,在拉开叙事距离的反讽手法和作者观点的正面 表述之间作出明确区分就成为建构“隐含作者”、推断“文本意图”的关键所在。比如 ,在李蒙投奔爱密利亚之初的有关叙事中,叙述者几次提到李蒙时用了“不知从哪里钻 出来的一个肮脏的小罗锅”(p.176)、“这个陌生的客人”(p.177)这样的指代称谓,其 中明显包含着轻蔑的成分,既可以看作叙述者视角与小镇群体视角相互重合的具体例证 ,也可以理解为叙述者以反讽手法对小镇群体视角的讽刺性再现;无论哪一种情况,这 一叙事距离都有效地体现了群体观念同“隐含作者”对遭受排斥的“外来者”的同情心 之间的相互抵触。
正如麦卡勒斯本人所讲,上述那段被指控为“反犹倾向”的文本中隐含着反讽意味: 叙述者和隐含作者与小镇群体之间的叙事距离表明女性化犹太受难者的传统形象背后的 种族主义意识形态在文本中实际是作为批判的靶心出现的。Paulson在分析上述段落时 提出了这样的观点:这里的犹太人形象被当作正面人物来处理,预示了爱密利亚的不幸 ;作者“显然是在谴责将女性化的男子和富有女性气质的女人当作弱者来压迫的男权社 会”(Paulson,1996:189)。作为例证,性格截然相反的马西兄弟两人分别成为小说的正 面和反面人物。与恃强凌弱的恶棍马文相反,亨利是“一个羞怯、胆小的人,举止温和 ,有点神经质”(p.170);“他恰好是他哥哥的反面,是镇上第一厚道第一温和的人”( p.193)。由于亨利性格温和、心地善良,他不忍心目睹罗锅李蒙将会被爱密利亚驱逐的 情景,还没等爱密利亚作出反应便悄然离开了:“他是个软心肠的人,小罗锅的处境很 使他同情”(p.173)。相比之下,马文归来后一见到李蒙便开始欺负他,不仅称他“断 脊梁的”(p.213),而且还经常对他施以暴力,逢迎讨好也无济于事。同时,文本从侧 面暗示了爱密利亚小姐对种族主义的不屑甚至反对立场:婚后,她在赶走马文之后“把 他的三K党长袍剪开来盖她的烟草苗”(p.197)了。另外,爱密利亚对前来投奔她的罗锅 李蒙所作的反应足以表明她的反主流立场:她不顾旁观者将罗锅比作犹太弱者“莫里斯 ·范因斯坦”的讥笑,自作主张将罗锅收留下来。并且,多亏了爱密利亚的保护,李蒙 才逃过了像“莫里斯·范因斯坦”一样受到小镇人们百般凌辱的不幸遭遇:“这些年来 ,没人敢动李蒙表哥一根汗毛,虽然不少人心中都有过这样的诱惑。”(p.214)因此, 从作品的反讽手法和人物的正面塑造两个方面,我们进而可以推知作者意图:麦卡勒斯 本人曾经明确表示“没有人比她更恨偏见和残忍”,她正是想通过文本警告世人最大的 危险莫过于“失去个人主见,屈从于将犯罪等同于英雄行为、将种族主义视为理所当然 的富于攻击性的男性群体”(Paulson,1996:194)。这样看来,文本的深层寓意在于这样 的警示:法西斯主义不仅存在于大肆屠杀犹太人的欧洲战场,而且就在美国国内特别是 南方的社区群体中滋生泛滥,因而很容易成为个体意识形态及其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
分析至此,我们完全可以说,匿名信的作者对《伤心咖啡馆之歌》的解读未免有断章 取义之嫌,他无意中提供了一个“过度阐释”的反面例证。若以Eco对“阐释圈”
(hermeneutic circle)的解释为鉴——“文本中存在不止一个参数来证实阐释有效,文 本是一个客体,在其自身产生的结果的基础上证明自身,阐释就在这一循环运动中得以 逐渐形成”,文本意图则必须从文本自身的整体逻辑关系之中找到答案。上述分析的意 义就在于这一封匿名信引发的思考有助于读者了解麦卡勒斯创作时的特定社会文化语境 ,并对麦卡勒斯相对于主流意识形态的反叛立场获得一个更为深刻的感性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