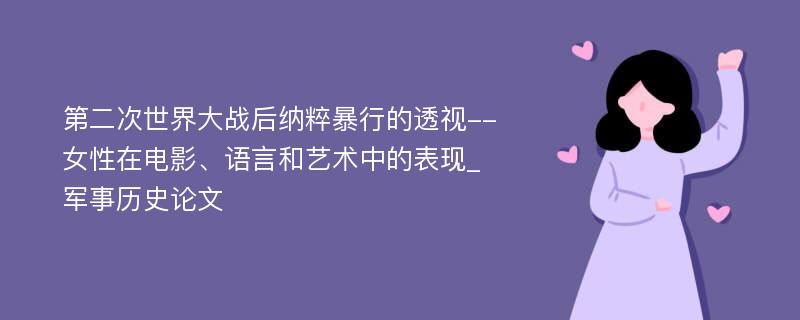
战后对于纳粹暴行的透视:女性在电影、语言以及艺术中的表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纳粹论文,暴行论文,战后论文,透视论文,语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绪论:纳粹德国凶残本性传承之下的女性透视
在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60周年之际,我希望从性别的角度来讨论那场战争以引起大家的关注。当我的陈述涉及到战后对于战争的反应以及与之相关的在欧洲发生的暴行,我希望同时可以对比你们对于在亚洲发生的战争暴行所做出的研究。我将通过六位北美洲和欧洲女性学者的研究事例,来阐释她们在电影、语言和艺术领域中独特的探索。
曾经有人争论说这种研究途径对于女性来说不够典型,因为从传统意义上说,女性并没有在战争的地缘政治本体中扮演过值得注目的形象。但是,相对地缘政治,历史将意味着更多。在目前这个后现代主义的历史编纂之中,试图来理解女性对于历史事件的观点是合乎时宜的。
这个观点需要承担些什么呢?我们知道在上个世纪,由于男性需要离开家庭去打仗,女性不得不成为家庭的主要劳力,不仅要料理家务还要进行工业生产。虽然对于战争她们是旁观者,但是她们却常常需要去承担照顾战争伤员的重担。更为残酷并且被经常提到的是,对于那些不是在战争中伤亡的女性来说,在敌军胜利的进程中,她们的命运和那些战争牺牲者的遭遇是一样的,成为在许多例子中所谓的“性战利品”。因而,正是对这些女性的透视,才使得我们去关注那些非战斗人员和受害者的遭遇。
我将在以下陈述中继续这方面的阐释,这会涉及纳粹德国对那些非战斗人员却依然是敌人的人们的暴行,这足以使我们看清战时的罪恶政权如何成为最大的危险,而这最大的受害者就是那些没有防卫能力的人们。战后,需要一张清单,不仅仅是以胜利或正义的名义,而是要提醒人们有义务去防止这种人为灾难的再次发生。
尽管在战争时期纳粹德国不是唯一一个以它的这种态度来对待妇女和儿童的,但是社会进化论的意识形态以及之后所谓的“种族清洗”(Rassenhygiene)论调,在19世纪晚期已经出现。纳粹党人实施计划去征服欧洲,但是他们的野心与以前所有欧洲战争不同。他们意图“从西部到东部踏平欧洲”以消灭不分性别、年龄以及地域的所有犹太人。
我今天提到的这些女性的作品传达了女性对于那些恐怖事实的看法,尽管她们的观点从未被那些大影片所忽略。虽然同情经常是女性观点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她们也必须认清那些现实的细节,有些甚至是历史的基础。在那些我今天提到的反映欧洲战争的女性作品中,这种二元性是可以看到的。比如说,Elida Schogt、Ruth Liberman和Vera Meisels所创作的那些以大屠杀为题材的电影或艺术作品反映了战争幸存者或他们后代的一些观点。德国出生的Anna Rosmus一直致力于对抗德国人中的纳粹分子和揭示他们对于犹太人的罪行。Danuta Weselowska,一位波兰语言学家,用文字反映受害者在集中营的经历。最后,我这个母语是德语的人将会以我的作品,讲述纳粹分子如何通过语言来达到他们迫害犹太人的意识形态的目的。然而,所有的这些女性对于这个主题所做的努力移情于她们每个人的愿望——对于保护受害者的回忆,告知并教育战后的一代,并且最终鼓励我们这个文明社会向全球化的人道主义迈进。
一、电影
(1)对家乡的纳粹历史的揭露:《坏女孩》
《坏女孩》(1990)是以年轻的安娜(Anna Rosmus)和她位于德国南部的家乡Passau所发生的一个真实的故事为摹本的。在影片中,桑娅开始写一篇关于她的家乡在第三帝国时期如何反抗纳粹分子的文章。她通过故事对那些和法西斯政府勾结的人的罪行进行了揭露。我们看到,随着她探索的深入,她逐渐触及到那些被深深地隐藏在公共档案馆里的Passau的历史,为此,她遭到来自上至政府官员下至普通市民的种种强烈地反对。通过天生的机敏,她得到了那些敏感的材料,并把那些发现公布于众,从而让一些所谓的“优秀人士”的罪行曝光。然而她的胜利是有代价的:受到威胁的,最为动乱的家庭生活。
此片在1991年获得了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提名,同时也获得了其他的几项重要奖项。更为重要的是,安娜坚持不懈的努力为其他学者对纳粹时期不公开的档案的搜寻开了先例。
对于安娜,这仅仅是她所要进行的搜寻的开始。她写了几本书,全部是来揭露当地官方的协作通敌以及与罪恶的纳粹分子的关系。虽然由于她坚持不懈的努力搜寻受到国内外人们的尊重,但却在家乡受到威胁和排挤,甚至被人叫做“Passau的女巫”,最后付出了离婚的代价。在90年代早期她离开了德国,现在和两个孩子定居在华盛顿。
2005年5月,Rosmus在巴伐利亚和奥地利组织了名为“60年:连接过去”的纪念旅游活动。她还说服了1945年曾解放这一地区以及奥斯维辛Mauthausen集中营的美国老兵。我是北美代表团的一员,代表团都是由目前定居在以色列和美国的犹太幸存者组成的。就像她组织的那些活动,她也使地方政府官员牵扯其中。我们受邀请去参加很多招待会、演讲和宴会,最后一个是在维也纳的市政厅。Rosmus作为一个杰出的例子告诉我们一个坚持不懈的研究,如何使他人同时也使战斗过的老兵以及任何富有同情心的人们努力将过去公布于众。对于这样一种独有的揭示历史的方式,我只能用上面短短的文字作为总结。
(2)《Zyklon雕像》:对毒气屠杀后果的追问
第二部影片《Zyklon雕像》(2003)是来自多伦多的Elide Schogt的一部纪录片作品。
她的观点是通过一个犹太族的祖父母被杀害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加拿大妇女表现出来的。影片中一个叙述者的声音是一个带着德国口音说英语的男人,他读着乌托邦式的纳粹种族清洗规则的册子并解释了纳粹之所以要消灭犹太人的原因。他同时也读了奥斯维辛集中营司令官Rudolf Hoess的日记。它向我们展示了一幅关于生和死的让人触目惊心的场景。随着那个男人的声音出现的是那个女性电影摄制者,她和她的母亲有一段关于她祖父母的对话。她个人的涉及、疑问以及陈述与那个男人凶残的声音相抗衡。这种两相结合的视角在这部较短的影片中传达了一个强有力的信息。
在以家庭为背景的影片中,我们可能会期待一部充满了怀旧与失落的典型影片。但是这部影片中的后现代主义并没有去演绎怀旧,相反,在这部独一无二的纪录片中,Schogt用了一种科学的方法去揭示化学气体Zyklon-B和它的危害,德国人就是用这种致命的气体去屠杀人类的。这位女性叙述者将纳粹的理论和客观的发现融进了她自己的故事、她所挚爱的祖父母的命运以及他们在战前的生活,以她的母亲将二者联系起来。尽管这是一部自传体的片子,但是她并不想去渲染痛苦,或是责难、审判正义,留给观众的是对于那些公然无视整个人类灾难的杀人者的深刻反思。
二、语言
(1)犯罪者的自述:《纳粹德国:德意志第三帝国语言的英文词典》
也许是由于长期以来受好莱坞战争题材的科幻和非科幻影片的影响,犯罪者的语言已经在第三帝国的荣誉中占据了意想不到的重要地位。这里有许多口号、标语以及概念为今天的文明所熟悉,就像战后德国在语言学上对于纳粹特有符号的确定一样。这种语言学上的意识和纳粹利用语言作为工具来推进并掩藏他们军事上种族灭绝的目的和行动的事实,引导我们去研究纳粹德国。我成为了《纳粹德国:德意志第三帝国语言的英文词典》的合著者。它证明了语言在历史,尤其是在种族灭绝大屠杀中的重要作用。文字仍然需要去破译、修正并确定,以便找出其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真正含义。字典里的解释经常是被伪装的,并且用那些难懂的词将阴险的目的隐藏其中。这些术语已经被翻译成现代的英语。例如,举两个无伤大雅的词:Volksgemeinschaft和Lebensraum。从表面意义来看,这两个词很容易被理解为“人民团体”和(纳粹分子提出的)“生存空间”(指国土以外可控制的领土和属地)。但是如果说它们特有的纳粹的含义,它们只是用在具有德国人种的人身上。它们包含这一个并没有声明的计划,那就是将来人口在德属欧洲领地上的迁入和迁出,以及其他的放逐和消灭。因而,德语“生存空间”也就有了其他许多意思,成了“死亡地带”。
在战争年代,纳粹官方决定文字的使用或被替代,目的是为了继续实施其庞大的欧洲新秩序的重新组建计划。不难看出,“特殊的生存条件”、“特殊的待遇”或是“特殊的汽车”比“大屠杀”,“死刑”以及“毒气运送车”来得更模糊。这样的谎言和托词可以使种族大屠杀计划实施并使公众保持中立态度,对事实真相一无所知。更有甚者,那些纳粹分子继续将这些邪恶的口头或视觉上的诡计利用到死亡集中营的杀人机器上。在那里,毒气室的接待厅门口你会看到“淋浴房”或是“浴室”这样的字。这些伪造的标识目的是欺骗那些无助的人们去合作,从而使犯罪者的杀人计划得以更方便实施。那些杀人者常常不愿意告诉那些犹太受害者将要被处死。因而,他们就变成了在精神层面上模糊的“灰色地带”犯罪的合作者。他们的工作组织已经在语言学上被确定为“特遣部队”。在人类毁灭过程中的这种奇异表现揭示了德国杀人者所特有的深不可测的邪恶。
Judeocide一书从头到尾都留下了德国语言的印迹,这并不奇怪。在那本6500词的词典中,几乎没有一页将犹太教徒(Jews)和犹大书(Jude)单列出来,给出参考条目。更为讽刺的是,今天许多德国人避免使用“第三帝国”这个说法,以及具有疑义的“犹大书”的用法。他们说“对那个词感到不安,因为与之相联系的有许多种含义”。他们试图使用“犹太人”或“犹太血统”这些词。同时,德国人依然使用这些委婉的说法作为在语言学意义上的对隐藏起来的纳粹意义上的遮蔽。为了掩饰他们犹太族邻居或是朋友的放逐和毁灭,他们更喜欢用一些熟悉的词,例如“重新安置”、“撤离”和“转运”。
(2)“被侵蚀的记忆”:幸存者战后对德语的回忆
对于幸存的犹太人来说,一些德语术语由于它们的多意性依然难以翻译。Umschlagplatz是指“迁移地点”,但对于那些有过亲身经历的人来说,它依然是指犹太人被驱逐的集中地。在许多场合中,他们忍受着德国犯罪者在各种场合包括公共布告、政府公文中的这种说法,更为重要的是,在私人的交往中,也是如此。在一次语言调研方案中,我采访了大屠杀的幸存者,他们形象地回忆了当年德国纳粹党卫军官员以及德国和奥地利士兵们的威胁、侮辱和咒骂。到了今天,他们引用了这些如此熟悉的词。对于许多人,德语的声音依然等同于卑鄙、残暴和谋杀。因此,甚至连无伤大雅的德语惯用语“ Alles raus! ” (“每个人都出去”)也会在感情上伤害到他们,让他们回忆起战争。尽管他们也在尽量消除对德国、德语以及对普通德国人的不信任。
(3)受害者在语言学上的反应——《来自地狱的话语》:奥斯维辛集中营受害者的语言
人为制造的种族灭绝大屠杀依次影响着被关押在奥斯维辛集中营里人们语言的发展。“ lagerszpracha” 就是独一无二的德语—波兰语合成词。直到最近,波兰语言学家Danuta Weselowska在她1996年的一卷《来自地狱的话语》中才对此定义并进行了研究,这本重要的书被翻译成德语并在德国出版。
集中营的语言反映出了语言的破坏作用,就像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幸存者利瓦伊所回忆的那样——“德语——尖刻的、咆哮的、充满猥亵和诅咒……”然而这并不仅仅是了解集中营的一个途径,它还证明了那些被关押在集中营里的人们是如何被剥夺了作为人的权利。我在这里要说到两个词:囚犯头儿和穆斯林,它们足以成为集中营以及里面种种状况的缩影。囚犯头儿是有一定权力的,是被纳粹党卫军授予“特权”高于其他囚犯的囚犯,囚犯头儿经常行为残忍,但可以免受惩罚。他们的暴力和愤怒经常发泄到那些由于饥饿、疾病和虐待而受到蔑视的最虚弱、最没有反抗能力的囚犯身上,例如穆斯林。这个意为“穆斯林”的德语词被用在那些虚弱的不足以活命的人身上。Weselowska对于这个词在集中营里的特殊用法做了语源和意义上的解释。除了这些词在生理和心理上的意义之外,它们在那些囚犯的身上也可以体现。他们被称作就像祷告的穆斯林一样,从头到脚披着破烂的毯子,并来回抖动着。在这样的状况下,也就没有了性别的差异,但是这个词有女性的形式,Muselweib,其中Weib在德语中是对妇女的一种侮蔑。
这样的人很少能幸存下来——即使有,也是因为其他人的惊人的、无私的照顾。穆斯林表现了人活着已经退缩为一个“活物”,他们可怜的状况被那些幸存者所目睹,其中一个说道,“对于这些人,已经没有任何的尊严可言。他们拖着满是伤痛的身躯穿行于集中营之中,瘦弱的脖子拖着摇晃的脑袋,完全不顾身上的伤口上污浊的泥污。我们对这种悲惨的处境都非常恐惧,我们都希望死神快些降临,即便死是不可避免的,但可以不使我们遭受同样的命运”。
从这引用的话中可以看出,集中营中的状况和遭遇比即刻死亡更令人恐惧。它用魔法召唤着使之产生的“邪恶”。
三、艺术
(1)破译“人类密码”:穆斯林的形象
这种在集中营所产生的让人恐怖的人,就是穆斯林,它意味着存在于文明生活中最底层的、所有生存的希望都被践踏的人。作为诗人和幸存者的维拉(Vera Meisels)这样描写它,“你无法分辨他是个男人或是个女人……如果我可以比喻,那就像是‘影子’或是‘草人’。他们是一架披着黄色干瘪皮囊的骨骼。更糟的是,他们对生存完全丧失了希望,变得行尸走肉一般,经常是没过多久就死去了”。她幸存了下来,并且刻画了这样一个不朽的类似于僵尸一般的形象,就像是透明合成树脂的雕刻。在她的作品里,有三点较为讽刺的地方。第一,Meisels刻画了这个不朽的形象,这个形象现在也被世界所瞩目,然而现在作为它的模型的人们都已经不复存在了。第二,穆斯林这个形象已经从它曾经被嘲弄和辱骂的卑下地位中解放出来了。污秽的、腐烂的臭味和可见的痛苦消失了,留下的这样一个雕像,我们只看到了它形象的方面,就像没有生命的透明合成树脂。最后一点,这个形象所流露出的审美层面上的美感对于一个艺术品而言是具有典型意义的,尽管这种艺术得自于大屠杀之中。
(2)德国文字的使用:“文字之战”
对纳粹过去和记忆的恐惧并没有随着《犹大书》(Judeocide)结论和战后消灭纳粹化的出现而消失。许多关于大屠杀的记忆和证言揭示出它依然存在于幸存者思想深处的无意识中和德国人集体的记忆中。只有一小部分犹太人的幸存者现在仍然留在德国。但由于“异族”而被认为是“和人类(德国人)的种族不相容”时,许多人开始怀疑他们的犹太人身份。在当今这个民主的德国,他们注意到了“公开的忏悔和官方的亲犹太态度”,但他们也察觉到缺少德国人的同情和来自“持续反犹太”的困扰。他们对于德国和德国人的这种恐惧与愤怒传承给了他们的孩子。由于在大屠杀之后的环境中这样一些“产物”的存在,对过去灾难性的历史关注有时会显得很尖锐。艺术家鲁思(Ruth Liberman),一个德国犹太人幸存者的后裔,已经开始触及她父母那曾经留下过创伤的生活。她的一个独特的计划就是将文本与艺术相融合,而憎恨那些德国传统文字。由于对它们的扩大和揭露,她使得它们变得易受攻击,之后再攻击它们。在舆论的战场上,它们遭到了猛烈的抨击。或许是由于她开始承担她父母所遭受的一切,她甚至连“负担”这个词也要抨击。
当幸存者和他们的后人表达在过去历史中所受到的伤害时,Liberman对带有污点的德文的否定在思想领域陷入了一种进退两难的局面。文字攻击是对于她的“进展中的工作”最恰当的表述。目前的这种象征性的行为或许对于那些德国人是一种稳妥的但却迟来的了解。当她逐渐地使那些词语相形见绌的时候,在她的艺术作品中有对这些德语的“刺痛”。从心理上讲,她是复仇,但有些人认为过去的创伤已经导致了她的病态症候。
Liberman认为德语“预谋杀害的人的名单”(“ hit list”)包含了Jude一词,因为它使她回想起那段悲惨的遭遇。然而,这个词却使她犹豫。或许这个词真的是有污点,但它同时也证明了犹太人的身份和(悲惨的)历史。她希望通过对它的攻击可以表示犹太人的第二次死亡并可以再次展现德国人到底做了什么。她的作品也反映了与理论上不同的另一方面:在大规模的屠杀面前,个人最终会放弃失望和愤怒。
四、 纳粹暴行60年后: 冬青——抑制谋杀:犹太儿童坟墓遗址的标记
在影片中,安娜作为作者写了一本名为《冬青——抑制谋杀》的书成为影片的结束。冬青在德国是经常被种植在墓地的一种植物。安娜选择它作为德国人想要掩盖历史的一种恰当的象征。那些经历过它的人们想要忘记它,但是战后的一代却想要了解和谴责它。现在的第三代人以不同的方式表示疑问。从积极的方面说,现在德国的学校里有关于大屠杀的课程,同时年轻的大学老师和艺术家对于那些逝去的犹太人的生命的遗迹进行揭示。德国官方的职责也包括纪念犹太遇难者并安慰幸存者。但是,这些广为公开的事实却隐藏了在公众之中那种持续的感情上的压抑、敏感和禁忌。更大程度上的事实是,大部分德国人是由于羞耻感而拒绝面对大屠杀,而不是出于敌意。对于把犹太人驱逐出自己的社会,对他们造成的迫害以及不论是作为目击者、犯罪者还是旁观者对他们实施的谋杀,这一切要如何来偿还?或许德国正在遭受的可以称得上是德国大屠杀后综合症候,这其中包含了作为德国公民对于犹太人的被压抑的明确的记忆。在当今德国,这个悲哀的事实被许多社会学和心理学的研究所证明。
五、结语
作为结语,我想总结一下这些女性在我们如何铭记历史的过程中所做出的种种贡献。尽管她们的方法各有不同,但是这都为其他想要纪念过去和教育新一代的人们提供了范例。由于深思熟虑的目的,安娜使她德国的家乡再一次回想了纳粹的历史。作为对于那些犹太儿童的祭奠,她不仅对于将当年实施暴行的遗址标示出来,并且使这段至少是对于那些曾经被囚禁在这里的幸存者来说的被遗忘的历史再不会被遗忘。对于2005年的一些短暂的瞬间,即便不是自愿的,她也使过去的敌人、胜利者和被征服者在以前的犯罪者的土地上站在了一起。对于那些几乎对这个地方遗忘的人来说,这是可行的。
Elida Schogt,影片《Zyklon的肖像》的制作者,她让我们想起那些在数以万计的毒气战争中被谋杀的人们。她用对科技的机械化屠杀的解释,激励我们去深思每一次死亡所带来的痛苦以及人们控制科技的强迫性冲动。
Karin Doerr,通过她的关于第三帝国语言的作品,她使我们认识到语言在帮助成就邪恶罪行的过程中的作用。《纳粹德国:德意志第三帝国语言的英文词典》使我们认识并且注意到那些幸存者的关于语言的记忆。它提醒我们要反对纳粹术语的任意使用,这些语言可以印证犯罪者的想法,同时也可以促使谋杀事件和受害者个人在心理上和语言学意义上的区分。词典就像一个鲜明的提示,告诉我们种族主义如何毒害了整个社会并深深影响了下一代。
Danuta Weselowska在语源学意义上的对于集中营中出现的术语的研究向我们揭示了德国纳粹灭绝人性的过程,同时也显示了它在社会—语言学上的重要性。通过编辑和分析,她再现了那些受害者的语言和遭遇,避免它们被遗忘。
作为雕刻家和诗人的Vera Meisels以一个遭遇过令人恐惧的人类大屠杀的死亡集中营的幸存者的口吻在讲话。她的作品不仅展示了对于她而言意味深长、持久永恒的影响,同时也表明了艺术在娱乐之外的意义。她的艺术不仅保护了对于沉默的受害者的记忆,同时也对未来敲响了警钟。艺术可以激励社会。
Ruth Liberman通过艺术作品“文字之战”揭示了德国文字残留的影响。在她的评论中,“关于证词、文案以及‘最后的文字’中的诗学”,她对于伤痕累累的历史十分关注,尤其是大屠杀,这在美国艺术中具有纪念意义。
这些北美和欧洲的女性的言论表现出她们用各自不同的方式对于纳粹暴行所造成的持续影响的关注。她们的作品向我们展示了后现代主义如何打破了将历史置于被社会所遗忘的角落里的传统禁锢。每一部作品都向我们昭示着那场罪恶的战争。因而,我们与会的所有人都应当从这六位女性的作品中吸取教训:不要忘记第二次世界大战罪恶的历史并且尽最大的努力从中吸取教训,当然不是作为战争的胜利者,而是在今天,世界各国如何朝着一个更为安全和人性化的目标而努力。
译者简介:唐培林,中国传媒大学教师。(北京 1000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