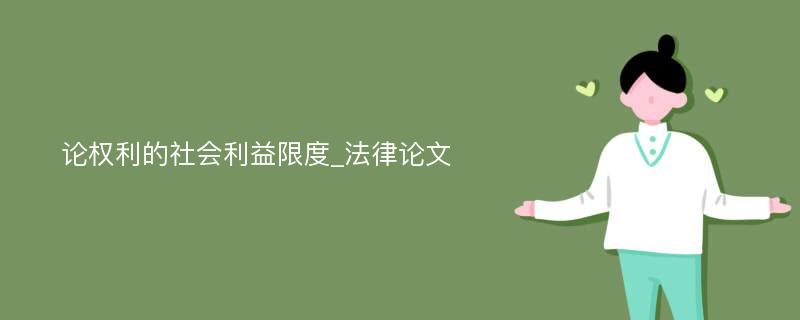
论权利的社会利益限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限度论文,权利论文,利益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F0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525(2010)05-OO1-08
一、问题的提出
2008年5月15日下午3时左右,成都全搜索网站志愿者组织的一支救灾物资车队由绵竹市区开往绵竹土门,在途经板桥镇八一村与西南镇隆兴村地界时,部分当地灾民拦住车队,请求车队人员给予救助,但车队押运人员未表示同意,之后少数灾民爬上一辆小货车,将车上物资掀下,由车下众灾民将其哄抢一空。小货车被哄抢完后,灾民停止了哄抢行为,救灾物资车队继续前行至土门镇及广济镇分发物资。被哄抢的小货车上装载的物资有帐篷30余顶和毛衣60余件。2008年5月16日,网友“仁爱.兔斯基”在“成都全搜索”网站“四川地震专题”版块,发表了一篇名为“骑着摩托抢物资,我在绵竹看到最丑陋的一幕”的文章,文章除用文字回放当时事件外还附上了被哄抢时的现场照片,此文发表后,社会各界反应强烈,几乎所有网友都对哄抢物资的人予以了强烈地批评和鞭笞,言辞激烈,愤恨之情随处可见。随即,绵竹警方成立了调查组调查此事。据德阳刑警顾安民透露:“经过实地认真调查,调查组发现当地参与哄抢的大约有20人,都是板桥镇八一村五组与西南镇隆兴村六组的村民,但与原文所称不同的是,他们确系地震灾民。当地的房屋倒塌和损坏非常严重,绝大多数房屋已无法入住,而在发生地震后帐篷和防水雨布一售而空,时天又下雨,在万般无奈之下,他们才哄抢了上述物资。调查组在综合考虑当地受灾情况并报经上级批准后,决定让参与人员退回被哄抢物资,并对他们进行批评教育,责令具结悔过,并向物资捐赠者探路者公司及组织者成都商报道歉。”① 之后调查组发布了对于此事件的事实调查和处理结果,在获知调查报告后,许多网友对于哄抢灾民予以了理解和原谅。
二、生存权优先性的正当性证明
在真相发布中,德阳刑警顾安民还指出,“生存权是人的第一权利,面对一群被地震恶魔反复蹂躏而苦苦挣扎的灾民,为了一个能遮风避雨的帐篷而作出了一定的过激行为,你忍心对他们下重手吗?”② 这就构成了警方不对灾民哄抢行为给予犯罪定罪处罚的理由。尽管我们认为不予处罚是人性化的表现,符合当时灾民的实际情况,但是不予处罚的理由不充分。
有学者对这种不予处罚的正当性给予了充分的论证。他们认为,在刑法意义上,参与绵竹哄抢的灾民确实构成我国刑法所规定的聚众哄抢罪。但是为什么不给予刑事处罚呢?理由有两个:第一,这与刑法上紧急避险理由相关。他们引用西方格言“紧急时无法律”(Necessitas non habet legem; Necessitas caret lege)的格言,认为“在紧急状况下,可以实施法律通常情况下所禁止的某种行为,以避免紧急状态所带来的危险。在紧急状态下所产生的这种权利,被称为紧急权。”③ 依此理论,参与绵竹哄抢的灾民的行为符合以下四个要件:(1)必须针对正在发生的紧急危险。之所以说参与哄抢的灾民面临着正在发生的紧急危险,在于受地震灾害的影响他们自身及其家人已经处于生存受到极大威胁的状态之中。(2)所采取的行为应当是避免危险所必需的。参与哄抢的灾民之所以哄抢帐篷在于地震后帐篷已经成为生存的必要条件,而没有帐篷他们基本的生存就无法得到保障。(3)所保全的必须是法律所保护的权利。灾民哄抢帐篷的目的在于维系自己和家人的生存,我国宪法明确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而生存权是人之为人的基本人权。(4)不可超过必要的限度,所损害的利益应当小于所保全的利益。④ 他们认为参与绵竹哄抢的灾民的行为是符合紧急避险之要件的。
而且,他们还从权利冲突的视角给予了进一步的正当性论证。这些学者们指出,“现代意义上的生存权已发展为一种复合型权利,具体而言包括生命权、基本生活保障权、生存发展权等。法律意义上的生命权是以自然人的性命维持和安全利益为内容的人格权。”⑤ 但是在有关人权利体系中,权利之多是我们已经能够预期的,所以权利之间的冲突在所难免,那么权利之间必须给予排序,即“有权利冲突就必有权利位阶,权利位阶是解决权利冲突的必然措施。”⑥ 他们将在权利位阶中居于强势地位的权利称为优先权,优先权的效力是:其一,时间上的有限性;其二,优先权的限制性;其三,优先权的优先保护性。在此理论基础上,他们引用博登海默的话作为观点,“生命的利益是保护其他利益(尤其是所有的个人利益)的正当前提条件因此它就应当被宣称为高于财产方面的利益。”⑦ 所以,人格权之首的生命权优位于财产权性质的所有权,即生存的需要永远高于保有财产的利益。
这些学者们指出,生存权是以“极穷权的生存权”开始其思想萌芽的,极穷权的生存权指的是满足人生存的基本需求,保障最为基本的生存需要,使人的生命得以延续的权利。极穷状态指的就是维系人生存的最低限度的基本条件处于得不到保障的边缘,人的生存状态受到了实质的威胁。⑧ 就参与哄抢的灾民的行为来看,由于“哄抢的灾民在震后无法通过市场交易或政府安排来及时获得维系自己及其家人最低限度生存条件的必需基本物资,而同时囿于突发事件的突发性、紧急性、复杂性、关联性、危重性、不确定性等特征,在国家无法全面及时地施以救援的紧迫时间点上,为了生存他们只能依赖于自身的自救,而极穷状态下的生存权赋予他们去有限获取他人物资以维持最低生存需要的可能,此种状态下的极端行为并不能构成犯罪……只要不危及他人的生存状态,极穷状态下的灾民为了保障自己的基本生存,有权利获取他人的财产。”⑨
实际上,这种观点在学术上有绵延的传承。一直以来,人们的内心都认为,人的生命是无价的,是不可以重新再来的,因此,在权利的位次上,生命权的优先性因为生命权的特性而生成。笔者承认,这种说法是有道理的,也认可生命权的优先性终极真理,但是想反驳的是生命权压倒一切吗?当然,上述的作者们可能不同意这个命题,他们的意思仅指,在紧急状态下(如地震),因为生命权受到危害,因而可以获得他人的财产。但是,笔者的命题依然是与此相关:即使在人的生命权受到危险的状态下,获得他人财产也是有限度的。
三、生存权能压倒一切吗
问题的讨论依然要回到灾民本身,当然,也不会仅仅局限于灾民本身。我们先来看一下地震后灾区的景象。“地震发生第二天起就面临食品短缺,‘有的人实在饿了,就在废墟里找吃的。’高伟说。断水、断粮、断路,为了争夺有限的供给,桃关开始出现‘丛林法则’,抢粮食的团伙开始出现。地震当天,两个商店被抢,其中几个工厂食堂的东西也被抢劫一空。”可见饥饿在灾区是普遍存在的,而且“几万人的安置,库存不过几百顶帐篷,杯水车薪。雨中,大家自发保护老人和孩子。雍强等年轻人把带上山的毛毯和被子让给老幼和妇女,只剩最后一根烟了,几个小伙子每人抽一口。‘灾难让大家成为一家人,凡有吃的东西,大家就分着吃,’县委书记王斌备感欣慰。”大家都等着空降物质,“空降物资是第三天。5月14日,空降很不成功,只收到3样东西:两箱矿泉水,一点食品,七顶帐篷。天气原因,峡谷一直刮大风,空投效果很差。汶川到理县的公路打通前,县城最紧张的时候,只有1万斤粮食储备,够县城人吃一顿饭,而且是在前几天全县所有人每人一天只吃一顿饭的情况下,再也支撑不下去了。”⑩
这种境况在地震后的灾区随处可见,毕竟这次地震涉及到了将近1000万人口,四川西部的许多地区。也就是说,受到生存权威胁的何止百人?笔者毫不否认下述论述,如中世纪神学家托马斯·阿奎那说:“如果一个人面临着迫在眉睫的物质匮乏的危险,而又没有其他办法满足他的需要,那么他就可以公开地或者用偷窃的办法从另一个人的财产中取得所需要的东西。”“一个人为了足够的生活品,可以使用暴力。”格老秀斯也认为:“在极度必须的时候,关于诸物使用的原理可复活为原始权利,这时候物的状态是共有的。为何?因为根据人类派生的一切财产法都是把极穷状态排除在外的。”(11) 换句话说,“人在生存受到威胁的时候,应当把这种危险转嫁于社会,让拥有财富的人与之共担。这种时候人无论用什么方法获取他人的财物都不是犯罪而是权利。”(12) 生存权是维系人的生命的民生权利之核心,生存权受到侵犯的时确实有维护自己权利的必要。但是,从上述论述中,可以看到的是,即使是生存权受到威胁的时候,也是有限制的,换句话说,生存权不是能够压倒一切权利的权利。
第一,参与哄抢的灾民的行为是自救吗?生存权是一种维护生命延续的权利,这意指个人确实应该对自己的权利给予足够充分的重视和救济。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就说参与哄抢的灾民的行为就是自救。(13) 在地震灾区中,饿的人很多,要吃饭的人很多,要帐篷的人很多,但是给予不足或者给予有限,这时候就不能够把哄抢的行为当做是自救的行为。在引言的案例中,经过绵竹的救灾车所运输的救灾物质按计划不是给参与哄抢的灾民的,而是给其他地方的灾民的,因此,实际上,这并不构成自救,而是一种危害别人生存权的行为。我们可以再举个简单的例证进一步强化:有5个人因地震被困在一起,只有20个饼(5天以后才有食物供应),这可以维持他们一段时间的生命,结果有一个也很饿的人跑进来把他们的粮食全部偷吃了,这样的结果是这5个人在这5天之内就有可能有人饿死。你说这种偷窃合理吗?肯定不合理。能够以生存权为理由对抗别人吗的生存权吗?当然也不可以。
第二,有生存权需要的人可以抢另一个有生存权需要的人的物品的权利吗?如果一个人面临着迫在眉睫的物质匮乏的危险他就可以公开地或者用偷窃的办法从另一个人的财产中取得所需要的东西,然而对此带来的疑问是,如果被抢的那个人也正要需要这些东西呢?也就是说,生存权和生存权之间存在冲突了,怎么办?这时我们就不得不强调生存权的有限性了,毕竟个人与个人之见的生存权是平等的。所以,笔者之所以不认可绵竹参与哄抢的灾民的行为,根本原因在于,他们是灾民,但是其他地方也有灾民,甚至其他地方的灾民可能比参与哄抢的灾民更加严重,或者说,其他地方的灾民更加需要这些救灾物质。孟德斯鸠曾经说:“自由是做法律所许可的一切事情的权利;如果一个公民能够做法律所禁止的事情,他就不再有自由了,因为其他的人也同样会有这个权利。”(14) 即,如果因为生存权受到威胁可以剥夺别人的生存权,那等于生存权就没有了。所以一切权利都是有限度的,一切权利都应该以不侵害别人的权利为前提,一切权利的拥有者都要能够合作为前提。所以,在面对生存权与生存权的冲突的时,是不可能简单的下结论说,某个人的生存权比其他人的生存权重要或者具有优先性。只有承认这一点,参与哄抢的灾民才具有法律意义上的合法性和道德意义上的合法性,否则,法律意义上的合法性不仅不可能,道德意义上的合法性更不可能。但是事实上,不管是法律还是道德告诉我们,绵竹灾民的哄抢行为都是有悖于我们的知识常理的。当然,绵竹灾民如果哄抢的财务是物产丰富的某个人的财产,但是这个人又是一只一毛不拔的“铁公鸡”,或者他想囤积居奇,那么这种哄抢的道德合理性就能够成立了。
第三,最核心的问题是,生存权在何种条件下能够压倒一切?否认生存权的重要意义并不是本文的基本目的所在。甚至本文也认可这种观点,即在生命权与其他非生命权相冲突的时候,可以考虑将生命权作为价值位阶较高的价值来考察。但是,如果生命权与生命权相冲突时,该如何抉择呢?英国历史上著名的“女王诉杜德利与斯蒂芬案”(Her Majesty The Queen v.Tom Dudley and Edwin Stephens)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详细的样本。1883年,澳大利亚游船木樨草号从英国埃塞克斯前往悉尼,途中沉没,四个幸存者——船长杜德利、助手斯蒂芬、船员布鲁克斯和见习船员帕克——被困在一艘救生艇上,全部食物只有两个罐头。在第19天,杜德利建议,以抽签的方式选出一个人被杀掉,让其他三人吃掉,以求生存。对此,布鲁克斯反对,斯蒂芬表示犹豫。而杜德利表示:无需犹豫了,帕克身体最弱又没有家人,他肯定先死。杜德利随后杀了帕克,他们三人以帕克的尸体为食撑着。四天后,他们被路过的法国帆船蒙堤祖麻号救起,蒙堤祖麻号进英国法尔茅各斯港短暂停留,杜德利、斯蒂芬和布鲁克斯以涉嫌故意杀人罪被逮捕收监。陪审团同情被告,但为了避免无罪宣告的结果,法官要求陪审团进行特殊裁决,只认定事实。根据陪审团认定的事实,法官宣告被告犯有故意杀人罪,驳回他们的紧急避难抗辩。被告被判处绞刑,随后被维多利亚女王赦免了。(15)
围绕这个案例,1949年,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L·L·富勒在《哈佛法学评论》上提出了一个虚拟的人吃人案件,这个名为“洞穴探险”的案例后来被称为“史上最伟大的虚拟案例”:4299年5月上旬,在纽卡斯国,五名洞穴探险人不幸遇到塌方,受困山洞,等待外部的救援。十多日后,他们通过携带的无线电与外界取得联络,得知尚需数日才能获救,但已水尽粮绝,为了生存,大家约定通过投骰子吃掉一人,牺牲一个以救活其余四人。威特摩尔是这一方案的提议人,不过投骰子之前又收回了意见,其它四人却执意坚持,结果恰好是威特摩尔被选中,在受困的第23天维特摩尔被同伴杀掉吃了。在受困的第32天,剩下四人被救,随后他们以故意杀人罪被起诉,而根据《刑法典》规定:“任何故意剥夺他人生命的人都必须被判处死刑。”(16)
在纽卡斯国的初审法院,被告被判处死刑。被告上诉到最高法院,富勒虚拟了五位大法官就此案出具的五份不同的判决意见书:首席大法官特鲁派尼从法律实证主义的观点出发,认为法律是法律,道德是道德,同情心不会让法律人违反自己的职业判断,去创造例外,所以他支持有罪判决;福斯特大法官则主张应该根据立法目的,对法律规则进行解释,联邦的法律不适用此案,被告无罪;唐丁大法官认为这是一个两难的案件,选择回避退出此案;基恩大法官主张法官应当忠于自己的职责,不能滥用目的解释,去规避法律规则的适用,坚持被告有罪;汉迪大法官则主张,抛开法律,用常识判案,通过常识来平衡道德与法律的冲突,坚持被告无罪。(17)
在这个案例中,各种法理学流派知识充斥,各种观点也争锋相对。最核心的问题是,为了多数人的生命权,能不能牺牲其中一个人的生命权?如果强调生命权压倒一切,显然这是不可以的。但是,如果按照我国现有刑法,以紧急避险来抗辩,似乎又是可以的。面对这种两难,法律该如何抉择呢?
我们可以重现电影《2012》中的镜头来在更宏观的意义上展现。当地球到了要毁灭的时候,人类面临着灭种的危险,这时各个国家的元首秘密开会决定在世界上的最高峰造“诺亚方舟”,让一部分人幸存下来,挽救人类作为一个种族覆亡的命运。而获得登上诺亚方舟资格的人都是有政治地位的人和有钱捐助的人。在这部电影里,我们看到了世界快要灭亡时,人类的生命权实际上是没意义的,甚至,还比不上那些“做种”的动物。但是,从可行性来看,这时元首们的决策又似乎是正确的,为的是人类作为种族能够延续。显然,这里讨论的是一个放大版的“洞穴探险”问题。如果从电影《2012》的立场来看“洞穴探险”问题,则“洞穴探险”问题是一个正当的行为,这也否定了生命权压倒一切的命题。这个结论是悲哀的,但是又是很实在。当然,承认这个结论不是为了要人们鄙视自己的生命权,相反,从学理上讲,就是要人们正确估价自己的生命权,从而获得超越于简单的伦理价值之上的意义认识。
总之,对绵竹参与哄抢的灾民不予处罚是正确的,但并不意味着在“生存受到威胁”时的哄抢行为是合理的,这意味着个人在享有权利的同时,实际上要也受到制约。或者明确地说,权利还应该受到社会利益的制约。
四、权利的社会利益向度
现在,我们有必要进一步对以生存权为重点的权利范围和界限做一个更为深刻的界定了。上面所指出的生存权不能够破坏另一个人或另一些人的生存权,隐含的意义也在于权利的限度所在。实际上,这种道理和逻辑还可以进一步的演绎,即所有的权利都是有使用的范围和限度的。
权利的社会利益向度意味着在权利话语中,个人绝不是唯一的利益主体,个人在享受自己权利的同时,必须共同承担为了社会利益的实现而应承当的损失以及为了实现社会利益而承当对自己权利的侵害,但,非常重要的是,这绝不意味着社会利益的造就应当建立在公民个人的重大损害乃至完全损害之上。也就是说,个人的权利确实可能为了社会利益付出而有必要奉献自己的权利,但这不应该是无私的,而应该是等价有偿的。
我们可以再讨论一下财产权的变化来看待这一问题。当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写入一些西方国家的宪法以后,这些国家很快就发现权利的绝对化有重大隐患和后果,即导致了许多社会公益措施和设施无法施行和实现,或由于财产主人的拒绝合作而耗费高额成本。比如,在一西方国家,再修建铁路的时候需要拆迁一个老人的一座房子,补偿款是非常丰厚的,可以供他在这个城市的任何一个角落买一套很大的房子;但是老人的怀旧心理比较浓重,不管政府如何做工作,老头就是拒绝合作,最后导致的是该铁路计划不得不得重新规划设计,这就是权利绝对化的后果。所以西方一些国家在近百年来纷纷放弃了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硬性原则,而走向了为了更高的权利目标请求权利合作的新理念。这对于我们国家的启示意义是多重的。在我国,房屋拆迁问题是一个时时面临新问题的老问题。房屋拆迁在中国之所为成为问题,就是公民个人承担了为社会利益的损失但没有获得相应的足够补偿。这是我国公民权利没有获得应有地位和重视的表现。我们主张民生权利确实要为社会利益让位,但是绝对不是通过剥夺民生权利的做法或借社会利益之名来伤害民生权利。实际上,在我国的法治发展语境中,公民的权利还只是出于弱势地位,所以学者们和群众以非常期待的心情渴望权利有足够的“硬度”,因此,在我国加强民生权利保护非常重要。只是,为了吸取美国的权利绝对化观念的教训,我们对权利的未来发展需要有适度的限制和克制之道,以免重蹈美国之覆辙。从社会利益对民生权利的要求来看,其基本要求有三:
首先,权利应当具有可合作性,这是社会利益能够实现的基本前提。上面已经指出,权利是个人生存和发展之权利体系,是每一个人都享有的权利,权利的内容是相等的,因此,一个人的权利不成为另一个人的权利的对抗理由。但是个人的权利是出于社会中的权利,因此,个人权利的实现必须放置于社会这一舞台中的考虑和评价,“一种利益要具有成为一种权利的资格,仅当一个有效的法律制度通过使用集体的资源来保卫它,并把它作为权利来对待。”(18) 麦特·里德雷对此也有深刻的认识。他认为,个人权利之所以实现,端赖来人类社会的分工和合作。麦特·里德雷从细胞的社会可以看出劳动分工的具体意义。他发现,正是因为有了细胞的劳动分工,所以人类肌体才得以和谐的生存发展。他说,“血液中的红细胞对肝脏细胞来说至关重要,同样,肝细胞对红细胞来说也不可或缺。两者之间协作的力量远非单个细胞所能比。人体内的每一个器官、每一块肌肉、每一颗牙齿、每一根神经、每一块骨头都有自己的作用,支持着整个肌体的运作。它们从未想过要独自承担所有的任务,因此人才比动、植物高级得多。实际上,从生命一开始劳动分工就扮演着重要角色。基因个体之间不仅要分担细胞的运转工作,而且它们早就学会了如何储存信息,如何与负责化学物质和结构建设的蛋白质进行分工。我们知道这也是劳动分工,因为核糖核酸(RNA)这一生产基因的更为初级更为稀少的物质本身就杂而不精,它虽然既能储存信息又能担当化学物质的触媒,但在储存信息方面它比不上脱氧核糖核酸(DNA),在化学物质的催化过程中又无法与蛋白质相匹敌。”所以,“正是由于各机体间的协同作用人类社会才能顺利运转,也正是这一点将我们与其他群居动物区别开来。”(19) 权利的救济与此原理相同,一个细胞受到了病毒侵害,单个细胞是不可能完成杀毒任务的,而是要考各个细胞的协调合作杀毒才得以清楚病毒;同理,一个细胞权利妨碍了其他细胞的权利的实现,实际上会阻碍人体的有机运行,那么人体健康的恶化会影响这个细胞的生存空间。人的生存和发展也一样,没有合作条件,即使是英雄般的巨人,也会在孤单中老去;而合作的人们,即使再为孱弱,也会产生合作的力量。个人的权利是保证个人能够生存和发展的理由,但是不是更好的生存和发展的理由;如果个人权利的实现是建立在对别人权利损害的基础之上,那么实际上反过来并不意味着个体权利是成功的,相反,危害甚多。总之,正如博厄德和理查森所说:“遵奉习俗,相互仿效的文化传播机制为人类团结协作的精神提供了至少一个无可辩驳的理论依据,从经验论的观点看同样合乎情理,它解释了人类有别于其他所有动物的协作行为,不管是否与自己的利益相抵触,人类都能与自己关系疏远的同类进行合作。”(20)
其次,权利应当具有互惠性,这是社会利益能够实现的理论基础。权利的互惠性即权利应该促进作为人们之间的发展而不是构成人们之间权利发展的天敌。“在罗尔斯的正义论中,互惠(reciprocity)的概念居于枢要的地位。”(21) 早在很多年以前,人们就考虑到,为什么社会能够形成呢?许多思想家把问题的根源归结于社会中的人们是互惠互利的,一如富勒所说,“社会是由一个无所不在的互惠性纽带绑结着的,在社会中,各种义务一般都能追溯到互惠原则。”(22) 他举合同规范程序之例证明“生动地保留在人的心智中的互惠性,它构成了全部社会生活的基础。此外,习惯于相互交易的社会人,他能洞穿人们各种活动间的相互关联,并明白为什么有些付出与索取之于公共生活是十分关键的。”(23) 正是因为互惠正义的存在,规则才有了形成可能,法律才有发展的现实,人类才有进化的基础。伯尔曼在考察西方法律发展史的时候,注意到互惠性在11世纪时期西方的重要意义,他说:“就相互的给和取的意义上说,互惠性本身在所有的文明中就是一切商业的实质所在……然而,自11世纪晚期和12世纪以来,西方人所理解的权利互惠性原则,涉及的还不只是交换。在观念上,它还包含有在进行交易的双方之间那种负担或利益均等的因素,即公平交换的因素。这点依次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程序上的,另一方面是实体上的。在程序上,必须公平地参与交换,即不存在强迫、欺诈或其他滥用任何一方意愿或认识的行为。在实体上,即使是自愿和故意参与的交换,也不得使任何一方承受与他所获得的利益极不相称的代价;这样的交换也不能不正当地损害第三方的利益或一般的社会利益。”(24) 这样,对法律规则程序的遵守,对互惠的诉求,也就有了权利的启蒙,所以,“欧洲数以千计的新城市和城镇发展出它们自己的法律类型,这种法律也具有以下特征:客观性、普遍性、互惠性、分享裁判权、整体性和发展的特性。”(25) 也就是说,“无论是权利互惠性的程序方面还是实体方面,都蕴含在自11世纪晚期和12世纪以来西方人所理解的‘权利’这个术语之中。”(26) 进一步说,权利的互惠性不仅在古代西方是可能的,在近代全球也应该可能,毕竟互惠互利是人追求的价值之一,否则人类社会很难在竞争中发展。这也是我们今天强调民生权利的互惠性的原因之一。权利的互惠性,不仅是对西方的模仿,而且也是中国现实的必要要求,如有学者指出,“应当对权利发展与社会发展在中国的具体历史场域中是如何发生互动的过程与进程进行描述,对中国人权利发展为什么会达到当前的现状进行解释进而发现中国人权利发展的特定道路,以及对促使中国人权利发展之特定道路得以形成的背后更为深层的文化与历史因素做出分析。”(27) 我们的传统文化中“仁者爱人”、“兼爱”等思想就为我们提供了权利互惠的良好前提,从而也成为民生权利互惠性的知识渊源。我们不仅不能埋没这种传统,还应当将其发扬光大。
最后,权利应当具有宽容性,这是社会利益能够实现的基本品质。《大不列颠百科全书》认为,“宽容是指允许别人有判断和行动的自由,耐心、不带任何偏见地容忍那些有别于自己或被普遍接受的观点、行为的人。”按照一些学者的解读,宽容“要从人与人或文化与文化之间的相互平等、理解和尊重的基础上来理解,其基本前提和方式是,在不背离或放弃根本原则的情况下,以和平友善的方式,来看待、理解和宽恕他人的异己言行以及‘文化他者’。”(28) 也许宽容含有宗教意味,“但是,就其核心要义而言,它要求人们在人格平等与尊重的基础上,以理解宽谅的心态和友善和平的方式,来对待、容忍、宽恕某种或某些异己行为、异己观念,乃至异己者本身的道德与文化态度、品质和行为。”(29) 这既是一种生活实践,也是权利的一种内在品质。现代社会已经更多的把个人与个人联系到了一起,人的权利与权利之间不可避免的存在一定的冲突,宽容也就成了必要的品质追求,否则,纠纷迭起,权利暴政。可以举一个案例以说明。现在很多人都住在小高层楼里,楼层与楼层之间特别是上下楼之间只有水泥地板之隔,楼层在上的人家比较大的声响可能会影响到楼层在下的人家的生活。假如有这么一个小区,楼上住着运动员张大三,楼下住着音乐家王大四。张大三每天在家蹦蹦跳跳地活动锻炼,王大四心理气愤就在半夜弹钢琴以示抗议。从权利来看,两者都是在自己的家里行为,似乎都是自己权利的正确行使,但是实际上两者都没有适当地考虑他人的生活需要。如果日久,则还可能构成侵权,可见即使有权利作为,也要在适当的度之内,这就是宽容意识所主张的。正如有学者所说,“权利不仅体现为一系列物质性的规定、制度与组织结构,而且更为重要和更为深刻的是,它同时也是或者应当是人的一种生活态度、一种生活立场、一种精神与信仰,这就是把人要真正当做人,或者说不仅自我尊重其为人而且尊重所有的人为人。”(30) 宽容实际上意味着妥协,但是妥协并不是无原则的,而是建立在对权利的充分尊重的基础之上的,“愿意妥协与有原则地维护自己的立场,或批评别人的立场,这二者之间毫无抵触之处。如采用妥协而不是武力的解决方法,正确的原则很可能终于居于优势。如果把具有远见的接受与表里不一等同起来;如果错误用坚持原则作为决不妥协的理由,那就是民主的灾难。”(31) 因此,无原则的固守权利绝对性就意味着权利是冷冰冰的,既没有人性,也没有激情;既没有人情,也没有美德;既没有善良,也没有公正,一切都是个人的自私而已。
五、结语
一切权利,是自我存在和发展的凭借条件;一切权利,不是自私构成的前提。权利的实现,不可能存在于以权利为封闭圈的自我中心之间。人类的合作史早就告诉我们,权利之所以可能,乃是合作、互惠、宽容之故。合作给予我们生存的力量,互惠给予我们社会的美德,宽容给予我们道德之进化,此三者,诚谓民生权利之三醒也。
收稿日期:2010-06-10
注释:
① 参见http://news.uc.sina.com.cn,新浪网,2009年12月3日访问。
② 参见http://wenba.ddmup.com/28/3758093.htm,丁丁网,2009年12月3日访问。
③ 张明楷:《刑法格言的展开》,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241页。
④ 龚艳、尚海涛:《极穷权边界的限定性研究》,《西部法学评论》2009年第5期。
⑤ 同注④。
⑥ [韩]权宁星:《基本权利的竞合与冲突》,《外国法译评》1996年第4期。
⑦ [美]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00页。
⑧ 同注③。
⑨ 龚艳、尚海涛:《极穷权边界的限定性研究》,《西部法学评论》2009年第5期。
⑩ 张悦:《挣扎与求生:孤岛汶川的人性百态》,《南方周末》2008年5月22日。
(11) 徐显明:《生存权论》,《中国社会科学》1992年第5期。
(12) 同注(11)。
(13) 同注⑩。
(14) [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张雁深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54页。
(15) Cannibalism and the Common Law:The Story of the Tragic Last Voyage of the Mignonette and the Strange Legal Proceedings to Which It Gave Rise,(1984)。另可参见《当法律遇到人吃人案》,《南方都市报》2008年3月30日。
(16) 《当法律遇到人吃人案》,《南方都市报》2008年3月30日。
(17) 同上注。
(18) Stephen Holmes and Cass R.Sunstein,The Cost of Rights,Why Liberty Depends on Taxes,New York:Norton Company,(2000),p.14.
(19) [美]麦特·里德雷:《美德的起源:人类本能与协作的进化》,刘珩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版,第38页。
(20) [美]麦特·里德雷:《美德的起源:人类本能与协作的进化》,刘珩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版,第195-196页。
(21) 林来梵:《互惠正义:第四次修宪的规范精神》,《法学家》2004年第4期。
(22) Lon.L.Fuller.The Morality of Law.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69),p.186.
(23) RobortS.Summers.Lon L.Fuller.Californi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4,82.
(24) [美]伯尔曼:《法律与革命——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贺卫方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第425页。
(25) 同注(24),第657页。
(26) 同注(24),第425页。
(27) 邓正来:《中国人权利发展研究的理想与现实》,《中国法学》1996年第1期。
(28) 强昌文:《契约伦理与权利》,山东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25-126页。
(29) 万俊人:《寻求普世伦理》,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507-508页。
(30) 姚建宗:《法治的生态环境》,山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76页。
(31) [美]科恩:《论民主》,聂崇信、朱秀贤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18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