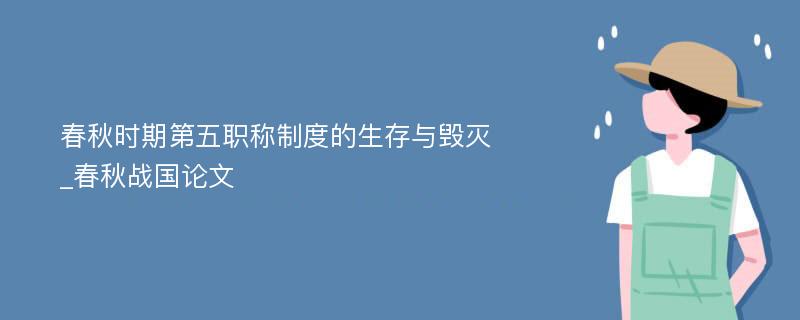
春秋时代五等爵制的存留及其破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春秋论文,时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0559-8095(2006)04-0132-06
西周、春秋时期,诸侯列爵五等:公、侯、伯、子、男。五等爵是分封制度下诸侯的法定身份,诸侯阶层内部依据五等爵规定的等级制原则分配权力和财富,并确立对天子承担的不同义务。迨至春秋,五等爵仍被奉为重要的外交准则,对列国的朝聘会盟活动发挥一定的影响。然而,随着天子的衰微和诸侯的强大,春秋列国开始依据实力强弱进行权力的再分配,五等爵原有的政治功能逐渐丧失,五等爵制遭到了破坏。关于周代五等爵,学界已取得不少重要成果,但多集中于探讨五等爵制的存在与否以及考辨各爵等之间的细微差别,对于这一制度在春秋时期的发展演变则缺少专门的研究。本文拟在前贤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春秋时期五等爵制的存留及其破坏作一探索,敬请方家指正。
一、五等爵制的存留
春秋时期,贵族的爵制又称“列”或“班”。传世文献以及金文材料所载春秋时期的“列”或“班”,诸侯的爵秩为公、侯、伯、子、男。这是五等爵制在春秋时存留的证据之一。
《春秋》是鲁国的编年体史书。瞿同祖先生曾将《春秋》所载诸侯爵称进行全面的排比,发现各国爵称除个别变例外,都是固定不变的,例如宋永称公,齐、鲁、卫等永称侯,郑、曹、秦等总是称伯,楚、吴等国总是称子,许永称为男,等等。[1](P45)杜正胜先生也认为:“《春秋》的五等爵制是宗周旧礼无疑。”[2](P322)对于《春秋》所载的五等爵,顾颉刚先生则持怀疑的态度,他认为:“至春秋一经所以有此秩然之五等者,乃笔削之结果,非鲁史之原文。”[3](P20)赵伯雄先生赞成顾说。[4](P126)其实,在《左传》、《国语》、《孟子》、《公羊传》、《逸周书》、《新书》、《春秋繁露》、《白虎通》等先秦两汉文献中也载有五等爵制。众多文献明载五等爵制,用“笔削”的说法显然是难以讲通的。陈恩林师通过检索上述文献,认为“周代诸侯公、侯、伯、子、男五等爵的排列是有序的”。[5]陈师的结论信而有据,其说可从。
金文中的诸侯爵称较为复杂,存在着侯公兼称、侯伯兼称、侯子兼称、侯公伯兼称、公伯兼称、公子兼称、伯子兼称等所谓“爵无定称”的现象。[6]傅斯年、郭沫若、杨树达等先生据此遽然否定了周代的五等爵制。①他们的论断在史学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后来,王世民先生从西周、春秋时期的金文材料出发,同时吸收了传世文献的一些记载,重新研究了五等爵制,认为除生前尊称和死后追称的情况之外,金文中确已有了固定的五等爵称,它们合于《公羊传》所载的“天子三公称公,王者之后称公,其余大国称侯,小国称伯、子、男。”[7]王世民先生突破了全盘否定五等爵制的观点,对金文所载的五等爵制作出了肯定性的论断。无疑,这就把五等爵制的研究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笔者赞成王世民、陈恩林师的观点,西周、春秋时期确有诸侯五等爵制。否定五等爵制的学者,主要依据是金文、文献中的“爵无定称”的现象。我们认为,金文、文献中即使有“爵无定称”现象,也不能据此遽然否定五等爵制,对“爵无定称”现象的复杂性应作具体的分析。
首先,诸侯并非一次受封而爵位世代不变。诸侯袭位必须经过天子重新的赐命授爵。《白虎通·爵》引《韩诗内传》曰:“诸侯世子,三年丧毕,上受爵命于天子。……世子三年丧毕,上受爵命于天子何?明爵者天子之所有,臣无自爵之义。”嗣君可能因故受王命而改爵。以卫、杞、薛等国为例。据《史记·卫世家》载,康叔始封为侯,其后六代为伯,“贞伯卒,子顷侯立。顷侯厚赂周夷王,夷王命卫为侯”。武公时,“将兵往佐周平戎,甚有功,周平王命武公为公。”卫君的爵位就因王命而经历了数次变动。杞为夏之后,据《逸周书》,西周时为公爵,入春秋后称侯,至鲁庄公二十七年以后则称伯。杜预注云:“杞称伯者,盖为时王所黜。”薛在鲁隐公十一年称侯,至鲁庄公三十一年后则称伯。顾栋高《春秋大事表·外诸侯卒葬表》引《汇纂》云:“薛称伯,时主所黜。”瞿同祖先生考察《春秋》中诸侯降爵的例子,发现“降爵以后,便永从降爵的称谓。”[1](P46)可见,因王命所改的爵位,便成了诸侯新的法定身份。诸侯入为王朝卿士,则升为公爵,但公爵及身而已,其后若非天子特许仍恢复本爵,这是诸侯改爵的另一种情形。如周初伯禽始封于奄,号“鲁公”,并事康王,为王室卿士,其后鲁则为侯爵。郑于宣王时始封,为畿内小国,本爵是伯,东迁之后,武公、庄公连任王室卿士,所以晋升为公,其后又恢复为伯。
其次,诸侯出于习惯可以使用其它尊称、谦称、泛称、贬称等。这些称号与爵位无关,但由于用字相同而容易与爵称混淆,这是造成所谓“爵无定称”现象的主要原因。值得注意的是,诸侯不同称呼的使用不是随意的,要遵循一定的规律。金文材料由于自身的零散性、孤立性,是难以说明这一问题的,而传世文献却保留了宝贵的线索。诸侯称号在实际使用中的复杂情形,见诸文献有以下几种:1.诸侯居丧称子,逾年称公。《公羊传》庄公三十二年:“君薨称子某,既葬称子,逾年称公。”。《春秋》僖公九年宋襄公称子,据《左传》曰:“宋桓公卒,未葬而襄公会诸侯,故曰子。凡在丧,王曰小童,公侯曰子。”2.诸侯卒称本爵,葬时则加谥称公。《春秋》僖公三十二年:“冬,十有二月己卯,晋侯重耳卒”,三十三年:“癸巳,葬晋文公。”《春秋》桓公十年:“春,王正月庚申,曹伯终生卒。夏,五月,葬曹桓公。”《春秋》昭公元年:“六月丁巳,邾子华卒。……葬邾悼公。”类似的例子很多,兹不备举。孔广森《公羊通义》云:“生有五等,没壹称公。王者探臣子之心莫不欲尊其君父,故假以爵之最尊,又为之作谥以易其名。”可见,诸侯葬时加谥称公,是臣子对先君的尊称,而非爵称。3.诸侯在国内可统称“公”。如《春秋》中鲁国十二君皆称呼公,《左传》、《国语》中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白虎通·号》:“伯子男臣子,于其国内,褒其君为公。……心俱欲尊其君父,故皆令臣子得称其君为公也。”所以,诸侯于国内称公,公也是尊称。4.公、侯等可以作为诸侯的泛称。如《尚书·顾命》:“群公既皆听命”,《左传》昭公七年:“王臣公”,《诗经·兔罝》:“公侯干城”,《仪礼·大射》:“公则释获”,其中公、侯皆包括五等诸侯在内。5.《春秋》因特殊原因对诸侯使用贬称。如楚僭称王,《春秋》贬为子;杞用夷礼,《春秋》三称其为子;《春秋》桓公十七年:“葬蔡桓侯”,诸侯葬时例应称公,而蔡桓称侯,何休注说是因为桓侯“有贤弟而不能任用,反疾害之而立献舞,国几并于荆蛮,故贤季抑桓,称侯所以起事”。这是“春秋笔法”的一种表现。②虽然诸侯出于习惯可以使用不同的称呼,但在朝聘会盟时诸侯则一律各称本爵。《国语·鲁语上》:“朝以正班爵之义。”《白虎通·号》以为“诸侯有会聚之事,相朝聘之道,或称公而尊,或称伯子男而卑,为交接之时不私其臣子之义。”《春秋》所记载会盟场合上列国国君的公、侯、伯、子、男爵称,都显示了区分等级的实际意义。[5]因此,在研究五等爵时,应充分注意到爵称与尊称、谦称、泛称、贬称的区别,不能因诸侯称呼的复杂性而贸然否定五等爵制的存在。
春秋时期,在列国纷繁的交往中,五等爵制仍被奉为重要的外交准则,这是五等爵制在春秋时存留的另一证据。五等爵制对春秋列国外交活动的影响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在朝聘会盟中,五等爵制是等列诸侯的原则之一。《左传》桓公十年:“初,北戎病齐,诸侯救之。郑公子忽有功焉。齐人饩诸侯,使鲁次之。鲁以周班后郑。郑人怒,请师于齐。齐人以卫师助之。故不称侵伐。先书齐、卫,王爵也。”鲁国按照周班为诸侯分发粮饷,郑是伯爵,故战功虽著却被列于最后。郑因此愤愤不平,联合齐、卫一起进攻鲁国。三国来战,郑为戎首,《春秋》仍依据王爵列郑于齐、卫之后。“周班”、“王爵”就是五等爵制。鲁以周班后郑,是“犹秉周礼”的具体表现。《国语·鲁语上》载,晋文公解曹地以分诸侯,鲁臧文仲前往,途中有人劝他速行,说:“诸侯莫不望分而欲亲晋,皆将争先;晋不以固班,亦必亲先者,吾子不可以不速行。鲁之班长而又先,诸侯其谁望之?”意思是说,晋文公虽未必完全按照班爵分地,但班爵仍是合理的依据之一,鲁国爵尊而又先至,得到的土地自然比其它诸侯要多。
其二,诸侯爵位不同,相应的外交礼仪也有所区别。《左传》庄公十八年:“虢公、晋侯朝王,王飨醴,命之宥,皆赐玉五瑴,马三匹。非礼也。王命诸侯,名位不同,礼亦异数,不以礼假人。”按照爵位,虢是公爵,晋为侯爵,因而赏赐应有所区别,但周惠王不辨虢公与晋侯的爵秩高低,赏赐同样的礼物,所以被认为是有违礼制。《左传》僖公二十九年:“在礼,卿不会公、侯,会伯、子、男可也。”杜注:“大国之卿当小国之君,故可以会伯子男也。”《左传》哀公十三年:“王合诸侯,则伯帅侯牧以见于王。伯合诸侯,则侯帅子男以见于伯。自王以下,朝聘玉帛不同。”《左传》昭公四年:“王使问礼于左师与子产。左师曰:‘小国习之,大国用之,敢不荐闻?’献公合诸侯之礼六。子产曰:‘小国共职,敢不荐守?’献伯、子、男会公之礼六。”宋为公爵,故献公合诸侯之礼,郑为伯爵,故献伯子男会公之礼。由是可见,诸侯爵秩不同,其外交礼仪也有所差别。
在特殊的情况下,诸侯可在本爵的基础上加等行礼。《左传》僖公四年:“许穆公卒于师,葬之以侯,礼也。凡诸侯薨于朝会,加一等;死王事,加二等。于是有以衮敛。”许为男爵,许君死于为周王伐楚,故葬礼从优,以侯礼葬之。《孟子·万章下》:“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以子、男而从侯礼,是为加二等。《国语·鲁语上》载鲁僖公替卫成公向周天子和晋文公说情,使卫成公得到赦免,“自是晋聘于鲁,加于诸侯一等。”诸侯加等,只是礼遇上从优,其本爵则不发生改变。
其三,五等爵是确定诸侯贡赋之次的重要依据。《左传》昭公十三年:“子产争承,曰:‘昔天子班贡,轻重以列,列尊贡重,周之制也。卑而贡重者,甸服也。郑伯,男也,而使从公侯之贡,惧弗给也,敢以为请。’”子产认为,郑为伯爵,而在男服,让它承担公侯之贡,是不合理的。经过子产据理力争,郑国的负担才得以减轻。《左传》哀公十三年:“鲁赋于吴八百乘,若为子男,则将半邾以属于吴,而如邾以事晋。”按照侯爵,鲁应对吴承担八百辆兵车的贡赋,若降为子、男,贡赋也就相应地减少。
历史表明,在春秋霸政体制下,五等爵制仍发挥着一定的影响。五等爵制在春秋时代的存留是由当时的阶级结构决定的。李学勤先生说:“东周时期,社会动荡变乱,礼制规定的等级遭到冲击,出现了一定变化,列国的制度也不尽一致,不过决不能认为等级的阶梯已经彻底摧毁了。不同的等级间,常常还维持着很难逾越的界限。”[8]印群先生通过研究春秋列鼎制度,得出结论:“春秋时期列鼎数目的规范清晰地反映出当时以列鼎墓墓主为代表的贵族等级构成相当稳定。”[9]陈恩林师说:“周代社会是等级制社会,这是它最本质的特点。它的卿大夫阶层是有等的,它的贵族家庭也是有等级的”。[5]陈师所说的周代社会包括春秋。笔者补充一点,周代奴隶也是分等的。《左传》昭公七年:“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俞正燮《癸巳类稿·仆臣台义》云:“自皂以下得相役使,故曰臣曰等也。”可见,春秋社会各阶层都是由更加细密的等级构成的,卿大夫、士,甚至是奴隶都分等,列国诸侯不会没有等级。这个等级就是五等爵:公、侯、伯、子、男。
五等爵制在春秋时期的存留,还离不开另外两个重要因素。一是王权的存在。春秋是“政由方伯”的时代,然而“周德虽衰,天命未改”,[10](宣公三年)周天子作为天下共主,在政治上仍发挥着重要的影响。霸主利用代表周室秩序的五等爵制规范诸侯关系,既能赚取“尊王”的政治资本,又能减少诸侯的反对,可谓一举两得。例如,吴本伯爵,春秋时吴君自称王,在黄池大会前,晋国利用吴君“欲守吾先君班爵”的诺言,折辩吴君说:“今君掩王东海,以淫名闻于天子,君有短垣,而自逾之,况蛮、荆则何有于周室?夫命圭有命,固曰吴伯,不曰吴王。诸侯是以敢辞。夫诸侯无二君,而周无二王,君若无卑天子,以干其不祥,而曰吴公,孤敢不顺从君命长弟!”[11](昊语)吴王同意改称吴公。晋国正是利用五等爵制,成功地使吴君放弃了王号,取得了外交上的一次胜利。二是等级名分观念的影响。春秋时期,人们极重视等级名分。《左传》庄公十八年:“不以礼假人。”《左传》成公二年载:“卫人赏之(仲叔于奚)以邑,辞,请曲县繁缨以朝。许之。”孔子听说此事,评论道:“惜也,不如多与之邑。唯器与名,不可以假人。”可见当时人们对等级名分的要求甚至超过了对土地的看重。五等爵制的存留,与春秋时期尊崇等级名分的社会舆论亦有着密切的关系。
二、五等爵制的破坏
五等爵制是分封制下的诸侯等级制。春秋时期,随着分封制走向衰落,五等爵制也遭到了破坏。
周代的礼,包括“仪”和“礼”两个方面,“仪”是形式,“礼”是实质。[12](P150-151)作为一种重要的礼制,五等爵制也是如此,与之相关的各种礼仪是其外在形式,它所具有的政治功能则属其内在本质。以下即从这两个方面来分析春秋五等爵制破坏的情形。
先看五等爵的礼仪形式。礼书中保存了五等诸侯的若干礼仪。《仪礼·觐礼》:“上介皆奉其君之旗置于宫。公侯伯子男皆就其旗而立。”是为诸侯朝聘天子时依爵而设的不同礼位;《周礼·大宗伯》,“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国:王执镇圭,公执桓圭,侯执信圭,伯执躬圭,子执谷圭,男执蒲圭。”是可见诸侯命圭依爵有别;《周礼·典命》:“典命掌诸侯之五仪……上公九命为伯,其国家、宫室、车旗、衣服、礼仪皆以九为节;侯伯七命,其国家、宫室、车旗、衣服、礼仪皆以七为节;子男五命,其国家、宫室、车旗、衣服、礼仪皆以五为节。”是为五等诸侯在宫室、车旗、衣服、礼仪等方面的差别。春秋时期,列国在遵行五等爵旧礼的同时,有时出于外交需要,也有所变通。如上文所举,周惠王对虢公、晋侯同赐无别,提高了晋侯的地位,惠王为了讨好强晋而并不拘泥于旧礼;鲁以周班后郑,引起了郑国的不满,可见有些诸侯也试图突破礼仪的限制,抬高自己的身份。有些诸侯国,对五等诸侯旧礼已不太了解。《左传》昭公四年载楚灵王会盟诸侯,宋国向戍“献公合诸侯之礼六”,郑国子产“献伯、子、男会公之礼六”,楚灵王“使椒举侍于后,以规过。卒事,不规。王问其故,对曰:‘礼,吾所未见者有六焉,又何以规?’”可见,春秋时期,即使与五等爵相关的礼仪形式,也往往被破坏或忽略。
再看五等爵制的政治功能。春秋五等爵制的破坏,集中表现为“礼”与“仪”的分离,五等爵制徒有外在的礼仪形式,而其原有的政治功能则丧失殆尽。
五等爵制的功能之一,是用等列诸侯的方式来加强天子的权力,即“等级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13](阶级)而这一功能的实现,是以天子强大的政治、经济、军事实力为保证的。诸侯若有非分之举,天子有能力予以惩罚。《国语·周语上》:“于是乎有刑不祭,伐不祀,征不享,让不恭,告不王。”《孟子·告子下》:“一不朝,则贬其爵;再不朝,则削其地;三不朝,则六师移之。”春秋时期,天子衰微,无力阻止诸侯的僭越,五等爵制的维护权转到了霸主手中。前632年,周襄王应晋文公之召往温会见诸侯,明知“臣而召君”不合周礼,为了得到晋霸的支持,只好屈尊前往。《左传》十五年载,晋国使臣参加周景王王后的葬礼,没有贡献器物,周景王责备他“数典而忘其祖”,晋人反过来指责周王“非礼”。两个事例真实反映了天子的虚弱。在此种情势下,周天子欲通过五等爵,凌驾于等级制秩序的顶峰,根本是无法实现的。
五等爵制的另一个功能是利用爵制规定诸侯的权力与义务,从而将诸侯纳入等级的秩序中,限制其过分的发展。西周封邦建国,各国封土大小、军队规模要与其爵秩保持一致。《左传》襄公二十五年:“且昔天子之地一圻,列国一同,自是以衰。”《孟子·万章下》:“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礼记·王制》:“天子之田方千里,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春秋时期,列国开始大肆扩张领土。《左传》成公八年,申公巫臣曰:“夫狡焉思启封疆以利社稷者,何国蔑有?唯然,故多大国矣。”《左传》襄公二十五年:“今大国多数圻矣,若无侵小,何以至焉?”天子对诸侯的辟土扩张也无可奈何。在周初,爵秩是诸侯制军作赋的根据。《国语·鲁语上》:“天子作师,公帅之,以征不德。元侯作师,卿帅之,以承天子。诸侯有卿无军,帅教卫以赞元侯。自伯、子、男有大夫无卿,帅赋以从诸侯。”何休《公羊传》隐公五年注云:“天子六师,方伯二师,诸侯一师。”陈恩林师认为:《国语·鲁语上》和何休注记载的是西周初期的军事制度,在周初,公爵诸侯可组建三师,元侯(方伯)可组建二师,诸侯(一般侯爵诸侯)拥有一师,伯子男不能组建独立的军队,遇有征战则出兵车、甲士以从大国诸侯。[14](P64-67)西周晚期,军事制度演变为“王六军,大国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14](P79)春秋时期,诸侯国不论大小,爵不论高低都积极扩军。列国普遍建立起了三军,有些大国甚至建立四军、五军、六军。[14](P106-107)由此可见,春秋时期五等爵制对诸侯国的约束作用已十分有限。
春秋时期,随着五等爵制约束力的丧失,一些诸侯国跳出了五等爵之外,自称为王,如楚、吴、越等。中原各国表面上虽维护五等爵制,但它们也不再以五等爵秩而是以实力来论大小强弱。《左传》成公三年:“晋侯使荀庚来聘,且寻盟。卫侯使孙良夫来聘,且寻盟。公问诸臧宣叔曰:‘中行伯之于晋也,其位在三。孙子之于卫也,位为上卿,将谁先?’对曰:‘次国之上卿当大国之中,中当其下,下当其上大夫。小国之上卿当大国之下卿,中当其上大夫,下当其下大夫。上下如是,古之制也。卫在晋,不得为次国。晋为盟主,其将先之。’”依爵,晋、卫皆为侯;依国家实力,晋是霸主,卫乃小国,故卫国使者虽为上卿,晋国使者位在第三,仍以晋国使者为先。臧宣叔所讲的邦交原则,是以国家的实力为依据的,与五等爵制的原则绝不相同。《左传》哀公十三年:“吴、晋争先。吴人曰:‘于周室,我为长。’晋人曰:‘于姬姓,我为伯。’”吴、晋争盟,完全是实力的较量。宋尊为公爵,春秋时却沦为二、三流的国家,又处于晋、楚之间,所以在春秋时饱受欺凌。鲁和齐同为侯爵,鲁终因国力不济,在与齐的交往中居于下风。因此,五等爵制在春秋虽发挥着一定的影响,但诸侯的大小强弱却是由实力决定的。根据实力,春秋列国可分为霸主、大国、次国、小国和附庸等。《左传》襄公四年载,鲁襄公请晋侯同意以鄫为鲁之附庸,晋侯不许。孟献子曰:“以寡君之密迩于仇雠,而愿固事君,无失官命。鄫无赋于司马,为执事朝夕之命敝邑,敝邑褊小,阙而为罪,寡君是以愿借助焉!”可见,春秋诸侯国关系的实质是:大国剥削小国,小国又剥削更小之国。
霸主对五等爵的维护,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利用五等爵制规定的贡赋原则,加重对列国的剥削。上面所举“子产争承”的例子足以为证。为了减轻贡赋,春秋时期一些国家甚至自贬其爵,甘居附庸地位。[5]《左传》襄公二十七年载,晋、楚在宋召开弭兵大会,邾、滕为摆脱向晋、楚纳贡的负担,甘心成为齐、宋的附庸。此会之前,鲁正卿季武子以国君名义命与会的叔孙豹曰“视邾、滕”,要求把鲁降为邾、滕那样的附庸国。鲁国“犹秉周礼”,在沉重的负担之下,竟欲自贬其爵,屈尊于附庸的地位,霸主盘剥之烈,可想而知。所幸叔孙豹不堪此辱,曰:“邾、滕,人之私也;我,列国也,何故视之?宋、卫,吾匹也。”拒绝执行君命,这才使鲁国保住了原来的爵秩,没有沦落为附庸国。可见,春秋五等爵制已由天子之器演变为霸主的工具了。
五等爵制是周代分封制下的诸侯等级制。西周时期,五等爵制对于建立贵族政治秩序、确立诸侯的权利和义务、维护天子的独尊地位,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春秋时期,由于以分封制为基础的阶级结构尚未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加上王权的存在和等级名分观念的影响,五等爵制依然存留,并对列国的外交活动发生着一定的影响。然而,这种影响是很有限的。春秋时期的五等爵,更多地表现为一种外交礼仪,而丧失了其原有的政治功能。到了战国,随着分封制被郡县制所代替,五等爵制也正式退出了历史舞台。所以,对于周室的班爵,战国时期的人们已经不很清楚,即便是孟子,也只能“闻其大略”了。[15](万章下)
收稿日期:2006-05-10
注释:
①傅斯年:《论所谓五等爵》,《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二本,中华书局1987年影印本。郭沫若:《周代彝铭中无五服五等之制》,《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杨树达《古爵名无定称说》,《积微居小学述林》卷六,中华书局,1983年版。
②关于诸侯称呼的复杂情形,可参见瞿同祖:《中国封建社会》,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葛志毅:《周代分封制度》,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陈恩林:《先秦两汉文献中所见周代诸侯五等爵》,《历史研究》1994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