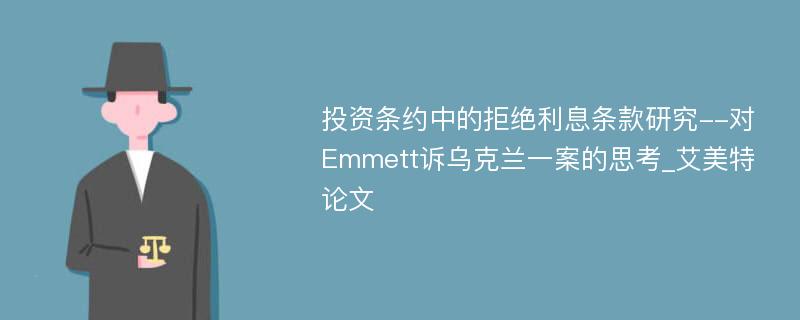
投资条约中的利益否决条款研究——由“艾美特公司诉乌克兰案”引发的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乌克兰论文,条约论文,条款论文,利益论文,艾美特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问题的提出:“艾美特公司诉乌克兰案”①
由俄罗斯公民控制的拉脱维亚投资公司——艾美特公司——自1999年即开始在乌克兰的核能源领域进行投资,至2003年年底其共购买在乌克兰注册成立的扎尤梅公司67%的资本股。扎尤梅公司是乌克兰最大核电站扎尔斯公司的服务提供商,艾美特公司与扎尤梅公司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使艾美特公司成为扎尔斯公司的主要债权人。2002年,扎尔斯公司遇到财务危机,无法偿还债务,加之乌克兰政府分别于2003年和2005年颁布了关于能源公司的相关法令,从而使得扎尤梅公司一直无法从扎尔斯公司获得赔偿,于是艾美特公司提出仲裁申请,主张被申请人乌克兰政府违反《能源宪章条约》(ECT)第10条的相关规定,不仅没有给予外国投资者公平公正待遇而且采取了歧视性措施等,要求获得赔偿以及其他救济(即“艾美特公司诉乌克兰案”,以下简称“艾美特公司案”)。在该案中,已经是ECT成员国的乌克兰政府认为,由于艾美特公司实际上由非ECT成员国俄罗斯的公民控制并且在名义上的母国拉脱维亚境内并没有从事实质性商业行为,因此乌克兰作为东道国有权以ECT第17条利益否决条款作为抗辩理由,拒绝给予艾美特公司以ECT第三部分赋予的各项保护。该案仲裁庭经过审理认为,虽然艾美特公司的最终控制人是俄罗斯公民,但它已经在拉脱维亚从事实质性商业行为,乌克兰政府没有权利否决艾美特公司应当享有的条约利益。
“艾美特公司案”涉及ECT第17条规定的利益否决条款。作为投资条约,ECT在赋予投资者在能源领域的各项权利的同时,也将某些具有特殊身份的投资者排除在外。一般而言,根据投资条约,一成员国境内成立的公司在另一成员国境内投资时享受投资条约提供给投资者的优惠待遇或保护,然而有些公司的真正所有者或控制者实际上并非投资条约的成员国国民,这些所有者或控制者往往利用在一成员国境内成立的“邮箱公司”向其他成员国投资,“骗取”条约保护。②这种“条约选购”行为在国际投资实践中屡见不鲜,特别是在能源等重要领域,由于投资周期长、资本密集度高和行业敏感等特点,东道国以相关投资条约赋予其的利益否决权作为抗辩理由的几率也随之增大。ECT框架下发生的多起由利益否决条款引发的纠纷案即为适例。投资条约中的利益否决条款被视为防止“条约选购”或“免费搭车”的保护条款,是抵制投资者利用“国籍策略”的有效手段。③许多投资者出于投资便利的需要,往往选择利用“邮箱公司”向其他国家进行投资,从而也使得利益否决条款的适用不再仅限于能源领域。利益否决条款虽然是一条旨在防止投资者“选购条约”或“免费搭车”的条款,但在实践中,国际投资仲裁庭却往往做出对投资者有利的裁决,使该条款无法实现其功能,不能达成东道国保护与投资者保护的平衡。基于我国目前的资本输入和输出现状,我们很有必要对投资条约中的利益否决条款进行深入研究,并结合相关的国际投资仲裁实践,揭示该条款的适用趋势,以期对我国的相关缔约活动有所裨益。
二、利益否决条款的缘起:基于投资条约的考察
投资条约中的利益否决条款是为了使东道国能够有效地拒绝给予在另一成员国境内仅仅以控股公司形式存在的、没有从事实质性商业行为的投资者以条约利益而设置的。④利益否决条款最早出现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下简称二战)后的美国投资条约中,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国友好经济关系条约便赋予了东道国利益否决权,此后美国几乎在所有的友好通商航海条约(FCN)、双边投资条约(BIT)以及多边投资条约中都规定了利益否决条款,⑤只不过早期投资条约中的利益否决权并没有以独立条款的形式存在。美国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在BIT中制定单独的利益否决条款,如1985年的《美国-摩洛哥BIT》和《美国-土耳其BIT》都专门制定了该项条款。此后,1994年、2004年和2012年的《美国BIT范本》也都制定了利益否决条款。例如,2012年《美国BIT范本》第17条规定:“……如果投资是由第三国或者缔约一方的私人拥有或控制的法人进行的,且该法人在另一缔约方境内未从事实质性商业行为,那么缔约一方有权拒绝将条约利益授予缔约另一方的法人”。在美式BIT的影响下,一些多边投资条约如《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ECT也制定了利益否决条款。例如,ECT第17条规定:“每一个缔约方保留否认本部分利益的权利:一个法律实体如果被第三国的居民或国民拥有或控制,并且该实体在所成立的缔约方境内没有从事实质性商业行为……”通过上述规定,我们不难发现,多边投资条约和BIT中的利益否决条款存在细微差别,前者的利益否决条款并没有排除东道国投资者的权利,只要最终的控制者或所有者并非来自第三国便可;而BIT中东道国否决的对象既包括第三国的投资者,也包括本国的投资者。也就是说,B1T成员国行使否决权的对象更多,对于本国投资者的“条约选购”行为也一并予以排除。
以保护投资者和促进国际投资自由为宗旨的投资条约将以保护东道国利益为宗旨的利益否决条款纳入其中有着深刻的动因。具体而言:(1)从经济背景来说,虽然美国在二战之后已经跃居世界第一资本输出国,但对于外来资本的流入仍然非常警惕。美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力图降低外国投资可能带来的危险,利益否决条款便是其中之一。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欧盟、日本、中国、韩国、巴西、墨西哥以及一些产油国开始大规模地增加对外投资,⑥美国将不得不接受越来越多的海外投资和跨国公司,行使利益否决权的可能性也随之增加,因此单独的利益否决条款在投资条约中频繁出现。现今的国际社会没有纯粹的资本输出国,很多国家都逐渐向资本输出国和资本输入国的混合身份转变,出于保护国家安全和经济利益的目的,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接受利益否决条款,瑞典、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家也在相关投资条约中设立了利益否决条款。(2)从条约本身看,投资条约的基本任务之一便是决定投资者与条约成员国之间的关联程度,进而确定受条约保护的投资者范围。如果条约允许非成员国私人获得利益,那么就意味着成员国放弃了与其他国家对等协商的权利。⑦“巴塞罗那公司案”⑧确立下来的习惯国际法规则是根据成立地/注册地标准确定公司国籍,这种方法虽然稳定、方便并且易于判断,但也为老练、世故的投资者提供了“骗取”更优惠条约保护的机会。一国选择与某一个或者某几个国家签订投资条约,意味着该国希望在彼此之间给予某些特殊的利益,但这种利益并不是普遍适用于所有国家的。只有使真正的成员国投资者获得条约利益和保护,才能够吸引更多的国家加入到条约体系中来。然而“条约选购”或者“免费搭车”现象在国际投资领域屡见不鲜,如果不设法加以阻止,那么将会对国际投资市场的发展和国际投资体系的构建造成严重的甚至是致命性的影响。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很多投资条约的起草者将利益否决条款作为公司国籍的补充或者例外订入投资条约之中。⑨既然利益否决条款被视为公司国籍的补充或例外,为何要以单独条款的形式存在,而不是在投资者定义部分进行约定呢?笔者认为这主要是由两个原因造成的:一是“目前的投资条约对于合格投资者的界定非常宽泛,即便有所限制,在最惠国待遇的作用下,这种限制也很有可能被抵消”。⑩而独立的利益否决条款既可以在宽泛含义的基础上排除某类投资者,也可以防止最惠国待遇对于国籍限制作用的冲击。二是利益否决条款给予东道国选择是否行使否决权的自由。也就是说,即便满足了相关条件,东道国也可以不行使否决权,这与投资者定义的普遍适用是不同的,因此将其单独列出更为妥当。
利益否决条款是一个潜在的保护条款,目的是让东道国在关键时刻有能力维护自己的权益。它既可以避免国籍标准的固定性,也能够增加非成员国融入国际投资体系的动力;既能够维持成员国之间权利义务的平衡,也有利于实现东道国与投资者之间权利义务的平衡。在美国的影响和推动下,利益否决条款已经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所接受,并且以不同的表述方式在投资条约中普遍存在。然而,国际投资仲裁实践并没有实现利益否决条款的上述目的和价值,而是以不符合相关要素为由否认东道国的这项权利,使得利益否决条款的适用陷入困境。
三、利益否决条款的适用:基于国际投资仲裁实践的考察
真正引发理论界和实务界对利益否决条款热烈讨论的是4起涉及ECT利益否决条款的案件,即“帕拉马公司诉保加利亚案”(11)(以下简称“帕拉马公司案”)、“柏卓巴特公司诉吉尔吉斯斯坦案”(12)(以下简称“柏卓巴特公司案”)、“艾美特公司案”以及“尤科斯公司诉俄罗斯案”(13)(以下简称“尤科斯公司案”)。从这4个案件的裁决看,争议的焦点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利益否决条款适用的可仲裁性、行使否决权的构成要件和举证责任。实际上这几个争议点也是利益否决条款适用的关键要素,以下笔者将结合相关案例,针对这三个问题逐一讨论,以揭示该条款的适用趋势。
(一)可仲裁性
目前各种投资条约仅对适用利益否决条款的可能性作出了规定,而对这一条款的启动是否影响仲裁庭的管辖权问题没有作出规定。例如,一方面ECT第17条允许成员国保留否认投资者享有该条约第三部分利益的权利,另一方面ECT第26条又明确规定争端解决机制仅处理违反ECT第三部分义务的争议。对ECT成员国而言,既然给予其否决ECT第三部分利益的权利,那么其在行使否决权时,仲裁庭便没有管辖权。例如,在“帕拉马公司案”中,被申请人保加利亚即主张根据ECT第17条行使的利益否决权并不具有可仲裁性。该案仲裁庭根据《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1条第1款进行解释,认为应该从整体上把握条约用语,ECT第26条为投资者的诉求提供程序性救济并不是ECT第三部分中投资者享有的实质性利益,ECT为其第三部分规定了一定的免责理由,但这种免责需要满足特定条件才可以实现。该案仲裁庭根据条约目的和宗旨,裁定东道国的利益否决权并不影响ECT第26条规定的争端解决机制的适用;并强调由于判断公司国籍、商业行为所在地等问题的艰难性,如果投资者不能获得ECT第26条规定的救济,那么意味着提出适用ECT第17条的成员国成为自己案件的仲裁员,将涉案的投资者视为完全不受ETC保护的对象,这是极不公平的。在“艾美特公司案”中,乌克兰认为ECT第26条第1款赋予投资者将关于国家“义务”的法律争议提交仲裁的权利,但ECT第17条涉及的仅仅是一国的权利,而非义务,因此仲裁庭对此没有管辖权。该案仲裁庭驳回了乌克兰的主张,认为一国可以主张权利、权力、特权或豁免来拒绝、取消或者回避某项义务,但对这种行为的描述并不能将申请人的主张与违反“义务”的事实区别开来,东道国利益否决权的行使实际上是对义务的描述,因此也属于仲裁庭的管辖范围。“尤科斯公司案”仲裁庭认为:“投资条约中的争端解决机制是赋予投资者的一种保护手段,如果没有争端解决条款中的救济方式,投资者的很多权利无法产生预期效果。”“西门子公司诉阿根廷案”(14)仲裁庭也指出:“进入争端解决机制的权利是条约提供保护的一部分,也是给予外国投资者待遇的一部分。”因此,“仲裁庭不能因为利益否决条款而否定投资者应该获得的实质性保护”。(15)由此可见,仲裁庭对利益否决条款的适用是否影响仲裁庭的管辖权问题所持态度是一致的,即仲裁庭并不因为利益否决条款而否定投资者应该获得的实质性保护。
(二)适用条件
国际投资仲裁庭普遍认为东道国行使利益否决权必须满足三个条件:法律实体为非成员国私人所有或控制;法律实体没有在其名义上的国籍国从事实质性的商业行为;东道国行使利益否决权之前必须进行合理通知。但是,仲裁庭对各要件的具体内容并没有作出具体、明确的界定。
在投资领域,关于控制标准的争议由来已久。按理说仲裁庭对东道国行使利益否决权的第一个条件即由非成员国私人所有或控制的认定应该存在很多争议,但有趣的是,实践中并不存在这一问题。各仲裁庭对这一要素的判断没有出现任何分歧或者不确定性,在他们看来,“所有”、“控制”是可替代的关系,只要满足其中之一便可。“所有”也包括间接所有和对收益权的所有,拥有超过50%的表决权资本便属于“所有”;而“控制”既包括法律上的控制,也包括事实上的控制,如对法律实体的管理、运营、董事会或其他管理机构人员的任命能够发挥实质性影响的能力。
东道国行使利益否决权的第二个条件即投资者在公司成立地没有从事实质性商业行为更具有现实意义。根据字面含义理解,实质性商业行为应该超出法律要求的通常的表面行为,如交税、召开股东会议等,也应远远高于东道国法律规定的最低程度的商业行为。但是,到目前为止,并没有任何条约对这一要素进行深入说明,我们无法将真正的、实质性的与非真正的、非实质性的商业行为进行明确的区分。在“泛美能源公司和BP阿根廷勘探公司诉阿根廷案”(16)中,BP阿根廷勘探公司的年度报告记载公司共雇佣37000名员工,并在50个国家成立营业所,仲裁庭便据此裁定BP阿根廷勘探公司在东道国从事了实质性的商业行为。“帕拉马公司案”的申请人承认自己并没有在成立地塞浦路斯从事过重大的商业行为,仲裁庭便在其裁决中认为申请人没有从事实质性商业行为是很明显的,但仍然没有具体说明得出这一结论的理由。“托克欧斯·托克勒斯公司诉乌克兰案”(17)的仲裁庭认为,申请人提供的1991-1994年的财政报表、雇用信息和生产加工记录表明其在立陶宛的活动构成了实质性商业行为。“艾美特公司案”的仲裁庭认为成立营业所、缴纳税款以及雇佣员工足以构成实质性商业行为。“柏卓巴特公司案”的仲裁庭对这一问题也没有进行深入细致的讨论,只是特别考虑到了商业行为的目的,并基于柏卓巴特公司的商业行为的目的而认定其从事了实质性商业行为。在“尤科斯公司案”中,仲裁庭因申请人承认自己并没有从事实质性商业行为而提出无须对此问题进行分析。可见,“我们无法从过去的案例中推导出统一、连贯的适用标准,一家公司是否从事了实质性的商业行为只能因具体案件而异”。(18)但可以肯定的是,仲裁庭认定实质性商业行为的标准很低,并没有要求投资者在东道国从事大规模或者深入的经营,因此东道国的利益否决权不被认可的可能性增加。
关于东道国行使利益否决权的合理通知问题,“帕拉马公司案”的申请人主张利益否决条款是自动适用的,不需要东道国采取进一步的行动。但是,该案仲裁庭认为权利的存在和权利的行使不同,ECT成员国拥有ECT第17条规定的否决某类投资者条约利益的权利,但并不必然行使这项权利,因此该利益否决条款并不是自动适用的。“艾美特公司案”的仲裁庭持相同的观点,认为由于乌克兰没有给予投资者合理通知,因此不能援用利益否决条款。“柏卓巴特公司案”的仲裁庭也认为吉尔吉斯斯坦在仲裁程序开始前和开始后都没有援引ECT第17条,而是在仲裁程序的后期才提出,具有阻碍仲裁程序的非法动机,因此其无权否决柏卓巴特公司的条约利益。关于通知的时间问题,各案的裁决则有所不同,“帕拉马公司案”和“柏卓巴特公司案”的仲裁庭认为东道国应该在投资者投资之前便通知他们是否能够获得条约利益,一旦投资者进入东道国,该国便无权拒绝给予投资者条约利益。但是,“艾美特公司案”仲裁庭则认为,投资者可以在任何时间行使这项权利。“尤科斯公司案”的仲裁庭认为,根据ECT“保护和促进投资”的宗旨和目的,东道国的利益否决权以通知申请人为前提条件,但其并没有强制要求通知的时间。笔者认为,每一位投资者都有申请仲裁的权利,但可能并不会行使这项权利,这与东道国行使利益否决权的情况相似。如果要求东道国在投资者进入东道国之前便通知其是否会行使利益否决权,那么意味着投资者在此时也应该告知东道国其是否会提出仲裁申请。既然后一种情况是不可能实现的,那么在时间上对东道国的苛刻要求也是不合理的。
(三)举证责任
举证责任问题在利益否决条款的适用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帕拉马公司案”中,申请人帕拉马公司主张保加利亚必须证明其能够援引ECT第17条,而保加利亚则认为申请人有责任证明其所有权和控制权从来没有掌握在第三国私人手中。该案仲裁庭没有明确解释举证责任问题,只是在裁决实体要件时提及申请人由ECT成员国私人所有或控制的举证责任应该由申请人一方承担。那么,是否可以由此推断申请人由非ECT成员国所有或控制的举证责任由被申请人承担呢?“柏卓巴特公司案”仲裁庭貌似对这一问题作出了肯定的回答,其裁定ECT第17条是为ECT第三部分的条约义务提供的具体例外,必须由被申请人证明法律实体被第三国私人所有或控制的事实及实质性商业行为的缺失。“艾美特公司案”被申请人乌克兰主张申请人有责任证明自己没有被第三国私人所有或控制,或者在拉脱维亚从事了实质性商业行为。该案仲裁庭认为,虽然ECT第17条对举证责任问题的规定非常模糊,但根据国际仲裁“谁主张谁举证”的证据规则,申请人应该证明其满足条约中“投资者”的条件并享受条约利益,这其中包括证明其直接或间接的控制权到底归谁所有。但是,《关于〈能源宪章条约〉第1条第6款的谅解》规定,如果争议双方对投资者直接或间接控制投资的问题存在争议,那么主张拥有控制权的东道国应该证明控制的存在。因此,“尤科斯公司案”仲裁庭根据这一规则推定,当被申请人主张申请人仅仅属于享受可撤销条约利益的投资者时,举证责任便转移到被申请人,也就是说东道国必须证明其具备适用ECT第17条的必备要件。(19)关于行使利益否决权的举证责任不能简单地套用国际仲裁的一般证据规则,对东道国来说,证明某公司没有从事实质性商业行为已经很困难,证明一个私人实体在外国管辖权下没有从事实质性商业行为更足难上加难。如果将举证责任完全强加给东道国,那么未免有失偏颇。当然,有些仲裁庭已经意识到要求东道国证明他国公司的规模、价值和重要性等问题的难度,因此对举证责任采用相对灵活的解决方式。例如,有的仲裁庭认为可以通过其他途径增加申请人的信息披露义务,如果披露的信息是难以理解的,那么仲裁庭有权要求申请人予以澄清;如果申请人没有提供相关信息,那么仲裁庭可以对他作出不利推定。(20)也就是说,被申请人可以利用证据的稀缺性和模糊性强迫申请人补充信息。
通过上述仲裁实践可知,利益否决条款本应是防止投资者根据“国籍策略”进行“条约选购”的有效手段,(21)但仲裁庭过于偏袒投资者的解释将这一权利置于形同虚设的尴尬境地。笔者认为,既然是赋予东道国的权利,那么它的最初动机应该是侧重于保护东道国的利益,而且东道国拒绝给予投资者本不该享有的条约利益也是无可厚非的;为了准确地体现条约成员国的意愿,最直接的办法就是将条文内容详细化、标准化。
四、我国的缔约选择
越来越多的国家对利益否决条款的认可和接受表明各国希望它能够发挥预期效果。(22)除了《中国—墨西哥BIT》和《中国—东盟投资协定》,我国在目前已经生效的投资条约中都没有制定利益否决条款。在已经成为资本输入大国的情况下,我国在未来的投资条约中是否应该设立利益否决条款呢?如果设立利益否决条款,那么又应该如何安排该条款的规定呢?以下笔者将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对这些问题作出回答,以期为我国的相关缔约实践提供有益的建议。
(一)利益否决条款的选择
利益否决条款可以减少国籍标准固定化带来的负面影响,防止“条约选购”、“免费搭车”以及国际商业透明度缺失等问题,对保护东道国的利益、保护公平的竞争环境等都具有重要意义。(23)可以说,利益否决条款数量的多少直接反映一国制定投资条约的水平,表现一国对自我状况的认知程度及谈判能力。遗憾的是,我国并没有意识到利益否决条款的重要性。总体而言,我国在条约实践中对投资者的界定是比较宽泛的。截至2012年,我国签订的绝大多数BIT采用成立地/注册地标准、管理地/经营地标准或者将两者相结合的复合标准。这种做法与美国的投资条约实践颇为相似,但不同的是,我国绝大多数投资条约都没有单独设立利益否决条款,这为非成员国私人进行“条约选购”或“免费搭车”提供了便利。如前所述,虽然很多欧洲国家的BIT也没有制订利益否决条款,但因他们将“控制说”作为公司国籍的判断标准,所以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将“邮箱公司”排除在外。但是,笔者认为美国的做法更值得借鉴,理由如下:(1)作为资本输入国,利益否决条款可以限制我国资产外流的数量,引导投资流向;作为资本输出国,它又能够防止非成员国公司对我国的经济“扩张”。因此,不论以哪种身份存在,利益否决条款的作用都不可忽视。当然,作为赋予东道国的一项权利,利益否决条款更侧重于对东道国的保护,而我国目前也正是以资本输入国的身份为主,设立利益否决条款更是大有裨益。(2)利益否决权的行使并不具有强制性,东道国可以对是否否决特定投资者的条约利益进行选择,当东道国处于困境时完全有权根据利益否决条款拒绝给予某些投资者条约利益以减少国家损失。我国目前正处在经济转型时期,经济的稳定性还有待进一步加强,因此很难保证实践中不会出现较大的经济波动。为了促进经济的稳定和发展,对某类投资者的利益进行否决是在所难免的。(3)控制标准在实践中难以把握,国际社会对控制标准的相关要素存在很多争议;并且仲裁庭倾向于采用成立地/注册地标准,(24)通常不会单独适用控制标准,而仅仅是将其作为认可公司与东道国之间存在经济联系的证明,甚至直接忽略控制因素。(25)“有仲裁庭认为,控制标准在很多情况下是用来扩大投资的范围,而非限制投资者的范围”。(26)因此,单独的控制标准并不能够达到利益否决条款的效果,我国政府只有设立单独的利益否决条款才能真正排除那些通过“条约选购”骗取条约保护的投资者。
需要注意的是,我国商务部于2010年4月草拟的《中国投资保护条约范本》第1条第2款在对投资者含义进行界定时,明确指出法人实体必须“依照缔约国法律组成或组织”并且“在其领土范围内从事实质性商业经营”,由此《中国投资保护条约范本》已经借鉴了美式BIT中“实质性商业行为”的概念,将管理或经营的含义进一步深化,遗憾的是其并没有设立单独的利益否决条款。2012年8月9日,祖国大陆与台湾地区签署了《海峡两岸投资保护和促进协定》。虽然该协定并未生效,但可以肯定的是,各缔约方都将承诺给予投资者以更多的优惠待遇。根据《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的实施经验,海峡两岸相互给予的投资保护将超过其他的投资条约,这又为“条约选购”提供了充足的“动力”和条件。令人欣慰的是,根据目前掌握的资料,《海峡两岸投资保护和促进协定》第11条专门设立了单独的利益否决条款。虽然这一条款略显粗糙,但它是我国在条约实践方面的巨大进步。通过利益否决条款,两岸可以防止其他国家的投资者利用《海峡两岸投资保护和促进协定》,通过在一方成立“邮箱公司”的形式向另一方投资,获得高水平的投资保护。此外,我国正在与美国进行BIT谈判,而美国签订的所有投资条约都单独设立了利益否决条款,美国很有可能在未来的中美BIT中也作此要求。因此,我国在未来的投资条约中应该接受利益否决条款。对于尚未加入但非常重要的投资条约,我国也应该在寻求国际合作的同时,力争获得高标准的条约利益。ECT是关于能源投资领域的第一个也是唯一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多边条约,能源问题已经成为投资领域最引人瞩目的焦点之一,在这种背景下,拥有50多个成员国的ECT对国际能源市场将产生重大的影响。虽然我国还不是ECT的成员国,但如果能够获得ECT的保护,对我国海外能源投资将是极大的鼓舞。然而,我国在考虑是否加入ECT的问题时还必须考虑如何应对东道国的利益否决权。虽然仲裁庭的解释倾向于保护投资者,但投资者仅仅通过简单的“条约选购”或者在ECT成员国设立“邮箱公司”是难以获得条约利益的。笔者认为,我国的能源投资者可以考虑在ECT成员国境内设立从事实质性商业行为的公司,然后再向其他ECT成员国进行投资,这既避免了东道国主张行使否决权的可能性,也能获得高标准的条约保护。总之,不论是作为成员国还是作为第三国,了解、接受或在未来的投资条约中设立利益否决条款,都将是我国政府必须面对的问题。
(二)利益否决条款的设立
2008年生效的《中国-墨西哥BIT》第31条规定:“缔约双方可以共同磋商决定拒绝将本条约之利益授予缔约另一方之企业及其投资,如果该企业系由非缔约方之自然人或企业所有或控制。”通过这一条规定,我们不难发现《中国-墨西哥BIT》中的利益否决条款采用的是美国早期的做法,完全排除由第三国私人所有或控制的法律实体,这样使公开交易股份的公司面临巨大风险。除此之外,我们还必须考虑的是,条约规定缔约双方“可以”而不是“应该”共同磋商,这是否意味着磋商与否并不影响利益否决权的行使呢?再看2010年生效的《中国-东盟投资协定》,该协定第15条专门规定了利益否决条款:“如果投资是由非缔约方的私人所有或控制的法人进行的,且该法人在另一方境内未从事实质性商业行为;或者如果该投资是由拒绝给予利益一方的私人拥有或控制的法人进行的”,经事前通知及磋商,一方可拒绝将协定的利益给予另一方投资者。通过这条规定,我们又可以发现以下两个事实:(1)与其他多边投资条约相似,《中国-东盟投资协定》中的利益否决条款既排除了非缔约方投资者,也排除了东道国投资者享受条约利益;(2)《中国-东盟投资协定》虽然规定将“实质性商业行为”和“事前通知及磋商”作为行使否决权的构成要件,但并未对具体的判断标准作明确的规定,这仍然相当于将决定权转交给仲裁庭。虽然我国尚未发生涉及利益否决条款方面的争议案件,但通过前文对仲裁实践的研究可以发现,当条文规定不明确时,仲裁庭一般是根据“条约的目的和宗旨”来解释条文含义的。由于投资条约的目的几乎都是促进资本的自由流动和保护外国投资,因此这种解释方式不可避免地倾向于对投资者的保护。为了有效防止投资者的“条约选购”、避免仲裁庭的任意解释、体现缔约方的真正意图,笔者认为我国未来设立的利益否决条款应该主要从三个方面加以明确:
1.明确“实质性商业行为”的判断标准。由于国际投资仲裁庭到目前为止对“所有和控制”的裁定标准几乎是一致的,因此我国未来签订的投资条约应将落脚点放在“实质性商业行为”上。在“实质性商业行为”没有具体标准的情况下,善意的投资者很有可能一直认为自己享有条约利益,一旦遭到东道国的否认,必然产生争议。因此,如果能对“实质性商业行为”进行具体、明确的约定,那么善意的投资者在进入东道国时就可以知道自己的投资行为是否能够满足“实质性商业行为”的要求。笔者认为,我国可以在条约中明确列举几种“实质性商业行为”的标准,如税务清单、银行的日结账单、与员工的长期雇佣关系等都可以成为“实质性商业行为”的有力证据。与此同时,采用否定式非穷尽性列举的方式进行排除,如规定缔约国的公司在另一缔约国境内的营运资本低于一定百分比,或者运营时间不满一定期限的不属于“实质性商业行为”,等等。
2.明确“通知”的标准。是否援用利益否决条款取决于东道国的态度,如果东道国希望创造一种广泛接受投资的氛围,那么就不会援用该条款,反之则会援用。这将使投资者处于非常被动的境地,因为他们没有办法确定东道国到底是否会否决以及何时否决他们享有的条约利益。笔者认为,可以从两个方面改善这种状况。一方面在投资者进行投资时,允许他们在信息充分披露的情况下询问东道国的态度并为此进行专门的程序安排,如果东道国承认其条约利益或者在约定的时间内没有答复,那么发生纠纷时则不得援引利益否决条款;如果投资者在进入东道国前没有完成询问程序,那么提出利益否决的东道国最晚必须在得知投资者申请仲裁时发出通知。另一方面,明确“通知”的标准。在投资者没有主动询问的情况下,这一标准的设定便显得更加重要。但是,关于“详细、合理的通知”的含义,实践中并没有统一的标准,只能由仲裁庭根据个案作出裁定。“帕拉马公司案”的仲裁庭认为,ECT成员国官方公报上的一个普通声明,或者成员国在相关法律中的明确规定,又或者成员国与投资者在信件往来中的提及等都属于“详细、合理的通知”。笔者认为,我国在签订条约时可以借鉴仲裁庭的某种观点,并且与缔约方协商,选择或创设几种彼此认可并能够合理获得的通知方式。
3.明确并合理分配举证责任。根据国际仲裁规则,举证责任由提出肯定性主张的一方当事人承担,否则将对其作出不利裁决。然而大多数仲裁庭并没有严格执行这一规则,而是要求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彼此协调、互相补充。笔者并不反对仲裁庭这种灵活的处理方式,但这种方式过于随意且有偏袒投资者之嫌。对于东道国而言,举证证明申请人从事的商业行为在规模、价值和重要性等方面都不能满足“实质性”是非常困难的。笔者认为,我国应当在利益否决条款中明确规定举证责任由申请人(投资者)一方承担,但如果利益否决国对相关申请人提供的信息提出异议,则其应提供证据证明其主张。因为私人实体对于自身的所有权、控制权和商业行为的运行状况最了解,也最容易收集资料。这并不会加重申请人的负担,因为这些证据本身也属于公司信息披露的一部分。并且,在仲裁庭倾向于保护投资者的趋势下,将举证责任归于投资者一方,更能体现公平正义原则,更有利于实现投资者与东道国利益的平衡。
注释:
①See Amto(Latvia) v.Ukraine,SCC Case No.70,2005.
②See Rimantas daujotas,Jurisdiction Ratione Personae and Corporate,Nationality i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rbitration-Legitimate Corporate Planning or Abuse of Right? November 2011,p.2,http://papers.ssrn.com/sol3/papers.elm? abstract_id=1955110,2012-06-07.
③(21)(23)See Panayotis M.Protopsaltis,The Challenge of the Barcelona Traction Hypothesis:Barcelona Traction Clauses and Denial of Benefits Clauses in BITs and IIAs,The Journal of World Investment & Trade,Vol.11,No.4,2010.
④See Louka A.Mistelis; Crina Mihaela Baltag,Denial of Benefits and Article 17 of the Energy Charter Treaty,Penn State Law Review,Vol.113,2009.
⑤See P.B.Gann,The U.S.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y Program,21 Stan.J.Int'L.Vol.373,1985,pp.379-380.
⑥(15)(27)See Linda A.Mabry,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and U.S.Technology Policy:Rethinking the Concept of Corporate Nationality,the Georgetown Law Journal,Vol.87,1998-1999.
⑦See J.W.Salacuse,BIT by BIT:The Growth of 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ies and Their Impact of Foreign Investment in Developing Countries,24 Int'l Law,1990.
⑧See Bacelona Traction Light & Power Company Limited(Belgium v.Spain),Judgement of 5 February 1970,ICJ Rep.,1970.
⑨See Norah Gallagher,Wenhua Shah,Chinese Investment Treaties,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9,p.80.
⑩Matthew Skinner,Cameron A.Miles,and Sam Luttrell,Access and Advantage in Investor-State Arbitration:the Law and Practice of Treaty Shopping,Journal of World Energy Law and Business,Vol.3,2010.
(11)See Consortium Limited v.Bulgaria,ICSID Case No.ARB/03/24.
(12)See Petrobart Limited.v.The Kyrgyz Republic,Arbitration Institute of the Stockholm Chamber of Commerce Arb.No.126/2003.
(13)(19)See Yukos Universal Ltd.v.Russian Federation,Interim Award on Jurisdiction and Admissibility,PCA Case No AA 227,30 November 2009.
(14)See Siemens A.G.v.The Argentine Republic,Decision on Jurisdiction,3 August 2004.
(16)See Pan American Energy LLC and BP Argentina Exploration Company v.Argentine Republic,ICSID Case No.ARB/03/13.
(17)See Tokios Tokeles,ICSID(W.Bank) Case No.ARB/02/18.
(18)The Working Group of the International Law Association German Branch Sub-Committee on Investment Law,The Determination of the Nationality of Investors under Investment Treaties,A Preliminary Report,2011,p.61.
(20)See Dominique D'Allaire,The Nationality Rules under the Energy Charter Treaty:Practical Considerations,The Journal of World Investment & Trade,Vol.10,No.1,2009.
(22)See Peter Muchlinski,Federico Ortino and Christoph Schreuer,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aw,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p.77.
(24)See M.Sornarajah,The International Law on Foreign Investment,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p.329.
(25)See Christopher F.Dugan,Don Wallace,Jr.,Noah Rubins,Borzu Sabahi,Investor-State Arbitrati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p.307.
(26)Antoine Martin,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Disputes,Nationality and Corporate Veil:Some Insights from Tokios Tokeles and TSA Spectrum de Argentina,p.7,http://papers.ssrn.com/sol3/papers.cfm? abstract_id=1781768,2012-07-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