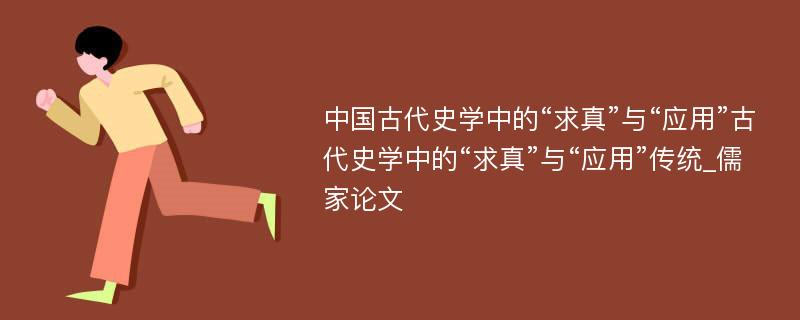
中国古代史学的“求真”与“致用”——1.古代史学的“求真”与“致用”传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学论文,致用论文,中国古代论文,古代论文,传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古代史学在发生与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些值得称道的优良传统。这些优良传统与中国史学独特面目的形成有着直接的关联,同时它们也在推动中国史学进一步发展以及史学发挥社会功能方面起到了重大作用。在这些优良传统中,“求真”与“致用”居于主导地位。
一、“求真”是古代史学的根本要求
追求历史记载的真实,在古代的史学观念中居于相当重要的地位。可以说从人们有意识地进行历史记述之时起,如实地记录历史就成为对史学工作的根本要求。对此,白寿彝先生曾举《左传》庄公二十三年“君举必书。举而不书,后嗣何观?”等例,说明“可从这些引文里看到,直书就是当时史官所应当共同遵守的法度。”并说“在战国以后,直笔的传统一直传下去,成为史学领域里最重要的优良传统之一。(《中国史学史》第1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57、358页)
随着史学在实践中的发展,人们对这一问题有更多的关注,对它的看法也丰富起来。
“求真”从根本上决定了历史记述以至史学的价值。对此,古代史家是有明确认识的。上举《左传》“君举必书。举而不书,后嗣何观”之言可以说明,当时的人们已意识到能否秉笔直书直接关系到史学作用的发挥。刘勰之言:“然史之为任,乃弥纶一代,负海内之责,而嬴是非之尤,秉笔荷担,莫此之劳。……若任情失正,文其殆哉!”(《文心雕龙·史传》)更是从史学的社会责任角度讲明了“失正”会导致史文衰歇的严重后果。基于“求真”关乎史学价值的根本认识,刘知幾把秉笔直书的典型董狐、南史列为史学的最高典范。他说:“史之为务,厥途有三焉。何则?彰善瘅恶,不避强御,若晋之董狐,齐之南史,此其上也。编次勒成,郁为不朽,若鲁之丘明,汉之子长,此其次也。高才博学,名重一时,若周之史佚,楚之倚相,此其下也。”(《史通·辨职》)他的看法在传统史学领域中有广泛的代表性。
对于“求真”的高度重视,致使人们逐渐把它作为衡量史学作品价值的关键尺度。班固在评论司马迁史学成就时,引用刘向和扬雄的话,说他们“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汉书》卷62,《司马迁传赞》)。这段话是史学批评史上著名的权威之论,产生了相当大的历史影响,此后,“实录”事实上成了古代史学稳居前列的“关键词”。
“求真”有两方面的要求:一是著述者有良好的史德,有忠于史实的勇气,甚至可以不惜献出自己的生命;二是对史实的真伪进行技术考察,把真实的历史展示出来。只有史家把主观上对历史真实的追求和客观上对历史事实的严谨考察很好结合起来,才能形成所谓的实录。
事实上,因为当权者干预等复杂的社会原因,历史作品要想达到实录的要求相当困难。而由于避祸与取媚于统治者等的现实制约,与直书对立的曲笔现象是经常出现的。可以说直书传统是无数有胆有识史家以生命和鲜血为代价,在与恶势力的抗争中形成的;是他们在不断抵制曲笔以求全求荣的诱惑中发扬光大的。这方面最值得一提的当然首先是董狐和齐太史及南史氏的事迹。董狐之事请留待下文,先来看看齐太史与南史氏的无畏气概:《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载:当齐大夫崔杼杀齐庄公后,“太史书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杀之,其弟嗣书,而死者二人,其弟又书,乃舍之。南史氏闻太史尽死,执简以往。闻既书矣,乃还。”他们的事迹甚至超出史学领域,成为国人高尚精神气节的典范。唐朝史家吴兢不避权贵的事迹也很感人。在《武后实录》中,吴兢直叙张说诬证魏元忠之事,后来张说为相,“读之,心不善,知兢所为,即从容谬谓曰:‘刘生书魏齐公事,不少假借,奈何?”意思是把事情推到刘知畿身上,而让吴兢曲笔更改这一记载。吴兢回答:“子玄已亡,不可受诬地下,兢实书之,其草故在。”不留情面地把张说顶了回去。张说还不死心,“屡以情蕲改,”吴兢就是不买账,“辞曰:‘徇公之情,何名实录?’卒不改。”以敢于对抗权贵而获得了“世谓今董狐”(《新唐书》卷132,《吴兢列传》)的崇高赞誉。对于正直史家这种高贵品质,刘知幾有一段很让人动情的议论:“盖烈士徇名,壮夫重气,宁为兰摧玉折,不作瓦砾长存。若南董之仗气直书,不避强禦;韦崔之肆情奋笔,无所阿容。虽周身之防有所不足,而遗芳余烈,人到於今称之。”(《史通·直书》)
在技术方面,重视搜罗详尽的史料,考订材料的真实,是有作为史家的一贯作法。这个作法也可追溯到史学初起之时。我们知道中国的史官起源很早,在商周时期就形成了“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礼记·玉藻》)的相对成熟的记注制度。这对保证历史记载的真实性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在儒家经典著作中,我们也可看到有关审慎处理、考辨历史材料的记载。孔子在谈到前代典章制度时,曾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论语·八佾》)这句话由于出自孔子之口,又是较早的无征不信的论述,所以被作为严肃对待历史的范例而广为人们征引。《谷梁传》强调:“《春秋》之义,信以传信,疑以传疑。”(《谷梁传》桓公五年)成为史家处理历史材料的基本原则。此后史家认真搜集、考订史实的例证不胜枚举,直到清代考据学大兴,代表了传统历史考辨的最高水平,把对历史真实的追求带入了一个新的境地。
二、“致用”是古代史学的主要动机
经世致用是中国史学源远流长的传统。在商周时代,把历史作为现实的一面镜子,就是个很明确的观念,《诗经·大雅·荡》中说:“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诗经·大雅·文王》又说:“殷之未丧师,克配上帝,宜鉴于殷,骏命不易。”《尚书》中周公、召公等政治家以夏商历史为鉴的言论在他们为政的议论中占了很大的篇幅,更是为人们所熟知的。召公尝言:“相古先民有夏,天迪从子保;面稽天若,今时既坠厥命。今相有殷,天迪格保;面稽天若,今时既坠厥命。”(《尚书·召诰》)论述要把夏商两代从兴到亡的历史作为周人的借鉴。周公说:“古人有言曰:‘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今惟殷坠厥命,我其可不大监抚于时?”(《尚书·酒诰》)说明以“民”的行为为鉴在周初就已是权威性的古训了,而且这个鉴戒思想包含着对历史深入思考的内容。
较早以历史著述作为工具干预现实,而产生重大历史影响的莫过于孔子修《春秋》。对此,孟子有切实明白的说明:“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孟子·滕文公下》)汉代的司马迁对此有更细致透彻的论述:“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诛死之罪。”(《汉书》卷62,《司马迁传》)《春秋》正因为积极的经世功能而成为儒家最重要的经典。
以史学为经世工具的认识,由历代学人不断加以阐发,越来越丰富也越来越深刻。汉初的贾谊把取鉴于历史作为国家施政的要务看待,他说:“君子为国,观之上古,验之当世,参以人事,察盛衰之理,审权势之宜,去就有序,变化有时,故旷日长久而社稷安矣。”(《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赞》)刘知幾论述史学对于人生和治国都是相当重要的,他说:“史之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有国有家者,其可缺之哉!”(《史通·史官建置》)顾炎武把明史以“致用”作为学者的重要职责,论说:“引古筹今,亦吾儒经世之用。”(《亭林文集》卷4,《与人书八》)章学诚对“致用”之于史学的意义做了总结性的论述:“史学所以经世,固非空言著述也。且如六经,同出于孔子,先儒以为其功莫大于《春秋》,正以切合当时人事耳。后之空言著述者,舍今而求古,舍人事而言性天,则吾不得而知之矣。学者不知斯义,不足言史学也。”(《文史通义·浙东学术》)龚自珍更把史学看作与国家民族命运生死攸关的大事,恺切地提示人们:“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隳人之枋,败人之纲纪,必先去其史;绝人之材,湮塞人之教,必先去其史;夷人之祖宗,必先去其史。”(《古史钩沉论二》)
理论认识的不断深化,推进着这一传统的不断发扬光大。纵观中国史学发展的历史,可以清楚看到历代杰出史家多以《春秋》为榜样,以匡世济民为己任,而用自己的史笔书写下光耀千秋的不朽史著。杜佑著《通典》明确要“征诸人事,将施有政。”(《通典》自序)司马光著《资治通鉴》,专门留意于“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进〈资治通鉴〉表》)者,宋神宗因而命其书名为《资治通鉴》。……都是比较典型的例子。
史学“致用”的功能表现为不同方面。古人大致有:以史为鉴的认识、惩恶劝善的认识、以史蓄德的认识、疏通知远的认识、宣扬功德的认识等,为避文繁,此处就不展开论述了。
三、“求真”与“致用”的关系
“致用”与“求真”用现在的眼光看是一对对立统一的矛盾。大多数情况下他们是统一的,是相得益彰,互相促进的。古人知道,用真实的历史为现实提供有益的借鉴从而产生积极的社会作用,是理想的史学局面,也是优秀史著具有久远生命力的关键所在。因此,史学既要关注社会需要,又要严格对自身的写实要求,这是二而一之事。刘勰之言:“原夫载籍之作也,必贯乎百氏,被之千载,表征盛衰,殷鉴兴废;使一代之制,共日月而长存,王霸之迹,并天地而久大。是以在汉之初,史职为盛,郡国文计,先集太史之府,欲其详悉于体国。必阅石室,启金匮,抽裂帛,检残竹,欲其博练于稽古也。是立义选言,宜依经以树则;劝戒与夺,必附圣以居宗;然后诠评昭整,苛滥不用矣。”(《文心雕龙·史传》)对此论述得是很清楚的。刘知幾的论述:“况史之为务,申以劝诫,树之风声。其有贼臣逆子,浮君乱主,苟直书其事,不掩其瑕,则秽迹彰於一朝,恶名被於千载。”(《史通·直书》)提示的也是二者并重的要求。正因为认识到历史知识有很强的作用于现实的功用;人们才对历史著述格外重视,从而激发起史学创作的极大热情,导致史学成为“显学”,在中国的学术中居于特殊重要的地位。正因为无数史家对“求真”的执着追求,中华民族才创造了世界上罕有其匹的丰富而可信的史学遗产,为人类文明做出了特有的贡献。
当然由于“求真”和“致用”各自有不同的内涵与要求,加上社会需要等复杂因素,它们之间有时也会出现矛盾冲突。对此古人是有认识的,也采取了他们认为适当的处理方式。
从董狐直笔的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对“直”有自己的理解。《左传》宣公二年在记载了赵穿杀灵公之事后,接着写:“太史书曰:‘赵盾弑其君。’以示於朝。宣子曰:‘不然。’对曰:‘子为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讨贼,非子而谁?’宣子曰:‘乌呼!我之怀矣,自诒伊戚。其我之谓矣。’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赵盾,古之良大夫也,为法受恶。惜也,越境乃免。’”董狐写的并不是直接的历史事实,而是在强调赵盾所应承担的历史责任,如果没有后来的解说读者会误认为杀死灵公的人真的是赵盾。可当事人赵盾和后来的评判者孔子以至以后的读者,都认为董狐是在秉笔直书,是书法不隐。显然在这里客观史实与主观认定已出现了一定的间隔。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看到古人对“直”的另一种认识了。《论语·子路》中孔子有一段与叶公的对话,表明了他对“直”两重性的认识。文曰:“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躬者异於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这个“直”与客观事实拉开了更大的距离。在孔子看来,“直”的把握是有限度的,违反了人性的“直”是不足取的。也就是说面对人伦亲缘等必要的社会要求,“直”应当有一定的弹性,应当包含更丰富的内涵。儒家是以人伦为出发点建立起社会结构与运行理论的,在他们看来亲缘关系的松弛会直接导致君臣关系等上下等级制度的不稳定,所以破坏了伦理秩序,就会危及社会的安定。在这个前提下孔子对“直”表述的看法,是有深意的。这是对儒家思想的一个重要理论阐述,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
从史学上贯彻孔子的思想,就产生了适当牺牲客观事实而求得伦理意义上的“直”这样的处理原则。说得直白点就是为了“致用”而让“求真”做出适当让步,也就是说在“求善”与“求真”之间,“求善”是占压倒优势的。典型例子还是孔子创造的。如果说在记述春秋时期历史时,《春秋》的“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春秋公羊传》隐公元年)还包含技术方面考虑的话,那么把“为亲者讳为尊者讳”作为一条重要的原则,体现的就完全是“求真”服从于伦理的政治考虑了。而声言在史书有所隐讳,事实上已与“求真”渐行渐远。近代以来这类所谓的《春秋》笔法为人所诟病,也正是为此。但在古代的思想背景下,这个原则是为人们所认同,并赞赏的。刘知幾在《史通·直书》中说:“肇有人伦,是称家国,父父子子,君君臣臣,亲疏既辨,等差有别。盖‘子为父隐,直在其中’,《论语》之顺也;略外别内,掩恶扬善,《春秋》之义也。自兹已降,率由旧章。史氏有事涉君亲,必言多隐讳,虽直道不足,而名教存焉。”反映这是人们所普遍认可的史学观念,成了人们普遍遵循的史学原则。
对此,我们今天可以有三方面的认识:其一,古人对“直”的内涵与运用有值得注意的深入思考,这对史学理论的丰富是有益的。其二,从积极方面考虑,为了社会准则的贯彻而对史实做适当变通处理,只要运用得当,对于国家、民生的安定和社会的发展是有好处的,因此这个作法是我们可以理解的。其三,在“求真”让步的同时,也为曲笔打开了大门,多少曲笔讳恶之事,可以假此名而行,不良史家也可以由此找到遁词,为自己的秽行开脱,曲笔这一史学浊流泛滥与此不无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