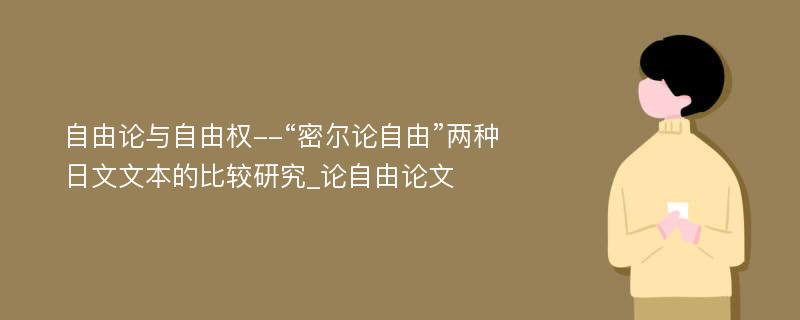
《自由之理》与《自由之权利》——密尔《论自由》两种日文译本的比较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自由论文,日文论文,两种论文,译本论文,之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561.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8862(2010)06-0034-06
约翰·密尔著《论自由》(J.S.Mill,On Liberty,1859)一书在日本的明治时期(1868-1912)曾出版过两种全译本,一是1872年出版的中村正直译本,译名《自由之理》;另一种是1895年出版的高桥正次郎译本,译名《自由之权利》。本文拟围绕这两种译本诞生的时代背景、所传达的思想内涵之间的差距以及两者问世后的各自命运等问题进行比较研究,期望能对我们相关的思考有所助益。
一
密尔《论自由》在日本的首译者中村正直(1832-1891),号敬宇,是日本明治时代前半期重要的启蒙思想家、教育家、作家。中村正直出生在幕府封建统治的末期,自幼学习儒学,后因成绩突出,被选任为幕府儒官。中村正直自1855年前后开始关注英国的学问,1866年以“赴英留学生监管官员”的身份被派往英国,明治维新当年即1868年回到日本。由于当时日本国内旧的封建幕府政权已被推翻,长期驻外的中村正直没能在改朝换代后的明治新政府中得到相应的职位,于是他就在“静冈学问所”这一教育机构中担任教授,并积极参与当时的启蒙运动,成为与福泽谕吉等人齐名的著名启蒙思想家。
在中村正直的译作中,影响最大的有两部。一部译名为《西国立志编》(又名《自助论》)①,另一部就是本文要探讨的《自由之理》。我国近代著名思想家梁启超也曾在1899年撰文称赞过中村正直,可见译者的影响之远之大。②《自由之理》在1872年初版时是线装六册本,1877年开始改为铅字胶装本并多次再版。
密尔《论自由》第二次在日本翻译出版是在首译本问世23年后的1895年。译者高桥正次郎生于1860年,卒于1921年,1895年入赘高桥有三家之后改姓高桥,除去这些信息以外,他的生平履历在目前所查史料中全无记载。密尔《论自由》的这个高桥译本在出版后长期堙没不为学界所知,到20世纪70年代末期,该书才开始重新受到关注。③
二
密尔在《论自由》中要讨论的问题是,通过推翻专制政府等手段使得政府与人民之间的对立问题获得一定程度的解决,以及在民主社会这一新的历史条件下个人的自由问题。他认为,在政治权力之外,还存在着社会性权力,个人也必须要摆脱这种社会性权力的控制而获得自由。密尔在《论自由》“引论”中开宗明义地表述了这一基本观点。他说:
The subject of this essay is not the so-called liberty of the will,so unfortunately opposed to the misnamed doctrine of philosophical necessity; but civil,or social liberty:the nature and limits of the power which can be legitimately exercised by society over the individual.A question seldom stated,and hardly ever discussed in general terms,but which profoundly influences the practical controversies of the age by its latent presence,and is likely soon to make itself recognized as the vital question of the future.It is so far from being new that,in a certain sense,it has divided mankind almost from the remotest ages but in the stage of progress into which the more civilized portions of the species have now entered,it presents itself under new conditions and requires a different and more fundamental treatment.④
密尔在这里明确提出,他写作本书的主旨不是要讨论“意志自由”(liberty of the will)问题,而是要论述“市民的自由”(civil liberty)和“社会自由”(social liberty)的问题。
省略第一句,中村正直《自由之理》对密尔这段开场白的译文是:
此书论述人民的自由即人伦交际上的自由。要阐明的是,同伙组织即政府能够对各个之人所实施的权势的本质及其限界。对自由问题的公开性讨论古未有之,人世间的实际情况是,政府与人民之间为得到它而进行的争斗自古以来却早已在暗中存在。世道开化至今,此事愈加显然,自由之状况亦生出了新的变化,现在必须要讲明此道理之原由。⑤
由这段译文可见,第一,译者没有把密尔《论自由》所针对的那个时代的社会发展特点——资产阶级在夺取政权方面已获得一定胜利这一点正确地传达出来,依然把“政府与人民”的对立日益加重的问题当成是《论自由》的中心议题。因此,第二,该译文没能展现原著的基本特征及其深远意义所在,即著者要探讨的是作为“社会”与“个人”关系问题的自由问题。
中村《自由之理》在译文中把civil译为“人民”、society译为“政府”,individual虽在译文的前半部分中暂时被译成“各个之人”,但在译文的后半部分还是透露出译者对原著理解的真实结果——把社会与个人的问题当成了“政府与人民之间”的问题。
高桥《自由之权利》对相应内容的翻译是:
斯论趣旨在于“民权”即“社交性自由”,在于社会对于个人所能正当实施的权能的性质及限界。关于这个问题,总体上看,不仅是尚未在世间展开讨论,既便是提及此事的也属稀少。但是,当代的那些现实的纷争就是源于此问题潜在的深刻影响。所以,作为未来的紧迫问题,近期内它将被认识到。自远古之日起,人类社会就因这个问题而遭分裂,所以从某种意义上看它绝不是新问题。然而,现今开化优等的民族到达了人世间的进步阶段,随着这种进步程度的提高,此问题在新境遇下又出现了,所以必须要以一种与过去不同的、更为根本的处置去对待它。(文中“此问题在新境遇下”等等以下的部分暗指,昔时因是政府与臣民间的问题,故而要做的事只是限制政府之权能;但今天是多数党与个人之间的问题,故而不能只限制政府之权能却不限制舆论之权能。“新的境遇”暗指政府与舆论,“根本的处置”暗指限制政府之权能和限制舆论之权能。——译者)
高桥此译文中特别值得重视的是译文的后半部分和括号中译者的译注。由此可知,译者不仅正确理解了密尔所论的意义,更是在有意识地纠正前辈中村译文中的谬误之处,最关键的改正就是将“政府与人民”译为“社会与个人”。
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如“how to make the fitting adjustment between individual independence and social control”一句,《自由之理》将其译为“应如何处置人民自主之权和政府管辖之权,才能获得两者的和谐恰当?”在高桥《自由之权利》中,此处被改译成“应如何在个人之独立与社会之管辖之间建立恰当的平衡?”再如,《论自由》第四章的标题是“Of the Limits to the Authority of Society over the Individual”,《自由之理》将其译为“论同伙会所即政府向人民之各个人施行权势的限界”,高桥的翻译是“论社会针对个人的权能”。可见,高桥在翻译“社会”和“个人”这两个概念时使用的译词是完全统一的。
相比之下,《自由之理》译者中村正直对密尔所论“社会”与“个人”的概念内涵理解困难,导致他在选择对应的译词时常举棋不定,对同一个词语的翻译,出现了多个不同的词汇,甚至在一些关键性的语境中出现了重大误译。与society对应的译词就出现过“同伙组织”、“同伙会所”、“人民会所”等几种,尤其是常用加标注的形式说明该词语的意义等同于“政府”;而与society相对的individual则以极高的频率被混同于“人民”。⑥
三
造成上述两种译文明显不同的原因是什么,研究者们已有过一些分析⑦,但两位译者对原著的理解程度的不同应是造成译文内容存在重大差距的首要原因。
中村正直曾在英国受洗,是一名基督徒。他在《自由之理·序》中交代了自己的译书动机:“凡事不可无限界,唯爱不可有限量。……此书论政府之权当有限界,明白详备。故余别举当无限量者言之。夫爱不可有限量。”整篇序文的内容都在宣扬“上帝之爱”的无限永恒性。中村正直从一开始就把密尔《论自由》看成是一部详细论述“政府之权当有限界”的书,他的理解与原著要论述“市民的自由”和“社会自由”问题的主旨差距很大。
然而,《自由之权利》的译者高桥正次郎则不同,他在该书“自序”(注明的写作时间是1895年10月)中写道:
本世纪中期,在英吉利,代议制度渐达善美之域,立法行政司法之权已确立,政府与国会蔑视人权、轻视自由之举已很稀少。然而,前门逐虎后门来狼,舆论的制裁又现弊端,它们专横跋扈、动辄束缚制裁个人的言论和个人性行为。而在个人这方面,又有人以自由为名,放纵自恣,怠于自身义务,也有人侵害他人权利。或许是鉴于此种状况,密尔氏慨然而起,著成此书,欲在道德上倡导正确之原理,阐明社会与个人之分限,使社会知其所向,个人悟其所守。不仅是个人无侵害他人权利之权,舆论、国会、政府也同样无此权。若个人或舆论或国会或政府动用有形之强迫或无形之制裁妨害或中止解散人民之演说,或是禁止关停报纸著述等,或者钳制人民的个人性行为,这就不单是属于立宪性质的举动,也是不道德之所为。
在这里,译者将密尔《论自由》诞生的社会历史背景和著者意图概括得非常精确,反映出他对原著的理解程度远远超出了20余年前的首译者中村正直。
同是一部密尔的《论自由》,为什么两位译者对原著的理解程度却相差甚远?造成这种差异的因素当然不是单方面的,但促成重大变化的最为直接和根本的因素只能是二人所处的时代发生了剧变。
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取得成功,致使维持了近三百年之久的幕藩体制崩溃。这成为日本资本主义以及近代天皇制国家形成的起点。但这仅仅是一个起点,这个以天皇为中心的统一国家虽然业已形成,但实际的政治领导层是由“讨幕派”的藩阀官僚组成的,其作为专制政府的本质并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所以,这个中央政权虽然在富国强兵、对抗西方列强的旗号下短时间内实行了征兵令、学制改革、地租改正、殖产兴业等一系列新政,但却遭到了地方及下层民众的反对。那些被剥夺了特权的士族贵族阶层也心存不满,最终导致“西南战争”的爆发。
在明治新政权面临重重危机的情况下,到了1870年代的中期,“自由民权”运动在日本各地兴起。起初,运动的核心阶层是那些对新政府怀有不满的士族贵族阶层,但随着地租改革的推进,强调农民利益的豪农阶层也加入进来并日趋活跃。“自由民权”运动得到这些支持后逐渐扩展升温,发展成为全国性政治运动。1880年,结社组织“爱国社”改称“国会期成同盟”,发动了全国性签名请愿活动,最终得到20万人的签名支持。民权运动者们向当时的明治政府提出的最主要的要求就是:制定宪法、开设议会。与此同时,民间的“私拟宪法”不断公开发表在各类刊物上。⑧
为应对上述全国性运动,明治政府发布“报纸条例”、“集会条例”等法令,要镇压这些活动。但随着运动规模的扩大和国民气势高涨,政府最终不得不于1881年向全社会公开承诺要开设国会。同年,又宣布要颁行钦定宪法,同时确定了该宪法的天皇中心主义的基本方针。随后,明治政府派人赴欧洲考察宪法。
中村正直赴英国任留学生监管官员时,正是明治维新取得胜利的前两年,是幕府封建专制政权最后的也是最黑暗的时期,如何解决政府与人民之间对立的问题是当时政界内外人士共同面对的历史性课题。他在明治维新导致政府更替的同年归国,他所见到的现实是,维新前的课题在维新成功之后依然存在,政府与民众间的对立甚至有加剧的表现。在这种独特的历史背景下,中村正直对《论自由》的理解和翻译在最基本的问题上出现了偏差。
高桥正次郎翻译《自由之权利》时,日本社会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巨大变化,高桥在该书“自序”中对当时的社会状况和他本人的心情做了较为全面的描述。他写道:
我邦既已在数年前定立宪法开设国会,今日又成为了东洋第一强国,能够与世界文明国并驾齐驱。这样一来,道德就会取得显著进步,是否就不必担心个人以自由为名,怠于自身义务、侵害他人权利的行为,舆论也不制裁个人的言论及其个人性行为等弊端,不必担心议会与政府蔑视人权轻视自由了呢?然而,在今日如此状况下,如果再喋喋不休地讲述自由主义,那就像白昼点灯,颇有不合拍之嫌。常言说,病愈时祸忽生,居安思危,不忘乱世,此为忧国者之心,胜利者不收盔甲,此为谨慎者的行为。遂公开此书,以自警并求教于大家。对于会遭“过时”之讥讽,本人已做好准备。
在高桥正次郎看来,当时的日本已经自5年前开始实施《大日本帝国宪法》,国会也已设立,专制政治已经得到遏制。而1895年日本在中日甲午战争中获胜的事实更被认为是这些政治改革的直接成果。从外表看,日本已经“成为了东洋第一强国”,侪身于世界文明国家之列。高桥要强调的是,越是在这种时候,越是需要重温《论自由》的思想。这种坚定的信念正是来源于上述他对密尔思想的正确理解和强烈共鸣。因此,他以重译《论自由》的方式重新提出“密尔课题”并试图通过正确传达原著精神来提醒当时的日本社会。从后来的发展情况可知,高桥的这一目标只能算是部分地实现了。他更正了原有的中村译本中的误译,推出了一种更为接近原著的新译本,这是高桥的成功;然而,遗憾的是,新译本《自由之权利》并未在当时和以后的日本学界、言论界受到关注,更没有发挥出译者所期待的社会作用。
四
《自由之理》和《西国立志编》、《代议政体论》(密尔著,永峰秀树译,中译名《代议政治论》)等翻译书籍一起,在当时受到追求自由解放的进步青年知识分子的热烈拥戴,其影响波及全日本的各个阶层。尤其是在蓬勃于1870年代中期以后的全国性政治运动“自由民权运动”中,这些书籍被公认为发挥过精神导师的作用。之所以能发挥如此巨大的作用,主要是因为,一方面,《自由之理》等书中宣扬的反对专制政府、在政治上争取人民权利的思想理论满足了民权运动组织者和参与者的理论需求;另一方面,读者将书中所传达出的思想奉为经典,用以激励自己的行动,起到了鼓动人民与政府进行斗争的作用。地方行政长官河野广中(磐州)读了中村正直译《自由之理》后,“一夜间思想起了大革命”,毅然转变思想,从一个“攘夷”运动家转身变为一个“自由民权运动家”。⑨ 像这样的典型事例在当时有很多。
在自由民权运动日益兴盛之时,福泽谕吉在他1879年写成的《通俗民权论》第二编中指出:
“民权”之“民”字解作“人民”之义,人民与政府对立之时,其关系在人类社会中最为重大,首先就惹人耳目,所以,(民权运动)因其名称显赫于世。
福泽谕吉清醒地看到,“民权”受人关注的原因就在于,这一概念指称的是作为与政府对抗的“人民”这一集团整体的权利。福泽谕吉虽然在他的论著中不断强调即便是在“人民”这一集团的内部,“人权”(福泽也称之为“私权”)的重要性也不容忽视,但他的声音只是少数派,影响力非常有限。有的研究者把这种将“民权”看做“人民”整体之权利的倾向称为“集体实在论”倾向的一种表现形式。所谓的“集体实在论”即是一种轻视集体是由个人组成的这一方面,把“集体”看做是超越于个人之上的、如同有机体一般的整体而实际存在之物的观点。这种观点导致的错误是:集体内部的表决程序被简化甚至忽视,使人感到“集体意见”似乎是作为一种整体性观点理所当然地实际存在着,而不是通过一定的程序逐步形成的。⑩ 前述高桥译文把中村译文中的“人民”全部改回“个人”,是十分重要的贡献,如果能切实贯彻这一立场的话,日本或许能够在那以后的历史中避免这种“集体实在论”倾向所造成的灾难。
自由民权运动重要的直接成果之一是《大日本帝国宪法》的颁布实施。1888年,参照德国君主制宪法(普鲁士宪法)起草的《大日本帝国宪法》在枢密院批准通过。这部宪法因发布于明治22年(1889)又被称为“明治宪法”,它是日本第一部现代意义上的宪法,于1890年11月开始实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它是日本的国家基本法。1947年5月3日新宪法实施之日起废止。
明治政府选择普鲁士宪法作为宪法的范本,是因为该宪法容许君主拥有很大的权限,这正可以满足明治政府一方面不能无视民众的民主呼声,同时又希望保障天皇的主权地位的需求。明治宪法并非民定宪法,而是以君主(即天皇)授予国民的形式成立的,是一部钦定宪法。
明治宪法规定了上下两院制、责任内阁制、司法权的独立、臣民的权利义务等内容,从形式上看,这是一部体例合格的现代宪法。
但是,明治宪法同时规定,以神圣不可侵犯的天皇总揽统治权的天皇主权是本宪法的基本原则,在国会之外尚设有枢密院、贵族院等特权性机构,大臣也要由天皇任命并对天皇负责,这些规定都使得议会制的功能受到了制约。通过规定“臣民的权利”达到了运用法律手段限制民众的权利的目的,还广泛保留了“独立命令”、“紧急敕令”、“非常大权”等不需要经过议会批准的立法手段——“天皇大权”。同时,军队直属天皇,被置于内阁的统辖之外(即统帅权的独立)。
这部深具钦定宪法性质的《大日本帝国宪法》的思想本质即是,国民的各项权利均来自国家的主权者天皇的恩赐,没有体现“人权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不可侵犯的永久性权利”这一启蒙精神。因此,在宪法中的规定是,国民是“天皇的臣民”,是天皇的附属物。所以,明治宪法中列出的受到保障的臣民权利范围,现在看来很少而狭隘。而且,从那以后的历史看,这些权利还有可能依据后来由帝国议会制定的法律被限制、否定。如在《大日本帝国宪法》中虽然规定了居住、迁移的自由、信函的保密、信教自由、言论自由、集会结社自由等自由权,但后来这些自由有很多被帝国议会制定的法律法规限制或取消。1925年出台的《治安维持法》就是这类恶法的典型,它以要对否定天皇制和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者”进行管制为借口,对全体国民进行思想上的控制,封杀对政府的不满言论。在此之前的1900年,明治政府曾出台《治安警察法》,宣布禁止结社自由;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1938年实施的《国家总动员法》也是同样性质的法规,即对那些已经写入宪法、受宪法保护的人权加以限制。如前所述,早在1895年,高桥正次郎翻译的《自由之权利》就已经问世,可见他在书中提出的警示并未能在现实政治中发挥实际功效。
注释:
① 此书原名Self-help,作者Samuel Smiles,我国在1911年前曾在上海出版过由日文本译出的该书,译名为《论邦国与人民之自助》。最近的中译本名为《自己拯救自己》,北京燕山出版社,1999,刘曙光等由该书英文本直接译出。
② 梁启超曾说“日本中村正直者,维新之大儒也。尝译英国斯迈尔氏所著书,名曰《西国立志编》,又名为《自助论》。其振国民志气,使日本青年人人有自立自重之志气,功不在吉田、西乡下矣。”(《梁启超全集》,北京出版社,1999,第344-345页)这里的“吉田”、“西乡”分别指吉田松荫和西乡隆盛,在日本推翻封建幕府统治、促成明治维新的过程中,二人均被视为功勋卓著的政治家、思想家和军事家。
③ 冈田与好:《自由经济的思想》,东京大学出版会,1979。
④ John Stuart Mill,On Liberty Penguin Classics,p.59.作为参照,列出一种现代汉语译文:“这篇论文的主题不是所谓意志自由,不是这个与那被误称为哲学必然性的教义不幸相反的东西。这里所要讨论的乃是公民自由或称社会自由,也就是要探讨社会所能合法施用于个人的权力的性质和限度。这个问题,很少有人用一般性的说法予以提出,更从来没有人用一般性的说法加以讨论,但是它却在暗中深刻地影响着当代一些实践方面的争论,并且看来不久就会被公认为将来的重大问题。它远非什么新的问题,从某种意义说,它几乎从最远的年代以来就在划分着人类;不过到了人类中比较文明的一部分现在已经进入的进步阶段,它又在新的情况下呈现出来,要求人们给以一种与前不同而且较为根本的处理。”(许宝骙译《论自由》,商务印书馆,2005,第1页。)
⑤ 龚颖译自日文原文。翻译时尽量保存了当时的日文汉字词。下同。
⑥ 松泽弘阳:《〈西国立志编〉与〈自由之理〉的世界》,日本政治学会编:《日本的西欧政治思想》,岩波书店,1975。
⑦ 例如,语言学家森冈健二在《〈自由之理〉的译词——与英华词典的关系研究》(《日本文学》第18号,1962)中指出,中村正直翻译《自由之理》时,其中的译词有很多来源于当时在中国出版的《英华字典》。但我认为,由前述可知,如在《论自由》最初段中的“civil”在《自由之理》中被译为“人民的”,但在《英华字典》中,“civil”的对译词是“民、民的”,“individual”在《自由之理》中除去极少被译为“各个之人”之外,常被混同于“人民”,而《英华字典》中该词语的对译词是“独一个人、独一者”,“society”在《英华字典》中的译词是“会、结社”,不是中村译文中出现过的“同伙组织”、“同伙会所”、“人民会所”等。特别是将“society”等同于“政府”的译法,《英华字典》中是不存在的。因此,《自由之理》的译词受当时中国出版的“英华词典”类书的影响很有限,两者之间的关系问题尚需进一步探讨。
⑧ “私拟宪法”即民间人士从自己的立场观点出发在各类刊物上发表的各种“宪法草案”。如1880年发表的由东京五日市的千叶卓三郎等农村青年写成的《五日市宪法》、1881年植木枝盛(1857-1892)的《日本国国宪案》等。植木枝盛拟订的《日本国国宪案》中明确规定了权利、自由等的详细内容以及抵抗权等,后人评论这份草案中有与现代相通的民主性内容。现已发现的这类“草案”已达40余种。
⑨ 《河野广中(磐州)传》上卷,河野盘州传刊行会,1923。
⑩ 《基本人权》,东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编,东京大学出版会,1968,第18页。
